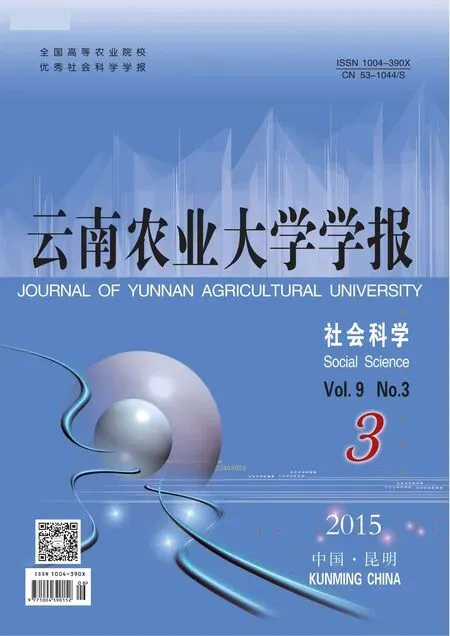语言选择与文化身份:再论苏珊娜·穆迪《丛林中的艰苦岁月》
语言选择与文化身份:再论苏珊娜·穆迪《丛林中的艰苦岁月》
李娟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苏珊娜·穆迪是早期加拿大英语文学中很有影响力的女作家,其重要作品《丛林中的艰苦岁月》记录了她早期移民加拿大时的生活状况。作者对于语言字词的选择修饰以及对于英国和加拿大的评论,其中暗含着她在文化身份上的边缘性。进入当代,苏珊娜·穆迪与她的作品又作为写作素材被新一代加拿大作家加以吸收与利用,成为加拿大人集体意识的象征。通过对这一个案的考察,可以看出文化身份是研究加拿大英语文学的重要问题,以及早期移民文学对于加拿大当代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苏珊娜·穆迪;丛林中的艰苦岁月;移民;文化身份;语言
DOI:10.3969/j.issn.1004-390X(s).2015.03.021
中图分类号:I 106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2014-11-08修回日期:2014-12-08网络出版时间:2015-06-0220:22
基金项目:云财教2010年288#助学成才100万子项目(A3007337); 2014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云南的近代化:科技进步与制度变革”阶段性成果(2014Z084)。
作者简介:车辚(1969—),男,云南昆明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学、经济技术史研究。
Language Selec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A Interpretation ofRoughingItintheBush
LI Juan
(School of Humaniti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Susanna Moodie is a writer of early Cana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and Roughing It in the Bush is her important work recording her life experience as an immigrant. Marginality of her cultural identity can be reflected in her choosing of the words in Roughing It in the Bush and commenting of England and Canada.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Susanna Moodie and her story were regarded as writing materials of Canadian writers and became the symbol of th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in Canadian literature. It can be found from this case study that the issue of cultural identity is important to the study of Cana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and how Canadian immigrant literature has an giant effect on contemporary works.
Keywords:Susanna Moodie; Roughing It in the Bush; immigrate; cultural identity; language
苏珊娜·穆迪(Susanna Moodie,1803-1885)是早期加拿大移民女作家,代表作品有《丛林中的艰苦岁月》(RoughingItintheBush,1852)等。在加拿大英语文学中,穆迪不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她和她的作品后来还成为当代作家吸取灵感的源泉。本文将借助于穆迪在写作中微妙呈现的对语言的选择与风格的塑造来分析其文学创作中反映的文化身份问题,以及这一问题又如何在当代加拿大作家笔下得以重新理解和诠释。
一、从这里到那里:苏珊娜·穆迪的移民生活
苏珊娜·穆迪出生在英国,在移民加拿大之前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浸淫在英国文化之中成长起来的英国淑女。父亲托马斯·斯特里克兰学识渊博,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文学素养。1832年,穆迪夫妇移民加拿大。同年,姐姐凯瑟琳一家以及哥哥一家都移民加拿大。穆迪夫妇到加拿大后,在彼得伯勒以北的丛林中度过了七年时光。1840年,苏珊娜·穆迪的丈夫被委任为维多利亚地区的治安长官,遂迁往贝尔维尔镇,从此结束了拓荒生活。1839年到1951年间,她是蒙特利尔《文学花环》杂志(LiteraryGarland)的主要撰稿人,写下了大量诗文。《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一开始就是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这本杂志上。1847年到1848年间她还和丈夫一起共同主编了当地的《维多利亚杂志》(VictoriaMagazine),刊物的宗旨是向当地读者灌输英国的礼仪风尚,提高他们的素质。拓荒生活成了苏珊娜·穆迪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1852年到1854年间,她的三部以在加拿大的经历为题材的长篇作品即《丛林中的艰苦岁月》、《拓荒生活》(Lifeintheclearyngs, 1853)和《弗洛拉·林赛》(FloraLyndsay, 1854)问世。[1]需要强调的是,《丛林中的艰苦岁月》最初出版于英国伦敦,却直到1871年才在加拿大出版,1962年又经过重新删改后再版,这与当时加拿大文化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关联。
苏珊娜·穆迪的作品在加拿大文学史上一般被归入移民记事作品,是对加拿大移民生活的生动记述。“一八六七年之前,并不存在加拿大这个国家,而是仅有一些边远哨所和几块殖民地。这些地方相去甚远,人们依依不舍地离开帝国各大都会前来落户,这一切都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留下了印记。……这个时期占主要地位的文学形式大致都可归入报道类,包括日志、信件、编年纪事、文献记录,凡此种种都是身处文明边缘的人们向本国权威人士汇报的印象和感想。”[2]早期来到加拿大的移民大多是由于环境所迫,出于经济、政治或者个人心理上的原因来到这里。他们更多地将这看做一种文化上的流亡,因此很难对于这片新的土地产生认同感,对于故国有着明显的依恋之情。苏珊娜·穆迪在《丛林中的艰苦岁月》第一版作者序中表示:“在多数情况下,移民是环境所迫,而非自愿选择。尤其对有相当社会背景的人来说,或者对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来说,移居他国更是不得已之事。对习惯了欧洲社会高雅和优裕生活的人来说,除非迫于当务之急,是很少有人会自愿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而远走他乡,置身在故国悠久传统的呵护之外。”[1]移民之初,在穆迪笔下这种“迫不得已”的情绪不时有所显露。一方面,她在生活上需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她在心理上也需要克服种种难题,过去在英国受到的良好教育与优雅的生活方式在这片荒蛮之地似乎失去了用武之地,她念念不忘故国的“文明”,同时又不得不打起精神来应对既成事实的环境变化。她的生活从大英帝国的“这里”转移到了加拿大的“那里”,这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转移,更是文化空间的变化。
二、乡土与文雅:语言风格的选择
苏珊娜·穆迪力图以一种她自认为客观的态度来讲述丛林生活,因此她在这部作品的最后部分才会表示:“读者们,我无意于继续讲述我们的故事来烦扰你们。我为你们讲述了加拿大丛林生活的真实画面,任你自己从中得到结论。”[1]然而,如果认真考察,我们会发觉作品中隐藏着不易觉察的文化立场,下文将从苏珊娜·穆迪写作出版《丛林中的艰苦岁月》时对语言风格的调整和言辞的删改来加以论述。
苏珊娜·穆迪的姐姐凯瑟琳·帕尔·特雷尔(Catharine Parr Traill)也是加拿大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写有《加拿大的丛林地区》(TheBackwoodsofCanada)等作品。但凯瑟琳写作风格比她显得质朴,善于记录当地的方言,相比之下,她“更醉心于高雅的文学,力图运用修饰语使作品更有说服力”[2]。在贯穿19世纪30年代到19世纪末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女性的写作风格都偏于典雅浪漫。开始创作之初,苏珊娜·穆迪的写作无论从题材还是风格上都体现出这一时期的类似特征。在移民加拿大之前,她已经是一名相对成熟的写作者,早在1822年她20岁之前就出版了第一本书《斯巴达克斯:一则浪漫故事》(Spartacus:ARomanticStory)[3]。在后来的写作中,她在艺术风格上的追求始终没有太大变化。在《丛林中的艰苦岁月》开头,她对加拿大景色的描写不可谓不壮丽:“当那些云雾从灰色的光秃秃的山顶悬崖上袅袅卷起,在围绕着山岭周围宽阔的林带上投下浓密的阴影时,山岭便像巨人一样隐隐地呈现出来——它们是大地上的泰坦,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粗狂与威严的美——一阵惊奇与喜悦充满了我的心头。”[1]其中使用的词汇、典故如“袅袅卷起”(rolled away)、“隐隐呈现”(loomed out)、“大地上的提坦”(Titans of the earth)[3]等十分优美文雅,显示出她善于使用“一套套的词汇”[2]。在这些看似生动优美的描绘中,她所感受到的是自然的震慑力与美,是还未受到“文明”(civilisation)影响的原始世界的震慑力与美。在不经意间,原始荒蛮与文明开化成为她审视眼前景色的一个参照系,“在更为遥远的地方,那儿的森林从未响起过樵夫的斧子声,也从未留下文明的印记,初次接近这样的地方唤起一种令人沉思的敬畏,其强烈程度达到令人痛苦的地步。”[1]在这些描写中,“从未回响起过樵夫的斧子声”(has never echoed to the woodman′s axe),“令人沉思的敬畏”(a melancholy awe)[3]等措辞明显带有维多利亚时期淑女写作的痕迹,借助于优美的语言对自然进行的描摹与由此激发的感悟不是来自于置身其间劳作期间的生活,而是来自文明世界的人对于原始自然的“文化凝视”。
如上文所述,《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一开始是在《文学花环》杂志上片断连载的,最后才在伦敦结集出版。成书出版之前,苏珊娜·穆迪重新进行了文字加工。学者迈克尔·彼得曼把最初的连载与修订出版的文本比较,发现修订后的文稿中更换了不少原先的题材、颇具地方风味的词语,“用一些法语、拉丁语词源的词去取代原来的盎格鲁-撒克逊词,从而使文体变得正式而优雅”,并且删去了外科手术、婚姻生活等生活细节的描述,还增添了一系列委婉语、《圣经》典故,等等。具体的细节对照可参见表1。[2]

表1 “丛林中的艰苦岁月”连载文本与
从这些修改可以看出,除了避讳个人隐私的细节删改,最重要的改动是言辞上的替换,原文中那些平实甚至稍显粗陋的词语都被苏珊娜·穆迪替换成了更文雅的词语。例如,“脸”(face)、“肚皮”(belly)等词语显得直接质朴,换成“面容”(countenance)、“腹部”(stomach)无疑就得体正式多了,如说这是“为了保护阅读该书的英国女读者那种维多利亚时期的敏感性”[4],那么将“印第安人”(Indian)置换为“野人”(the wild man),更是拉开了自己与当地土著居民的距离,是以英国文明社会的眼光来看待加拿大土著,显现出作者在文化上的优越感。无可否认的是,《丛林中的艰苦岁月》里仍然保留了一些“乡野”言辞,但这类措辞是为了增加作品的“异域色彩”,有利于显示作者在异乡环境中所承受的种种不便。也就是说,这些少量的“乡野”言辞只是苏珊娜·穆迪的写作策略,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凸显了她英国淑女的文明身份。
从本质上看,语言和文化密切相关,是构成文化身份认同的基本要素。语言不仅是信息交流的载体,同时也是体现文化身份的特征之一,选择使用什么样的字词会影响到创作风格,也体现出作者的写作理念与文化选择。穆迪与丈夫一起主编《维多利亚杂志》就是为了传播英国的礼仪风尚,希望这份刊物起到文明教化的作用。在写作中,由于她“更严格地遵循她所赞赏的文艺形式,因而也就更背离殖民地的乡土话,于是她的描写就显示出她与她引为乡土的地区之间的疏远”[2]。因此,这部作品呈现出来的特点就是题材上表现拓荒生活的“域外性”与叙述语言上的文雅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实际上也显露了她固守的文化身份——大英帝国的淑女身份,虽然在加拿大生活的后期她越来越适应粗糙的生活,身上具有了加拿大人特有的荒野气质。
对苏珊娜·穆迪而言,一边是“可爱的英伦,为什么我非要弃你而去?我崇拜你,但我究竟干了什么可耻的错事,使我必须离开你神圣的心胸,落落寡欢独处异国他乡”,而另一边是“加拿大,你是伟大、自由、蒸蒸日上的国家,——是文明世界弃儿的再生父母。你脱胎于不列颠,你定会伟大,我将依恋着你,你是收养我的国家,是我世代生息的国度,对于一个母亲而言,更加珍贵的是你是我子孙长眠的国度”[1]。两者之间的角力一直是隐含在她作品中的主题,虽然她力图客观地记录移民生活,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情感却显现出内心的波动与复杂。在她看来,“这片殖民地”的生活“平凡而乏味”[1],莽莽丛林与恶劣的气候更容易让人怀念英国的“文明社会”,她也始终强调自己与英国的精神联系,将英国文化作为精神的根基。她远离文化母体在此地安家,移民加拿大是一个离开“家园”的过程,通过写作她与母国保持了文化上的关系。她书写的是“这里”的故事,面对的却是在“那里”的英国读者,固守的是高雅的“那里”的文化身份。
严格说来,《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体裁杂糅,类似于各种人物描写、奇闻异事、诗歌小说的大拼盘,在艺术上不能说精湛,但“还是成功地展现了一幅极其引人的描绘紧张心理的图画,这种紧张心理必定是她那个时期的许多移民身上的一大特征”[5]。作品描写的是作者本人的移民经验,其中透露出她在移民之初的不舍与憧憬,移民之后因文化隔膜感受到的痛苦以及既此又彼的身份,其中包含了“她明确表达的信息和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深意之间的差距”,也包含了“穆迪夫人认为她应该具有的思想情感和她实际的思想情感之间的冲突”[6]。从文化层面上来看,这部作品的意义与其说为读者提供了丰富有趣的阅读素材,倒不如说她呈现了一种典型的社会心理的紧张结构。存在这种文化夹缝经历的不止苏珊娜·穆迪一人,但她移民作家的身份让她有机会将其诉诸笔端,一方面成为加拿大边疆地区移民文学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也为后来者理解和阐释她的文化境遇提供了更直接而丰富的素材。
三、从“你们”到“咱们”:文化身份的变化
通过《丛林的艰苦岁月》等作品,苏珊娜·穆迪记录了自己的移民生活,同时也寄托了她对于自我归属的思考。一开始,移民行为产生的流亡感让她将英国文化视为“我”的一方,将移民的新环境视为“他”的一方,称其为“你们”。这在上文中已有详尽论述。然而,从文本中也不难看出,穆迪在积累本地生活经验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正是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信仰与归属”,也开始有信心对读者说“你们将会渐渐爱上加拿大,正如我现在这样”。[1]她既对英国文化充满了怀恋,同时也越来越对加拿大的生活产生认同感,由此逐渐弥合了“自我”与“他者”文化界线。继在英国结集出版之后,1871年《丛林中的艰苦岁月》首次在加拿大出版,这时距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土国成立已有四年。在为这一版新写的序言中,她已经表现出一个定居加拿大的人对“这里”强烈的认同感。这是穆迪个人生活中的情感与认知变化,但同时也体现了社会文化的影响。
1)在梨小食心虫越冬前,树干绑诱虫带,诱集幼虫越冬,冬末解除集中烧毁。春季越冬幼虫化蛹羽化前,刮除树干老翘皮,消灭根颈周围土壤中的越冬代幼虫。
19世纪70年代,加拿大的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虽然仍旧受到英国的影响,但加拿大人已经有了独立身份与独立意识,这种独立意识同样也反映在文学领域。当时的加拿大人亟需在文化上在文学上建构起属于自己的历史,彰显独立的民族身份。正如弗莱指出的,“加拿大可以依凭的创造本土文化特色的唯一东西就是加拿大的写作和加拿大的想象。针对加拿大人的后殖民环境,加拿大人并没有被动地接受,尤其是在文学写作上(这个代表着民族创造力和想象),加拿大人力图创造出自己的神话与文学”[7]。在追溯文学源流、重塑文化身份的过程中,时隔几年之后这本书在加拿大出版时其中那些“英国特质”被不知不觉淡化了,强调的是她移民加拿大之后,作为加拿大人的生活与心理体验。苏珊娜·穆迪本人无疑也在配合这种文化背景的变化,她对加拿大版《丛林中的艰苦岁月》再次进行了删改,去掉了那些“会引起不快的段落”,以免“激怒”加拿大人[3]。总之,是那个时代对于民族独立性以及民族文学独立传统的塑造让苏珊娜·穆迪被吸纳进了加拿大民族作家的队列之中,并成为其中十分典型的代表。她的形象在历史文化与文学史中出现文化身份的转变是内力与外力合作的结果。加拿大文学史家威廉·赫伯特·纽(William H. New)发现:“尤其富于戏剧性的变化是到了一八七一年时,‘咱们’这个代名词已经把苏珊娜吸收进加拿大人的行列中了。因此,我们不仅应将《丛林的艰苦岁月》看作那个时代的记录,还应视为不断变化的时代的不断更新的记录;尽管从语言角度来说它属于过去,但是它还力争改变形式去迎接未来。”[2]他敏锐地指出了苏珊娜·穆迪和她的作品在文学史维度上呼应时代变革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具体表现在后来的一批加拿大当代作家的创作实践中。
进入20世纪,苏珊娜·穆迪的经历成为不少加拿大作家的写作素材。比如加拿大作家罗伯逊·戴维斯(Robertson Davies) 在五十年代时就将苏珊娜·穆迪的事迹写入剧本《我心深处》(AtMyHeart′Core, 1950) 。剧本描写了凯萨林·帕尔·特雷尔、苏珊娜·穆迪和弗兰西斯·斯图尔特这三位加拿大早期女拓荒者的生活片断,着重表现她们内心的争斗,在现实生活与理想生活之间的矛盾和选择。作家让“魔鬼”与她们每个人谈话,借以呈现出当时加拿大移民生活对这些移民者的影响。
如果说戴维斯的剧本再现了苏珊娜·穆迪作为早期移民女性的生活场景与情感矛盾,那么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诗作《苏珊娜·穆迪日记》(TheJournalsofSusannaMoodie,1970)则特别强调了这位移民女性文化身份的建构问题。对于《丛林中的艰苦岁月》,阿特伍德曾入木三分地指出“书中最复杂、最暧昧的人物是穆迪夫人自己”[6]。阿特伍德所说的复杂与暧昧,指的就是苏珊娜·穆迪在英国文化与加拿大文化之间的双重处境与身份困境。阿特伍德本人尤为关注的正是这种复杂与暧昧所体现的文化张力。《丛林中的艰苦岁月》隐约透露或者暧昧表达的文化身份处境,成为阿特伍德重新创作与诠释的灵感来源。只不过不同于原作的是,阿特伍德在表现了穆迪文化选择的困境之后,将这一人物牢牢地确定在“加拿大人”的谱系之中。诗歌中基本没有描写苏珊娜·穆迪在丛林里拓荒的生活,而这本来是苏珊娜·穆迪本人在《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中重点叙述的内容。《苏珊娜·穆迪日记》从第一部分开始到第三部分结束,苏珊娜·穆迪的形象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不断塑造和变形的过程中,生发出多维层面的文化意义,“明显体现出阿特伍德认为的加拿大人生存状态中那种强烈的双重性”[8]。这一形象想要展现的实则是加拿大女性与加拿大文化所处的困境。对于当代读者而言,从阿特伍德的《苏珊娜·穆迪日记》中能瞥见的并不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历史人物,而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也就是说,阿特伍德对于苏珊娜·穆迪这一素材的吸收,并非局限于再现加拿大移民历史,而试图赋予其更为丰富的文化意义。她以充满想象力和隐喻性的文字重新塑造了穆迪的形象,诗歌结尾处的穆迪不再是诗歌第一部分那个与丛林格格不入、需要重新确认自身文化身份的英国淑女和加拿大移民的混合体形象,而成为加拿大人民以“纪念碑”标注的人物,一个“象征性的徽章”,一个代表了加拿大人集体意识的文化符码。
由此可以看出,经过当代作家的吸收与再诠释,那位在加拿大荒蛮丛林中克服艰苦的自然环境努力生存、在优雅的英国文字中寻求归属感的历史中的苏珊娜·穆迪的形象逐渐发生了变形,从“一位深受欧洲文明熏陶的文化女性转变为充满原始与野性的加拿大旷野的精灵”[9],由一位具有他者身份的移民作家转化成为代表加拿大本土文化的标志性人物。
四、结束语
苏珊娜·穆迪以文字记录了早期移民的生活与思想状况,是具有代表性的早期加拿大移民女性作家,其作品在文化层面的意义要大于艺术审美层面上的意义。如上文所述,在她的《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中体现了移民作家文化身份的边缘性以及遭遇的文化身份危机。进入新的时期,当她本人成为当代加拿大作家再创作的素材来源时也为后者提供了文学演绎的新起点,在新的历史背景中重新焕发生机。在这个意义上,穆迪本人以及当代加拿大作家笔下的穆迪形象无疑能够成为理解加拿大人文化身份的典型个案,其中既体现出某一时代移民者文化身份的双重性,也反映出以文学手段再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可能性。在当下的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相信还会出现更多的文学文本,以苏珊娜·穆迪的文学创作为题材继续探索民族文化身份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1](加)苏珊娜·穆迪.丛林中的艰苦岁月[M].冯建文,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249,5,7,45,16.
[3]MOODIE SUSANNA. Roughing it in the Bush or Life in Canada[M].Montreal: Carl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xx,17,18,xlviii.
[4]THURSTON JOHN. The Work of Words:the Writing of Susanna Strickland Moodie[M].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133-166.
[5](加)威·约·基思.加拿大英语文学史[M].耿力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5.
[6](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好奇的追寻[M].牟芳芳,夏燕,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74,78.
[7]江玉琴.理论的想象——诺斯洛普·弗莱的文化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94.
[8]STAINES DAVID. Margaret Atwood in her Canadian Context[C]// HOWELLS, CORAL AN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garet Atwo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7.
[9]傅俊.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研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371.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3.1044.S.20150602.2022.022.html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Journal of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2015,9(3):113-122
http://xb.ynau.edu.cn
ISSN 1004-390X; CN 53-1044/S
E-mail:ynndxbsk@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