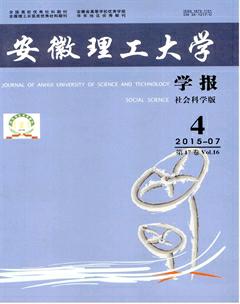论《淮南子》之“奇”
高旭
摘 要:《淮南子》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绝代奇书”,其之所以“奇”,主要表现在作者生平、著述过程、思想内容和流传命运等四个方面。《淮南子》以其博采百家,兼综诸子的开阔气度,不仅历史总结战国以来的黄老道家思想,而且在引庄入黄的基础上,充分实现老、庄、黄的内在的思想沟通和融合,创造性地发展出“淮南黄老道家”的汉代“黄老”新形态。《淮南子》丰富多彩,深刻独到的思想内涵,使其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道家巨著。
关键词:《淮南子》;淮南王;刘安;黄老;淮南黄老道家;百家之学
中图分类号:B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5)04-0001-08
Abstract:Huainanzi is a peculiar piece of work in the Chinese ancient cultural history, the peculiarity of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author's life, the writing process, content, and the spread of fate. Huainanzi openly integrates around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s. In addition to the Huang Lao Taoist thoughts since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t also integrates the thought of Zhuangzi, creatively developes a new form of "Huang Lao" in "Huainan Huang Lao Tao" thoughts in Han Dynasty. Its rich and colorful contents and unique connotations make it a rare great work in the Chinese ancient cultural history.
Key words:Huainanzi; the king of Huainan; Liu An; Huang Lao; Huainan Huang Lao Tao; theory of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s
西汉前期的江淮流域地区,曾产生过一个名闻汉王朝的学术思想中心,即以旧楚故都寿春为中心的淮南王国。当时这里汇聚着来自天下各地的“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1]2145,均为淮南王刘安所延揽和礼遇,这使得淮南王国孕育出有汉以来最具地域特色、影响也最为卓著的淮南学术集团。在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便记载着淮南学术集团的多部重要著作,如:《易》类的《淮南道训》二篇,杂家类的《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诗赋类的《淮南王赋》八十三篇、《淮南群臣赋》四十四篇、《淮南歌诗》四篇,以及天文类的《淮南杂子星》十九卷。此外,《汉书·淮南王传》还提到:“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1]2145,这与《淮南内》、《淮南外》共同构成淮南学术集团的一部宏篇巨作。而以上的学术著述中,又尤以《淮南内》二十一篇最具代表性和知名度,因为此书即是广为后世人们所熟知的《淮南子》。
不论是淮南学术集团的出现,抑或《淮南子》的诞生,都与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密不可分,这就是西汉淮南王刘安。正由于刘安的存在,使原本民风“剽轻”的淮南王国,前所未有地形成较为浓厚的思想文化氛围,一跃成为西汉前期学风弥盛、声名煊赫的区域文化中心,甚至与同时代的吴、梁、楚、河间等诸侯王国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正是这位被后世学者称为“天下奇材”的淮南王刘安,在景、武之际组织门下宾客,精心撰著出“绝代奇书”《淮南子》。在这部彰显汉代黄老思想的道家巨著中,刘安试图以兼收并蓄先秦百家之学为基础,“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2]1462,为西汉王朝的稳定发展和长治久安,探索出一种“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能适时“与世推移”[2]1463的新治国方略。在《淮南子》创作完成后,刘安将其作为重要的政治礼物,在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入朝长安时,献给即位不久的武帝刘彻,而后者则对这部“新出”的奇绝博大之作,甚为“爱秘之”。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如《淮南子》一般,既为王者所撰述,又能为皇帝所看重,并对当时及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论著,实为不多见,故而《淮南子》不可不谓是一代奇书。但如要具体言之,《淮南子》究竟“奇”在何处?在笔者看来,或许可从作者生平、著述过程、思想内容和流传命运等四个方面,得到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一、作者生平之“奇”
《淮南子》一书的成功创作,得益于淮南王刘安的核心的组织作用,同样也得益于淮南宾客们的竭诚努力,但是,这些《淮南子》的作者们,其生平经历却都充满着跌宕起伏的政治患难,最终在西汉前期汉廷与地方诸侯王国的角力中,走向难以避免的悲剧结局,而淮南王刘安的一生,则在最大程度上代表和反映出淮南学术集团的这种历史命运。淮南王刘安的生平有着不同于汉代一般诸侯王的奇特经历,但这种“奇特”并不是积极而美好的,相反,却始终显露出强烈的悲剧色彩,是其家族发展与皇权政治冲突激荡后的现实产物。在某种意义上,淮南王刘安终其一生也未能摆脱皇权政治套在其家族及个人身上的严酷桎梏,最后只能与其父刘长一样,成为皇权政治中权力斗争的失败者和牺牲者,在汉代历史上谱写出两代淮南王皆因“谋反”罪名而败灭的惨烈悲剧。
淮南王刘安的人生悲剧,始于其父刘长,而后者的人生悲剧则又肇源于其母赵姬与汉高祖刘邦之间的萍水姻缘。汉高祖八年(前199年),已经58岁的刘邦从东垣(今河北石家庄市西北)途经赵国。当时的赵王张敖为取悦刘邦,便将自己身边的美人赵姬献给后者,结果赵姬竟因此而孕。由于刘邦对赵王张敖态度恶劣,并不礼遇,致使赵相贯高等人密谋在“柏人”之地(今河北隆尧县西)刺杀刘邦,此事后因刘邦警觉,未能实现。高祖九年(前198年),贯高等人的篡弑行为暴露,刘邦大怒,由此兴起赵国大狱,将赵王张敖、赵相贯高等一干人等逮治收捕,而赵姬也被牵连其中。赵姬虽在狱中告知看守官吏其怀有刘邦骨肉的实情,但因刘邦正在盛怒之时,故此没有对赵姬进行宽赦和照顾。赵姬在生出后来的淮南王刘长后,羞怒自杀,于是为淮南王家族种下悲剧的历史种子。
因其母不幸冤死,幼年的刘长在刘邦的安排下,由吕后抚养。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刘邦在平定异姓淮南王黥布之乱后,将幼子刘长分封为新的淮南王,使其以寿春(今安徽省寿县)为都,镇抚江淮地区。刘长成年之后,不满于其母
的悲惨遭遇,迁怒辟阳侯审食其当时不为其母尽力求情,在文帝三年(前177年)入朝长安之际,以谋请见审氏,“自袖铁椎”将其击杀。这次的复仇行为,震动汉廷,刘长虽然得志于一时,但也造成汉廷的不满和警惕,同时让淮南王一系与审氏后人之间形成难以化解的历史仇怨,为日后淮南王刘安“谋反”案的促成和扩大埋下严重隐患。刘长由于幼年失母,性格“骄蹇”,又因是吕氏之乱后仅存的刘邦二子之一,自以为和文帝“最亲”,所以日常行事比较任性放纵,多有僭越之举,甚至“数不奉法”。刘长在淮南王国期间,更是“益骄恣,不用汉法,出入称警跸,称制,自为法令,拟於天子”[3]3076,这引起汉廷的猜忌警惕,也促使文帝决心借棘蒲侯柴武太子谋反一事,严厉惩戒牵连其中的刘长,将其发配流放于“蜀郡严道邛邮”(今四川荣经县西南)。经此严重的政治打击,刘长内心极度抑郁,最终在流放途中绝食而死。刘长之死,使后来的淮南王刘安也成为无父孤儿,遭遇到与其父相类似的家族悲剧。
文帝十六年(前164年),16岁的刘安被汉廷立为第二代的淮南王,其弟刘勃、刘赐也同时被立为衡山王和庐江王,刘长时期的淮南王国被一分为三。刘安继位之后,一改其父尚武骄恣、僭越有为之风,“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3]3082,十分注意收敛自身言行,以此取容于汉廷。在淮南王国的实际发展中,刘安也“行阴德拊循百姓”,推行有利于淮南民众的政治举措,取得“流誉天下”[3]3082的政治声誉,在当时的诸侯王国中产生一定的影响。
景帝三年(前154年),震惊西汉王朝的“七国之乱”发生,吴王刘濞曾派使者前往淮南王国,试图招诱刘安,使之加入反叛大军之中。刘安其时有所动摇,“欲发兵应之”,但由于淮南国相临机夺取兵权,“因城守,不听王而为汉”[3]3081
,加上汉廷救兵已至,故而淮南王国在“七国之乱”中逃过一劫。事后景帝尽管没有追究淮南王刘安的责任,让“淮南王如故”[3]3082,但实际上已加深对后者的疑忌防范之心。在景帝后期,刘安比较谨慎从事,并无任何有为之举,而是专心于《淮南子》等书的思想文化著述,以此安然无恙。
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41岁的淮南王刘安入朝觐见即位不久的侄子汉武帝,随后献上新近作成的《内篇》,即后世所谓的《淮南鸿烈》或《淮南子》。年轻的武帝对这位“辩博善为文辞”的叔父,礼遇有加,曾让其作《离骚传》,而且“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1]2145,度过双方关系最为融洽和谐的一个时期。刘安此时也对武帝表达臣服颂赞之情,又为其先后献作《颂德》及《长安都国颂》,宣扬汉廷之德。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刘安进谏武帝,劝阻后者出兵征伐闽越。武帝开始对其不满,又因刘安在淮南王国“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形成规模颇大的人才集团,而实际上对其有所猜嫌防范。
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淮南王太子刘迁因与雷被比剑,怒被其误伤,导致雷被惊惧外逃,试图从军出击匈奴,以此避害。淮南王刘安误听太子之言,“斥免”雷被。后雷被逃入长安,向汉廷上书申诉,揭发淮南王刘安父子的不轨行为,由此引发武帝即位以来第一次对淮南王国进行政治整肃,将其“群臣近幸素能使众者”,皆“系诏狱”[3]3090,沉重打击了淮南宾客集团。虽然武帝事后不为己甚,没有废除刘安的王位,仅是削夺其“二县”,以示惩处,但事实上已对刘安形成严重的政治压力,使其内心惶惧。就在这种危险局势中,武帝元朔六年(前123年),刘安之孙,其庶长子刘不害之子刘建,因刘安与王后、王太子皆不以其父“为子兄数”,产生强烈的“怨望”情绪,又因“诸侯皆得分子弟为侯”,而其父刘不害却无缘分侯,因而指使寿春人庄芷赴汉廷告状,自曝“淮南阴事”[3]3088,引起武帝及汉廷公卿的密切重视。也就在淮南王国风雨飘摇之际,辟阳侯审食其之孙审卿借机复仇,“深购淮南事”于其所善丞相公孙弘,推动后者“深穷治其狱”[3]3088,试图将淮南王刘安一系置于死地。刘安这时已失方寸,原本计划与太子刘迁发兵反抗汉廷派来的惩治官员,但计划未遂,于是只好交出太子,让其自首。太子自杀,未死。而身为刘安谋臣“冠首”的伍被此时也向汉廷自首,供出极为不利于刘安的证词。元狩元年(前122年),武帝和汉廷公卿大夫在得到惩治官员的具体汇报后,将“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而且专派“宗正以符节治王”[3]3093-3094,以汉廷和皇族的名义惩治淮南王刘安。在汉廷官员未到之前,刘安为免受辱,于是自刎而死。就此,第二代淮南王终于也以惨烈的人生悲剧落幕。
从刘长到刘安,西汉前期出身皇族的两代淮南王,均未能善终。如果从赵姬算起,到最终同样被诛灭的淮南王太子刘迁,身为汉高祖刘邦的嫡亲后裔,与文、景、武三帝一系关系最为亲近的西汉皇族支系,淮南王家族四代人都是以悲剧人生而告终,这在汉代历史上委实罕见,称之为“奇”,毫不为过。也正由于祖母、父亲的政治悲剧,深刻影响淮南王刘安的内在性格,使其形成浓厚的忧患不安的心理意识,一生之中多次犹豫辗转于是否反抗汉廷的政治抉择,而这种极度缺乏安全感的政治心态,也被其具体反映在《淮南子》一书中。比如:刘安总是高度紧张于“时机”的能否把握,恐惧因“失时”而受制于人,导致不可预测的祸患,因此反复强调:“得在时,不在争”[2]46,“动不失时”[2]49,“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时之反侧,间不容息,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逮”,“非争其先也,而争其得时也”[2]54,等等。
淮南刘安的生平经历是悲剧性的,与之捆绑在一起的淮南宾客们,同样遭遇到极其悲惨的政治命运。如果说元朔五年,因雷被事件,导致淮南宾客集团经历前所未有的政治打击,使其中的才能之士大都被“系诏狱”,沦为阶下之囚,那么元狩元年的“淮南大狱”,对劫余之后的淮南宾客集团而言,更是毁灭性的。这一次无人再能幸免,宾客们大都陷入族灭之惨境,因此案“坐死者数万人”[3]1424。可以说,淮南王刘安与其宾客,在《淮南子》中深层次表达出的政治忧患意识,最终成为历史谶言。
任何一部思想著作,如果其承载着撰著者如此奇特而惨烈的悲剧人生,那么就注定这绝不是一部平凡之作,而是充满历史的沉重,引人深思,发人慨叹。无怪乎现代著名学者徐复观先生在其《〈淮南子〉与刘安的时代》一文的最后,由衷而言:“当我在写的过程中,渐渐发现了那一批以大悲剧收场的宾客们活动的面影,不知不觉地以感激之情,代替了原来的厌恶心理,而在结束这篇文章时,不免感到有一番怅惘。”[4]
二、著述过程之“奇”
不但以淮南王刘安为代表的《淮南子》的作者们,有着非同一般的生平经历,而且《淮南子》一书的历史出现也极不平凡,因为这是一部酝酿于大时代,又产生于大时代的思想论著,其创作过程与
西汉王朝的盛世发展息息相关,在很大程度上,能折射出日益上升,走向巅峰的西汉王朝的思想精神风貌。这种厚重的时代内涵,赋予《淮南子》的产生以特殊的历史意义,也让《淮南子》无论在著作产生时机、著者群体构成上,还是在内在著述动机、实际编撰方式上,都显示出自己的独特之处。
《淮南子》的产生,是处于西汉王朝治乱之间的历史交替中,具体的说,就是在景、武时期的剧烈政治变动中。景帝三年(前154年),一场西汉王朝建立之后空前的皇族内乱席卷而来,因汉廷采取强势的“削藩”政策,认为:“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3]2825,由此导致吴、楚为首的七个诸侯王国铤而走险,以“清君侧”为名强力反弹,反抗汉廷。这场大乱致使数十万人丧生,也让吴王濞、胶西王卬、楚王戊等皇族成员,身死族灭,结果十分惨烈。“七国之乱”的产生,是汉初以来封国体制的历史产物,有其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但其最终仍以家国内乱的形式反映出来,这不能不对承平已久的西汉王朝形成强烈冲击。大乱之后,景帝放弃强势的“削藩”政策,着重进行汉廷与诸侯王国之间政治关系的调整,尽管其仍旧对诸侯王国严加监控和防范,但不再对后者过于紧逼压迫,以此缓和统治阶层的内部关系。在景帝后期,西汉王朝由乱而治,重新进入稳定的发展时期,《淮南子》的产生即是在此期间。淮南王刘安这时也近而立之年,“无论是其人生阅历还是其学识才思均处于成熟阶段。各方面的条件都已达到一种难得的最佳状态”[5],这便为《淮南子》的酝酿产生提供了最为适宜的历史时机。正是在这种稳定良好的内外氛围中,淮南王国成为刘安与宾客们安心从事思想著述的有利环境,而充分体现出文质化的王国政治,也能让远在长安的汉廷有所放心。因此,这一时期实际上成为刘安继位淮南王以来,淮南王国发展最为稳定,也最具有文化活力的阶段。
《淮南子》书成之后,刘安将其献给武帝,但武帝时期西汉王朝的政治发展又开始有所变动,积极有为的武帝重新加紧“削藩”步骤,采取各种政治措施削弱诸侯王国的实际力量,使其逐渐丧失与汉廷抗衡的条件。西汉王朝也随之进入充满不可测因素的历史动荡时期,淮南王国重新感受到来自汉廷的强烈的政治压力,淮南王刘安的政治心态也不再保持景帝后期的平稳,而是时刻关注长安的形势动态,患得患失的心理起伏日渐频繁。可以说,《淮南子》的出现恰好处于西汉政治的稳定与变动之间,不论此前,抑或此后,都非这部思想巨著理想的创作时机,故而《淮南子》产生于西汉前期治乱的间歇之中,是西汉王朝迈向政治巅峰期的历史产物,对其来说,如此理想的创作时机,不可多得。
《淮南子》的产生,也得益于淮南学术集团的群体构成形式。淮南王刘安从年轻时起,就受到汉初以来诸侯王国盛行的“养士之风”的影响,门下宾客人数多达“数千人”,而且其中“英隽以百数”[1]2167,有不少人具有真才实学,以致当时形成“道术之士,并会淮南,奇方异术,莫不争出”[6]317的繁盛的人才景象。从实际构成来看,淮南学术集团主要包括四种类型的宾客:一是道学之士,以苏飞、李尚、左吴等“八公”为著;二是儒学之士,有“诸儒大山、小山之徒”;三是方术之士,这些人在淮南宾客中人数不少,《史记》中曾着重指出“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突出其在淮南学术集团中的分量;四是墨者等其他士人,汉昭帝时桓宽所撰写的《盐铁论》中,曾言及淮南王刘安“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7]113,可知墨家士人也是淮南学术集团的重要构成,而“游士”中亦当有不属于以上三派的士人。
从中可知,淮南王刘安时期所形成的淮南学术集团,其内部构成多元而复杂,并未体现出较为单一的人才风格,既不同于文赋之士为主的梁王国,也有异于儒学之士为主的楚王国和河间王国,而是“兼收并蓄”,将各种士人收为己用,使其各展其才,从而让淮南学术集团“从事的文化既有辞赋、音乐,又有天文科技和道家哲学”,呈现出较强的“综合性”[8],成为西汉前期区域人才政治中的一大亮点。淮南王刘安这种不拘一格招揽人才的政治特点,使淮南学术集团具备更为雄厚的人才基础,这也让《淮南子》在创作上能“兼于数家,无遗力矣”,表现出“牢笼天地,博极古今”[9]的丰厚内涵。
正因处于较为理想的创作时机,又拥有坚实的人才基础,所以以淮南王刘安为代表的淮南学术集团对《淮南子》的思想著述,也产生强烈的内在动机。从客观原因上说,《淮南子》的创作距离西汉王朝的建立,已有半个多世纪,王朝在汉初以来黄老政治的作用下,持续得到稳步发展,不管是社会经济,还是民生水平,都远较此前为优。虽然景帝时期由于汉廷的强势“削藩”,引发“七国之乱”,但这场皇族内乱持续时间不长,并没有动摇王朝发展的基本趋向,而且战后景帝又迅速恢复黄老政治的举措,轻徭薄赋,慎刑约法,重新让整个社会回到稳定的发展状态。因此,对汉初以来王朝的统治经验,适时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历史性总结,为此后进一步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思想指导,这就成为西汉统治阶层的当务之急。而从主观原因上说,淮南王刘安身为西汉皇族的重要成员,又是高祖刘邦的嫡亲后裔,自然对这种现实诉求有着深切感受和冲动。也正因此,《淮南子》书中表现出浓烈的以汉为本,为“刘氏”立言的政治意识,积极推崇汉政之德,谋求汉政的新发展,如其所说:“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发边戍,筑长城,修关梁,设障塞,具传车,置边吏。然刘氏夺之,若转闭锤”[2]894,“刘氏持政,独夫收孤,财有余也”[2]826,“逮至暴乱已胜,海内大定,继文之业,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图籍,造刘氏之貌冠,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2]944,等等。出于此种显著的西汉本位意识,淮南王刘安称《淮南子》为“刘氏之书”,并在全书的最后豪言此书能“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是一部竭心尽力于西汉王朝发展理念的著作,坚信其“与世推移”的务实变通的治国思想,能充分有益于西汉王朝的现实发展。
对《淮南子》的创作,淮南王刘安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一是“受到盛极一时的藩国文化的直接促动”[10]37。文、景时期,西汉藩国文化繁荣,接连产生吴、楚、梁与河间等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中心,其中又尤以楚元王、河间献王的尊崇儒学,梁孝王的热衷诗赋文学为著名,同这些诸侯王相较,淮南王刘安也不甘落后,自然产生“不效仿别人、独出心裁的‘争胜心理因素”[10]41,试图让淮南王国脱颖而出,成为超越前者的思想文化重镇,这也是其为何不惜丰金厚酬,竭诚延揽天下游士名流的现实动因。二是汉人著述大都具有“立言”以求名的强烈意识,如司马迁著《史记》便为“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3]3320,淮南王刘安也不例外。“凡属书者,所以窥道开塞,庶后世使知举错取舍之宜适”[2]1453,《淮南子》在创作上之所以“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力求能“纪纲道德,经纬人事”[2]1437,究其根本都在于为西汉王朝的长远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指导,而通过这种积极的创作实践,淮南王刘安也能随之“流誉天下”。对刘安而言,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既很危险,又缺少个人才能的施展空间,那么通过“文治”事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也不失为皇权政治下诸侯王自我有为的安全之术。事实上也是如此,千载悠悠,同时期其他诸侯王都未能留下一部以自己国名彪炳史册的鸿篇巨作,惟有淮南王刘安,其名与书并存,亘久不灭,依旧“流誉天下”,甚至于世界。
作为一部卓越的思想论著,《淮南子》实际的编撰方式也很有特色。虽然《淮南子》书中并没有对作者情况作出具体说明,但从书中二十一篇的文字叙述来看,其采取的是“总—分—统”的编撰思路,即:全书在创作前,明显有着一定的总纲规划,对所写各篇也均有着具体认识,创作的基本思路并非杂乱无序,急就成章;在全书的实际著述中,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中的杰出之士,分别著述各自擅长的部分;随着全书各篇的渐次完成,由淮南王刘安统稿修订,并进行文字润色,然后合编成书。这种统筹规划的编撰方式,充分实现了创作个体与群体的相互结合,使《淮南子》在产生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较为明晰的撰著思路,尽管著者并非只是一人,而是群体,且书中内容也极为繁复博杂,但却没有成为“杂乱无章的拼凑,各篇既独立成文,又有内在联系,并围绕一个中心,是自成体系的完整之作”[10]28。正是这种独特的撰著方式,使得淮南学术集团比其他任何藩国都显示出更强的群体著述能力,不仅让淮南王刘安充分施展出“辩达,善属文”的才华,而且让淮南宾客们各自发挥所长,促成《淮南子》“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2]5的著述特色。与战国后期的《吕氏春秋》相较,虽然“《淮南子》是以《吕氏春秋》为蓝本而写成的”[11],二者的著述意图和内容也多有相近之处,但就编撰过程来看,很显然,淮南王刘安的实际作用要远大于秦相吕不韦。如果说后者主要是署名其作的话,那么刘安却是完全有资格代表淮南学术集团,成为《淮南子》的署名作者,因为其“远不止是一个组织者,该书的大部分内容当出于他本人之手,其余也必经过他细致地加工、润色”[10]28。
在同时代的思想著作中,《淮南子》能表现出空前宏大深厚的理论内容,毫无疑问,这与其所处时代、著者群体,创作动机和编撰方式,都存在着紧密关联,也正由于这些独特的著述因素的良好具备,让《淮南子》横空出世,喷薄出一代奇书所具有的繁思华彩。
三、思想内容之“奇”
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曾评价《淮南子》,认为“其书博大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12],梁氏这里所言“博大而有条贯”,正是《淮南子》思想内容的独特之处。
以“博大”来论《淮南子》,是指其在文献资料上广征博引,继战国晚期《吕氏春秋》之后,又一次对先秦时期的历史文献进行全面的承续和保存,“堪称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客观上为我们研究西汉及其以前的文化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13]。《淮南子》中前后“引用先秦文献达四十余种”[10]129,遍及汉人对传统学术所作“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的所有的划分范围。其中为《淮南子》多次引用或化用的先秦典籍有:《易》、《书》、《诗》、《春秋》、《论语》、《老子》、《庄子》、《管子》、《韩非子》、《慎子》和马王堆出土的《黄老帛书》等。在同时代的思想论著中,极少有如《淮南子》者,能对先秦以来的历史文献采取如此全面的博采择取,更可贵的是,还能对这些文献资料进行更为深入的贯通和融会,使其成为自身思想学说的有机组成,而非仅是简单化的引用。在此意义上,如果说《淮南子》对待先秦历史文献的态度是以“博”取之,那么其对这些文献资料的积极理解和运用,则反映出汉代思想家在新的大一统王朝的时代形势下,所显露出的突破狭隘学术门户之见的“大”胸怀、“大”气度。
以“有条贯”来论《淮南子》,则是指其在思想内容上,不仅对先秦以来的各种学说进行“综合性的集大成的工作”[14],而且以汉代新“黄老”为核心,熔铸百家,会通诸子,构建起极富秦汉时代精神的理论体系,卓然自成一家。
在《淮南子》理论体系中,道家思想的地位极为特殊,是其根本所在。《淮南子》对先秦时期的老庄、黄老两大道家支流都有深入的承袭,并不存在单一化的继承。发散南方楚文化气息的老庄道家,对《淮南子》所秉持的基本的道家哲学,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淮南子》对“道”、“自然”、“清静”、“无为”和“不争”等核心概念的理解和诠释,都是基于老庄道家的历史前提。老庄道家的自然主义的政治观,也是《淮南子》用以批判现实中过度“有为”政治的理论武器,成为其对理想社会进行设计和追求的思想渊源。而且,《淮南子》尤为重视老庄道家的生命哲学,试图将其转化为自身新“黄老”的核心内涵,使之与稷下以来黄老道家的治国要义相融合,形成新的“身、国同治”的政治学说。
表现出强烈治国诉求的北方道家,以稷下黄老为代表,是《淮南子》面向现实,所深入汲取的核心的道家思想。西汉王朝从建立之后,为适应社会经济恢复与发展的需要,统治阶层日益主动采纳昌盛于齐国稷下的黄老道家治国学说,坚持奉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这种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实践,跨越高、惠、吕、文、景时期,已经成为经受实践检验的成熟理念,因此对《淮南子》来说,在思想上对其进行全面的反思和总结,并进一步有所深化和发展,便成为根本的理论任务。《淮南子》中所体现出的汉代“黄老”,之所以为“新”,不同于稷下黄老或汉初黄老,就在于它前所未有地将先秦老庄道家的生命哲学深度融合进黄老道家的治国思想中,使原本黄老道家强于治国,弱于治身的理论不足得到极大弥补。更为重要的是,《淮南子》对庄子的生命哲学进行特殊的对待和扬弃,用之深化和拓展黄老道家对政治主体的精神内涵的理性认识,使高度功利化的政治人格,开始具有审美化的政治境界,以此适应和满足统治阶层对超越性的生命信仰的理想追求,使其不仅成为“成功”的统治者,而且也能成为“自得”“内乐”的统治者,形成功利化、信仰化和审美化并重的政治人格。
由此而言,《淮南子》在汉代黄老道家的思想发展上,实际上具有不同于前人的新内涵和意义,这使其无法用简单化的“道家”概念来界定,更遑论“老庄道家”、“黄老道家”、“阴阳道家”等片面概括,至于“杂家”之说,更只是看到《淮南子》思想的外在表象,而无法真正抓住其“杂”中“不杂”的实质内涵,结果只能是忘“道”而论“杂”,以此错误贬低和菲薄《淮南子》
在对《淮南子》思想类型的界定上,自古以来,学界基本游移在"道家"与"杂家"两说之间。其中秉持"杂家"说者,古有班固、高似孙、黄震、刘绩等,近有范文澜、冯友兰、金春峰等,凡持此说者,大都对《淮南子》思想价值有所贬低。而认为《淮南子》为道家者,古有高诱、章学诚等,近有梁启超、胡适、刘文典、牟钟鉴等,且"道家"说又衍生出多种不同认识,如许地山的"老庄道家"说,侯外庐的"阴阳道家"说,熊铁基、吴光、丁原明、陈广忠的"黄老道家"说,台湾学者陈德和的"淮南道家"说,以及台湾学者劳思光、于大成、李增、陈丽桂等主张的"杂家化道家"说。与上述各说有异,笔者力主《淮南子》为"淮南黄老道家",认为对其思想类型的认识,必须打破单一化的"道家"或"杂家"界定,应充分认识到《淮南子》贯通和熔铸老、庄、黄等道家三宗的思想特质,并对其以此为核心和根基,全面撷取先秦诸子百家之学后所形成的汉代"新黄老"的理论形态,进行新的学术界定和评价。质而言之,笔者认为《淮南子》在秦汉历史条件下,实际上为中国古代道家思想谱系创造出一种新的汉代"黄老"形态,这种道家思想的新发展,尽管其中仍存在一些粗糙矛盾之处,但已呈现出别具特色、自成一体的理论形态,既不同于先秦时期的老、庄、黄,也不同于汉初的黄老。
。如若选择一种合乎《淮南子》思想实际的类型界定,在笔者看来,或许无过于使用“淮南黄老道家”为宜。因为如前所述,《淮南子》对战国以来黄老思想的理论发展,已经在汉代黄老政治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性地实现了老、庄、黄的历史性的内在沟通和融合,这种汉代“黄老”的新的思想形态,虽然由于历史原因,未能在西汉王朝的政治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但它的最终产生,不但标志着汉代黄老思想的完全成熟,而且代表着汉代黄老发展的思想巅峰。与“淮南黄老道家”一致,《淮南子》所表现出的道家思想学说,亦可相应称之为“淮南黄老道学”。
《淮南子》从坚持新“黄老”的立场出发,主张“持以道德,辅以仁义”[2]497,试图调和道、儒思想,实现以儒补道、道儒相融的思想发展。《淮南子》虽然对儒家的仁义礼乐有时仍然持批评态度,认为:“仁义礼乐者,可以救败,而非通治之至也”[2]569,“知道德然后知仁义之不足行也,知仁义然后知礼乐之不足修也”[2]569。但没有完全否定仁义礼乐的实际功效,而是认为仁义礼乐对国家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能充实国家政治的正义性内涵,“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国无义,虽大必亡”[2]702,“故乱国之君,务广其地而不务仁义,务高其位而不务道德。是释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2]949。《淮南子》还接受儒家以“德”治国的思想主张,提出:“地以德广,君以德尊,上也;地以义广,君以义尊,次也;地以强广,君以强尊,下也”[2]754,“重莫若国,栋莫若德”[2]1423,要求统治者不盲目追求功利政治,而是要着重实现具有“德”“义”内涵的国家发展。《淮南子》从以往国家发展的历史教训着眼,指出:“故仁义者,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张其广者毁,不广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明确主张:“故仁义者,治之本也”[2]1423,“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 [2]1422。出于对儒家政治思想的兼融需求,《淮南子》对儒家思孟学派的心性思想也有着不少汲取,主张统治者以“德”修身,以“诚”感人,进而实现天人相感相通的政治发展。《淮南子》中儒家思想的充分表现,既是对西汉王朝发展中儒家思想影响的现实反映,也是《淮南子》立足新“黄老”,对儒家思想采取兼收并蓄态度的理论结果。必须指出的是,《淮南子》中的儒家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其新“黄老”的思想需求,出现普遍的道家化倾向,试图与道家思想保持一种和谐并存、互渗相融的理论关系。《淮南子》这种思想表现,缘于其著者主要为道学士人和儒学士人,因而虽然无法在思想上做到完全一致,甚至有时还有所抵牾,但却都有意识地与淮南王刘安的新“黄老”理念采取相近或相同的立场。这决定了《淮南子》中,道、儒关系的本质仍然是以“道”为主,而非“儒”为“道”主,正所谓:“仁义之不能大于道德也,仁义在道德之包”[2]1124。
在《淮南子》进行以儒补道、道儒相融的过程中,其对法家、阴阳家的思想也有着深度汲取。汉代黄老道家原本就是“道法家”,这是从战国稷下黄老以来的思想传统,不论是《管子》,还是韩非、慎到、鹖冠子、马王堆出土的《黄老帛书》,都对此有着深刻的历史反映。受前者内在影响,作为汉代新“黄老”,《淮南子》一方面坚持“法”从“道”出,“道”“法”合一,但另一方面却更为注重“法”所内含的正义性,强调:“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2]662,“府吏守法,君子制义,法而无义,亦府吏也,不足以为政”[2]699,反对“法与义相非”[2]822的法治歧途,试图矫正秦王朝曾出现过的以工具性压倒正义性的“法”治弊端。在根本的法治理想上,《淮南子》追求黄老道家的“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为非,其次赏贤而罚暴”[2]621的政治发展,要求统治者对“法”的工具化使用不以“苛察”为务,而是力求实现“威厉而不杀,刑错而不用,法省而不烦”[2]610的良好状态。为防止“法”的滥用,《淮南子》还十分强调统治者理应以身作则,自觉维护“法”的权威性,“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2]663。《淮南子》还对法家思想中的“势”与“术”进行时代性的去取,既突出二者有益于统治者管理国家的一面,也试图避免法家极端强调君主之“势”、“术”,却严重忽视民众利益的思想局限,在思想上提出以“众势”调和“君势”,以“道术”代替“法术”的黄老新主张。
《淮南子》在治国思想上,同样重视阴阳家的时序政治观,将一年十二月的自然时序与人类社会的政治时序相结合,逐月进行规划和安排,“阴阳大制有六度:天为绳,地为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2]439。《淮南子》认为国家政治发展只有严格遵循天地四时的自然规律,实现阴阳家式的天人合一,才能得到理想结果,因为“与天合德,与神合明,所欲则得,所恶则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2]439,背离天地四时的时序原则,只能使国家政治陷于紊乱之中,走向消极发展。阴阳家这种对国家政治的时序化设计,是《淮南子》治国思想的重要组成,深刻反映出《淮南子》对国家政治发展所作的框架性构想。《淮南子》对阴阳家政治观念的汲取,根本上出于新“黄老”的思想认识,在其看来,“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2]244,这种时序化的政治发展,其内在的自然主义倾向,与新“黄老”的“道治”理念,根本上具有内在的相通性,能够有机结合在一起。
儒家、法家与阴阳家,这是《淮南子》在新“黄老”思想的前提下,所着重汲取和融会的先秦思想学说,但除此而外,《淮南子》对墨家、名家、农家和兵家的理论因素,也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借鉴和吸纳。但从理论体系的整体来看,与前三家相比,处于次要地位。
对待先秦百家之学,《淮南子》始终表现出包容通达的思想气度,坚持主张:“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体也”[2]799,认为不论是何种思想学说,都能得到新“黄老”道家的容纳和兼融,因为其本质上皆是“合道一体也”。而且,《淮南子》还明确指出:“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2]922,从国家政治的实际发展着眼,揭示出百家之学的根本的共识之处,在其看来,百家之学在具体观点上的区别并不是最重要的,而能否充分促进国家发展的“务于治”,这才是思想关键所在。《淮南子》形象指出:“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趋之,或以瓮瓴,或以盆盂,其方员锐橢不同,盛水各异,其于灭火钧也”,百家之学在其眼中,即是如此。不管所使用的器皿是何种形状,只要能盛水,那么结果都是将火扑灭,由此可见,百家之学实质上是“异路而同归者”[2]1327。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在治国思想上强调:“圣人兼用而财制之”[2]1396,主张对各种政治学说进行统合使用,认为既要抓住其共同的根本所在,又要能体现出“其美在调,其失在权”[2]1394的政治灵活性。
《淮南子》之所以是一代奇书,根本而言,是因其在思想内涵上极具开放性、包容性和融通性,不仅能对先秦历史文献采取广采博收的态度,给予积极的保存和运用,而且更能对先秦诸子百家之学,在秦汉时代条件下进行创造性的贯通和整合。尽管由于书成于众手,难以完全做到思想一致,对百家之学的整合中仍存在一些粗糙矛盾的地方,但这只是次要的,因为从整体上看,《淮南子》在将老、庄、黄深度融为一体的基础上,以新的“黄老”理念统摄百家之学,并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思想汲取,这最终使其形成不同于战国黄老和汉初黄老的理论特质,充分展现出“淮南黄老道家”与“淮南黄老道学”的历史风采。
四、流传命运之“奇”
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很少有典籍如《淮南子》一般,不仅作者人生、著述过程和思想内容充满历史的奇特之处,而且连流传命运也与众不同,坎坷多难,不绝如缕。从淮南王刘安将《淮南子》献给武帝时起,到现今,历史已过去两千多年,在此期间,《淮南子》并没有如刘安所愿,产生应有的巨大的思想影响,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发展中声名显赫的鸿篇巨制,而是长期处于要而难传,隐而不显的尴尬境地。与其他汉代思想论著相较,其流传命运始终平淡无奇,甚至堪虞。
毫不夸张的说,《淮南子》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实”与“名”最不相符的著作之一。很大程度上,《淮南子》的流传命运从西汉中期始就受到其创作者命运的根本影响。淮南王刘安在武帝之际被汉廷借机以“谋反”之名削藩,身死而族灭国除,成为有汉一代的“反王”典型,这种惨烈的政治命运,导致《淮南子》一书因人而废,长期得不到广泛的社会流传,严重局限其思想影响的真正发挥。而后人也时常囿于正史偏见,以淮南谋反之事来贬低《淮南子》,认为其书别有用心,且驳杂散漫,故而价值不高。由此,曾经在产生之初便进入过中国古代政治中心舞台的一部奇绝之作,在此后的历史流传中却长久处于边缘地位。这不仅使《淮南子》本身,而且也让淮南王刘安与淮南学术集团,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长期被忽视、被冷淡和被贬低,其书其人之命运,皆凄悲可叹!
在两汉时期,《淮南子》虽然渐有流传,但未能得到广泛的重视和研究,真正对其关注的学者并不多,而其实际的流传情形主要有两种:
一是提及《淮南子》,并有所研究或评价者。西汉宣帝时的桓宽,在其整理编著的《盐铁论》中,最早涉及《淮南子》,其书记有盐铁会议上朝廷大夫的批评之言:“(淮南王刘安)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不臣,使谋叛逆,诛及宗族”,而“著书数十篇”中当有《淮南子》在内;到西汉晚期,刘向、刘歆父子,对《淮南子》一书进行“校定撰具”,并“名之《淮南》”[2]6
,成为对《淮南子》流传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扬雄在《法言》中对《淮南子》也有论及,认为“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并以儒家态度贬其思想为“乍出乍入”[15]。
东汉时期,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将《淮南内》二十一篇著录,但将之归于“杂家”部类,这成为后世贬低《淮南子》的渊薮;王充在《论衡》中也多次引用《淮南子》,并对淮南王刘安有所论述,认为“淮南王作道书,祸至灭族”[6]1183;在东汉刘珍等人所著《东观汉记》中,曾提到汉章帝“赐黄香《淮南》、《孟子》各一通”[16],帝王将《淮南子》作为赏赐之物,这在历史上也不多见。应该说,东汉时期在《淮南子》流传史上最值得一提的是,马融、许慎、延笃和高诱等著名学者都曾先后为《淮南子》作注,但可惜的是,最终却只有许、高二人之作得以部分保存,马、延所作者均已失佚。《淮南子》一书能流传后世,与东汉学者在文献学上的“保存和整理之功”[17],密不可分。
二是虽读过《淮南子》,甚至受其影响,但却隐讳不提其名者。如西汉的司马迁、董仲舒等人,二人所著《史记》、《春秋繁露》中,都有着《淮南子》的思想影响,但因淮南王“谋反”故,均采取暗用而不提的做法。
两汉之后,《淮南子》虽然流传日广,但并未能得到学者与政治家的特别关注,其思想影响仍比较有限。历代学者因其文献资料极其广博,所以引用其文字者多,如《文选》、《艺文类聚》和《太平御览》等,但专门研究者少,只是时有学者对其进行零散的论述和评价,重要者有唐代的刘知几、南宋的高似孙、黄震、明代的王世贞等。清代朴学大盛,《淮南子》迎来学术研究的高潮期,惠栋、黄丕烈、王念孙、王引之、钱大昕、俞樾、陶方琦等人都先后涉足其间,但清代学者更多的是从事《淮南子》的文献学研究,较为侧重文字的训诂考证,而十分忽于思想内容的系统研探。
从民国以来,至于现今,是《淮南子》不仅流传最广,也是日益得到全面研究的历史时期。学者们对《淮南子》愈来愈重视,其研究领域也不再主要局限于文献方面,而是深入扩展到思想内容的各个方面,既涉及哲学、史学、文学、美学、逻辑学、军事学等人文学科,也涉及天文、地理、农学、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而且其中逐渐出现跨学科研究的新趋向,这在《淮南子》流传史上前所未有。近一百多年以来的《淮南子》研究,从胡适的《淮南王书》始,产生出一批思精研深的学术成果,以及一些知名的研究者,如刘文典、萧公权、何宁、张双棣、牟钟鉴、陈广忠、于大成和陈丽桂等。而且,可贵的是,时至今日,《淮南子》的研究者也早已不限于中国学者,而是包括一些国外的汉学家,如美国的安乐哲,加拿大的白光华,马来西亚的郑良树,日本的池田知久、金谷治、谷中信一、久保爱,以及韩国的朴胜显、朴文铉等,可以说,《淮南子》研究正在日渐走向世界,开始对人类的精神文明发挥其应有的东方影响。
综上所言,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淮南子》堪称为一部“绝代奇书”,因为不论是其作者人生、著述过程,还是思想内容、流传命运,都充满着历史的奇特之处,令人印象极为深刻。作为西汉黄老政治的理论总结,《淮南子》试图在前人基础上,创造性地形成自己更为理想的治国理念,这种“淮南黄老道家”的新的思想探索,在秦汉政治思想史上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及影响。综观两千多年的流传历程,《淮南子》一书虽然坎坷不平,在儒学独尊后的历史进程中,长期不为思想家、政治家重点关注,但终归拨云见日,在现代中国迎来更为良好的传播环境。这不但使《淮南子》自身的思想价值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研究和肯定,而且也让淮南王刘安与淮南学术集团在秦汉历史上的影响及地位,日益为学者们所重新审视和评价。值得一提的是,在《淮南子》诞生的安徽省,“淮南子学”的研究也方兴未艾,作为皖北地区“淮河文化”的卓越代表,正在与徽文化、皖江文化一起,成为构建“美丽安徽”的重要的思想资源,充分发挥出积极重大的现实影响。《淮南子》历史命运的这种根本改变,充分证明:一部应秦汉大时代需求而产生的“绝代奇书”,其内在的思想价值是不可磨灭的,尽管长期不遇其时,但这犹如一颗沉落尘泥的稀世明珠,最终不会被人们所忘记,仍会有其重放光彩的时候,而这璀璨的思想之光,将不会再被忽视和泯灭。
参考文献:
[1]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何宁. 淮南子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98.
[3]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4] 徐复观. 两汉思想史(二)[M]//徐复观.徐复观全集.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267.
[5] 雷戈. 道术为天子合——后战国思想史论[M].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351.
[6] 黄晖. 论衡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7] 王利器. 盐铁论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2.
[8] 刘爱敏. 《淮南子》道论研究[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25.
[9] 浦起龙. 史通通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91.
[10] 马庆州. 淮南子考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1] 刘玲娣.熊铁基. 秦汉道家与道教[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23.
[12]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263.
[13] 许匡一. 淮南子全译[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16.
[14] 牟钟鉴. 《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79.
[15] 汪荣宝. 法言义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87:507.
[16] 吴树平. 东观汉记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8:763.
[17] 李秀华.《淮南子》许高二注研究[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383.
[责任编辑:范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