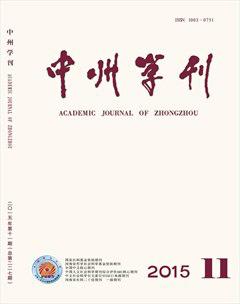我国批评性报道的四次转型及变革前瞻 *
【新闻与传播】
我国批评性报道的四次转型及变革前瞻*
张 萍
摘要:在当今风险社会,批评性报道对风险的监测、建构与监督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当代批评性报道的发展呈现出与当代社会转型大体一致的阶段性,具有曲折性、深入性、分化性等特点。作为权力机制重要组成部分,批评性报道成为政治、经济、社会力量交锋的重要领域。其发展既受记者素养、新闻主义因素影响,也受制于传播环境因素。作为潜在的社会力量,批评性报道不仅呈现风险,也影响风险化解。建构开放的生产系统,妥善处理批评性报道生产过程中各种风险,实现合作式治理,是消解批评性报道带给社会转型风险的关键。
关键词:批评性报道;现代化;新闻主义;权力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1-0163-05
收稿日期:2015-06-05
作者简介:张萍,女,四川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成都610068)。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剧烈而复杂,将世界两次社会转型压缩在一起:从农业社会转为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①大规模、高速度转型使城乡差别、贫富分化等矛盾问题的产生不可避免。新闻是潜在的社会力量,它既反映现实,也影响现实。作为审视暗礁险滩的瞭望塔,批评性报道在报道家族中始终占独特地位。与正面报道为政府倚重却常被民众漠视所不同,批评性报道常同时受到政府与民众关注,影响力不容小觑。尤其在当今风险社会中,风险对政府、民众均释放着强大威胁力。“‘风险’(risk)一词,实际上暗指了风险议题所包含的‘危机’(crisis)内涵与‘社会问题’的性质。”②批评性报道在风险与问题的监测、建构与监督方面不可或缺。新媒体的开放性催生了新闻生产机制的社会化,传统媒体不得不对新媒体上民众所揭发的风险与问题积极跟进。作为双刃剑,批评性报道既可能化身为风险报警器,也可能成为激化风险的隐患。处理不当的批评性报道不仅危及媒体声誉,也对政府、民众造成伤害。
笔者试图融合历史意识、学术思考与现实关注,关照批评性报道与社会现实的相互作用,尤其关注批评性报道的变革规律与方向,希冀有助于推动批评性报道与社会良性互动。
一、我国当代批评性报道的演进轨迹
1.发展阶段
我国当代社会转型分为以下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第一阶段,1978年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第二阶段,1992年至2002年党的十六大为第三阶段,2002年至今为第四阶段。我国当代批评性报道发展阶段也大体如此。
(1)1949年—1977年:宣传本位语境下的举步维艰。此阶段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意识至上,泛政治化倾向导致宣传新闻主义居绝对主导地位。由戈夫曼提出、被吉特林引入新闻传播领域的“框架”概念,表征了报道对社会现实选择性呈现特点。典型报道以体现社会主义新闻最重要特征的身份成为这一阶段报道主力军,而批评性报道则少有发展空间。
(2)1978年—1991年:新闻本位语境下的深度思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使报道从宣传本位转为新闻本位,不仅推动现场短新闻、散文式新闻等新闻改革,也为批评性报道勃兴注入政策活力。1980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同时报道了1979年11月25日的渤海2号沉船事故,虽时效滞后,却成为批评性报道发展突破口。此后“舆论监督”一词频见于报端。这时的人们不仅反思“伤痕”,更思考改革,努力寻找中国现代化之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些以深度报道面貌出现的批评性报道蓬勃发展。1987年《中国青年报》“三色”报道剖析了大兴安岭火灾深层次原因,开创了灾难报道新模式。1987年“舆论监督”进入党的十三大报告。1988年前后批评性报道明显增加,批评重点集中在不正之风。③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课题“社会转型中当代新闻报道的流变”(14SB0033)。
此阶段批评性报道记者以反思者角色走上时代舞台,凸显出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启迪民智的担当;报道围绕体制问题展开监督,呈现出强烈的社会政治性;报道不以曝光为指向,旨在深度思辨,反思改革背景下新旧体制、观念冲突背后的问题。1988年全国优秀电视新闻评选中,批评性报道在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中分别占60%、33.3%、33.3%。1989年起批评性报道陷入低谷。1989年和1990年评选中,批评性报道在特等奖中为零,在一等奖中分别为20%和4.79%。④
(3)1992年—2002年:市场本位语境下的微观叙事。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媒体从单一事业体制转为“事业性质,企业管理”二元体制,市场化浪潮汹涌而来。都市报崛起催生市民新闻涌现,民生领域暗访曝光成媒体看点,逐利动力导致批评性报道呈现泛滥倾向。全国性媒体也成为批评性报道活跃的重要舞台。1994年《焦点访谈》、1996年《新闻调查》相继问世。1995年《南方周末》步入黄金时代,从娱乐性文化周报转型为以舆论监督见长的专业主义媒体。上述以深度报道为特色的栏目及媒体,在延续80年代思辨色彩的同时,也为报道注入平民化气息,从民生角度直指社会转型问题,实现了从80年代宏观叙事向90年代微观叙事的转向。
如果说80年代批评性报道以解惑为己任,体现了记者作为知识分子的思辨气质,那么90年代批评性报道则重在解气、解闷,显示出记者的新闻生产者功能。其报道从国计转向民生,以民生题材、平民视角、故事化手法凸现接近性、冲突性、戏剧性。地方媒体的市民新闻更以家长里短的琐碎走向平面化。批评性报道的社会政治性弱化,娱乐消费性凸显。此阶段也出现了批评性报道记者受贿问题,如2002年繁峙矿难记者受贿事件。
(4)2003年至今:平权化语境下的纷繁复杂。加入WTO后我国市场经济框架基本确立,利益诉求多元化加剧社会分化与断裂,为批评性报道发展孕育了强劲动力。受新媒体平权化特征影响,我国政府角色从控制型、全能型向服务型、有限型转变,政府对社会转为原则性控制,直接干预减少,个人话语空间增大。民主与监督的内在关系,使舆论监督获得发展空间,也使影响批评性报道的权力关系越发复杂,批评性报道发展呈现繁杂态势。
2003年,《南方都市报》“孙志刚案”报道终结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制度。4月至5月的“非典”报道推动了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机制建立。5月《每周质量报告》在央视问世,批评性报道进入小黄金期。2004年,中宣部下达文件,严格限制批评党政系统和官员,禁止媒体进行跨地区舆论监督。⑤批评性报道跌入低潮。同年《南方周末》减少“揭黑”报道,实现主流化转型。2007年,《突发事件应对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为舆论监督复苏提供支持。2008年,周老虎案、三鹿奶粉事件等引发舆论监督又一高潮。其后影响较大的批评性报道呈井喷状态,如上海钓鱼执法等。其间网络舆论监督发挥了重要作用,传统媒体对网络监督热点的积极跟进为批评性报道繁荣创造了条件。
此阶段记者在食品安全报道领域因报道不当而伤害企业、百姓权利的情况也有发生,从毒香蕉事件到“蛆柑”事件等。批评性报道借助监督力量成为权力机制重要组成部分,它一方面对社会实施监视的权力,另一方面也受外部权力的干预,成为外部权力借以实施权力的手段。影响批评性报道的因素越发多元,影响批评性报道的方式也更多样。
经济力量的影响方式,从制造看点吸引广告乃至为广告商利益阉割批评性报道,扩展为以批评性报道为手段进行各种形式权力寻租,如陈永洲事件。由此2014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规定记者开展批评性报道须经本单位同意。而政治力量对批评性报道的影响则突破发布政策文件方式,记者在正常采访中被殴打、通缉等情况也有发生,如朱文娜事件。在少数地方公权力与记者监督权发生激烈冲突之际,一些省市电视台首次携手政府部门开展舆论监督。2010年武汉台《电视问政》开播及问政节目在一些省市落地开花,推动批评性报道迈入新阶段。
此阶段批评性报道成为政治、经济、社会力量交锋的重要领域,也成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激烈竞争的一大阵地。“与别的文化生产场相比,新闻场在结构上更受外部压力的侵扰。”⑥监督与反监督、正当监督与不当监督、对抗与合作、私利与公共利益等二元关系,使批评性报道呈现出更繁杂的状态。
2.发展特点
(1)曲折性。我国批评性报道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呈现出多次高潮与低潮交替的波浪式发展轨迹,该轨迹折射出我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批评性报道发展的曲折性既表现在报道数量增减上,也反映在报道领域及方向的变化中。批评性报道被调控的历程映射出新闻场域关系结构的变化。
(2)深入性。批评性报道的发展虽一波三折,其批评锋芒走向却体现出逐渐深入特征:从第一阶段无生长点到第二阶段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生根发芽,再到第三阶段进入民生领域,直至第四阶段深入权力部门与政治改革领域。虽对权力部门的监督还较有限,但新媒体推动报道向权力系统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转型的逐渐深入。
(3)分化性。批评性报道的发展在媒体层级、地域、定位及类型方面呈现鲜明的分化现象。媒体级别越高,舆论监督话语权及影响力也越大。民主开放意识越浓重的地域,媒体舆论监督的动力与活力也越大。专业新闻主义色彩越鲜明的媒体,批评性报道的力度与力量也越大。网络媒体因开放性优势,舆论监督更具活力。
二、影响我国当代批评性报道发展的因素
从上述发展特点可见批评性报道与社会转型的互动:作为管窥风险与问题的窗口,批评性报道对社会转型影响不容小视,批评性报道得当,将推动社会顺利转型,否则将阻碍社会转型进程;而社会转型进程也经由社会环境变革制约批评性报道发展,导致其发展阶段与社会转型进程基本一致。在此过程中影响批评性报道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1.记者专业素养
专业素养由专业精神、专业学识和专业能力构成,它会影响批评性报道品质。专业精神体现在新闻行为、新闻作品、新闻活动主体的动机与需要中,是“职业新闻主体的内在品格和工作气质”⑦。专业学识和专业能力围绕批评性报道特定要求形成独特理论系统和能力框架。记者专业素养受新闻教育及其他社会化因素影响,尤以前者影响为甚。片面追求技术的新闻教育,缺乏对新闻伦理、理论学养的关注,培养的多为工具使用者,报道者熟悉常规报道流程,却很难处理好敏感的批评性报道。优秀的批评性报道需要的不仅是常态报道方法及突破采访障碍、采集真实材料的技能,还需新闻精神支撑及新闻传播学、法学、社会学等理论支持。缺失“求实为本的科学精神,正义至上的人文精神和和谐为美的自由精神”⑧,对批评性报道的舆论导向及分寸把握不到位,不能按法律要求取证,无法从法律层面明确义务与权利,不仅给记者带来诉讼纠纷,也对舆论环境、社会转型产生负面影响。
2.批评性报道背后的新闻主义
批评性报道常以揭露黑幕、真相为口号,看似践行新闻理想的阵地,实则反映出宣传新闻主义、商业新闻主义、专业新闻主义的博弈。不同新闻主义导致批评性报道面貌迥异。
宣传新闻主义以维护社会稳定及政府权威为目的,对批评性报道数量实行紧缩策略,严格审查内容,批评性报道发展空间受限。商业新闻主义视批评性报道为赚取注意力或换取利益的手段,导致问题呈现耸人听闻,批评性报道被滥用。专业新闻主义以服务公众为指向,追求批评的质量,如深度与品质,尽可能排除政治、经济力量干扰,以独立姿态发掘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三种新闻主义力量此长彼消,占绝对优势的是宣传新闻主义,它对批评性报道有硬控制力。其次是商业新闻主义,在消费主义时代,它对批评性报道的侵蚀不容小觑。力量最弱的是专业新闻主义,它总在夹缝中求发展。最终能问世的优秀批评性报道,往往集勇气、责任、艺术、分寸于一身,在坚守专业底线前提下,力求在三种新闻主义之间达到微妙平衡,在批评的深度、尺度、可看度间实现巧妙和谐。
3.传播环境因素
社会转型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转型,身处社会转型环境中的批评性报道必然会受相关因素制约。从批评性报道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其与政治因素,尤其是与政策环境的密切关系,可以说政策法规、领导意识直接影响批评性报道命运起伏。从1998年朱镕基总理视察《焦点访谈》所赠“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对批评性报道的推动作用,到2002年山西长治吕日周式舆论监督的兴盛,再到近年来问政节目的繁荣,均反映出政治因素对批评性报道的重大影响。
如果说政治因素影响批评性报道荣衰,那么经济因素则影响媒介运作机制,进而影响批评性报道生产动机与方式。一些媒体对采编与经营分开原则的违背给记者监督权形成压力。
文化因素通过影响文化环境中传者与受众的价值取向、审美趣味,进而影响批评性报道形态。在文化因素中,媒介文化的发展成为影响批评性报道气质的重要动力。每种媒介都有内在偏向,“都有自己的议程,都是等待被揭示的一种隐喻”⑨。批评性报道发展史浓缩了媒介历程。“传媒不止是工具,它是带着它的观念一起走进现代社会的。”⑩不同媒介形成不同传播情境,形塑了不同阶段批评性报道内在气质。80年代是报纸时代,报纸的逻辑性与思想性开启了“阐释的时代”。此时批评性报道与深度报道交织,呈现出理性与思辨性。90年代电视唱主角,其与生俱来的大众化、娱乐化特性宣告了平民化时代到来,批评性报道成为电视追求利益最醒目的噱头。21世纪初网络天生的民主倾向使批评性报道深入至对权力机构的监督,与公民新闻结盟成了批评性报道发展的重要策略,批评性报道也因此成为民众维权、监督权力的工具。
三、合作式治理:我国批评性报道的困境突围
批评性报道在揭示风险、推动社会转型方面大有用武之地,合作式治理与开放式发展,成为我国批评性报道未来方向。
1.批评性报道:注重批评艺术
(1)在时机把握上,批评性报道要实现时机与时效的统一。时机指报道符合形势,时效强调报道速度。只讲时效,不讲时机,报道无法达到最佳传播效果并可能存在风险;只顾时机,不谈时效,媒体可能因反应滞后而丧失对热点问题的舆论引导主动权。时机把握得益于记者对形势走向的洞察和对大政方针的把握,记者可通过前瞻性策划找到最佳时机。在重大热点问题上不失声及团队作战、分工协作是确保时效的关键,而在时效失去优势时如何后发制人、以视角和深度取胜也至关重要。
(2)在问题聚焦上,要选择政府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的问题予以关注。既不对问题有闻必录,也不以轰动效应为标准筛选问题。本着典型性、全局性、前瞻性、深刻性原则,报道应站在全局高度发现社会转型中有代表性的重大问题。及早发现影响社会进程的问题苗头,对当前不具备解决条件的报道暂缓公开,以内参形式上报有关部门。报道重心放在对问题深层次原因尤其是制度、观念原因挖掘上,变就事论事为就事论理。
(3)在善意立场上,避免为曝光而曝光的破坏性倾向,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建设性。不停留在揭露问题层面,不为关注度而渲染问题,避免引发社会不必要恐慌及“烂尾新闻”,重视问题追踪,既跟踪问题改进情况,又给有关部门改正错误的机会。
(4)在批评策略上,力求准确、全面、客观,做到有理、有据、有度、有方。即把握好法律政策关;用事实说话,用证据说话;掌握好分寸;注意保全证据,确保采访行为合法;预想报道风险及社会效应,提前想好规避对策。
记者对批评艺术的掌握,有赖于新闻教育对“折衷人文主义”的坚持,确保“操作和理论之间的合作关系”,既重视专业技能传授,又强调新闻精神的养成及新闻传播学、法学、社会学等理论积累。
2.媒体:从批评性报道入手构建对话式新闻
(1)与政府系统形成良性互动。媒体与政府理想关系的形成,有赖于二者对批评性报道功能的准确认识。仅从商业新闻主义出发制造看点,只会恶化媒体与政府关系。本着报喜不报忧心态视批评性报道为政府敌人而非助手,二者良性关系也无法建立。电视问政节目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媒体与政府对批评性报道功能的认识趋于一致。
建立专门机制对批评性报道所反映问题梳理汇总,把重要问题反馈给有关部门,是媒体与政府共建良性关系的重要举措。这既能及时发出预警,又有利于问题解决。政府部门也可围绕焦点为媒体提供问题菜单,与媒体合作开展批评性报道。问政节目在合作监督、创新城市管理方面提供了启示。
(2)为民众建构公共论坛。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的现代化发展理论认为:“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这样的国家才真正称之为现代的国家。”尽管新媒体语境下批评性报道融入了部分公民新闻因素,但把批评性报道作为切入点建构公共论坛的空间还有待拓展。美国传播学者马杰德·泰拉尼安认为,通过真正的参与性传播行为可以达到对生活世界的理解,并最终达到公共领域的扩大。从批评性报道切入问题讨论,激发民众对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是推动民众向公众转化的重要途径。如果说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利用新媒体开放性与互动性,形成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联动,是构建公共论坛广度的可循之道,那么如何引导民众对批评性报道衍生的公共问题进行理性思考,提升其思考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则关涉民众参与深度。
以批评性报道为切入口,记者与政府部门、与受众的互动及受众间的讨论,显示出“对话新闻学”走向。伴随着新媒体及公民新闻崛起,与印刷媒介相对应的传统“客观新闻学”正向与电子媒体和数字媒体相适应的“对话新闻学”转向。“对话新闻学”则主张记者不是“局外人”,新闻报道是记者与其报道对象之间相互对话和沟通的产物,也是不同话语和立场相互冲突、调和与协商的结果;新闻文本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开放性的、蕴含多种阐释可能性的“话语建构”;新闻报道的首要功能是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内引发建设性的“公共对话”。“对话新闻学”成为批评性报道突破发展障碍的重要思路。建构记者、政府、民众间的互动机制,通过对话增进相互理解,是批评性报道良性发展的方向。
3.政府:视批评性报道为行政管理创新手段
公权力对批评性报道的介入同我国政绩考核制存在关联。报喜不报忧的“喜鹊文化”,渗入到权力结构中。批评性报道被一些官员视为阻碍其升迁的绊脚石,而非促进工作改进、体制完善的利器,地方政府求稳心理导致批评性报道生存空间逼仄。一些问政节目的繁荣足以说明,政绩考核机制改革及地方政府领导素养提高对批评性报道的促进作用。
以批评性报道为重点做好舆情监测,是发现风险的重要起点。监测目的并非压制批评性报道,而是以批评性报道为窗口及时发现风险隐患。视批评性报道为行政管理创新手段,指向社会关系重构,强调以整合思维处理政府与媒体、与民众关系,以社会合作应对社会风险。
在碎片化、去科层化的风险社会中,泛政治化与亚政治化成为两大趋向。泛政治化表现为在风险挤压下,政治与生活的界限日趋模糊,而亚政治强调政治参与,“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自我组织”规避封闭性官僚体系给政治合法性带来的风险,意味着建构应对风险的多元化主体。针对批评性报道,政府应变微观业务把控为宏观规范调控,通过确定相关法规引导报道健康发展,积极参与公共话语空间的官民互动,共同应对社会风险。
事实上,传统自上而下的办事程序和决策机制钝化了政府解决问题的自觉与能力,加剧了政府与民众隔阂。在此环境下,批评性报道就可能成为凸现社会矛盾、激化官民关系的触发点。要改变批评性报道这一异化功能,首先要改变政府与民众的连接状态,实现生态民主政治。政府以批评性报道为契机,借助媒体尤其是网络支持,把线上讨论与线下行政结合,提供公共服务及问题查询、投诉和评价,了解民众诉求,解决报道折射出的问题。同时在理性对话中引导舆论,形成官民良性互动,把批评性报道对行政管理的压力转化为动力。
批评性报道是折射社会转型风险最清晰的镜子,不仅呈现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风险,也影响社会转型过程中风险的化解。建构开放的生产系统,妥善处理批评性报道生产过程中各种风险,实现合作式治理,是消解批评性报道带给社会转型风险的关键。
注释
①参见陶文昭:《正确应对快速转型带来的复杂问题》,《北京日报》2013年8月19日。②郭小平:《风险社会的媒体传播研究:社会建构论的视角》,学习出版社,2013年,第51页。③参见刘海贵:《中国现当代新闻业务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8页。④参见陆晔:《电视时代——中国电视新闻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2—33页。⑤参见展江:《新世纪的舆论监督》,《青年记者》2007年第11期。⑥[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5页。⑦⑧杨保军:《新闻精神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前言第4—5页。⑨[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章艳、吴燕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4页。⑩陈龙:《传媒文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6页。沈荟:《折衷人文主义新闻教育:对密苏里方法历史缘起的探寻及思考》,《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2期。姚君喜:《社会转型传播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14页。参见史安斌、钱晶晶:《从“客观新闻学”到“对话新闻学”——试论西方新闻理论演进的哲学与实践基础》,《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2期。陶建钟:《风险社会的秩序困境及其制度逻辑》,《江海学刊》2014年第2期。
责任编辑:沐紫
201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