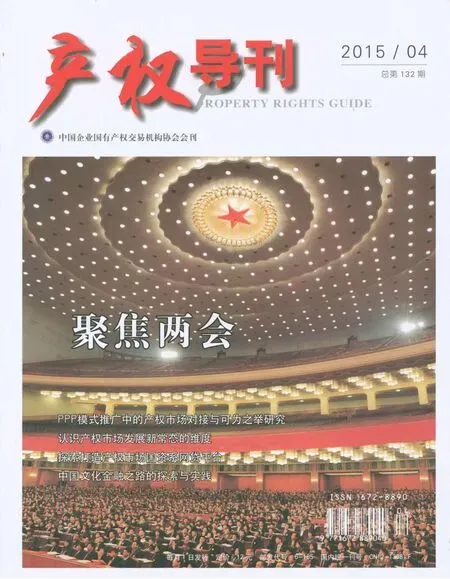观点集萃
中国经济GDP转入中高速或中速增长
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1月10日表示——
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有两个特点。一方面,中国经济GDP增速进入下行通道,转入中高速或者中速增长,今年的趋势还会继续;另一方面,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需要从粗放发展向集约增长转型。这两个特征的发展不一样,前者已是事实,而后者是期望目标,需要经过努力才能实现。如果经济发展效率没有提高,那么之前我国经济粗放增长、数量扩张的矛盾问题就会暴露。此外,原有的经济发展推动因素弱化了,经济下行速度会加快,各种矛盾就会激化。当前中国经济需要在保证不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推进改革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上。

2015是中国经济关键的调整年
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韬葵1月10日发表专栏文章指出——
2015年中国经济的关键词是调整。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深层次的调整期,其关键点是旧的增长点逐步淡出,而新的增长点正在逐步营造出来。这些新增长点并不能像过去那样在统计数字上得到充分反映。比如各种服务业及新的业态是很难纳入统计范畴、进行全口径计算的。改革是调整的关键。如果2015年改革能较顺利地深化,改革的力量将会化解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整顿时期的问题,那么中国经济的调整期将会走得相对顺利一些。如果中国经济的调整期能顺利度过,那么中国经济有望在2016年后再出现相对增长速度比较高,在7.5%左右甚至更高的增长新时期。
投资者才是股市的根
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1月10日在“新常态下的中国与世界”论坛上表示——
在中国股市里,只有10%的股民在赚钱。而政府的税费、证券公司以及监管当局等‘陪玩者’拿到的钱是股民分红的三倍。股市不仅仅是企业融资的场所,更是股民投资的场所,股民应该获得与生产者同等的待遇,政府监管应立足保护投资者利益,不是要给企业送亲,投资者才是股市的根,是魂,是本,是源。所以要“盯住”分红。
新常态下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前外贸部部长龙永图1月10日在“新常态下的中国与世界”论坛中表示——
新常态下中国对外开放呈现出高速引进外资和大规模走出去并进的新特点,而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营造了好的硬环境。亚太地区共建自由贸易区的提议,将进一步消除各国的贸易壁垒和投资壁垒,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打造更好的软环境。“软硬环境”的兼备将会为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
中国企业债务杠杆率全球最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余永定1月10日在“新常态下的中国与世界”论坛中表示——
按照标准普尔数据计算,当前中国企业债务为14万亿美元,美国是13万亿美元,中国已超过美国。而经济增速下降一般会伴随着杠杆率的上升,高企的杠杆率只能说明企业负债和还债能力差距过大。因此,必须提高企业的效率,提高整个经济宏观配置效率,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当前经济增速稍微下降一点,使我们的债务暂时得到缓解,我们可以更大胆加紧结构调整,加紧改革,不要担心经济速度下降对我们带来的损害。
2015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张晓强在1月10日在“新常态下的中国与世界”论坛发言中表示——
2015年中国经济将面临比2014年更加复杂的局面。从外部环境看,政治上,日渐复杂化的地缘政治,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不甚理想的发展环境。经济上,以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反应了全球需求的疲软。可以说,全球的地缘政治、需求不旺以及金融波动等因素,随着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都将对中国产生影响。
未来服务业会成为支柱性产业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年会理事长海闻1月9日受邀做客《金融街会客厅》时表示——
我们现在服务业占到GDP的47%,我觉得起码占到60%至70%的时候,产业结构会比较正常。现在制造业大概每年7%左右增长,服务业每年10%左右增长,这样,比重会不断改变,我相信在四五年内,新的产业就会逐渐形成,但长期的产业结构大概需要一二十年,那时候,服务业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
股市要完善制度
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1月10日在“新常态下的中国与世界论坛”上表示——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股民的平均持股率只有32天,这说明中国股市是一个完全的投机市场。如果不把投机市场变成投资市场,那么问题是很大的。投资应该变成真正的价值投资,配合稳定的制度建设才能形成稳定的市场。目前中国上市企业多是“包装上市、捆绑下海”,只是为了圈钱,因此需要完善的制度来保障股民的利益。比如政府不要用过多的行政手段干涉股市,而应该完善一些制度建设,比如完善信息披露、加大对上市公司造假以及揭露证券欺诈等一些扰乱市场和操作市场的行为的惩罚等。

央行货币政策隐性超宽松 物价反弹只是时间问题
财经专栏作家肖磊1月9日发微博表示——
随着大规模投资项目的上马,以及央行货币政策的隐性超宽松,物价的反弹只是时间问题,中国的CPI最低可能是去年11月份创下的1.4%。原油下跌可以拉低全球通胀水平,但对中国CPI的影响有限,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宁愿通胀上行,也不能承受失业压力,新闻联播天天鼓励大学生创业就是希望降低失业率。
中国资本外流已相当严重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1月2日发表观点认为——
中国资本外流实际上已相当严重,中国对资本流动的管制主要是对短期跨境资本的限制。“倒逼”并非全无道理,但完全放开的不确定性太大,中国的国内条件和国外环境决定了不应该冒如此大的风险。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前提是先加速国内产权制度、经济体制和金融体系改革。这些改革并非必须以资本项目完全自由化为前提条件,因此,为了中国的经济安全,资本项目完全自由化就应该作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最后一步。
未来稳增长需降低投资对GDP贡献率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2014年12月28日在财经战略年会上表示——
增长的两个来源中,目前资本产出比的增速不可持续,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很慢,令人担忧。其中,2008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大大降低,甚至为负。之所以1978年以后投资这么多,主要来自于非居民建筑与基础设施,而这部分投资的增长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降低。投资里面投到机器设备的太少了,投到研发的太少了,投到修路、建桥、盖房子里面太多了,造成一系列问题。投资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负面影响,未来需要优化投资结构,使投资对GDP增长贡献率低一些,这样才能保持比较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

勤打“苍蝇”让企业真正轻松前行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2014年12月29日在题为《经济下行的挤压性原因》的演讲中表示——
目前企业经营环境仍不乐观。一些行政部门不敢向企业吃拿卡要了,同样,也不给办事了。更重要的是,一直在强调清理行政审批权。真正清理的总是一些多年用不着的权力,关键性的权力还是不愿清。保护民营企业权益,就是要保持一个健康干净的营商环境。一些地方的司法部门自身涉嫌违法,在嫌疑人未被认定的时候就开始拍卖所有人企业的资产,这种做法只能让其他民营企业退避三舍。我认为反腐应当从打老虎转向苍蝇。企业普遍反映“苍蝇”太厉害。企业每天面对各个环节的“苍蝇”骚扰,要严厉打击各种“苍蝇”对企业的侵害。只有这样才能让企业在干净的环境中健康发展。
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仍有8%的增长潜力
经济学家林毅夫在2014年12月27日举办的“2014年中华工商时报年会”上表示——
判断未来增速有多高主要看两个因素:首先是中国目前发展阶段的潜在增长率还有多高。其次还要看内部和外部条件怎么样。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年均9.8%的增长,与我国充分利用跟发达国家技术产业差距的后发优势有关,后发优势我们已经用了35年。未来判断一个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还有多高,可看现在的收入水平跟发达国家差多少。从这个指标衡量,中国现在相当于日本在50年代初的时候,新加坡在60年代中的时候,台湾地区和韩国在70年代的情形。所以,我认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还是8%。我们有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参考、借鉴,技术可引进、消化、创新。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跟发达国家技术和产业差距,发挥好后发优势,她的经济增长速度可比发达国家高好多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