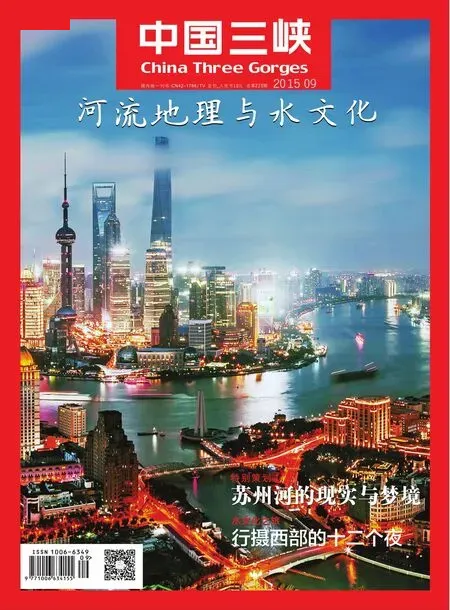塞纳河:一切的触手可及
文/熊若云 编辑/李颜岐
塞纳河:一切的触手可及
文/熊若云 编辑/李颜岐
依然记得从法兰克福飞抵巴黎的那个夜晚,灯光璀璨的巴黎城像一个隆重登场的梦境,而埃菲尔铁塔则是这梦境的顶端。埃菲尔铁塔是不难书写的,他占据着这个城市的制高点,醒目而独特,他俯瞰一切,你抬头便可仰望,但你走得再近,也仅仅能止于仰望中。
塞纳河则是你触手可及的一切。她优雅而绵长地穿越了整个巴黎大区,她途经各个街道,她懂得欢乐、微笑、孤独和泪水,她针织细密地编织着巴黎各个角落、各个阶层的爱恨与荣光。
塞纳河自西向东,将巴黎分割成南北两岸。法国人民惯分左右,如我们惯于把山坡分阴阳面,便以北岸为右,南岸为左。

塞纳河边,巴黎古监狱(Conciergerie) ,全称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建于14世纪,原是法国皇家豪华寝宫,1391年改为监狱。摄影/赵玉明/FOTOE
左岸
巴黎人的咖啡馆,讲究的不过是一份方便而又惬意的舒适。
左右岸的特色,从塞纳河两岸的大区便可见一斑。广义的左岸以埃菲尔铁塔所在的七区起,流经影院和剧院云集的六区,到五区——狭义的左岸便是指这圣.米歇尔大街和圣.日耳曼大街交汇的方圆几公里。古老的索邦神学院、法兰西学院、各大书店,文学艺术与学术在此交汇融合,也孕育了众多因文艺而大放光彩的咖啡馆。人们口耳相传的左岸,就是指这艺术家的浪漫气质之所在。再往下走,十三区是华人等外来民族汇聚地,也是漠视、暴力、敌对频发之地。越是浪漫轻飘的地方,越是隐藏着未知与黑暗。尽管也有埃菲尔铁塔和夏宫这样的繁盛美景,在巴黎人的眼里,左岸仍是相对贫穷的平民阶层的象征。
是否有人和我一样,曾以为左岸只有咖啡馆。
初到巴黎时,总是一遍遍在最繁华的塞纳河岸北,寻找文人墨客们造访过的双偶与花神。那里有过海明威笔下流动的盛宴,有过毕加索与朵拉小姐的一见钟情,有过波伏娃与萨特的闲坐与言说……却总是苦寻不得。
事实上,名扬四海的双偶和花神在巴黎并非那么出名,即使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十个里也未必有一个知道双偶与花神的位置。巴黎人的咖啡馆,讲究的不过是一份方便而又惬意的舒适。法国让人歇脚喝咖啡的地方遍布大街小巷,在广场的一角,在家门口的拐弯处,在河边的树荫下,在人潮涌动的香榭丽舍大街旁,只要花两三欧点上一杯咖啡,就可以选一个称心的位子坐下。可以和朋友谈天说地,可以看街头人来人往,更可以什么都不做,只感受时光行走的静谧与喧嚣。
红色的遮阳棚、错落摆放的桌子、各式各样的音乐,巴黎有太多咖啡馆,寻常而不造作。咖啡馆是法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就如早茶之于广州人,菜场之于家庭主妇。咖啡馆里不分等级,无论何种身份的人,西装笔挺的金融分析师,还是不修边幅的艺术家,甚至居无定所的流浪汉,都是同一家咖啡馆里的寻常面孔。这里的咖啡文化源远流长,绝非吃喝消遣般简单。一杯咖啡,一个巧克力面包,配上一个下午的时光,这是典型的法式咖啡,重要的不是味道,而是阳光下的散漫。
因为左岸的著名,所以错把繁华热闹的右岸错认为左岸的我,终于找到一河之隔的左岸。一路打听,一路走向平凡的街角。这样著名的“文艺胜地”,却在这样不起眼的街道,越发让人怀疑走错路。
双偶正在停业整修,于是去了一巷之隔的花神。远远便望见半空中氲绕不散的烟雾和橙黄灯光下穿梭忙碌的服务员,花神热闹得像一个黄昏集市。白色的咖啡桌紧密排布在咖啡馆内外,挑了个外缘的位子坐下,四周的男人和女人高谈阔论,交织成这个咖啡馆独具风格的现代音乐。唤了良久终于唤来了如临大敌的服务员,巨大的客流量令其不堪重负。同样不堪重负的还有后台的主厨们,招牌的热巧克力乏善可陈,价格倒是贵得深入人心。坐在深黄炽热的灯光下,恍惚中产生一种置身撒哈拉大沙漠的错觉。黄金时代的文人墨客已如塞纳河水般消逝在远方,故地凭吊不过平生感慨。花神早已不是花神,这里贩卖的仅仅是物质。
巴黎脱掉看客的精神外衣,变出调皮的玩笑,就如双偶的名字一样,不是两个可爱纯真的天使,而是两个丑八怪(Deux Magots)。
在法国的一整年,去了许多咖啡馆,大多都靠着味美的面包和一两样招牌饮料,经营得十分热闹。无论到哪个陌生城市,咖啡馆都是同样的温馨地标。越是偏僻的角落,越是惊喜频现之地。在布列塔尼省城的市中心喝到过甚合心意的卡布奇诺,在阿维尼翁早起闲逛时吃到的巧克力面包至今难以忘怀。一进店门总能听见主人热情招呼,他们站在一堆老式家具之中,也许正擦着一只玻璃酒杯,笑容中闪着光亮,让人产生莫名的信赖,尔后端上的热巧克力和面包便多半不会让人失望。大清晨即有众多的老主顾光顾,他们或坐或立,专心读着报纸,闲来与店主攀谈。也有为赌马博彩的“投机者”们开设的咖啡店,这样的咖啡店往往以啤酒为主打,心情急切的客人们排坐在长长吧台前的高脚凳上,欢呼声、扼腕声随着吧台后的电视直播画面高低起伏。
到法国之前,对咖啡的印象主要停留在传统的Espresso,一小杯浓缩的苦味,喝得人满嘴苦涩,连香气都来不及回味。或者是雀巢式的速溶,苦涩之外淡淡的甘甜,至少符合大多数人的味蕾。到法国之后,看着咖啡馆里名目众多的咖啡种类,只能由着外表下手。卡布奇诺往往最先吸引姑娘们的眼球,厚厚的快要溢出的奶泡铺在杯面,然后带着一丝天真和淘气沾在唇边。卡布奇诺实现了人们对于咖啡视觉上的幻想。但若要喝到甜美的咖啡,焦糖玛奇朵和摩卡是更好的选择,混着焦糖、牛奶和巧克力的搭配,既不失咖啡的清香,又多了几分熟悉味美的平易近人。
到了法国咖啡馆才第一次将“促膝长谈”看得真切。无论是门外各色遮阳伞下随意摆放的折叠桌椅,还是室内有些古色古香的桌椅。窄小的桌面刚好容得下食物和饮料,相对的两个人隔着的是刚刚好适合谈天的距离。常常能看见席间托着腮帮子攀谈的恋人,语调婉转轻柔,眼神默契交会。也有相聚的亲戚朋友,一起吞云吐雾谈天说地,转眼间哈哈大笑。更多是带着宠物狗或者独自发呆的人,法国人善于思辨,而这小小的桌子便是一片独自思辨的小天地。

上:20世纪的艺术骚动主要集中在美国,同时,巴黎也有一批外来的卓越群体正在革新艺术和文学。巴黎的咖啡馆经常有海明威等人物光顾和进行社交活动。咖啡馆成了这一时期的标志。供图/文化传播/FOTOE

下:1952年,法国巴黎咖啡店外景。摄影/Robert Capa/FOTOE
太多人慕文艺之名来巴黎,向往咖啡馆里精心调配的“小资”,文艺因此变成墙上的意大利风景画、深灰蓝的棉麻大衣、早晨必喝的蓝山咖啡。带这样的心态来巴黎恐怕要失望,这里的音乐并非蓝调,家具有些古色古香,如居家般平实。随处可见的人形形色色,不只有你侬我侬的年轻恋人,还有做着填字游戏的老太太,或者闲坐打发下午时光的老先生。巴黎脱掉看客的精神外衣,变出调皮的玩笑,就如双偶的名字一样,不是两个可爱纯真的天使,而是两个丑八怪(Deux Magots)。
他们的书摊,像是阿拉丁的神灯,总是可以让人轻易从中发现自己心念已久的愿望。
咖啡馆之外,二手书摊是左岸一条流动的风景。去巴黎前就多次听老师说,一定要记得看看塞纳河畔的旧书摊,带着发酵已久的想象,一到塞纳河畔就开始寻觅二手书摊。
从圣米歇尔桥,到金碧辉煌的艺术桥,二手书摊沿着塞纳河边零零散散排开,简陋的架子上书籍各色各样,从文学、艺术到历史、哲学,琳琅满目,英文的《哈利波特》全集,老旧的精装版《全球通史》,甚至还包括日本连载漫画。书架两边的绳子上挂着各色各样的画:彩色的现代抽象画,黑白的素描,还有以附近的景色为题的风景速写。偶尔也顺带着卖一些明信片和邮票,供人将此地此景的心情邮寄给远方的朋友。据说旧书摊始于18世纪,由于大革命时期许多图书馆被劫,货郎开始搜集和贩卖散落在各地的书籍。他们拎着装书的箱子沿着河堤和城墙行走,停下来休息的空隙就成了流动书摊最早的雏形。
尽管已过两个世纪,用书箱装书的传统倒是留了下来。旧书商把深黑色的大书箱抵放在岸边的护墙上,脚边常常趴着一只听话忠诚的狗,或者擦着书摊跑来跑去的猫。他们身着深灰色大衣,戴着咖啡色的帽子,常年累月坐在塞纳河畔,任风吹拂他们的衣角和书页。他们常常都有一副好脾气,你可以独自翻阅,也可以向前攀谈。经受过暴风骤雨、骄阳酷暑的四季变幻,也经受了门可罗雀的孤单,摊主们依然守着这片精神庄园,日复一日,亲切善良。他们的书摊,像是阿拉丁的神灯,总是可以让人轻易从中发现自己心念已久的愿望。
加缪曾在《堕落》中写下“河水在旧书店关门的书箱中闪闪发光”的句子,在以现代时尚著称的巴黎,来源于传统和底层的旧书摊让人怦然心动。世界上所谓的国际大都市越来越多,比肩继踵的摩天大楼旁,有多少地方能容得下破旧的书摊?多数是被拆迁,幸存者过着提心吊胆的游击生活。而在这同样游人如织的塞纳河畔,充满人情味的旧书摊依然牢固占据着城市的一角,伴着潺潺的流水成为都市记忆的一部分,成为抵抗现代化大潮的力量,和不远处的教堂,以及更远处的埃菲尔铁塔,组成这座城市立体而包容的风景。

巴黎塞纳河边,街旁的书摊。 摄影/刘必荣/东方IC
至今法语仍将“经久耐用”的东西比作“新桥”,所谓“历久弥新”,是对新桥的生动诠释。
告别书摊向前,便到了巴黎最著名的新桥(Pont-Neuf)。
所谓新桥,其实一点不新,最初由亨利二世在十六世纪开始筹建,五十年后的1607年由亨利四世主持落成仪式。法国人盖房子,真是应了“磨洋工”一语,巴黎圣母院建了二百多年,协和广场前后耗费了八十余年。新桥建成后至今未重建过,法语里将“经久耐用”的东西比作“新桥”,所谓“历久弥新”正是对新桥的生动诠释。
两座独立拱桥之间的空地上,矗立着亨利四世的青铜塑像。原作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遭熔化,现在的雕像则是1818年的仿制品。这屹立在桥头的雕塑,在巴黎的夜色下显得异常高大。
新桥长232米,宽22米,两段式的独立拱桥将左岸经西岱岛与右岸相连。宽阔的人行道为艺术家们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桥上歌声几乎从未间歇。亦有街头画家在此摆起摊位,将塞纳河畔的风光入画。隔着暮色传来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夕阳下的河畔,不时有鸽子飞过,停留在行人的脚边、石凳旁、画架上。假如爱丝美拉达牵着她的小山羊路过此处,一定也忍不住跳一支活泼的舞。
艺人坐在新桥的长凳上,拉着悠扬的手风琴,唱着那首忧郁却意境开阔的《巴黎天空下》。他的脚下是一顶礼帽,里面零星散落着硬币。在蒙马特的山坡,在巴黎地铁站,常常不经意就与街头艺人相遇,他们鼓动着手风琴,唱着欢乐的歌,那歌声传到半空中,大街小巷都充满愉快的味道。

艺术桥上的锁,祈愿将爱锁住。 摄影/JB Autissier/东方IC

塞纳河上的木质老桥——艺术桥。这里有古色古香的木椅和桥灯,可以站在桥上饱览的塞纳河美景之外,还有那两旁栏杆上大大小小的爱情锁。 摄影/Chesnot/Getty Images/CFP
新桥的一旁是艺术桥(Pont des Arts)。这个名字人们或许会感到陌生,但提到爱情锁,所有人都会恍然大悟。艺术桥曾是座木质的老桥,始建于1804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德军轰炸被毁,最终在上个世纪80年代得以重建。除了古色古香的木椅和桥灯,桥上醒目独特之处就是那两旁栏杆上大大小小的爱情锁。爱情锁的风潮并非源自巴黎传统,而是来自2006年费德里科·莫恰的一本小说《对不起,我爱你》里的情节。小说中主角将带有名字的锁挂在罗马米欧维奥桥,并把钥匙扔进泰伯河以代表永恒之爱,随后,这股风潮在罗马兴起,继而席卷整个欧洲,来到巴黎。
形态各异的爱情锁,见证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情侣们对爱的执着与真诚。但数十万个无法解开的锁,长年累月地对巴黎古桥的桥身带来了沉重负担,甚至有倒塌危险,巴黎政府不得不定期拆锁为桥减负。多年后重游的恋人们,未必能找到一起挂上的爱情锁,甚至恋人或许早已萍飘离散,不过多年前的心愿和相爱的眼神也许仍可在此处穿越岁月,故地重逢。
右岸
无论选择哪个点开始在巴黎的旅程,无论向东或向西,都必然会与西岱岛相遇。
倘若说巴黎是丰盛的筵席,左岸便是餐后的甜点,是奶油杯上点缀的樱桃。右岸才是那秀色可餐的盛宴,是让人灵魂为之激动的流光溢彩。左岸是额外的惊喜,右岸是扑面而来的震撼。倘若说在左岸流连就足够,未免显得有些舍本逐末。没有左岸,巴黎变得严肃而单调;而少了右岸,巴黎就不再是巴黎。
巴黎的右岸,应该从四区的西岱岛说起。每个到巴黎的旅人,或多或少会有这样的印象:西岱岛是巴黎的中心。无论选择哪个点开始在巴黎的旅程,无论向东或向西,都必然会与西岱岛相遇。
西岱岛与圣路易斯岛是塞纳河中心的湖心岛,两个岛由小小的圣路易斯桥相连,犹如在河心精心镶嵌的珍珠。西岱岛是巴黎的中心,是巴黎历史开始的地方。
公元前三世纪,这个小岛便是全部的巴黎,后来罗马帝国皇帝凯撒一世不断扩张,把法国大部分地区并入罗马帝国的高卢省,罗马人在这里修道路,挖水渠,筑宫殿和神庙。为了纪念最早在此生活的西哥特人祖先——巴黎西人,凯撒大帝下令将西岱岛改名为巴黎,简洁而不失风情。随后巴黎不断变迁扩大,岛的周围相继建起了市政府、卢浮宫、杜丽花园、协和广场……西岱由河心孕育了整个巴黎的瑰丽和文明。
塞纳河水温柔包裹着西岱岛,两岸是沉默的林荫。河水和树林过滤了现代都市的喧嚣,给西岱岛营造出时光亘古的意境。
教堂仍岿然屹立,仿佛她能存在多久,就能把历史带向多远的未来……
巴黎圣母院安于西岱岛的东南角。远观圣母院,大大小小的尖塔争先恐后钻入云霄,气势强烈而蓬勃。哥特式的建筑代表了中世纪人们对天堂和上帝无限崇拜的精神美学,崇尚直线上升的陡峭空间,把全部视线引向天际。雨果曾在作品中以独立的篇章赞誉这座建筑为恢弘的“石头的交响曲”。据说后来引来市民大量募捐,巴黎圣母院得以修缮。
站在巴黎圣母院脚下,不难理解雨果对这座教堂怀有的情感。八百年的风霜雨露从四面八方吹打在墙上,打在袒露在外的石像、雕塑、彩色门窗上,见证过拿破仑的加冕、戴高乐的葬礼,再强大的人也终归于死亡之寂静,教堂仍岿然屹立,仿佛她能存在多久,就能把历史带向多远的未来……
进入巴黎圣母院,顿时感受到粗砺下的温柔。四周的柱石支撑起高大巍峨的穹顶,头顶金碧辉煌的壁画容纳进多少能工巧匠的人生。抬头望见基督与众先人的眼神,虚弱的或悲悯的,直击人心。参加过一次大主教主持的弥撒,当风琴的声音从头顶响彻整个教堂,命运的不可知与何处求霎时涌入心神,抑制不住流泪的冲动,为这里的广阔恢弘,为一己的渺小和虚弱。
巴黎圣母院的右侧,总有长长的队伍等待攀登钟楼。这个角度可以看到众多面目狰狞的雨兽附刻在墙上。它们丑陋的脸让人楼梯想起加西莫多,对钟楼产生些许期待,毕竟那是加西莫多日夜敲钟的地方。沿着陡峭的千层螺旋楼梯上去,终于到了钟楼,却原来是圣母院的半山腰,沉思的怪兽或呆坐在塔沿上,或眺望着远处的巴黎圣母院,像同样在此处神游的自己。
巴黎圣母院的领地之外是一个花园,花园没有围栏,调皮的孩子们聚在一起玩耍,游人可以从这个角度拍摄巴黎圣母院的全景。花园的尽头,是阴森恐怖的巴黎附属古监狱(Conciergerie)。法国大革命时,多少人从这里走上断头台。玛丽王后、丹东和罗伯斯庇尔都在这里度过最后的不眠夜。教堂-花园-监狱的组合让人意外,是否靠近教堂,就能让这些焦灼的灵魂找到归途?

7月14日国庆日的“法兰西巡逻兵”的飞行表演。机群经过凯旋门上空时喷出蓝色、白色和红色的烟雾,正是法国国旗上的三种颜色。图中前景是卢浮宫附近的圣女贞德雕像。 摄影/Huang Zheng/CFP
西岱岛以西,右岸的上游,紧密相邻的一区与八区是巴黎的荣光。
从巴黎圣母院脚下穿过圣路易斯桥,便到达了圣路易斯岛。整个岛是一个以圣路易斯冠名的迷宫。一条叫圣路易斯的大街横贯其中,从每条整洁干净的街道,都能看出它身份的高贵。这里可以找到最好吃的冰淇淋和热可可,古着店的老板们守着各地淘来的宝贝,小木马在玻璃窗前显得乖巧。艺术画廊里众多绘画等着被收养,记得最心仪的那一副,暖红的色彩却让人能想见小桥流水的苏州。宽敞的马路上总能看到戴着头盔骑着重型摩托的年轻小伙,一阵轰隆就不见了身影。
西岱岛以西,右岸的上游,紧密相邻的一区与八区是巴黎的荣光。沿塞纳河一带,协和广场-香榭丽舍大街-凯旋门构成八区的瑰丽图景;杜丽花园-卢浮宫使自然之美与历史韵味在一区交融。
协和广场几经易名,最初叫“路易十五广场”,由路易十五在十八世纪下令营建,广场上摆放了路易十五的骑马雕像,以展示其皇权的至高无上。路易十六则设计了断头台安放于此,力求以“人道主义精神,迅速处决死囚”。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期间,雕像被革命人民推倒,广场易名为“革命广场”,路易十六及其王后在这里被雅各宾派首脑罗伯斯庇尔下令处死,戏剧性地被送上自己设计的断头台。一年之后,当初反对极刑与独裁的罗伯斯庇尔也因独裁,在同一个广场和断头台上被处死。直到十九世纪广场重建,为了纪念战争年代的结束,满足人民祈望和平的愿望,“革命广场”更名为“协和广场”。
广场的正中央是高23米,有3400多年历史的埃及方尖碑,于1831年由埃及总督穆罕默德赠送给法国,据说这块完整的重230吨的花岗岩雕塑费尽险阻从埃及卢克索运送至巴黎的过程就是一部空前绝后的英雄史诗。方尖碑竖立在宽阔的广场上,犹如一个巨大的日晷,分分秒秒地记录着流逝的时间,巍峨肃穆。
走出协和广场的沉寂,对面就是典雅活泼的香榭丽舍大街(les Champs-Élysées)。从18世纪起,香榭丽舍大街就成为小说中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天堂。尤记得小仲马描绘的茶花女玛格丽特在此漫步的动人身影,香榭丽舍大街是繁华优雅的背景。而在现代电影让·吕克的《四百击》中,它又成为奢侈昂贵的符号。
现实中的香榭丽舍大街远比想象丰富。从协和广场出发,左边是法国总统所在地爱丽舍宫,一旁竖立的戴高乐将军雕像十分传神,他身着戎装迈开步子,仿佛从远方走来,不远处大小皇宫的圆形屋顶在灯光反射下晶莹透亮。爱丽舍宫对街是一条长满榆树的林荫道,当人们刚开始为这闹市中的清幽欣喜,很快又发现了榆树后铺满绿草的秘密花园,花园中的小天使喷泉和女神雕像为它增添了几分艺术气息。
林荫道以西,就是香榭丽舍的高级商业区。整个商业区其实不长,大概一千多米。玻璃橱窗里展示着各式各样的欲望,一流的服装店、香水店从这里向世界各地输送奢华美丽。尽管随着大众品牌的驻扎,这里的商店不再显得高不可攀,奢侈品商店内身着高级西装,挺直站立的服务员,还是能让人感受到昔日属于特定阶层的昂贵。商业是可以复制的,如今纽约第五大道、米兰蒙提拿破仑街的热闹繁华不输香街。不过,似乎都缺少了些香街的优雅和克制。
协和广场的另一端,一条轴线将杜丽花园和卢浮宫相连。杜丽花园亲切随和,是整个巴黎城中最没有架子的花园,绿树青草间随处摆放着可移动的座椅,人们可以坐在水池旁写作、绘画,或者发呆、喝茶、看树、看云。褪下满眼的繁华,旅人的心灵在这里得到调剂。
卢浮宫就在杜丽花园的身后,这座始建于1204年的宫殿本身就是一个宏伟的艺术品,其整体建筑呈U型,包裹着贝聿铭设计的玻璃金字塔如众星捧月。卢浮宫是一个探索不尽的巨大宝库,雕塑馆里有“胜利女神尼卡”之类的高洁,也有海边嬉戏的少年、偷东西的天使的天真可爱。阿拉丁的神灯和一千零一夜的宝贝隐藏在东方艺术馆的各个角落。而北欧绘画馆里风吹麦浪的大地风光,引发出人集体无意识中对田园牧歌的向往。
站在卢浮宫二层的玻璃窗旁,落下的雨水模糊了远处的街景,近处拐角宫殿上的众神雕塑却依然清晰。停歇的步履中,忆起童年凝视寺庙中佛像的情景,此刻另一种形态的文明近在眼前,让人的灵魂几欲颤动。这眼前的宏伟,宫殿外静静流淌的塞纳河,河边的落叶,远处的塔楼和高耸的尖屋顶,这一切无数的细微相伴相生,组成一切的触手可及,一个令人心生热爱的巴黎。

夕阳下的法国巴黎圣母院与塞纳河。 摄影/谭伟/FOT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