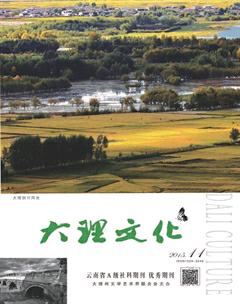记忆中的《洱海》
一
我在拙作《抹不掉的记忆》中,写了大理市下关职工业余文学创作小组的活动,写了几位从那儿走出去的作家、诗人。习作发表之后,我仔细读了一遍。读完,内心感到有点不安。因为篇幅所限,很多人没有写到。
究竟先写谁呢?那么多人,真是憨狗咬石狮子——不知从何下口?猛然间,我想起了下关文化站最初成立文学创作小组的初衷。
当时,下关文化站,成立职工业余文学创作小组,是为创办一张文艺小报,招徕作者。一张报纸,有了作者,才不致成为无米之炊。否则,报纸稿源从何而来?缺乏稿件,报纸就难以为继。
就是在这个创意之下,下关职工业余文学创作小组应运而生。我也有幸成了业余创作小组的一员。
记得,我们单位收到的邀请函是这样写的:
邀请函下关总站工会:
为繁荣下关地区职工业余文学创作,下关文化站决定创办一张文艺小报,暂定名《风展红旗》,为我市业余作者提供作品发表园地。要办好《风展红旗》,就必须有一支业余创作队伍。有鉴于此,经研究,我们将组织下关地区职工业余文学创作小组,每周星期六下午,在下关文化站开展业余文学创作学习活动,特邀请你站业余作者韩如龙、彭怀仁两同志参加。敬请支持为谢!
如蒙同意,请通知他们下周周六,按时参加学习为盼!
此致
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下关市文化站
1973年x月x日
我和工农弟兄们,就是被这张邀请函,邀约到文学小组的。文学小组活动,在那家伦和施沛老师的主持、领导下,每周六,雷打不动,风雨无阻,一直开展活动。其间,那家伦老师四处奔走,求爷爷告奶奶,到处化缘,都没有筹到办小报的经费。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展红旗》小报,却始终未能风展红旗。那家伦老师,只好发动大家,将文学小组集体讨论修改过的稿子,投寄给报刊。幸好没过多久,就有人在省内报刊发表习作。
但是,小组成员,水平参差不齐。有些人的作品上公开刊物,就还差那么一点点。如果有一个自己的内部刊物,让大伙演练演练,便可以从小池塘的浅水,游向大江河的深水。为此,文化站的老师们一直忧心忡忡。“哪一天能有自己的刊物就好了?”那家伦如是说。
二
说到《风展红旗》,我想起了广东作家何百源,他读过我发表在2015年第二期《大理文化》上的《抹不掉的记忆》之后,给我写来一封信。披露了他误入其门的事。
何百源来信说,当时,下关市文化站组织职工业余文学小组,根本没有通知他。他们单位通知了诗人舒宗范。市文化站第一次开展活动,恰好,舒宗范外出进行森林资源勘察去了。单位领导老王找到他,让他拿了写着舒宗范名字的邀请函,去文化站听听精神。于是,他便去了。去到文化站,一听各人自报家门,他才发觉,参会者大多数人都发表过作品,少数是爱好文学多年,并且写过不少文章。而他,一个西南林学院毕业的林业勘察工作者,涉猎文学不多,根本没有他说话的份。那天,他一言不发,只让耳朵做客。临走时,那家伦问他:你想不想参加学习,我看你签名时,字写得很好,将来文化站办《风展红旗》,你可以帮忙抄抄、写写。他回答说,我当然愿意参加。之后,他便成了业余文学小组的成员。
看了他的信,我恍然大悟。我一直以为,早年那个业余文学小组,是我们走上文学创作小路的跳板,没有那几年的弹跳,我们都是散兵游勇,修不成正果。我根本想不到,何百源去学习业余创作,完全是一种偶然。假设,第一次学习时,舒宗范没出差,就不会轮到他;或者,单位领导另叫一人顶替,那么,他兴许也不会爱上文学。一次偶然的机会,成就了一位出版了10本书的中国作协会员,让人难以想象!要不是42年后,他说出了那一次偶然,至今,我也不知道原委。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一个林业学院毕业生,在森林勘察单位工作,结合专业,学以致用。那是没得说的了。他报考林学院,就是想当一个林业工程师。有趣的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命运!上世纪的1985年,他在大理的林业单位工作20年后,调回老家广东南海,先是在政府机关工作,后来,因他在当地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被调到《佛山文艺》当编辑,不久,升任副主编;之后,又调到市文联工作。他为当地培养了300多个业余作者,其中不乏小有成就的青年作家,可谓桃李成荫。退休之后,他笔耕不辍,经常为当地报刊写专栏稿;不时还到文学创作培训班讲课,扶持新人。他年过七旬,精神健旺,妙语连珠,一点也不显老!我想,这大抵是文学滋养了他吧?
想到这儿,我给他回了一封电子邮件,我对他说:我一直以为,你早就喜欢文学,想不到,你跨进文学之门,纯属偶然。我们第一次活动,参加的都是文学爱好者,没想到你是被人拉壮丁,更没想到,这一拉,改变了你的人生之路。真不知你是该感谢出差的诗人舒宗范,还是感谢临时拉你当壮丁的那位领导。
他回复说,我是被错拉的壮丁,搞文学纯属偶然!
三
2013年冬天,白族作家李友文打电话告诉我,下关回族作家杨水清的妻儿,自己掏钱,为老水出了一本书。我们那一辈的人,都亲切地称杨水清老师为“老水”。老李还说,过几天,我把书拿来给你看看。
三天过后,老李给我送来杨水清的书。水清是下关文学小组最平易近人的一位资深作家。他的家人,在他过世10年之后,为他整理出版专著,精神司嘉。
据说,这本由杨水清家人结集出版的《水韵清香》,是作者在世时,就剪贴好,准备编辑成册的。因水清是一个厚道人,一直未能为自己出书。本来,他作为大理市文联主席,多少有点权,找主管领导要点钱,完全可以为自己出本书。但他不以权谋私。心里想着的是业余作者,不替自己打算。所以,他在世时,出书的愿望未能实现,成了平生憾事。好在他的妻儿,最后帮他圆了出书梦。
我在翻阅水清的《水韵清香》时发现,书中所选的69篇文章,有好几篇,选自《洱海》小报,浏览着文章,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下关文化站创办文艺小报《洱海》的前前后后。
《洱海》就是由最先创意的《风展红旗》演变来的。经过下关文化站的多方努力,办文艺小报的经费终于有了着落。这一回可以风展红旗了,可是,风展红旗的名字,太革命化了。下关就在清粼粼的洱海边,洱海是白族儿女的母亲湖,白族作家那家伦说,我们都是喝洱海水长大的,就定名“洱海”吧7
1979年1月30日,第一期《洱海》小报呱呱坠地。当然,之前,那家伦、施沛老师,以及下关职工业余文学小组的哥们,也为它费了不少心力。
1978年秋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绿了大理的苍山、洱海,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给白族地区带来了文艺的春天。白族作家那家伦在《洱海》第一期上写的《春风赋》说:“春风,美好的春风,使祖国变得年轻,使大地充满阳光,使人间充溢希望,使时代满是生机。”“我们被压抑的智慧、力量和创造精神,已经不可遏止地迸发出来,进发在新长征路上”,正是这一阵春风,吹亮了《洱海》。
第一期《洱海》,都是下关文学小组成员,给下关文化站交的作业,有那家伦的《春风赋》,杨水清的《蜜》、张焰铎的《花》、舒宗范的《怀念乌蒙金沙间》、谢本良的《翠柏·雨花石》、还有著名画家谢长幸的篆刻、著名画家董浩川的国画,著名摄影家钏培基的摄影。可谓图文并茂,熠熠生辉。
《洱海》的诞生,是下关市业余作者的福音,下关市的业余作者,从此有了自己的家园,有了一展技艺的平台,拿着第一期《洱海》,我们奔走相告!
四
《洱海》第一期问世之后,犹如一块巨石投入洱海湖面,激起层层涟漪。不少文学爱好者纷纷给编辑室写来热情洋溢的来信。
读者刘波说,生活中,值得歌颂的事情很多。于是,我下决心学习文艺创作,想用自己笨拙的笔,描绘新时期欣欣向荣的喜人局面。《洱海》这样的刊物,为我们初学写作者,提供了学习创作、交流经验的园地,很受大家欢迎。
刘波,就是当年下关文学小组刘傅森老师的儿子,他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喜爱文学,尔后,写过不少文学作品,他的处女作,就发表在《洱海》上。
之后,下关地区的文学爱好者,纷纷给《洱海》投寄自己的习作,到《洱海》里游泳,一试身手。有的,很快就在《洱海》上发表处女作,而后,一发而不可收,成了终身与文学相伴的痴情人。后来成为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的作家赵守值,杨中兴、杨腾霄、曹高德、赵阔,当年便是《洱海》的忠实作者和读者,也是从《洱海》这个小游泳池,游向省内外的大江大河的健儿。
《洱海》初创时期,下关地区,可谓文学爱好者云集,不少后来成名的作家,都在《洱海》试过笔,都在《洱海》上空呼吸过《洱海》的氧气。更有一些后来从政的官员,他们也曾经给《洱海》留下他们的生活手记。我在《洱海》第5期上,读过一篇题为《彝山素描》的散文,作者是陈天祥,这是他下乡归来写的短文。几年之后,他成了大理市市委宣传部部长,后来,又担任管思想政治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在大理市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记得前年秋天,大理学院原民族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张锡禄教授,打电话给我说,他在填一张表格,表里有一栏,何时发表处女作。他思来想去,处女作应该是发表在《洱海》上,《洱海》上的作品,是他的开山之作。让我帮他查查,发在哪一期?
我当即应允。当时我想,尽管,张锡禄后来有《大理白族佛教密宗》、《明代大理总管史》等民族文化研究的扛鼎之作,但是,他的处女作,发表在《洱海》上,是不争的事实,《洱海》是他初练游泳之海。经查,他的处女作发表在《洱海》第12期上,题目是《白族民歌有自己特有的艺术形式》。如今,张锡禄已是发表多部研究白族历史文化专著的知名学者了,但他的第一步,是从《洱海》迈出去的。这是决定他人生命运的第一步,也是他著书立说的起点。
五
1979年4月24日出版的第5期《洱海》,洱海二字,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仔细一看,报头题字变了。再一看,报头是中国文坛泰斗茅盾先生的墨宝。
《洱海》编辑室,写了一篇题为《“把《洱海》愈办愈好!——贺茅盾同志为本刊题写刊名”》的文章,介绍了他们怀着对沈老十分崇敬的心情,怀着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责任心,怀着进一步办好《洱海》的愿望,呈函,向沈老汇报了创办《洱海》的目的及意义,寄上已出的《洱海》,敬请沈老审阅,恳请沈老为《洱海》大笔书题刊名。沈老在政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于1979年4月5日挥毫写了两份刊名,并勉励编辑人员:“把《洱海》愈办愈好!”
茅盾先生为一个边疆小市的小报书写刊名,不知当时是否空前绝后,但足见文坛泰斗对边疆白族儿女的眷眷爱心。
之后,《洱海》编辑部召集业余作者座谈,大伙,感慨万千!茅盾先生的题字,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创作热情,不少人纷纷表示,一定要刻苦读书,勤奋写作,以此报答茅盾先生的关爱之情。有人还即席朗诵诗歌,抒发激情。
那天,那家伦老师,非常激动,因为,请茅盾先生题写刊名,都经由他一手运作。能够如愿以偿,他当然比谁都激动。有人说,那老师,这刊名,是靠你这个著名白族作家的名气,要来的。他说,不是靠我的名气,而是靠苍山、洱海,靠白族人民的名声要来的。我们要珍惜茅盾先生的题字,要加倍努力,创作出无愧于茅盾先生“把《洱海》愈办愈好!”的作品来!
与会者群情激动,纷纷表示,一定要进一步深人生活,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来,以此回报茅盾先生对《洱海》的厚爱!
六
1979年5月,我国自卫还击战取得重大胜利,中国军人将凯旋而归。为了歌颂中国军队在前线取得的胜利。《洱海》第6期推出《热烈欢呼自卫还击战重大胜利特刊》。
特刊刊登了解放军前线歌舞团、上世纪70年代当红诗人任红举的诗歌《东线西线祝捷歌》、《英雄们归来了》,刊登了白族作家那家伦的散文《战火燃烧的诗花》,刊登了白族作家彭怀仁的小说《无畏的战士》,刊登了白族作家杨恒灿的散文《意外的收获》,刊登了著名画家杨晓东的版画《欢迎您,最可爱的人》。小报图文并茂,套红印刷。
这期特刊,是《洱海》编辑室为了配合宣传自卫还击战的重大胜利,而约请作者写的专稿。从组稿到编稿,前后三天时间,真是逼着牯子下儿。《洱海》编辑室的编辑给作者下死命令,一定要按时交稿。无论如何都得写出歌颂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的文章来。应邀写稿的作者们,接到任务后,重任在肩。大都认为:歌颂在前线浴血奋战的中国军人,是文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写不写,是态度问题;写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于是,咬咬牙,挑灯夜战,硬着头皮,咬断笔杆,终于写出了各自的文学作品,交到编辑室,完成了这个硬任务。
报纸很快就编好,然后,交印刷厂排字、印刷。印刷厂工人,加班加点印出小报。离大理驻军参加自卫还击战凯旋归来的日子还有几天。
欢迎参加自卫还击战部队凯旋归来那天,下关市民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安排下,排列在下关的主要街道上,夹道欢迎从前线归来、劳苦功高的解放军英雄,军车、炮车,雄赳赳驶来,小学生纷纷上前,给解放军叔叔献花,工人老大哥紧紧握着子弟兵的手,“向解放军英雄们学习、致敬!”“亲人啊!你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口号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到处是感人至深的军民鱼水情场面。
第6期《洱海》,成了下关地区业余文学创作者送给凯旋归来的解放指战员的一份小礼。
七
《洱海》虽然是一张县级文艺小报,它是下关市文学创作者的园地,是初学写作者的练兵场。但它也博采众长、广纳百家。
下关的作者们,为有了一块自己的写作阵地而高兴万分。他们纷纷把自己的习作投寄给《洱海》,想到那儿寻一小块栖身之所。有基础的人,如作家张焰铎、舒宗范、谢本良、杨水清,很快就在《洱海》亮相。稍后一点亮相的有何百源、吴崇仁、邓英鹦、曹高德。还有一些刚学步的新作者,他们一次、一次地给洱海投稿,《洱海》编辑室的老师们,看了他们的稿子后,把他们请到文化站,让他们参加文学小组活动,一起学习,帮助他们提高写作技能。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反复修改作品,不少新作者的文章,也陆续在《洱海》露面。既扩大了《洱海》的作者队伍,又使新作者看见了黎明的曙光,也成为他们跨上文学舢板的跳板。而今,不少作者,依然在文学的崎岖小路上行走,矢志不移。
不少省内知名作家都在《洱海》上发表过作品,我州著名军旅作家樊斌,在《洱海》连载过中篇小说《鲜花湮没的罪人》,我州安徽籍作家杨美清发表过散文《怀念张明德和尚景波》、《洱海,灿烂的明珠》,著名诗人周良沛发表过诗歌《金桥玉路》,白族作家杨伊达发表过短篇小说《归来》,纳西族作家戈阿干发表过短篇小说《天神岩》,回族作家马瑞麟发表过散文《歌声的怀念》,著名白族作家、云南人民出版社《山茶》主编赵橹的散文《玉白菜》,也发表在《洱海》上,更为可喜的是:发表于《洱海》的《玉白菜》,被收入2014年由中国作家协会编的《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白族卷)》,让《洱海》小报传扬四海,名传千古!
此外,我省作家刘允裎、王雨谷、骆虢、凝溪也都先后在《洱海》发表过作品。《洱海》还发表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赵衍荪的《浅谈白族语言及其他》,湖南作家鲁之洛游大理时写下的散文《洱海恋》,也在《洱海》问世。
值得一提的是:《洱海》还连载过原中央民族学院吴重阳、陶立瑜撰写的《云南少数民族现代作家传略》,系统地介绍了白族作家晓雪、杨苏、张长、杨明、那家伦等。
八
在《洱海》发表处女作,又从《洱海》扬帆,驶向内地江河的作者,不计其数。翻开《洱海》,我看见一张张熟悉的笑脸。
1979年春天,白族作家杨腾霄,看到新创刊的《洱海》后,立即产生了创作冲动。于是,他创作了一篇寓言,投寄给《洱海》。寓言在《洱海》见报后,他便踏上了文学创作的崎岖小路。在白族作家那家伦的指导下,他慢慢从《洱海》游向省内外报刊,发表了不少小说、散文,出版了小说集《云在洱海上空》,成为我州活跃的白族作家之一。至今,他说起《洱海》小报来,口若悬河,感慨涕零。他说,没有《洱海》,就没有他的今天!
那个曾经在大理学院中文系任教的大理女作家邓英鹦,从下关职工业余文学创作小组,到《洱海》创刊,以致《洱海》成长的年月,她都与《洱海》相伴相守。她在《洱海》上发过小说、散文,是一位年纪轻、也有才气的女作者。她十分善于学习,虚心向别人求教。作品写了改,改了再写,不厌其烦。写字一丝不苟,像是写书法作品那样认真。
在学习写作的同时,她不忘复习功课,准备应考升学,功夫不负有心人,恢复高考后,邓英鹦成了第一批考进下关师专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那时,原在大理师范任教的谢本良老师,已调到下关师专担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写作课教师。在下关文学小组时,谢老师就与邓英鹦熟识。于是,邓英鹦成了谢老师的高足。理所当然地成为谢老师倡导、扶持的学生文学小组“洱海文学社”的头儿,也是学生中发表过文学作品的佼佼者。她热心组织文学社的同学创作,并仿效下关文学小组讨论作品的做法,组织学生讨论自己的作品,活跃了文学社的创作活动。经过四年苦读,邓英鹦学习成绩优良,文学创作小有成就,毕业时,留校任教,担任写作课教师。她一边为大理地区培养师资,呕心沥血:一边坚持业余创作。同时,她还继承谢老师扶持学生开展文学创作的好传统,帮助学生修改文章,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使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读书阶段就能在报刊发表作品。这些学生毕业后,成为大理地区文学创作队伍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尽管后来,邓英鹦调离大理,到昆明钢铁公司党委宣传部,从事宣传工作,但她一直坚持业余文学创作,并以丰厚的创作业绩,加入了云南省作家协会。向下关文学小组和《洱海》小报,递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九
2014年7月,《洱海》小报的忠实作者、工人诗人曹高德,带着一叠诗稿,来我家找我。让我帮他挑选一些诗歌,投寄给《大理文化》。因为,他一直用纸、笔写作,没有用电脑,不知道怎样发电子邮件,特来找我咨询。
老曹与我都是在工厂干过苦力的主儿,后来,我在《大理市报》当副刊编辑,他是我们报纸的铁杆作者,我俩相交甚好,经常在一起切磋文字。他的诗,朴实无华,而又韵味十足。语言粗犷、豪迈,掷地有声。说实话,我一向喜欢他的诗歌。在我当小报编辑时,他的诗,我编得较多。
我接过他的诗稿,说,你拿着纸稿,到电脑室,请人打好后,买个U盘,然后,拷在U盘上,再带着U盘,去杂志社,请诗歌编辑拷在他的电脑上,就行了。
老曹看着我,笑了笑,说:“阿彭耶,真不好意思,跟不上趟了。又不甘心,还想写,更想发表出来。”
望着他满头卷曲、雪白的头发,我顿生爱意。写到这份上,真不容易!70岁的人了,还能写出激情满怀的诗篇,不简单!于是,我翻阅了他的诗稿,选了两组诗稿,又吹捧了他几句,可谓互相吹捧,共同提高。
他笑眯眯地与我告别,然后,去电脑室请人打稿子。
第二天,他打电话告诉我,他昨天打好稿子,拷在U盘上,当即就拿着U盘,去《大理文化》编辑部,把U盘交给诗歌编辑、彝族作家李智红,李智红立马把他的诗拷到电脑上。不知能不能用出来。电脑确实方便,看来,换笔的人真省事!
放下电话,我翻出了当年的《洱海》小报,老曹在《洱海》上发表的诗歌较多,他是众多作者中,在《洱海》游来游去的一个,后来,他游出《洱海》,游进诗歌的海洋,发表了数百首诗歌,先后出版了诗集:《白山茶》、《二重奏》、《崇山净水厚人情》,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我和白族诗人杨黎明介绍他加入了云南省作家协会。
2014年12月初,我在第12期《大理文化》上,看到老曹题为《风光》的组诗发表了,一共有12首,高兴之余,我立即拨通他的电话,把这喜讯告诉他。我还没有说完,就听到他会心的笑声。这是70岁诗人曹高德心花的绽放!
十
说到《洱海》的前前后后,我的眼前,便浮现出87岁高龄的壮族作家刘傅森老师的灿烂笑脸。刘傅森老师从参加下关文学小组活动至今,42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文学翅膀的煽动。
刘傅森老师是云南解放之后不久,被派到大理工作的。他长期在文化部门从事文化工作,为繁荣大理地区的白族文化,做出了应有贡献。同时,他还创作、发表了大量反映白族人们建设祖国边疆的文学作品。
1973年夏天,他来参加文学小组学习时,已在省级报刊上发表过不少作品。但是,他非常谦虚,不以能人姿态出现,不以长者自居。依然一副学生模样,认认真真学习。那时,他正值中年,精力旺盛,一直坚持读书、写作,他博览群书,他读过的书,说出书名来,我连听都没有听过。他虽发表过不少文章,但他从不张扬。有人读了他的文章后,对他说,刘老师,你的文章很老辣。他淡淡一笑,说,一般一般,我也是才学写不久。有人发表了文章后,常常在小组里夸夸其谈,他仍旧耐心地听别人讲完。其实,在小组里,他属于文学前辈,写作经历长,发表作品也多,他完全可以大讲特讲,但他,除了在讨论作品时给别人出个点子外,从不标榜自己。
刘老师对于一些初学写作的人,满腔热情地帮扶,只要你有一小点进步,他都及时给以鼓励,巴望初学者早日上路。我就是在他的指导下,逐渐学步,最终走上文学之路的。经过练笔3年之后,我在《云南文艺》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这篇小说的发表,增强了我继续在文学小路上前行的信心。
42年来,刘傅森老师一直辛勤笔耕,常常有文章见诸报刊。26年前,他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之后,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当年的学友,花甲之后,是他第一个吃螃蟹、率先换笔,用电脑写作。
这些年来,刘傅森老师写了不少大理旧貌换新颜的文章,从他的文章里,听得见白族人民合着时代节拍前进的槖槖足音。他是1956年11月22日,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的众多见证人之一,他参加了自治州的筹建,对成立白族自治州的往事,如数家珍。他从事多年的文化工作,多次接待过文化名人、专家,我曾经读过他发表在1999年第9期《民族文学》上的《诗人的足迹一——怀念田间》的美文,他在文章中,详尽地讲述了诗人田间到大理的始末。我还在2011年第12期《大理文化》上读到他发表的《岁月如歌——记忆中的徐嘉瑞老人》,得知省文化部门老领导徐嘉瑞,对全省文化工作呕心沥血的往事。他还是一位潜心研究白族历史文化的学者。他在2007年第一期《大理文化》发表的《关于白族扎染的文化思考》,在全国引起普遍关注,不少网站争相转载。他还在2014年第7期《大理文化》上,以《大理天歌之忆》为题,追溯了1955年春夏之交,他第一次采访白族民间老艺人杨汉的往事,彰显了杨汉先生毕生为传承白族民歌,耗尽心血的奉献精神,唱出了一曲清新的天歌。
更让人欣喜的是:2009年9月17日,笔耕60年、81岁高龄的刘傅森老师,被省作协批准加入云南省作家协会。2013年,我又闻听到刘傅森老师两本散文集《彩云之南》、《洱海月色》相继出版的消息。
近几年来,刘老师年年有作品发表在《大理文化》上,《梦断鸡足山》、《滇缅公路的记忆》、《再走滇缅公路》、《步行到大理》等,都是脍炙人口的篇章。
“打虎还靠亲兄弟,上阵全凭父子兵”,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刘老师还影响、培养了儿子、影视剧作家刘苹,刘苹写过电影《血魂》、写过电视剧《阿惠》,《艾伦在大理》等多部作品。他的作品,在全国播出后,引起极大反响,为大理地区扬了名,争了光。
刘家父子二人,不愧是闪烁在大理文学天空里的两颗星星。
十一
在创办《洱海》小报的过程中,编辑室的老师们十分热爱自己的事业,十分珍惜这张来之不易的《洱海》小报。为小报倾注了不少心血。他们认认真真阅读来稿,仔仔细细挑选好稿,字斟句酌地编辑文稿。他们还开门办刊,请作者到文化站,不厌其烦地与作者交流,给作者出主意,帮助作者改好稿子。凡是能用的稿件,他们都争取编上。毕竟是自己的小报,应该让自己人一展身手。稿子排好版后,他们带着稿件和划版纸,走路到位于下关刘家营的下关市印刷厂,交到排字车间。那时,还是铅印。排字工人,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拣。一行、一行地排字,排完版后,他们又到印刷厂排字车间校对。校对完了,经他们签字后,才送印刷车间印刷。校对之后,他们又走路回单位。
之后,接到印刷厂印完报纸的电话,他们又走路去取回报纸,然后,分发到市属各单位。尽管,工作十分琐碎,但他们总是默默无闻地做着重复、枯燥的工作,为他人做嫁衣裳。上一期出版后,又忙着下一期的编辑工作。
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洱海》的作者们,经过《洱海》的演练之后,一天天熟悉水性,愈来愈游得远。大多在省内外办刊发表了一定数量的散文、小说、诗歌。除那家伦外,小有成就的张焰铎、袁冬苇、赵守值、杨腾霄、彭怀仁,都有作品入选多年后出版的《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白族卷)》。《洱海》编辑室的老师们当年的心血,没有白花!
《洱海》初创时期的热心作者们,大都没有辜负《洱海》编辑老师的期望,也没有辜负中国文坛泰斗茅盾先生:“把《洱海》愈办愈好!”的嘱托。他们,一天天长大,一步步登高,至今还在不断呼吸文学的氧气,至今还在与文学苦苦相伴,恩爱有加。
细细想来,《洱海》是下关业余作者的家,是作者游泳的海,《洱海》编辑室狭窄的办公室里,常常人来人往,谈笑自如;不像当今一些编辑部那样,壁垒森严,让人望而却步,《洱海》,确实为大理地区培养了不少作者,而最初的那些忠实作者,走上合适的岗位后,又带出了一批批新作者,使《洱海》精神四处开花。
正是:《洱海》真如海,活水滚滚来。编辑手记:
《洱海》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由下关文化站创办的一张小报,但它是下关文学创作者的大园地,是初学写作者的“练兵场”。通过彭怀仁先生娓娓道来的叙述,让我们看到了当年一座小城里诸多文学爱好者难能可贵的精神追求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