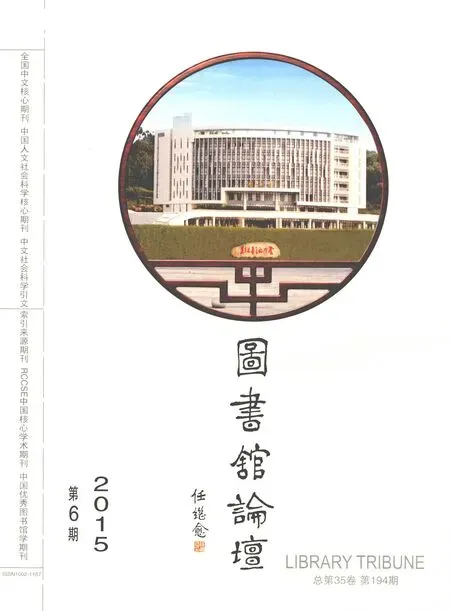美国信息素养标准的全新修订及启示*
彭立伟
美国信息素养标准的全新修订及启示*
彭立伟
信息素养标准是指导信息素养理论和实践的典范。随着信息生态环境的变化和高等教育的变革,2013年美国开始对《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进行全面修订。根据2015年ACRL标准委员会向董事会提交的最终文档——《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对六大信息素养基础性的核心临界概念——“阈值”进行简介,探讨新框架为中国信息素养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启示。
信息素养 信息素养标准 美国
0 引言
2000年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ACRL)颁布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以下简称“旧标准”)具有里程碑意义,不仅影响了美国的信息素养教育,而且被译成多国语言,影响多个国家信息素养标准的制定或实施。随着时代变迁,旧标准难以适应信息生态环境和高等教育环境的变革,2011年ACRL成立工作组讨论是否继续使用该标准;2012年6月发布的评估报告指出现存标准应该被全面修订;2013年3月工作组正式探索新的信息素养标准修订工作;2014年2月、4月、6月、11月分别颁布三个版本《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以下简称“新框架”)修订草案;2015年1月16日ACRL标准委员会向ACRL董事会提交最终文档[1]。全新修订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的颁布反映了美国高等教育界和图书情报界对信息素养教育的最新认知,将对信息素养实践产生很大影响。
1 ACRL信息素养标准修订背景与原因
1.1 信息生态环境的变迁
旧标准颁布之时,信息素养正处于第一代互联网环境中,当时“Google尚是个婴儿,Wikipedia还没有诞生,Twitter远未存在。”[2]进入21世纪,尤其在2004年后,Web2.0极大地改变了人们获取和创造信息的环境,通过提供简单易用的参与工具,用户能方便快捷地创造信息,大学生不再仅仅是信息的消费者,而且成为信息的创造者、共建者和分享者。信息的格式类型也日趋多样化,文本、视觉、听觉、数据等格式类型共存。新的信息创建、组织、传播模式逐渐形成了多样化的信息生态系统,挑战了具有传统信息素养的人的认知,面向第一代互联网的旧标准已难以适应迅速变化的信息生态环境,亟需修改。
1.2 高等教育环境的变革
高等教育环境的变迁对信息素养也形成了挑战。新的教育理论,如社会建构主义和关联主义,逐渐影响了信息素养教育。它们认为,学习并不单纯是由教师向学生传递知识,而是包含创造、交流、反思、情感和批判性思维的过程,其中,教师的角色在于营造积极的学习环境,成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和指导者。整合式、混合式、反思式、协作式学习日益受到提倡。在美国,一些大学生在低年级时组成学习社团,共同学习一系列课程,以培养跨学科的批判性思维和交流技巧;随着开放教育资源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近年来逐渐兴起了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s),混合式学习逐渐成为流行的教学模式[3],“翻转课堂”日益受到欢迎,这一切都影响了美国的高等教育环境。
1.3 互补的多元素养类型
信息素养与其它多种素养具有交叉关系,如媒介素养、视觉素养、数字素养。以往的研究多强调各种素养之间的区别,但近年来学界逐渐扩大信息素养的内涵,认为它包含以上各种素养类型。例如,2007年美国学校图书馆协会(AASL)修订的《21世纪学生信息素养标准》指出:“随着资源和技术的改变,信息素养的内涵逐渐从找到信息的简单定义发展为包含了多元素养,包括数字、视觉、文本和技术素养等。”[4]英国2011年修订的七支柱标准指出“信息素养是一个总称,包含数字、视觉、媒介素养,学术素养,信息处理,信息技术,数据管理等概念。”[5]旧标准注重的是信息素养与信息技术及其它素养之间的区别,与上述标准相比明显滞后。
近年随着信息环境的变革,美国对其它素养标准重新进行修订,除修订《21世纪学生信息素养标准》外,2008年媒介素养中心修订《21世纪媒介素养标准》;同时也出现了新的标准,如2011年ACRL发布《高等教育视觉素养标准》。随着这些标准的修订或颁布,ACRL旧标准如果保持不变,将难以为其它标准提供有效指导。因此,通过全面调研,为了适应迅速变化的高等教育和信息传播环境,扩大信息素养内涵,包含多种素养类型,在借鉴阈值、元素养、跨媒体素养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对原有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
2 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
2.1 信息素养新定义
信息素养的概念自1974年诞生后,关于它的内涵一直存在争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图书馆协会1989年的定义,认为信息素养是指个人“能认识到何时需要信息,并能有效地检索、评估和利用所需的信息的能力”[6],2000年的旧标准对此加以引用,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该定义将信息素养视为包含信息意识、检索、评估和利用的能力谱系,认为信息意识、检索、评估和利用等要素是信息素养中的“不变维度”,具备信息素养需要历经培养信息意识、进行信息检索、对检索信息进行评估和利用的基本流程,而且流程是线性的,不可反复。该定义影响了21世纪之交的众多标准(如美国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英国的《信息素养七支柱标准》和《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信息素养框架:原则、标准及实践》)的二级指标设置。
受社会化媒体、高等教育理论、信息素养理论与实践等最新进展的影响,新框架对信息素养定义进行了扩展,认为:“信息素养是包含一系列能力的整体,包括:反思性发现信息,理解信息如何产生和进行评估,利用信息创建新知识并合乎伦理地参与学习社团。”[7]与旧标准相比,新框架具有一定的活力和灵活性,突破了从具备信息素养的流程的角度对信息素养的界定,更加强调具备信息素养过程中的元认知和情感因素;同时,与强调个人学习的旧标准相比,新框架更加强调学生间的合作学习,认为信息素养是延伸学生学习生涯的杠杆,应与其它学术和社会的学习目标相融合,通过学习社团中的合作学习,促进个人成长。新定义对新框架的结构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
2.2 新框架理论基础
影响新框架的理论与结构的主要概念包括阈值和元素养;阈值由Townsend等研究者引入信息素养研究领域;元素养由Mackey与Jacobson提出。两种理论的主要研究者Townsend和Jacobson都加入了负责新框架修订的任务小组,其中,Jacobson担任小组组长。
2.2.1 阈值
“阈值”原文为“threshold concept”,也可被译为“临界概念”。虽然阈值一词早在21世纪之前已经被应用于学术研究领域,但其重大影响则起源于英国“提升本科生教学环境”的国家项目成果,由Meyer和Land提出,他们认为,阈值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打开以前从未认识到的新的思维方式的入口,引入到某一学科的教学领域,阈值可以被描绘为“核心概念”。阈值有助于形成对事物的新的理解,具有转换性(改变学习者态度或观点)、整体性(将不同概念统一为一体)、不可逆性(一旦被理解就不会忘记)、界限性(确定学科界限)、困惑性(针对学习障碍)等五大特征。为了更好地解释某一学科中的阈值,Meyer和 Land以数学和经济学为例进行了说明[8]。Meyer和Land的研究对其它学科的教学也产生了较大影响,自2003年提出后,已影响到经济、历史、物理、生命科学、第二语言教学等诸多领域。2011年,Townsend等研究者借鉴Meyer和Land的研究成果,将阈值引进信息素养研究领域[9],尝试探索“在过程中理解格式”“权威是建构的和语境化的”“信息是商品”“分清学科主次要资源”“去图书馆”等五大临界概念。
新框架在Townsend等人的研究成果上进一步对信息素养教育领域的阈值进行了探索。新框架认为,虽然信息素养教育领域的阈值比较根深蒂固且难以识别,但是作为学科内最基础性的核心临界概念,通过在行为、认知、元认知、情感等方面的累积训练,可以使学习者达到领悟一个“问题/概念”的临界点,一旦掌握,将改变学习者的态度和观点,达到“恍然大悟”之境。为了更好地使学习者掌握这些核心临界概念,新框架除了对每一个核心临界概念进行详细说明外,还添加了知识实践(knowledge practices)和意向(dispositions)两大指标体系,其中,“知识实践”主要指能提升学习者理解阈值的方式,以及理解阈值后能达到的目标;“意向”侧重于学习中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因素。
2.2.2 元素养
元素养在2011年由Mackey与Jacobson提出[10],并通过召开相关会议、撰写专著、开设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2013年、2015年)等相关活动进行了深化。元素养认为,传统信息素养的界定并没有考虑社会化媒体情境下协作式的知识生产;而新兴素养(如数字、视觉、网络素养等)在确定、获取、评估、整合、运用、理解、生产、协作和共享信息等方面和信息素养具有共同元素,因此,应以信息素养为基本框架,整合多种素养类型,充分考虑学生的信息消费者和创造者角色,构建一个融合知识获取、生产与共享的有机整体,以提升学生在数字时代的批判性思维和协作能力。元素养培养分为行为(强调技巧与能力)、情感(态度)、认知(理解、应用)与元认知(对认知过程的反思)四大目标。新框架借鉴了元素养的一些核心概念,突破了旧标准对认知因素的关注,重点关注信息素养教育中的情感因素和元认知,以培养能适应迅速变化的信息社会中的自主学习者。
2.3 内容框架
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有六大种,每一种框架包含阈值及其阐释、知识实践、意向三大要素(见表1)。阈值部分侧重于探索信息素养教育领域的核心临界概念;知识实践部分强调有助于掌握这些临界概念的行为方式及其理解;意向部分侧重其中的态度和情感。六大信息素养核心临界概念包括“权威是建构的和语境化的”“信息创建是过程性的”“信息具有价值”“研究即探究”“学术即交流”“检索即策略性探索”等基础性概念。由于侧重于核心临界概念的掌握,而非注重掌握信息素养的具体流程,新框架明显不同于旧标准的“决定所需信息的性质和范围”“有效地获取需要的信息”“评估信息”“利用信息实现特定目的”“熟悉相关的经济、法律和社会问题”五大体系结构。新框架的六大临界概念之间没有主次和先后顺序之分,而是互有交叉之处。为了对不同层次的学习者提供有效指导,新框架将学习者分为“初学者”与“专家”两个层次。其中初学者指开始了解这些核心临界概念的学习者,而专家指完全掌握了核心概念后的有经验的研究者。

表1 美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
2.3.1 权威是建构的和语境化的
Web2.0颠覆了自上而下的互联网体系,大量的用户生产的信息内容由于没有传统的审核机制,大大侵蚀了原来比较静态的、稳固的信息环境,如何判断信息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并确定研究领域的权威,成为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一大挑战。在新框架看来,信息源反映了创建者的专业知识和可靠性,对信息源是否权威的判断需要理解权威是建构的,又是语境化的。
新框架认为,权威是建构的,它的产生往往会受到世界观、性别、文化和学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某一学科经过长期发展可能已经确认了一些比较权威的学者和出版物,但是这些权威在其它学科领域内可能并不会得到高度认可;再如,某些宗教领袖或权威出版物可能会受到一些宗教团体的重视,但可能会受到其它宗教团体的排斥。权威又是语境化的,不同的信息需求对信息权威性的要求程度也有所不同。例如,出去野餐前并不需要最前沿的气象学权威信息。
初学者可能会凭借一些表面特征(如出版物类型或作者声誉)对权威性进行判断,但专家能认识到权威是由历史、文化、学科、需求等建构的社会化产物,对权威持怀疑态度,能识别信息源中的思想流派或特定的学科范式,并接受新的观念和思想流派。理解“权威是建构的”能够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在判断权威时考虑到自己的偏见,通过对起源、语境以及信息需求是否适合等相关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实现由初学者向专家的转化。
2.3.2 信息创建是过程性的
传统上对信息源价值的判断一般依赖于最终的信息产品,经过同行评审的图书和期刊文章往往被认为优于用户自主创造的网络资源。在格式类型上,新兴媒体的信息由于未经过滤和编辑,往往被排斥在权威的信息源之外(这可见于国内一些核心刊物的征稿要求和知名专家的论断中)。虽然旧标准指出:“找出以多种格式(如多媒体、数据库、网页、数据、声像和书籍)存在的潜在资源的价值和不同之处”[9],但旧标准关注的主要是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的最终信息产品。
新框架认为信息创建是过程性的。尽管信息产品最终格式有所不同,但创建的目的都是为了传达某种消息,并通过信息传播机制共享;信息产品的研究、创建、修改和传播过程并非线性的,而是可以反复、交替进行的,最终的信息产品是信息创建过程的结果。因此,对信息价值的评价应该既要考虑最终产品,又要考虑信息创建的过程。
对这一概念的理解能使初学者摆脱单纯格式类型的限制,认识到信息创建过程的重要性,以及为满足信息需求而要做出的复杂选择;专家能区分某一领域内新旧信息创建过程和传播模式之间的不同,能识别静态和动态的格式信息,接受以新兴格式呈现的信息的模糊性,认识到语境对信息价值的影响,参照信息创造过程中的某些相关元素(如出版前后的修改和评论过程,维基百科中的发帖作者、历史、引用等信息)对信息价值做出判断。
2.3.3 信息具有价值
社会化媒体时代存在大量免费信息和相关服务,而搜索引擎及移动技术的发展正在使信息获取变得越来越容易,“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获取所需要的任何知识”正在日益成为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初学者在遭遇有关引用、抄袭和知识产权等相关问题时,可能会产生困惑。
为解决这种困惑,新框架提出“信息具有价值”的核心临界概念,认为信息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包括作为商品、教育手段,以及作为世界沟通和理解方式的价值。法律、社会经济利益等因素会影响信息的生产和传播。
在信息素养教学中引入“信息具有价值”的核心概念,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引用、版权法、合理使用、开放获取和知识产权法”等相关的问题。它能使初学者了解有关引用和知识产权等背后的原因,经过一系列知识实践后,成为有经验的专家,从而在社团活动中能了解相应的权利和责任,尊重他人的原始思想,同时理解“在何时抗议或遵守与信息价值相关的当今法律、经济和社会实践方面,个人应当做出明智的决定。”[11]
2.3.4 研究即探究
研究是可以重复的。提出复杂的或新的问题,找出答案,可答案往往又发展为新问题,或触发某一领域内的一系列探究。初学者逐渐掌握探究的策略,能运用越来越全面的调研方法,从而成为熟练掌握信息素养技能的专家。专家能够将研究视为一种探索的过程,根据某一学科或跨学科领域尚未解决的难题或可能矛盾的信息提出自己的研究问题,确定探究调查的范围,概括基本现状,询问相关问题,利用多种研究方法,通过与同行的合作与交流,进行不同观点的辩论和对话,探索更加多样化的观点。
2.3.5 学术即交流
某一专业领域内的学术研究是长期观念形成、辩论和权衡的话语实践。当今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微学术逐渐成为学术研究领域的一大景观。在某一专业领域内,研究者或相关人士等通过竞争性观点的解释、交流、对话,产生新见解,发现新知识。以社交媒体为主的新的学术交流机制为不同层次研究者的对话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初学者尽管也能加入学术交流中,但已经建立的权威体系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参与能力。专家在进行学术交流时,不是寻找问题的明确答案,而是倾向于寻求多元化的观点,通过了解学术对话的语境和过程,对某一领域的学术价值做出判断。
2.3.6 检索即策略性探索
信息检索经常以提问开始,包括调查、发现、检索以及获取这些资源等环节。信息检索是可以重复的,并具备一定的灵活性,能够寻求替代途径。信息检索是语境化的,受到搜索者认知、情感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初学者搜索的范围较小,而专家搜索的范围更广、更深;初学者利用的检索策略较少,而专家则能根据信息需求的类型、范围和语境从众多策略中选择合适的检索策略。
3 引进新框架,建构中国本土化的信息素养框架体系
3.1 修订过程科学化、协作化
信息素养标准是指导一个国家、区域、学校信息素养教育的规范体系,其制定过程须科学、规范。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修订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继承了《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的规范化和严谨性,为国内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启发。
新框架修订过程大体可分为两大阶段:修订前(2011年7月-2013年3月)和修订中(2013年3月-2015年)。2011年7月ACRL成立任务组,评估旧标准到2016年是否仍能使用;2012年6月评估报告发布,指出指导理念仍然适用,但需要大量修改内容;2013年3月任务组开始全面修订新框架。任务组组长由Gibson和Jacobson担任,成员来自从事信息素养教育的图书馆界、高等教育界以及其他领域。在修订过程中,任务组利用ALA和ACRL所建立的有效交流渠道,向单位成员和个人进行广泛咨询,约有1300人参加网上听证会;同时还和非图书情报领域引用旧标准的60位研究人员进行广泛联系。通过网上听证会、个人访谈、邮件、社会化媒体(博客、微博)等多种方式,任务组就标准的修订、三版草案进行了广泛的专家论证和讨论,并将任务过程及相关文档通过网站进行公示[12]。整体而言,新框架制定过程严谨、规范化、协作化,能够汇集当前美国研究领域对信息素养的最先进的集体意识和认知,有利于新框架成为具有前瞻性的纲领文件。相比较而言,国内虽然有部分学者和机构进行了信息素养标准的相关研究,但是由于没有专门的机构进行规范化的信息素养标准研制工作,因此,严重影响了标准的权威性及其普及推广[13]。
3.2 充分利用新框架,建构本土化信息素养标准
新框架通过对信息素养基础性、核心、临界概念的探索,创新性地改革了旧标准的结构化体系,分为“阈值-知识实践-意向”三大指标体系。不同于旧标准的“标准大类-表现指标-学习成果”三级指标体系,新框架三大指标体系并不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层级指标系统,而是各有侧重。“阈值”侧重于对核心临界概念的阐释。“知识实践”强调能提升学习者理解阈值的方式,以及理解阈值后能达到的目标,提出知识实践的目的不是为了使学习者单纯地掌握一些技能,而是通过掌握一些基础性的临界概念,革命性地改变原有观念,产生新知识。“意向”包含学习中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因素,除认知因素外,学习过程中的兴趣、情感和态度会影响到学习效果,该指标的设置不仅有利于教师设置学习目标,而且有助于学生对新概念的态度和感情的自我感知,而同学之间的交流和分享,可能还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自我反思能力和元认知[14]。旧标准主要关注行为和认知能力的培养,新框架则强调应该充分发挥情感因素在学生信息素养学习中的作用。国内的信息素养教育实践虽然也重视情感因素,但如何对情感因素进行测评,在国内的信息素养研究文献中尚未见详细的说明。未来可参照新框架的情感指标体系,在信息素养测评时,加入科学、规范的情感评价指标,通过强调情感因素,提升学生信息素养。
虽然新框架面对的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信息环境,但是,由于该框架主要针对的是一些信息素养的基础性核心概念,而基础性核心概念在一个学科的学科体系中,往往都是相通的。在当前国内尚没有权威的、更新的信息素养标准体系的情况下,中国信息素养教育领域可参考和借鉴美国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开展信息素养教育及其标准制定的相关工作:在宏观层面,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和中国图书馆学会可以借鉴新框架及其修订过程,在国内已有研究基础上,展开国内信息素养标准的制定工作;在中观层面,一些区域性组织机构或学科机构可以借鉴新框架,开展区域或学科信息素养标准的研究;在微观层面,一些高校可参照新框架制定本校的信息素养课程目标、学习指南,由于新框架没有具体的学习任务模块,可以根据学校具体情况,制定适合掌握相关核心临界概念的学习任务,并召集信息素养教师、专业教师、技术人员以及管理人员召开研讨会,就教学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及有关改革进行探讨。
4 结语
与《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相比,修订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更新了信息素养内涵,阈值的引进革新了信息素养框架的体系结构,突破了格式类型的限制,实现了多元素养的融合。新框架代表美国图书馆界和教育界对信息素养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认知,为我国信息素养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提供了较好的借鉴与启发。如何借鉴新框架全面修订的过程和成果,建构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中国本土化的信息素养框架和标准,成为当前国内信息素养理论和实践研究需要思考的一大问题。
[1][7][11]Framework forInformation LiteracyforHigherEducation[EB/OL].[2015-01-20].http://acrl.ala.org/ilstandards/.
[2]BanksM.Time For aParadigm Shift[J].Communications inInformationLiteracy,2013,7(2):184-187.
[3]FrameworkforInformationLiteracyforHigherEducation [EB/OL].[2015-01-20].http://acrl.ala.org/ilstandards/wp-content/uploads/2014/02/Framework-for-IL-for-HE-Draft-1-Part-1.pdf.
[4]American Association ofSchool Librarians.Standardsfor the 21st Century Learner[EB/OL].[2015-01-20].http://www.ala.org/aasl/guidelinesandStandards/learning-Standards/Standards.
[5]Society ofCollege,National,and University Libraries. SCONUL Seven Pillar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Core Model for Higher Education[EB/OL].[2015-01-20]. www.sconul.ac.uk/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oremodel.pdf.
[6]A ProgressReport on Information Literacy:An Update on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Presidential 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Literacy:Final Report[EB/OL]. [2015-01-20].http://www.ala.org/acrl/publications/ whitepapers/progressreport.
[8]Meyer J,Land R.Threshold conceptsand troublesome knowledge:linkages to ways of thinking and practising within the disciplines[M].Edinburgh:University of Edinburgh,2003.
[9]Townsend L,Brunetti K,Hofer A R.Threshold conceptsandinformationliteracy[J].Portal:Librariesandthe Academy,2011,11(3):853-869.
[10]Mackey T.P.,Jacobson,T.E.Refram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as Metaliteraly[J].College&Research Libriaries,2011(1):62-78.
[12]ACRL.About The Revision Process[EB/OL].[2015-01-20].http://acrl.ala.org/ilstandards/?page_id=17.
[13]马艳霞.信息素养评价标准研究[J].情报资料工作,2010(3):102-106.
[14]Framework for Information Literacy for Higher Education Draft 2[EB/OL].[2015-01-20].http://acrl.ala. org/ilstandards/wp-content/uploads/2014/02/Framework-for-IL-for-HE-Draft-2.pdf.
The Extensive Revision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Competency Standards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 and Enlightenment
PENGLi-wei
Information literacy standards provide frameworks for assessing the individual information literacy.With the rapidly changing higher education environment and the dynamic information ecosystem,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Competency Standards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 had been extensively revised.In January 16,2015,the ACRL Standards Committee submitted Information Literacy Framework for Higher Education to ACRL Board of Directors.Based on this document,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six threshold concepts to China,and explores the enlightenment which the new framework brings for Chinese information literacy instruction.
information literacy;information literacy standards;America
格式 彭立伟.美国信息素养标准的全新修订及启示[J].图书馆论坛,2015(6):109-116.
彭立伟(1980-),女,硕士,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
2015-01-28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青年课题“大数据时代高校师生个性化信息素养教育研究”(项目编号:EIA130418)和天津师范大学教学改革项目“混合式信息素养教育研究”(项目编号:2013039)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