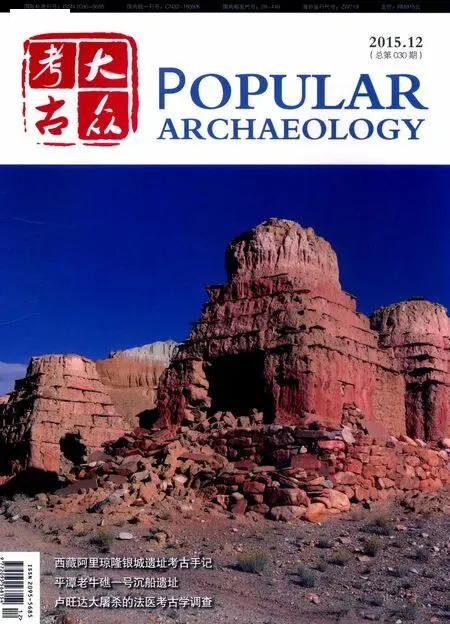考古学中发现的有趣的东西方不同文明模式
在 考古学语义中,“文明”即国家,文明的诞生就是国家的诞生,正如恩格斯所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在考古学上,一般把金属工具、文字和城市的出现视为国家或文明出现的典型标志。人类迄今走过长达数百万年的历程,文明的出现所占不过5000多年,可以说文明或国家是人类文化发展到很高阶段的产物。
根据经典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国家的诞生需要超越“石器“阶段的新型生产力作为基础,这就是使用青铜工具时代的到来;文字的出现也代表着一种知识性生产力的诞生;而城市作为新型生产力的集聚中心和文明治理中心,往往会作为国家的都城而出现。5000 多年前诞生于尼罗河地区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4500 年前诞生于印度河谷的哈拉帕文明以及4000 年前出现于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等,几乎都有青铜冶铸业及青铜工具、文字和堪称发达的城市中心。环地中海的几个古老原生文明之诞生,青铜、文字等新生产力发挥了为文明奠基的作用。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东亚,距今5000~4500 年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出现了最早的文明,苏秉琦先生称之为“古国时代”,严文明先生称之为“龙山时代”,还有学者采用《史记》的说法,称之为“五帝时代”、“万邦时代”等等。考古学揭示出的中国早期“文明”的突出标志包括不同规模或等级的城的出现,以及祭坛、贵族墓地和贵族阶层占有的表示“礼”制的精美玉器,精致陶器等;文字或已经诞生,在山东、浙江、江苏、山西等“龙山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极少量刻、写在陶器上的文字,当然它们还远远不是一种普遍的书写工具;青铜生产工具则几乎无一发现,而且即使到了夏、商王朝时期——可称之“方国时代”,青铜铸造的对象也不是生产工具,而是多用于构建国家权力符号系统的青铜礼器,其主要生产工具主要还是石器。这是一种让人深思的“文明模式”,或可称之为“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文明模式,即先行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以国家为标志的文明形态——通过国家制度进行社会力量的动员和组织,以推动新生产力的发生和发展。这样的一种文明模式,在此后的中国文明进程中一再展现出其鲜明的特色。如西周“王国时代”,新的以“铁器”为代表的新生产力尚未诞生,但更先进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社会已经建立,通过这种制度,在广大地域内实现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统一。新的社会组织形态极大推动了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周王统治下的各诸侯国几乎都实现了经济上的飞跃,最终创造出春秋时代“百家争鸣”的文化奇观,实现了中国“原典时代”的非凡创造,同时也孕育出了新的生产力阶段——战国开始的“铁器时代”。考古实证材料告诉我们,以先进的生产关系构建起“文明”共同体,进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甚至是东亚古代文明的重要模式。从全球视野下观察,考古学揭示的不同的文明模式、不同文明的动力系统和要素构成,为我们探讨人类文明多样性提供了独特的认知资料。
当然,更为深层的问题就是:上述两种不同的文明模式为什么会出现?又各自有着什么样的文明理念?它们在发展进程中面对的挑战存在什么差异性?它们各自又存在什么样的运动规律和运动结果?这些都是给考古等领域学者提出的更加有意思的话题。如果从总体特征上而言,环地中海诸古代文明更重工具、物质、战争和“神”;而中国古代文明更重制度、精神、协和与“人”。美国学者斯波德告诉我们:苏美尔城邦国家成就非凡,但是它们的成绩往往是以战争为代价,“战争特别具有毁灭性,因为国王和战士都相信,自己在为神而战”。而在东亚,不是说没有古国之间的争战,否则不会发现这么多龙山时代的防御城市,但是比之环地中海区域,中国早期古国文明更重不同文明间的“协和”共处,以德服人。《史记·五帝本纪》记述文明初起时,“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黄帝能“修德振兵”,促使“诸侯咸来宾从”局面的出现;尧帝时,继承黄帝之策,使“百姓昭明,合和万国”;至帝舜,修五礼五玉,使“百姓亲和”,“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大禹执政时,于涂山会天下诸侯,“执玉帛者万国”,九州之内“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其职”。至夏、商及西周的“王国”时期,虽然征战乃存,但和合、协同的理念始终占主流,最终乃至形成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
当然,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文明,不同的文明模式各有优点和不足,它们的关系应该是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彼此尊重,和平发展。可以说,通过考古学揭示的人类原生文明的不同模式,能够让我们更多地去思考人类不同文明的经验和教训,以更好地面对今天与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