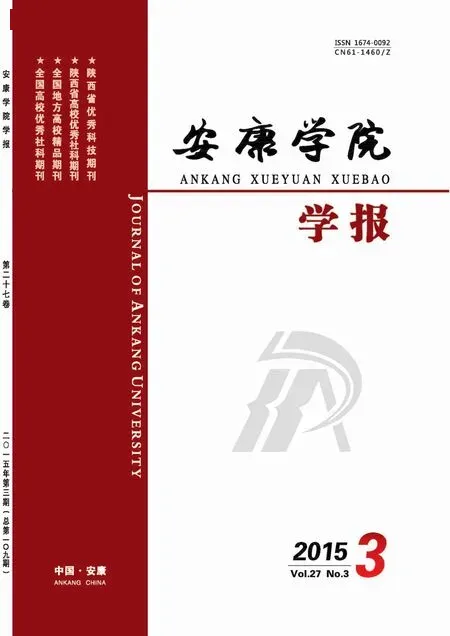“乡土中国”的家文化考察——以《家》和《白鹿原》为例
周龙田
(安康学院 中文系,陕西 安康 725000)
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中,与推翻旧政权相伴随的是推翻支撑旧政权的文化,而旧文化的罪恶就是对青年人生命价值的扼杀。青年人是革命的主角,是未来的新人,扼杀青年人的一切制度文化都要打倒铲除,“家”由此变成了封建思想文化的符号而被坚决批判。革命成功以后,当革命理论(意识形态)无法产生效力时,出现了替代品,即中国传统文化。但是这种替代是无效的、可笑的。从巴金的《家》对“家”的批判到陈忠实的《白鹿原》对“家”的肯定,显示了历史和现实的悖论,展现了“乡土中国”精神结构的变迁。
一
五四文学革命是一场思想革命,即引进西方思想文化改造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五四革命的先驱者要用民主与科学来打倒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居于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使中国向现代转型。要实现这一终极目标或者宏大理想,就要破坏一个旧世界创建一个新世界,即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中国。要完成这一革命目标,就要彻底否定支撑封建王朝的各种社会制度和文化力量,这就是鲁迅彻底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的历史意义。而巴金的《家》直接对封建社会的微缩社会“家庭”予以根本性地否定和批判,他的历史价值值得肯定。吴虞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中说:“推而广之,如《大戴记》所言,‘居处不住,非孝也,侍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盖孝之范围,无所不包,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虽胶固而不可以分析。而君主制度所以利用家族制度之故,则又以孔子之言最为切实。孔子曰:‘孝悌也者,为人之本。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期于消弭犯上作乱之法,惟持孝悌以收其功。”[1]这就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极力批判家族制度的历史文化原因,因为“家(家庭、家族)”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支柱。家文化以孝为本,形成了长幼有序、尊卑贵贱、服从忍让的家族伦理和文化观念,而这种观念与五四启蒙主义重个人的文化是完全对立的。在巴金的《家》中,高老太爷就是这种封建秩序的象征。虽然作者对高老太爷进行了病态化的描写,极力描写他的脸色蜡黄、神态疲倦,有气无力、身体很差,但是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决定着整个家族和家庭成员的命运。他管理整个家庭的信条就是服从,不允许任何人进行反抗,要求家庭成员必须服从家庭利益。这就是典型的封建小朝廷,他直接扼杀了个人的意志和自由选择权,否决了个人的生存权和对个人价值的追求。觉新的痛苦并不完全是婚姻自主权的剥夺,而是敷衍长辈,失去了生存的目标和意义。觉慧的痛苦是在这个家庭里,各种人道主义理想难以实现,个人难以成为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性独立思考能力和主体意识的人,自我价值难以实现。所以,封建家庭所代表的封建专制文化是必须要被打倒的对象。
从上世纪初开始,中国就以现代性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关于现代性有各种解释。“马克斯·韦伯将之解释为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是从中世纪神魅世界中脱魅,由人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人的理性代替超越性的意志,成为最终行动和理性的过程”[2]21。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对青年人提出六个要求:“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3]。这是陈独秀要求的新青年的形象。毫无疑问,独立自主、积极进取、敢于行动、面向世界是成为“新”青年的特征。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强调“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4]47。人的觉醒是国家自强的关键,而人的觉醒首先要“平等自由,凡事是首”,可是“家”的专制权威与此是针锋相对的。“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事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4]58由此可以看到,人的个性、尊严、价值能否实现,人能否主宰自己命运是人觉醒的标志。这是一个从“臣民”“子民”到个人、个体的生成过程。
巴金在《家》中,揭示了封建家庭的罪恶,主要指向其对青年生命力的扼杀——这显然与五四时期对“人”的主体意识进行强化相对立。觉新与瑞珏、梅表姐的爱情悲剧,是封建家长意志、封建伦理、封建习俗对青年人的扼杀,是封建文化对自身社会基础的破坏,是封建肌体的自毁性创伤。觉新的罪责就是对这种“吃人”文化的顺从和妥协,没有任何清醒的反思,更谈不上反抗。觉慧与鸣凤的爱情悲剧,更是揭露了封建文化的残忍性,它让一位16岁的女性失去了生命,让社会最底层的女性难逃被害的厄运。觉慧对这个家庭的不满,并不是与这个家庭有了你死我活的矛盾,即使鸣凤之死,也没有使他对这个家产生强烈的绝望之情。他对大家庭的憎恨首先来自《新青年》这些杂志上宣传的新文化,接着是从自身经验出发对家庭中各个个人平庸生活状态的不满,他看清了爷爷和长辈们及大哥的虚无的面目,看清了亲情背后的人心险恶,看清了这个家制造的人间悲剧,明白了生活在这里,人生的目标和价值将难以实现。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告诉我们,平庸是一种恶,它会导致人性丧失,导致人们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使大众处于一种愚昧状态。它会造成没有人敢于质疑现实生存的逻辑,反而鼓励人们去服从这个现实生存逻辑。由此造成可怕的社会现实,社会不允许公开不服从的现象,价值评估被权力高度垄断,不服从者被边缘化、被唾弃、被遗忘直至最后被消灭。整个社会变成一个病态的社会、专制的社会、暴力的社会和愚昧的社会。在《家》中,觉慧借《前夜》的文字呼唤:“我们是青年人,不是畸人,不是愚人,应当给自己把幸福拿过来。”[5]这种自我意识的养成,以及对人生价值的主动追求,是他走出家庭的真正动力,即理性觉醒的过程。而琴表妹的爱情,就是反抗封建文化、争取个人自由的过程。这也就是作者宣称的“激流”,它是冲垮封建家庭制度的激流,它不是“春梦”,是可以实现的,因而是一种反封建的革命行为。
二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革命的意识形态开始消解。“80年代是一个后神圣化的时代,革命乌托邦开始消解,但现代化意识形态作为新的乌托邦替代出场,社会弥漫在后理想氛围中,无论是思想解放运动,还是新启蒙运动,为现代化理想图景所感召,到处充满着激昂的献身精神和理想主义激情。”[2]33此时,虽然主流意识形态开始解体,但人民大众还沉浸在革命的终极美梦中。
到了20世纪90年代,社会发展有些出人意料,市场经济强烈地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使它强大的控制力被消解。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繁华局面,形成了世俗化、物质化、功利化的社会现实,理想主义革命精神迅速退场,革命者许诺的终极目标看来不可能实现,变成了乌托邦。中国知识界“新左派”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共同趋势,中国的社会改革和市场经济已经是全球市场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开始和解,经济改革压倒了政治(社会)革命。告别革命的时代来临了,就连坚持保守主义的李泽厚也提出来“要改良不要革命”的主张,他说:“如果不改变这种观念,未来的中国也许有更大的灾难。将来可能会有一批人打出革命的旗号以造成巨大的道义压力,结果又使一批有热血的青年和有正义感但缺乏理性的知识分子,以及大批的人民去做牺牲。”[6]李泽厚的观念引起了知识界巨大的争议。不可否认,革命的神话开始终结,革命的神圣光环开始暗淡。为了支撑执政者执政的合理性,巩固革命政权,必须寻找一种替代性文化。但是他们又不愿意抛弃固有的意识形态,接纳自由主义思想,只好向内寻找文化资源,垂而不死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重新焕发出青春的魅力。但儒家文化原是革命的对象,而今却以中国传统文化、新人文主义、国学等好名称悄悄地复活,其背后所隐藏的政治意识形态意图尤为值得思考。经过论争,美国的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认为,“作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的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恰好构成了从‘五四’到‘文革’的一脉相承的谱系。二者不仅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都采取了全盘否定的立场,而且这种立场的形成都是深受源自中国传统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支配之结果。”[2]46在他看来,中国当下现实问题的症结就是原来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些海外汉学家的观点迅速在国内得到了响应,中国传统文化再次被重估,并逐渐成为主流文化,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认同和肯定,西方文化(革命文化)要被中国传统文化替代。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这种文化的替换,其实就是执政者企图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找进行改革的合理性,只不过不是从西方而是从东方,即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陈忠实的《白鹿原》以新历史主义姿态登场,反响巨大。冷静分析其对家族文化的叙述,极具历史文化价值。
陈忠实所做的首先是解构革命历史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主宰白鹿原的不再是神圣的革命理论和革命英雄。在这里,不同党派的革命理想和革命价值不分高低,都是白鹿原上一种破坏性的力量,这就是朱先生总结的“鏊子论”。但它无法摧毁白鹿原上传统家族社会的控制力,无论哪个党派的革命运动都是天上的云,风一吹就散了。鹿子霖虽然是国民政府的基层官员,但是在家庭生活、家长权威、人格魅力、道德品质、行为习惯等各方面,都难以得到好评,甚至作者有意从家庭出身和人格修养上对他进行矮化。这告诉人们,在白鹿原上,鹿子霖代表政权只是表层,白嘉轩才是领袖,他的精神权威具有巨大的威慑力和控制力。而那些革命者是游离在白鹿原上的边缘人,和白鹿原上的民众生活是疏离的,没有有机联系。特别是鹿兆海用掷钱币来决定参加共产党的行为,直接消解了革命信念对革命者的引导作用,革命者对革命信仰的追求变成了游戏。在笔者看来,这就是消解革命的手法。
那么,统治白鹿原民众的力量是什么?是家族制度,是家族文化,是德高望重的族长白嘉轩。他成为一种人格神话,这就是陈忠实所说的“一个民族生存的秘史”。这里,作者特别强调了儒家文化“修身为本”的精神特征,这体现在内与外两个层面上。在自我行为中,白嘉轩身上体现了“仁者爱人”的精神。他把长工鹿三当做自己家里人看待。他以德报怨,营救鹿兆海,原谅黑娃,具有一种侠义精神;他正直无私,严惩白孝文的荒淫行为;他以身作则,一生参加劳动;他严守封建伦理,蔑视女性,修塔镇压小娥;他多次娶妻,传宗接代。当然,白嘉轩的行为并非严格符合儒家的规范,他采用投机取巧的手法,换取别人的风水宝地;他买轧花机自己经商,与儒家重农轻商的理念不合;甚至为了发财,他还在白鹿原上种鸦片。在维护家族和族长的权威时,他还利用祠堂、乡规民约、文化认同(族长权力),来控制人们的生活和行为。可是这样努力维持的结果是什么?白孝文不是认错了吗?可他毫不留情地杀了黑娃。黑娃娶了贤妻,读了圣贤书,进了祠堂,跪拜了祖先,不是照样没有保住自己的性命?
为了解释白鹿原上维系人们生存的传统文化的精神魅力,作者塑造了朱先生的形象。朱先生具有和神一样的主宰力,深受白鹿原上村民的顶礼膜拜,因为他能洞穿现在和未来。对此,与朱先生神会的白嘉轩感受最为深刻:“他敬重姐夫不是把他看作神,也不再看作是一个‘不咋样’的凡夫俗子,而是断定那是一位圣人,而他自己不过是个凡人。圣人能看透凡人隐情隐秘,凡人却看不透圣人的作为;凡人和圣人之间有一层永远无法沟通的天然界隔。”[7]做为圣人的朱先生。一生“爱人”,爱天下的百姓,为天下百姓奔走呼号,具有民本意识。他淡薄名利,从不当官,却常常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天下百姓出头,做到爱人救人,体现了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即世俗的“达则兼济天下”。辛亥革命时,朱先生乾州退兵,使西安免遭涂炭;白鹿原上发生饥荒,朱先生赈灾放粮,救民于危难之中;白鹿原上罂粟盛开,他扶犁铲除,使乡民远离毒害;鹿兆海为国战死,他迎接灵柩,为抗日英雄洒泪;抗日烽火之中,八君子宣言震动全国……生逢乱世的朱先生一介布衣,一生居住在白鹿书院,诵读诗书,但心中却装着天下百姓,始终关注世界的变化,常常有惊人之举,铸就了儒家文化的品牌,实践了“爱人”的哲学[8]134-135。
朱先生终其一生都遵守儒家文化的信条,无论是社会活动、宗教活动、学术活动和日常生活,都做到了表里如一,善始善终。坚持愈久,愈能显出超人的光采,真可谓“砥柱人间是此峰”。白嘉轩兴办学堂,把朱先生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是因为学堂可以教孩子们“敬”和“孝”,“得教他们识字念书晓以礼仪,不定那里头有治国安邦的栋樑之才呢。”朱先生一生的奇事很多,但是持续时间最长的是修县志。修县志是修史的一种,它是圣人们评点历史的手法,是褒贬人物善恶的途径。他聘请白鹿原上八位老先生,闭门修志,把对历史的评说写进县志,把对儒家文化的要义写进历史,让它永远流传。当他完成这一伟大的事业以后,才平静而又心满意足地离开人世。朱先生一生俭朴,死后也简单朴实,不要任何装饰,以期达到与天地无隔,最终完成了对儒家文化的实践[8]135。但是朱先生是一个从社会中心走向边缘的人,他对白鹿原的影响有一个日渐衰竭的过程,他无法改变白鹿原的历史走向。他死时露出的硕大生殖器证明了他是一个凡人,难以挽救儒家文化的衰落。特别是儒家文化无法自律人性之中恶的蔓延,它也无法抵挡人性之中的贪婪、重商、贪利。面对同宗同族的鹿子霖的堕落,白嘉轩只能从出身来解释。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儒家人格文化在社会阶级意识面前,在革命风暴来临时,顿时失去活力,完全被剥离和抛弃。对此,白家轩束手无策。它发生权威时必须要与大儒、玄虚妙论、神秘象征、家族人格融合,而无法成为一种人人信奉的宗教哲学。朱先生的大儒形象是一种人格化的神,由人学而走向玄妙。他的学说与世道日益背离,只能在书院中修志。这明显可以看出他对世事失去了控制,只能退出历史的建构。而作者极力用玄学色彩对他予以强化,表明了作者内心的焦虑和脆弱、渴望和无奈。这一切都表明,以儒学实现人格的完善,用家族权威来维系人际关系是徒劳的。作者脱离政治话语对历史进行阐释,力图用中国本土文化来重构历史记忆,却走到了悬崖边上,这表明作者的历史诉求出现了文化危机,它揭示了当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困境,足以惊醒众人[8]137。
三
“家”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承载着不同的政治文化主题。巴金的“家”孕育着激进的革命潮流,陈忠实的“家”代表着保守主义的思潮。前者固然值得商榷,却是应该走的一条道路,它与现代中国的历史走向一致,是在建构现代性社会的远大目标。要想使中国从传统宗法社会的封闭结构中走出来,融入现代世界,必须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在巴金的《家》中,留下来的是死,走出去的是活。
而后者,在引进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后,为了寻找支撑革命政权的合理性,向传统文化寻找资源,注定是徒劳的。因为这种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理念是完全异质性的。现代社会是一种流动性、陌生化、契约化、分工合作的社会,它要充分发挥人的个体价值,体现个人的生存意义,遵从自由竞争的原则,遵从法治的原则,体现社会发展的公正公平。这和传统文化讲求以个人道德修养为本、以宗族伦理维持社会秩序的“臣民”文化是对立的。白嘉轩和朱先生的最终没落是必然的,是不值得留恋和伤悲的。
[1]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M]//张骏严.新潮:民初时论选.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122.
[2]许纪霖,罗岗.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争论研究[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3]陈独秀.敬告青年[J].新青年,1915(1):15.
[4]鲁迅.文化偏至论[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巴金.家[M]//巴金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02.
[6]刘再复,李泽厚.刘再复李泽厚对话录:告别革命[M].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04:69.
[7]陈忠实.白鹿原[M]//陈忠实小说自选集:长篇卷.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436.
[8]周龙田.文化·人格·困境——对《白鹿原》中儒家文化的重释[J].小说评论,2007(S1):133-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