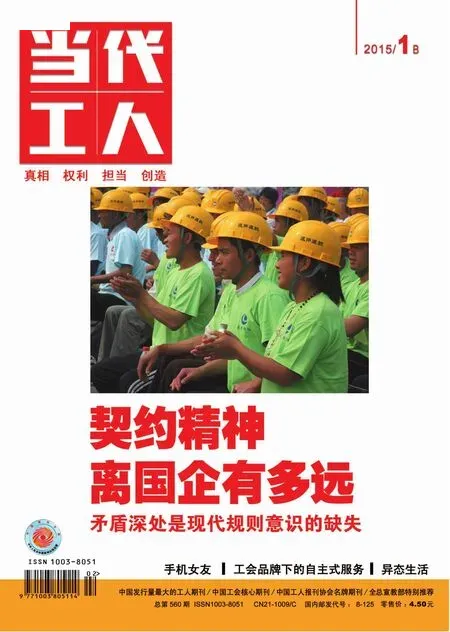“我们命运在人家手里捏着”
文/青阳
“我们命运在人家手里捏着”
文/青阳
毁约 企业放弃对职工保障的责任与义务,职工则选择法律或上访等手段进行自济,这种博弈即是约定毁弃后的恶果。现代企业市场契约精神的根基与前提是法治,而许多老国企在发展和转型中恰恰有所缺失。若要历史不再重演,企业和职工都需依法定约,依法守约。

原先辉煌的游泳馆,早已破败不堪。
谁也没想到,下岗失业会突然落到自己头上。
2014年5月22日,某电力公司下属工程公司的李全博和工友们接到通知:厂里要破产,准备召开职代会讨论解除劳动合同等事宜。“好好的厂子咋就黄了?电力公司为啥不出面安置咱们?”他们要求厂里给出解释,却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答复。
一场情感与法律、历史与现实的对峙就此展开,至今已经持续了6个月有余。
原本是一家
如果仔细梳理就会发现,电力公司下属工程公司的历史,恰好是国企改革发展的历史。而它所遭遇的问题,也正是国企市场化不充分弊端的后遗症。
李全博告诉记者,工程公司是集体企业,从建厂之日起就是为电厂服务的。“1981年因为建电厂占了3000亩土地,政府要求安置失地农民,咱厂子就是这么来的。”
省政府曾为此印发文件,要求电厂和承建电厂的企业安置350名失地农民就业。“咱们电厂安置了250人。”多年后工人们才知道,当年文件要求把他们吸收为全民或集体所有制工人。但因渠道闭塞、政令不通,他们全都是以集体工的身份入厂。
党宝文是最初的250名集体工之一。“大家都开玩笑叫咱们二百五。”跟当时所有集体企业一样,工程公司主要是在电厂的辅助岗位服务。“清理车间、卸煤,去拉煤的火车道口看道闸。”
这些工作大多是与电厂工人一起完成的。党宝文回忆说当年虽然身份有别,但工程公司集体工和电厂全民工都是混岗作业的。
工程公司还有一项主要业务是建房。“电厂的一些厂房、家属楼,都是咱们盖的。”家属楼建成后,其日常的物业维修等也一度由工程公司负责。
工作业务扩展带来工人数量的递增。电厂和工程公司一些职工的家属或子女,开始以各种名义进厂工作。李全博的母亲就是以家属的身份被调到厂里,而他本人则于2000年底被分配入厂。
彼时,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界线混沌不清,工人也自然认为跟电厂是一家人。“咱经理、中层干部都是电厂任命的,不是一家人谁允许他这么干?”

一笔糊涂账
电厂和工程公司的亲密关系第一次被打破,是在1997年。
是年6月,一家香港企业注资,电厂变为合资企业,自此后电厂更名为合资电力公司。不过,工程公司似乎没有搭上这次改制的顺风车。
“我们和多种经营公司都没合进去。”李全博告诉记者,多种经营公司成立晚于工程公司,也曾是电厂下属集体企业。1997年合资时多种经营公司工人找到省里主管部门,要求将他们一起合并。“人家闹完就进去了,据说把我们落下了。”
之所以没有跟着闹,党宝文说那时工人们认为合不合并都无所谓。“对我们来说有班上有钱挣,不都一样吗!”
表面看似乎变化不大。合资电力公司成立后,工程公司人事权依然归其掌控。“我们经理上任,必须电力公司同意才算过关。”李全博向记者出示了一份2007年11月的文件,内容为工程公司经理的任职通知书,“报请(电力)公司经营者集团,总经理同意聘任。”
工人依旧为合资电力公司服务,他们工资少得可怜。“我2000年上班,一个月才开300多元,后来涨到了五六百元。”李全博说,他的工资乘了1.5倍系数,有些工人收入更低。
其实按法律规定,如果工程公司被合并,工人首先要与原集体企业解除劳动关系,获得相应经济补偿后再与合资企业签订新的劳动合同。而原来的集体企业不复存在,工程公司变为合资企业的子公司。
不知何故,合资电力公司未接收工人的劳动关系,却保留了与工程公司的隶属关系。这笔糊涂账为日后的对峙埋下了隐患。
2007年下半年,某大型国企旗下的电力公司出手,购买了合资电力公司港资部分的全部权益。电厂二次易主,更名为目前的辽西某电力公司。
工程公司工人认为,自己的劳动关系就包含在被收购的权益内。“你来了是重新开始,我们应该与电力公司职工享受一样的待遇。”不过,2008年后电力公司职工重新签订了合同。这之后李全博和工友也签过,但他们签订对象还是工程公司。
跟当年合资时类似,工程公司与电力公司的关系依旧暧昧。李全博说,每周电力公司领导班子会议,工程公司经理都列席参会。“十一”的职工活动,两家也一同召开,“活动服都是电力公司发的。”
突然破了产
两家企业的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
2009年前后,电力公司领导希望工程公司与多种经营公司合并,“想让咱归多种经营管。”工程公司拒绝了。
此后,工程公司经理不再列席电力公司的领导会议,双方也开始签订正式的劳务合同。“咱们以前给电力公司卸煤,干多少直接拨钱,后来就是一年一签合同。”
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将二者关系彻底逼上了死角。电力公司所使用的发电机组能耗高、污染重,为配合国家“上大压小”的政策(建设大容量、低消耗、少排放机组的同时,关停一部分小火电机组),2013年8月底其发电机组全部停机。
服务对象停工,工程公司也陷入没活可干的境地。“从2013年8月到现在一直在休息。”李全博说,工人们等着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电力公司工人先闹了起来:电力公司出台退养分流方案,大部分工人将被退养回家,另一部分则被安排到外地进行检修工作。因感觉退养待遇过低,工人们多次上访维权。
工程公司的工人们等着搭顺风车。“经理告诉咱们,等他们闹完了,肯定会妥善安排咱们。”很快,电力公司工人被迫接受了退养分流方案,工程公司这边却迟迟没动静。
2014年3月,公司突然发不出钱了。“经理说连1月和2月开工资的钱都是从电力公司借的。”就这样,断饷两个多月后李全博和工友们接到通知,公司濒临破产,准备召开职代会讨论解除劳动合同等事宜。
职代会上工人们疑虑重重。“厂子怎么就黄了,为什么不公布财务信息?电力公司工人都可以退养分流,为什么不能安置我们?”公司经理避而不谈,只是要求大家投票表决,是否同意解除劳动合同。“你不答疑,我们怎么表决?”双方不欢而散。
这次会上,电力公司老总带着律师出席。面对工人的质疑,他回答工程公司是独立法人,“从法律上讲跟咱们没有关系,我只是来旁听的。”
生死难测
工人们第一次知道自己是独立的。“那咱经理为啥要参加你们的班子会?为啥两家节日一起搞活动?”电力公司领导说,那是历史遗留问题,现在要讲法律。
这个法律指的是《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1〕18号文)。文件规定,“对不具备重组改制条件或亏损严重、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厂办大集体,可实施关闭或依法破产。”
工人们却有不同理解。“不具备条件的要破产,咱们不一样。”李全博说,退一万步工程公司也是电力公司下属集体企业,电力公司拆了旧机组后会上新的,那就不该关闭工程公司。
而且国办发〔2011〕18号文规定,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再就业有困难的集体职工可实行企业内部退。李全博认为电力公司并未依法办事,“为啥一刀切要让所有人都下岗?”
为促使工人尽快解除劳动合同,在法定的经济补偿外,工程公司提出每人可以多得48个月的工资,当年被占地职工另加3万元。工人们依旧不愿退步,“最多得10万元,少的才六七万,以后连社保都缴不起!”
李全博和工友们多次到政府主管部门和电力公司上级机构反映情况,却一直没得到满意答复。对峙中,公司欠发的工资补了两个月,又停发了。没了生活来源,工人们连采暖费都缴不起。“好多老弱病残的,这不是断咱活路吗?”
李全博说,其实合资时公司的集体性质就变了,因为历史欠账才导致工人日后不能与电力公司职工享受同等待遇。“你跟它(电力公司)讲历史,它跟你讲法律;你跟他讲法律,它又跟你谈现实。说不清楚。”
目前对峙还在继续。对工人来说前景莫测,“我们命运在人家手里捏着,让咱生就生,让咱死就死,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