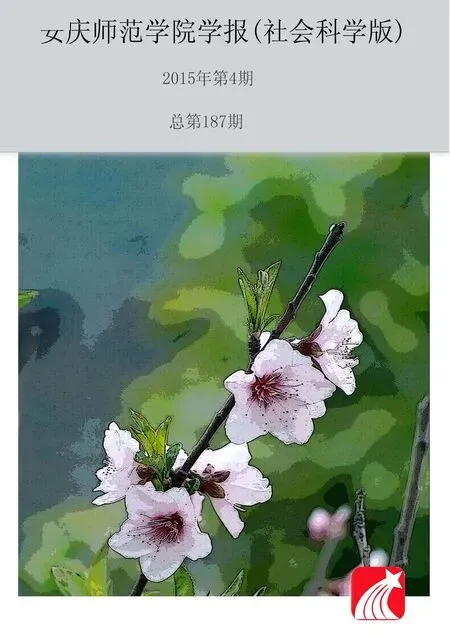两个时空的对话——评多甫拉托夫的中篇小说《手艺活》
胡 晓 静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 北京 100089)
两个时空的对话
——评多甫拉托夫的中篇小说《手艺活》
胡 晓 静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北京100089)
摘要:谢尔盖·多纳托维奇·多甫拉托夫的中篇小说《手艺活》是一部基于作者生平经历而创作的伪纪实主义作品。小说中设置了两个平行并置的时空,即以列宁格勒为中心的“苏联时空”和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时空”,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苏联和美国两种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下的城市生活图景。苏联时空是多甫拉托夫对“自由在何处”的追问,而美国时空则是对追问的回答,作家通过“问—答”对话模式的构建来表现人在两个不同的时空下对自由不断求索的生命体验,揭示自由的本质和人之忧郁的根源。
关键词:苏联时空;美国时空;自由;对话
谢尔盖·多纳托维奇·多甫拉托夫(1941—1990)是俄罗斯当代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俄罗斯文学第三次“移民浪潮”的重要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多以幽默诙谐的风格描写后苏联时期知识分子的生活百态,展现生命存在之本真与荒诞的杂糅。1978年,多甫拉托夫为寻求更为自由的创作环境,与家人一起途经维也纳迁至美国纽约,开始了流亡的写作生涯。因此,“苏联移民在纽约”也成为作家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手艺活》(1984)就是一部横跨苏联和美国两个时空的小说,是多甫拉托夫“自传系列”小说创作中处于总结性地位的作品,凝聚了作家对新生活的感悟和对旧生活的怀念。小说共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叫作《看不见的书》,记录了多甫拉托夫在苏联时期的文学创作屡屡不被认可的挫败经历;第二部分为《看不见的报纸》,讲述作家在纽约与朋友共同创办俄罗斯侨民自己的报纸并最终遭遇失败的故事。多甫拉托夫在《手艺活》中巧妙地设计出二元并置的时空,即以列宁格勒为中心的“苏联时空”和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时空”,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苏联和美国两种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下的城市生活图景。他在小说的开篇序言中就流露出这样的情感:“为什么我感到自己处在身体灾难的边缘?我那绝望的、生活上的无用之感又是缘何而生?为什么我如此忧伤?”[1]8《手艺活》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两种意识形态的时空孰优孰劣,而是将视角聚焦在作为生命个体的人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的生存和精神状态,进而探讨人的忧郁(тоска)——这一精神疾患之原发性和永恒性的问题。
一、专制与逃离——苏联时空
小说的第一部分《看不见的书》写于1976年,具有浓厚的“苏联印象”,是苏联社会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苏联社会文化生活的缩影。这部分小说中随处可见带有苏联特征的典型事物,如公共住房(коммуналка)、共和国内卫部队(ВОХР)、苏共中央委员会(ЦК)、书刊检查制度(цензурный режим)、克格勃(КГБ)等。对于多甫拉托夫来说,苏联时期的书刊检查制度不仅改变了他的文学创作之路,甚至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看不见的书》这个题目本身就暗示了多甫拉托夫小说的命运。当他把小说手稿寄给杂志社时,编辑通常会客套地赞扬几句,然后几乎毫无例外地在评语的最后写上:“很遗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小说不适合发表。”[1]30这里“众所周知的原因”其实就是指多甫拉托夫的小说不会得到书刊检查机关的认可。《看不见的书》中所记录的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文学界的状况。当时正值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掌权时期,虽然“解冻文学”的余温在一定程度上仍有延续,但苏联当局并未放松对人民思想动态和意识形态的管制,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大力扩招情报工作者。该局主要任务是为苏共当局提供有关国家文化与社会生活、知识分子意见和情绪以及国外媒体对当局的评论等详尽信息[2]。此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苏联文坛仍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为主要题材,官方要求作家塑造“高、大、全”的正面人物形象,而多甫拉托夫笔下的主人公多是不入流的艺术家、作家、酒鬼、投机倒把分子等等,“他的主人公与那些构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生产小说中的人物之生活意义的一切均格格不入……作家拒绝生活导师的角色,他的任务就是来讲述一些有趣的、可笑的、感人的故事”[3]648。综合上述原因,多甫拉托夫在苏联国内几乎没有通过官方途径发表过自己小说,唯一发表的作品集也被克格勃下令销毁了。
《看不见的书》讲述了多甫拉托夫未发表的小说《营区》夭折的命运,为此他还遭到了全体编辑部成员的“批斗”。每一个人都仿佛拿着放大镜来审视多甫拉托夫的小说,唯恐找不到可以拿来批驳的东西。编辑部的记者是为苏联当局鼓吹政治思想的“喉舌”,他们已经丧失了客观判断的能力,对任何事情都要“意识形态化”,总编辑的发言总是带着高瞻远瞩的架势:
“如果手稿不慎落入敌人的手中会怎么样呢?……两个世界正在斗争,两个体制正在争斗……” 同事涅伊法赫直截了当地问:“你到底爱不爱自己的祖国?”我回答:“和每一个正常人一样……谁不带一点忧愁和愤怒活着,谁就不爱自己的祖国。”然而,这位同事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立刻打断,“这是谁说的?是哪一个莫斯科的持不同政见者?”[1] 69
而实际上,多甫拉托夫只是引用了维克多·涅克拉索夫的诗句。在这个充斥着愚昧、虚伪的编辑部里已经没有一点自由呼吸的空气,人们无情地批判一部尚未出版的小说手稿,这是对作者权利粗鲁的践踏。同志般的爱和友谊已经化作无缘由的憎恶与谩骂,充斥着主观臆想和妄言,而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与“肇事者”划清界限,明哲保身。多甫拉托夫用讨论会上的发言深刻揭露了在专制制度统治下人的虚伪面目与扭曲道德,这也是当时苏联社会人的精神、道德面貌的缩影。
在《看不见的书》中,多甫拉托夫着力刻画在苏联时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多是列宁格勒的非官方派作家——展现他们身上与众不同的气质和“怀才不遇”的苦闷。与其前辈相比,他们没有宗教背景,崇尚自由,桀骜不驯,无论在生活方式还是创作理念上都受到国外作家和文学的强烈影响,“首先是雷马克、海明威、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夫卡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五六十年代引起了一阵巨大的模仿浪潮”[3]642。然而这些作家往往因为对官方要求的刻板文学样式不予妥协,有时甚至走上反叛的道路,因而很难跻身苏联官方作家的行列,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他们的小说不能通过官方途径发表,只能在某些文学团体、组织内部传播,或者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在读者中慢慢扩散。“第三次浪潮中的多数人是以颠覆现存文学传统的异端面貌出现的,他们对国内主流文学以及文化政策、社会制度的敌视决定了他们只能到西方去寻求自己作为一个作家所需要的生存空间。”[4]164不少多甫拉托夫当年的好友最后都成为俄罗斯文学第三次侨民浪潮的成员,如约·布罗茨基、伊·叶菲莫夫、弗·玛拉姆辛、瓦·波波夫、鲍·瓦赫金等。
多甫拉托夫的《看不见的书》讲述了苏联20世纪六七十年代整整一代作家的命运,该题目本身表达了一种躁动、不满的时代情绪。作家唯一的愿望就是自己能拥有读者,而“书不被人看见、不被人读”无异于对作家创作才情最大的漠视与扼杀。在此种情况下,“逃离”成为必然结果,而对于苏联时空下的多甫拉托夫来说,美国是他向往已久的自由民主的乌托邦,此外别无他处:“要逃离美国,只好到月球上去了。”[1]110
二、自由与迷失——美国时空
《手艺活》的第二部分《看不见的报纸》写于1984年,也就是多甫拉托夫举家移民美国后的第五年,“时间乘以空间创造奇迹”[1]97。来到美国后,苏联对于多甫拉托夫来说不仅仅是大洋彼岸的祖国,更是关于一段时期的记忆,那里有他的童年、少年以及哪怕并不如意的初恋和不被出版的小说。
多甫拉托夫在移民之后患上了严重的“怀乡病”。踏入一个新时空的多甫拉托夫回望过去时不得不反思:“我更幸福了吗?”纽约生活已经过去五年,他仍然不能适应新生活,因为移民之后发生改变的“不是社会制度,也不是地理环境和气候。不是经济、文化或者语言。而且,也不是自然本身。人们只是用一种忧伤代替另一种忧伤。这就是全部”[1]97。来到美国,一些基本的生活问题仍然存在,比如生存问题。多甫拉托夫与其他移民美国的人一样,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找工作。但对于一个不会说英语的俄语作家来说,想在美国继续自己在苏联时的工作是很困难的。于是在来到美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多甫拉托夫都无所事事,生活上多靠朋友们的接济,“某些慈善机构给我们一点钱,美国邻居给我们一些家具和旧衣服。此外,比我们早来美国的老朋友也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些很有价值、实际的提醒”[1]102。因为找工作,多甫拉托夫的家中常常聚集一些各个领域的苏联知识分子,大家共同分享一些就业信息。从“专制时空”来到“自由时空”的人们显然还有些不适应,他们平日里最爱做的事情就是骂美国人,把小区里的美国当地人称作“外国人”。渐渐地,在他们中间形成了“俄侨圈”,他们把俄侨聚居区——Rest-hills108号大街戏称为俄罗斯在美国的“殖民地”。[1]97
毕竟是呼吸了自由的空气,知识分子们思想也随之“解禁”了:音乐家伊丽娜·戈莉茨想凭借自己优雅的气质和不俗的品位嫁给美国的有钱人;经济专家斯卡法里希望被有钱人收养,作为他的继子;宗教活动家列姆库斯的想法更加荒谬,他建议在纽约的富人区闲逛,看到有人遛狗时,就走上前去,撩拨小狗,争取被咬,一旦被咬成功,富人就会为了避免法律纠纷而支付一大笔钱作为补偿,以此便可大赚一笔(他以“上帝眷顾穷人”和“劫富济贫不是罪”为自己的想法开脱)。纽约是一个现实的地方,在这个资本横流的城市,钱是生活必需品。这对于刚刚从“计划经济”走出来的苏联知识分子来说,的确需要时间去充分认识和适应。多甫拉托夫通过一种反讽的方式来审视在美的苏联知识分子,“玩笑”中既有无奈,也有自嘲。
来到美国之后,多甫拉托夫发现,“资本生产最基本的知识——‘做生意’并不可耻……在莫斯科,那些小偷和骗子才会称自己是‘商务人士’。‘经纪人’、‘商人’这些概念会让人和‘坐牢’联系起来。而在文学和文艺界对‘精明能干’的鄙视就更加一致和公开了。要知道,我们可是诗人、艺术家、有艺术气质的人”[1]158。知识分子的清高和自矜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面前变得空洞、乏力。生存与艺术孰高孰低?这是来自苏联的“艺术家们”在全然不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冲击面前不得不思量的问题。多甫拉托夫曾经“宁可去偷,也不去做买卖”的想法在来到美国后彻底颠覆了。在经历了一次创业的失败后,他终于明白,“商人是严肃的、令人尊敬的职业。它需要智慧、洞察力、高尚的道德品质”[1]158。这次创业就是多甫拉托夫和其他侨民朋友一起创办报纸的经历。小说中多甫拉托夫为这份报纸取名《镜子》,寓意这是一份忠实反映苏联侨民在美国生存状况的刊物。而事实上,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初曾在美国红极一时的侨民报刊《新美国人》,除了报刊名称,包括创办人员的名字和报社的发展状况,多甫拉托夫在小说中都做了一定的虚构化处理。
在小说中,莫克尔、德罗兹托夫、巴斯金和多甫拉托夫是四位主创人员,他们在苏联时都有做记者的经历,能创办一份属于自己报纸,是每一个人心中期盼已久的梦想。《镜子》一经发行就以其独具一格的文风和丰富多样的内容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半年后,报纸的发行范围从纽约扩大到芝加哥、底特律、波士顿等城市,但经营报社的过程困难重重。一开始,《镜子》的赞助商拉里在确立报刊主题上就与编辑们发生重大分歧,他希望把报纸办成一份宣传犹太思想的专刊,面向所有从苏联逃离出来的难民,引领他们皈依犹太教,而多甫拉托夫和好友却想扩大报纸的读者群——面向所有说俄语的人。逐渐地,投资人对报社的资金支持力度不断减少。除此之外,《言与行》报纸的主编博戈柳博夫觊觎《镜子》日渐增长的声望,以高额稿酬和优厚待遇挖走大量专栏作家,并且不断诋毁多甫拉托夫及其同仁是“为苏联克格勃服务的人”,使得《镜子》在短期内失去大量供稿者,稿源和声誉都受到极大的损害。很长一段时间,《镜子》的运营都是亏损的,日常开支完全依赖赞助商的支持,报社的所有工作人员也是免费劳动,对于他们来说,《镜子》是他们期盼已久的自由言论的平台,是争取民主的胜利,是“奉若神明的孩子”[1]159,如果《镜子》变成和香肠、鲱鱼一样的商品——这样的事实才令他们难以接受。最后,多甫拉托夫安排了一场意外的火灾宣告报社的终结。
对于多甫拉托夫本人来说,这段时期则是其文学事业的上升阶段。与苏联时期被压抑、被雪藏的经历相比,美国纽约的确帮助他实现了成为作家的梦想。先是他的小说被翻译成英文发表在美国著名杂志《纽约客》上,随后他又接到美国和俄罗斯出版社的邀请,他们打算刊发他的其他作品。但多甫拉托夫等待这一时刻太久了,以至于认为,无论怎样的结果都不能弥补那漫长的期盼和为此所做的牺牲。所以,当这一时刻真的到来时,他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平静与淡定——“自然,我是满意的,但仍然比我预想的程度要低一些”[1]160。20世纪60年代,在苏联的多甫拉托夫认为自己是一个怀揣远大抱负与才能的作家,严格的书刊检查制度虽然截断了小说与读者见面的通道,却给予了他“幻想自己是个不被认可的天才”的权利,他曾以为获得了自由就能写出“《哈姆雷特》之类的东西”。当他来到西方后,才发现自己并不是天才,那些幻想破灭了。多甫拉托夫无论获得怎样的荣誉,都无法彻底治愈他的忧郁。他始终认为,作为一个用俄语写作的作家,他真正的读者在大洋彼岸的俄罗斯。而此时身在美国的他,却永远失去了祖国,失去了写作的对象和动力,这一事实无时无刻不在折磨他。“写些关于俄罗斯的东西给美国人看?还是写些美国的东西给俄罗斯人看?”[1]171结果是写给自己看,就像照镜子一样。多甫拉托夫在美国的生活依然充满忧郁与迷茫。
三、回望与反思:两个时空的对话
《手艺活》与多甫拉托夫的其他小说一样,是一部拟自传体小说。他采用伪纪实主义手法,把自己的真实经历同虚构融为一体,模糊真与假的界限,混淆现实与虚构的存在。而自传体小说的本质是反思,无论《手艺活》中有多少虚构的成分,都无法改变其对个人生命历程反思的本质。多甫拉托夫一直在追求自由,无论是创作自由还是人格自由。他曾以为在苏联时一切痛苦都源于自由的缺失,可当他得到所谓的自由时,却发现自己仍然忧郁,于是他转向反思,反思自由的本质,反思人之忧郁的根源。多甫拉托夫的反思建立在两个时空的对话基础之上,苏联时空是作者对“自由在何处”的追问,而美国时空则是对追问的回答,“问—答”模式是对话的原型。需要指出的是,多甫拉托夫在小说中并未构建显性的问—答机制,而是将问题和答案隐藏在叙事过程中,构成隐性的对话关系。
在《看不见的书》的结尾,多甫拉托夫两次感叹“没有出路了”[1]94,但随即他又做了一个“淡化冲突”的处理,他说:“我甚至想感谢这些暗中的力量,因为他们,我获得了极大的荣幸——为我唯一的挚爱而受苦!”[1]94虽然这句话中流露着无奈与讽刺,但从客观上来讲,多甫拉托夫的确对曾经“折磨”过他的祖国仍然心存怀念,他曾说:“纵然如此,但俄罗斯,你仍是我心中最珍贵的地方。”[1]287如果说,他曾经憎恨过扼杀他作品的苏联当局,那么此时,他已经彻底宽容了祖国所加诸他的一切,甚至怀抱着感激。一方面,苏联生活题材是多甫拉托夫在美国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我们一家人》(1983)、《保护区》(1983)、《手提箱》(1986)等作品,都是围绕苏联时期作者的生活经历展开。苏联时期的点滴记忆成为支撑多甫拉托夫创作的基石,甚至苏联严酷的书刊检查制度也从一个束缚创作自由的刽子手转变为小说的情节主线而走进他的多部小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看不见的书》,那些被克格勃查封的书我们已经看不到了,而“克格勃查封书”这件事情本身成为小说的主要情节。这部小说于1978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单独发表,获得很大的关注,这也是多甫拉托夫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另一方面,多甫拉托夫同其身边其他苏联侨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适应了苏联的思维模式和习惯,当初之所以选择移民美国,只是为了争取一个自由民主的创作环境,可以算作为艺术而移民。当他们来到美国后才逐渐发现,“周围全是民主,而我们自己却在囚牢里”[1]142。理想与现实的错位使得多甫拉托夫更加怀念在祖国的日子。因此,他对苏联复杂的感情促使他不断回望历史,对比苏联生活和美国生活究竟有什么不同。这也构成了两个时空发生对话的情感基础。
“一切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5]对话的目的是探寻真理,而对话的结果也使人们更加接近真理。因此,多甫拉托夫舍弃了对苏联时空和美国时空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让它们在小说中对话共存。小说中苏联时空和美国时空处于平行位置,作者给予它们平等的对话权利。多甫拉托夫既肯定二者的差异——两种不同体制下的社会,同时也指出二者的共性——生活在两种社会体制下人的精神忧郁的本质没有改变,从而否定了“孰优孰劣”的绝对对立关系。多甫拉托夫借用小说文本搭建一个平台,让两种“正在斗争”的体制发生对话,这本身就是一种亦此亦彼的多元共存思想。此外,他在“自由王国在哪里”这个问题的回答上,既放弃了对苏联专制制度的批判,也放弃对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两面性的批判,即从根本上放弃对政治意识形态本身的批判,而从外部世界转向对人自身的内部批判。他曾提出三个独特的命题:“专制就是我们自己”[1]146,“祖国就是我们自己”[1]164,“地狱就是我们自己”[6]。多甫拉托夫承认,每一种体制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弊端,但它们不是诱发人精神危机的根源。以苏联政权为例,“多甫拉托夫把苏联政权去概念化了”[7]。他说:“苏联政权不是鞑靼蒙古人的桎梏。她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里,在我们的习惯和气质里,在我们的酷爱与厌恶里,在我们的意识和我们的心中。苏联政权——就是我们自己。也就是说,我们最重要的事就是战胜自己。”[1]146多甫拉托夫认为,人要获得终极幸福——也就是灵魂上的安宁与自由,不能幻想依靠某一种社会制度,从一个时空逃离到另一个时空,不断地寻找却不断地迷失,最根本的途径应该从自身入手,去寻找通往自由王国的道路,精神上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对任何一种外部世界存在的意识形态的盲目追随与信赖都是危险的。来到美国之后,多甫拉托夫对自由的理解更加全面、深刻,他既看到了自由的无私,也看到了自由的盲目。这既是多甫拉托夫对苏联年轻作家的告诫,也是他与年轻时自己的对话,是对人生之路的反思。
结语
《手艺活》是一部关于寻找自由并在自由里迷失的小说。多甫拉托夫通过对称结构文本的构建实现了苏联时空与美国时空的遥远对话,揭示了在两种时空下所产生的不同生命体验。小说不仅呈现了两个意识形态时空之间的对话,也表现出人的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不断交锋与碰撞。俄罗斯是有着独特的移民历史的国家,“俄罗斯的侨民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中一道独特的风景”[8]。当国内的社会、历史条件无法给予人们足够的自由和权利之时,移民——往往成为不得已的选择。对西方和欧洲世界的盲目崇拜与偏信却造成移民者的二次灾难。多甫拉托夫的这部小说恰恰为人们厘清了自由的本质——自由与幸福并非永远同步,无论身处何种时间和空间之下,忧郁都如影随形,因为“天堂的实质就是我们所没有的东西”[1]135。人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不可能只有所得而无所失。因此,忧郁将与人永生共存。同时,生活的继续需要不断同忧郁进行抗争。多甫拉托夫采用的是一种以幽默对抗忧郁的策略,小说中随处可见的幽默对话和插入型结构的笑话为小说营造了一种忧中带喜的氛围。在这个矛盾体中,读者既对生命中的悲剧因素有所认知,又从中汲取力量来对抗这种悲剧性。这也是多甫拉托夫透过两个对话的时空所诠释的生命哲学和处世观。
参考文献:
[1] Довлатов С. Ремесло //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3 [M]. Состовитель А.Ю. Арьев. СПб.: Азбука, 2000.
[2] Горяева Т.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M]. М.: РОССПЭН, 2002:351.
[3] 弗拉基米尔·阿格诺索夫.俄罗斯侨民文学史 [M].刘文飞,陈方,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4] 单之旭.俄苏侨民文学的第三次浪潮[J].北京大学学报(外国语言文学专刊),1999.
[5] 巴赫金.诗学与访谈[M].白春仁,小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40.
[6] Довлатов С. Чемодан. //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2. Состовитель А.Ю. Арьев. СПб. : Азбука,2000:8.
[7] Генис А. Довлатов и окрестности. М.: Вагриус,2004:33.
[8] 刘文飞.20世纪的俄罗斯文艺学[J].文艺理论批评,2006(8):15.
责任编校:林奕锋
中图分类号:I5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15)04-0035-05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5.04.009
作者简介:胡晓静,女,安徽淮北人,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4-12-09
网络出版时间:2015-08-20 12:55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50820.1255.0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