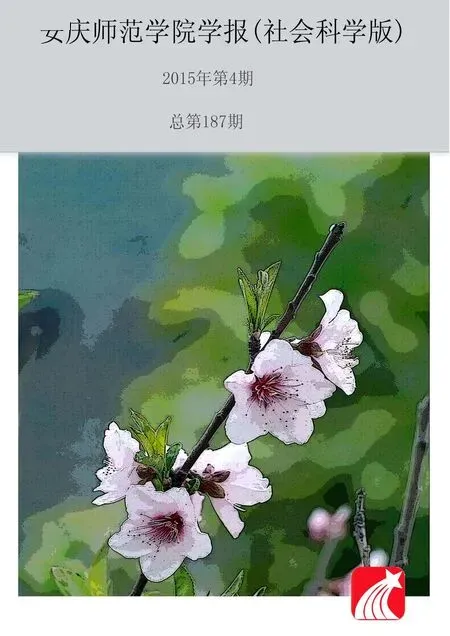劳伦斯短篇小说中的精神生态思想
叶 敬 霞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劳伦斯短篇小说中的精神生态思想
叶 敬 霞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摘要:作为一个现代主义作家,劳伦斯十分关注现代文明对人性的异化,在其中短篇小说中生动地再现了人的自然本能与现代机械文明之间的冲突。劳伦斯小说中永恒不变的主题是对扭曲人性的机械文明的鞭挞和对自然人性回归的呼吁。他认为只有回归自然,恢复两性的本来面目,才能使人类摆脱文明的梦魇,远离机器的摧残。
关键词:劳伦斯;短篇小说;精神生态;工业文明
大卫·赫伯特·劳伦斯是20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其作品受到国内外批评界广泛而持久的关注。其短篇小说以主题鲜明、结构紧凑见长,往往被认为是劳伦斯最优秀和最出色的作品。国内关于劳伦斯作品生态解读的论文虽然比比皆是,但是其中和精神生态分析有关的不到10篇,且多局限在某一部小说的范畴。本文希望通过对劳伦斯短篇小说的精神生态解读,体现劳伦斯对人类精神生态失衡的关注,呈现他应对这种社会现象所提出的解决方法。
精神生态研究主要是针对人类精神生态领域的研究实践活动。“现代社会过于注重技术、经济、物质的发展,忽视了人类精神性的存在,形成社会生产力飞速提高,精神却并没有随之发展的失衡现象,造成了精神生态危机。”[1]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更加关注精神生态,关于精神生态的研究也呈急剧增长的趋势。精神生态批评由此而生。精神生态批评的使命是“应对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清除精神领域的污染,维护人类精神生态的健康、洁净”[2]116。在精神生态研究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出现各种应对精神生态危机的对策,其中主要一点是回归自然。“自然是人类身体和精神成长的基础,它以其博大神秘启示着人类,赋予人类以灵性。”[1]114劳伦斯在其短篇小说中,深刻地反映了他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注,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幅精神生态危机的图景。
一、 阶层对抗与战争阴影下的人性沦陷
劳伦斯于1885年出生于英格兰中部的一个矿工家庭。父亲约翰·亚瑟·劳伦斯与母亲莉迪娅“是一对不协调的夫妻”[3]3。父亲出身卑微,而母亲来自上流社会,受到良好的教养。目不识丁的父亲无法理解母亲,他们无法沟通,有时情绪激化起来还会上演厮打的场景。这一切在劳伦斯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两人身份的悬殊对劳伦斯身心的影响都体现在他的小说里。青少年时期劳伦斯还由于自己是矿工的儿子,受到了同学的冷落,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体会到了令人窒息的阶级压抑。
劳伦斯于1912年4月邂逅了当时著名的威克利教授夫人弗里达,开始了二人的传奇故事。弗里达的叔叔和父亲都是男爵,是西西里岛的贵族,地位显赫,受人尊敬。据弗里达回忆,劳伦斯与她父亲的第一次会面是这样的:“他俩目光犀利地对视着——一边是我的父亲,纯粹的贵族,一边是劳伦斯,矿工的儿子。我父亲不无敌意地请劳伦斯抽香烟。”[4]后来弗里达做了一个梦,梦中丈夫和父亲打了一架,结果劳伦斯赢了。从这个梦境可以看出劳伦斯蔑视贵族、反抗贵族的阶级观念。现实生活中两个阶级对抗的情景被劳伦斯描绘在自己的小说里。
1913年劳伦斯和妻子弗里达来到德国的巴伐利亚,劳伦斯在这里完成了短篇小说《普鲁士军官》。小说讲述的是一个上尉和一个勤务兵之间的故事。两人的身份等级悬殊分明。上尉是一个普鲁士贵族,飞扬跋扈,目空一切。一方面,上尉对勤务兵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嫉妒勤务兵的朝气蓬勃,“每当勤务兵伺候他的时候,他总不免要感觉到这个血气方刚的人。那就像一团烈火,烧灼着这个年纪较大的人的紧张、僵硬、死气沉沉、转动不灵的身体”[5]3。他对勤务兵的感情像是着了魔一样,爱恋、嫉妒、憎恨。另一方面,由于饱受压抑,勤务兵对上尉的感情是恨多于爱。身份的差距使得上尉这种单向的无以宣泄的同性恋欲望受到了极大的挫伤,结果导致了上尉丧失人性而肆意妄为。他病态地发泄自己的欲望,不仅喜怒无常,而且对勤务兵总是吹胡子瞪眼,甚至拿着皮带头抽打勤务兵的脸,直到鲜血淋漓。上尉用这种残忍的行为来获得内心畸形的快乐。故事的视点聚焦于处于下层勤务兵的内心世界。由于受到长期的奴役和虐待,勤务兵极度痛苦地在自己的生存与世界的对抗中挣扎,最后终于忍无可忍,杀死了上尉。“年轻的脸上一副严肃认真的神情,他用一只膝盖一下子跪到上尉的胸膛上,把他的下巴往树桩的另一边按下去。他按着,内心感到一阵松快,紧张的手腕也变得很松快。”[5]20在完成小说之前,劳伦斯就有自己的构思。劳伦斯的好友奥尔丁顿回忆说:“有一天他到沃辛去,见到了一些大兵,他们给他的印象极坏,他断言他们是一群‘虱子和臭虫’,他们迟早会杀了他们的长官不可。”[3]162可见,沃辛之行的产物便是《普鲁士军官》。小人物受到阶级压迫的后果被劳伦斯用放大镜似的呈现在读者面前。勤务兵的谋杀行为反映了勤务兵精神上的沦陷,他的这种行为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正义行为,完全越轨了。精神的异化和扭曲是精神生态污染的根本表征。
如果说阶级压抑是人性沦陷的根源,那么万恶的战争则加速了人性沦陷的速度。劳伦斯认为战争是一种致命的疾病,能够导致人类尊严的崩溃。《普鲁士军官》虽创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但劳伦斯已看出战争对人性的毁灭。小说揭露了德国军队中毫无人性的等级观念。“从默里的笔记来看,到1914年圣诞节前,劳伦斯的情绪开始受到战争的压抑。”[3]156出自对战争深深的焦虑,他想逃离到一个叫“拉纳尼姆”的“另一个地方”去。那里没有龌龊的战争,没有金钱。
劳伦斯创作小说《狐》时,已是一战的尾声。由于战争,男子奔赴战场,女人则独守空巢。女人和女人之间靠互助而生存,班福德和玛奇就是这样的两位女性。在班福德父亲的资助下,班福德和玛奇经营一家农场。然而农场的经营非常惨淡,两人过着艰辛无味的生活。
故事中两位女主人公的命运自始至终都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小说中虽然没有硝烟弥漫的战场,没有惨无人道的厮杀,但是战争对人性摧残的痕迹却十分清楚。班福德和玛奇在一起,是战争导致男人的离开造成的。“虽然她们平时十分要好,在长时间的孤独寂寞中,她们对彼此还是容易变得有点儿烦躁,有点儿厌倦。”[6]45小说另一主人公亨利的出现是由于战争结束了,男人得以重返故里。亨利疯狂地追求玛奇,他将班福德视为自己的情敌。当他返回军营,收到玛奇的拒绝信时,不禁怒火中烧,人性的丑陋一面暴露无遗。“在他的脑子里,在他的心灵上,在他的全身,有一根刺刺痛了他,使他简直要发疯了。他非得把这根刺拔出来。”[6]101班福德就是他的肉中刺。诚如劳伦斯暗示的那样,亨利如狐狸般阴险、狡诈、狠毒,最后不留蛛丝马迹地干掉了班福德。如此干净利落、不着痕迹地杀人,如果不是战争的历练,对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恐怕是难以做到的。
二、 西方物质文明背后人类情感的扭曲
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文明的兴起和急剧发展对西方社会产生了剧烈的冲击,“传统遭到扼杀,人性变得扭曲,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变得极不和谐”[7]57。生活在英国工业革命迅猛发展的时期,目睹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带来的种种残酷的现实,劳伦斯在小说中辛辣地揭露了英国工业文明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苦以及生活在重压下的人性的扭曲。他的许多作品都反映了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生活。
劳伦斯敏锐地观察到了工业文明背后人类精神的异化和自我的人格分裂。不仅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被打破,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也被活生生地割断。为了揭露这种丑陋的社会现象,劳伦斯在短篇小说《木马赢家》中更是不惜颠覆描写母爱伟大的传统,一步步描述母子之情如何遭受物质文明的腐蚀而名存实亡。《木马赢家》创作于1926年,是劳伦斯较为著名的短篇小说。故事探讨了劳伦斯所关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母亲与儿子之间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工业社会中金钱对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的扭曲。
母亲海斯特表面上无比温柔,在外人看来非常关心、疼爱自己的孩子,但是只有她自己明白,她是一个无法给予爱的母亲。正因为没有母爱,男孩保罗才渴望母爱。可悲的母亲因为对金钱的追求已经窒息了母爱的天性,她丧失了爱的能力。房子里始终萦绕着一句没有说出去的话:“得有更多的钱。”这句恐怖的话“在故事中反复出现,以其诗化节奏强化了故事的童话风格,也烘托了小说的主题,突出了现代社会金钱对人内心的腐蚀”[8]。一个偶然的机会,保罗发现自己骑木马时可以预测赛马的赢家,为了讨母亲欢心,为了让那个恼人的声音停下来,保罗疯狂地骑木马,达到了癫狂的状态。开始时,每一次都能准确地预测结果,保罗赢得了很多钱。劳伦斯并没有让结局就这样完美下去。他知道在物欲的刺激下,人的需求是无止境的。家里的声音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大。在最后一次预测中,保罗从木马上摔下来,力竭而死。文章中,除了保罗,母亲、叔叔以及其他的人都为了金钱而牺牲了人的价值。
《公主》是劳伦斯住在新墨西哥陶斯农场期间所作。《公主》中有两个对比鲜明的世界:一个是公主的那个与世隔绝的、脆弱的超现实世界;另一个是以现代工业文明为背景的庸俗的资产阶级的现实世界。自称有苏格兰王室血统的科林·厄柯特在混沌的现代工业世界中还保持着一份近乎“荒诞的”的纯真。从女儿多莉出生以来,他就全身心地照顾着女儿,向女儿灌输自己的一套理论。“在他的视野中世界已成了一片荒原,高贵者已所剩无几,人性已被自私和冷漠的资产阶级工业社会压榨到只剩下绿色的恶魔永驻于灵魂的至深处。”[7]147多莉由于一直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以至于到38岁时还不知道怎样与异性交往,体会不到男女间灵与肉的血性结合。父亲的去世使她感到“四周的一切似乎全蒸发掉了。先前,她生活在一种温室里,在她父亲疯癫的气氛里。突然,温室从她四周移去了,她到了阴冷、辽阔、庸俗的室外”[6]196-197。父亲去世后,她来到西部印第安人居住的地方。在这里她遇到了墨西哥人罗美罗,被罗美罗的相貌、声音和气质所迷倒。与罗美罗在山顶的独处到最后的悲剧结局,其实是公主本人自导自演的结果:她心里想要得到罗美罗,却又不敢被世人所知。与其说善良淳朴的墨西哥人罗美罗是死于枪口之下,不如说他是死于公主的爱无能。一直活在父亲羽翼之下的公主,并不知道真正的爱情是什么,如何去爱别人。劳伦斯有意让《公主》周旋于神话与现实之间,揭露了人们情感世界荒漠化的冷酷现实。
三、 回归自然,寻找灵魂的栖息地
劳伦斯是一位先知的文学评论家。在小说中,他不仅揭露了人类精神生态的失衡现状,也间接地提出了针对这种现状的良方——回归自然。劳伦斯本人亲力亲为,辗转于世界各地,寻找理想的栖息地。他与自然亲密接触,一生游走在荒野乡村,远离现代文明而广泛接触异域文化,如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地区、德国的黑森林、澳大利亚、美国的新墨西哥州、亚洲的锡兰等等。他能站在其他同时代作家无法企及的精神生态高度去诠释人类的生存状态。
在《狐》中,那只充满象征意味的狐狸让玛奇神魂颠倒。“每逢她陷入半沉思的状态中,当她半入迷、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眼前发生的一切时,支配着她无意识的思想,占有她沉思的空白的一半的,不知怎么总是这只狐狸。”[5]205小说的象征意义显而易见,劳伦斯通过玛奇的眼睛,看到了狐与人和谐地交融在一起。“他在摆脱英国社会世俗人生的羁绊之后,企图到人类以外的生物界和大自然中去寻找他所向往的纯真的力量和生命的魅力。”[9]
1922年,劳伦斯同弗里达来到了新墨西哥的陶斯农场,期间除了几次短暂的欧洲之旅外,他一直住在墨西哥或新墨西哥。在新墨西哥柔和的高原夜色中,劳伦斯寻找到了创作的灵感。劳伦斯无限同情印第安土著居民的悲惨遭遇,痛斥西方文明。《骑马出走的女人》便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女主人公生活在死气沉沉、被人遗忘的西班牙小镇上。“死气沉沉”一词频繁出现在小说中,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生存状态。丈夫满腔热爱的只是工作,而女主人公则是丈夫摆布的物件,从来没有一个人单独出去过。在巴黎、纽约、伦敦待过的她萌生了要去印第安人住的地方。“她觉得她命中注定了该到山里去,到这些无始无终、神秘莫测的印第安人的隐蔽的居住地点去遨游一番。”[5]129当她独自一人骑马来到一个空荡荡的山谷时,她感受到的不是孤独,而是奇妙与欢快。主人公逃离白人社会,来到印第安部落。从与印第安人的文化碰撞、摩擦到最终被接受,一直都在她的预料之中。甚至最终的牺牲,她都坦然面对。精神与肉体都得到了解脱与释然。
以西西里为故事背景的《阳光》创作于意大利热那亚附近的海边别墅。小说女主人公居里叶与丈夫之间存在严重的问题,去西西里之前,她心里怀着深深的愤懑和挫败感,丈夫和孩子搅乱了她内心的平静。医生对她的建议是进行阳光的理疗。在西西里,经过多次与阳光的亲密接触,她情感中阴郁紧张的成分不见了,思想的枷锁也解开了,疲惫冷却的心开始轻松暖和起来。居里叶在与自然、阳光的接触中,找回肉体与灵魂的平衡。“她勇敢地剥去现代文明的伪装,置路人不顾而将自己裸露在美丽的阳光下,接受它的洗礼。这也是她挣脱一切桎梏,灵魂内血性意识的复苏。”[7]28相比之下,现代男人的生存状态却岌岌可危。居里叶的丈夫由于长期远离自然,在工业文明下挣扎。他骨子里苍白无力,怯懦胆小,已经变成了机器的附庸。劳伦斯欲通过对莫里斯外在形象的贬低和丑化,来反映莫里斯精神层面的畸形,从而鞭挞工业文明对人性的摧残,提倡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结语
人与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谐发展的系统。生态环境的恶化势必危及人的精神世界,精神生态的危机已经成为人类不可忽视的问题。作为一个现代主义作家,劳伦斯十分关注现代文明对人性的异化,在其中短篇小说中生动地再现了人的自然本能与现代机械文明之间的冲突。劳伦斯小说中永恒不变的主题是对扭曲人性的机械文明的鞭挞和对自然人性回归的呼吁。他认为只有回归自然、恢复两性的本来面目,才能使人类摆脱工业文明的梦魇,远离机器的摧残。
参考文献:
[1]朱鹏杰. 中国精神生态研究二十年[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5).
[2]朱鹏杰. 范畴与体系:中国语境下的精神生态批评研究[J]. 鄱阳湖学刊, 2010 (4).
[3]理查德·奥尔丁顿.劳伦斯传[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
[4]弗里达·劳伦斯. 不是我,是风[M].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6:10.
[5]劳伦斯.劳伦斯中短篇小说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6]D.H. 劳伦斯. 劳伦斯中短篇小说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7]汪志勤. 劳伦斯中短篇小说多视角研究[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0.
[8]陈兵.劳伦斯《木马赢家》中的俄狄甫斯情结问题[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3).
[9]毛信德.20世纪文学泰斗劳伦斯[M].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111.
责任编校:林奕锋
Eco-spirituality in Short Stories of D. H. Lawrence
YE Jing-xi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Anhui, China)
Abstract:As a modernist writer, D. H. Lawrence paid much attention to alienation of humanity. In his short stories, there are conflicts between natural instincts of human beings and mechanical civilization in modern times. The unchangeable theme of Lawrence’s short stories is the scourge of mechanical civilization which twists humanity and the appeal to natural humanity. According to Lawrence, only by returning to Nature and the original truth can men get rid of the nightmare of civilization and be away from destruction.
Key words:Lawrence; short stories; eco-spirituality;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15)04-0031-04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5.04.008
作者简介:叶敬霞,女,安徽怀宁人,安徽大学外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3-08-19
网络出版时间:2015-08-20 12:55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50820.1255.0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