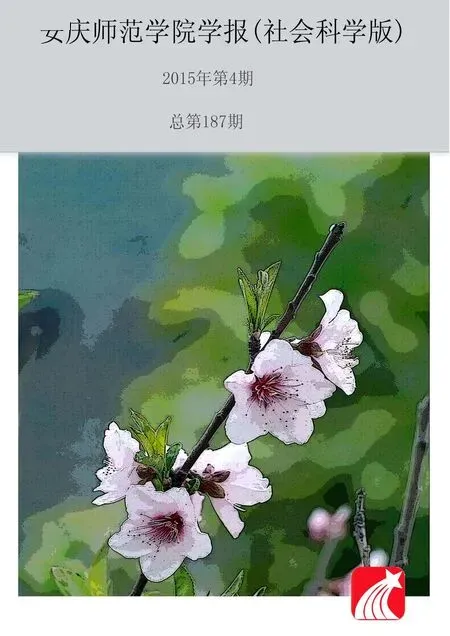解构主义误读理论对当代西方文论的影响
王 敏
(西安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8)
解构主义误读理论对当代西方文论的影响
王 敏
(西安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8)
摘要:解构主义误读理论与当代西方文论关系密切,其批判性和开放性为反中心、关注边缘的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阅读的、修辞学的、边缘研究的理论资源。女性主义批评实质是对传统男性中心的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误读”。新历史主义以文本论对抗真实论、以修辞论反对模仿说、以解构论反对客观论、以新历史代替旧历史,都有解构主义修辞性误读理论的痕迹。同时,解构主义误读理论中的“他者”观念对后殖民主义文论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
美国耶鲁大学学者保罗·德·曼、哈罗德·布鲁姆、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于上世纪70年代组成了蜚声一时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流派——“耶鲁学派”,其“一切阅读皆误读”的思想彰显着批判传统的激进锋芒,宣告了文学意义的不确定性。随着80年代德·曼的去世和米勒的离开耶鲁,以及90年代哈特曼的退休和布鲁姆批评观念的转向,“耶鲁学派”作为一种流派虽已过了鼎盛期,但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的精神却继续留存,在当代西方文论中创造了新的气象。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对当代西方文论的影响,正如学者盛宁所总结的:“在特定的条件下,解构主义也许能具有一定的革命性,西方的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种种文化批评流派都不约而同地向解构主义寻找理论武器。因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版图上,上述批评流派都处于边缘状态,受到根深蒂固的主流文化的排挤和压制,它们要想站稳脚跟、谋求发展,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把这个中心解构掉。这说的是解构主义对它们的直接影响。”[1]206-207如果把社会文化作为一种广义的“文本”来看待,解构主义误读理论所提供的文本批评方法,为反传统、反精英主义、边缘化的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批评提供了理论武器,并突破语言、形式的领域,把现实、历史的因素重新引入文学批评,对性别、历史、种族等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误读”和重建。
一、“对抗式阅读”观念对女性主义文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认为女性主义批评与后现代意义上的解构是同时代的,是“在战后——甚至在其时限以西蒙·波夫娃为标志的那个时代之后很久,才发展起来的。不早于60年代,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就最直观最有机的证明来讲,甚至不早于60年代末。与解构的主题、阳物理性中心论之解构同时出现,未必或不总是意味着依赖于它,但至少表示属于同一组合、参与同一运动,属于相同的动机”[2]24。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之后,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同时兴起是有必然性的,它们都具有反结构、反秩序、反传统的特征。从发生学的角度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解构主义思想“未必或不总是意味着依赖于它”,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解构主义思想的影响。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指出,虽然“一些女性主义者根本不愿意理会理论,特别是在学术机构中,‘理论’往往是男性的,甚至是阳刚气十足的——坚硬的、抽象的、先锋派的理智性著作……然而,尽管最近许多女性主义批评渴望逃脱理论的‘凝固性与确定性’,以便发展出一种不至于与那些公认的(因此极可能是男性生产的)理论立场拴住一起并受其钳制的女性主义话语,但它们还是在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想中获得了理论支持,当然绝不仅是因为它们似乎在拒绝(男性的)权威或真实观”[3]141。女性主义批评以其敏锐的性别意识警惕着“理论”背后可能存在的男权立场,然而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女性阅读与女性写作两个方面。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首先是一种以社会政治变革为目的的文化运动,与解构主义误读理论具有内在联系,解构主义反二元对立的激进思想直接为女性主义批判传统的男权中心提供了依据。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要求以新的视角来审视已有的“经典”,塞尔登说:“女性分析是一个有说服力的政治的、文化的、批评的解构形式。它重新评价和塑造(如果不是爆炸)文学经典,拒绝接受统一的、被普遍认可的意义,公然使话语实践的整个领域政治化。女性分析并不认为‘女人’在经验上是可证明的,它认为‘女人’是造成主流叙述困扰与不稳定的一个裂隙和缺场。”[3]257传统有关“女人”的界定基本上是站在男性的角度来进行的,因此“天使”和“妖妇”这两种极端的女性在文学史中极为常见,但这两种形象并不是现实中“女人”的实际状态,只是站在男权中心主义立场上来进行想象的结果。因而,从“女人”这个“造成主流叙述困扰与不稳定的一个裂隙和缺场”出发,就能发现男权中心主流话语背后的力量与意义。
体现在文学阅读与批评领域,女性主义批评实质是对传统男性中心的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误读”。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基础上提出,女性作家除了具有来自文学传统的焦虑外,还具有来自性别的“作者身份的焦虑”。男性文学经典是建立在男性经验之上的,它所培养的女性读者通过扭曲自己来与之认同。由于女性在传统文学中是以男性的话语来讲述的,从男性经验出发的“男性真理”就是意义产生的唯一标准。女性主义批评家要求以女性立场来抵制男性文学传统,最终将传统的男权主义思想祛除。“误读”是女性主义阅读的必然要求,通过女性经验的文学阅读来改变文本的理解,从而“在阅读中改变世界”。基于女性阅读经验,提出新的文学批评标准和批评尺度,所有被阅读的文本因其所依赖的女性主义理论框架而产生新的意义。比如吉尔伯特和古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1979)一书中就得出疯女人伯莎是简·爱另一面的独特结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性别入手重新阅读和评论文本,以女性的特殊经验为消解男权中心的先决条件,借以解构了西方传统的男性中心文化体系,创立了以女性为中心的新观念新话语,重建人类两性关系。
反过来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为解构主义思想的可行性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美国学者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1942- )曾说:“与其说解构主义为女性主义者打开了通道,不如说妇女的形象和话语也同样在为德里达指点迷津。”[4]315斯皮瓦克是出生于加尔各答的孟加拉人,大学毕业后赴美深造,后留美任教。在学术研究领域她有着多重身份,她于1976年将德里达的《论文字学》译成英文并写了篇著名的序言,是解构主义批评的优秀阐释者,同时她又是一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多重学术身份赋予了她开阔的学术视野,斯皮瓦克认为,应将对男权中心主义的批判作为对整个逻各斯中心主义批判的一部分来进行。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误读”,在传统的文本中重新发现了女性意识的历史存在,同时也发现了女性写作的历史存在。语言的产生和运用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传统的父权制文化也在文学领域表现为男性语言的建构。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写作被视为与女性无关的男性活动,女性在传统文化中受到压抑而失语。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向这一传统提出了挑战。一方面,着重发掘女性文学传统,撰写女性文学史。美国学者伊莱恩·肖沃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一书中梳理了从勃朗特姐妹以来的英国女性小说家,从男性垄断的文学史中挖掘出一套女性文学传统。另一方面,主张根据女性经验来书写文学。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艾莱娜·西苏提出“女性书写”理论,倡导在文本写作中建构女性意识的文学来表达女性对自身存在方式的理解。西苏强调妇女与身体的关系:“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4]194身体写作是女性确立自身主体地位的革命性行动。女性写作的语言不同于男性语言,传统文学中男性的语言“是理性的、逻辑性的、等级的和直线型的”,而女性的语言“是不重理性的(如果不是不理性的)、反逻辑的(如果不是不逻辑的)、反等级的和回旋式的”[1]225。女性语言削弱了西方叙述传统中的语言、句法的传统规范,从而改变父权意识形态语言对女性的忽视与扭曲。
二、“修辞”观念对新历史主义文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历史和文本的关系问题是新历史主义的核心问题,也是新历史主义受解构主义“修辞”观念影响最深的领域。朱刚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中说:“新历史主义非常重视语言的修辞、隐喻、叙事、想象功能,使得新历史主义带有‘平面化修辞’和叙事模式,和解构主义十分相似,也就难免带上后者的形式主义之嫌。”[5]盛宁也在《二十世纪美国文论》中表示:“解构主义的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说白了就是‘咬文嚼字找缝隙’,只要有辞源学、训诂学的训练,就可以在词义演变的任何一个环节上找到需要的缝隙……即使是新历史主义这样的批评,尽管它声称反对解构主义批评的文化虚无主义倾向,主张回到文本的社会历史意义上来,然而在具体的批评方法上,我们则经常看到,它总要自觉不自觉地滑入解构批评碾出的深辙。”[1]207新历史主义以文本论对抗真实论、以修辞论反对模仿说、以解构论反对客观论、以新历史代替旧历史,都有解构主义修辞性误读理论的痕迹。
根据海登·怀特的元历史思想,历史事件不再能被直接感知,不可重现和复原,对历史的第一手把握已经不可能,对历史的了解只能依靠关于历史的记录。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只不过是一种文本,它总是被“叙述”(narrated)出来的,“这种叙述是语言凝聚、替换、象征化和某种贯穿着本文产生过程的二次修正的产物”[6]101,需要阐释才能存在。由于“历史文件不比文学批评者所研究的本文更加透明”[7]169,文学与非文学文本之间不存在界限,相互可以不断地交往沟通。这正好印证了德里达的观点:“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可以说,新历史主义对美国解构主义的改造,不过是把对文本的形式主义分析,改变为对社会历史的分析,社会历史在此成为一个超级的、充满歧义的解构性文本。就历史阐释本身而言,不存在我们所想象的统一的、大写的“历史”,所谓的历史其实是“断断续续充满矛盾”的历史叙述,它是小写的,以复数形式出现。由于叙述语言的修辞性,历史学家不可能客观地、科学地复原过去,只能从现在的视角去构造过去。历史话语的虚构性与文学语言虚构有相同之处,可以运用解构主义批评“踪迹”式的细读方法来挖掘历史文本中的多重意义。新历史主义学者与传统的历史研究者比较起来,“表现出对历史记载中的零散插曲、轶闻轶事、偶然事件、异乎寻常的外来事物、卑微甚或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情形等许多方面的特别的兴趣”[6]107,他们以历史文本中边缘性因素来解构和修正居于统治地位的意义形式,这正是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的批评模式。
三、解构主义误读理论中的“他者”观念对后殖民主义文论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德里达的观念批判对于重新思考社会组织的可能形式而言具有积极意义,这种社会组织形式现在只是在——我们或许会称之为——激进话语中微微显露。在女性主义思想中,在批判马克思主义中,在反种族主义斗争中,在工人合作组织中,在更具革新性的工商行业中,甚至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一些部门中,出现的问题大都来源于这同一个根本的问题:如何应对差异?”[8]“差异”、“他者”观念是后殖民主义的核心话语。德里达说:“解构,不仅仅在于批判或摧毁某种模式,而是要开始对世界化或全球化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诸多争论的关键问题进行思考,这些文化总是被轻易地一刀切式地划归为西方文化或远东文化的名下。”[9]德里达的延异理论是后殖民理论的直接理论来源,在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尤其是在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批评文字中,对殖民主义霸权的解构和对民族与叙述的重新阐释都可从德里达的理论中见出“踪迹”。德里达由语言的差异性原理推演出“延异”的概念,意义来源于符号之间以及符号内部的差异,全然的他者是不可避免的。文本的他者,并不限于其他的文本,也包括文化历史这种“他者”。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发生、发展历史,不存在主次、高低、优劣之分,所谓的“优势”、“劣势”只是一种相对的存在。解构主义批评家往往站在文本解读的边缘位置,重视揭示文本内部被忽略和遮蔽的边缘意义,这种边缘性位置实际上就是与中心相对应的他者性位置。
后殖民主义借以解构传统西方中心的文化观念,将东方文化放置到一个显著地位,启发人们关注东方文化的独特性和特殊地位。美国后殖民主义代表理论家霍米·巴巴标举边缘文化立场,认为差异性是客观存在、难以抹去的,在各种话语的交流中,任何同一性的话语都隐藏着一种话语暴力和文化霸权。依据解构的理路,所有这些代表边缘性的词汇,都只存在于谈论它的人的话语之中,对这些术语的界定也取决于它所被讨论的语境,由此权力话语出现了合法性的危机。被压制的非主流文化,完全可能对主导地位的殖民文化进行改写。只有承认差异的存在,鼓励误读,才能使双方真正达到理解和对话。他们通过对西方传统的经典文学文本的文化政治分析、对殖民文学的分析,挖掘西方建构他者的方式,解构西方形而上学的文本观;主张对文化的价值判断不能绝对化,应持一种宽容的、开放的态度;消解西方中心的话语霸权,在同一背后寻找差异,在差异中求得新的和谐,形成文化多元的格局。
总之,解构主义误读理论是文学语言研究的纵深发展,是一种专注于文学语言却又具有批判性、开放性的意义阐释理论。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特征,它为反中心、关注边缘的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阅读的、修辞学的、边缘研究的理论资源,这些后现代系统的文论把“误读”思想运用到文化批评中去,使这一以文学语言内部研究为主的阅读观念显示了多方面的理论力量。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后殖民理论的兴起,是运用解构思路进行的文学、文化的批评,“误读”作为一种消解文本中心的阅读策略和批评性尝试仍在进行,解构主义的思想原则广泛地渗透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解构主义误读理论深化和激活了人文科学,启发许多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拆解各种传统文化观念,创立了新的文化体系,开创了西方文学、文化和理论界无主流的多元格局。把解构主义误读理论与新批评、读者系统文论、后现代系统文论进行比较与归纳,能够进一步认识这一理论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位置,从历史的角度对之进行审视。
参考文献:
[1] 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2] 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 拉曼·塞尔登,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读[M].刘象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5] 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93.
[6] 海登·怀特.评新历史主义[M]//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7]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M]//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8] 罗伊·博伊恩.福柯与德里达:理性的另一面[M].贾辰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24.
[9] 德里达.南京大学座谈记录[M]//杜小真,等.德里达中国讲演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93.
责任编校:林奕锋
The Influence of the Misreading Theory of Deconstructive Criticism on Modern Western Literature Theory
WANG Min
(Chinese Department,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Shaanxi, China)
Abstract:The misreading theory of Deconstructive Criticism correlates closely to the modern western literature theory. The criticalness and openness of the misreading theory offer theoretical resources of reading, rhetoric and marginal research for Feminism, New Historicism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Feminism can be regarded as the misreading of the traditional male-centered literature and literature criticism. New Historicism insists on text vs truth, rhetoric vs imitation, deconstructive theory vs objective theory and new history vs old history. All these show signs of the rhetoric dimension of the misreading theory of Deconstructive Criticism. At the same time, the “Other” concept in the misreading theory has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Postcolonial Theory.
Key words:deconstruction; misreading; Feminism; New Historicism; Postcolonialism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15)04-0027-04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5.04.007
作者简介:王敏,女,湖北襄阳人,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研究”(10YJC751088)。
*收稿日期:2014-12-28
网络出版时间:2015-08-20 12:55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50820.1255.0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