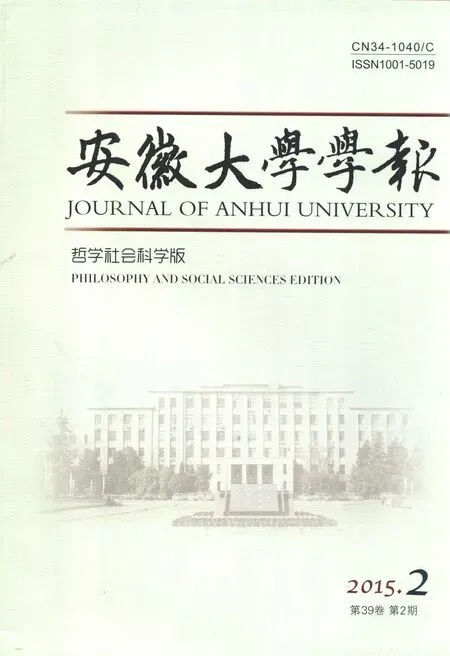论破窗效应及其在犯罪治理中的应用
伍德志
破窗效应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心理现象,在西方国家的城市执法与犯罪治理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并取得良好的效果。破窗效应是指信息匮乏者可能在有限的正面或负面表象信息的误导之下,做出合法或违法的行为,而且出于做出决定的迫切需要,信息匮乏者会人云亦云,不计风险与后果地模仿他人行为,而不论其是合法还是违法。破窗效应源自理性有限的人类的模仿心理,呈现出明显的盲目性与扩散性特征。根据破窗效应,由于公民守法可能并不是一个基于充分信息基础上的理性认知过程,执法者就可以利用破窗效应通过一些有意或无意的印象管理策略“欺骗性”地放大法律制裁风险,使人们往往在“错误”的假定之下做出遵守法律的正确决定。尽管破窗效应可能会树立坏榜样,导致违法行为的扩散与模仿,但如果我们能够恰当利用公民与执法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通过一系列印象管理策略将正面信息符号注入公民与执法者之间的认知鸿沟,即便在实际执法力量非常不充分的情况下,我们同样也能收到动员公民普遍守法的功效。破窗效应还具有对法律制裁进行再符号化的意义,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以一种更加虚幻的暴力印象替代暴力符号本身,这不仅能够保留暴力的信息符号价值,而且还会使执法更加人道化与文明化。破窗效应也能够为中国城市建设与城市执法以及对恐怖活动的打击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
一、破窗效应、信息匮乏与相互模仿
破窗效应强调的是环境信息对于犯罪的诱导。尽管在西方很早就有学者意识到了犯罪与环境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如孟德斯鸠、弗莱彻、哥里德、奎特勒特、盖瑞等早期学者对犯罪与环境地理特征之间的关系均有研究,但这些研究主要限于宏观层面,而没有涉及特定的环境与具体犯罪之间关系的微观层面①参见李本森对破窗理论的历史渊源的研究,李本森:《破窗理论与美国的犯罪控制》,《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而且这一类研究大多限于对犯罪与环境关系的外在描述,还没有对这种现象的内在运作特征与社会心理原因的深刻分析,也没有提出通过环境治理与环境设计来治理犯罪的明确构想。而破窗理论则对犯罪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细致具体的经验研究与分析,这能够为犯罪治理提供更具有实践价值的指导。
破窗效应现象最早的具体经验研究可能要追溯到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的汽车实验研究。尽管津巴多并没有明确地提出破窗效应,但他进行的研究与后来提出的破窗效应异曲同工。津巴多将两辆同样的汽车中的一辆放在治安比较混乱的贫困街区,另外一辆汽车放在治安非常良好的街区,并将两辆汽车的车牌都摘掉与车顶棚都打开。后来奇异的情况发生了。对于位于治安混乱街区的那辆车,先是有人拿走了散热器与电池,最终三天内几乎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被逐渐盗取殆尽,而放在治安良好街区的汽车则在一个星期内都无人问津。津巴多和他的学生后来当着路人的面开始公开用大锤砸良好街区的汽车,而这引起了周围人的起哄、围观与效仿,最终这辆车被掀翻,并被完全毁坏②See,Phillip G.Zimbardo,The Human Choice:Individuation,Reason,and Order Versus Deindividuation,Impulse,and Chaos,W.T.Arnold and D.Levine(eds.),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iation,Vol.17,1969,pp.237-307.。之所以出现这种对比鲜明的结果,原因就在于治安混乱的街区所体现出来的种种混乱、肮脏的外在表象,给予了潜在违法犯罪者重要启示:这个街区是无人管理的,并由些断定违法犯罪风险是比较低的,从而就激发了更大胆的犯罪动机。而津巴多砸汽车所引起的效仿则进一步表明,即使在治安良好的街区,不明真相的公众也可能在不准确信息的误导之下,做出一些非理性的模仿行为。
另外两位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威尔森与乔治·科林在1982年的一篇论文中则明确地提出了为学界所熟知的破窗效应现象,并对美国各城市的执法模式与犯罪治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认为,一栋建筑物如果有一个破窗户得不到修理的话,会导致更多窗户被损坏,得不到修理的破窗会向人们暗示这个社区没有秩序,因此会激起更大胆的破坏行为。城市中的犯罪现象与此类似,也具有扩散性与传染性。对于任何被忽略的轻微违法行为或不文明行为,如滋事、醉酒、逃票,我们都应该严厉禁止,因为这些轻微的违法或不文明行为,如果初期得不到惩治,就会渐渐蔓延开来,造成更严重的犯罪现象。这不仅使社区居民认为社会控制已经崩溃,从而逃离社区,致使社会控制水平进一步下降;而且也给潜在的犯罪分子提供启发,让他们推断社会秩序混乱或者警察监控薄弱,进而制造更多犯罪,最后雪球越滚越大,最终导致社会秩序的完全崩溃③James Q.Wilson & George L.Kelling,Broken Windows,The Atlantic Monthly,Vol.211,1982,pp.29-38.。我们对周围环境的认知往往是混沌一片的,但在这混沌一片中,某些具有高度象征性但也许未必相关的信息符号就可能左右我们对复杂环境的判断,如一扇破窗,往往会成为人们判断犯罪风险的重要依据,并由此引导我们做出一些不理性的破坏举动。破窗效应还具有恶性循环的趋势,因为混乱的社区环境特征与不安全地点的社会表征还会增加犯罪率也许实际并不高的地区的居民对犯罪的恐惧感④Sergi Valera and Joan Guàrdia,Perceived Insecurity and Fear of Crime in a City with Low-crime Rate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Vol.38,2014,pp.195 – 205.,这就可能致使人们逃离社区,结果就是社区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水平进一步降低,导致犯罪频率与严重程度的进一步上升⑤R.B.Taylor,The Incivilities Thesis:Theory,Measurement and Policy,R.H.Langworthy(eds.),Measuring What Works:Proceedings from the Police Research Institute Meeting,U.S.Department of Justice,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and Office of Community-Oriented Policing Services,1999,pp.65-88.。初期的失序会使居民对社区安全环境丧失信心从而导致逃离社区,而居民的逃离则会使社会秩序失去控制的信息更加明显可辨,由此进一步降低潜在违法犯罪者的风险认知,从而又激发更广泛的犯罪动机。
破窗效应现象的原因首先在于信息匮乏。由于人们无法获知政府执法效率与秩序安全情况的具体信息,他们就会根据一些容易获知但未必准确的表面信息来判断违法风险大小。当城市街道整齐明亮、无人滋事醉酒、警察定点巡逻、社区生活井然有序时,他们就会潜在地假定社会控制比较完善,执法力量比较强大,大家都能遵纪守法,而对于那些同样信息匮乏的潜在犯罪者来说,他们也会做出犯罪被惩罚的风险比较大的推断,从而遏制自己的犯罪动机。但如果社区日常秩序混乱,被破坏的窗户与汽车会向公众暗示这个社区执法力量薄弱,这会使潜在的犯罪者假定犯罪风险比较低,从而可能由比较轻微的违法行为进一步升级为更严重犯罪。破窗效应还反映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特征:由于无知而产生的模仿性。信息匮乏不仅使人们产生信息的压力,也会产生规范的压力,信息匮乏使得做出决定的信息依据与规范正当性都成了问题,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人如何行为就成为人们“一个强大且有用的知识来源”①[美]Timothy D.Wilson,Robin M.Akert:《社会心理学》,侯玉波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202~236页。。在法学理论中,我们一般认为人们遵守规范是出于社会共识或个人利害权衡,但信息的匮乏则会使人们难以辨识何为共识、何为利害,从而导致对信息饥不择食,在面对令人困惑的社会情境时,出于做出决定的社会压力,会盲目跟随他人,做出在事后看来不可理喻的不合法与不道德的行为。这里的信息压力与规范压力也类似于孙斯坦所谓的信息连锁效应与名誉连锁效应②[美]凯斯·R·孙斯坦:《风险与理性》,师帅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6~48页。。人们行为的正当性,不仅取决于合理性,也取决于道德正确性,而对于信息匮乏者来说,他人如何行为就成了如何界定这两者的关键依据。在集体行动的盲目模仿中,任何既定的合理性与道德正确性都可能被颠覆,人们是否合作主要取决于是否相信他人也采取同样的行动的期待与信念,而不在于对于违规行为的惩罚③[美]罗德里克·M·克雷默等:《集体信任与集体行动》,刘穗琴译,[美]汤姆·R·泰勒等编:《组织中的信任》,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第482页;Dan M.Kahan,The Logic of Reciprocity:Trust,Collective Action,and Law,Michigan Law Review,Vol.102,no.1,2003,pp.71-103.。人们是否守法也遵循类似的集体行动逻辑,他人的行为是自己的行为风险与收益的重要指示器,在他人行为的示范之下,自己既可能不自觉地变得遵纪守法,但也可能会变得盲目与疯狂,而破窗效应正展示了这一点。社会中所展现出来的人人文明礼貌、生活秩序井然、街道整齐安宁的表象会使人们假定他人都会遵纪守法,这种对他人都会自觉遵纪守法的期待与信念也促成了自己的遵纪守法,并进而将这种推断延伸至更严重也更隐蔽的犯罪行为上,从而进一步遏制自己的犯罪动机,减少了犯罪。反之亦然。
破窗效应对传统法律理论关于守法的理性解释模式提出了挑战,因为人们在社会环境中各种关于有序或失序并且可能失真的信息符号影响下的行为选择远不是对惩罚风险的具体理性计算。信息符号也仅仅是一种符号,符号之所以必要,那是因为我们看不见符号背后的东西,因此符号并不能排除现实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④[德]N.卢曼:《社会的法律》,郑伊倩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页。。各种关于社会控制能力与社会秩序状况的符号完全可能误导我们对政府执法效率的认知。破窗效应固然可能导致违法行为的大规模扩散,但如果我们能够及时修复破窗,即使在政府执法效率没有实际提高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操纵关于违法风险的社会符号来“欺骗性”地提高人们对违法风险的主观认知,从而在客观上实现减少违法行为的功效。正由于此,破窗效应能够为政府的执法模式提供重要启发,政府可以通过一系列减少“破窗”的信息控制策略如社会环境的建设、对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治理、对警力象征性存在的强调,来营造社会秩序的正面信息符号,放大实际可能非常有限的社会控制能力,使潜在违法犯罪者形成他人都在遵纪守法的普遍印象,从而自觉遏制违法犯罪动机,并最终减少违法犯罪。破窗效应不仅可以用更少的执法资源更好地预防违法犯罪,而且还可以减少人们对违法犯罪的恐惧感,提高公民生活品质。由于公民与政府之间不可避免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政府执法能力的有限性,破窗效应不仅具有普遍的可能性,而且具有很大的必要性。
二、破窗效应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破窗效应之所以能够操纵人们对于违法犯罪的风险意识,是源于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破窗效应之所以对政府执法非常必要,则是因为政府执法能力的有限性以及暴力制裁信息价值的弱化。政府的实际执法能力与效率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低得多,但由于公民与政府之间所存在的高度信息不对称,公民大多数情况也不能准确判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信息差异,通过一系列的印象管理策略将一些正面的但也可能并不准确的信息符号注入公民与执法者之间的信息鸿沟,从而以一种“欺骗性”的方式来展示貌似普遍有效的执法能力,掩饰自己实际上非常有限的执法力量,由此使人们相信法律是普遍有效的并做到自觉守法。在此过程中,暴力制裁作为一种符号还能够进一步被更间接的暴力印象所再符号化,执法在保留暴力的信息价值的同时,能够避免更多的暴力,执法也因此变得更加人道化与文明化。
(一)破窗效应的可能性: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破窗效应对于提高公民守法水平的可能性源于公民与政府之间不可避免的信息不对称。政府运作比较依赖于专家理性,但大多数公民是从道德角度判断公共决策,因为道德是克服无知的一种替代方式①[德]尼克拉斯·鲁曼:《对现代的观察》,鲁贵显译,台北:台湾远足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5年,第194页。。这两者常常不能进行有效沟通。政府的统计数字由于缺少直观性而往往得不到大多数公民的首肯,这就源于信息不对称。关于守法的理性主义解释认为,公民的守法主要出于对制裁威胁的理性计算,如霍布斯认为惩罚对于法律的实施是必不可少的,人们守法主要是由于惩罚的威慑②[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延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8页。。而边沁根据其功利主义原则,认为人们遵守法律的动机有两种:引诱性动机与强制性动机,前者为奖赏,后者为制裁③[英]杰米·边沁:《论一般的法律》,毛国权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171~176页。。韦伯也认为强制手段对于法律的实施具有根本性意义④[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47页。。理性主义解释的最大问题在于信息的局限性,公民实际多数情况下并不能获得关于政府执法效率与守法所产生的利益回报的具体信息。很多守法行为对于公民来说利弊得失是不清晰的,甚至有些守法行为对于个人来说具有明显的不利性,如遵守税法的行为,在税法这一领域,很容易产生“搭便车”行为。而且公民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准确地判断自己所缴纳的税款与所获得的公共服务之间是否能够对应起来,很多公共服务只是一种弥散的好处,惩罚风险也不得而知,公民遵守税法所产生的利弊并不能被精确计算。而且由于个人所得税申报的隐蔽性,公民实际上也很难计算违法行为被执法机关发现的概率与风险⑤See,John T.Scholz,Trust,Taxes and Compliance,Trust and Governance,Valerie Braithwaite and Margaret Levi(eds.),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8,p.139.。政府的执法效率到底有多高,很多时候当事人也并不明确。其他制度领域的情况也非常类似,如日本有学者指出,人们是否选择利用审判制度,并不是合理计算的结果,由于审判涉及的因素太复杂,对利用审判可能带来的利弊以及是否会实现期待的利益进行预测是非常不确实的⑥[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0~211页。。因此,人们守法的动机基础并不是出于对风险收益的理性计算。不仅如此,即便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很多法律对某些群体施加的成本与给予某些群体的权益,也是无法精确计算的,人们很多情况下会根据直觉来判断一项法律对社会的好处。对于这些法律,要想人们给出一个明确的肯定或否定态度是很困难的,大多数人也缺乏相关信息与知识来判断一项法律决定对群体产生的各种影响。例如,我国制定《劳动合同法》的目的本在于更好地保护劳工权益,但经济学家却指出劳动法无固定期限条款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可能会收到反效果,雇佣成本的增加会使企业主在加工资与聘用员工上变得更加谨慎,这反而减少了涨工资与就业的机会①张五常:《新卖桔者言》,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284~294页。。很多法律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极为复杂,要想对这些法律有一个准确的理性权衡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而且,政府很多情况下的产出主要是一种奥尔森所谓的“集体物品”,也即不论是那些已经付费者,还是那些“搭便车者”都可以享用集体物品②[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12~13页。。这意味着对于绝大多数公民来说,由于政府制定与实施法律所产生的收益会为所有人所共享,遵守法律为个人所带来的收益并不清晰。
由于信息不对称,当事人对法律制裁的主观风险常常会受到一系列偶然性或者不相关的因素的误导或影响。例如,当事人对惩罚风险的评估可能受到启发式(heuristics)认知心理的影响。例如,百分之十的被发现与惩罚概率的总风险会被当事人视为低于百分之五十的被发现概率与百分之二十被惩罚概率合计后的风险,尽管两者客观的总风险是相同的,但由于较高的被发现概率是一种显著性(salience)因素,这会影响到人们对法律制裁风险的主观判断③John T.Scholz,Trust,Taxes and Compliance,Trust and Governance,Valerie Braithwaite and Margaret Levi(eds.),p.143.。由于人们的信息局限性,人们往往会根据一些信息成本较低的显著性因素来判断风险,即使显著性因素的发生和实际的风险大小没有关系。被高估的风险是引人注目的和具有轰动效应的事件,而被低估的风险则是不引人关注的事件,人们对危险的反应通常是建立在后果的恶劣程度与形象程度之上的,而不是基于对后果发生概率的估计④[美]凯斯·R·孙斯坦:《风险与理性》,第42、56页。。如果你居住的小区发生了一件命案,这种鲜活的事件会立即让你变得提心吊胆,在你看来,被谋杀的风险变高了,而客观风险可能并没有变化。有美国学者通过对泽西城的治安状况、社会心理以及警察局的犯罪统计资料的调查后认为,犯罪率的变化对于人们对犯罪的恐惧感没有明显的影响⑤Joshua C.Hinkle and David Weisburd,The Irony of Broken Windows Policing:A Micro-plac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order,Focused Police Crackdowns and Fear of Crime,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Vol.36,2008,pp.503-512.,公众对于法律维护秩序或实现公正的要求与客观的犯罪率统计数字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也就不可能等同起来⑥George Kelling and Catherine Coles,Fixing Broken Windows:Restoring Order and Reducing Crime in Our Communities,Ldondon:Touchstone,1998,p.238.。公众往往是从街头巷尾的耸人听闻与八卦传闻中获知犯罪风险的,而与讲究证据与统计的专家理性有着天壤之别。这一点就如同人们对于客观风险更低的飞机的风险认知往往高于实际风险更高的汽车的风险认知,因为飞机事故直观上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汽车事故。因此,潜在犯罪者同样无法根据客观犯罪率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机会主义行为。又如,人们对风险的评估还受到模糊效应(ambiguity effect)的影响,人们如果知道违法被发现的准确概率,相比于人们并不能肯定这种猜测的情况,会更有可能实施违法行为⑦John T.Scholz,Trust,Taxes and Compliance,Trust and Governance,Valerie Braithwaite and Margaret Levi(eds.),pp.143-144.。模糊效应的产生也源于公民的信息局限性,因此即便执法机关的执法能力没有实质性的提升,但相比于定期的执法,不定期的执法对于违法行为的震慑效果更大。公民面对不定期的执法往往有着更高的风险判断,不定期执法尽管不可预测,但往往显得突然,因此更令人印象深刻。
政府与公民之间高度的信息不对称固然可能会误导公民做出是否守法的决定,但正由于信息不对称,这也为政府在执法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提高公民守法水平提供了可能。信息只是一种符号,符号的所指与能指之间总是会存在难以克服的差异,符号固然提供了操纵认知与强化偏见的可能,但鉴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如果我们能够控制好符号的意义指向,那么符号也可以成为引导人类行为的有益指南。正由于信息作为符号所具有的填补认知鸿沟的功能,破窗效应作为信息不对称环境下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也为政府从正面激励公民守法提供了可能。
(二)破窗效应的必要性:政府执法能力的局限性与暴力制裁信息价值的弱化
破窗效应的意义还不仅仅限于弥补信息不对称,鉴于政府执法力量的固有局限性,破窗效应还能减少政府的执法负担。破窗效应不仅能够实际减少犯罪率,而犯罪率减少之后政府执法力量也会相对变得强大,而这又为政府进一步修补更少的破窗、实现更显著的破窗效应提供更大能力。传统法律理论一般认为法律实施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这可能是因为暴力制裁在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的比较中有着显著的标志性意义。卢曼曾指出,“如果法律的功能在于依靠权力和制裁来保证所规定的作为或不作为的贯彻,那么实际的法律运行就会经常甚至多数情况下不能自己运转”①[德]N.卢曼:《社会的法律》,第78页。。以我国香港特区为例,香港是一个高度法治化的地区,香港也有着极为良好的治安环境,香港每10万人中的犯罪率远低于东京、纽约、巴黎、伦敦、多伦多这些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但即便如此,香港警察的破案率多年来也只能维持在45%左右,这并不是说香港警察执法效率低,恰恰相反,香港警察的破案率远远高于上述发达国家的城市,如纽约市警察局的总体破案率为35%、日本警察厅的总体破案率为33%,以及伦敦警察厅总体破案率为21%②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务处:《详细罪案统计》,http://www.police.gov.hk/ppp_sc/09_statistics/csd.html,2013年11月24日访问。。其实这些统计数字还只是根据被发现的罪案统计出来的,还不包括那些未被发现的罪案,因此实际的犯罪率要高于统计出来的犯罪率,而统计出来的破案率也低于实际的破案率。国家的各种监控力量,如政府、警察、法院并没有收集一切违法信息的能力,如果法律的实施完全依赖于国家的信息收集能力与监控能力,很多法律将根本得不到实施。如在美国的刑事法律领域中,被逮捕、审判与监禁的客观风险是相当低的,强奸的制裁风险只有12%,抢劫的制裁风险只有4%,恐吓、盗窃与汽车事故的制裁风险只有1%③Tom R.Tyler and Yuen J.Huo,Trust in the Law:Encouraging Public Cooperation with the Police and Courts,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2,p.22.。法律制裁风险比统计出来的犯罪率低得多,因法律制裁风险还涵盖了没有被警察发现的案件。如果客观风险与主观风险完全一致,那么人们不论对于社会还是政府都会丧失信心,而犯罪行为在理性的指导下多数情况下也会变成一项有利可图之事。对于数量更多的民事违法行为与行政违法行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政府与公民对这些违法行为的重视程度远逊于刑事犯罪的情况下,法律制裁效率会低得多。法律之所以难以做到追究大部分的违法行为,是因为执法资源总是非常有限的,执法机关几乎总是从最容易侦破的那些案件中选择他们的追诉对象④[美]理查德·波斯纳:《联邦法院:挑战与改革》,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17页;。不仅如此,警察部门往往还根据对违法行为严重性的主观感觉来决定是否执法⑤[美]让妮娜·贝尔:《警察与警务》,刘毅译,[美]奥斯汀·萨拉特编:《布莱克维尔法律与社会指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2页。。正是执法资源的有限性导致了选择性执法这一现象。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很多法律是通过民间的非正式规范机制得到实施的,但毫无疑问,法律对于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护仍然是根本性的。尽管政府的法律实施能力存在种种局限,但如果我们根据破窗效应虚构信息符号,放大政府执法能力,就可以在不增加执法资源的情况下,提高人们对违法犯罪的风险认知,从而起到遏制违法犯罪的功效。
由于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执法资源的有限性,还导致了这样一种悖论性现象:暴力本身可能会成为政府展示暴力实施能力的一种信息符号。法律制裁有很多种,但暴力制裁仍然是必不可少的“最后一招”,尽管暴力制裁大多情况下备而不用。作为政府执法手段核心机制的法律制裁,特别是暴力制裁,在多数情况下被塑造成展示规范有效性的信息符号,而不在于实际的行为控制。暴力的本身在任何时代的国家治理中都不可能实施到每一个人,但通过符号化我们就超越人类在经验上的时空局限性①[英]A.N.怀海特:《宗教的形成/符号的意义及效果》,周邦宪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1页。,将暴力的效果达至更广泛的范围。暴力作为权威基础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高度的结构独立性,因为暴力可以脱离语境的限制仅仅以力量优势为前提,而不受等级秩序、角色语境、群体身份或价值判断等结构性因素的限制②[德]尼可拉斯·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第144~145页。。暴力的效果不依赖于各种文明结构关系,因此是最为直观的信息符号,其所体现出来的信息价值可能远远超越实际的暴力实施能力。暴力是以“行动取代行动”③[德]尼可拉斯·卢曼:《权力》,第70页。,正由于这种物理力量的自然性与原生性,暴力相比于各种文明创造物,如文字、文化、政治、道德,少了结构上的繁琐束缚,能够诉诸最原始的生物本能,因而在社会秩序出现突发状态、文明创造物由于结构过于复杂而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时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不论是社会控制能力比较弱的传统国家,还是社会控制能力比较强的现代民族国家④关于传统国家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控制能力的分析,请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50~72页;以及[英]安东尼·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郭忠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161~180页。,都极为倚重暴力制裁的信息符号意义。如古代西方与中国都有着极为残酷的刑罚,并被公开实施,而且极富仪式化与戏剧化,很多触目惊心的酷刑是无法从行为控制的角度得到解释的,其更大的意义不在于其强制功能,而在于信息展示功能⑤可参见福柯对于欧洲中世纪酷刑的论述,[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35~77页。而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酷刑,我们通过对中国法制史的了解已经很熟悉了。。即便到了现代社会,法律制裁已经实现了文明化与人道化,但其信息符号意义仍然大于其实际的行为控制意义。卢曼认为,法律制裁无论是为了促使他人实施符合期望的行为,还是为了在遭遇失望时宣示既定的期望,法律制裁的主要意义都不在于制裁,而在于宣示⑥[德]尼可拉斯·卢曼:《法社会学》,第97、135页。。如进入公开审判程序的案件都是属于少数,但正因为是少数,这些少数案件中的法律制裁对于法律整体的公正性与有效性就具有了指标性与代表性意义。如果少数进入公开审判程序的案件都得不到有效处理,那么法律制裁的信息符号价值将会受到破坏,其影响范围将远远超过个案本身,并影响到那些无数尚未进入法庭程序的当事人的行为决定。这正如南京彭宇案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并不仅仅限于个案本身,而是现实当中无数的根本不会进入诉讼程序的行为决定。当人们再次看到摔倒老人时,决定他们行为的既不是当下这个老人的诬赖风险,也不是法律支持他们的胜诉概率,因为这些都不得而知,而是彭宇案中法律在制裁倚老卖老上的无能为力这一众所周知的信息。这一来自过去案例的信息决定了未来大多数人看见摔倒老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心理。当法律制裁作为一种信息符号的意义受到破坏时,所影响的也不仅仅是个案公正,而是未来无数的个人行为决定。政府有时为了维护政府的象征性权威,甚至罔顾事实真相,摒弃复杂的司法调查与论证环节,通过近乎赤裸裸的暴力维护法律制裁的普遍信息价值。如我国80年代的“严打”所体现出来的重典治国及其所制造的无数冤案也反映了政府在社会秩序濒临崩溃的危机之下对暴力制裁的信息意义的强调,严打中的公审公判、游行示众、公开处决极为直观地传达了政府打击犯罪的决心与能力的重要信息,从而使民心与社会秩序能够得到快速的稳定⑦陈兴良:《严打利弊之议》,《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尽管这些做法已经不符合现代司法理念,但面对政府执法力量由于犯罪高发而力有不逮的严峻形势,政府已经等不及根据严格而又费时费力的现代司法标准来处理犯罪案件,而只有简单化的暴力制裁才能够起到快速震慑犯罪、树立公众信心的更好效果。这里恰恰是利用了暴力制裁的符号价值。暴力制裁在现代社会作为放大政府执法能力的符号价值已经大大弱化,大多数国家不仅已经不允许刑罚的公开展示,并且以更强调人权的司法程序掩盖了暴力在视觉上造成的不快或者用自由刑替代了对肉体的直接伤害。与此相应,很多著名学者如罗尔斯、哈贝马斯从现代人权观念出发,将守法的正当性完全建立在实质性共识或程序性共识的基础上,但面对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与不稳定性,暴力特有的结构独立性与普遍信息价值即便对于已经极为人道化的现代法治秩序仍然具有必不可少的意义,尽管很多人出于道德立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并同时兼顾到人权的要求,我们可以对法律制裁进行再符号化,以一种更加虚幻的暴力印象进一步替代暴力本身。破窗效应中的各种印象管理策略就在于实现这一点。
三、破窗效应中的印象管理策略及其实践效果
由于政府的执法效率的低下以及暴力制裁符号价值的弱化,普遍的守法就不可能建立在公民对实际法律制裁风险的理性认知上,但正如银行的可信性可以不必计较其存款大于贷款,只需我们相信其他人都不会同时去挤兑,政府执法能力的可信性也可以不必依赖于其实际拥有的警力超过其对全部法律的实际实施能力,而只需我们相信其他人不会同时造反①[德]尼可拉斯·卢曼:《信任》,瞿铁鹏、李强译,上海:上海世纪集团,2005年,第77、91页。。这种相互信任不仅可能基于实质性共识或程序性共识,也可能基于法律制裁的普遍可能性,但法律制裁的普遍可能性不可能建立在无所不能的暴力基础上。由于法律制裁本身的局限性与实施成本的高昂,法律制裁即便作为信息符号,还必须被“再符号化”,以成本更低的信息符号机制来进一步塑造法律制裁的普遍可信性。而破窗效应在此就有了用武之地。根据破窗效应我们就能利用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差异,将正面的信息符号注入两者之间的认知鸿沟中,从而放大政府的执法能力,提高违法犯罪的风险认知,遏制违法犯罪动机,促使公民自觉守法,从而达到和实际法律制裁类似的效果。借用戈夫曼的术语,我们可以将这些信息控制策略称为印象管理②[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45、179~201页。。与戈夫曼不同的是,他所研究的是人际关系中的印象管理,目的在于维持自我形象的一致性与可信性,而政府的印象管理目的在于维持社会控制能力与社会秩序安全的可信性,但两者都是因为真相往往比较令人恐惧,而必须通过掩饰真相来维护安全。通过运用破窗效应的各种印象管理策略,我们不仅可以减少人们对违法犯罪的恐惧感,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也可以更好地预防违法犯罪,大大节省执法资源。而随着违法犯罪的进一步减少,政府会更加游刃有余地处理少发的违法犯罪,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社会治安环境的改善会进一步强化社会控制能力的符号表象的正面意义,使得人们关于违法的主观风险进一步降低,违法犯罪率因此会更低。任何反映社会治安状况与社会控制能力的外在信息符号都可能成为引导公民判断违法犯罪风险的印象管理策略。印象管理策略只是一种表象,但任何实在都是通过表象展现出来的,实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还不如表象来得坚固与有用,因此,这里更重要的不是真假,而是是否有用。
(一)环境设计与可防卫空间
城市环境的好坏也是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与执法效率的一个重要信息符号。在西方国家,基于环境设计的犯罪预防理论(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简 称CPTED)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处理犯罪以及对犯罪的恐惧感的策略③See,G.Steventon,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ousing and Home,Amsterdam:Elsevier,2012,pp.280-284;P.M.Cozens,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and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 for the British City,Cities,Vol.19,no.2,2002,pp.129-137.。环境设计中的各种策略,如地面景观、公共照明、街道模式、物理障碍、安全设施、个人化标志、居屋周围环境的维护与垃圾的处理等等,能够强化所有权意识,促进非正式监督与日常监督,减少违法犯罪接触目标的机会、提高潜在违法犯罪者的风险意识,营造社会秩序良好与安全保障制度健全的正面印象①See,Massoomeh Hedayati Marzbali,et al.,The Influence of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 on Victimization and Fear of Crime,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Vol.32,2012,pp.79-88;Siti Rasidah Md Sakip and Aldrin Abdullah,Measuring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 in a Gated Residential Area:A Pilot Survey,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Vol.42,2012,pp.340-349.。这些策略并不能完全从对违法犯罪的实际打击的角度来理解,其也是展示政府社会控制能力的外在信息符号。如果一个城市道路宽敞,卫生整洁,绿化常新、夜晚灯火通明,居民生活秩序井然,我们就很容易因此判断该地区有着良好的社会控制,这种判断会进一步延伸至对政府打击违法犯罪时的执法效率的判断,从而能够影响人们对违法犯罪风险的主观认知。在政府执法效率实际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人们基于这种可能不正确的风险认知也会自觉遏制自己的违法犯罪动机,同时,这也会在犯罪率可能并未实际降低的情况下相应地减少人们对犯罪的恐惧感。一个没有路灯、肮脏、狭窄的恶劣街道环境容易导致更高的犯罪率,因为这向人们暗示此处犯罪高发,法律力量薄弱,容易激发犯罪动机。城市的恶劣环境就像瘴气一样会使犯罪产生传染性。法律对此的处理就不能仅仅着眼于通过警察力量打击犯罪,而也需要通过清除垃圾、安装路灯、拓宽道路、改善公共卫生等措施来建立一个看起来干净明亮的环境,在这种看似安全的环境中,人们对于他人的行为动机会产生普遍信任②David Sunderland,Social Capital,Trust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1780-1880,New York:Routledge,2006,pp.98-99.。城市环境是否良好能够为每一个人所观察与理解,人们很容易推此及彼,从而也能够对他人是否同等遵纪守法以及政府控制违规行为的能力抱有信心。有学者通过对伦敦三个街区的经验研究指出,改善城市照明在减少社会骚乱与不文明行为进而在减少犯罪以及对犯罪的恐惧感上有着极为显著的效果,城市照明以及由此增加的人流与车流,是一种社会控制与监督的“无声信号”,由此会增加公众对犯罪风险的主观认知,从而对潜在侵犯者形成心理威慑③See,Kate Painter,The Influence of Street Lighting Improvements on Crime,Fear and Pedestrian Street Use,after Dark,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Vol.35,1996,pp.193-201.。城市照明除了通过更大的可见度与透明度方便了社会的可持续监控之外,对于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也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美国有一项对公共住宅的调查表明,由于惧怕犯罪,洛杉矶公共住宅的四分之三居民晚上出门都会故意将电灯、电视机、收音机打开④刘广三:《城市居住环境与犯罪预防》,《山东法学》1994年第3期。。这种做法可能为很多人所熟悉,这实际就是利用潜在犯罪者与实际安全状况之间的信息差异并通过操纵虚假信号放大犯罪风险。而在中国有学者对沿海城市的犯罪特征研究也显示,旧城区往往是犯罪高发的地区⑤王益澄、林 玲:《东部沿海城市犯罪问题的城市地理学研究》,《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1期。。这并非偶然,因为旧城区的建筑大多显得破旧,防盗设施不够健全,这容易形成破窗效应,使潜在犯罪者误以为政府管理松懈,从而激发犯罪动机。特别是在城乡接合部,土地利用、道路设施、地面景观缺乏统一规划,住宅、厂房、农田、菜地相互交错,城乡之间文化与人口互相交织,不动产所有权与物业管理混乱不堪⑥王发曾:《城市犯罪中的边际空间盲区与综合治理》,《人文地理》2004年第1期。,这样的边际空间特征除了不利于犯罪的实际治理外,也会给潜在的犯罪者以秩序失控的强烈暗示,从而成为违法犯罪的重要心理诱因。近年来流动人口犯罪高发,在某种程度上也与流动人口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流动人口大多居住于城乡交界地带,这个地带房屋设施破旧、卫生条件差、垃圾遍地、社会管理混乱,这些环境特征具有强烈的犯罪暗示⑦楼伯坤、满涛:《我国流动人口犯罪的防控策略》,《犯罪研究》2013年第6期;刘晓龙、叶萍:《破窗理论与流动人口犯罪控制》,《河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使得已经脱离乡土熟人关系束缚的流动人口更加容易走向犯罪。由此看来,我国目前在各个地方风风火火推行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也许客观上减少了犯罪的发生。在很多人看来,我国各个城市所建设的漂亮的道路、公共设施、大楼是地方官员为了获取政绩而建设的面子工程,但面子工程客观上也反映了政府出色的管理能力与组织能力,因为做不好面子工程的政府同样也做不好里子工程。潜在犯罪者置身于井然有序的城市公共设施中时,也会潜在地假定政府在打击违法犯罪上具有出色能力。
另外,某些环境设计策略如物理障碍、安全防范设施、个性化标志、居屋周围环境的维护还具有象征所有权领地的信息价值,这些社会环境表征都构成了纽曼所谓的“可防卫空间”。所有权并不仅仅是法律与个人空洞的言辞宣告,所有权还可以通过上述种种环境特征信息表达出来,这些信息都含有对侵犯所有权的正式或者非正式的监督与抵抗等潜在意义①See,Oscar Newman,Creating Defensible Space,U.S.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Office of Policy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1996,pp.9-30;Massoomeh Hedayati Marzbali,et al,The Influence of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 on Victimization and Fear of Crime,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Vol.32,2012,pp.79-88.。所有权领地与可防卫空间的信息标志既可以是实质性的,也可以是象征性的,如围墙、栅栏、院门、台阶、篱笆、墙墩、房门、标志以及铺设不同颜色的路面砖等等②刘广三:《城市居住环境与犯罪预防》,《山东法学》1994年第3期。,但象征性的所有权标志就足以为他人设置心理障碍从而对违法犯罪者起到震慑作用。很多犯罪实际上就发生于没有明确所有权归属的空间盲区,如楼梯、走廊、停车场以及其他一些过渡性或边际型的空间③王发曾:《城市空间环境对城市犯罪的影响》,《人文地理》2001年第2期。,这些空间盲区不仅可能降低居民的防护意识,也能够向潜在违法犯罪者暗示非正式社会监督与可防卫空间的缺失。凡是有人居住或活动的地理空间都应有所有权标志,并能够得到人们的日常维护。不论是对于公共设施还是个人设施的维护,在昭示所有权领地的同时都能够使环境特征以及环境中行为的性质变得更加一目了然,不仅能够激发相关或不相关的人的注意与监督,也并预示了当受到侵犯时可能遭遇抵抗的可能性。尽管所有权领地的标志并不一定代表着实际的防卫能力,但对于信息匮乏的潜在犯罪者来说,这些能够在相当大程度上左右他们的风险判断并对财产犯罪率的降低有着显著的影响④可参见一个相关的经验研究,B.B.Brown& I.Altman,Territoriality and Residential Crime,P.J.Brantingham & P.L.Brantingham(eds),Environmental criminology,New York:Sage Publication,1981,pp.56-76.。当潜在犯罪者通过这些信息标志看到未必实际存在的监督与抵抗可能性时,就能够大大遏制自己的犯罪动机。
(二)对轻微违法行为与不文明行为的治理
社会当中是否存在大量的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也会成为人们判断社会秩序安全状况、政府执法能力的一个重要信息符号。由于这些轻微违法行为与不文明行为在日常生活中更为常见,对于普通居民来说意味着信息成本更低,虽然轻微违法行为与不文明行为和更严重的犯罪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但却是普通居民判断社区整体犯罪风险的重要信息依据。即便是不属于犯罪的不文明行为或不美观的现象如乱扔垃圾、破坏公物、被涂鸦的墙面、脏乱的空地、废弃的建筑物也能影响到人们对犯罪风险的判断,而且这些现象与犯罪率的高低以及人们对犯罪的恐惧感也有着直接的关系⑤Douglas D.Perkins,John W.Meeks and Ralph B.Taylor,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of Street Blocks and Resident Perceptions of Crime and Disorder: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Measurement,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Vol.12,1992,pp.21-34.。斯科根据对美国6个主要城市40个社区的13000名居民的调查认为,“可见的社区混乱提供了社会失序直接的行为证据”,如公开醉酒、年轻人在街头游手好闲、吸毒、行乞、卖淫等等,这些轻微违法行为或者不文明行为会增加社区居民对犯罪的恐惧感,与社区居民对于抢劫犯罪的经验感受有着重要的相关性⑥Wesley G.Skogan,Disorder and Decline:Crime and the Spiral of Decay in American Neighborhoods,New York:Free Press,1990,pp.21-50,65-84.。这种经验感受即使未必准确,但也可能成为人们判断政府执法效率与社会控制能力的关键信息,从而降低对法律制裁风险的主观认知,激发更多的犯罪动机。因此,执法机关避重就轻打击轻微违法犯罪不仅能够收到震慑更严重犯罪的功效,也能够大大节省执法成本。严重犯罪不仅可能造成更多的人间悲剧,而且治理起来也更困难。敢于实施重大犯罪的犯罪者,可能都采取了更隐蔽的掩盖措施,执法机关的调查成本与执法成本会更加高昂。破窗理论对于城市警务工作的启示就是执法者在符合法定授权与程序的前提下重点治理那些轻微的违法犯罪行为或无法定性为犯罪的不文明行为。如果轻微的违法犯罪行为得不到治理,反而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犯罪。美国有学者通过对达拉斯市警察部门的相关的资料研究发现,对轻微违法者的传唤频率在一定的期限内就开始与该市财产犯罪率的降低具有显著的正相关①Jonathan W.Caudill et al,Discouraging Window Breakers:The Lagged Effects of Police Activity on Crime,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Vol.41,2013,pp.18-23.。不仅如此,将破窗理论应用到城市警务工作上也确有成效。如纽约市警察部门根据破窗效应实施了一套执法模式,他们通过打击轻微违法行为与不文明行为,如骚乱、流浪、街头醉酒,卖淫、公开贩毒,不仅减少了严重犯罪的发生,而且他们还发现通过惩治地铁逃票者也能减少地铁系统的犯罪与混乱②Hyunseok Jang,Larry T.Hoover,Brian A.Lawton,Effect of Broken Windows Enforcement on Clearance Rates,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pp.529-538;B.E.Harcourt& J.Ludwig,Broken Windows:New Evidence From New York City and a Five-City Social Experiment,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Vol.73,2006,pp.271-320;See also Hope Corman and Naci Mocan,Carrots,Sticks,and Broken Windows,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48,no.1,2005,pp.235-266.。加利福尼亚州的类似执法模式也取得了类似的效果,通过打击扰乱治安的行为、扰乱社区安宁行为以及公共场所酗酒行为,有效地减少了一些犯罪,特别是严重暴力犯罪与盗窃犯罪③John L.Worrall,Does Targeting Minor Offenses Reduce Serious Crime?A Provisional,Affirmative Answer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County-Level Data,Police Quarterly,Vol.9,no.1,2006,pp.47-72.。在这些执法实验中,对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零容忍”政策所产生的遏制更严重犯罪的效果主要不是惩罚与控制的直接结果,而是这种政策所塑造的他人是否愿意遵守普遍规则与进行集体合作的印象与符号的结果④可参见德国一些学者在受控的人际交往实验中所得出的结论,See Christoph Engel,et al,First Impression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Early Intervention:Qualifying Broken Windows Theory in the Lab,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Vol.37,2014,pp.126-136.。在破窗效应中,更重要的不是惩罚,而是印象管理。有鉴于此,对于中国类似的公共场所,我们也可以通过实施类似的执法模式来遏制更严重的犯罪。如市民广场、火车站、繁华的街区是一个陌生人高速聚散的场合,同时也是信息高速流动的场所,机会主义行为会非常泛滥,政府对轻微盗窃、买卖欺诈、倒票行为、非法乞讨行为、传销行为的打击可以成为展示政府执法能力的重要窗口,这些信息符号会随着人员与信息的高速流动而传遍大江南北,可以大大加强人们对法律制裁风险的主观认知与减少对犯罪的恐惧感。而对于城市这种人员与信息高速流动的更大的地理区域,除了要改善城市卫生环境与规划水平外,破窗效应对于遏制犯罪动机、减少人们对犯罪的恐惧感具有更大的信息意义。这么说来,我国的城管制度似乎有了值得辩护的正当性理由。满街的小摊小贩,冲鼻的油烟,满地的果皮纸屑以及频频发现的市场欺诈,确实可能给人一种无序的印象,这种印象可能会吸引各种坑蒙拐骗者,坑蒙拐骗者的泛滥可能又会进一步刺激更严重的犯罪的产生。但我国的城管执法的问题可能不在于对小摊小贩的驱逐,而在于驱逐过程的暴力化倾向。城管执法通过改善城市环境遏制犯罪动机的同时,也可能造成反面的破窗效应,城管的粗暴执法也会成为公众观察政府的公正性与文明性的一扇窗户。当凶神恶煞的城管执法者气势汹汹地冲向那些为生计奔波风餐露宿的小民时,给人的直观印象就是恃强凌弱、以大欺小,这又会造成人们对政府粗暴、霸道的整体性印象,不仅现场可能会发生旁观民众对小摊小贩的声援,而且可能在其他政府与民众发生冲突的场合,人们也会不问具体个案的是非而首先假定政府存在过错。这造成的结果就是民众对小摊小贩一面倒的支持,对政府一面倒的反对。政府驱逐小摊小贩无非是为了改善城市环境,打造安全、清洁、有序的形象,但也不能无视小摊小贩的生计。鉴于这种情况,我们不妨在城市规划中要求每一个小区都配套供小摊小贩营生的固定场所,并实行收费管理,这一方面方便了附近社区居民的生活购物,另一方面也不会造成混乱无序的印象。
(三)社区导向的警务巡逻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实行经常性警务巡逻制度,也就是不论有无公民报案,警察都需要在街头巷尾甚至深入社区进行不定时巡逻。无论巡逻的警察是否会真的发现大量违法行为,但穿着标准警服的警察本身就是执法力量与社会监督存在的一个重要标志,仅此一点,就相当大程度地威慑那些对法律制裁风险一无所知的人的违法犯罪动机。除此以外,警察的存在也有利于加强社区非正式的自我控制机制①James Q.Wilson & George L.Kelling,Broken Windows,The Atlantic Monthly,Vol.211,1982,pp.29-38.,减少社区非正式的制裁被报复的可能性,能够使社区居民更加大胆地谴责与惩罚违规者。相比于汽车巡逻,步行巡逻能更好地发挥警察保护力量的象征性意义,震慑犯罪效果更加显著②Arthur O.Sullivan,Urban economics,Boston,Mass:McGraw-Hill/Irw,2003,pp.669-670.。除了能够更高效地处理违法犯罪外,警察巡逻也能够将执法力量以信息成本较低的直观方式鲜明地展示出来。尽管警务巡逻是展示政府执法能力的重要信息标志,但这一信息标志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平时安静的街头突然出现大量的警察也可能在不明就里的公众心中制造恐慌。这会提醒人们可能存在某些不可知的社会安全问题,警察巡逻的突然出现会使人们推断犯罪率已经上升,他们的街区因此更加危险③Joshua C.Hinkle and David Weisburd,The irony of broken windows policing:A micro-plac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order,focused police crackdowns and fear of crime,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Vol.36,2008,p.509.。如何平衡警务巡逻的正面与负面信息意义?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实施社区导向的警务巡逻模式来予以克服,在实施警务巡逻的同时,我们不妨将警察的职能扩大,使警察也承担保障日常生活安全、指导居民安全维护、排解邻里纠纷、制止市场欺诈等职责。警察履行这些职能的过程可以完全是非强制性的,但是否拥有强制性权力不影响警察保护力量无处不在的象征性意义。社区导向的警务巡逻能够以更为可亲、更为熟悉、更接近人情的方式为居民所接受。警察通过社区巡逻很多情况下获得的可能不是有价值的严重犯罪信息,而可能是街头巷尾的八卦传闻,百姓的柴米油盐琐事,以及日用品市场的纷纷扰扰,但这些微不足道的信息正是来自居民对于社区生活秩序的切身感受。如果我们能够处理好这些信息,我们也就能够直接地提升人们对于政府社会控制能力的评价以及减少人们对犯罪的恐惧感,从而也能够提升潜在违法犯罪者的风险意识,从而达到遏制更严重犯罪的功效。社区导向的警务巡逻也有助于形成“邻里守望”:邻居之间形成集体性的协作意识,相互之间守望相助,积极向警察报告嫌疑情况,从而成为警察的“眼睛”和“耳朵”④李本森:《破窗理论与美国的犯罪控制》,《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刘晓梅:《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犯罪预防理论与实践》,《犯罪研究》2009年第6期。。警务巡逻通过警力在社区日常存在的展示,有利于社区居民降低对举报犯罪的风险意识与提升对社会秩序的安全意识,从而激励居民报告嫌疑犯罪,这也能够实质上增强社区对于犯罪的自我控制能力。社区导向的警务巡逻在执法实践当中也确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美国休斯敦市与纽瓦克市为了预防犯罪,就采取了以下一些策略,如与社区居民进行沟通、登门拜访并说明来意,及时回应居民需求,指导社区卫生清理,鼓励标识私有财产,了解并解决日常生活问题,设立社区警察巡逻站点或警察社区服务中心,定期举行警民见面会,设立警民通讯机制等等,这些措施不仅有效地减少了可感知的社区混乱,也减少了各种人身犯罪与财产犯罪⑤Antony M.Pate,Mary Ann Wycoff,Wesley G.Skogan,Lawrence W.Sherman,Reducing Fear of Crime in Houston and Newark,Brown,Police Foundation,1986,pp.15-22,31-34;L.P.Brown & M.A.Wycoff,Policing Houston:Reducing Fear and Improving Service,Crime and Delinquency,Vol.33,1987,pp.71-89.。而对实施了类似执法模式的芝加哥市的民意调查也发现,加强街头巡逻,与居民加强沟通,鼓励公民参与,登门解决居民日常生活中的琐碎问题等社区治安行动,在种族关系复杂的芝加哥市,不仅能使人们感觉到城市更干净更安全,生活更为舒适,而且也使警察机关所记录的犯罪率大为降低①Wesley G.Skogan,Police and Community in Chicago:A Tale of Three Cit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3-20,271-304.。总之,警务巡逻不能仅仅是用一种冷冰冰的格式化方式来治理社区的各种问题,要积极融入社区生活,要能够让社会居民感受到警察的善意与尽心尽职,要能够获得社区居民的认同与理解。更令人惊奇的是,还有学者通过对美国谋杀率与汽车事故致死率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交通警察在街头或者公路上巡逻不仅会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率,而且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遏制更严重犯罪。如果缺少警察交通执法的可见性,这会向人们暗示,警察是缺席的或者不关心违法犯罪情况,这不仅使人们漠视交通安全法规,而且可能引发严重的社区犯罪②David Giacopassi,David R.Forde,Broken Windows,Crumpled Fenders and Crime,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Vol.28,2000,pp.397-405.。因此,法律对于犯罪的惩治并不仅仅局限于打击犯罪本身,还可以通过营造社会控制健全的印象与信号,使人们信任执法机关的社会控制能力,信任其他人都在遵纪守法,从而自觉遏制自己的违法犯罪动机。
四、结 语
尽管关于破窗效应的实践效果还存在一些争议,如关于破窗效应的适用条件与范围可能存在一定的限制,破窗效应是否适用于乡村地区尚无经验研究,对不文明行为的治理只是影响某些犯罪而非全部犯罪,根据破窗效应的执法更容易歧视低收入群体等等③李本森:《破窗理论与美国的犯罪控制》,《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Jacinta M.Gau&Travis C.Pratt,Revisiting Broken Windows Theory:Examining the Sources of the Discriminant Validity of Perceived Disorder and Crime,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Vol.38,2010,pp.758-766.,但现有的各种经验研究更加偏向于对破窗效应的佐证。破窗效应也许很难完全消除违法犯罪,使全体公民做到完全守法,但破窗效应对于我国的启示意义是很明显的。中国南方很多城市犯罪率高,某些边疆地区恐怖活动也时有发生,对于这些情况的治理,除了社会政策与民族政策的适当调整外,执法机关可以利用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差异,通过一定的印象管理策略,如加强城市建设,美化城市景观,设置防卫标志,实施警务巡逻等等,来塑造公众对于法律制裁风险与他人遵纪守法情况的主观认知,从而在执法能力难以实际提升的情况下收到遏制违法犯罪的效果。在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实际犯罪率以及警察打击犯罪的实际效率的情况下,人们就只能根据某些未必相关的表面印象进行推断,尽管这种推断不一定符合事实,但如果法律能够控制好这些表象,不仅可以减少暴力制裁的实际适用、大大节省执法资源,而且也可以提高公民生活品质,有效地预防犯罪。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到,法律运作所制造的可信外在形象可能远远超出法律运作本身的实际能力。这在很多人看来可能就是一种“欺骗”,但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法律系统如果不通过此种虚构的方式来维护人们对法律能力的信任,那么法治秩序将无法得到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