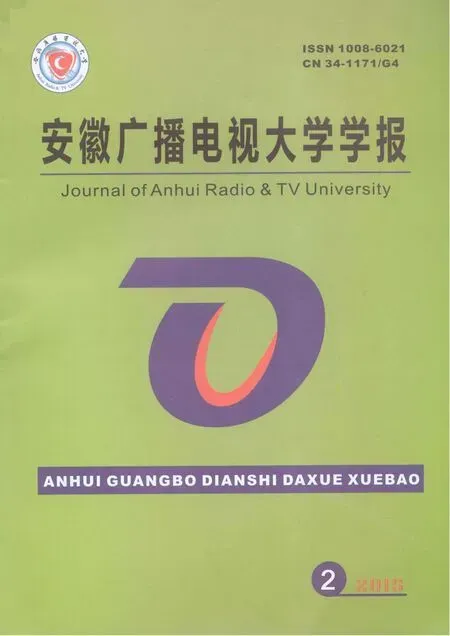开放大学的课堂文化精神建构
张亚斌
(北京开放大学,北京 100081)
精神是大学存在和发展的灵魂,宏观上它表现在大学文化的各个层面,既表现在其宏观的校园文化、文化传统、文化氛围、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活动、文化符号等各个方面,也表现在中观的管理文化、教学文化、学习文化、科研文化、评价文化等亚文化层面。然而,在相关大学精神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大量的成果集中在宏观和中观层面研究上,鲜有成果从微观的课堂文化角度对之展开研究。不过,现实的情况是,在开放大学这样一个向社会成员全面开放的大学之中,其人文精神建构恰恰是从其远程教育教学课堂中开始的,其创造了一个让所有社会成员都可以自由进入的远程教育课堂,进行以人为本、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远程开放教学,确保人类实现教育公平,满足每个学习者与生俱在的接受高等教育的天赋人权的现代神话,促进学习者在职业、社会和人生三个向度实现全面发展,成为时代所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因此,从课堂文化角度,探索开放大学的教育精神构建,具有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研究开放大学的课堂文化精神的建构,不仅事关学习者的学习使命、学习责任、学习能力、学习价值实现,而且还影响其社会使命、社会责任、社会能力和社会价值的实现,甚至还决定其社会理想人格的文化塑造,从而使他们从生命个体的“自在”状态,进入到社会主体的“自为”境界。基于这样的认识,从课堂文化视角,研究开放大学的人文精神建构,有利于我们推动远程学习者完成对人生社会真谛的追寻,以及对生命终极价值意义的探索和实践。而这,也正是我们研究撰写此文所要达到的文化目的。
根据开放大学的课堂文化表现形式,我们认为,它对远程学习者的人文精神建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一、独立探索精神
众所周知,在开放大学的远程学习模式中,自主学习永远是第一位的,而自主学习的本质要求就是学习者要有利用多媒体资源进行独立学习的能力,也就是说,它首先必须培养出学习者的独立探索的学习人文精神品格,以使之适应远程教学“时空隔离”“教学分离”的现实教学文化环境。这正如我国学者庞维国所言,自主学习把学习建立在人的独立性上,自主学习要求学生在学习的整个过程中,尽可能摆脱对教师和其他人的依赖,由自己做出选择和控制,独立地开展学习活动。它要求学习者主动地创设学习策略、目标和意义,并根据目标和标准来评估自己的学习效果,形成一种积极、主动、自觉地从事和管理自己学习活动的能力,从而使得他们有效规避在外界的各种压力和要求下被动地从事学习活动,或需要外界来管理自己的学习活动的环境文化氛围规定,从而把自觉地从事学习活动、自我调控学习,固化成远程教育自主学习主体能动性的最基本的要求,这样就使得自主学习的出发点和目的都落在了学习者尽量协调好自己学习系统中各种因素的作用上,使得其自主学习发挥出最佳的学习效果,推动其真正演化成采取各种调控措施使自己的学习达到最优化的过程的学习形态,造成学习者独立学习或者“学习的自主水平越高,学习的过程也就越优化,学习效果也就越好”的现实”。[1]况且这种独立探索精神的培养,也能够促进学习者铸就健全的社会文化人格,使其在社会上行得端,走得正,如学者王启勇所指出的那样,使其不会盲从,知道为何所爱,为何所恨,甚至在社会生存和发展中,多了尊严,多了傲骨,多了正气,进而少了奴性,少了媚骨,少了邪气,不作任何人的附庸,将自己培养成社会发展进步的中流砥柱。唯因如此,他指出,如果开放大学里的每个人都能够独立,那么,我们的社会才能成长进步。[2]
二、主动交往精神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开放大学的远程课堂教学面对的是整个社会的远程学习者,因而其知识信息传播范围浩浩冥冥,因此,面对远隔天涯的教师和同学,学习者还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交往精神,积极与他人进行主动交流,这样,它们才能摆脱孤立无援的尴尬状况,达到远程求学、答疑、解惑的目的。我国学者张东娇认为,“沟通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努力克服障碍实现人与人或人与文本通连的过程,教育沟通是利用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的差别,不断克服由诸多差别引起的冲突取得认识一致和情意匹配的过程,这种通连包括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在认知领域与情意领域等多方面的通连,既可能是多元视界的和平并存,也可能达成高度的一致性见解”。[3]对于学习而言,远程学习沟通,不是权力和权威的消失,而是在权力或权威存在的前提下谋求对话,尊重差异或达成共识。[3]在远程学习情景当中,他们要主动与老师和其他同学交往,通过有效语言,采用合理协调方式,与他们在远程教育媒体平台特定行为者经验视界之间,进行学习和知识的对话、意义理解和建构,这样才能达成共识,达成真理解的文化行为,而这,其实也恰恰正是在开放大学校园文化情境中,师生之间、生生之间,试图努力建构的主动交往人文精神。他们将借此寻求到彼此间的真正理解,了解和掌握彼此间的个人的和主体间的终极教学和学习的意义和动机。因为在这样的课堂文化教学中,“人的学习既是个体化的活动,又是社会性的活动,学习不仅是接受书本知识的认识活动,而且是与生活同时发生的实践活动,是学习者个体与社会经验相互转化、丰富、发展,受社会孕育,又为社会贡献的活动”,它通过促进学习者实现自我意识的社会文化超越,从而确认,主动交往精神是人类学习活动最本质的特征,而且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4]
三、群体协作精神
在开放大学的远程课堂教学和学习当中,师生沟通、生生之间的沟通从来也只是基础,因为只有真正地行动起来开展协作学习,他们才能真正实现其远程教育价值。更何况因为开放大学的远程学习,由于利用的是大众传播媒介四通八达的信息传播通道,这就导致其学习的主动交往最终都会形成像藤蔓状的网络,使他们每一个人,因为被牵扯进这个网络之中而彼此具有互联性。很自然地,在这种情况下,若要在教师与学生的沟通活动中,促进双方的认知、情感、意志水平与个性心理都能得到某种程度的协调发展,就必须依赖群体合作,使学习者获得更多的知识信息,并通过这种信息,完成其学习角色的转变,使得其实现由孤独的学习者变为“有支持的学习者”的角色转变,这样,才能使学习者间接获得大量的人类文化的优质信息,更大程度地改变原有的心理结构,以新的图式同化新经验,发生顺应过程。毫无疑问,此种协调学习发展方式的实现,其核心正是要学习者发挥远程教学与学习中的群体协作精神,因为只有协作,才能“缩小师生之间的心理距离,形成认知与情感的共鸣、共振效果”,才能超越他们彼此间的个性人格和知识水平差异,让他们走出原本封闭的私密学习心理,产生使之乐于接受的心理效应,实现认知结构与水平的对接,从而使双方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信息沟通回路,实现认知沟通,进入彼此的情感世界和精神境界,走向人格沟通之路。
四、资源共享精神
在开放大学的远程教育媒介课堂文化氛围中,最为重要的人文精神之一,就是学习者一定要超越因为时空分离而导致的自我心理封闭,培育与他人进行学习资源共享的校园人文精神意识,实现彼此间的知识信息共享和教育价值共享,造成彼此的共同进步和发展共赢,避免学习行为上的孤立文化倾向,防止在网络时代出现“鸡犬之声相闻”,然却“老死不相往来”的消极学习文化现象。为此,开放大学应做出积极的体制规划、平台设计和制度安排,通过技术支持和倡导协作学习精神,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一位学习者共享知识信息资源和远程学习的需求、动机和快乐,因为毕竟只有学习资源共享,才真正有利于学习者共同掌握和拥有知识财富,有利于他们一起通过头脑风暴,相互激荡,激活知识学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发挥出各自的天才禀赋,实现优势互补,创新出更大的教育价值,全面提升远程开放教育和学习的文化绩效。我国学者张震宇、陈劲指出,开放式创新模式大大拓展了学习者可利用创新资源的范围,提高了他们远程教育技术创新学习活动中资源利用的效率,同时也使开放大学教师管理各类创新教学资源的工作量和难度增大,也使得学习者越来越意识到“谋求独占大量创新资源在开放式创新条件下既不现实,更不经济”,只能是损人不利己,而这,也许正是开放大学校园文化情境中,知识信息共享所带来的学习方式可选择性、知识信息的大流动性、教学资源的非独占性等社会边际效应的深层文化原因。[5]正如我国学者胡峥嵘所言,正因为开放大学的课堂文化范围没有围墙,才使其教学资源的介入更具广泛性、共享性,具有人人、处处、时时学习的服务功能和手段,以及能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提供教育服务的精神文化功能。[6]
五、技术理性精神
开放大学就是一种借助技术媒介进行远程课堂教学的文化传播形态的学校,这就决定了它的课堂教学文化氛围必然洋溢着一种注重实用、注重操作、注重流程、注重标准的技术理性精神。由此可见,开放大学教育技术理性实质,就是应用教育技术专业领域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来构筑远程教育课堂,帮助开放大学师生解决远距离条件下的教与学的实现问题,正是远程教育的媒介技术理性,催生了开放大学的远程教学课堂,活化了开放大学师生的远距离教与学的生活,使得他们在非接触性的知识传播语境里,不断跟踪信息技术进步,寻求科学的方法,促进知识增殖。诚如我国学者周钧所言,“技术理性把科学和技术置于重要位置,把科学理论作为专业知识的源泉,把专业实践视为一种应用科学和技术解决问题的过程”[7]。可见,在这种课堂文化里,由于采用的是多种媒体的技术支持方法,师生可以采取文本、音频、视频等方法,实现实时或非实时的教与学的远程互动,对某些存有疑惑、问题或兴趣的知识,自觉提出问题,然后采用比较恰当的媒体,在技术操作行动中思考并逐步解决这些问题,以更加深刻地理解知识,强化他们远程教与学的行动及其远程课堂文化的技术理性,从而将远程教育课堂文化,最终演化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在技术支持中进行知识探索的发现式学习、在技术行动中进行知识反思的启蒙性学习、在技术实践中进行知识迁移的交互性学习、在技术模式中进行知识建构的模式性学习等先进的课堂学习文化形态。
六、文化融合精神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开放大学的远程教育媒体课堂是一种面向社会学习者的开放式课堂,它的这种开放性,决定它的校园文化精神建构,必然是一种海纳百川的融合式校园文化精神建构,必须交融和汇聚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知识观点和学习方式,形成多元化的社会远程学习终端。诚如我国学者陈平所言,它的“文化的多样性以统一性为前提,而文化的统一性又以多样性为基础,从而构成了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矛盾统一”,它的文化融合,可以抽象划分为物质技术、制度行为和精神观念三个层次,其“文化的融合,体现了不同文化之间三个层次的交流和渗透。”[7]76-79具体地讲,就是在开放大学的远程教育平台教学课堂中,教师是一端,是开端,而学生是另一端,是多端,是终端,教师的一元化远程教学与学习者的多元化学习形成了辩证统一的融合关系,学习者的学习多样性,以教师的教学统一性为基础,反过来又超越了教师的教学统一性,赋予了远比其原有文化生命力和发展动力更为强大的学习文化力。无疑,开放大学的远程开放课堂教学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在信息传媒物质技术、教与学灵活开放制度、知识融汇整合精神观念的三个层次上,不断进行有层次性的互动文化融合过程,进而铸造出了学习者的文化融合精神,终结了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中,教师“一人独语”,学习者“众生缄默”的文化时代,开辟了一个远程社会学习者“众声喧哗”,而教师只能“一人应和”的新纪元,就像陈平所断言的那样:“21世纪是一个世界多元文化融合化的世纪,世界文化的发展应该是在全球意识关照下的文化多元发展”[8]。正是在这样一个文化语境里,学习者变成了国际文化公民,他们彼此间,或与教师间的跨文化远程教学合作、课堂互动合作、学习交流合作,逐渐成为常态。
七、爱岗敬业精神
开放大学的远程教育课堂也是学习者走上职业发展的预备学校,谋求职业发展的社会学习课堂,攀登职业发展高峰的人生文化起点,不可避免,它的这种“爱学敬业”的主体校园文化人文精神,必然推动他们自觉树立“爱学习就是爱岗位、敬学业就是敬职业”的学习发展意识,激励他们将“爱学敬业”内化为自己远程开放学习的自觉心理需求,外化为自己职业发展的最基本的思想道德规范。当然,这种人文精神的建构,已远远超出了传统大学的校园文化人文精神建构范围,使得开放大学的校园文化人文精神建构,从主体意识层面,向着大学后教育的方向发展,使其不自觉地融入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等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先进理念,进而为远程学习者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原发性文化动力。正由于此,我们说,爱岗敬业精神不仅是开放大学主体校园文化人文精神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开放大学职业社会学习课堂教书育人的最终归宿,它不仅是学习者个人在远程开放教育数字化生存和职业发展中的一项基本文化心理需要,而且也是社会现实存在和职场经济发展对其提出的一项最基本的人才成长市场需求。它使得学习者清醒地意识到,自从进入开放大学的那一天起,就必须认真对待自己的远程教育课堂学习及其社会实践学习,正确对待远程开放学习对他们未来职业岗位发展的文化影响,并秉承对自己工作和岗位职责负责到底的认真态度,坚持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能自觉地尊重自己的开放大学远程开放教育课堂学习和社会实践课堂学习,尊重自己的社会职业发展、岗位职责发展等人生规划选择。
八、质量保障精神
开放大学的远程教育和社会实践课堂文化也是一种有质量保障的教育文化,它通过建设面向整个办学系统和所有社会公众的远程教育质量保证体系,为所有远程学习者提供比较到位的学习支持服务,并借此树立起学习者的质量保障学习意识和质量保障从业意识。远程学习者精神,其起点是远程教育质量保障文化,落脚点是学习者的学习及工作质量保障意识。正由于此,我国学者李兵指出,高等学校质量保障应主要体现三全一多原则,即质量保障全面性、全员性、全过程性和管理方法的多样性。按照他的观点,“全面性指的是对整个高校的质量管理,它不仅是系统目标的实现,还能使系统的整体功能达到整体满意值;全员性指的是高校的各个部门和教职员工都要参与到质量保障活动中来,充分发挥管理者、教师和学生三方面保障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根据高教大众化进程中高等学校显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全面建立校内质量管理、质量控制、自我评价、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新机制”,建立一个包括社会各个行业的“校外质量管理、质量控制、自我评价、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新机制”;而“全过程指的是高校把质量意识贯穿于高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主要包括课程与教学质量保障、教师遴选与保障、论文质量保障、毕业生就业状况及声誉反馈等。它把开放大学的校内质量保障文化理念,从传统的校园面授课堂,延伸到了广阔的校外社会课堂,并鼓励学习者将开放大学的质量保障文化理念,内化为实实在在的社会学习质量保障精神,甚至是职业发展文化精神。显然,正是从此角度言,李兵认为,大学当发展多元质量保障主体,吸引广大社会学习者和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士的广泛参与,以保障开放大学质量监督的民主性、公正性、科学性的实现。[9]
九、社群归属精神
由于在开放大学的远程教育教学模式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虚拟学习生活社区,诸如BBS留言、QQ群、微信群等小型化虚拟学习生活社区,从而将开放大学的远程教育课堂文化内涵和影响范围大大拓展了,这些随信息技术而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新型远程教育社会共同体,也分别担当着开放大学远程教育虚拟课堂的文化角色和职责,对学习者的远程开放教育凝聚力形成,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它们已经成为显现开放大学师生群体归属精神的又一时空轴心。这正应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R·M·基辛(RogerM.Keesing)的观点,“人类存在于地球上的99.9%的历史是以小型社区生活为特点的,而亲属、朋友及邻里的亲密关系又是小型社区社会生活的主体”。[10]人们之所以以血缘、邻里、朋友、同学、同事、同道和同业关系为纽带联结起来建成如此纷繁复杂的小型化虚拟学习生活社区,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学习、工作、生活中的相互关心、爱护、协作、支持、配合和照应,实现学习生活的共享共荣。特别是由于开放大学的学习者来源于社会的各行各业,自然,他们也就传承并弘扬了人类与生俱有的此种文化血脉天性,他们在开放大学这个远程教育特定社会化文化圈内,依靠现实校园、虚拟校园和社会校园构建出了一个学习者人生教育价值观念一致、教学关系密切互动、遇到问题彼此相助、学习快乐共同分享的社会教育共同体,并通过这种社区意味非常浓厚的社会化学习文化氛围,培育出了其生生不息的远程开放学习群体归属文化精神。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以为,开放大学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全新的社会化、公众化的大学课堂文化形态。正是它,支配远程学习者在热爱开放大学远程教育课堂的同时,滋生出热爱社会、职业和工作的无限豪情,生发出对先进知识生产力、知识经济和知识文化的眷恋之情。诚如我国学者连洁、王火生所言,在这样的大学课堂文化形态里,学习者们能将学习引入工作,融入社会运行的各个阶段,以实现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使学习成为创新发展、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的动力,使学习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主动要求,使每个学习者的主体作用得到极大的提升,并通过学习,重新塑造自我,完善自我,创新自我,重新认识世界与生存和发展的关系,从而变被动地接受客观知识为主动地提高内在素质,把学习看成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途径。由是,他们学习就成了“一种社会性活动”,他们的一次性学校“充电”、一生在一种工作中“放电”的时代,永久地成为历史,他们的学习动力就不再来自于个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民的需要,他们学习的主体就不再局限于某些特定个人,而是每一个人。毫无疑问,这样的学习条件和氛围的创造不仅需要个人的付出,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因为这样的学习的内容更强调时代性和社会性。[11]而这,也恰恰正是我们构建全民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人文基础,它必将促进每一位远程学习者,在全民终身教育体系构建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行使自己作为一个大学人、知识人、文化人的权利,践行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人、职业人、工作人的价值。
[1] 庞维国.自主学习:学与教的原则和策略[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6-7.
[2] 王启勇.开放大学精神内涵及培育研究[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1):62-66.
[3] 张冬娇.论教育沟通及其过程特性[J].学科教育,2002(3):5-11.
[4] 桑新民.创新学习文化回归大学精神:21世纪大学通识教育新探[J].教育研究,2010(9):75-80.
[5] 张震宇,陈劲.基于开放式创新模式的企业创新资源构成、特征及其管理[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8(11):61-65.
[6] 胡峥嵘.国外开放大学精神的研究及启示[J].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4):25-29.
[7] 周钧.技术理性与反思性实践:美国两种教师教育观之比较[J].教师教育研究,2005(6):76-79.
[8] 陈平.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35-40.
[9] 李兵.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构建综述[J].当代教育论坛,2005(7):98-100.
[10] R·M 基辛.文化·社会·个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10(1):561.
[11] 连洁,王火生.关于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思考[J].教育学术月刊,2010(12):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