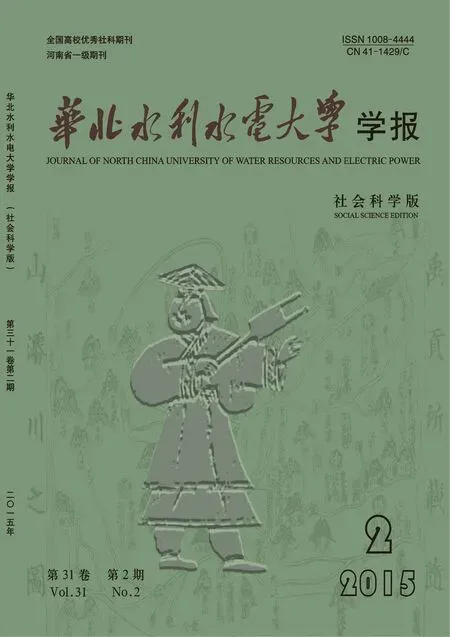装帧设计中的同题异构
赵小勇
(河南传奇故事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河南郑州450008)
一、艺术设计中的同题异构
自符号学产生以来,符号就有着多个定义,我们选择其中最通俗易懂的一个来诠释此文中涉及符号学的问题。
“一个符号就是代表或指称另一个事物的东西。”[1](P4)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将符号的概念分解为能指和所指两个部分:“我们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2](P102)法国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家罗兰·巴尓特认为,符号是“由一个能指和一个所指组成的。能指面构成表达面,所指面则构成内容面”[3](P26)。
任何产品设计在视觉传达上的类型特征都是认知性和审美性,艺术设计的目标就是将认知性和审美性通过符号编码有机地统一起来。设计中的形式创造有着极大的自由度,同样的一种产品可以有许多种设计构成,这就是同题异构。“普拉察”咖啡具的美妙曲线,用图形符号传达出人们对大自然的心仪;“格拉西亚”咖啡具的中国传统纹样的运用,用图形和色彩符号表现出雅致的东方韵味;而皮尔·卡丹设计的“马克西姆的巴黎”咖啡具,却以肌理符号创造出饮食文化和服饰文化间的联想,作为服装设计师的皮尔·卡丹在为坚硬的瓷器做设计时也试图表现飘柔的丝绸美感。
然而,无论怎样的异构,其核心只有一个,就是将认知和审美在设计人所建构的“符号集合”(德国斯图加特学派定义为“符号文本”,即一组与主题相关的符号组成的一个“合一的表意单元”)中发生关联,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进入视觉传达。在上述那些不同的咖啡具产品设计中,认知性已经被牢牢地确认,没有“在转换和接收中附加于信号(符号)的非信源所愿的任何东西”[4](P7),也就是约翰·费斯克称之为“噪音”的因素,它的能指最大程度地趋向于所指。由此,在视觉传达中不会有人认为它们是茶具、餐具或别的什么。产品的认知性确定了,审美的符号建构却多元化了。也就是说,产品的装饰风格多样化了,人们消费的选择自由度也随着形式创造的自由度而扩展。
二、书籍装帧设计中的同题异构
对于一本书而言,装帧设计是代表或指称它的符号,设计人将文字符号、色彩符号和图形图像符号组成一个符号集合(符号文本),用设计编码浓缩了书的信息,从而完成了设计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符号建构。在一本书完成了生产程序进入传播领域之后,这个“符号就是负载或传播信息的基元,表现为有意义的代码及代码系统”[5](P105)。
当同题异构发生在书籍装帧艺术领域时,其传播形式中的符号建构更值得玩味,有着更为复杂的符号组合过程。
书籍装帧艺术在传播意义上的类型特征同样也是认知性和审美性。书籍的装帧是一本书的符号,就认知性而言,设计人将文字符号、色彩符号和图形图像符号进行组合,完成其信息编码。作为读者的信息接收人通过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可以无“噪音”或者尽可能少“噪音”地认知这本书的大致内容;就审美性而言,文字、色彩和图形图像等符号所进行的组合的终极意义,就是完成一种平面形式美感的创造。一件理想的书籍设计作品就是这二者的完美统一,这一点与工业产品设计并无区别。
之所以说这个符号组合过程较之工业产品更为复杂,是因为书籍的社会文化内涵和设计中复杂的符号修辞。
这些不受约束、无籍可开的学员是抱着各取所需的目的来上课的,相继提出很多问题要巴克夏回答。如谷子卷叶是什么毛病啦——玉米苗发黄是化肥烧的吗?红头苍蝇是不是草地螟等。
语言学的修辞是加强言辞或文句说服能力和艺术效果的手法,而符号修辞是运用具有表意功能的符号来有效地传递信息,取得最佳的表现效果。在艺术设计中,符号修辞的明喻、暗喻、转喻、提喻及其各种变体可以使得符号的表现力生动而形象,有着非常大的运用空间。
一本书的设计元素包含文字符号、色彩符号和图形图像符号等,这些符号元素按照设计人的艺术思维和审美个性组成一个符号集合(符号文本),而伴随这个符号集合同时传送给信息接收人的相关因素还有“伴随文本”,即“伴随着一个符号文本,一同发送给接收者的附加因素”[6](P141)。就一种书的装帧设计而言,它的伴随文本可能远远大于它自身的符号集合(符号文本),书的内容和思想、作者的身份和履历、成书的背景和过程、体例、形制、版别,成书以后接收人的批评和反馈等等,所有和这本书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和技术因素都会成为它的伴随文本,而这些因素都要作为原始信息进入设计人的符号组合系统,尤其是在当代书籍装帧设计中。
因此,书籍装帧设计的符号组合系统须达到一个相对准确的尽可能减少“噪音”的意指。也就是说,这个符号的能指必须尽可能地达到所指。其中,最具意义的是图形图像符号,而图形图像符号完成意指的最重要的手段就图像修辞。
三、同题异构中的图像修辞
人类有了纸质的书籍后,文字和图像之间就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汉语对书的正式称谓是“图书”。书封的装饰、插图的运用,通过冗余现象重复和强调着书中的各种信息。没有插图似乎也未尝不可,但绝对不能没有封面,而再简单的封面也具有图形意义。哪怕书封中只有文字,它们的组合排列、色彩构成所传播的也不仅是文字符号本身的信息,它们组合成的整体视觉形象本质上仍然在建构一种图形符号的意指和平面形式美感。当文字符号、色彩符号和图形图像符号组合在一起时,符号的各种意指和符号之间的关联就担负了重要的修辞功能。因为在今天大众传播的层面上,语言信息几乎存在于所有图像之中,如广告、海报、标识设计、文字图解、多媒体、连环漫画等(“图像文明”“读图时代”的称谓描述了图像在我们时代的特殊意义)。“由于内涵的存在,一段冗长的文本可以只包含一个总体所指,与图像相联系的正是这个所指。”[7]所以,在书籍设计的各种符号修辞中,图像修辞尤为重要。
我们所要关注的就是从图像修辞的角度来看书籍装帧艺术中同题异构的现象。
以波斯诗人莪默·加亚谟《鲁拜集》的两个中文译本为例。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拜集》为32开长形本(见图1)。封面上图形构成简洁,中绿的边框、淡绿的底色通过书脊延伸至封底的三分之一处。封面上唯一的图形是一朵小花,那个时代的诗集和散文集多采用这样的图案和开本。就图形图像符号的修辞而言,通过那一朵小花和具有抒情意味的长形开本的提喻,告诉信息接收人,这可能是一本短诗或散文的结集。在色彩符号的修辞上,用绿色调的转喻,使人隐隐感到这些诗歌来自阿拉伯国度。30年以后,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2009年再次出版《鲁拜集》时,装帧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见图2)。正度16开本的幅面中,花的图像和图形多次出现,与图1相比,图2的内容仍然是花,也即图像修辞的喻体一样,但修辞手法已经不同了。作为喻体的花在此因为居于衬托的位置,加之以开本的因素,不再具备明确的比喻功能。在色彩符号中,与图1一样,图2的绿色调转喻了阿拉伯国度。在文字符号中,图1封面上的文字只有书名和作者名,图2的封面上有作者、英译者、中文译者、插图者、出版者、英语书名、丛书名称,加之封底的英语书名、前后折口的编辑者、设计者、丛书书目,等等,文字符号编码给予信息接收人的东西非常丰富,接收人可以接收许多伴随文本的信息。有趣的是,英语书名的字体设计也带有阿拉伯文字的笔画特征,使得文本给图像增加了新的信息,文字符号的意指产生新的修辞意义。这当然不是语言修辞,而是图像修辞。
以信息接收的强弱来排序,如上所述,我们在两个版本的《鲁拜集》中分别解读到了这样的信息:图1的设计符号编码传播出书名、作者、诗歌或散文集(有可能出现的联想)、阿拉伯国度等内容;图2传播的信息是书名、阿拉伯国度、作者、译者、插图者等等,有大量的伴随文本,但却缺少了一个“可能的所指”,也就是有可能产生的关于书的内容(诗歌或散文)的联想。如果只从符号集合(符号文本)认知性的明确程度来看,符号集合(符号文本)和伴随文本庞大的图2逊于简约的图1。这其中有一个客观因素,图2的《鲁拜集》是系列丛书《名著图文馆》的一种,设计中会兼顾丛书的整体性。

图1 《鲁拜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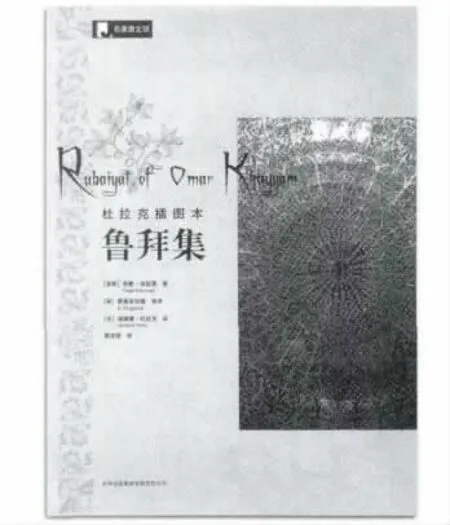
图2 《鲁拜集》
就审美性而言,图1与图2几乎没有可比性。但这已经是两个概念了,审美性是传播中的另一个类型特征,认知性和审美性在传播中并不互相取代。
法国史学家伊波利特·阿道尔夫·丹纳认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隶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8](P7)爱娃·海勒也说过,“每一种被广泛接受的风格均发源于一种真正的需求,也只有如此,这种风格看上去才不会显得生硬,并符合时代的要求。”[9](P12)由此可知,审美的因素更多是由于时代的要求。
仅仅基于探讨图像修辞在设计中的意义来分析这两个案例,不难发现,图1以其简约的符号修辞完成了传播意义上的相对完整的符号建构,而时代的因素造成了它在今天看来审美上的不足;图2的图像修辞有所缺失,但在审美上已臻化境。
再来看一组设计案例。
以下是各种版本的《人间词话》。在中华国学再度引起国人高度热捧的今天,各出版机构竞相再版了王国维的这部名著。同题产生出如此丰富多彩的异构,这不能不令人发生兴趣,尤其是其中的图像修辞现象。这些设计或以古色古香的团花纹样提喻古典,如图3;或以隽秀的花草图形提喻文学,如图4和图5。图6的内容仍然是《人间词话》,但书名是《王国维谈诗词》,封面中的王国维像“冗余”了书名和作者,为不熟悉这位百年前国学大师的读者提供了图像认知。图7同样也是以花草提喻文学,但色彩符号的修辞因素加强了,缤纷又不失典雅的弱对比色彩转喻了文学艺术的曼妙。图8中图像修辞手法与前几例相同,书名和花纹虽然在色阶上对比很弱,不十分醒目,但压凸效果的别致使人忍不住要近距离看它,结果使得这一肌理符号的妙用强化了传播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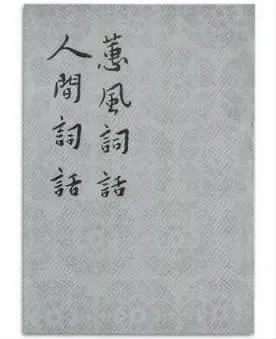
图3 《蕙风词话人间词话》

图4 《人间词话》

图5 《人间词话典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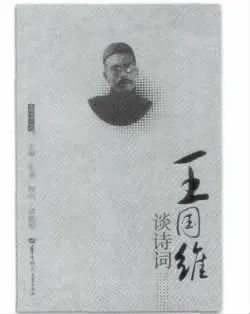
图6 《王国维谈诗词》
图9、图10、图11的封面上都出现了中国传统绘画作品,以绘画作为图像符号进行提喻,本体仍是古典。图12、图13、图14的设计都是完全以文字进行建构的符号集合(符号文本),又都从属于其所在的丛书系列,故而没有特定地针对“人间词话”这一主题进行信息编码。但如前所述,哪怕是只有文字的装帧设计,它们的组合排列、色彩构成所传播的也不仅仅是文字符号本身的信息,它们组合成的整体视觉形象,本质上仍然在建构一种图形符号的意指和平面形式美感。在这三例设计中,文字排列的线性感觉或平或直,视觉形象端正大气。这些没有图的图像把“经典”“学术”“国学”等概念作为比喻的本体,恐怕已是不言而喻了。
以上各例中,不尽如人意之处肯定在所难免,但至关重要的是,它们用多种不同的形式美无“噪音”或少“噪音”地传播了对同一个《人间词话》的认知。

图7 《人间词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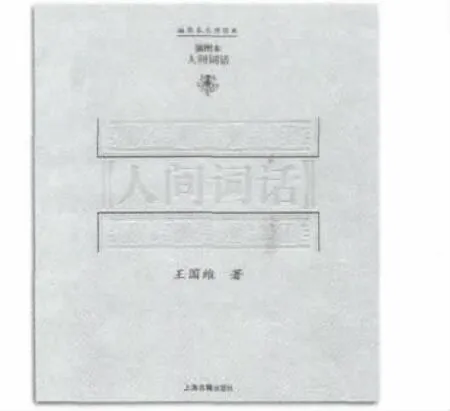
图8 《人间词话》

图9 《人间词话》

图10 《人间词话新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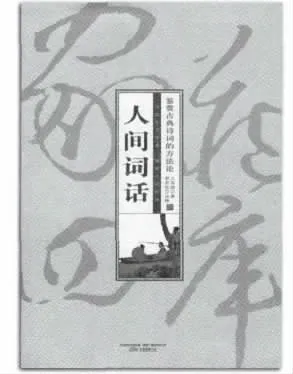
图11 《人间词话》

图12 《人间词话》
“我们也可以不揣冒昧地认为,意义的整体世界以内在的(结构的)方式被分割为文化的系统和自然的组合:正是通过成功地运用不同的修辞辨证手段,大众传播的作品才将所有一切融为一体,其中既有对自然的迷恋,包括叙事、故事、组合的自然性;也有对文化的认知……”[7]

图13 《人间词话》

图14 《人间词话》
同题的装帧作品产生的诸多异构,在履行各自符号使命的过程中,用不同的图像修辞展示了设计人不同的信息切入点,融合了“文化的系统和自然的组合”。罗兰·巴尔特称意指作用是“一种把能指和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在艺术设计的世界里,设计人所从事的“意指”行为以其艺术劳动践行着各自的艺术理想,为接收人创造出同一的传播认知,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审美选择。这正是社会和设计人自己都需要的。
[1]徐恒醇.设计符号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2]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罗兰·巴尓特.罗兰·巴尓特文集:符号学原理[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4]约翰·费斯克.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M].许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李彬.传播学引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
[6]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7]罗兰·巴尓特.图像修辞学[J].方尔平,译.王东亮,校.语言学研究,2008(6).
[8]伊波利特·阿道尔夫·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9]爱娃·海勒.色彩的性格[M].吴彤,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