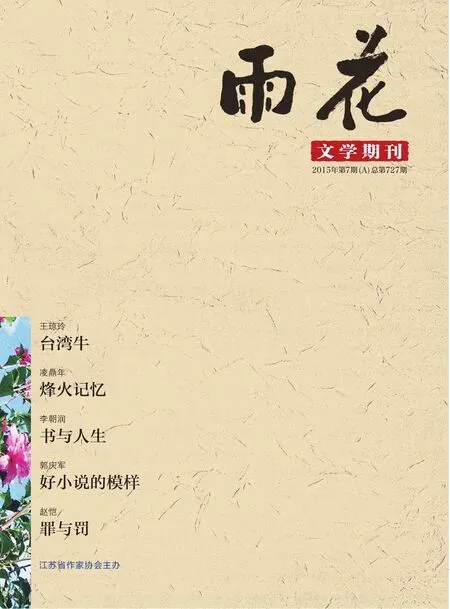盛夏已过
■流瓶儿
盛夏已过
■流瓶儿
1
你这肚子不会是双胞胎吧,太大了。
才做过检查,我这肚子完全符合标准,将来你也一样。
我记得现在该有六个月了吧。
快七个月了,差几天。
城郊的一座院落掩在葡萄架下,孕妇是加颖,她手拉着瘦瘦的皮肤有几分黑的是于秀。
加颖肚子大了,整个人都有些变了。没有化妆,一条极简单的蓝碎花孕妇裙。刚出车站时,于秀一眼没有认出邵加颖。
这里落后,你不会嫌弃吧。加颖被肚子顶着而坐得笔直,两手分放在肚子两侧的大腿上。
于秀坐在矮桌前的小凳上,从随身的包里拿出梳子来梳头发。一番热闹几乎使她忘了自己的烦恼,加颖的这一问竟有几分扫兴。然而,她还是快乐的。
她们有七个月没见了,加颖的婚礼于秀没能参加。原本说好于秀是伴娘,她继母却忽然旧病复发,她在医院里陪了一周,之后是丧事。她不记得亲生母亲,十岁时继母进了她家的门。十六岁时,继母患病切除子宫,这以后的记忆逐渐变得阴暗起来。继母慢慢地开始变了,身体一寸寸干瘪下去,正值青春期的她一寸寸地丰满起来。继母会忽然抬起头死死盯住她的胸部,寻出个理由就开始歇斯底里地骂,言辞不堪入耳。她生就是要勾引男人的,而她的爸爸,一定是在外被人勾引了。
一次于秀在被骂着,惊恐地望着继母的那张脸呆了,活脱脱的是个男人。继母看着她的骂被隔绝了般没产生反应,也愣住,不由得向镜子看过去,那一眼,她自己也怔住,继而疯了,操起手边的擀面杖就照着于秀的胸部砸过去。于秀把继母狠狠地向后推去,先撞到门框,然后摔倒在旁边的沙发角上。继母的手里还抓着她的一缕头发。她父亲刚好回来,狠狠地给了她一记耳光。她想跑出去,却被父亲一把推进她自己的小卧室。她把头埋进被子里用力哭,觉得痛苦却又茫然。只一会儿她就哭不出来了,人伤心都是有理由的,她觉得自己的这理由是怪异而虚弱的。天已全黑,屋里没有开灯,黑暗里只有狭长苍白的窗帘一掀一掀地随风动着,窗子四方格的影子,像牢笼的栅栏。她说不清,想不明白,脑海里只有继母那张扭曲变形了的男人般的脸。她起身趴在门上听外面的动静,听到父亲穿着拖鞋走动的声音。
大二她开始住校,直到工作到此次失业,她都没再回过家。
2
入夜,于秀和加颖躺在床上,灯熄了。窗外的月光透过白色的纱帘,照亮床对面墙上画,黑白的一对外国人相拥抱着,女人向后仰着头完全陶醉般地闭着眼,男人则将头埋在她的胸前。
你们还挺浪漫的吗?于秀用胳膊肘儿捣了一下加颖。加颖也回捣她一下,去,说你自己吧,男朋友都谈了十八个了吧。
哪有那么多,也就七八个。
那还不够多……加颖想继续说,终又忍住了,说道,这个范什么来着的,你们怎么没成呢?
于秀慢慢地将身上的毛巾被整理了一下,半响才说,其实已经很没意思了,他倒是什么都不说,我有感觉,我也不想让他难堪,他一直都不回家,我住在他家里算什么,我自己搬出来了,他妈妈也什么都没说,我给他打电话说,我搬走了,他说,好,以后有事可以打电话找他,之后就说了再见。那天之后再没见过面也没通过话,我自己都怀疑我跟他之间就是做了场梦。说完,于秀叹了口气,侧身背向着加颖。
加颖轻轻地哦了一声,俩人都不说话了。
于秀楼房住惯了,在这样的平房底下,觉得自己与脚下的大地如此的接近,想起曾看过的电影《清凉寺的钟声》,幼年时的法师曾直直地躺在地上,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躺在地上安全,因为再也没有地方可以掉下去。这个镜头与这句话她总记得。她从搬出家门之后其实心一直是悬空的,努力学习,有个稳定工作,嫁个好人,其实这些无非是想找个安全。她的心是干瘪的口袋,张着饥饿的口,可是唯有泪涔涔。她翻过身向着加颖想伸手抱下她,哪怕得到一刻的安慰也好,却发现加颖已传出沉重的睡息声。其实又能怎样呢,即便加颖是自己的亲生姐妹,自己的路还是要自己去走。
屋外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那是与自己无关的,睁着的眼看到的只是自己破败而混乱的世界。可是当初,她本来是有希望嫁掉的,只要她想。有一段时间似乎她可以嫁给任何一个人,追求她的人有不少。但是不一样,她心里明白,不一样。
记忆之门的拉开,仿佛色彩里的渐变,她一天一步轻飘飘地光彩起来。但也只能绚丽的一闪,然后又归到黑暗里去。她交了男朋友,是同事的朋友,她瞒着加颖。恋爱不到一年便完了,她哭了足有半个月。她是当真的,温顺得像猫一般只想他能带她回去,给她一个安稳的家。这话她不便明说,而那个他却是刚步入社会,即不能领会于秀的心思,同时也并无安稳的想法。只有一次求于秀成全他男人的终极欲望时,才说了句,我早晚是要娶你的。只这一句话,于秀松开了紧抓着的裤腰,这一松便是另外一个世界了。以后的日子,她总是忍不住就流泪了,逼死了也不说出个理由。他不懂得她为何伤心,于是她就越发地要失望流泪。如此越来越糟,开始不断地争吵,却又切入不到主题重点,终是为丁点鸡毛蒜皮而结束。
其实真正的空白完全结束是不容易的,他们俩人的结束都还要归功于身边的追求者。于秀的眼泪让另外一个男人捧起来,吻干了。新的爱情开始,旧的才甘心了。
3
早晨于秀跟着加颖去买牛奶,是最新鲜的。
从大院的后面,绕过一片杨树林,穿过菜地荆棘栅栏间的小道,有一片不大的麦地,麦子已收割过了,收割得十分粗糙,像蹩脚的理发师修过的头发,乱的,成群的麻雀起起落落,十分欢快。
在同样的一个大院里,饥饿的小牛犊被赶开,俩人捧着温热的黄牛的奶离开。早年读书时,于秀记得有书上有用瓦蓝形容天空,她站在乱蓬蓬的草丛里,觉得这个词很好,真好。只是那天空再好,也是遥远的,能做什么呢?
加颖的婆婆在院角的厨房照看煮饭的锅,一边一只手挑起竹门帘向于秀张望。加颖,地里给我拔几根香菜过来,我烧汤。老太太扬起温柔而欢快的声音。
于秀坐在小饭桌旁,拿了根茅草逗弄一只黑白花猫。猫仰卧在地,伸长着两只前爪与她争夺茅草,饭桌上放着的手机是寂寞的。于秀期望它会忽然地开始唱响,但是她的希望中几乎没有什么人了。
加颖的婆婆拿到香菜,问加颖,这丫头有对象没有?加颖隔着竹帘看于秀,于秀的年龄这两年似乎在倒长,不过人瘦些就是显得小,她们初次见面时粗笨看起来像个老姑娘的于秀,此时如同一个大家出来的小女孩一般。加颖略犹豫了一下说,她没有对象。嘿,加颖的婆婆喜不自禁地出了一声。
加颖一把掀起门帘出来。她太明白老太太的心思了。二哥至今未婚,老太太做梦都在给他张罗着找对象。于秀这样一个可人坐在这里,老太太自然是要惦记一下。然而加颖太了解于秀,于秀打掉过孩子,跟过几个男人,这些她怎么能说出口。她们俩是朋友,但是朋友有很多种。
中午临开饭,院外传来巨大的发动机的嗡嗡声响,然后由一个悠长的“嘁”声结束,紧接着便听到说话声,院门吱地被推开了,进来了两个男人。加颖的丈夫四峰一眼看到了于秀,先是一惊马上笑起来,说,早知道我去接你了。加颖起身去给他们盛饭添碗筷。四峰向于秀介绍另一个是二峰,四峰的二哥。哥俩长得很像,只是二峰瘦且白净有几分书生气,不像是大的。二峰不多说话,坐下便开始专心吃饭。
于秀也专心地吃着饭。她将盘中的浸满油的生菜放在自己碗里的白米饭上,慢慢拨弄着,拨开她记忆里曾有过的一段美好。另一个人。
他陪她逛街,一逛就是一整天,一直在身后替她拿着包。喝啤酒对着瓶子咕嘟咕嘟地大口灌,他抱着于秀的肩跟他的朋友们说,我有福气,遇到了秀。他从那天那刻开始叫她,秀。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变得踌躇不安。于秀是他的初恋,他目不转睛地望着于秀,直望到于秀身体里的一把火慢慢地烧上来。她主动熄了灯为他脱去衣服,咬住他的唇,这是她第一次主动要男人的身体。
这样的火热终究没有烧多久,只有火没有热,她有身体,令她自豪的肉身和年轻的情欲,她的继母没有,一想到这里她甚至有种是在发泄在报复的快感。而在内心,身边的男人虚成一个影,爱情这个词一出口便是个笑话。没有人知道她心底里的想法。他们去酒吧喝酒,去唱歌,她在这些人群里如蛇一般地蜕皮,将她身上原以为注定的傻气、粗糙,一点点地脱得干干净净。没有人能够想到她从前的模样,那样精致的一个小女子。
他的家人不同意他们结婚,倒是不因为于秀,而是他一无所成。不管怎样说,他们在一起于秀从未掉过眼泪,倒是他。是他,在于秀说分手的时候,眼泪几乎是喷涌而出。他和他的那帮朋友筹建了一个小工厂,他一头扎进去了。而那时候的于秀正是最亮丽,最出风头的时候,明的暗的追求于秀的有不少。遍地的爱情,她以为她可以嫁给任何一个人。他忽视了于秀三个月,再回头,眼睁睁地看到于秀在另外一个男人的怀抱里。
老太太将一块排骨放在于秀碗里,眼睛跟皱纹连成一条长长的线,幸福的人家,可是她遇到的太晚。于秀向老太太甜甜地笑过去,她没能有这样一个好妈妈,如果有又会怎么样呢?如果她能有一个好的家,或许她不会那样的不安,那样地想有个可靠的归宿。
于秀,发什么呆,快吃饭。四峰用筷子轻轻地敲了一下于秀前的盘子说。
于秀慢慢地说,如果我生在这,我也会留下来的,这里多好。
那就嫁到这里来吧,还不晚。四峰说。于秀笑着低下头。
4
下午加颖带着于秀去逛街。小县城的街,市区里打的士从东到西只要五元钱。街上倒是什么品牌的专卖店都有,只是小而粗糙。街上的人也是什么样的都有,衣着也是极时尚的,但脸上的妆差得太多,依旧用艳丽的口红。于秀没有化妆,嘴上用了淡的唇彩。因为心情的缘故,只随便带来了几件T恤和牛仔裤,头发也懒得去弄,随便地在脑后绑了一把,这样干干净净清淡的样子正好让老太太看了高兴。
于秀拉着加颖一定要给老太太买样东西,加颖见推辞不掉,便直说,他们是真的什么都不缺,你还是省着些吧。一句话说得于秀低下头去,她包里有一千多元但也只有那么多,现在失业当中,每天又要花钱。来之前,她偷偷地回家,没有进家远远看到她父亲站在院门口看人下棋,竟然穿着很多年前的一件旧衬衣,下面的扣子掉了,就那样半敞着,头发该理了,脑后有一撮高高地翘着,阴沉着脸。那是她父亲,远远地都可以看出衣服上的油渍,她的家,她忽然感到绝望。一次偶然在街上遇到邻居告诉她,她爸爸带着个不像样的女人在家里住着,她不想看到。掉头往回走,碰上一家服装店在甩货便进去买了两件T恤,写了一张纸条放进手提袋里,回去准备交给门卫,又看看她的弟弟—继母生的孩子,抱着一只篮球跟几个同龄的孩子走过来,便去叫,于端民。又黑又瘦刚长开的孩子,嗓子里发出与他不相称的一声低沉,姐。那一声让于秀几乎要打出冷战,她是这样一个孩子的姐,几乎忘了。从包里抽出一百,又抽出一百交给她的弟弟,家里还好吗?没等回答,她便说,这钱你拿去,一定不要乱花掉。然后把装着T恤的手提袋交给他,转身快步走了。她想哭,真想哭。
最后俩人买了一些水果叫了辆的士回去。街上到处都是的士,没有防护网,车窗上有尘土,司机快乐地回答刚有人包车下乡才回来,还没来得及去洗车。小县城,低矮的房屋,低矮的天空,杂乱的农用品铺在路边上。来来往往的自行车和摩托车,低低的热闹,朴素的繁华。
5
晚上吃过饭,去唱歌。小县城里的娱乐场所也正如加颖所说,都是仿制品,猛地看上去是不错,一坐下来细细感觉,就发现太多粗陋的地方。于秀喜欢唱歌也唱得好,加颖特为她点了一些歌让她唱。很多都是老歌,王菲的《我愿意》她唱了几年,现在依旧在唱:……特別是夜里/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就算多一秒…… 于秀唱着我愿意,可是这些年来有谁是她愿意的人呢?她不知道,一个又一个,她没有痛心彻骨地爱过人。如此想着,高音处唱不上去了,空空的,什么都是空空的。
有男女合唱的,他们硬要于秀跟二峰一同唱。二峰也唱得很好,引得他们一起为二人鼓掌。于秀感受到二峰向他敞开的默契,他在等她的回应。这些年来,于秀深谙男女间的暧昧,她懂得如何把握这种无法言传的感觉,她不说话不动便可使人对她动心,可是现在她觉得怕。不只是因为加颖在这里,也不是因为二峰是四峰的二哥。她只是觉得怕。
她的初恋是在上大二时的同班同学。个子比她还略矮一些,家里境况非常好。她真爱上他什么了吗?其实都很简单,他追求了她。那时的于秀或者说在学生群的她并不出众,只是一种灰扑扑的笨拙感。她的家里也不能给她更多,一个女生相貌不很出众,才艺再无高人之处,通常也引不起男生主动追求。那个男生除了家世也实在同她一样普通,一张苍白的瘦长脸,小小的眼睛注定使人忘记,两个人或许都是出于寂寞。于秀倒是好奇,有那样好的家庭背景的孩子竟然没一点志气的样子。
两个人开始恋爱了,至少形式上是。一起打饭,给对方占座位。在一起说的话其实也是有限的,低低地讲一些趣事,说出来又仿佛是给自己听的,还没说完兴趣已尽,如同对待学业,觉得应该。于秀早早为将来就业做好打算,那男生的家庭背景是可利用的,更何况是那样一个老实可靠的人,她的一个打算直算到了自己的终老。她的继母进了她的家之后,她便没有了家的感觉,无依无靠的恐慌把她的青春咬噬得斑驳陆离,可是有谁看出来了呢?亲戚们背后甚至要夸赞一下她,说亏她傻乎乎的没心眼。她倒是爱笑,露出一对小虎牙。一个宿舍里的人背地里说闲话,好的说她是憨,坏的说她傻。她也只管吩咐那个男生买了大堆的零食请宿舍里的人吃,她那时候胖,虎背熊腰的,走起路来左右晃,精明的舍友甚至不愿与她同行。
老人们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不知是否有人会想到,有一天于秀也会窈窕到女人眼红。
到那个时候,那男生已不在了。他们的爱情在男生家人眼里是荒唐,男生打小就被家人贴上了没出息的标签,他们俩人在一起,他似乎也像有些骨气,可是一毕业回到他的家里,他就什么都没了,他的前途都是家人早设计好了的,于秀根本是个负累。俩人坐在他家里的沙发上,在男生母亲滴水不漏的言辞前,俩人竟然不能为自己做一点辩白,像是做了小动作的学生被老师捉了个正着。他们的那点主张和计划,在强大的现实面前如同小孩子的游戏面对成人世界的工程。
一场所谓的初恋结束了,于秀穿着为了登他家的门特意买的高跟鞋,在大街上喝醉了般走得东倒西歪,她也恍惚着,也许他们根本就是在模仿着做了恋爱的游戏,她没有为与他分手难过,只是为原先的打算落了空失望。
那一段的记忆在于秀脑中,灰暗得一闪要不了一秒便过去了。她记得清楚的是,一年以后的同学聚会。她的登场让在座的同学全部一怔。她学会了化妆,学会了穿得体的时装。
6
晚上安排于秀休息了,老太太又把加颖和四峰叫过去。
于秀睡在加颖他们这边的小套间里,她听到老太太叫他们俩口子过去。心里有种预感,一直嘭嘭地跳,就一直竖着耳朵听动静。听到他们俩在院子里说,二峰真有些看上于秀的样子,你发现了没?四峰说话的声音。然后是开门声,加颖低低地说,我也看出来了,但是……后面的声音被另一扇门关住了。
这一个“但”字后面是什么?于秀看着夜的漆黑向她压下来,她要窒息。她猛地拿起毛巾被蒙在头上,她已经完了,彻底地完了。还有加颖不知道的,单是知道的已足以把她打入地狱。她曾经以为这些不是什么问题,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可是她想真正的嫁人的时候才发现,爱情跟婚姻不是一回事。其实她的那些所谓的爱情是爱情吗?
在她内心底下的黑暗里,她曾走在厚厚的没有声音的地毯上,空气里有种别致的暗香,另外一个世界。楼下的奔驰载着她去的,别墅。是个中年的男人,于秀慢慢地跪下去。她想要一个家,想要依靠,想要更多,想一生衣食无忧。
她狠狠地闭上眼,想把那些记忆斩断,或许还是死了的好。
半天后她又忽然醒悟,一下将毛巾被掀开,睁开眼睛,自己真是可笑,自作多情什么呀,其实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发生不是吗?自己不过是来消遣几日,还是要回她的世界里去,回到那个城市。她释怀了,在黑暗里甜甜地一笑,她学了一种笑,这笑是迷人的很迷人的,与内心无关的笑。这世界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重要吗?
唯独梦不会做假,在那个小县城的夜里,她疯狂的哭泣却闯不出那睡得很死的梦。
第二天,第三天,接下来的几天,于秀都是快乐的。陪着加颖散步,帮着加颖做孕妇体操,在医院做检查时,她看到加颖雪白的肚子高高地耸立在那里,几乎透明的感觉,正好胎儿在动,那肚皮缓慢地变着形状。于秀是第一次这样看过一个孕妇的肚子,感到十分惊诧。一个小生命在那里面,这是多么奇异的事,有一天一个小宝贝会出来,会叫着加颖妈妈。想到这里她呆住,妈妈,妈妈,这是个多么美丽的词汇,可是她没有叫过,对继母她一直都是直接就说话,尽量省了前面的称谓。自己也会做妈妈吗?简直不敢想,仿佛跟自己不是一个世界里的事。
四峰也陪着来了,医生让他们听胎儿的心跳,急促的声音仿佛是奔跑着的马蹄声。四峰即高兴又担忧不住问医生加颖的脚有些浮肿会不会有问题,还要不要再多补些钙,还有什么注意事项。于秀站在他们身后,他们的热闹反衬着她的孤单。她寄住在朋友那里,回去要找工作,要找新的地方去住。想到这里只有厌倦和悲哀,她什么时候才能把皮箱里的衣服一件件地挂出来,什么时候才能安稳地躺在一张床上不用为明天担扰?想着忽然鼻子一酸,忙弯下腰去理了一下腿上的裤子,然后抬起头来露出她的小虎牙笑。
7
晚上吃完饭,于秀说准备明日就回去了,加颖吃了一惊,而心里又全都明白。
院里没人了,加颖和于秀看着猫在墙下的灯光里扑飞蛾。
其实,这里是不错的,留下来也挺好。加颖向于秀望过去,于秀微笑着低着头扯她的牛仔裤的裤角。这夜天不是很晴朗,月亮半隐在云堆里没有星星,院外的树一阵阵地传来沙沙的风声。加颖看着黑暗里被灯光照成青白色的于秀,不知怎的,想起自己小时候看过的小人书,聊斋的《聂小倩》。黑白的画面,月夜下凄凉的女鬼。这跟自己眼前的人和夜似乎扯不上什么关系,但是她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当时看到那图的心情。谁能救得了她,那个时候她希望聂小倩能够被救,于秀是不同的,可是……
说真心话,留下来也不错的,于秀。
不,我想好了,我一定要回去。
在加颖发呆想到女鬼的时候,于秀也在想。她要离开,这里越是使她感到留恋,她才越要离开。她要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要搬家,要找一个可以嫁的人,回家去看看,她下着决心却越往下想越感到了无望。像上学时哪门功课一开始落下了,后面是怎样刻苦都觉得无能为力,但是她已别无选择。
夜里,于秀躺下不久便睡着了,很平稳的一觉,睁开眼睛或许还在那个出租屋里的小床上,不过是个梦吧。
早晨很早就起来了,而老太太早已在院里弄小菜地里的菜了。
于秀洗濑整理好,一家人也都起来了。饭桌上又提起了留下的事,不过只说了两三句也不提了。在院中一一告别,上车时才发现二峰坐在驾驶座上,而加颖和四峰都不预备上车。
加颖依旧是挺着那个笨重的肚子,穿着俗气的孕妇裙,不够好看的浮肿,于秀来时在车站心里暗暗生出的鄙夷已天翻地覆地变成了羡慕甚至是妒嫉。
于秀坐在了后座上。二峰很平静也不说话,只管发动了就走,方向并非是要去的客运站。
我直接送你回去。车开出近十分钟,二峰才说话。
于秀也不知道说什么,车已上了高速公路。他们在一起时,那团空气便是专给他们的,使他们没法像一般人那样正常说话玩笑,他们非得说些心里话,只属于他们俩人的话。而他们预备张口时又感觉说出来的话会变成电影里内心独白的台词。
于秀想挣脱这种感觉,她不许自己这样,二峰不是她以前遇到的那些男人,她完全感觉得到,他是完完全全打开着一片空白等着她。
这里的景色真不错。
有很多事都不是你的错,你何苦为难自己。
于秀一怔。然而这样的话她听过,有些男人是专会说这样的话来叫女孩子上当。但是二峰是那样低沉的声音。于秀把脸转向窗外,爱情她经历的太多了,麻木了,什么样的情话都听了,还能有什么话能使她感动的吗?她自己都想不出来。
加颖还有两个月就要生孩子了,到时候你来吗?
我一定要来。听二峰说这话于秀一下高兴起来,不由得笑起来,一抬头却看到二峰在后视镜里直直地看着她。
嗯,我会去接你。两个月的时间够吗?
什么够不够?
考虑是不是想要有个家,考虑是不是想生个孩子,考虑是不是愿意……
正说着一辆车打着尖锐的喇叭,呼啸着超了过去。于秀睁大眼睛,她没听清二峰后面所说的话,那车走远了,她耳朵里依然是那刺耳的鸣笛。二峰说的愿意什么?她不知道该不该问一下,她担心是她怕的,又是最想要的一句话。
高速公路上,车辆都在飞奔,不能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