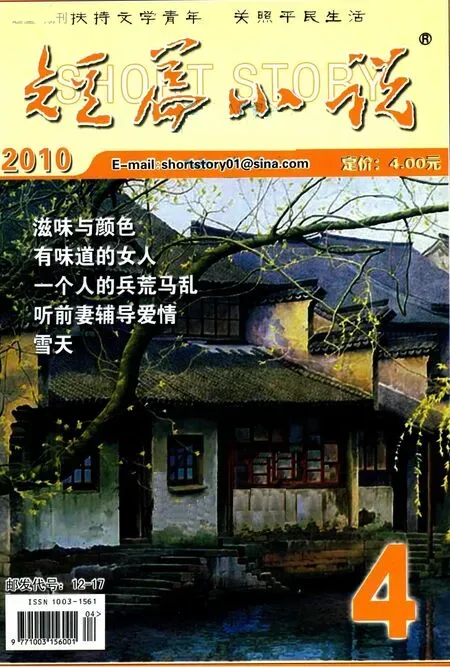半个魂灵
◎曹洪波
半个魂灵
◎曹洪波
屈驴子是在一声巨响的爆炸中,成就了他半个人形的。
那声爆炸炸断了他一条腿和一只胳膊,还炸瞎了他的一只眼,失去了的东西都在他身体的右边,他几乎成了半个人。爆炸是他自找的,他自己用炮仗做炸药,就在他装捻的时候炸药在他怀里爆炸了。任谁也不会相信他做成了炸药是要害人的,后来人们知道了,他要炸死的是他的爹、大哥大嫂和侄女。这样一个没有人性的东西,人们觉得没有把他炸死是便宜他了,上天给他留下半条命就是要让他活受罪的。
屈驴子的大哥屈骡子是个顶头秃子,论个儿论样儿都没有屈驴子人长得有形象。屈驴子长得白白净净还算得上英俊,像个白面书生。但屈驴子从不干白面书生的事儿,整日游手好闲,地不上活不干,不务正业。偷鸡子摸狗,戏场里调戏妇女,电影院里解人家姑娘的裤腰带,又看不上他爹的手艺。
他爹是个兽医仙儿,在埋碑镇这一带还挺有名气,看骡子看驴都有一手,常常为这手绝技引以自豪,就给两个儿子起了骡子和驴子的名字。屈驴子的不务正业让他的兽医父亲十分恼火,常常掂着棍子满镇撵着揍他,声称要把他这个不争气的狗日的腿打断。他挨了揍就半月二十天的不进家,和镇上的小混混们夜聚明散。他兽医父亲从内心里是很向着他的,一心想让他成为他的接班人。不知道他教育这个叫驴子的儿子多少回了——学会了他的这门手艺一辈子都吃喝不愁了。他经常这样吼叫他的儿子屈驴子,但屈驴子就是听不进去。也许他这个儿子一出生他就把名子起瞎了、起错了,千不该万不该让他这个儿子叫驴子。驴子就有驴脾气,既邪又踢套,他给他这个儿子取名时忘了这一层。
屈驴子说,各有各的活法儿,我不学你掏驴屁眼的手艺难道就活不下去了?
驴是直肠子,到了秋天驴们的生活变好了,豆秧、薯秧、花生秧随便吃,便吃出了病,这些庄稼秧子都是由极强极韧的纤维组成,驴们在吃的时候连嚼带挛就把那些秧子挛成了一团结子,堵在了肠道里,黏在了肠壁上,驴们使上吃奶的劲儿也屙不下来了,急得吭啊吭啊地直叫唤,更急的是驴们的主人,驴屙不下来是要被憋死的。秋后他们还指望这些骡子、驴给他们往地里送粪犁地呢。他们唯一的办法是找屈大仙儿,屈大仙儿给这种生病的驴治病既不用药,也不打针输液。他把袖子挽起来,用净水净过胳膊,把手慢慢地伸进驴屁股眼里,随之胳膊也进去了,动作既不能快也不能慢。快了驴受不住,又踢又跳;慢了人的手在驴肠子里找不到症结驴也受不了。屈大仙儿的手又准又狠,在驴肠子里一把就抓着了那团结子,拉出来那团结子是比驴屎要大得多的硬屎团。
屈驴子是见过他爹给驴治病的,他哼了一声。心里说,我才不用手掏自己的屁股眼呢。他不掏他哥屈骡子掏。他哥屈骡子很听他父亲屈大仙的话,背着个木药箱,木药箱拍打着小屁股,一副赖痢头屁颠屁颠地跟在父亲身后,游乡串户。屈骡子也很用功夫学,上手也快,很快就学到了父亲的真传。
那时候才散了生产队,家家户户有田种了,牲口也与日俱增。特别是大牲畜,牛呀、马呀、骡子和驴就多了起来。屈大仙儿和屈骡子的活也多了起来,活多挣钱就多,时间不长,屈大仙儿家就盖起了大瓦屋,蓝丝丝的一溜儿五间。接着有人上门说媒了,是说给老大屈骡子的。那年月,媳妇不好找,屈骡子和屈驴子年龄都不小了,特别是屈骡子再不娶媳妇就兔子跑过了岭。别看屈骡子秃头八脑的,还真有人能看上他。看上他的人不是别人,还是镇上的一枝花,是镇上唱曲子戏的,台下人们叫她浪八圈儿。浪八圈儿人长得高高挑挑,脸庞儿亮亮的,一对又粗又黑的大辫子搭拉到屁股沟里,走起路来,一对圆鼓鼓的小屁股一扭一扭的,一双脚像踩在高跷上。浪八圈儿是唱花旦的,唱花旦的在戏台上既得会浪又得会唱,哪场戏也离不开她浪八圈儿。浪八圈儿一上台,屁股一扭,飞个媚眼,手里掂个花手绢,兰花指儿一翘,台下就会笑声、嘘声、响哨声一片。
分田到户的前几年,到了农闲的时候,乡下人的心里突然空荡起来。可不像现在,衣裳被子用蛇皮袋一装去城里打工去了,是血是汗是泪、是喜是忧是贱总是要趟两腿的。那时候乡下人有了土地的收成就知足了,只是缺少乐子,乡下人自有找乐子的门道。好在还留下几个懂戏的,锣鼓家什,古旧戏装是有心人塞藏起来的,红卫兵那会儿没能搜出来,晒晒洗洗补补就能穿了。剧团是乱串班子,都是农闲时临时组织起来的,闲暇时还有人教戏,浪八圈儿的戏就是这个时候学会的,她除了唱花旦还客串青衣。扮相好,嗓门儿也亮,在台上小碎子步走起来风摆柳一般,乜着个浪腔浪调:
小女子青春十八岁
小哥哥今年也十八
又挑又逗,还有点骚情,所以镇上给她起了个外号——浪八圈儿。
浪八圈儿不缺相好的,在镇子上有头有脸的人怕没有不睡过浪八圈儿的。屈驴子也想睡浪八圈儿,只是他有那个贼心还没长出那个贼胆,他知道浪八圈儿连眼角夹也不会夹他一下。他逢浪八圈儿的戏每场必看,还撵着戏台子看。屈驴子看戏不是看戏,他是在闹场,每次只要浪八圈儿岀场,他都要放嘘声吹口哨,那口哨又长又亮,啾儿——啾儿的,胜过了锣鼓家什和琴声。别看他长得人模狗样却是个讨人嫌的家伙,戏场上的人们都痛恨他,就有人趁黑朝他扔砖头,扔烂鞋。屈驴子就满场找着要打人,乡里乡亲的人们不跟他一样子,任他在戏场里胡窜乱跳,这时候他会碰到大闺女小媳妇,就顺势照人家怀里摸一把,朝人家屁股上掐一下。为此他也没少在戏场里挨打,也挨了不少死打,只是他狗改不了吃屎,是个记吃不记打的货色。
一次他撵着浪八圈儿到外乡看戏,他禁不住心跳眼热,戏散场的时候他摸到后台。后台是用高粱秆子围起来的,他通过缝隙看见浪八圈儿正在卸装。浪八圈儿脱了戏装就露出了内衣,内衣雪白,兜着一对欢实的大奶子。屈驴子也顾不得三七二十一了,这双大奶子在他心里也不知道扑腾了多少个夜晚。他扒开高粱秆跳上了后台,抱着浪八圈儿就用臭嘴去啃。浪八圈儿惊叫,流氓……流氓……刚散场的观众一阵回头,突然醒悟过来后,就有了屈驴子的好受。棍棒,砖头,拳头,冰雹一样落在他身上。屈驴子也真犟,也是他挨打挨惯了,抱着浪八圈儿就是不肯放手,外乡人又不认识他,就朝死里打他。一个人突然夺过了还在那愣神的手里的大锣,他把大锣猛地朝屈驴子头上砸去,大锣“哐”的一声只剩下了个锣圈套在他脖子上,屈驴子不由自主地松了抱着浪八圈儿的双手,人们又一阵子猛打,只打得屈驴子皮开肉绽不醒人事。这一次屈驴子算把丑丢尽了,坏名声响了几十里。为此,屈驴子的父亲屈大仙儿和大哥屈骡子,不但没有为他讨回一分钱的医疗费,还因为他耍流氓惹他爹屈大仙儿为挽回点面子,免费为那个村的牲口看了一年病。
后来浪八圈儿不唱戏了,她的屁股越来越大,腰也越来越粗,她想嫁男人能挑一个排一个连的人,但她单单挑中了秃子屈骡子。屈大仙儿不嫌浪八圈儿屁股大腰粗,屈骡子也不嫌浪八圈儿屁股大腰粗,就这么着经媒人一说事成了。屈驴子却不愿意让他哥娶她,他知道些浪八圈儿的底细,浪八圈儿的屁股咋大,腰咋粗的屈驴子倍清。但绝不是他干的,他只是眼谗罢了,他也只是知道睡她的男人多,他却不知道谁把她的屁股睡大了,腰睡粗了。
其实不光他倍清,他爹屈大仙儿及全埋碑镇的人,几乎都倍清。她是怀了别人的种,才肯嫁给屈骡子的。屈骡子秃头八脑的娶了浪八圈儿就能省下许多劲来,自己不用下力就能当爹了,屈大仙儿也知道儿子屈骡子可能没本事留下后,无论如何有浪八圈儿他儿子秃头八脑的总算成了个家。屈驴子也是吃不到葡萄才说葡萄酸,平时不管不问家事的他跳了岀来,硬是要顶坏屈骡子的这门婚事。
屈大仙儿和屈骡子是一个立场,先是仨口人相互吵骂。屈驴子言词凿凿地说,她是个浪八圈儿,睡过多少男人?屈大仙儿说,睡过多少男人碍你啥事了?过了门她只要给你哥睡。屈驴子说,那也不见得!屈大仙儿说,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就没有安好心。屈骡子也记起了屈驴子抱着浪八圈儿啃的事来,嫉火猛生,掂个家什就大打出手了。屈大仙儿和屈骡子用棍棒满镇子撵着屈驴子又是一次痛打,屈大仙儿扬言再也不要他这个儿子了,他是生怕这个儿子会在他嫂子身上生出事端来。屈驴子是害怕他爹屈大仙儿的,他怀疑他不是屈大仙儿亲生的,他只亲生了一个秃头八脑的屈骡子。更让屈驴子想不到是,他爹屈大仙儿果真把他撵出了门,那一溜五间大瓦屋给了哥哥屈骡子,把他撵到了老院低矮的茅草屋中。屈大仙儿还煞有介事地请了村长罗狗子和四邻作证,把屈驴子也叫到了场。屈驴子听了事由,端起酒杯饮了满满一杯,酒杯朝地下一下子摔了个粉碎,连哼也没哼一声,卷起铺盖搬进了茅草屋中。
浪八圈儿是挺着个大肚子嫁给屈骡子的,很快浪八圈儿就为屈骡子生下一个女儿,这下喜坏了屈大仙儿和秃头屈骡子。屈大仙儿和屈秃子这时候事业正旺,就在自己的五间蓝瓦屋前清了个大场子,拉了围墙,办了个兽医站,不再游乡串村了。兽医站日渐红火,驴骡马拴满了院子,咴咴的叫声响彻镇子。浪八圈儿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滋润,肚也小了,腰也细了,只是一双奶子撑破了衣衫。每日里穿得花枝招展,涂脂抹粉,逢集了就挎个篮子到了街上买菜,大鱼大肉香菜白菜采购得满满当当,一路上见人就喜形于色,扭着个浪腰,一脸淫笑。屈驴子无所事事每天都在镇子上游荡,他眼气死了他嫂子浪八圈儿的这种浪劲,在无数个夜晚梦见过她柔软的屁股和扭动的腰肢,想象着她颤微微的奶子,他恨不得张开一张大口把她吞到肚里去。
终于有一天他发现他嫂子浪八圈儿还一直和村长罗狗子约会。
罗狗子有几间门面房子,经营着糖烟酒,生意比较冷清,后院拴着两条恶狗,他不在的时候,恶狗就为他看门。他嫂子浪八圈儿每次上街都要拐进罗狗子的门面房里,开始的时候是装着买东西,糖呀盐呀火柴和香烟她都稀罕,看看摸摸,然后扭扭屁股就进了罗狗子的后院,罗狗子就会放出两条恶狗为他看门,出来的时候浪八圈儿的篮子里就会多上一条烟或者是一包盐,这烟或盐也不是罗狗子免费送给她的,是她掏了咯嘣嘣的现钱买的。这种事情屈驴子见到好几次,有一次他趁两条看门的恶狗相互打闹不注意,还顺走了两条上好的香烟,美美地吸了一阵子。还有一次,他又看到嫂子浪八圈儿进了罗狗子的门店,他心里实在痒痒,决定一看究竟,就心生一计,跑到食堂给人家要了一些鸡骨头,他用纸包着鸡骨头悄悄进了罗狗子的店,把鸡骨头撒在门店的角落里,那两条恶狗闻着香味便上去了,他就又悄悄溜进了后院,他把耳朵贴近窗户听了,里面果然传出了浪八圈儿的声音。
看看,我又怀孕了,还是你个死东西的。
你这块地就是对我亲。
他爹没给他起错名,他就是个骡子。
骡子能每夜搂着你,也够有福气了。
他也想有自己的孩子,但他连个秃子瘸子也生不出来。
咱有一个妮儿了,这回你再给我生个娃儿。
想得美,是妮儿是娃儿还早着呢,现在谁也看不出来。
敢整不?
你少整了?
亲亲,亲亲,腰还是恁细恁柔,再过几个月就搂不成了。
浪八圈儿一定是在脱衣服了,他们大天白日找个机会就干那事儿,头个女孩还有现在她肚子里的孩子,原来都是狗日罗狗子的,屈骡子他妈的就是在给人家养孩子。屈驴子无心骂下去,他想看看他夜思梦想的嫂子浪八圈儿脱了衣服是个什么勾人的样子。正如罗狗子说的,不管怎样秃头八脑的屈骡子还是有福的,他还能夜夜搂着香喷喷的美人睡,他却只能偷鸡子摸狗,钻寡妇的不栓门子,招呼不好还会挨上一顿毒打。他扒着窗户使劲往里看,玻璃是毛玻璃,他任凭如何爆珠子瞪眼,也看不到屋里的任何情况。他急得猴扒豆一样,歪着头张着嘴想找个缝隙,玻璃窗严丝合缝,他只能听到屋里的哼哼声和扑哧扑哧气筒打气一样的声音。就在这时,一只恶狗冷不防呼的一声蹿到了他身上,他赶忙身子一趔逃也似的逃出了罗狗子的门店,这次他没能顺走罗狗子的香烟。
屈驴子逃到大街上,大街上人不多,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尴尬的脸色和愤怒。他想也没敢想破门而入为他大哥捉奸,他是无论如何也对付不过罗狗子的,加上会掏驴屁股眼的父亲和他秃头八脑的哥哥。罗狗子在埋碑镇可不是个等闲之辈,是个黑白两道都能吃得开的人物。那个时候黑道上的人们在社会上还没那么猖獗,人们还分不清黑白二色,黑道上的人已称他为大哥了。罗狗子还有更深的官方背景,据说他的姑父是县里的大官,连书记镇长都要敬他三分。屈驴子充其量是个爹嫌弃哥不爱,好吃懒做的街混混。即使他把在罗狗子家看到的给他爹他哥说了,他爹他哥也不会相信,即使相信了他们也无何奈何,只是装作没那么一回事儿,还要骂他无事生非,惹不好棍棒加身,又要把他的腿打断了,他们还会替嫂子浪八圈儿说话。
你见她在大街上浪了,脱光了让人整啦,你是不是又想打你嫂子的主意了?
况且现在他和那个掏驴屁股眼的家里没了一点关系,早已和他们形同陌路。虽然罗狗子给他们家带来了耻辱,但他们家把耻辱二字看得很淡,他也只想做他愿意做的事,哪怕人们骂他打他。在他心里,他的一腔怒火只会对准他的家人,他不务正业,懒惰,懦弱,一副不要脸的嘴脸。要是逼着他恨罗狗子,他也怕恨不起来,他只能恨他的爹屈大仙儿,还恨他哥哥屈骡子,还有浪八圈儿。浪八圈儿竟要给罗狗子生两个孩子,还要一男一女。这时候他对罗狗子的恨,是在他猝不及防中,开始慢慢地滋生下来。
眼看父亲通过掏驴屁股眼创下的家业,很快就要被浪八圈儿独吞,吞后再领着一对子女回归罗狗子的名下,屈驴子从心里是不愿意的,他还眼谗着跟别人生儿育女跟秃子大哥睡的女人,他要一只脚插进去。想一脚插进去,他必须要有重大变化,不但让小镇人看还得让他爹看得见,摸得着。这会儿,他爹屈大仙儿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经常咳嗽。兽医站的生意却分外红火,热闹得像牲畜市场,牛马猪羊得了病都往这儿赶,大包小包的草药被带走。浪八圈儿现在也能打下手了,嘴里边哼着小曲边给牲口抓药,屈大仙儿忙成了四节子菜,不单单掏驴屁股眼了,还要给牛马看牙口,给猪羊量体温。秃子屈骡子则给牛灌药汤,给温猪打针,五间蓝瓦屋的院子里传出的是不绝于耳的牲口们的叫声。
屈驴子想,他们的生意这般红火,一定缺人手了,还不如回去说两句软话,赔个不是,帮他们牵牵牛,搬搬腿,拽拽猪尾巴也算干上正业了。不但能分些钱财,还能接近浪八圈儿,逮着机会睡了她说不定落下个一儿半女也是俺姓屈的,就不至于肥水只流外人田了。他觉得他这个决定是再也聪明不过的决定了,父亲屈大仙儿一定认为他改邪归正了,浪子回头金不换嘛。
他来到兽医站找到他爹屈大仙儿,屈大仙儿正给一头牛看舌苔,双手吃力地掰着牛嘴,还不停地咳嗽。屈骡子正忙着给一头猪打针,粗大的针头扎进猪脖子里,那猪刺耳般地嚎叫。浪八圈儿扭着细腰正在一间改建过的柜台前忙碌,她的肚子看不出她又怀了罗狗子的种。几个给牲口抓药的人不是看她称药包药,而是在看她的胸脯,两眼谗得涎水都流出来了。她的双胸装在一件低领的衣衫里,露出半边雪白的奶子。有时候,她还会拉过女儿,搂起胸脯就给孩子喂奶,白大的奶子裸露在外面,像两堆刺眼的雪,她也毫无顾及。在屈驴子看来,平添了些故意的成分。屈驴子觉得,那些扯了牲口来看病的,不论牲口大病小病都往这儿牵,多是冲着浪八圈儿来的,不但能给牲口看病,还能和浪八圈儿说说话,看一看她的浪劲儿,她那双雪白的奶子更能饱一饱眼福。
屈驴子慢不经心无所事事地在院子里晃悠,人们见到他像没见到一样,谁也不理会他。他禁不住地来到柜台前,把一双膀子架在柜台上,狠了狠心叫了一声嫂子。这是平生第一次叫浪八圈儿嫂子,浪八圈儿突然把脸扭向药柜前,给了他一个背影,那背影浑圆,一团逼人的肉气,而他感到了冷漠。

冷漠对于屈驴子来说是个好东西,他就是被冷漠磨炼出来的。
他又去找他的爹,屈驴子说,爹我来看您了。
屈大仙儿扭头看了他一眼,一阵猛咳。
爹您病了,憩憩吧!
去,哪来回哪去!小心老子把你腿打断。屈大仙儿说。
屈驴子想,你把我腿打断我也不走了,现在我就懒在这了。
这时候屈骡子正要给另一头猪打针,那猪个头大,又不老实,蹦着跳着还要扭头咬人,猪的主人抱着猪脖子,大猪把他甩得团团转,屈骡子手里握着大针管也跟着转,怎么也扎不下去。屈驴子赶忙跑去一把抓着了猪尾巴,生生地把猪的后半部拎了起来,猪一下子老实了,屈骡子稳稳地给猪打了一针。
哥,我过来帮忙吧!
屈骡子斜视他一眼,秃头上的红光一闪一闪,忙别的去了。
屈驴子又来到屈大仙儿身边,屈大仙儿正给一个牛看病。他拽着牛绳说,爹我过来帮忙吧!屈大仙儿照牛身上击了一掌,对牛主人说,这牛没事,回去多饮水就好了。
屈驴子叫道,爹,我改好还不行吗?
屈大仙儿咳了一声。秋阳西下,快要收秋了,到了收秋的时候,生意会清冷起来,收罢秋大牲畜的毛病都出来了,到那时会更忙。屈大仙儿想,如果驴子肯学好,他还是乐意他来帮忙的,趁他还活着,只要他回心转意务了正业,给他盖几间屋,娶房媳妇,弟兄俩和和睦睦安安生生地过日子,他便是两眼一合也就知足了。
屈大仙儿心里这样想着,却没有答复他,只是看他的眼光突然柔和起来,不像以往凶凶巴巴的样子了。屈驴子从他爹的眼光里看到了希望,他在心里一时高兴起来。
也是该出事儿,浪八圈儿想在晚上煮稀饭时,在稀饭里掺些嫩苞谷籽,老爷子喜欢喝这样的稀饭。她就对屈大仙儿说,爹我去地里掰俩嫩苞谷棒儿。
浪八圈儿扭出门外后,在院子里晃来晃去的屈驴子一闪身子不见了。
屈驴子尾随嫂子浪八圈儿去了地里,浪八圈儿是极少上地的,这天也是她鬼使神差,也都怨公公在一次喝稀饭的时候说,要是里面再丢些嫩嫩苞谷粒就更好喝了。她才在临做稀饭时想起来,要到地里掰几棒子苞谷的。她家的地是和屈驴子的地紧挨着的,分家的时候自然也给屈驴子另分开了。她家地里的庄稼是公公和丈夫秃子抽闲干出来的,苞谷长得绿油油的,高大粗壮,棒子个个支楞着,棒槌那么粗。屈驴子地里的庄稼却长得不像样子,他把种子丢进地里后就再也没管过,草比苞谷还要高,一撮一撮的,苞谷苗也没间。极度营养不良,长得黄毛尿脐一样,有个小棒棒也像小孩鸡巴。
浪八圈儿走进地里挑选嫩苞谷,这时天有些暗了,偶尔一二个人影匆匆朝家里奔。浪八圈儿心里虽有些发慌,但她想,自己轻易不下地,下回地就会被人跟踪了,没那么巧的事。而这时屈驴子却偏偏就在她身后,只是躲在一行密不透风的苞谷棵里。就在她伸手掰苞谷棒时,屈驴子在背后一把抱住了她,她吓得大叫了一声。
屈驴子说,嫂子嫂子是我。
浪八圈儿已经感觉到是他了,她熟悉他抱她的样子,把她箍得死死的,呼哧呼哧喘着热气。
她说驴子你放开我放开我,再不放开我喊人了。
屈驴子就是不放手,他说,亲亲能整不?能整不?
浪八圈儿突然记起来了,这是罗狗子前天说的话,咋会到他嘴里了?怪不得那天罗狗子的院子里有点不对劲儿,狗们后来一阵狂叫,原来是屈驴子听了墙根。既然他屈驴子知道了,浪八圈儿的胆也大了。
浪八圈儿说,你放不放?你知道我是谁的人了吧,你想作死?!
屈驴子松了手一屁股坐在地上,他变得可怜起来。
他说嫂子我想你喜欢你,你让我睡一次我就回去帮你一家干活,当牛做马干一辈子都行。
浪八圈儿恨恨地说,看你那德行!啪啪,麻利地掰了俩棒子,扭着让他眼谗的身子走了,丢给他屈驴子的是一副模糊身影。
屈驴子屋冷灶凉,心灰到了极点。浪八圈儿能看上他秃头子哥哥,能和村长罗狗子偷情生孩子,却对他冷若冰霜还报有敌意。他突然间觉得他现在的这个样子,全是他爹屈大仙儿和他的秃子哥哥屈骡子一手造成的。他们容得下浪八圈儿,能容得下浪八圈儿跟别人偷情生孩子,却不能容得下自己,他觉得他自己白活了,白在社会当了这么多年混混。强烈的愤怒产生了强烈的报复。天黑下来了,村子很静,他坐在自己幽暗的茅草屋里,聆听着寂寥的虫鸣。黑暗和虫鸣使得他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原来要回去帮他父亲屈大仙儿的想法,被强烈的报复欲冲得七零八落。
这个草屋他是不经常回来住的,他游荡哪就会在哪滚上一夜,现在屋子里有一股股潮湿呛鼻的霉味,他摸索着点了一根蜡。他现在还在点蜡,村里人家早就用上电灯了。他心里是一直想过上村长罗狗子那样的生活的,当个村官吃不愁穿不忧还能睡漂亮女人,他觉得自己很失败、很无奈。然而,他的爹不能给他这些,还成了村长罗狗子的帮凶,他的恨不打一处来了。有一箱炮仗还是年下在乡下的一个店里偷的,想换些过年钱,却没能卖出去。今晚他要让这些炮仗发挥作用,他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儿。他要炸掉那一溜儿篮丝丝大瓦屋、炸掉为浪八圈儿挣钱的兽医站、炸死那个混蛋老不死的、炸死浪八圈儿和她偷情生的女儿还有她肚里的野种。
屈驴子把炮仗一只一只全拆开来,倒出里面的黑药,黑药倒了一桌子。他想起了电影里炸碉堡用的炸药包,他模仿炸药包的样子找来了麻袋,他把那些黑炸药小心地用麻袋包了。没有导火索是不行的,炸药包就不会爆炸。他就用炮仗上的捻子,他把那些捻子都捻在一起,捻得粗粗的,长长的。他以为他的炸药包做成了,他就找来了一根钢筋,要把炸药包钻个窟窿,把捻子续进去。他咬着牙,恨恨地用钢筋钻着炸药包。嘴里还不停骂着,恶狠狠的:炸死恁龟孙们、炸死恁龟孙们。就在这时,轰的一声巨响,炸药包爆炸了,他头顶上的茅草房被掀了个顶朝天,茅草四散飞扬。
等屈驴子醒来,他已经是个废人了。右腿右胳膊右眼全没了,还是他爹屈大仙儿把他弄到医院的,又拿钱治好了他的伤。他出院后被他爹屈大仙儿又扔回了那个破院里,然后大声咳嗽着走了。走时身子是摇晃的,与他半架身子差不多了,看来父亲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他的心不由得酸了一下。
是为自己也为他的父亲。
茅草屋也不知是谁给他收拾过了,像他这样的人活该受罪,他躺在一张破床上,他知道被炸成了半个人儿,还炸跑了他半个魂灵。浪八圈儿再也不在他眼前晃悠了,再也走不进他的梦里了,只有夜夜的疼陪伴着他。他问自己这是报应吗?他觉得应该是的,但为什么这么大的报应不会报应到罗狗子身上,他百思不得其解。他只能死在这间茅草屋里了,半个身子不能站也不能爬,不被饿死也会被冻死。父亲为他尽了力了,现在他再也没有勇气恨父亲了。
他想,他必须活下来。
活下来的诱惑比一个女人的诱惑更大,屈驴子的一只手抚摸着他那条被炸断的右腿,他想像不出为何炸药就把自己的腿炸断了,他爹常骂他要把他打断的,现在果然断了,一直断在大腿根上。被炸断的右腿伤口已经愈合,愈合成了鲜嫩的肉疙瘩。他的右胳膊断了半截成了一截没用的肉棍。他必须站起来才有活路,才能自立更生。他开动所有能够思维的机器,灵光一闪。那是他发现杂乱的院子里还有一棵稚嫩的桐树,桐树恰巧有大腿那么粗。桐树是轻便木材,中间空,又容易鼓捣。他觉得那棵稚嫩的桐树就是他的腿了。他的聪明才智终于得到了发挥,他连滚带爬地到那棵桐树下,使出了全部气力才用一把锈刀把那棵桐树砍倒。比着自己的另一条腿截下一节树干,没日没夜地又是用刀剜又是用碗片刮,做起了假肢。功夫不负有心人,假肢终于做成了,他把大腿上那节肉疙瘩塞进桐树做的假腿后,他就觉得自己又能站起来了。
他仰天长笑,一只独眼流着泪,而另一只眼却是深不见底的洞。
每走一步都是钻心的疼痛,僵硬的假肢支撑起半个身子,一高一低地练习走路。桐树杆的假腿,磨烂了他的鲜肉,血从裤筒里一次一次地流岀,他终于发现了自己是有毅力的。
他开始上街行乞,埋碑镇多了一道风景。一个胡子拉碴的独眼男人,甩动一只空袖筒子,一只脚轻一只脚重,咚一声、咚一声地响过街道,挨个门店乞讨。有人愿意施舍,给他一张毛票。有人不愿施舍就撵他,滚、滚得远远的。有人给他端饭,他不要饭,只要钱。这就更引起了小镇人的愤怒。他再去人家门店前讨要,店主就会用棍子赶他,人们的眼里满是不屑和鄙视。
一次他走过村长罗狗子的门店,他是想隔了他家的门店过去的,他终于鼓足了勇气要过去。他觉得任凭谁不施舍,他也不能恨。但他罗狗子就是施舍了,他也不要。但是,罗狗子还是叫住了他。
这不是驴子吗?你没死呀?!
屈驴子说,驴有犟命,死不了!他猛地说出这句话,说得很有底气,像换个了人似的。
村子罗狗子冷笑了一声,从柜台上用两个指头捏了五块钱,丢在他面前。那钱轻飘飘地落在他那条断腿的脚下。屈驴子用那条桐木做的脚咯吱一声踏过,咚一下、咚一下,踩得街面直动弹。
他必须学会种地了,他还有一亩二分地,是爹分给他的。他不知道他爹的咳嗽好点了没有,好像喂大牲口的人家一下子突然少了许多,不见了牛骡马犁地,地里的拖拉机倒是多了起来,隆隆声要把他的茅屋震塌,他莫名地担心起了他爹屈大仙儿的兽医站。
现在荒草和黄毛尿脐一样的苞谷还戳在地里,别人家的地里已长出了麦子,绿了整个田野,就他的田地还荒芜着,要想生存必须下苦力了。他找来锛子,他把锛子用绳子绑在残去了的右肢上,用左手费力地砍。他想,等他砍完了这些杂草,就用讨来的钱租台拖拉机犁地,然后种上麦子,让自己这个半拉人过一过自食其力的生活。
他一天又一天就这样砍着,苞谷秆倒了,野草倒了,他的成就感就来了。躺在草堆上憩一憩,听蛐蛐叫两声,半个魂灵就活了,又有了气力。
这天,村长罗狗子却把小车开到了他的地头上,晃动着肥胖的身子,笑咪咪夸他道,屈驴子啊屈驴子啊,你还真是个人物,有种,你爹没白给你起这个名子。
屈驴子不理他,又要去砍草。罗狗子说,你这半拉子人就甭干这活了,我给你说个好事儿,你听了我活,能吃香的喝辣的,还有钱赚,保你后半生享福。
屈驴子对他不报好意,但他要看他到底有什么好事儿。
屈驴子说,说!
村长罗狗子说,我拉你进城。
进城?屈驴子感到意外,他罗狗子突然发了善心了。村长罗狗子把一支香烟刁在嘴里,眼光毒毒地看定他,一脸的邪笑。他说,对,进城,凭你这半拉身子,在城里最好混饭吃了,车站、广场、地铁隧道……随便在哪儿都能挣钱。我一个哥们打群架被人砍了,在北京发大财了,你去了就找他,不用下力准保也能发大财。
屈驴子刚刚安定下来的思绪一下被他打乱了,他要决然回绝他,却又犹豫了一下。
罗狗子说,你犹豫啥犹豫,在家还能混出个人样儿吗?你前些年都没混出来,半拉子人了,种地还不累死!
屈驴子想的不是这些,他在想,上天是不是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和罗狗子一同下地狱。
瞬间产生的想法,使他的心尖打颤。
他说你用车拉我去?他说是呀!你要愿意咱现在就走,我也要见见我那个哥儿们。
屈驴子问,现在吗?
罗狗子说,就现在,你还有啥东西值得收拾?
屈驴子说,没啥收拾,我是半拉人儿,半个魂儿。
坐上车后,屈驴子想了想说,我得拿着我的锛子,我就这一件家具了。
罗狗子笑了笑。屈驴子一高一低趔着身子,又回到了地里,地里一深一浅留下了两道脚印。小车飞速地离开了埋碑镇,他从车窗里看了一眼埋碑镇,又远远地看了一眼他父亲屈大仙儿和哥哥屈骡子家的那一溜五间蓝瓦屋。
屈驴子不知道的是:他嫂子浪八圈儿和镇上的人要把他轰出小镇,村长罗狗子就想出了这么个歪主意。
村长罗狗子不知道的是:屈驴子左手里的铁锛子,在寻找着机会,随时会劈向他的头去。
责任编辑/乙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