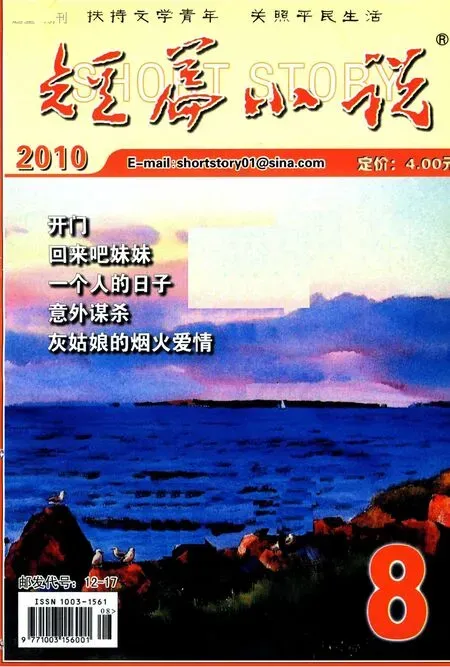通灵的女教师
◎郑建武
通灵的女教师
◎郑建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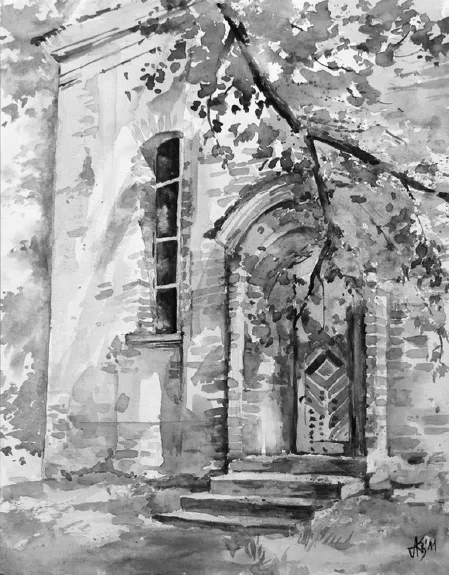
1
开始这个故事之前,我想我有必要对故事的讲述者做一个简短的介绍,这也是我凭借不多的几次来往,和妻子多年的交往,所做出的总结。话说回来,现在像她这样的大龄单身女青年,到处都是,长相倒也过得去,就是有些挑剔,要说人家的要求不合理,年轻时候也不乏长得帅又懂得浪漫的追求者,也谈过一两个,时间不算短,三年两年的,不知怎么就断了联系。妻子有时候带着调侃意味地劝她,可她说,相亲的那些,长相总体还是过得去,除了一两个活得真有勇气,其他的都还能接受,就是性格对不上榫。有一个本来她觉得各方面都还过得去的,虽说年龄大了近十岁,有房子,跟父母住在一起,这些她都能忍受,可第二次见面,就一副商量终身大事的气势,问她能不能接受他目前还有个交往了七八年的情人,就像这样的人,还相什么亲呀,脑子摆明就有问题。妻子的这位女同学叫杨柳凤,今年三十一岁,一直跟兄嫂住一起,富于幻想,做梦都想着浪漫,平日里乐于打听一些他人的风流情史,性子里也爱极了那些神神秘秘古灵精怪的恐怖故事。
就是这样一个女人,有一天晚上突然拜访我们,一进门就吧啦吧啦地跟妻子讲,她再也受不了她的嫂子了,她这一次一定要搬出来,不能再跟她哥哥嫂子一起住下去了。正好赶上我们在吃晚餐,我就给她斟了一杯红酒,在杨柳凤看来,红酒是餐桌的心灵,那红艳艳的飘荡在透明高脚玻璃杯里的液体,是对她的烦恼最大的安慰。她的第二大安慰,就是有了我们这对愿意安安静静听她唠叨个没完的朋友。她也深知自己的这个毛病,所以她又在她找老公的条件里添加了两个:一、爱喝红酒;二、善于倾听。
“你们一定很奇怪我怎么跟嫂子闹翻了。”杨柳凤接过我递给她的茶,抿了一口,发现有点烫嘴,又放下。
“他们又给你介绍相亲对象了?”妻子坐在我们中间,手里拿着遥控器,盯着电视选台。
“这次没有。”
“上次听你说起你嫂子怀上了,孕妇情绪上多多少少有点变化。”
“小变化我能理解,大变化我就无法接受了。”
“大变化?”妻子终于选定一个台,放下遥控器,“有的人是变化挺大的。就比如我当年吧……”
“我说的变化可不是因为大肚子,”杨柳凤说到这里止住了,拿起茶杯,停留在嘴唇边,似乎在试探茶水的温度,又似乎是在考虑该不该把她所想的事说出来,最后,嘴唇一收,把整杯茶吸进口里,放下杯子,好像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继续说道,“嫂子跟我哥结婚六七年了,一直怀不上,为此他们没少跑医院,检查报告单家里都垒了半人高,吃过的中西药,堆起来都能占去大半个客厅。因为这事,嫂子跟哥哥没少吵架,要不是因为我事前藏着他们的结婚证,事后充当和事老,他们婚都不知离了多少回了。”
杨柳凤就这样在我家的客厅里讲了起来。
2
今年二月份,我们都回老家过年。老实说,我们谁都不愿意回去,横在我爸妈头上有两个大问题,他们的儿子结婚多年一直没捣鼓出个小孩来,他们的女儿奔出了三十这个大门,却总是蹦不出娘家这个门。这同时也是让我们头痛的事,谁愿意回到老家受那些七姑八婆的指指点点,他们个个口头上很关切地询问,其实心里头,都乐得看我们家的笑话。嫂子更是打心里不愿意跟着我们回去,想以单位过年值班为由一个人留在城里,我也清楚,她比我们谁都怕面对我的父母,后来母亲跟哥哥嫂子谈了一件事,嫂子才同意跟我们一起回去,我也是等到老家才知道。母亲说村里有个仙姑能帮妇女 “观花”,知晓她此生的子息,说白了,就是一种通灵术,通过它能够探知一个女人这辈子的婚姻、子息情况,甚至,母亲神兮兮地暗示着,能够心想事成。哥哥一向崇尚现代医疗,对老家流行的这类迷信行为非常不屑,无奈经过这么多年的尝试和无数次的挫败,哥哥终于低下头,答应母亲。回到老家的第二个晚上,我陪着嫂子,跟着母亲走出家门。
乡下的夜晚,特别是农历的月底月初那几天,走在路上,就像走进浓郁的墨水画里,到处泼着黏稠稠的黑暗,母亲走惯了,在前面带路,我跟嫂子十指紧握,不是用双眼在找路,倒成了瞎眼蝙蝠,靠母亲的鞋子碰撞路面回弹的声音来判断方向。走过几条村道,拐进一处老寨门,进入围寨里的老村,我低声跟嫂子说,围寨里的路面都是用墓碑石铺就的,嫂子在我的手臂上掐一下,不知哪里窜出来一只什么东西,黑漆漆的一团,在墙角“喵”的一声又消失了,嫂子抓紧我的手臂,我湿漉漉的手心能感受到嫂子传过来的寒冷。一处门楼口,一个老太婆坐在门槛上,在她身边点着一根蜡烛,老太婆张开掉光了牙齿的嘴,对我们露出慈祥的笑容。村里人都搬到外面去了,老寨一到了晚上就黑灯瞎火,偶有一两个屋里透出亮光,也只是上了年纪的人,留下来每夜思念他们的年轻岁月。
又拐进一条小巷子,母亲说,到了。
小巷子的尽头,一个门洞里透着光,站着一个瘦小的老头,抽着烟,白发在黑暗中润出光泽。
“来了。”老头说。
“来了。”母亲说。
“前面有几人。”
“我们等等。”
天井里不甚明亮的灯光下,笼罩着几个围坐在一起的中年妇女。我们便在几张凳子上坐下。里间的门挂着一面竹子帘,看不清里面的情形。一个妇女的低语询问声,又有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传出来,天井里先来的妇女都在倾听着,我站了起来,附耳问母亲,母亲低声责备我,我也就不再做声。天井的墙角边堆着好些盆栽,都是村里人常见的有吉祥意头的植物,最顶角是一株半人高的火旺,紧挨着一棵很有些年头的石榴树,一个破盆子里是密集的春草,还有些小株榕树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植物。
终于最后一个妇女翻开竹帘,从里面走出来。白发老头招呼母亲,我们跟随母亲进到里间。一个长头发瘦长脸的女子对我们点点头,示意我们在她面前的一张长凳上坐下。这就是仙姑了,我不敢瞪着她看,假装看着她身旁的神龛,用眼角余光在她身上斜斜地扫过。她比嫂子大不了多少岁,长发自然垂直,细长的眼睛外眼角往上提起,显得特别有神,望定人的时候,或许是因为职业的关系,让人感觉她一定知晓你什么秘密。不知道是因为灯光的关系,还是我的错觉,我总感觉她应该是长时间呆在一个空气不流通,缺乏阳光的空间里,脸上泛着不健康的白。
母亲说了我和嫂子的情况,仙姑开口了,声音很低,软绵绵的。她说鉴于我嫂子的情况,今晚她只能带嫂子一个人去,等下时间来得及,就帮我也观一观。我赶紧说,我本来就不打算要去的,我只是来看看。仙姑听到我这么说,提了提嘴唇,像是在微笑。后来我仔细观察,才发现,她时不时就提嘴唇,看着是在笑,其实只是一个习惯动作,她的眼里并没有笑意,只是望定一个方向,耀着光。
原来在神龛的背后,还有一个门,里面有一个更小的隔间。我们跟随仙姑走进小隔间。房间正中间是一张八仙桌,四面各摆放着一张跟八仙桌一样染红漆的横凳,我们分别坐在四个方向。八仙桌的中央安放着一尊香炉,两个烛台。仙姑点燃一对蜡烛,插上烛台,又点了三枝香,十指相参,把香枝捻在手心,举上额头,然后紧闭双眼,口中默默念叨,完了,把香枝插进香炉,用手把香灰压实,再把三枝香呈扇状分开。接下来,仙姑吩咐嫂子,双手平放在桌面上,头俯向桌子,额头顶着桌面,双眼紧闭,没有招呼千万不得擅自睁开。紧接着仙姑把双手放入一个装有十二色花的搪瓷盆里,沾了沾水,手做兰花状把水弹到嫂子和自己头上,同时口中吐出词咒,随着她念的词咒速度加快,蜡烛开始在静室中无风闪烁,很快,仙姑也像她要求嫂子那样额头和双手紧贴桌面趴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仙姑的身子开始微微抖动,嫂子的身体也跟着颤抖,两人的手并没有接触,但似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从仙姑身上传递到嫂子身上。颤抖先从双手和头部传入,霎时间到了肩膀,转眼就遍及全身。我有些害怕,赶紧从凳子上站起来,双手交叉在胸前,靠墙站着。一两分钟后,两个身体都恢复平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时恰好一截香灰掉下来。母亲开始向嫂子问话。
3
“嘉茹,”母亲喊着嫂子的名字,“你看到什么了?”
“很黑,”嫂子保持原来的姿势,或许是因为低头压着喉咙,声音听起来仿佛很遥远,有些沙哑,“我什么也没看到。我很害怕。”
“不要怕,我和妹妹都在这里。”母亲习惯叫我妹妹,“你就站在那里别动,仙姑很快就到你身边。”
“有人走过来了。他身上在发光。”
“你靠边站,不要朝他脸上看。”
“他又走了,为什么不能看他?”
“你就当到了一个陌生地方旅游,但不能盯着人的脸看,更不能跟人打招呼。”过后,母亲跟我讲,有个小姑娘在“观花”中跟那个世界的一个人点了头说了句话,就被人带走了,再也没有醒过来。
“仙姑来了。”
“跟着她走。”
“开始有光了,”嫂子似乎走了一段路,说道,“我看到路边一排很老很老的房子,有老人,有小孩,他们都站在门口,看着我。”
“不要说话,紧跟着仙姑走。”
“我很怕,他们看我的眼神好奇怪,啊,他们脸上……他们眼里……”嫂子好像被掐住脖子,想拼命往口腔外送话,可就是出不来,声音被硬生生堵在喉管里。
“我只有跟你们说话才不会感到害怕,仙姑只顾自己走,没回头。”嫂子说。
“那你说,但是不要跟仙姑说话,你们的对话是禁止的。”母亲说。
“我们进入一条热闹的街道,街上看不到一个人影,可我有一种感觉,这是一条十分热闹的街道,我走得很慢,很吃力,我感到人挤人,可是我身边没有一个人,整条街就仙姑跟我,我说不出这是一种什么感觉。沿街的建筑都很古老,但没有一丝残破的迹象,甚至,我感到这些房子好像没建多久。
“仙姑站在一个大门前,大门有一个很高很高,差不多到我膝盖这么高的一个门槛,木头做的,漆着黑漆,两扇厚实的大木门关着,大门的两边各有两个矮小得多的小门,仙姑走了进去,我也跟了进来。一个老太太在跟仙姑说话,声音很小,我一句都听不懂,我只注意到地板发出柔和的光芒,我好像走在云端,轻飘飘的。老太太带我们拐进一个月圆洞门,进了一片花园。
“哇,好大的花园,没有边际,比大草原还广阔,到处是花草,有自然生长的,有各色各样的盆里栽的,有挂着,有吊着,有蔓延着,有水里栽的,有土里长的,什么样的花草都有,有的已经枯萎,有的孤零零开着一朵花,有的很茂盛,满枝满叶都是花朵。仙姑示意我不要乱走乱摸,我当然知道。我们一直在花园里绕圈。
“老太太停下来,指着一丛植物。”
“快快,说说它长的怎么样,开了几朵花。”母亲说。
“没有开花,”嫂子说,“老太太拨开叶子,仙姑指着根部示意我近前看,很多黑油油的小爬虫,像蚂蚁,蚂蚁又不长得这么古怪,在啃噬着,爬满了枝叶,仙姑摇了摇头,又对老太太点点头。我们走出花园,回到大厅,仙姑随着老太太走到一面屏风后,我感觉她们谈的是我,她们出来了。老太太递给我一小杯子东西,我把它喝了,仙姑也喝了一杯。周围一下子又黑漆漆什么都看不见,我好像又回到刚来的地方。”
嫂子说到这里,就像沉入水底的人,声音也渐渐远去。
这时香枝也快燃完了,母亲在八仙桌上敲了三下。嫂子和仙姑的身体又开始一阵战抖,没有先前那么强烈,一会儿,两人同时抬起头来。嫂子一脸迷茫,看看我,又看看母亲,好像很奇怪怎么就睡着了,有些歉意,又有些莫名其妙。
后来母亲告诉我,平常仙姑醒过来,都会帮人解说一番,但嫂子那次,仙姑一回来就躺倒在床上,一定是累坏了。好在嫂子把一切都跟我们说了,母亲平时看多了,也知晓怎么解说,所谓久病成医。但令母亲怎么想也想不通的,她还是头一回听说那里头的老太太会给人东西喝。一个多月后,嫂子有身孕的消息传来,母亲也就认为这一切都是亏得仙姑跟老太太讨得的那杯仙液。
回家的路上,我很好奇嫂子在另一个世界的经历,想再从她记忆里搜刮出一些东西,可嫂子说,她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照仙姑的要求趴在八仙桌上,很快就有一股强烈的睡意袭来,再次醒来,只模模糊糊记得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就是想不起梦里到过哪里,见过什么人。要不是我把母亲和她的问答说给她听,她都怀疑自己只是趴在那里不小心睡着了,她甚至怀疑我和母亲合着跟她开玩笑呢。
当时我就想,这不过是一种小把戏,哥哥更是以为,这是一种在强烈的心理暗示下的催眠术。类似的手法,曾经风靡西方的知识阶层,令很多知识精英深信不疑。我就对哥哥说,凡事要试过才知道,况且,谁也没把它当真,只不过见识见识罢了。
所以当嫂子尖叫着激动地告诉哥哥她终于怀上的时候,哥哥还在给嫂子泼冷水,这样的误会又不是第一次了。隔天他们又测了一遍,哥哥还是不大相信他手中拿着的纸条上的红杠,后来他们赶到医院做了采血检查,才感叹幸福时刻来得太突然。
4
我说嫂子变了一个人,其实从那个通灵夜过后,我就感觉她的不一样。一开始,我还只是觉得嫂子经过一场长时间的通灵法术,身心疲惫是难免的。仙姑在一开始就说过,人从那边回来后会有一阵不适,这要看每个人的身体条件,有的人一醒来就跟没事人一样,有的人过后很长时间还昏沉沉跟丢了魂似的,这都很正常。嫂子就属于后一种。知道自己怀孕后,嫂子辞职在家安心养胎,我更是发现她很多习惯变了。嫂子以前是一个生活很有规律的人,从不熬夜懒床,从老家回来后,就变成夜猫子,有一天半夜,我起夜从厕所出来,客厅黑洞洞的,我走到茶几前准备倒水喝,一抬头看到嫂子披着长发,端坐在沙发上,直愣愣地瞪着我,我吓得把水壶和水杯都丢地下。哥哥听到玻璃摔碎的声音才从卧室里出来,把嫂子带回去。哥哥一边哄一言不发的嫂子睡觉,一边安慰在一旁高声尖叫的我,哥哥跟我解释,嫂子可能有轻度的梦游症,心理压力造成的,可是我跟她同在一个屋底下住这么久,怎么从来没有发现。
对嫂子的怀疑,并不是没有缘由的。那段时间,我从老家打听到不少关于仙姑的事。老家流传着很多关于她的故事。仙姑原名叫周文因,她还有一个姐姐叫周文阁。要说起这对姐妹,还得从她们的父亲周骏国谈起。
周骏国出生那年,父亲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成分,家里的土地房产都被政府没收,父亲的双腿在批斗中更是被打断,后来年纪轻轻就死了,村里就有人说,他周家要不是造了什么孽,怎么会遭这么大的祸,放在古代,这可是抄家灭门的罪,可认识周骏国的父亲的老一辈都说,他父亲和他祖父,在村里都是出了名的大善人,有穷人家挨饿,他们不仅把人带到家里来吃,过后还送人家一筐番薯,有人抓到小动物,就送到他家,他们就会出钱把它买下来,再放生。村里又有人不同意了,做了善事应该有善报才对,可他们周家差点就灭绝了,一定是上辈子造的孽太大,遗留到了这辈子。
周骏国是家里的独子,在我们老家,独子有另一个叫法,单丁,它除了有表示独子的意思,还有另外一种含义,每当人们说谁是单丁的时候,都有一种孤苦伶仃的怜惜意味。周骏国一辈子有两个夙愿,一个是上大学,一个是生很多个儿子。可惜一个都没有完成。因为生逢文革,又是地主家庭出身,他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文革后,恢复高考,他又因为已经成了家,受家庭拖累,没法再参加高考。第一个女儿出生后,他给取的名字叫文革,后来听人说,文革害人不浅,他才改为文阁。第二个女儿,也就是现在的仙姑周文因。周文因出生的第二年,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在村里强力推行,周文因的母亲躲到老家还是被拉到公社强行结扎,这一次,灾难再次光顾周家,周骏国的妻子结扎后受到感染身体一直病殃殃的,在两个女儿还没长到膝盖高的时候,就去世了。村里人说,周骏国读书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但是经营生计,却是个低能儿,所以家里一直很穷,靠远在南洋的华侨寄过来的那点钱过日子。周文因后来考上师范中专,毕业后,回到镇上的初级中学教书。
5
周家从来不缺乏供村里人街谈巷议的谈资,远在1949年前他们家里还有几十亩田地,他们就是村里人羡慕妒忌的对象,土改后,灾难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临周家,他们又成了人们可怜鄙夷的对象,但这些,都还只是关于一个家庭的财富地位的起起落落,和人生寻常遭遇的生老病死,说到底,每个家庭也都会遇上,只不过周家比较集中,结果也比较惨烈而已。人们无论在对周家低头哈腰的时代,还是避之唯恐不及的时期,抑或哀其不幸的时候,都还保存着几分敬意。但这份到了周骏国的第二个女儿周文因出嫁前还残留着一丝一毫的敬意,在周文因结婚后,就不仅荡然无存,相反,还生成了另一种极其负面的评论和看法。
周文因在初级中学教书的第三年,姐姐周文阁病死了,没错,死神再次光顾周家,如果人们在得知周文阁的死讯时,还会感慨死神来得太频繁,那死神很快就会让他们明白,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周家半步。据说,周文阁临死时一直不愿闭上眼睛,直到妹妹答应愿意嫁给她丈夫,共同照顾她唯一的儿子,她才合上双眼。
关于周文因嫁给她姐夫这段典故,村里人口头的传说的丰富多彩是和他们的封闭落后成正比的,在此,我原本无需加入这个无聊的行列,平添一层龌龊。但由于牵涉到我想说的整件事,所以我还是得简单地说一说。有一个版本说,周文阁临死求妹妹嫁夫是周文因编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掩盖自己早已爱上姐夫的事实;还有一个版本,我想是后来眼红周文因当上了仙姑的人编造的谣言,他们说周文因那时候就懂得作法,姐姐的死就是她作的法害死的——造谣的人说到这里,还扯上后来又一次发生在周家的灾祸——周文因嫁给姐夫还不到一年,丈夫和儿子就因车祸双双去世,那是因为周文因发现姐夫,也就是当时的丈夫,有了外遇,她便再一次作法把他们除去。谣言把周文因描绘成了一个歹毒、阴险的巫婆,末了,造谣的人们总喜欢添上一句自相矛盾的话,周文因的通灵术根本不灵,他们从来就不去找她。
谣言,有时候就像大风来临时的海浪,一层叠一层,一层比一层高。到了最后,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坚信,周家受到咀咒,周骏国注定要白头人送黑头人。
不是我爱打听别人的隐私,也不是我喜欢搬弄是非,老实说,我一点都不相信村里人对周骏国的预言,我相信自己理性的判断和有理有据的推测,可我还是不得不说,那一夜,我陪嫂子和母亲走到周家门前,在昏暗中看到周骏国瘦小的身躯,和他一头闪着银白色光芒的白发,我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周文因还在当初中教师的时候,距她的丈夫和孩子已经去世半年多,有一天出席学校礼堂的开工奠基仪式,没有任何前兆突然昏倒不省人事。被送回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出现在学校,也没有出现在村里人眼前。据去过周家的人说,周文因不言不语,就这样躺在床上,整天盯着屋顶的一根横梁。听她父亲说,女儿昏迷过后,什么都看不见了。村里就开始传说她快死了,要步她爷爷、妈妈、和姐姐、姐夫、儿子的后尘了,死神又开始敲周家的门了。一年多后,周文因并没有死去,村里就又传言,周文因在学校的奠基仪式上撞了邪,冲了神灵,精神失常了。又过了一年,一波波中老年妇女就开始往周家的老房子里拥,人们都在说,周文因被某某仙姑附了身,有了法术,能够替人算前世,卜未来,问婚姻,求子息,消灾厄,保平安,很快,从未踏过周家的家门的村里人就把周家围得水泄不通,雨淋不着,都说,周文因法术高明,法力高强,要走火路,睡钉床了。人们似乎都忘记了笼罩在周家几十年的晦气和周文因短命的预言,不再叫周文因为周文因,无论信不信她那一套,提起她的人,都敬称她为仙姑,提起周家,就说仙姑家。俨然,周文因成了神仙,周家成了神仙府邸,人们油然产生一种敬畏,就像他们每次经过村角的某个神庙,进入老寨的某个祠堂,不由自主地理一理衣服,端正一下面容。
人们都在说,仙姑通往世俗世界的双眼被关闭后,通往灵异世界的天眼就被打开了。可我依稀记得,周文因的双眸是那么明亮,闪烁着不同于常人的智慧。
6
事到如今,我也有些糊涂了,分不清嫂子到底是从老家回来后,还是自从怀孕后,开始产生变化。我也听说,女人怀孕后,身体和神经都要经受很大的考验,在怀孕的过程中,精神上有些不同往常,都属于正常范围。所以当我又听说了一个关于周文因的更离奇、诡异,甚至可以说完全是无稽之谈的传闻,禁不住把周文因和嫂子联系到一块时,我有那么一点讨厌自己,我只希望一切都只是我虚妄的联想,就像愚昧的远古人望着滚落在天边一轮黑洞洞的太阳,就臆想有一头恶犬吞食了他们的光明,我有时就是这么控制不了自己的大脑,假如一开始只是我毫无根据的联想,那么现在这个想法已经在我的脑袋里盘根错节,生根发芽了,我再也无法把它从我的头脑里挖走。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我,是一个一方面绝不相信下面我要讲的,另一方面又对之深信不疑的矛盾对立体。人的痛苦,大概就是这么得来的。我见过很多愚蠢、凶恶、丑陋、龌龊、贫穷的人,可他们都活得挺自在,也蛮开心,以前我不懂,现今我明白了,因为他们纯粹。纯粹的人,无论善恶、美丑、贫富,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并不窥视他人,更不会在内心揣着一把标尺,来衡量比较他人和自己。
从我搜罗来的周文因的所有传说,这一个是最具想象力,也是最令我不寒而栗的。传言说,周骏国的大女儿周文阁才是懂得通灵术的人,不止如此,她还会一种换身术。当年周文阁发现丈夫与妹妹的私情后,作了法,让自己和妹妹换了身子,并让自己的肉身很快重疾缠身而死,这样既消灭了情敌,又使自己重获丈夫的欢心。谁知再次嫁给丈夫后,自己的伎俩被丈夫识破后,失去他的爱情,她就又一次作法,害死了自己的丈夫。至于她的儿子的死,传言分为两种,一种认为她连儿子也害死,为的是不给丈夫留后,一种认为,她因为失误,牵连了儿子,这也是为什么她有几年神经兮兮的原因。
也许你们会问我,就因为听说周文阁会换身术,就怀疑自己的嫂子被换了身,先不管这法术首先纯属天方夜谭,再者,她凭什么要换到我嫂子身上。说实话,原先我对我自己产生这个想法,也只是一笑置之,甚至很厌恶自己的脑子里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离谱的怪念头,但当我得知哥哥和周文阁曾有过一段少为人知的感情,我才发现,我的这个怪念头也不完全是无中生有。
哥哥跟周文阁小学同过班,上了镇初中,也很意外地成了同班同学。初中三年,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偶尔擦身而过的时候,也只是互相点点头,在哥哥那个时代,男生女生的隔膜,远比后来的同学关系要远得多。哥哥上高中后,有一天搭公车从市区回家,正好与周文阁坐到一起,或许是因为都来自同一个村子,或许是因为两个人都曾经是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或许是因为两人彼此都有些倾心,两个人就聊了起来。周文阁考上的是市区的一所师范中专,每个周末也要坐同一路公车回家。接下来的每个周末,哥哥都会在同一路公车上碰到她,跟她坐到一起一同回村。那时候远没有现在的学生人手一台手机,他们唯一的交流,不是通过手机短信,也不是通过网络通讯工具,更不可能每天通过电话倾吐衷情,每周一趟回村的公车,就成了他们默认的交流,虽然路上并不谈很多,游离的眼神,浅浅的笑容,淡淡的气息,都构成了他们最美好的青春回忆。后来,母亲不知从谁的嘴里知道这件事,一定要哥哥断绝跟她的来往,并且以后不得跟她家的人接触。像所有媚俗的校园爱情故事一般开始的恋情也像所有媚俗的校园爱情故事一样遇到了阻挠。从此两人只能鸿雁飞书,哥哥考上大学后,周文阁也从中专毕业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天他们没有再通信,再后来,周文阁就嫁人了。
这是我老家的邻居告诉我的,我估摸着其中有很多猜测的成分,于是就一直在寻找机会撬开哥哥的嘴。
7
哥哥一向都很疼爱我这个妹妹,跟嫂子成家后,他也没有把我撇到一边,每次带嫂子出去游玩,从来没有落下我,送嫂子礼物,也不会少我一份。从来我有求于他的事,他都会答应下来。所以我经常想,我未来的老公就要像哥哥这样。
那天晚上,嫂子吃完饭在楼下散步回来,感觉很疲惫,早早就睡着了。哥哥终于答应我讲一讲他跟周文阁的往事。前提是我要保证绝口不在嫂子面前提起。
哥哥说,九十年代中后期,也就是他读初中那会,校园里流行写信,交笔友,学生们翻阅一些青少年杂志,从上面的笔友交友专栏抄写下来姓名地址,过后偷偷写信给对方。当然笔友的来源不仅仅是通过杂志,也有通过电台,报纸,书刊,或者通过朋友同学的介绍。相对于这些向远方寻找友谊的行为,在同校同班里寻找朋友的就少得多,写信的目的也不再那么单纯,常常是物色了某个长相秀丽皮肤白皙的女同学,私底下叫认识对方的人转交给她。那时候哥哥跟周文阁同一个班级,学校里很多男生往周文阁周文因那里写信,哥哥也没能免俗。不过哥哥大概知道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古训,只是偷偷把写给周文因的信塞在周文阁的书包里,让周文阁充当邮差。哥哥说,他给周文因写了三封信,才收到她的回信,回信并不是通过周文阁转递,而是通过正常的渠道寄到,被留在学校的传达室。后来,信写得越来越多,回信也开始多起来,有一次,他碰到周文因,因为信里头写得很熟悉的关系,哥哥就上前跟她说话。谁知道周文因说她根本不认识他,并且跟哥哥说,如果他想要写信给她,可以写到她班里,她也挺喜欢写的。哥哥后来才想明白,原来一直给他回信的,是周文阁。就这样,哥哥继续保持跟周文阁写信,同时也直接写信寄到周文因班里。有必要澄清一点是,哥哥并不认为那就是情书,相反,他觉得,那只不过是好奇寂寞的青春期的自然而然的表露,所以,当年,他们的信件之间,谈论的都是一些烦恼和琐事,更多的是填充字里行间的思想的贫乏和空洞。
初中毕业后,哥哥上高中继续读书,周文阁本来考取了一所中专,听说为了妹妹周文因第二年能够读上师范,周文阁放弃了中专,外出打工。后来人们看到哥哥同坐一车回村的,其实是周文因。周文阁打工供妹妹周文因读师范,还鼓励她跟哥哥交往,在她眼里,只有妹妹能够配得上哥哥,因为哥哥是要读大学的人。哥哥顺利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后,期间还保持与她们的书信来往。这时他们的通信已经不再是空泛的青春期忧愁和对未来幼稚的幻想,特别是周文阁,信里给哥哥写了很多她在工厂遇到的人和事,相对于妹妹周文因毕业后又回到学校教书,姐姐周文阁过早踏进社会,承受更多的磨难和痛苦。事情并没有像外人所想,哥哥与她们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朋友的倾诉。这种倾诉,很好地缓解了哥哥踏入大学校园的迷惘和无知,要知道,太多的人一考进大学就自以为从此人生路途坦荡无忧,他们缺乏像哥哥这样,有一个开向外界的窗口。哥哥并不是毫无情感触觉的人,他也在心里滋生过,想对她们表达自己的爱情,可是哥哥正如周文阁的敏感心理所感觉到的,他在两者之间犹豫不定。在哥哥的眼里,姐姐周文阁善解人意,妹妹周文因聪慧乖巧,不知道是由于自己的社会经验的匮乏,还是出于对周文阁的同情,他有点偏向于周文阁。大学第二年下学期,事先没有得到提示,哥哥从周文因的信里得知周文阁嫁了人,也不再给他回信,他才知道,周文阁再次为了理想中的妹妹的幸福做出牺牲。“牺牲,”周文因在信里写道,周文因理解的姐姐的牺牲完全是另一回事,“牺牲,姐姐为了我们这个家,为了爸爸,为了我,又一次做出了牺牲。按照老家的传统,没有男丁的家庭,必须有一个女儿招个丈夫,使他入赘,以继承家族的香火。我曾要姐姐答应,既然她打工供我读师范成了一名教师,招赘的事就应该轮到我。可她还是……”周文阁结婚后,哥哥并没有如她所愿,与她妹妹周文因成为男女朋友,相反,哥哥因为周文阁的断然离去,心中有了抹不掉的一段伤痕,与周文因的联系也渐渐淡了下来。周文阁的死,和周文因嫁给姐夫,这段被村里好事人翻来覆去成了传奇,哥哥还是通过别人听说的。周文因的精神失常,和随后成了村里的仙姑,都完全出乎哥哥的想象,在哥哥的印象中,周文因是一个很知性、现代的女子,这表现在她选学的是英语,她曾经在某封信里写道,“英语,是一种语言,也是一种通往外面世界的工具,我不想一辈子留在这个小地方,跟一群祖祖辈辈蹲守在农田里不知汉魏晋的农民一起生活,这里缺乏生活的热情,没有人生的变化,不见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和理解,他们的思想和几百年前至此创基的第一代祖宗没什么差别,除了身上穿的,家里用的,他们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周文因还在信里跟哥哥提到,她在这所乡下学校教书,简直无法呼吸,学生是多么野蛮愚蠢,老师又都是粗鄙无聊,她要继续自学本科考试,到省城大城市里去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心性高傲,对老家多有排斥反感,向往大都市的年轻女教师,会成为千百年来在中国乡下随处可见,代表着极端原始、迷信落后的仙姑,无论谁也无法想象。哥哥摇着头,大声的叹气,结束了谈话。
今天,我决定在嫂子身上试一试,我趁嫂子埋头坐在沙发上,抚摸着隆起的肚子,在安慰着肚子里的小宝宝,突然在她耳后轻声地喊了一句:周文阁。嫂子的手停下来,一边耳朵轻轻抖动了一下。周文因,我更低声喊着。嫂子立马回过头来,脸上刷白,瞬间又变得发青。我就是想让嫂子知道,她知道的,我也知道。
责任编辑/乙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