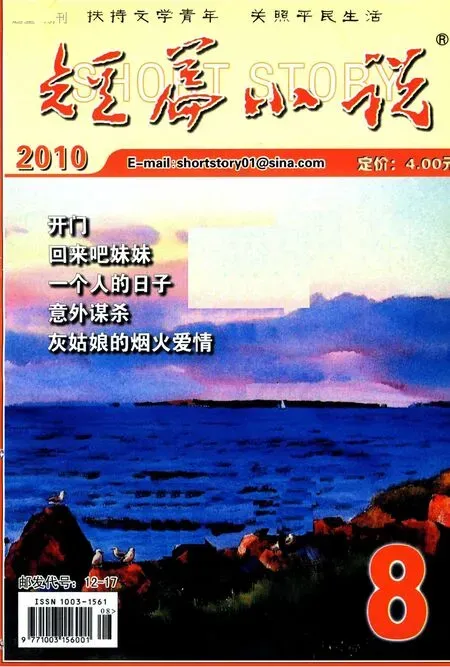拉魂腔
◎荣艳丽
拉魂腔
◎荣艳丽
荣艳丽,女,生于1970年,2012年秋开始业余创作,作品散见报刊杂志,现为江苏省宿迁市作家协会会员。

1
树英踹狗一脚,道:“起来吃。”
狗呜咽一声,跳起来,却挣不脱脖颈上的绳索,只转个小圈,又夹着尾巴,低眉顺眼地蹲着。
“还不吃是吧?最好赶紧饿死,好跟着她去!”树英端起食盆,走出锅屋。
“跟一只狗较什么劲呢?”老穆在院子里接过食盆。
听见老穆的声音,狗站起来张望,尾巴圈浪圈浪地摇,两条前腿先是频繁地原地踏步,接着是轻微的跳跃,老穆走近,它跳得更欢,几乎要扑到老穆怀里。
老穆放下食盆,随手捡根柴棒敲敲盆边,狗就叭嗒叭嗒吃起来,尾巴仍圈浪圈浪地摇。树英从门外瞧着门里的狗,咒骂道:“绝狗!我下毒在盆里了,还敢吃呢。”
老穆的前妻下葬未满一年,树英就从邻村嫁过来。之前算命先生对老穆说过,一年内不娶,就得等到三年后。既然反正是要娶的,又何必要等到三年后!老穆摆一桌酒席,一一邀请前妻娘家那边的亲戚,来与不来的,算是征得了他们的同意。
“买袋盐来!”来的是邻家女人。
树英迎出去,咕哝着“绝狗,到现在我喂食还不吃”。
两层的楼房,紧贴穿过村子的马路,一楼两间开了商店,树英和老穆的起居在另一间和后院。老穆的儿子立祥、女儿立梅都在城里教书,楼上就空着。
“可怜,狗通人性呢!”邻家女人拿了盐,忍不住要到锅屋里看一看狗,还叹了口气。
树英心里烦这女人了,可又不好说什么,只得蒙了冤似的,为自己申辩:“我也是没法子,才走这一步。我儿子十岁那年他爸死的,二十年,我都守过来了。但凡这个儿子还能指得上,我也不走这一步,哎——只说在外头打工,哪晓得他什么时候开始跟人家去赌钱的。连个媳妇还没找,竟坐牢去了。小闺女倒是最听我话的,嫁了个好人家,日子过得好样的。可是哪有靠闺女的道理……”
“立祥他大舅家得个孙子,你不去热闹一下?”邻家女人岔了话题,她太知道树英往下要说什么。无非是她的前夫是怎么出了车祸死的;孩子小的时候,她生病了怎么没人照顾;平时怎么受邻里的冷眼、妯娌们的孤立;怎么没白天没黑夜的劳作,辛苦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儿子怎么因盗窃罪入狱;小女儿的孩子怎么乖巧聪明,她的公公婆婆是怎样的和气,女婿兄弟姐妹几个,各自干着什么营生;自己是在怎样灰心的时候,媒人给她介绍了老穆……这些,村里几乎所有人都能倒背出来。
“怎么能不去?我也是小娃的一房姑奶奶呢!”树英大声说,要把邻家女人的目光从锅屋拉回来,“老穆说,去了,以后跟那边的亲戚们才好相处。”
老穆从上衣内兜掏出一叠大大小小的钞票,抽一张一百的给树英:“我在家看店,你赶集买点五花肉和鲜鱼。明天元旦,立祥、立梅回来,立祥爱吃红烧肉,立梅爱吃糖醋鱼。”
邻家女人往外走:“他穆叔对你真是没得说。他穆叔先前在公社食堂,这会子有养老金。光这养老金,你俩就吃穿不愁,小店和地里的收入全归你攒着。家里这样的宽敞体统,立祥又在城里买了房子,立梅是女娃,到时一份不拘多少的嫁妆罢了,虽说都还没成家,却也不沾你不靠你的。哪找这样满意的去?”
树英说:“什么满不满意的,也就瞎乎眼地过呗!连自家儿子都指望不上,难道我老来还指望立祥?老穆比我大十岁还多,万一走我前头去,立祥赶不赶我走还难说呢!”
从集镇回来,在村庄里穿行,树英跟遇见的每个人打招呼。就有那没心没肺的女人,当作一件大事似的问她:“听说你家那狗,不吃你喂的东西?你都来了快半年,这什么蹊跷狗,还这么能认生!”
树英没觉得人家问得有什么不妥,便停下来,也当作一件大事似的回答,然后蒙了冤似地说:“我也是没法子,才走这一步……”
你过的是老穆的日子。只要老穆对你好,什么都不成问题。这是树英嫁过来之前,媒人说的。
是啊,终归过的是老穆的日子,一只狗,还能翻了天去?
2
红烧肉和糖醋鱼,冒着索然无味的热汽。
立祥和立梅没有回来,电话也没打回来一个。
老穆忍不住给立祥和立梅各打一个电话,说着说着,他就抱怨起来:“国庆节就没回来,当时电话里不是说好了元旦是回来的吗?是不是就因为现在家里多了你姨?就因为她不是亲妈?”
老穆撂下筷子,到院子里摆弄二胡,那里有一大片阳光。他深深地看进虚空里去,那眼神,是孩童在仰望母亲。仿佛眼前有一个隐形的指挥者引领着他,怕错一错眼珠,就会搞错音符。
他的哀怨,在琴弦上流淌成一曲拉魂腔。拉魂腔是此地的小调,曲子以悲为主。老穆有什么心思了就喜欢拉上一阵子。
树英看着老穆没吃的大米饭,说:“这么好的菜,就不吃了,傻吗?我可不管那些,我都吃完。”
终究,树英没有吃完,她拨一些红烧肉到狗盆里。
狗臀部着地,前腿站立,侧身倚在灶前,头微微低着,始终不抬眼看一下树英,更不伸嘴嗅一下刚摆在面前的食盆。
“这绝狗,要翻天啦!前世跟我有仇啊?”树英把食盆丢在老穆脚边说。
“一只狗值什么说的,只要你舒心,我明天就摆布了它。”
树英对这桩婚姻是满意的。除了是邻家女人所说,她更畅怀的,是有了丈夫,有了完整的家,使她再不用承受作为寡妇的那些委屈;是这桩婚姻,把一个正常女人原本应有的体面还给了她,她甚至有点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扬眉吐气。
树英想要尽快和这个家庭融为一体,就像她原本就是这个家里不可或缺的女主人一样;她要让所有人看见她在这个家里,就像看见云彩待在天上、冻流流挂在屋檐上那样自然。
她要做这个家里的女主人该做的一切。
立祥和立梅还是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到了大舅家,来喝表兄得子十二天的喜酒。他们的另外两个舅舅和三个姨娘,都合家带口地聚在西屋,唯独少了他们的母亲。兄妹俩躲到没人处掉了一会眼泪,强撑笑脸仍到西屋。见兄妹俩红着眼睛,姨娘们也都红了眼睛,又不能掉下泪来,毕竟这是兄弟家的喜庆事,遂也都强撑笑脸,找些跟新生儿有关的笑话来说。
来送礼的近房本家,都分散在另外的屋子里,或者三三两两站在院子里、院子外,等待入席。
树英来的时候,跟在老穆身后,经过每一圈人群,总有人问:“这是谁啊?”
“小娃他姑奶奶啊!”老穆搂一下树英的肩,那意思是说你们还不知道这是我新找的伴?他想人家听了这样的介绍,至少会惊奇一下子,可是没有人惊奇,都是“哦”一声,便错开了目光。
小娃他姑奶奶,这是哪门子的姑奶奶?这不是指着棒面疙瘩硬说是水晶汤圆吗?还那样亲昵!对于老穆前妻的娘家人,这简直是一种明目张胆的奚落,但是又都像哑巴吞了黄莲似的,有苦难言,只暗暗幻想一下已经过世的那位姑奶奶的面容与身量。等老穆与树英走过去,对着两个后背,才小声嘀咕起来。
“不及姑奶奶一丁点儿!”
“差得不知远哪儿去了!”
最后,老穆和树英进了西屋,众人起身客套,落座。
这时不知谁在院子里支起一桌牌局,大概因为新生儿的外婆还没到,开席还早。
男人们朝牌局聚拢,老穆也撇下树英。
西屋里的那些眼神开始游移,不知该看哪个方向。所有人都尽力避免与树英的眼神交叉。没有人意识到,还是像刚才一样继续聊点什么也许更合适。
如果西屋原本是二胡上的一曲拉魂腔,那树英就是弹奏者突然痉挛的一根手指,让音乐戛然而止了。树英也成了人们不小心喝进嘴里的一口太烫的水,一时吞吐两难。
院子里,扑克牌摔得叭叭响,围观的喊得倒比打牌的起劲。
“他们喊什么哟!我瞧瞧去!”
离门口最近的姨娘总算找到借口逃离,她也立刻成了领袖,其他人像得了赦令似的,都说:“我也瞧瞧去。”
屋里剩下树英、立梅、一个年纪最轻的姨娘以及她六岁的儿子。
树英抓着立梅的手,像对自己的女儿。
“和你哥一起来的?”
“是。”立梅缩回手,看小姨娘一眼。
“怎么不先回家一趟呢?元旦放假也不回来。”
“哦,元旦我们参加万人长跑去了。”
小姨娘趁机与树英搭话:“你孩子也不小了吧?”其他姐妹不在场,背叛故去姐姐的内疚,也不必了。
“是啊,大的三十了,小的二十八。哎——我也是没法子,才走这一步……”
牌局那里偶尔安静下来的时候,树英的声音隐约传到牌局的外围,从西屋里出去的人,又陆续回屋,偶尔经过西屋门口的,伸头张望一下,也不声不响地靠在门边看着树英。
树英的讲述,换来一时没有隔阂的和睦,她的生疏与不安,正在消失。
忽然院子外面响起惊天的鞭炮声,立梅的小姨娘追到院子里,也没扯住儿子后襟,那孩子第一个冲出去。
新生儿的外婆率一干女眷送礼来了,立梅的表兄、舅舅和舅母忙迎出院外厮见,把人往屋里让。
女眷们伴着刚来的亲戚到产妇房里又看一回新生儿,不过仍称赞说笑一回,便都步行往镇上的酒店去坐席。
树英不得又被询问一回,被介绍一回。当别人知晓了她的身份,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只好奇而复杂地看着她,她说:“我也是没法子,才走这一步……”
立梅和她的姨娘、表姊妹们走在一起,她们已经不用紧跟着去听树英讲些什么,便与她拉开一段距离,低声说些零零落落的体己话。
“按理说,立梅爸爸有个伴,终归也不是坏事情。可这位看着似乎不大像个安淡人,不然改什么嫁!”
“就是,怎么那样能说!全是说她自己那点事!”
“看她,那样胖!还用走路么,睡地上滚倒省劲!”
“她那儿子,说是两年过后就出来了,看吧,到时找对象、结婚,麻烦多得很,还不知怎么个说法哩,麻烦多得很!”
……
当树英的身世连一个六岁的孩子都知晓,便再没有人愿意听她的唠叨。她与人搭话,收获到的也只有寥寥几句万不得已又最简短不过的客套,她仍然是那突然痉挛的手指,那口太烫、吞吐两难的水。
3
树英把带回的红蛋扔在桌上。
“她那些兄弟、姊妹,当初不是都没反对吗?记得还说拿我当一门好亲戚!可今天,他们对我怎么像对仇人似的?还有立祥、立梅,这次回来,连家都不来一趟!倒跟那些人亲近得很!你再瞧瞧,他大舅家有多小气,得了大孙子,才给十一颗红蛋,现如今,哪家得个男孩,不是给十九颗?”
“我心里有数哩!她的那些兄弟、姊妹,就没一个懂礼数的!你都来了这么些天吧,竟没人喊去家里吃顿饭的。虚让一句的,都没有!说句气话,以后我们就不跟他们来往了,省得憋气!立祥立梅跟他们走得再近,终归还是我的儿子、我的闺女!”
“不来往也不好,大面子还要顾一些。”树英又转过来安慰老穆。

下过一场雪,就快过年了。
树英赶集勤快起来。
集上的人,比平日里多出好几倍。家家户户办年货,街筒子像要被人挤歪了,撑破了。
有些从来不做生意的人,不知从哪弄来一堆孩子的玩具,或是年画什么的,也摆起摊子来。街道的尽头,像是长出一截长长的尾巴,延伸出去。
葵花子、花生、大糕,要买。
苹果、桔子,要买,平平安安,吉祥如意。
猪肉要买,除了做扣肉,还要炸肉丸子哩!
豆腐要买,都富啊。
大年初一早上要包韭菜馅的饺子,一年到头,长长久久!韭菜得到大年三十买,那样才新鲜。
包汤圆的糯米面、芝麻粉要买。
鱼要多买几条,大年三十炖一条;再炖两条,好大年初一压锅;留两条活的养在水里,连年有余。
锅碗瓢勺,桌椅板凳,该添的,也添置些吧。
一年到头的,总要像个样子,齐整圆满,人也舒坦。
过年,是大事!哪怕最节俭持家的主妇,也要给孩子添置一件新衣裳,也会多多少少买一些额外的东西,这些东西,平时恐怕连看一眼也觉得罪过,而这会儿子买了,眼都不眨一下。
比如买了葵花子,见还有西瓜子、南瓜子、开心果、核桃仁、葡萄干,也都买一些吧!
比如买了红对联、红挂廊,见还有大大小小的中国结、各种图案的年画、以假乱真的塑料花,也都买一些吧!
立祥和立梅是一定回来的。老穆已经给他们打好几次电话了。树英早早计划着,要做八大碗。这是她到穆家头一回过年啊!
年三十,家家早饭吃过,开始杀鸡撕毛,剖鱼刮鳞,准备这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顿晌午饭。
立祥立梅回来的时候,树英正在煎炸煮炒,老穆接下大大小小的包,冲后院的锅屋努努嘴道:“快去打声招呼,看有什么忙要帮,客气一下,也是不一样的。”
“我大,你也容我们喘口气!”立祥说。
“都是有知识的人,这点礼数也不懂。你考虑一下,人家心里会怎么想。”老穆的脸涨红着,他一不高兴,脸就涨红。
“哥——”立梅扯一下立祥的衣袖,两人穿过商店的后门。
菜蔬与热油惊爆着,锅铲与铁锅争吵着,这是多么熟悉的声音啊!恍惚间,兄妹俩以为锅屋里忙碌着的,仍旧是他们的母亲,不禁心头一热。然而,进入他们视线的,却是一个完全不相干的身影,瞬间,便如失了江山的帝王般颓丧起来。
没等兄妹开口,树英道:“回来啦!前头玩去吧,这里用不着你们。”
“我们帮你吧!”立梅说。
“不用不用。如今都是煤气灶,又不是以前的烧草锅,还要人专门烧火。都前头玩去吧!”
“姨,你辛苦。”立祥本要离开,又转回身来,“哎?大花呢?”
“就是啊,大花哪去了,我说怎没见跑出去迎我们!以前都跑到村头去迎接的。”
前头店里又来了邻家女人:“立祥立梅回来了?我来买刀火纸。”(火纸,方言,用来祭拜死人。)
兄妹俩喊着婶子,又到前面的店里,邻家女人买好火纸,他们送她到门口。
“满庄子就数你兄妹有出息,常来家看看你大。”女人瞬间泪水盈眶,不由抹了一把,“哎——多好一条狗啊!从来不吃她喂的食,都瘦干巴了,让她卖给后村的老刀了。”邻家女人并不知道,狗是老穆作主卖的。
八大碗摆上桌,树英解了围裙去前头喊老穆吃饭。
立祥把母亲的遗像摆在饭桌后面靠墙的几案上,又招呼立梅把饭桌抬到几案前。
“这是要烧纸啊?”老穆说。
“哪家大年三十不祭拜亡人?是哪个把我妈遗像收到楼上的储物间的?”立祥说。
“我大,往年大年三十,你都带我们先烧纸磕头,过后才许吃饭的啊!”立梅说。
树英悄悄退到店里。
老穆跪在当门,把火纸分成三堆焚起,念叨着,一堆给老祖宗和立祥的太爷太奶,一堆给立祥的祖爷祖奶,一堆给立祥刚去的妈,在那世好好享福,保佑这世一家平安。
三人轮流着,每人磕下四个贴地响头。
“立梅,去喊她来磕头。”立祥说。
“她信耶稣,信神哩!不来这一套的。”老穆说。
“哥,算了吧!”
老穆拿筷子搛点菜,撂在纸灰上,再撒上两杯酒,扫尽纸灰。
“立祥,来把桌子抬开。立梅,喊你姨来吃饭。”
饭桌抬开,老穆在遗像正前方站一会,然后双手向遗像伸去。
“我大,一年到头吃顿团圆饭,你就不能让我妈在这儿看着?”立祥说。
“我是担心——”老穆的手僵住。
树英已经跨进门来。
“没什么好担心的,孩子叫你放着,你就放着吧。我没那么小心眼。”
“开一瓶我带回来的红酒吧!”立梅又跑到前头。
老穆说:“家里开着店,你还带什么红酒!”
“我这个好,一瓶三百多块呢!”
“我的亲妈呀,这要多少斤粮食才换一瓶酒。孩子啊,下回可不要花这些瞎钱。三百多块,喝了也不能多长一块肉。”树英说。
晌饭过后,有些人家的主妇开始炒花生、炒瓜子、炸面果子,男人带着孩子们贴对联挂年画。
树英买的花生瓜子都是熟的,面果子也是炸好的,便勾兑面粉熬了半碗浆糊,又把红对联、红挂廊、中国结和年画拿出来。
“我妈才走,怎么能贴这个!三年不能贴红,不能放鞭!”立祥说。
“确实不能贴!”老穆说。
树英僵一会,红着脸把东西收起:“坑哩!我竟把这事忘了。坑哩!我怎能把这事忘了呢!”
“这事也能忘了!”立祥咕哝着上楼去。
老穆叫树英关了店门,说一年到头的,神鬼还放三天假哩!他自己则出门找牌局去了。
立梅推出自行车要去找同学。
立祥母亲在黑相框中面带微笑,看着树英收拾半碗浆糊。
树英洗了碗,快步走到前头店里,封住后门。
4
树英听见立祥下楼,又上楼去了,她就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出来后怎么个弄法,真是愁死人。嘴上说是不指望了,可是心里哪一时又能放得下!出来后最好是赶紧找个媳妇,管着他。可找了媳妇,在哪儿给他张罗婚事呢?那边家里倒有三间土墙瓦盖的房子,还是二十年前,前夫在的时候造的。那样的房子,谁会愿意嫁过去哦!如今,再不济的人家,也是砖石到顶的瓦房了。那么,在“这个家”里张罗自己儿子的婚事,老穆会同意吗?老穆一定会同意,他对她总是千随百顺的。楼上的三间屋平时都空着哩!不要说给自己儿子张罗一下婚事,就是在这儿把日子过下去,也没什么!
晚饭后,立祥说要考研,上楼看书去了。他不想与树英一起看春晚,与一个不相干的人同欢共笑,实在别扭。
立梅只看了一个节目,说困了,也要上楼。
树英递给她两条大糕。
“给一条放你哥屋,对他说,搁在枕边,明早一醒来就吃一点,这是开口糕,一定要吃;放几粒黄豆在鞋窝里,记得把鞋翻过来放;这是两千块钱,跟你哥一人一千,压岁的!”
邻家院子里正燃放一颗冲天炮,立梅被吓到了。
“哦,压岁钱不要的,都是大人了。我跟我哥本该给钱孝敬你呢!”
“拿着!你兄妹都没成家,就是孩子,是孩子就要拿岁钱。我也不算老,还能挣钱,暂且也不缺钱,不用你们孝敬。再说你哥月月还房贷,不容易。你的钱细细攒着做嫁妆。”
一个执意要给,一个执意不要,似乎要打起来,倒像是为了夺钱。
似乎过年终究也没什么意思,自家人吃吃喝喝,初二开始再串亲访友,互相帮着吃吃没用完的剩菜。
初二,太阳似披着金纱的少女,羞涩地露出脸来,树英给自己的闺女打电话:“一家三口都来吃晌饭。”
老穆也大声说:“都来啊,都来!你立祥兄弟,立梅妹妹都在家哩,热闹!”
立祥恰巧从院子角落的厕所里出来,隔着父亲的窗户说:“我大,我今天要去参加高中同学聚会,年前就说好的。”
立梅刚下楼梯,冲着父亲的房门喊道:“我大,我今天是初中同学聚会,也是年前就说好的。”
兄妹俩洗漱完毕,果真就一前一后地走了,树英弄好的早饭,也不吃口。
“都识文断字的,好歹顾个面子大家好看。他们倒好,听说我闺女要来,拔腿就躲!不是亲生的,到底不一样。”
“你家闺女不是说了不来吗?不来就不来呗,难道我也像你这样伤心生气?”
“她不来,那是不好意思,妈妈改嫁,什么有脸的事!”树英叹息着,“你比我大十岁还多,说句话你莫生气,万一哪天你走在我前头,难道我还再改嫁去?指望不上他们倒罢,瞧着现在的苗头,到时可不就要赶我走了?咱们又没领个证。”
“那就领个证呗!”
“领个证又怎么样,那时他们执意要赶我走,我能有什么法子。”
“那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证是要领。但是你得叫他们写个凭据,保证我到死都能够住在这里,要不然,你说我去哪儿?”树英抽泣起来。
“写,写,等天暖和就去领证,就写!”
5
树英关了店门,刚到邻家对过,又自言自语地往回走。
“你说这天,昨天风还呼呼刮,冻人要命的,今天陡的一下就这样暖和,棉袄竟穿不住了。”
邻家女人闻声出来。
“你那棉袄怕是租来的吧,明天都清明节了。清明还穿棉袄,耳朵要聋的哟,呵呵呵……”
“二八月,乱穿衣嘛!”
“怎么把店门关了?”
“刚才立梅来电话说跟他哥快到镇上,老穆接去了。他们一同去上坟烧纸,等会来家吃饭,家里什么也没有,我换件衣服买点菜去。”
“兄妹俩一来家,你就好吃好喝地操心,真是没得理挑。”
树英叹气道:“哎,有什么用?不是亲生的。”
“那边——你不去烧纸?”
“嗨,要去闺女去吧!二十年,我年年去,他也该知足了!早早就把我撂下,是他对不起我……”
镇集上,祭品摆得花花绿绿,人围得喧喧嚷嚷。
“其实你们倒不必去。”
树英回头,见老穆一边在祭品摊上挑选冥币,一边跟人说话。旁边是立祥、立梅,还有他们的姨娘和舅舅们,她赶紧蹲下,在一堆青椒旁细细挑选,背对着他们。
“看你说的什么话!立祥妈是我们亲姊妹,还什么必不必的。我们昨晚就跟立梅他们说好今天一起的。”顶小的姨娘说,“其实树英也该去烧个纸,按古礼,她来家头一天,就该去给我姐行礼,要三叩九拜呢!”
“还行礼,这才来几天,就打房子的主意了,还要我们写个凭据给她。这是安的什么心啊?”立祥说。
“哦!竟有这事!能安什么心,明目张胆地要霸占房产嘛!立祥妈苦一辈子,挣下这点家当,孩子也是个念想。他姑爷,你可要心里有数啊!”立祥大舅说。
老穆涨红着脸说:“写凭据,也就一说,没当真。只是说她儿子将来出来如果找下媳妇,想在这边办个婚事,婚事一办完,就出去打工,有媳妇看着,她就放心了。”
“我大,她的儿子凭什么在我们家办婚事?”立祥说。
立梅也说:“我大,她的儿子在我们家结婚,就是出去打工,我们家也成了他们家啊!”
老穆的脸更红了,连眼睛也红了:“你们两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人家哪里对不起你们?过年还给你们压岁钱,一人一千块!你见过哪家给压岁钱有这么多!二百块都了不得啦!”
“那还不都是我们家的钱嘛!”立梅说。
小姨娘挑了一些冥币、冥衣装进黑方便袋,见大哥正在付钱,客气道,“他大舅,我替你给钱。”
“这都是各人的心意,怎么能叫你给钱,各给各的,各人心意。总之,他姑爷,孩子们说得不是没有道理,你做事情,都要考虑好啊!”
一帮人买好东西,要走。
树英本想悄悄尾上,听听他们还要说出什么,可转念一想又没有必要,有老穆袒护着她,旁人再说什么也没有用。
她把一袋青椒递给摊主过秤,却听见身后的老穆说:“哎!怕什么偏偏有什么,我为什么一直没跟她去领证?就是担心这是个玍古事,瞧瞧,果真就是个罗嗦事。立祥,我还有多少年活头?你也快三十了,你是不打算让我看见孙子了吧?难道我不为自己儿孙,还为人家的去?立梅也二十七了,还是不急不躁的。你说我活个什么劲?”
摊主说了三次“一斤四两,四块二”,树英一句也没听到。
6
红烧肉和糖醋鱼仍冒着热汽,立祥和立梅没有回来,老穆也没有回来。
老穆一身酒气回来时,树英正在整理货架。
“晌饭到哪家吃的?也不说一声。”树英说,“俩孩子不回来吃饭,连一句话也没有。我一大早就关店去买菜,哪晓得弄了一桌子菜,一个都不回来吃。”
“一进门,就听你屁呱呱的。不就上亲戚家吃顿饭吗?立祥他妈在世,也没这样管过我!”
老穆进后院去,树英再一次愣住,老穆头一回这样对她。
货架理到一半,该弄晚饭了。树英想喊老穆到前头看店,可是老穆不见了,锅屋、茅厕、睡觉的屋,都没有。树英没法,只得一边听着店里的动静一边洗一把青菜,老穆酒后总要喝口菜汤。
青菜正要入锅,树英听见鼾声,而且在楼上。这老穆,喝多了酒怎么跑到楼上去睡觉!她撂下青菜上了楼梯,隔着窗户,老穆坐在地板上,两腿伸直靠着一个旧纸箱,抱着前妻的遗像睡着了,口水从嘴角挂到衣襟。
一时,恐慌似洪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漫过来,树英努力想抓住点什么,却什么都消失了。她又像一个在深夜里迷失了方向的赶路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伸手不见五指。她感觉冷,想哭,却哭不出来。
行尸走肉般回到锅屋,锅里的水已经烧干,葱花与姜屑成炭色粘在锅底,锅底眼看就要红透。
关掉煤气,洗锅。
冷水倒进热锅,爆炸似的,也惊不走树英眼前老穆的影子。坐在地板上睡着的老穆,抱着前妻遗像的老穆,没良心的老穆……坐在地板上睡着,坐在地板上睡着,天哪,这要着凉的。
树英奔到楼梯口,却又停住,老穆怀里抱着前妻的遗像,那遗像,让她发憷。
她奔到前头,用座机连续拨打老穆的手机,再到楼梯口张望,这样重复了几次,都毫无动静。她最终决定豁出去,干脆送床被子上去,闭着眼睛,不看那黑镜框,把被子往他身上一丢大吉。
抱起被子时,老穆下楼来了。树英丢下被子再去洗锅。
“汤里打鸡蛋花,还是鸡蛋鳖?”
“鸡蛋花吧!”
吃饭时,树英瞄一眼老穆,说:“在哪里喝恁些酒?”
“他大舅家不是近吗?我们又必经他家,回来时他大舅母再三让,大家都去,我一人不去,不好。我看这点事,你要估成病了!”
树英心里敞亮起来,一股委屈从喉咙哽到鼻腔,叫她流泪。
“你怎么了?”老穆问。
“噎住了。”
锅屋和前头店里的灯亮交汇处,老穆搬把椅子摆弄二胡,又演奏起拉魂腔,他凝神看进虚空的深处去。
树英收拾着碗筷,嘀咕道:“没事就拉,有什么意思……”
责任编辑/乙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