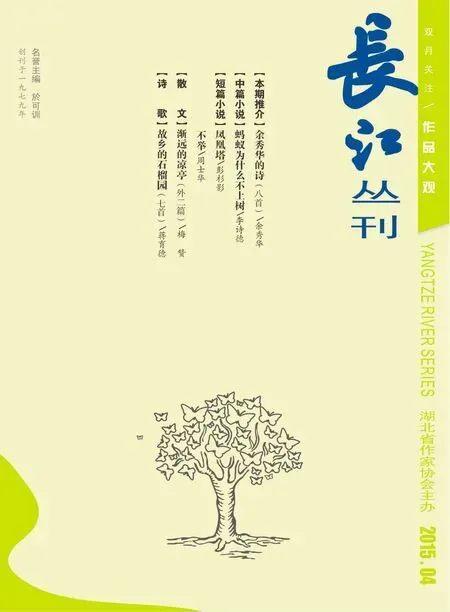渐远的凉亭(外二篇)
梅 赞
渐远的凉亭(外二篇)
梅 赞

梅赞,男,1963年12月生,湖北汉阳人。现在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工作。
1980年代开始写作,作品散见于《长江文艺》、《芒种》、《散文诗》、《家庭》、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武汉晚报、楚天都市报、现代人报、金融时报等报刊杂志。
出版有诗集《为你而歌》、《黎明的雨点》和散文集《远去的凉亭》。
小时候,我们一家蛰居在鄂南山村,几乎与世隔绝,离家最近的小镇也有几十里地,而且没有大道可走,一色的羊肠小径。去一次小镇,得花上大半天时间。记忆中,除了路特别远外,就是山顶上那通向外面世界的凉亭了。
在我看来,凉亭就像古时的驿站,只不过驿站是官方为信使补充给养而建的,而凉亭则是给过往客人歇脚乘凉之用。凉亭大都建在山顶风口,虽然简陋,但也讲究,虽是一间简单普通的亭子,但翘起的屋檐却临空欲飞,颇得中华民族传统建筑之精髓,尤其是风口的朝向,该南北向时,决不东西向,总是迎着风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给人纳凉之用。
我初到凉亭时,是一个炎热的夏天。自从父亲被打成“黑帮分子”遣送至江北老家后,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就被赶到这鄂南山村,于是,我们就很少再走出这山村。那年夏天,母亲到区里参加一个学习班,只有我和姐姐在家。放暑假了,自然我们是没有伙伴玩的,俩人闷得发慌,闲得无聊,便决定去小镇散散心。背上行囊,一副雄赳赳的样子,出了家门。
在山路上行进,我们像飞出笼中的小鸟,又是蹦,又是跳,简直就像跳跃在山路上的音符。可好景不长,随着太阳的升高,我们的体力急速下降,以至在山路上每行进一步,都要大口大口地喘气。尤其是我,又累又渴,喉管直冒烟。一屁股坐在地上,赖着不走了。姐姐哄着我说:“起来吧,不远了,前面有一处凉亭,我们到那里歇歇脚。”真的?我从地上爬了起来,望梅止渴,一下子来了劲。约莫又走了一袋烟工夫,还是不见凉亭。以为姐姐骗我,又气又急,本来就渴,此时更渴了。实在是忍受不了,便到处找水,可山里除了知了在不知疲倦地唱着歌外,哪里有一滴水?突然,看见一拐弯处,有一丘巴掌大的水田,稻子正扬着花,我像遇着救星般地冲了上去,捧起田里的水就准备喝。姐姐一把拉住我:“不能喝,水里有细菌啊!”我哪顾得了这些,咕噜咕噜地喝了下去。水一下肚,人精神为之一爽,又像小马驹一般,在山路上撒欢。
终于,到了姐姐说的凉亭。凉亭建在去小镇的山路中间,到此地恰好走了去小镇一半的路程。至于为什么建在这里,我想一是风口,这是最关键的;二是由于去一次小镇路途太远,又是一路山径,干渴难忍时,有一处这样的纳凉歇脚之地,岂不妙也?!
凉亭雄居在山口,飞起的屋檐煞是好看。一进入凉亭,迎面就是一阵清风,那种爽气顺着每一个毛孔沁入肺腑。我打量着凉亭,那斑驳的墙体上,居然长着杂草,可见很有一些年份;依稀可辨的字迹,告诉人们这凉亭系清末所建。凉亭内,一条小径从中穿过,两边各有一条条石凳,石凳面被磨得光光的,不知有多少南来北往的客人在此歇过脚。我坐在石凳上面,那种凉啊,沁入心脾,什么渴啊,什么累啊,全然皆无。
过往的山民们脚穿草鞋,挑着担子,连走几十里地,到凉亭时,便在这里歇下担子,袒胸露背,全身松驰。有的坐在条石凳上,掏出烟袋,点上火,靠着风口,猛吸一口,那一路的劳顿啦,好像就随着吐出的烟圈旋转而去;有的竟靠着墙呼噜呼噜睡着了,是一种劳累的艰辛,抑或是一种劳累过后的享受。我反正看到的是一种安详和宁静。每每这个时候,凉亭里,就聚集不少的挑夫和过客,烟雾中,古今中外,家长里短都成了最好的谈资。但在凉亭是不可久歇的,歇久了,会让人的斗志皆无;挑夫们也不是玩主,功夫做不完,不仅拿不到工分,还要被家里的堂客唠叨。于是,凉亭永远都不是目的地,而只是征途中的一个歇脚处,它给你体力上的恢复,它给你前行加油。
离开凉亭时,我站在凉亭口,猛吸一口清风,大声地吆喝,声音在群山间蜿蜒回响。此时的山径,弯弯曲曲,掩在青枝绿叶间,时隐时现,那不正是一段丰富而历尽磨难的人生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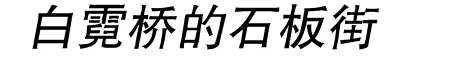
白霓桥是鄂南的一座古镇,那里的“父母官”们称之为我们县的“第二大城市”。她确切的历史已湮没在时间的隧道里。但据我所知,此镇至少也是在明代甚至以前就形成了。由于她处在幕阜山脉崇山峻岭的一处开阔地,自古便是鄂赣边陲的货物集散地,一直到今天都是商贾云集。
少年时,我在那里求学三年,古镇的每个角落我们都探寻过,但印象最深的却是那条长长的石板街。
石板街没有别的名字,它的名字也许本来就叫石板街。古镇只有一条丁字形的街,石板街就在那“丁”的拐脚上,百十来米长,用青一色的青条石铺成,据说是明代的产物。青石一块衔着一块,错落有致,构成了平整的街面。街两旁是青一色的青砖黛瓦房,瓦房的进深很长,门面皆店铺,往里则是会客室,再往里是厢房,最后才是厨房和厕所。开市时,家家打开大门,摆满了货物,街道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打货的,叫买的,络绎不绝;收市后,家家户户开始一块一块的上朱红的门板,刹时,刚才还洞开着的门就关上了,主人家盘点着一天的进项,守着喜悦或沮丧,只有点点烛火从门缝里漏出来。
我时常去石板街,但独爱清晨和天擦黑去那里流连,只有那时,石板街才最能显出她独到的美。
清晨,当第一道晨曦初露时,我便晨练到了石板街。那朱红的门板还整齐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让人仿佛置身于历史中,发思古之悠情。一丝光亮照在石板街上,仿佛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诗意。忽然,“吱呀”一声,一扇门露出了一条缝,一个着碎花衣的妇人闪了出来。早起的妇人用竹篮子挽着衣衫去石板街不远的毛家河浣洗,不一会儿,便从远处传来高高低低的杵声。此时的石板街是静谧的,我看着天空,也像一块青石板,只是弥漫着一绺雾霭,令你不由得一阵深呼吸。就在这种遐思和吮吸中,邻居老爷子的一声咳嗽划破了原先的宁静,于是朱红的门开始徐徐打开。浣衣的妇人也挽着竹篮回来了,晾好衣衫,便去后院准备着一家老小的早餐,石板街的上空便升起了缕缕炊烟。随即,家家户户的朱红门板一块一块陆陆续续地被卸了下来,各种山货又摆满了石板街,赶早打货的老表们也陆续来到了石板街。石板街新的一天就这样运转起来。
傍晚时分,吃过晚饭,我习惯地夹着一本书又闲逛着去了石板街。那是一个夏夜,暑热的风仿佛含有烈焰似的,然而,到了石板街,却又是另一番景象。一进街口,一丝凉风便不经意地扑面而来,脚下也有丝丝清凉,原来青石板还有祛热的效用,泼过水的青石板街面,确实要比沥青路面凉爽许多。这时,家家户户朱红的门板都还没有上上去,街面上已摆满了密密匝匝的竹床。老人们端坐在竹床或竹椅上,打着蒲扇,细声地说着话,怡然自得;妇人们却没有那么清闲,趿着拖鞋,聚在一堆,边纳鞋底边讲着婆姨堂客们之间才有的趣事,说到会心处,一阵笑声便从街头飘到街尾;只有男人们打着赤膊,就着一碟花生米或几块猪头肉,呷着陈年的米酒,有滋有味,尽管大汗淋漓,也是乐此不疲;孩子们光着小脚丫,满街上乱跑,或寻着蝈蝈的声音,或追着萤火虫的亮光,好一幅美妙的夏夜图。
在那三年,石板街给了我无穷的乐趣,落雨时的石板街,飘动的桐油伞会给你浪漫的灵性,说不定就能逢着丁香般愁怨的姑娘;雪覆盖着的石板街,家家户户燃起的炉火,会勾起你“夜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悠雅……
离开白霓桥好多年了,我魂牵梦绕的就是石板街,她像我生命的一部分流在我的血液里。
去年的一天,我终于有机会带着女儿去白霓桥。临去前,一宿都没睡好。在路上,我用最煽情的话语给女儿讲着石板街的美好往事,其实我经常给她讲着同样的话。女儿听都听熟了,但听说要亲眼去瞅瞅石板街时,她也是兴奋得不得了。
可当我像会初恋情人一样,再见着我的石板街时,我的心,冰到了极点,不是因为她老去的颜容和沧桑,而是,她已被破坏得面目全非。原来青一色的条石,缺一块,破一块;原来密不透风的石板路面居然裸出了泥土;原来青砖黛瓦的民居被高一层矮一层的水泥楼房所取代;原先朱红的门板没有了,也许塞进了家家户户的灶里。我怎么也没想到我会见到这样一幕,我伤心得落泪了,女儿也在一个劲地说我骗人。我能说什么呢?我无话可说。一方面,我们在大肆仿古,甚至造古,以招揽游客;另一方面,我们却在破坏着祖先留给我们的有价值的遗迹,不只在白霓桥,全国各地都有。如此,我们会留给子孙什么样的纪念呢?除了骂名,我想不出还有什么。谁幸耶?谁又不幸呢?

这条河在石山脚下,虽然地处江南,但却是一条典型的季节河,除了春天还像一条河外,其他季节几乎断流。即使有点水,充其量也只能叫“圳”(鄂南方言,小溪),是万万不能叫河的。
但这季节河上,有一处潭却四季有水。因为地势原因,在河的中段,陡然形成了一道坎,上下有四五米的落差,河里有水时,流下来,颇有点像黄果树瀑布;河里无水时,但坎下的潭因一口泉涌,却有着清水一泓。她四季都是澄清碧绿的,即使浑浊的水流进她的怀抱,也只一霎时的浑沌便又恢复了原样。于是她便成了我们那个村庄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水。也许是她的纯净,也许是她在月夜下的一如明镜,我们那里的人都称之为明月堰。
明月堰的春天是激情四溢的。桃花汛期,这条季节性的河流就开始有水流的声响。一夜间,从上游冲下来的河水就将昔日裸露的河床淹没。干枯的河床饕餮般的吮吸一路冲下来的河水,仿佛要吞噬这久违的恋人。然而,春水是无暇顾及这些的,更不会顾盼,一转眼就奔到了明月堰。明月堰的坝上便响起铿锵的水流声,发浑的河水猛烈地撞击着堰下的清泉,清泉刹那间浑浊起来,但刹那间又清澈起来,浑浊和清澈像交锋的敌我,拉锯似的争夺,蔚为壮观。站在明月堰旁,看坝上的流水,如观银瀑,飞溅的水花扑到脸上,好像嗅到了桃花的香味。
江南的春短,这样的日子不长,一不留神就入了夏。明月堰的夏是漫长的,但也是最热闹的。这时,河里的水开始变细,从高处看像妇人纳鞋底抽出的一条细线。过了五月端阳,便只有低凹处还积攒着一些残留的春水,如果此时你再站在高处看,河湾的水凼像极了村姑照的小圆镜。即便这样,但明月堰却有着别样的风情。尤其是暑期,明月堰就是我们这帮孩子的乐园。白天,我们在明月堰边放牛和嬉戏,骑牛当马,比赛输赢。一身臭汗后,便将身上的衣裤一剐,一猛子扎入明月堰里,顿觉爽意袭来,臭汗全无。我们时而沉入水底,时而仰面朝天,无论沉浮,清澈的堰水都让我们裸露得一览无余,那种舒服哇真是不言而喻。中午,明月堰便是属于汉子们的。在田里干了一上午农活的汉子们,趁着午休,三三两两泡在明月堰里解乏,消除疲劳。而傍晚则最动人最有风景,明月堰又成了姑娘嫂子们的天下,她们扛上竹席,在堰边围成一个圆桶,就在里面宽衣解带。只要她们在明月堰,整个村庄就会传来银铃般的笑声。引得男人们一肚子坏想。有一次,一男子忍不住蹿到明月堰偷窥,没想到还是让嫂子们发现了,硬是将他拖到堰里呛个半死,差一点被脱得一丝不挂。从此,再没有男人敢在傍晚闯入明月堰了。
明月堰的秋不像春那么热情洋溢,也不像夏那般躁,她是宁静和妩媚的。一道秋风一道凉,水冰冰的,家里的大人们就开始不让我们再去明月堰戏水了,明月堰顿时失去了往日的喧闹。但我们仍然会在中午时分偷着去,而那样的时候,我们只能“戏”一会儿,然后躺在坝上把身上的水晒干,免得被父母发现。有时因晒得太干,母亲只用指甲在手臂上轻轻一划,就能识别我们是否去戏水了。而此时,离明月堰不远的石山上的山楂红了,倒印在明月堰的清波里,像少妇被太阳晒红的脸颊,成熟却不失妩媚。
冬天的明月堰则显得有些寂寥。有一年,江南的冬出奇的冷,雪将明月堰掩在一片白茫茫中,只有堰水像喘着粗气似的,弥漫着一股神秘的清纱。雪天的大多时候,孩子们都龟缩在火塘边,听老奶奶讲着各式各样的灵怪故事。只有那些勤朴的媳妇们早上会挽着一竹篮衣服去明月堰浣洗,并担回一担清水,燃起炊烟,为全家人的吃喝忙碌着。一年就这样在明月堰的变幻中又过去了。
无数的日子在不知不觉中从指缝间滑走,离开明月堰也有二十多年了,当年不识愁滋味的莽撞少年已人过中年,岁月在变,人也在变,不变的只有那依然清澈的一潭堰水。每每这样的时候,不知谁在明月堰上喊:“割麦插禾!”于是,一滴思乡泪便已打湿衣襟。
责任编辑:袁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