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北海币考证
李银
几种北海币考证
李银
一 北海银行民国二十九年山东红五元考证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山东民国二十九年 (1940)红五元券北海币在莱芜首次面世,到目前为止,约有十枚。由于之前许多泉友对该币种是否存在提出种种质疑,笔者经过苦苦追寻,终于发现了关于该券的直接史料。这些史料不仅证明了当时笔者判断的正确,还提供了新线索。
2013年夏季,为配合山东省钱币学会在临沂举办纪念北海银行成立七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临沂市钱币学会进行了一系列的先期准备工作。在查阅早期的 《大众日报》时,刊载在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一版的一则告示引起了笔者的主意。告示摘要如下:
“省战工会规定查禁伪造北币办法 (以下简称 ‘办法’)
省战工会顷为巩固北海币信用,查禁伪造北币,特规定下列办法:
……
(4)由北海银行即日公告停止使用红色的及胶东版蓝色带 “繁”字的两种伍元票,以后再由银行公告定期全部收回,其兑换基金可暂由各地政府收入项下暂借,由银行拨款偿还。此外并指明如红色崭新面码号超过040000号以上的五元北币,即系伪造,因此票系去年春天一次发行二十万,总数四万张,号码止至040000号,以后即未续发。”
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年,“去年春天”,就是1941年春天。山东民国二十九年红五元券系总行约在1940年底至1941年春之间发行。那个时期,除一纵和胶东的北海银行曾经印过无地名北海币外,北海银行总行 (以下简称总行)发行的北海币印 “山东”字样,其他战略区发行的北海币印战略区区名。从 “办法”的叙述逻辑看,红色五元就是指山东红色五元。如蓝五元 “繁”字版就注明了胶东。“办法”透露出两条信息:一是红五元发行于民国三十年春天,二是红五元发行总量20万元。
笔者在山东省档案馆查阅北海银行档案时发现两份相关重要资料。一份是1942年1月11日省战工会关于查禁伪造北海币的指示 (山东省档案馆资料,索引号是G004-01-007-015,以下简称 “指示”)。另一份是1946年10月15日总行关于收回几种本币的通函(发字第六号,山东省档案馆资料,索引号是G013-01-0007-009,以下简称 “通函”)。“指
示”说,“最近在鲁中沂蒙山等地发现奸人伪造北海五元本币,计有红色的,第一次发行套版蓝色的及胶东版蓝色正面盖有 ‘繁’字的三种。”其中 “套版蓝色的”是指民国三十年山东天坛五元券。该券系总行第一次采用套色印刷技术印制的北海币。“指示”后面介绍了三种假币的特点。关于红五元假币特点的描述与 “办法”的描述相同。对另外两种假币的描述则十分详细具体。“通函”说,“三、五元券两种:A正面红色,反面淡枣色,山东字三十九年印,正面主要参考为左面山景,(印刷不好且假票过多故收回)。”其中,“三十九年”实为 “二十九”年之误。因为在 《渤海分行出纳发行工作总结》(1947年1月,山东省档案馆资料,索引号G040-01-0005-001)中,亦有总行的回收通知,同一票子的年份写作“二十九年”。这些史料对解开民国二十九年山东红色五元券 (以下简称 “山东红五元”)之谜大有裨益。
尽管 “通函”描述的红色五元与目前面世的山东红五元左边图景有差异,笔者仍然认为二者为同一币种。理由如下:
1.从纸质看,确系那个时代产物。从印刷工艺看,属于石印。如果这些红五元不是总行印制,则必定是日伪所为。日伪仿制北海币破坏根据地金融秩序,抢购根据地物资,必须以当时流通的北海币为造假对象。故,总行当年确实印发过这种版别的红五元。
2.“通函”对红五元正背面颜色的描述与面世的山东红五元正背面颜色相符,对印刷质量的描述亦相符。“通函”说红色五元左边是山景,而面世的山东红五元左边是寺庙山景,且以寺庙为主图,山景为虚景,二者虽有差异,但均有山景。差异可能是由叙述偏差导致的。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如 “通函”在回收民国三十一年山东十元券一款中就描述该券正反面色同。其实,该券正面是草绿色,背面为蓝色,差异甚大。再如,“通函”在回收民国三十年山东五元一款中描述该券主图右边图圈,圈内亭子,而 “指示”将该币的主图描述为楼景。其实圈内是天坛,等等。
3.除民国二十九年二角外,从1940年到1942年,一纵供给部 (总行筹建机构)或总行发行的北海币,同年份同面值仅有一种版别。民国二十九年二角券所以有两种版别,是由济南大中印刷局和一纵供给部分别独立印刷造成的。总行发展初期,制版能力极为有限,这种现象很容易理解。
“办法”说红五元系1941年发行。但直到今天尚未发现这种北海币。年份为民国三十年的山东五元券仅见到前面所说的 “套版蓝色券”。笔者认为不存在民国三十年山东红色五元券。“办法”所说的红色五元券,就是 “通函”中的民国二十九年山东红五元 (以下简称“通函红五元”)。原因有三:
1.据当年曾经参与印钞和发行工作的贾洪 (之前参与过打号码,1941年任营业科兼出纳科科长)、任志明 (负责印钞、发行)等人回忆,1941年以前,总行仅印过一角、二角、五角券,1941年才开始印一元、五元券。1941年以前,山东根据地的货币政策是巩固法币,支持法币的货币市场地位,发行的北海币仅是作为法币的辅币参与流通。1941年起,货币政策才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逐步提升北海币的地位。1942年的排法 (币)斗争后
推行以北海币为本位币的货币政策。综合这两条,笔者认为 “通函红五元”不是1940年印制的。
2.任志明曾提到,“银行发行的票子,印刷的时间都比发行时间提前,是一种惯例,记得是辛葭舟同志提意见这样打印的”。虽然这段话是任志明针对1940年 《大众日报》一则公告所说。但是,确实许多北海币票面印的时间比实际发行时间早,提前的时间也不尽相同。民国三十年山东蓝五元发行于1941年10月18日,所以 “通函红五元”应当发行于1941年1月以后10月之前。
3.前面说过,一纵及总行前期发行的北海币,一般情况下同年份同面值仅有一种版别既然已经有了民国三十年山东蓝五元,故不大可能再有民国三十年山东红五元券。无论《大众日报》还是 “指示”,在言及红五元时,均没有叙述其特征,说明1941年总行只发行了一种红色五元北海币。
“办法”与 “指示”均言明,红五元仅发行了20万元,即4万枚,4万号以上的五元券即系假币。以往公布某种北海币发现假票时,会同时公布真假票特征,以便广大群众识别。而 “办法”与 “指示”均仅仅以4万号为界判定红五元真假,且 “指示”对另外两种北海币的真假特征却介绍得十分详细,很不合常理。难道制假者只印制4万号以上的红五元?
笔者查阅了 《大众日报》、总行档案、《临沂地区金融志》、《沂南县志》、《莒南县金融志》等史料,发现1940年至1943年间,能判定行使山东地名假五元北海币的案例有4例这四例分别载于1942年12月23日、25日、27日的 《大众日报》及 《莒南县金融志》。根据这些报道对假币特征的描述,均可断定为民国三十年山东天坛五元券,无一例是山东红五元。假币数量方面,27日的 《大众日报》报道,“其中一百万元即系近日发现之伪造蓝色五元北海币”,莒南县志记载的数量次之,是10余万元。其余两条报道无具体数目,一说大批,一说数起。从现有资料看,并不支持山东红五元假票过多这一说法。

到目前为止,已面世的山东红五元号码有1万多号,3万多号 (如036522)(彩页8图1),4万多号 (如047059)、6万多号 (如069913)和8万多号 (彩页8图2),分布区域较广。除036522印刷较粗糙外,其余的印刷工艺水平基本一致。若按 “办法”所说,仅两枚可能是真,其余为假票。但是,基于以下理由,可以认定多数面世的红五元系总行印制:
1.从印刷工艺上讲,多数面世的山东红五元与同时期总行发行的其它北海币印刷工艺相当。以082868为例,与稍后印刷的民国三十年山东一元券 (彩页8图3)印刷工艺水平基本一致 (见二者局部放大图),与当年10月印发的套版天坛五元(彩页8图4)券比,印刷工艺水平是差点。符合“通函”所说 “印刷不好”这一特征。总体看,这些山东红五元的印刷水平符合总行印钞厂早期的
印刷水平。
2.不论北海币还是其他纸币,除了新假,面世的纸币基本上是真票远多于假票。仅就总行1941年前后发行且目前存世较少的北海币来说,笔者见过几十枚民国二十九年 “鲁南”字二角票,数枚一角票、五角票,无一假票;数十枚民国三十年 “山东”字五角、一元、五元券,仅发现一例五元假票;十余枚民国三十一年五分券,仅发现一例五分假票。其中五元券假票是依据 “指示”及 《大众日报》披露的真假币特点判断的。虽然 “通函”说山东红五元 “假票过多”,但是在此 “通函”回收的其他北海币中,多数也是说 “假票过多”,甚至说民国三十二年鲁中五十元是 “假票太多”。笔者见过数枚鲁中五十元券,和山东钱币博物馆藏的票样对照,无一是假票。曾经明确记载有110万元以上假票的民国三十年山东五元券,今天才见一假票,所见票中,假真比率小于三十分之一。一种发行不久就停发的票子,其流通范围肯定不广,影响力也不大,甚至根据地都很少人知道有此种票子,假票自然也不会很多。
3.面世的4万号以上的票子无一被加盖 “假票”字样或是剪角 (部分根据地曾以在票子上剪去一角作为假票标记)。这一现象说明4万号以上票子和以下票子可能无法仅从图案细节和纸张上识别。
笔者不否认山东红五元存在假票。在对比两券图案时发现,图案中大雁的两翅夹角有所不同,其中一券可能有问题。相邻时期有大雁图案的还有一纵发行的民国二十九年北海银行 “鲁南”字一角、二角、五角券。这些纸币上的近景大雁也都较肥大,所有的大雁都有个共同点,就是两翅之间的夹角都不是很陡,显得较平缓。而036522号券左边三只大雁两翅膀夹角明显较陡。

鲁南券三种面额上的近景大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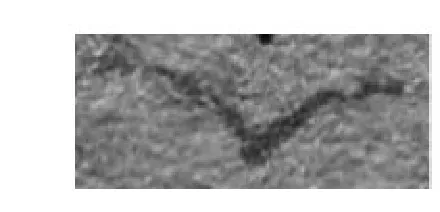
036522号券近景大雁

082868号券近景大雁
不仅如此,036522号券的印刷明显较其他山东红五元粗糙,与民国三十年 “山东”字五角、一元、五元券比,印刷工艺水平也差之甚远。与山东红五元背图基本相同的是民国二十九年北海银行蓝石坊五元券,该券为胶东分行1941年9月发行,钞版可能系总行代制。胶东分行印制的北海币大多较总行精致,但是差别不是很大。我们对比036522号券、“蓝石坊五元券”(山东钱币博物馆藏票样)及082868号券背图相同位置的局部放大图明显看出,082868号券的印刷工艺比较接近 “蓝石坊五元券”,而036522号券差之甚远。

036522背图局部

石坊五元票样背图局部

082868背图局部
根据任志明及黄嘉和 (1925年,原北海银行鲁中分行职员,笔者曾亲自采访过)等人的回忆,用石印机印出的票子,赶不上我们印得好的,就是假的。082868号券与036522号券均为石印,是非应该明了了。反过来,如果说082868号券是假票,而036522号券是真票,那么造假者以036522号券为蓝本印制的假票,背图细节怎么可能反而更丰富,更接近“蓝石坊五元券”?“通函”说山东红五元 “印刷不好”,并不意味着山东红五元印刷得很粗糙,只是与总行印的其他北海币有较大差距。仔细对比这些北海币与总行相近时间发行的其他北海币,发现他们的印刷工艺水平基本相近,差别并不大。同一印钞厂相近时期印刷水平有差异很正常,但是不会差得很多,毕竟是同一设备,同批技工所为。何况这批技工又是来自济南大中印刷局,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不是初学者。
既然4万号以上的山东红五元并非都是假票,为什么 “办法”要指真为假?细细推敲或许 “办法”与 “指示”里面有难言之隐。当时条件艰苦,设备简陋,制作一块钞版很不容易。制好钞版,绝不会仅仅印4万枚就弃之不用。根据存世的山东红五元已发现8万多号,但未发现10万以上的号码,估计当时山东红五元可能印制了近10万枚,但仅仅发行了4万枚就因故停发。在纸张极度匮乏,连干部用纸都实行配给制的年代,未发行的山东红五元绝不会就地销毁,而是被封存起来,伺机再发。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被封存的北海币又非正常地进入了流通领域。比如,人为盗出,扫荡中被日伪缴获,或遭国民党反共势力突袭被劫去,等等。当时总行印钞厂在沂南大梨峪,离蒙阴垛庄日伪据点很近,时有小规模的扫荡。1941年11月初至12月中旬,鲁中遭遇日伪5万人大扫荡,期间北海银行总行人员基本上分头行动,印钞厂曾被日军包围于蒙山之中。1941年9月,国民党五十一军、五十七军中的反共派曾连续数次袭击了鲁中根据地。纵观北海银行档案,被日军缴获票子、职员盗取票子等事件并非没有发生过。这也可能就是 “通函”不再说4万号以上是假票的原因。
山东红五元仅仅发行了20万元就停发,应当属于非正常停发。是什么原因导致其停发的?
抗战时期共产党政权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政府并拥护法币。早期,多数根据地以辅币不敷流通为由发行了元以下的小额纸币。随着国民政府逐渐停发八路军军饷,国共两党之
间关系的紧张,尤其是皖南事变后,部分根据地开始印制五元券试图挑战法币的统治地位,这样一来必然招致干预。
1941年1月13日,蒋介石给财政部长孔祥熙发了快邮代电。全文如下:“财政部孔部长极机密亲阅查第十八集团军在鲁成立北海银行擅发伪币强迫人民行使窃换粮食企图破坏金融吸收法币现国军为整饬纪纲除已令该军调开黄河以北作战外对于该北海银行破坏金融事应由贵部拟定计划定于卅年元月号日前迳电山东沈主席遵行并与洽办具报为要中正覃午令一元育 (意即13日午间,军令部一厅一处一科——笔者注)印。”①当月20日,财政部致电山东省主席沈鸿烈:“迅饬各该县政府即日布告并鸣锣周知禁止收受行使”。且不说沈鸿烈主席素与根据地不合,双方多有摩擦,利益攸关之大事,根据地是不会轻易让步的。从当时山东的金融形式分析,山东国民党游击区许多地方政府及一些武装力量也发行了元以下辅币,单独禁止北海银行发行辅币似不合理。但是,禁发五元以上大票的要求应该不算过分,毕竟根据地还打着拥护法币的旗号。在沈鸿烈与根据地交涉过程中,或交涉后,为了统战关系,战工会最终决定停发山东红五元券,转而发行一元券。再后来,随着当年3月2日朱信斋率部投奔国民党百十一师,“4·25”事件,5月8日的南马口事件,“7·25”事件,8月10日国民党六六五团抢粮事件,9月份国共双方多次交战等一系列摩擦的发生②,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当年10月,北海银行总行终于撕破面皮再次印发五元券。
发行于1941年春天的山东红五元,为什么票面时间印 “民国二十九年”?据时任分管印钞发行工作的任志明回忆,是辛葭舟 (当时对外宣称贸易局局长)建议票面上的时间要比发行时间提前。这样做应当有深层次的用意。当时情况下,根据地发行五元以上的纸币,肯定会受到责难和干预,将票面时间提前的最大好处,遇到干预可以推之于往昔所为。
山东红五元开了山东根据地纸币发行有意将票面时间提前之先河。此后,胶东分行经常采用此法,总行在首次发行大额北海币时也多次采用。
关于山东红五元的发行动机。1940年9~10月间,济南大中印刷局开始把卖给总行的印钞设备陆续拆卸运往根据地。这就意味着,大中印刷局代印北海币的工作逐渐停顿或已经完全停顿,到1941年2月,总行约有4个月未印北海币。加之当时战事频繁,军队及地方需求颇多,财政吃紧是肯定的事。为了应 “急”,选择印制五元 “大票”也在情理之中。
北海银行总行成立后,于1941年春天在大梨峪建立了印钞厂。笔者所知道的山东红五元发现地有莱芜和沂水两处,其中多数出于莱芜。这两地当时均属于鲁中区,离红五元的印制地点沂南大梨峪都不是很远。由于山东红五元发行于1941年春天,所以山东红五元很可能是总行印发的第一种北海币。
关于山东红五元印制的大致时间。根据任志明回忆,1941年春节过后,他带领济南来的技工由城子村进驻大梁峪 (实为沂南大梨峪——笔者注)印钞厂,开始了印钞工作。1941年春节是1月27日。以此推算,红五元当始印于2月份,即初春。
关于山东红五元钞版。山东红五元钞版是制版技师赵克勤亲自设计制作的。由于1941
年2月就开始印制红五元,钞版的制作要早于这个时间,所以,不排除钞版的制作始于1940年。
带胶东地名或无地名民国二十九年石坊蓝五元券 (彩页9图5)背图与山东红五元背图几乎相同,只是山东红五元背图下方有英文 “北海银行”,“石坊五元”没有。可以肯定二者使用的是同一设计制作单位制作的背版。“石坊五元”首发于1941年9月,山东红五元要比 “石坊五元”早发行近七个月,加上总行有刻版技师和制版工具,而胶东分行此时期什么都没有,所以笔者认为胶东分行使用的是总行雕刻技师雕刻的背版。
山东红五元是总行正式成立后自己印制的第一种北海币,亦是第一种印有 “山东”字样的北海币。总行在北海币上印 “山东”二字,意味着总行要逐步统一山东根据地流通货币。加上存世量稀少,山东红五元在北海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 六种无地名及一种无年号北海币考证
1.六种无地名北海币之考证
在洋洋大观的北海币中,除了重建后的胶东北海银行用民国二十七年掖县版印制的部分北海币,一纵供给部自己印制的北海银行二角券,以及总行1948年10月以后印制的北海币不带地名外,存世实物中,尚有六种不带地名的北海币,分别是:民国二十九年石坊蓝五元,民国二十九年天坛红十元,1941年、1942年蓝色一元,无年号红色山水一元,以及1942年红色山水一元券。所有山水一元券正背图案均一样,系同版所印。这些无地名北海币票面时间段基本分布在1940至1942年间。
由于胶东的北海银行创建最早,为了与之区别,总行筹建时印发的北海币,除供给部自印的北海币外,均印 “鲁南”字样,总行成立后,印制的北海币均印有 “山东”字样清河分行、冀鲁边分行发行的北海币分别加盖 “清河”、“冀鲁边”字样。在上述时间段内鲁中区、滨海区、鲁南区使用总行版北海币,渤海分行尚未成立。因此,有理由认为上述那些无地名北海币均为胶东的北海银行印发。
佐证一是,胶东北海银行发行无地名北海币由来已久,自1939年重建时就开始了。
佐证二是,上述无地名北海币除了红山水一元外,均有加盖 “胶东”地名的同版北海币。查总行并未发行过上述同版北海币。虽然民国二十九年石坊蓝五元有加盖 “清河”“冀鲁边”字样的,十元天坛有加盖 “清河”字样的,那都是胶东分行代印的。
佐证三是,《胶东区版别发行年月统计表》(山东省档案馆资料,索引号G013-01-0001-004)中有发行石坊五元之记录,始发时间是1941年9月。且1946年确定回收几种北海币的通知 (山东省档案馆资料,索引号G040-01-0005-001)中,胶东回收部分有如此记载:“(一)五元票,正背均是深蓝色,正面左图石坊树木,民国二十九年印,两端带‘繁’、‘荣’字,背面中间是楼房”。在 “回收通知中”,所有有地名的均标明,此处未说地名,当是无地名石坊五元券。另外,1942年12月11日,省战工会关于查禁伪造北海币的指示中将带 “繁”字的蓝色五元定为胶东版。其中对该券图案的描述与加盖 “繁”字的无
地名石坊券极为吻合。此二条中的任何一条都足以说明,加盖 “繁”、“荣”字无地名石坊券为北海银行胶东分行发行。目前已经发现的民国二十九年石坊 (俗称蓝牌坊)无地名蓝五元券 (以下简称 “无地名石坊券”)均加盖单个汉字,分别是 “繁”、“荣”、“春”三字。“繁”、“荣”二字显然系同一人书写。而所见的 “春”字与 “繁”、“荣”二字不是一种字体,极不协调。此字显然系模仿民国二十九年石坊蓝五元冀鲁边 “春”字版,但字的态势有倾斜之感。我们认为这类 “春”字可疑。
佐证四是,总行、冀鲁边分行并无发行天坛十元版北海币的记录。而 《胶东区版别发行年月统计表》中却有发行天坛十元记录 (始发时间实际是1941年秋季)。且该系列币上加盖的 “发”、“展”、“农”、“村”、“经”、“济”等字,与陈文其、刘涤生等人的回忆相吻合。更为重要的是,1946年确定回收几种北海币的通知中,胶东回收部分亦有如下记载:“(二)拾元正背面均是红色,正面图右面前门,左面图是楼,中间大写拾元,两边区别字有胶东,发、展、农、村、经、济,民国二十九年印,背面中间房子,石崩上有亭子”这两条中的任何一条都足以证明天坛十元为北海银行胶东分行印发。
佐证五是,查总行、清河分行、冀鲁边分行并未发行过山水一元券,但是 《胶东区版别发行年月统计表》中却有发行山水一元之记录。首发时间是1941年6月。《东海支行1942年上半年工作报告》中言及印制过 “发展”字一元及 “A”字一元券,与目前发现的无地名蓝山水一元上有加盖 “发”、“展”及冠字A相吻合。1946年确定回收几种北海币的通知中,胶东回收部分有如此描述:“(二)正面有红色绿色深蓝色,左面图内有山房子树木,1942年印”。结合存在1942年蓝山水、绿山水一元胶东版,所有山水一元券正背图案均一样,系同版所印,可以认为,所有1941年、1942年蓝山水一元,无年号红山水一元,以及1942年红山水一元均为胶东北海银行发行。
2.无年号红山水及蓝山水一元加盖不同冠字发行时间及印制单位考证
目前发现的无年号红山水一元券均无地名,号码前均不带冠字,票面两边要么加盖“繁”字、要么加盖 “荣”字 (这些字虽是为了防假,也相当于冠字)。票面年号是1941年的蓝山水一元券格式与红山水类似,均无地名,号码前没有冠字,且票面两边均加盖单个汉字——目前发现有 “发”、“展”、“农”、“村”等字。票面时间是1942年的无地名山水一元券则大不同了,流水编码前均有冠字,票面两边均没有加盖单个汉字的。红山水流水编码前均为天干冠字,蓝一元流水编码前为冠字A。由票面这些特点,笔者认为无年号红山水一元的印发时间和1941年蓝山水一元券相近。
胶东分行只有东海印刷所、北海印刷所两个印刷 (印钞)厂,其中东海印刷所是主力印刷所。从1942年东海印刷所印制北海币成品看③,1月7日至18日印制了 “发展”字一元成品296626元。3月22日至6月底,完成 “A”字一元成品2133503元。两种一元券合计共2430129元。之后,年内未再印制一元券。由于1942年至1945年间,胶东并未换发新版一元券,其间发行的一元券均为胶东地名绿山水一元券。
存世的蓝色山水一元券仅有1941年、1942年两种年号。票面时间为1941年的一元券
均无冠字,正面两边加印 “发”、“展”、“农”、“村”等单个字;票面时间为1942年的一元券均有冠字A。有理由认为1942年及以前,东海印刷所印制的山水一元券正面均为蓝色其中1月7日至18日印制的 “发展”字一元券票面时间是1941年,3月22日至6月底印制的蓝山水一元券票面时间是1942年。也就是说,票面时间是1941年的蓝山水一元券始印于1941年6月,止于次年1月。
按 《胶东区历年发行北海币统计表》④,1942年,胶东分行共发行一元券3115000元扣除东海印刷所印制的2430129元,另外684871元山水一元券必为北海印刷所印制。这些山水一元券肯定包含无地名红山水一元券。理由是山水一元券仅有无地名蓝山水、红山水及胶东地名绿山水三大类,蓝山水属于东海印刷所印制,胶东地名绿山水一元券年号均是1942年。年号为1942年的无地名红一元发行时间不会晚于胶东地名绿山水一元券,不会早于1942年。由此可以认定无地名红山水一元券系北海印刷所印制。两个印刷所用不同的颜色印制同版北海币,因不同颜色的一元券分别流通于不同的区域,这个识别主要是为了反假斗争。
胶东地名绿山水一元券发行较晚的理由如下:自1941年夏季,省战工会确定各大区的北海银行为总行的分行后,到1942年上半年,胶东分行仍沿用老习惯,未在发行的北海币票面上加印 “胶东”地名,下半年才开始出现加印现象,次年则全面加印地名⑤。有据可考的是,民国二十九年天坛加印 “胶东”地名十元券及民国三十年火车胶东区地方本位币十元均券始发于1942年下半年,风船胶东五元始发于1943年9月⑥。
按照胶东北海银行冠字及流水编码的演变规律,同一版式北海币,流水编码前无冠字的发行时间要早于有冠字的 (渤海区的北海币有个别例外)。无年号无地名的红山水一元券流水编码前无冠字,而1942年无地名红山水一元券流水编码前有天干冠字,故无年号无地名的红山水一元券发行时间早于1942年无地名红山水一元券。即无年号无地名的红山水一元券发行于1942年或之前。
东海印刷所3月份开始将一元券两边加盖单字改为流水编码前加盖冠字。同属一家银行的北海印刷所也应进行相应地调整。依据类比法,笔者认为,那些无年号又无地名的红山水一元券系北海印刷所1942年3月份或之前印发,1942年无地名红山水天干冠字一元券,系1942年3月以后印发。
据 《胶东分行一九四一年全年工作总结报告》⑦,“北海印刷所于下半年又因环境恶劣停止工作,至十月才恢复工作。”《胶东分行一九四二年一至三月份工作总结》则说,“北海因环境恶劣未工作,只东海印了十元券二百万元。”也就是说,北海印刷所在1941年6至1月和1942年1至3月两个时间段内并未印制北海币,所以无年号无地名的红山水一元券当印发于1941年10至12月间。在所有山水一元券中,无年号红山水一元券印制时间最短印量最少,所以,存世也最少。
由于东海印刷所1942年仅印了 “发”、“展”字蓝山水一元券,以后未再印两边加字一元券,故目前存世的两边加印单个 “农”或 “村”字的蓝一元肯定系东海印刷所印制于
1941年6至12月间。
三 关于民国二十九年天坛十元、民国三十年胶东地名火车十元始发时间之考订
目前存世的民国二十九年天坛十元券 (以下简称天坛十元),是已发现的十元券中票面时间最早的北海币,民国三十年胶东地名火车十元券 (以下简称火车十元)次之,其始发时间会如票面载明的时间吗?答案是否定的。
时任行长陈文其在谈胶东印钞厂时说,“大概到1941年冬 (由于是叙述者的回忆,时间不一定很精确,笔者注),北海印钞厂离开分行和东海厂搬到了乳山县 (现海阳县)牙山里。……印钞厂搬到牙山后才开始印发五元、十元券。⑧”也就是说,1941年秋冬季节,胶东印钞厂才开始印制面额五元、十元的北海币。《胶东区历年发行北海币统计表》也支持这一说法。该表中,1940年以前栏目里无面额五元以上北海币发行量,1941年栏目内载明十元券发行量是3746千元。
但是,查 《胶东分行版别发行年月统计表》却发现,胶东分行1942年4月才开始发行十元券,该月同时发行了两种版别,分别是火车版与天坛版。此与前述说法有较大差异。胶东分行1941年发行十元券,不仅有 《胶东区历年发行北海币统计表》中的具体数字作证明,还有时任领导人的佐证,肯定没有错。错的就是 《胶东分行版别发行年月统计表》。
笔者认为发行于1941年秋冬季节的十元券就是民国二十九年天坛十元券,民国三十年火车十元始发于1942年下半年。两种十元券均系东海印刷所印制。目前尚未发现东海印刷所、北海印刷所1941年的具体印钞资料。只能借助两印刷所及胶东分行1942年的资料加以考证。
根据 《胶东分行一九四二年上半年的工作布置》,上半年安排东海印制100万元十元券,未安排北海印刷所印制十元券。《东海支行一九四二年上半年工作总结》报告,上半年共印制了 “发”、“展”字十元券200万元,“经”、“济”字204.5万元。《东海支行一九四二年工作总结》⑨记载,全年共印制十元券1882万元,扣除为其他战略区代印的十元券,供胶东区使用的为1691万元。其中天坛 “发”、“展”字十元券200万元,“经”、“济”字493万元;天坛胶东地名字母冠字682万元;胶东地名火车版316万元。无印制五元记录。又据《胶东区历年发行北海币统计表》载,胶东分行1942年发行五元券333.5万元,十元券1736万元。十元券的差额45万元,如果不是统计有误,则为北海印刷所1942年下半年印制。对以上数据综合分析后,明显可以看出,当时胶东分行主要是安排东海印刷所印制十元券,北海印刷所印制五元券。据此可以认为,发行于1941年的五元券均为北海印刷所印制,十元券均为东海印刷所印制。
1942年下半年,天坛十元券由两边加盖单字改为字母冠字并加印胶东地名,此种格式延续至终。结合1942年东海印刷所只印了 “发”、“展”、“经”、“济”字十元券,以及“发”、“展”字上半年的印制量,可以进一步确认那些两边加盖 “农”、“村”字以及部分
“发”、“展”字的天坛十元券始发于1941年。按陈文其的回忆理解,五元、十元券似乎同时发行。
1942年7月,山东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一次排法斗争,宣布北海币为本位币。之前一直认可法币作为主要流通之货币。8月,胶东区排法斗争获得初步胜利。火车十元券正面下方印有 “胶东区地方本位币”字样。仅凭这一条,就可以排除该币始发于1942年4月的可能。《东海支行一九四二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及 《东海支行一九四二年工作总结》也支持这一判断。北海印刷所上半年未印十元券,东海印刷所上半年未印天坛十元券,下半年才开始印制天坛十元券。
顺便说一下,在 《胶东分行版别发行年月统计表》中,发行早的券种排在发行晚的券种之后并非孤例。如民国三十二年高楼版,就排在三十四年券之后。
四 北海银行鲁中民国三十二年房子树图景蓝色十元辨析
本世纪初在沂南发现两枚鲁中民国三十二年房子树图景绿色十元券 (以下简称 “绿十元”)。该券与鲁中民国三十二年房子树图景棕色十元券 (以下简称 “棕色十元”)图案相同。区别是前者正面绿色,无印鉴及流水编码,后者正面为棕色,有印鉴及流水编码。背面完全相同。泉界对此亦有争议,有说是真票,有说是假票,也有模棱两可的。
仔细对比绿十元和棕十元,除绿十元正面底纹比棕十元粗糙些,二者纸质基本相近图案基本一致,背面完全相同,仅正面局部有些小差别。这些差别不是由来自不同的钞版导致的,而是印刷过程导致的。总体看,棕十元比绿十元印刷质量要精良些,但二者印刷工艺差别不是很大。
三枚绿色券均有明显的流通痕迹。其中两枚正面有黏贴后揭帖的痕迹 (彩页9图6)很可能是当年为了反假宣传,特意将那些一面印偏色的北海票改作张贴用的票样。张贴的票样后来被人们揭下来使用了。笔者倾向于绿十元券系当年的不合格品。
五 北海银行鲁中民国三十三年牛耕地五角券辨伪
由王宣瑞先生主编的 《专题集钞》期刊2002年第2期封底珍品欣赏一栏中,介绍了一枚北海银行民国三十三年鲁中牛耕地图案五角券 (彩页9图7,以下简称 “牛耕地五角”)该纸币系某泉商十几年前在徐州购得,后转让他人。北海银行民国三十三年鲁中树房子图案五角券 (彩页9图8)已经比较难见到了,如果该票为真品,则必为北海币家族新贵之一。当年许多藏家曾见过此币,多数认为该票为真品。
但是笔者仔细审视图片后,感觉疑点有六:
1.由于北海银行鲁中分行是在北海银行总行留在鲁中的人员和设备的基础上建立的故其发行的纸币和民国三十一年北海银行总行发行的纸币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元以上面额的纸币,“北海银行”(以下简称 “行名”)四字和地名均为同一人书写,如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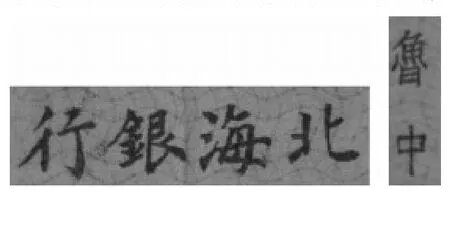
元以下面额的纸币,行名和地名书写虽与元票明显不同,但是,同一版别纸币的行名和地名仍为同一人书写,书写风格一致。而上述 “牛耕地五角券”行名书写与元票行名不一致,但地名 “鲁中”二字的书写却与元票一致,有悖于北海银行鲁中分行的常规做法,况且 “鲁中”二字与行名明显不协调,此其疑点一也。
2.所有的北海币,其行名字幅没有小于地名的,包括 “鲁中”地名北海币,而 “牛耕地五角券”地名却明显大于行名。此其疑点二也。
3.鲁中分行的纸币在发行量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流水编码前仅用字母A做冠字。目前发现的北海银行鲁中分行的纸币,除民国三十二年蓝五元、民国三十三年蓝十元因发行量大有多种冠字外,多数品种的流水编码前都仅用字母A做冠字。从民国三十三年开始,由于战争形势好转,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因而导致北海币供需缺口日益扩大,而印钞能力短期无法快速扩张,北海银行不得不加大大面额纸币的发行量,同时大幅度缩减小面额纸币的发行量。所以北海银行民国三十三年鲁中树房子图案五角券当年发行量很少,不足百万元,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难见到该券的主要原因。到目前为止,“牛耕地五角券”未再出现第二枚,如果该券为真,说明当年发行量极少。如此少的发行量,怎么可能会出现字母B做冠字?此其疑点三。
4.从构图效果看,基本是采用民国二十九年鲁南地名五角券的图案 (彩页9图9),只是树景不同。虽然该币正面的树和牛首看不清楚,但是,牛肚皮画得过于平直,体现不出牛肚子浑圆的感觉。人的前腿画得也很别扭,上下比例严重失调。尤其是树景,有两棵树几乎像长在田地里一样,部分树也画得很别扭。与北海银行总行民国二十九年五角,民国三十一年牛耕地二元券 (彩页10图10,当年亦在鲁中印制)比,艺术水准有一定的差距。此其疑点四也。
5.民国三十二年山东二角五券 (彩页10图11,该券系鲁中分行印钞厂印制)、民国三十三年鲁中树房子图案五角券,均没有加盖印鉴。也就是说,鲁中分行印发的角票是不加盖印鉴的。此为鲁中角票之一大特色,其他分行尚未发现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从民国三十二年起,北海银行角票已经开始逐步边缘化,到民国三十三年以后,角票仅是在市面急需时用旧版偶尔一印。而牛耕地五角券却加盖印鉴,真是画蛇添足,这也算一个疑点吧。
6.上述牛耕地五角券的流水编码为B0006701,如果该券为真,当为已经发行的纸币,而不会是试样票。鲁中分行发行纸币有一个特点,就是同年同面额的纸币只有一种主图。即便民国三十二年鲁中五元券有红、蓝两种颜色,但其主图却相同,何况红、蓝两种颜色五元券并非同年印发。蓝五元券是民国三十三年在红五元票版的基础上,对背版略加修改续印的。民国三十三年鲁中树房子图案五角券确为鲁中分行民国三十三年发行。鲁中分行怎么可能在印钞任务繁重的民国三十三年发行两种面额相同主图却不同的北海币,何况是已经边缘化了的角票!此为疑点六。
一枚纸币,仅正面就透露出如此之多的疑点,怎么能确认它是真品!仅仅一个疑点,
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或然事件,两个疑点也可以归咎于偶然因素,但是,如果疑点重重就说明这枚纸币肯定有问题了。
前些时候笔者又获得了鲁中牛耕地五角券的背图 (彩页9图7)。总体感觉印刷粗糙不符合鲁中印钞厂的印刷工艺水平。英文50分及四角的 “5”字基本上是仿造民国二十九年鲁南地名牛耕地五角券背面的写法,但过于生硬和别扭,尤其是英文50分,竟然写成了“FIFTYOENTS”。由于流通中的磨损,目前见到的民国二十九年鲁南地名牛耕地五角券背面 “FIFTYCENTS”中的字母 “C”,基本都有磨损,仔细辨认才能看出是 “C”。仿制者未看清,依葫芦画瓢,竟将背面英文面值中的字母 “C”误写作了 “O”。这种错误在北海币中还未曾见过。
英文面值是50分,按理四角应该印 “50”而不是 “5”,而该券四角却印了四个 “5”这是明显的错误。顺便说一句,鲁南地名民国二十九年五角、山东地名民国三十年五角以及清河地名民国三十一年五角北海币也曾出现过这种错误,但是山东地名北海币自民国三十一年起,所有角票都未再出现这种错误。清河分行之后未再发行角票。其他地名北海币未出现过类似错误。
鲁中牛耕地五角券背图下边的年号 “1944”,数字长度由左到右呈阶梯式减小,有点类似于当今人民币的流水编码,这在已知的北海币中绝没有出现过。
2014年11月29日,《北海银行货币大系》的编委们在临沂新闻大厦对鲁中牛耕地五角券图片进行了鉴定,参与者一致认定此票为臆造品。
鲁中地名北海币出现臆造品并非仅此一例。多年前,笔者曾见过一枚鲁中地名二角假票,红色,票纸系用解放前的票纸,印刷质量还是不错的,惜未留照片。今年又见一枚(彩页10图12),印刷工艺大不如前面那枚,图案、票纸及票幅也不一样,主图仿山东地名民国三十一年二角券。此票为臆造是显见的。一是鲁中分行民国三十二年档案资料中无此票,二是印刷工艺及纸张与鲁中地名北海币差异较大。此枚假票与 “牛耕地五角券”有个共同点,就是均以总行或其前身一纵曾经发行过的北海币为蓝本。鲁中地名北海币图案亦有沿用总行发行的北海币图案,但基本上是原图照搬。“牛耕地五角券”虽也沿用总行前身一纵发行的鲁南地名五角券图案,但对背景进行了较大的改动。
注释:
① 电文摘自山东钱币学会编,《山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第157页。快邮代电是用快邮寄递的简要公文,不是电报。“覃”字为民国电文中的韵目代日,即十三日,“午为地支代时,即十一至十三点间,“令”指军令部,“一”代表第一厅,“元”即一处,“育”这里可能读zhòu,古时指帝王与贵族的长子,代表一科。1938年初,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定,将原大本营所设第一部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合并组成为军令部。徐永昌为部长。下设总务及第一、第二3个厅:第一厅掌管国防作战事宜,辖4个处12个科。刘斐为第一厅厅长。
② 临沂地区史志办公室和山东省出版总社临沂分社编辑,《临沂百年大事记》1941年部分,山东人民
出版社1989年9月。
③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编辑,《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一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7页。
④ 同③,《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四册,第568页。
⑤ 1943年6月12日山东省战工会发布了 《北海银行组织章程》,第十二条规定:“本币之发行除经指定之分行外,其他分支行及以下之组织不得代理发行事宜,并依战略区为单位注以地名。”同③《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一册,第70页。另外,民国三十年火车版许多票面时间为民国三十一年,“胶东”地名北海币系1943年始发。
⑥ 《胶东分行版别发行年月统计表》。山东省档案馆藏资料,档案索引G013-01-0001-004。
⑦ 同③ 《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一册,第136页。
⑧ 同③ 《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一册,第133页。
⑨ 同③ 《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一册,第552、553页。
(责任编辑 刘 筝)
第三届中国金融史、货币史学术研讨会召开
由中国钱币学会和河北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金融史、货币史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6月13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召开。来自浙江、广西、甘肃、河北钱币学会以及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的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并做了交流发言。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王永生在会上做了讲话。会议由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戴建兵主持。
王永生副秘书长在讲话中指出,这是中国钱币学会首次与高校合作召开专题研讨会,对加强学会与高校联系,推动钱币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39篇,依据内容的不同,分设了钱币学、货币史与金融史两个小组进行研讨。这是本次与高等院校合作召开的研讨会的另一亮点,对学会今后组织开展专题研讨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北海银行纸币》出版发行
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中华纸币研究网站组织编撰的 《北海银行纸币》由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 “中国纸币标准图录”系列中的第二本,全书分上下两册,700页,全彩印刷,定价980元。
北海银行是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建立的金融机构,在抗日战争和随后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书对北海银行纸币进行了全面的归纳整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段烽火硝烟的历史。本书上册主要讲述从1938年北海银行在掖县建立至抗日战争胜利这一阶段的北海银行纸币,也包括了益寿临广流通券、莱芜农民合作社等与北海银行币配套的辅币券,及各个时期的小地名券北海银行纸币;下册则讲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北海银行纸币。本书资料翔实,图片精美清晰,且包含了众多珍贵的北海银行纸币图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以胶东文化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