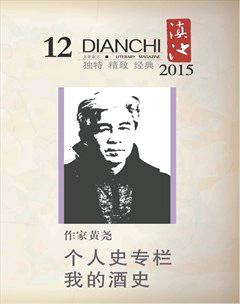张金凤
外套
一枚谷穗历练到了秋天
卸去鲜绿,有了阳光的颜色
开始垂下了桀骜不驯的头颅
到了成熟的年纪
要学会低头,对高贵或卑贱的事物
对着虚空的远方
以及太阳下自己的影子——
一只刺猬开始妥协
她收藏起那些天生的坚硬与尖锐
在角落里,把外衣脱下来
到了中年,豪言壮语变得可笑
谈爱情,甚至有些可耻
她开始试着翻穿起这件毛刺的外套
呈现给你想要的粉红和温柔
那些刺,却让我遍体鳞伤
流着谁也看不见的血
可我还是对世界微笑着,微笑着
与那件粉红的绵软外衣
保持着可贵的一致,并且说,看啊
春风多么猛烈,吹出我那么多眼泪
苇塘
黄昏时候它总是盗用天空的血
在污浊的水面上涂抹油彩
小莲就是在这里陷进一场戏
——他爹和一个有钱的山西客
密谋了一场比煤还黑的戏剧
于是她带着血痕斑斑的身体
在虚幻的黄昏里纵身一跃
接着,苇塘就哑了
猴子一样顽劣的孩子们也不敢去了
慢慢的,水面长满腥臭的绿苔
后来,被批斗的七老母跳了下去
在苇塘边哭了一夜的寡妇跳了下去
它成了乡村的一个魔咒
——那年秋天,苇子迅速衰败
不知道从哪里涌出了那么多拖拉机
用那么多山外的沙土和垃圾
还有遥远山西的煤渣
迅速将它填平了,到如今
苇塘只是一个老地名和古老的隐痛
春雨夜
那个冰凉的春天,我失去家园
寄居在表姨黑洞洞的檐下
和一只衰老的土狗作伴
柴草缭绕,烟火浓烈的灶间
表姨咳嗽着把小米锅巴铲进
我脏兮兮的小手里
颧骨高耸眼窝深陷的表姨
佝偻着,越来越像我过世的姑姥姥
每年冬天都要赌一次命
哮喘,浮肿,搂着寿衣过冬
艰难等待大雪消退,青草发芽
老梧桐荫庇的窄小庭院
瘦骨伶仃的枯草表姨
每天都会闻着寿衣里贮藏着干菊花睡去
有时候也会半夜起来
抚摸着多年前就买下新棉和被面
灰蒙蒙的望着外面
巴望在入土之前儿子娶回新娘
那夜,雨在窗外默默的下着
远方的黑夜里隐约有鸟的寒吟
在那春风冷湿的夜晚
我和表姨相对良久
是你娘当媒人把我骗到咱村里来的
最后她背对着我说了这句话
这时,窗外的雨更大了
什么也看不清楚了,像我们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