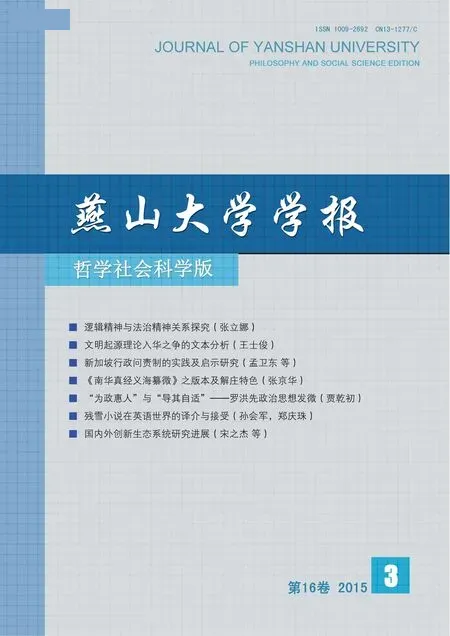“为政惠人”与“导其自适”——罗洪先政治思想发微
[摘 要] 罗洪先是阳明后学中江右王门的代表人物,其核心学旨为“主静无欲”与“收摄保聚”。他政治思想主要有两部分:一是为政以惠人的政治思想。主张一切政事的核心是惠人,强调解决基本民生的“不足”问题,认为政事也是“全其良知”的过程;二是“导其自适”的行政施治原则。将施治办法分为“顺导”、“检防”、“蹴迫”三策,以“顺导”为上。“导其自适”行政施治原则以明太祖“圣谕六言”的教化活动为基础。
[文献标识码]A
[文章DIO]10.15883/j.13⁃1277/c.20150306205
[收稿日期] 2015⁃05⁃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研究”(13&ZD008)子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贾乾初(1971—),男,河北沧县人,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罗洪先(1504—1564),字达夫,号念庵,江西吉水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后短暂任左春坊左赞善、经筵讲官,因忤旨罢官,乡居终生,以游晤、讲学为务。
罗洪先私淑阳明,并未及门。但为阳明高弟钱德洪与王畿激赏,属阳明后学中“归寂”派代表人物,为“江右王门”之重镇。浙中王门王畿曾说:“阳明夫子生平德业著于江右最盛。” [1]467黄宗羲指出,“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念庵、两峰、双江其选也。……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 [2]333时人亦有定论以为阳明后学中,“其私淑而有得者,莫如念庵” [2]390。可知,罗洪先在当时的阳明学界具有极大的学术影响。黄宗羲对罗氏之学概括说:“先生之学,始致力于践履,中归摄于寂静,晚彻悟于仁体。” [2]388其学旨以“无欲主静”与“收摄保聚”而著称。学界之注意往往集中著力于此,而于罗洪先的政治思想,鲜有理会。但这并不意味着罗洪先没有政治思想或缺少相应价值。儒学的逻辑从根本上指向政治,阳明学更是如此。对于罗洪先的政治思想,只不过缺乏归纳与分析研究罢了。罗洪先亦曾自谓其“未尝不以斯世为心” [3]243,鲜明地表达了对现实社会政治的关注。本文拟从其“主静无欲”与“收摄保聚”的核心学旨出发,初步探讨罗洪先的政治思想。
一、“主静无欲”与“收摄保聚”
罗洪先在阳明后学中影响巨大,与其思想的自觉有关,他的思想形成过程中深受李谷平、王畿、聂豹乃至宋人杨简等的影响,但在他的践履体悟过程中,最终都予以批判性超越,属大器晚成型思想家。其思想核心主张为“主静无欲”与“收摄保聚”,这也是他被日本学者冈田武彦划入“归寂”派的主要依据。 [4]5
罗洪先的早期思想,对阳明的良知学虽初有感受,却无深入把握,大体受阳明高弟王畿的思想影响。但随着罗洪先对良知学的把握和体悟渐深,他开始对王畿的“现成良知”说的流弊予以批判。二人于松原相会时,罗洪先直接批判王畿说:“世间那有现成良知?良知非万死工夫断不能生也。不是现成可得,今人误将良知作现成看,不知下致良知工夫,奔放驰逐无有止息,茫荡一生有何成就?” [3]696罗洪先亦曾辞锋尖锐地指出,“畏难苟安者”、“见小欲速者”都可以“现成良知”为口实,率意而为,其后果真是难以想像。
在其重要文章《甲寅夏游记》中,罗洪先说:“阳明先生苦心犯难,提出良知为传授口诀,盖合内外前后一齐包括。稍有帮补,稍有遗漏,即失当时本旨矣。往年见谈学者,皆曰‘知善知恶,即是良知,依此行之,即是致知’。予尝从此用力,竟无所入,盖久而后悔之。夫良知者,言乎不学不虑、自然之明觉。盖即至善之谓也。吾心之善吾知之,吾心之恶吾知之,不可谓非知也。善恶交杂,岂有为主于中者乎?中无所主而谓知本常明,恐未可也。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谓无乖戾于既发之后,能顺应于事物之本,恐未可也。” [3]81这里,罗洪先结合自己的工夫实践表述了他对良知学的领悟。并进而对“以一时之发见为本体”的观点提出批判说:“故知善知恶之知,随出随泯,特一时之发现焉耳。一时之发见,未可尽指为本体,则自然之明觉,固当反求其根源。” [3]81
随即罗洪先阐发了他的“主静”与“收摄保聚”思想。他说:
盖人生而静,未有不善,不善者动之妄也。主静以复之,道始凝而不流矣;神发为知,良知者静而明也。妄动以杂之,几始失而难复矣。故必有收摄保聚之功,以为充、达、长、养之地,而后定、静、安、虑由此以出,…… [3]81⁃82
罗洪先以为,“良知本静”,所以“主静”乃可以致良知。他进而又深入阐述“主静”思想说:“今之言良知者,恶闻静之一言,以为良知该动静,合内外,而今主于静焉,偏矣,何以动应?此恐执言而或未尽其意也。夫良知该动静,合内外,其体统也;吾之主静所以致之,盖言学也。学必有所由而入,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苟入矣,虽谓良知本静,亦可也;虽谓致知为慎动,亦可也。” [3]334
吴震将罗洪先的“主静”思想概括为三点:第一,“无欲”是最终目标;第二,“静坐”乃是具体工夫;第三,通过“静坐”才能识得本心。 [5]219这样,“静坐”——“收摄保聚”的工夫就凸显出来了。
罗洪先说:“夫心,一而已,自其不出位而言,谓之寂,……自其常通微而言,谓之感,……故酬酢万变,而于寂者,未尝有碍,非不碍也,吾有所主故也,苟无所主,则亦驰逐而不返矣;声臭俱泯,而于感者未尝有息,非不息也,吾无所倚故也。敬无所倚,则亦胶固而不通矣。此所谓收摄保聚之功,君子知几之学也。” [3]82⁃83此间对于收摄保聚工夫的强调解释,固然是罗洪先“主静无欲”之学臻于圆熟的体现,同时也是反拨、批判王畿“现成良知”说流弊的一个体现。
问题在于,罗洪先“主静无欲”与“收摄保聚”的思想仅仅局限于他发展良知学的思想领域吗?这些思想与罗洪先的政治思考与实践是相分隔而缺少内在联系吗?本文不同意这样的观点。罗洪先自己曾明确宣称:
儒者之学,以经世为用,而其实以无欲为本。夫惟用之经世也,于是事变酬酢之故,人物利害之原,家国古今之宜,阴阳消息之理,无一或遗,然后万物得其所;夫惟本于无欲也,于是死生祸福、毁誉得丧、荣辱喧寂、忧愉顺逆之本,无一或动,然后用之经世者,知精而力专。 [3]496
可知,罗洪先“主静无欲”、“收摄保聚”的学旨,正是其经世(政治)思想的根本,而且在他看来还是经世能够取得成就的重要保障。罗洪先在政治方面有着自己的思考。
首先,王阳明的良知学逻辑指向与实践指向都是现实的社会政治,作为高度认同良知学的阳明后学重镇,罗洪先显然不会与此指向相逆;其次,罗洪先秉承阳明“民人社稷,无非实学” [6]192的践履精神,对经世实学究心甚巨。他与好友唐顺之(1507—1560,号荆川)“跃马弯弧,考图观史,其大若天文地志、仪礼典章、漕饷边防,战阵车介之事,下逮阴阳卜筮,靡不精核。至人才吏事,国是民隐,弥加诹询”,并自称“苟当其职,皆吾事也” [7]759;复次,罗洪先在长期的乡居生活中,始终本“万物一体”之念,推动宗族建设,实践伦理教化,并致力于以乡约的手段来发挥社会探制功能。 [8]136由是可知,罗洪先本着对良知学的理解与发展,以及自身的政治与行政实践,在政治思想方面,决然是有着自己观点与认识的。
因此,尽管罗洪先传世文献中涉及其政治思想的内容不多,但悉心寻绎,仍可对其政治思想予以明确勾勒。
二、为政惠人的政治思想
与汉以来的儒者一样,罗洪先将治理国家的基本思想依据都寄予在儒学之上,“夫圣人立中国生民之命,设名教以绝祸乱之源,莫大于明物而察伦。” [3]27“儒者之学,固治中国之绳墨也。” [3]31在这种认识基础之上,他以阳明学对《大学》的解读来阐发其所理解的治平天下的“大人之学”:
大学,学之大者也。学其大者为大人,合人己而一之者也。明德,德本明也;明明德,学也。民而曰亲,莫非己也。与己不干,绝物矣,是谓异端,非大学也。
物者,知之感也;知者,意之灵也。知感于物,而后有意。意者,心之动也;心者,身之主也;身者,天下国家之本也。感而正曰格,灵而虚曰致,动以天曰诚,居其所曰正,中有主曰修。无无物之知,无无知之意,无无意之心,无无心之身,无无身之家、之国、之天下。灵而感之以正,曰知止;感而以止,天下国家举之矣,故曰至善,莫有善于是者也。虚灵能感,则意定;动以天,则心静;中有主,则安;举而措之天下国家,则虑无不当,大人之事毕矣。[3]12⁃13
可知罗洪先所谓的“大人之学”,不过是明德亲民、正己正物、静心定意,并以之举措于天下国家,最终以社会政治为根本落脚。罗洪先亦以是否能“以天下为己任”作为划分“圣学”与“异端”的根本标准。 ①所有这一切都要落实在“惠人”之政上。
1.“惠人”“爱民”是政事的核心
检《罗洪先集》得其所述“为政惠人”思想材料如下:
人之生也,食饮被服,安处而和亲,此天所与我者也。圣人惧劫夺攻取,而人之饥寒困苦不己若也,于是乎有官政焉。故为政者,将以惠人也。 [3]49
夫政,固将与民宜之者也。 [3]423
为政有大体,以爱民为主,而防患次之,治顽梗、追逋负又次之。使人人见吾此心如青天白日,如和风庆云,时而举其大甚者治之,渐令入吾规矩,始有次第,所谓信而后劳之意也。 [3]265
邑无小大劳佚,惟爱民省费可以得善誉。吾尝诵古人语:“欲致之民,非县令不可速达。”果尽吾心,即为令,胜作守,胜台省,惟有实心者可以语此也。 [3]364
在罗洪先看来,“惠人”是“为政”之本,“政”之所源;因此处理政事的首要原则应该是“与民宜之”,一切政事紧紧围绕“爱民”这一核心,地方行政治理的基本评判标准也应该是“爱民省费”。
2.“为政”首在解决民生“不足”问题
基于阳明学“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 [6]79的基本认识,罗洪先认为,人之作恶,并非良知本性使然,而是由外在条件的影响驱动,遮蔽了良知的结果。因而,只有解决民众基本民生的“不足”问题,才是稳定政治秩序的根本所在。他指出:
夫人之为恶,非必其性成也,要亦有以驱之矣。……三代之制,必有夫田分业定,衣食足,然后责其不肖,虽有非僻之心,不敢肆矣。夫饔餮不给,父子不能保其亲,况众人乎!是故行劫起于攘伐,攘伐起于聚积,聚积起于虑不足。无不足,则乱国之民可使由礼。 [3]38
也就是说,像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上古三代时期那样,使人们“田分业定,衣食足”,真正解决了民生“不足”的问题之后,即便是“乱国”也可以摆脱“行劫”“攘夺”等无序的状况,而代以秩序井然的礼治。
3.“政事”也是“全其良知”的过程
王阳明早就指明:“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 [6]95在他看来,政事作为实学,对于良知之学意义重大,“为政”的过程也就是“致良知”的过程,二者不能剥离为二。阳明后学多有此论,王畿更是专门著《政学合一说》一文予以申论。罗洪先亦抱持此种认识。他说:
夫古之所谓学者,全其良知者也。……诚能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时时、事事致力不懈,将见日精月明,日长月充,火然泉达,勃然不容已矣。是政事乃砥砺锻炼之资,而官府即讲究肄习之地也。而又何疑于致用乎? [3]323
对于一个始终以“全其良知”为目标的士人而言,任何环境与条件都无非是砥砺成就之资,何况政事与官府呢?因而,在官府处理政事,也就是体认“万物一体之仁”的过程,“惠人”“宜民”的实学,也就是著实地“全其良知”的过程。
不仅如此,罗洪先还明确说:学问正在事务中,了得此心,更无闲杂念虑扰乱,即学与政总是一件。 [3]369因为在他看来,“学”乃是“昔人政之所出”:“古者仕不去国,幼而学,壮而行,其政与教,固国人闻见之所及也。取其闻见者而为之师,在上者,不特备物释奠尔矣,自宰邑下,上以至方伯、连率之尊,其乡社饮酒、养老劳农、献馘讯囚之政,必于学焉,意曰:‘此昔人政之所出,吾得无有怠弃乎?’是于政而求其至者所弗容已也。” [3]117政学无二,都在“全其良知”。故而他坦言:“此学是大丈夫事,一切世情道理,兼搭遮饰不得,直心直意,是非一毫自欺不得。” [3]217“夫天文地理,人材吏治,财用粮储,边防兵议,无一而非当世之务,亦无一而非吾性之用。” [3]384
无疑,所谓的“大人之学”、“大丈夫事”表现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都应体现于为政者的“惠人”之政。尽管罗洪先长期乡居但对地方诸多方面的建设都投入极大心力,多有“惠人”之处。他在地理、经济、政治、宗族地方建设乃至军事等“实学”上贡献颇多。确如徐儒宗所说:“综观念庵的经世理论及其实绩,可谓知行合一,名实相符,决非空谈性理者所能望其项背。” [9]363
三、导其自适的行政原则
如前所云,罗洪先认为,为政以惠人乃是一切政事的核心。然而,具体到行政施治过程当中,应采取何种行政原则呢?以儒家之一般认识,当然是首重教化,阳明学诸子的“讲学淑人”正是这一思路的实践。敦行教化这一思路的基本前提是,人性本善,禀有良知,是可以教化的。
敦行教化的过程,对于士人来说,也是一个修治过程,这个修治过程同时具有“为政”的意涵。罗洪先在《与陈子为》中说:“今人笃行甚难,风俗日见污下。贵地近海滨,尚有淳庞意味。执事能朴厚诚实,躬行力学,内而事亲无违颜,外而交友无违心,言信事敬,后辈可视以为法。所谓‘是亦为政’,岂必有名位,然后称得志哉!” [3]344这无疑是孔子以来儒家的一种认识传统。问题在于,基于这种认识传统的教化思路及其实践,混淆了教化主体与客体的区分。教化过程中,作为教化主体的士大夫阶层本身亦有客体的意味,而作为教化客体的普通民众,只有当同时作为修治主体时才算承载了这一教化过程。这里积淀着儒家对教化对象所具有的道德自觉性的充分肯认。基于此,为政者在施治过程中充分发挥、拓展民众的良知本性才是最佳选择。
罗洪先认为:“夫人之为善,性成者上也,教习则其次也,畏威远罪又其次也。旌淑之典不行,而望美俗卓行踵出,难矣!” [3]725因此,他强调行政施治的原则应该是“导其自适”,即顺势而为,充分发挥教化对象所具有的道德自觉性,从而实现至治。他指出:
圣人之为教,非以绳束也,导其自适而已;圣人之为刑,非以迫蹴也,禁其不自适而已。导之不从,始为之禁,大抵约民于生全而休息之,此官师所为设也。 [3]582
“导其自适”是主导原则,以刑为禁只是补充手段而已。这样就会实现“约民于生全而休息之”的“惠人”之政,也是“官师”为政的最基本目标。
具体而言,以“导其自适”为原则,他将施治手段分别为上、中、下三策:
今之为政者,莫善于顺导之,其次检防之,而蹴迫为下。顺导之者,因其所欲而行之者也。人得其所欲,则令易行而患不及,故为善。检防之者,上下相疑者也。疑乎其下,则上之计劳;疑乎其上,则下之智专。专者众而劳者寡,得失半矣,故谓之次。蹴迫者,致期以逃责者也。不胜其弊,而又不能遽更其法,苟且以就之,是谓无策,故为下。 [3]586
“顺导”的施治手段之所以是上善之法,不过是“因其所欲而行之”,事半而功倍,充分调动了施治对象的主体积极性,故而“令易行而患不及”;“检防”的办法,因“上下相疑”,所以得失参半;而“蹴迫”的暴力强制手段,在罗洪先看来,基本等同于束手“无策”,所以最为拙下。况且“蹴迫”的暴力手段如果施用不当,还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夫民激而后为盗,犹牛马失放,而且风势至急也,而操箠夺刍,其何以生?” [3]492所以,就根本而言,罗洪先只认同“顺导”与“检防”二法,且以“顺导”为主,“检防”为辅。
另外,在“导其自适”的行政施治原则下,用“顺导”的办法治理民众,还需要给民众提供一个较好的吏治环境。尽量去“贪残之吏”,减少扰民情况的发生。罗洪先说:“大约去贪残之吏,则民自不扰,上之法令庶可行。若吏贪而无制,未有能宜民者也。” [3]355
如前所述,“导其自适”的行政施治原则,是基于敦行教化这一思路的。在明代,士大夫阶层的教化活动的首要内容,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六条“最高指示”,罗洪先也不例外。他也一再申明说:“我太祖高皇帝教民榜文,以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六者为首务。” [3]564他还发挥说:“宗族邻里,以谦和退让为尚,不可校量是非,久之情意浃洽,争讼自解。盖今人小不能忍,一言之间,据欲求直。报复相寻,毕竟何益!……训子弟,教《诗》、《书》,守道理,为第一事,不得假之声势,诱以利欲。盖年少习惯成性,既长变化甚难,此系家道兴衰不可不慎。” [3]710由此,所谓“导其自适”的行政施治原则,“自适”是“自适”什么便可以明白了,即以明太祖朱元璋“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六条圣谕来“自适”。
把敦行教化充分发挥、拓展民众道德自觉性作为基础,顺势而为,以“导其自适”为行政施治原则,辅以“检防”的刑禁之法,罗洪先心目中雍熙和乐的政治秩序也就形成了。如他在《赠靳两城序》中所描述的那样:“故上有安安之休,则下有浑浑之俗;内有幽玄之德,故外有恬愉之治。” [3]582
四、结语
罗洪先既以良知学为性命,则必然会对社会政治充满关注与忧虑,故其关于政治与行政会有这样的思考:“此学乃终身事,不是一时讲论便可了手,兼关涉世道甚大。” [3]337“窃以为学术之明,不在言说之归一,而在躬行之密实;不在言说之直谅,而在躬行之观磨。” [3]380从“主静无欲”“收摄保聚”的核心学旨到罗洪先的政治思考,由良知学逻辑牵引,再自然不过。无论是他“为政惠人”的政治思想,还是“导其自适”的行政原则,无不体现着罗洪先等阳明学诸子的“行道”激情。反过来说,在政治方面的思考与实践,又是考量一个阳明良知学崇信者体悟、践履阳明学水准的最重要方式。罗洪先便曾明确说过:“闻良知之说,既以自淑淑人,且试之政。” [3]787“且试之政”是把握了良知学“落脚”的实在考量,良知如何,一试便知。
然而我们必需看到的是,罗洪先乃至阳明后学士大夫阶层的政治思考空间是逼仄的。在明代专制王权高压空前酷烈的时代背景之下,他们的思考一方面沉溺于学理性的抽象探讨;一方面究心于具体事务的分析与处理,要求自己“任其职,庶几即有其具” [3]189,而对于专制王权制度本身除给予“高度评价”外,则很少置喙。他们的聪明才智也只能集中于性理良知的“内在超越”之路,寻找自身的价值安顿。这大约是王权专制政治条件下,士大夫阶层政治思考的宿命吧。
注释:
①罗洪先说:“近来见得吾之一身,当以天下为任,不论出与处,莫不皆然。真以天下为任者,即分毫躲闪不得,亦分毫牵系不得。古人立志之初,便分蹊径。入此蹊径,乃是圣学;不入此蹊径,乃是异端。”徐儒宗编校整理:《罗洪先集》卷七《寄尹道兴》,上册,第252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