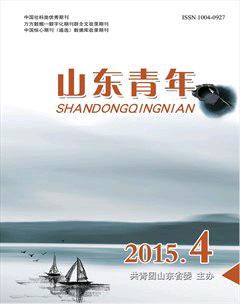略论青少年网络隐私权保护
阎愚
摘要:
鉴于青少年群体的特殊性,他们既容易成为网络侵权案件的侵害人,更容易成为这类案件的受害者。我国当前缺乏对青少年网络隐私权保护的专门立法,仅在《侵权责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文件中对网络隐私权和青少年隐私权保护略有涉及,且存在规定陈旧、责任人界定不清、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因此应借鉴国际相关立法实践,出台专门法律,通过规制网络用户、增加家长权利等方面加强对青少年网络隐私权的保护。
关键词:青少年;网络隐私权;COPPA;家长权利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接受资讯的方式。一条言论可以通过微博、bbs迅速转载,图片和视频在短时间内就会获得大量点击率,由此也衍生出了一种特殊的侵权案件,即网络侵权。青少年作为网络服务的主要使用群体之一,很容易成为这类案件的受害者。其中,侵犯隐私权是青少年最容易遇到的网络侵权行为之一。
一、网络隐私权的界定
“隐私权”,最早指“免受外界干扰的独处权利(right to let alone)”[1],1960年美国学者普劳瑟(William L. Prosser)教授在《隐私权》(Privacy)一文中将侵犯隐私权细化为四种不同的行为:侵入(intrusion)隐居、独处或私人事务;公开披露(public disclosure)令人难堪的事实;宣扬(publicity)以使公众产生歪曲的理解;为自己的利益挪用(appropriation)他人的个人信息。[2]可见隐私所及的范围为个人的生活与个人的信息。
网络隐私权的内容也可以用隐私权的维度界定,即网络生活不受干扰,网络上个人信息的使用与流转不受侵犯。所以干扰、窥探、妨碍他人的网络活动,非法入侵个人的网络空间是侵犯网络隐私权的一种表现,比如用垃圾邮件充斥甚至引爆邮箱,或者破译他人的网站密码。采集、持有、使用或披露[3]他人数据化的个人秘密是侵犯网络隐私权的又一种表现,这既包括侵犯仅存于网络中的各种信息,比如将他人不公开的网络日志公布于众;也包括用网络手段侵犯现实隐私权,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人肉搜索”,即网民使用网络上搜集的信息在现实中干扰受害人的生活。
网络活动时要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这一认知在网络愈加发达的今天看来并不算超前,但对于涉世未深、缺乏判断力的青少年而言,他们对自己隐私权的保护就显得不那么有力了。这一是由于青少年往往缺乏对隐私权的充分认识,容易泄露隐私;二是由于当隐私权受到侵犯时,他们也很可能没有能力甚至怠于去主张权利。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合理的外在手段,比如法律,来保护青少年的网络隐私权。
二、青少年网络隐私权保护的立法思考
无论是青少年隐私权保护,还是网络隐私权保护,在我国都欠缺专门性的立法,相关法规散见于多个法律文件中。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等针对未成年人的立法中有对隐私权保护的涉及,但无论是从立法技术还是规则设置上都略显陈旧;2010年实施的《侵权责任法》虽然承认了对隐私权的保护(第二条),并在第三十六条[4]对网络侵权行为进行了规制,同年施行的《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也用专节对三十六条进行了细化的理解,但从保护青少年网络隐私权的角度看来,仍有缺失之处。
1. 我国青少年网络隐私权保护的立法现状
首先,我国现在尚无法律专门针对网络隐私权,《侵权责任法》只是分别对隐私权和网络侵权作出了规定,这种概括性的立法模式一是过于笼统,缺乏针对性;二是与相关领域的国际立法实践相脱节。
隐私权本就是含义丰富的法律概念,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美国是通过最高法院的若干经典案例括出了隐私权的大致内容,且其内涵还在不断的发展之中。网络隐私权因为网络这一媒介的特性而更加特殊。网络上的信息传播迅速,网络用户遍及世界各地且互不相识,这都使得侵犯网络隐私权远比侵犯现实隐私权容易实现且难以规制。为此,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欧洲即出台了一系列保护网络信息的公约法规,如《个人资料自动化处理时个人保护公约》、《欧盟数据资料保护指令》等,1999年更是出台了《INTERNET上个人隐私权保护的一般原则》,直接针对网络隐私权保护。德国、日本、我国台湾也都有类似的保护网络隐私权的专门立
法。[5]可见,专门针对网络隐私权立法或出台特别条例是网络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一种立法趋势。
其次,现存的专门保护青少年人权益的法律制度在网络隐私权保护问题上均略显陈旧。限于法律出台的时间较早,《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虽然提到了对青少年隐私权的保护,但并未阐明这一权利的范围,对于侵害隐私权的方法和途径也预估不足,比如《未保法》三十九条仅规定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但“披露”显然不是侵犯隐私权的唯一途径。网络环境的特殊性与在网络背景下保护青少年隐私权的特点与难点在这两部“青少年保护基本法”中更是没有提及,因此它们难以成为规制侵犯青少年网络隐私权行为的法律依据。
这一缺憾能否通过地方性的《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弥补?笔者认为这也很难。虽然目前很多学者都主张通过地方性的《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来增加“未保法”的可操作性,可这些地方性法规与“未保法”之间存在下位法与上位法的关系,不能超越上位法的授权而授权,也不能给出上位法没有给出的处罚。但谈到青少年网络隐私权保护,必然涉及到对相关侵权行为的治理。所以,尽管目前很多省市的《未成年人保护条例》都关注到了青少年网络权益,但也只能语焉不详地做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具体的保护方法、权利救济的途径等只能有待专门立法作出补充。
2. 针对青少年网络隐私权保护专门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笔者认为,考虑到青少年网络隐私权保护的特殊之处,为这一权益保护专门立法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endprint
首先,青少年自身的特点使他们更容易成为网络侵权的受害人群。青少年或者尚未走向社会,或者刚刚走向社会,缺乏相应的人生阅历,网络对于他们而言,是一把“双刃剑”。网络方便快捷,能够让他们迅速学到知识,了解社会;但网络带来的不好的内容也使经验和定性不足的青少年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更何况,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网络侵犯隐私权的方法也越来越具有隐蔽性,有些连成年人都难以规避,更何况冲动、判断力不强又难以抵挡诱惑的青少年。因此有必要借助外部手段,特别是法律手段,对青少年的网络隐私权予以特殊的保护。
其次,出台一部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的法律,或者在现有立法中增加专章专节,不但能体现出对未成年人这一弱势群体的特殊关照,而且可以将现有法律中的不足之处于特别法中补全。比如现存立法中均未对网络用户进行规制,但网络用户往往才是直接侵权人,只约束网络服务提供商很可能难以实现对网络侵权行为的控制。这一问题有必要通过更细化的规则加以解决。
再次,出台专门性立法在国际上亦有前例可循,如美国在2000年出台了《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The 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Act, COPPA)要求网站或在线服务运营商只有在符合一定条件的前提下方可取得儿童的个人信息,也要求家长必须参与到儿童的网络活动中来,实施有效的监管,这其实为我国制定专门立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三、完善青少年网络隐私权保护的两点建议
青少年网络隐私权保护是同一名称下两个维度的问题,其一为青少年隐私权的保护;其二为网络环境的管理与规制;这两点近年来均为国家法治建设的重点。2013年10月23日出台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中有数条触及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2014年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特别强调要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为实现这一目标,特别是针对青少年这一特定群体,笔者认为,除了出台专门性立法或在现有立法中补充专章外,还有两点需要注意。
其一,可以仿照欧美立法,增加家长权利,转嫁注意义务。这里的家长,不但指青少年的父母,也包括负有监护义务的其他主体,比如学校。增加家长权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转嫁预防负担的方法,也是我国立法可以思索的一条进路。
事实上,家长是远比网络服务提供商、网络用户侵权者甚至青少年自己更有效的监督者,因为出于对子女的责任,家长会更主动地承担起相应的注意;而相比于其他外在的保护者,家长对子女的保护与监管是最有效且成本最为低廉的。在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COPPA)中就详细规定了父母的同意权、审查信息权和撤销同意终止服务权等家长权利[6],从侧面显示了家长的注意对防范网络侵犯青少年隐私权的重要性。
除家长外,学校也可以承担起一定的注意义务。同家长的监控义务不同,学校保护的侧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法制意识,让他们了解到自身的各种权利以及他们有可能接触到的侵犯权利的各种途径。正如前文所言,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更易受侵害的原因之一在于对法律和权利的“无知”。如果学校能承担起法制教育的责任,就很可能从源头上控制未成年人的网络活动,降低他们受害的可能性。美国2013年修订的COPPA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学校的作用,授予学校同意采集学生信息的权利,只要该信息不是用于商业目的。
其二,增加对网络用户的规制,提高侵权的成本。笔者认为《侵权责任法》三十六条第二款和第三款关于连带责任的规定[7]会使受害人出于便利仅向网络服务提供商求偿而放过直接侵害人,这就降低了侵权人的侵权成本。同样,《解释》第八条明确指出网络侵权适用过错责任原则,[8]第九条规定网络侵权的构成要件包括行为人的过错(故意或过失),[9]这就意味着要由原告对侵权主体的过错进行举证。可在网络侵权案件中,举证难又是原告难以逾越的障碍,[10]增加了原告的诉讼成本,反过来也意味着降低了侵权人的侵权成本,“纵容”了侵权行为的滋长。相反,增加对网络用户的规制,虽然可能技术上难以实现预先阻止侵权,但事后的惩罚会增加网络用户的侵权成本,形成一种威慑,从而从反面控制住来自网络用户的侵权行为。比如,可以通过细化网络青少年隐私权保护的内容为网络用户也增加一个“知道”条款,[11]将需要避开的属于青少年网络隐私内容的信息进行详细的界定,仍然非法获取、使用、披露、侵犯这些信息的网络用户侵权者就是“明知故犯”,在过错认定上会更加清楚。
另一方面,实名制,即在参与网络活动时提供有效的能证明个人身份的证件或资料这一新兴制度也可以用来实现对网络用户的规制。实名制的好处即是使网络用户的真实信息处于一种可得的状态,便于对网络用户的不法或严重不当行为进行追踪。
有学者质疑实名制会冲击网络言论自由权,这一点作者有不同的看法。实名制的确会使原本“肆无忌惮”的网络活动受到约束,但长远来看,实名制的约束会促使网络活动回归理性,从而净化网络环境,结果是保护了更多人的网络权。而且笔者认为,实名制也可根据网站的规模和影响力逐级采用,只在小范围内活跃的网站可以暂缓实名制的脚步。
此外,还需要注意,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由于心理或生理上的不成熟,不但很容易成为网络侵权事件中的受害人,还容易成为此类案件中的侵害者。在虚拟而方便的网络环境里,青少年与外界沟通互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很有可能为了一时的乐趣或好奇就侵犯了他人的隐私。因此,实名制对于青少年的网络活动就尤为重要了。知道自己的不当行为会被追踪,自己的信息真实可得会使青少年在网络活动中保持基本的审慎,从而极大地降低网络虚拟带来的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1]See Samuel D. Warren & Louis D. Brandeis, “The Right to Privacy”, 4 Harv. L. Rev., 1890, p. 193.
[2]See William L. Prosser, “Privacy”, 48 Cal. L. Rev., 1960, p. 389.
[3]“采集、持有、使用或披露”转化自1988年英国《数据保护法(Data Protection Act 1988)》“An Act to make new provision for the regulation of the processing of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individuals, including the obtaining, holding, use or disclosure of such information.”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