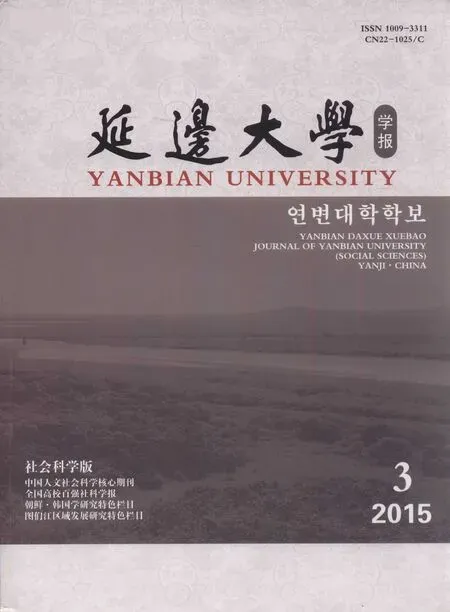东亚秩序与中蒙关系
陈维新
(延边大学 中朝韩日蒙文化研究中心,吉林 延吉 133002)
从过去近百年在世界被边缘化的中国又重新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勇于担当世界责任,直接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设。值此,总结中国以往两千年所走过的辉煌历史,重新认识以中华帝国为中心所开创的历史上的东亚秩序,在与时俱进中守正纳新,赋予以时代内涵,在“一带一路”加“两个走廊”,实现“三位一体”联通的周边战略新框架的形成与实施中,在增添了时代“亲、诚、惠、容”的理念中,在以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战略中,笔者探讨中国与毗邻蒙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丰富内涵,这对密切中蒙关系,实现“三位一体”周边战略和建立国际新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一、东亚秩序与古代蒙古部落朝贡、和亲和成吉思汗的关联
近年来,学者对古代东亚秩序或称东亚体系的发展与变迁研究已成热点。在研究中首先要明确体系,胡波曾提出:“两个以上的国家或类国家单元,在一相对固定封闭的区域内频繁进行剧烈的政治、军事等互动,即形成一个国际体系”。①胡波:《古代东亚体系的中心在北方》,《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27日,A04。而中国北方广袤无垠的大草原正是游牧文明的力量中心。匈奴人、鲜卑人、突厥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等都先后以此为根据地,建立了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与中原政权长期你侵我夺、对峙和争斗。蒙古民族部落的地方政权和后金政权曾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取代过中原王朝。所以,有学者常把在中国北方各地方政权间形成的关系,强调东亚体系中心在北方,其实中国的中原和中原的北方是一个整体,也因此构成了整体与北方各个部分之间的各种关系,也才构成了东亚体系,亦称东亚秩序。
古代的蒙古人与匈奴人、鲜卑人、突厥人、契丹人、女真人一样,是生存在中国地域的一个部落。蒙古人的前身叫室韦,据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阐述:“室韦之名,始见于北魏,系‘契丹之类也’。分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大室韦五部,互不相属,后又分为20余部,分布在东至黑水靺鞨,西邻突厥,南抵契丹,北达于海,今黑龙江上游两岸及额尔古纳河一带。隋初依附于突厥,‘突厥常以三吐屯总领之’,但室韦也直接向隋遣使贡方物;还与高句丽、契丹等邻近诸族多有交往”。①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81页。在唐朝武德八年(625年)和贞观三年(629年),室韦相继向唐朝遣使。贞观三年(629年),唐朝设师州,对室韦采取了羁縻统治,当后来突厥兴起,又处于契丹李尽忠大举反唐之际,室韦与唐朝联系中断了一段时间,而后开始受制于后突厥,由于忍受不了后突厥的凌辱压迫,又恢复了与唐朝的关系,正如《新唐书·室韦传》记载,于“景龙初,复朝南,并请助讨突厥”。开元天宝年间,连年入贡。到了开元十九年(731年)二月,“室韦遣使贺正,授将军,放还蕃”。“十月癸已岭西室韦遣使来朝,赐帛五十匹,放还蕃”。“开元二十年(732年)三月壬戌。室韦大首领薛渤海恍来朝,授郎将,赐帛五十匹,放还蕃”。②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82页。自618年至765年的百余年间,室韦与唐朝的友好关系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不仅室韦朝贡于唐,接受唐朝册封将军、郎将等官职,而且经贸往来也与日俱增,促使室韦部落繁荣发展。虽然“安史之乱”使室韦一度与唐朝断绝关系,但到了762年代宗时期关系又有了恢复。从大历元年(766年)到会昌二年(842年),室韦频频遣使者朝贡,唐朝任命室韦首领和解热素为室韦都督,其间还任命阿朱为室韦都督,接受了大都督阿成等30人朝唐,在此期间,高规格接待室韦大首领都督热伦等15人。到了唐代末年,伴随着社会的动乱,室韦诸部落向西部和南部迁徒,逐渐发展成为蒙古民族的先世一支。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自《尚书》记载的“五服制”与先秦朝贡的雏形,到汉唐朝贡制度的确立,后到宋明清朝贡制度的拓展,几乎都是“厚往薄来”,“怀柔远人”,都凸显“以不治治之”的理念。而到了元朝,蒙古人以华夏正统自居,但其统治区域空前广大。据《元史·地理志一》记载:“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③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第45页。整个元朝的国土面积为3300万平方公里。元朝对统辖的周边各个小国,如高丽、安南、占城、缅甸都在武力的征服下使其称臣纳贡,经遣使招谕的有马八儿、须门那、僧急里、南无力、马兰丹、那旺、丁呵儿、俱蓝等10个海外国家均遣使来华朝贡。元朝贡道大部分贡物的转运全赖驿站之便。据《元史》资料记载,统计共有34个海外国家遣使来华朝贡,朝贡次数达200余次。据不完全统计,元朝贡道驿站的陆站、水站、海站等有1519处之多,是历史上任何朝代所无法比拟的。但元朝纳贡改变了以往中华帝国“厚往薄来”的原则,完全是在武力胁迫下,将朝贡作为聚敛财富的手段,成为强化统治压迫的一种形式,与“怀柔远人”、“德治天下”背道而驰。
元朝统治者招徕海外国家前来朝贡,寻求奇兽珍宝,以满足其奢侈生活的需要,对此当朝御史赵天麟在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的上书中,陈述中华民族历朝历代合民心、顺民意、施惠于天下,才使四夷外国心悦诚服地归附上国。他说:“异物荡心,其害一也;使外国闻之而以国家有嗜好,其害二也;水陆转运,役人非细,其害三也。有三害而无一利,亦何尚之哉?伏望陛下昭播徽声,俾扬遐境。凡四远之纳款者,听书檄奏闻而不求其献物;听子弟入朝而不求其纳贿。若然,则化天下以德,示天下以无欲,将见西番东徼之主君、毳幕灵州之酋长承恩而来享,慕道而来王矣”。④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第49-50页。赵天麟这一番忠言进谏,却未得到世祖的采纳,从此以后元朝逐渐走向衰落。
由于元朝改变了中华民族在此之前历代统治王朝的朝贡本意,从反面给以后的明朝和清朝提供了经验,因此明清两朝恢复了朝贡的“以不治治之”的德治天下的本意,维持了从明朝到清朝360多年的封建统治,又进一步建设了比较稳定的东亚秩序。
东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观念是“和”,以“和为贵”。在中国历史上,“和而不同”一词已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哲学理念。在体现国家伦理方面也比比皆是。其中,“和亲”一词在先秦文献的《周礼·秋官司冠第五》、《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均有记载,这些文献所阐述的是华夏与蛮夷或各诸侯、家庭权力集团之间的往来修好活动,其中并不含有嫁娶姻亲的意思。但是在先秦社会诸侯王室之间,各政治集团之间通婚联姻现象却极为普遍。《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着传说的五帝之一喾玩是搞多元和亲的平衡外交的出色帝王。在周襄王(公元前651—公元前619)时期,襄王想利用戎狄的兵力征伐郑国,就采取了和亲的手段,娶戎狄女子为王后,与戎狄结为亲戚关系,然后与戎狄共同出兵讨伐郑国。这是中国史料记载的最为典型的通过和亲而结盟修好的举措。纵观中国历史,皇帝的女儿有目的的出嫁,特别是忍痛割爱的下嫁、远嫁,促使两个不同民族、不同政治集团,或同一民族的不同政权之间联姻修好;虽然伴随血泪铺就的和亲路,但能化干戈为玉帛,能停止战争,摒弃前嫌,保护了社会生产力,建立了和平、友好、亲睦的关系;和亲所促成的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联盟虽然不会保持长久,但是每个历史时期和亲政策的不断实施,也相对地保持了社会长久稳定的发展。自汉朝大臣刘敬所倡导的主动与匈奴结“和亲之约”开始一直承前启后延续了几千年。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906年,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二十四史记载比较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就有130多例。特别是华夏各民族与蒙古民族和蒙古民族与华夏其他民族和亲的,据《元史》记载,1209年夏襄宗李安全之女,即夏察合公主嫁给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第三女,即蒙古阿刺海别吉公主嫁给汪古部首领不颜昔班;元睿宗拖雷之女,即独木干公主嫁给汪古部首领聂古台;元世祖忽必烈之女,即月烈公主嫁给汪古部首领爱不花;元定宗贵由之女,即也里迷失公主嫁给汪古部孛要合之花;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忽必烈太子真金之女,即忽答迭迷失公主嫁给汪古部首领阔里吉思;元宗王阿只吉之女,即回鹘公主嫁给汪古部君不花之子乔邻察;元宗王兀鲁角寻之女,即叶绵干真公主嫁给汪古部首领术忽难;元宗王奈刺不花之女,即阿实秃忽鲁公主嫁给汪古部首领术忽难;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季女,即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嫁给高丽王世子王愖;1275年,元定宗贵由之女,即巴巴哈儿公主嫁给高昌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元太宗窝阔台孙女,即不鲁罕公主嫁给高昌亦都护纽林的斤;元世祖忽必烈时期,不鲁罕公主之妹,即八卜叉公主嫁给高昌亦都护纽林的斤;1295年,元晋王甘麻刺之女,即宝塔实怜公主嫁给高丽王王謜;元成宗铁穆耳时期,元太宗子阔端太子孙女,即朵儿只思蛮公主嫁给高昌亦都护帖睦尔普化;1316年,营王也先帖木儿之女,即亦怜只班公主嫁给高丽王王焘;1321年,元宗王晃兀帖木儿之女,即桑哥八刺大长公主嫁给汪古部首领马札罕;1325年,魏王阿不哥之女,即金童公主嫁给高丽王王焘。另据《西藏王臣记》记载:蒙古宗王阔端之女,即墨卡顿公主嫁给吐蕃白兰王恰那多吉;元成宗铁穆耳时期,元成宗之姐,即门达干公主嫁给吐蕃白兰王达尼钦波桑波贝;元宗王阔端子启必帖木儿之女,即贝丹公主嫁给吐蕃恰那多吉之子达玛巴拉。还另有《蒙兀儿史记》记载:元宗王兀鲁角寻之女,即叶绵干真公主嫁给汪古部首领术忽难;安西王阿难答女,即兀刺真公主嫁给高昌亦都护纽林的斤;1309年,元晋王甘麻刺女,即阿刺的纳八刺公主嫁给汪古部首领术安;元宗王卜罗出之女,即竹忽真公主嫁给汪古部火思丹;元宗王完泽之女,即奴伦公主嫁给汪古部阔里吉思弟阿里八斛。在《高丽史》中也有记载,如蒙古贵族之女,即也速真嫁给高丽王王謜;1330年,元镇西武靖王之女,即亦怜真班即德宁公主嫁给高丽王王祯;1332年,元宗王伯颜忽都之女,即庆华公主嫁给高丽王王焘;等等。
纵观中国历朝历代这些公主们结成的和亲史,学者在研讨中深有感触地说:“一部和亲史,就是一部悲欢离合的血泪史,她们以柔软的肩膀,似水的柔情,以她们的青春与智慧,以她们的热血与热泪,去充当国家无形的兵戈、城堡与纽带,化干戈为玉帛,为国家,为人民带来和平与安宁,但与此同时,她们也付出了青春,牺牲了爱情,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她们,那些为了中华民族的交流、融合、发展献出了她们情与爱,血和泪,青春与生命,美丽与幸福的和亲公主们!”①李鸿建:《和亲:那些远去的倩影》,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第8页。特别是56个民族之一的蒙古民族,是历史上和亲最重要的民族之一,虽然历史上多种原因使蒙古民族的一大部分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离出去,成为一个独立的蒙古国,但是却使我们倍加感到对蒙古国的亲近。正如习近平2014年8月21日至22日访问蒙古国时被称为是“走亲戚”。②孙广勇等:《习近平到蒙古国“走亲戚”》,《环球时报》2014年8月22日,第1版。走亲戚是有历史根据的。在东亚历史发展中有关和亲的记载很多,和亲不单纯是公主出嫁的问题,其中体现着“和”的思想,表现出交流、融合、友好、共生、共荣、合作发展的战略思想,应该说是东亚秩序的组成部分,与朝贡制度或者说与朝贡政策的效应是相通的。
2014年8月21日,习近平访问蒙古国,《环球时报》同日在“异国风情”栏目中刊登了《蒙古到处都是“成吉思汗”》的报道,可见“成吉思汗”已是蒙古国人民的自信和对民族身份认同的寻求。成吉思汗是留在世界记忆中的13世纪的人物,虽然他“只识弯弓射大雕”,但终究是“一代天骄”。一个时代人物的本质,是一个时代社会关系的总和。历史上,在广袤无垠的欧亚大草原上,历代游牧民族在那里大规模地碰撞和交融、战争与迁徒,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剧:斯基泰、匈奴、突厥、蒙古等马背上的民族所建立的草原帝国风起云涌,以成吉思汗为代表挥舞“上帝之鞭”,掀起横扫欧亚的历史狂澜。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的角逐中,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有了深度交流。可以说,是草原游牧文明对华夏的农耕文明的一次碰撞、冲突、交流与融合。成吉思汗以及忽必烈为保持马背民族横刀立马、骁勇彪悍的雄风,曾一度主张以草原文明取代农耕文明,把农田改成草地养马,却没有真正实施,最终将草原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转为多元一体文化。
元代虽是少数民族统治时期,但主体传承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自1206年成吉思汗(孛儿只斤·铁木真)建国,至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从此中华历史序列中的元朝正式诞生。就其国号而言,在建元诏书中即已提出“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已确认国号取“大易之乾元”之义。③张碧波、庄鸿雁:《华夷变奏——关于中华多元一体运动规律的探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2页。在文物典章制度上,实施文化整合,胡汉同朝共列,取“天下一家”之义。传承中华礼乐文化制度,“儒术有补治道”,“帝中国,当行中国事”,“信用先王之法”,并创造了新的运动规律。另外,在成吉思汗的一生中,我们也可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力量。蒙古人崇拜成吉思汗的金色马鞭。传说铁木真曾经以马鞭指天,发出“让蓝天下都成为蒙古人的牧场”的豪言壮语。他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带领蒙古骑兵征服了将近一半的世界领土,建立了横跨亚欧大陆的蒙古帝国,这段历史直到今天仍然让蒙古人热血沸腾。④白天天:《蒙古到处都是“成吉思汗”》,《环球时报》2014年8月21日,第9版。当然,成吉思汗的穷兵黩武、对外侵略扩张是不可取的。然而,对法先王之道,传承中华礼乐文化,坚持和合之道,以及告诫后人勿忘先辈创业和获取权力的艰辛,体现出中华文化“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理念,这些也是东亚秩序的应有内涵。
综上所述,可见现在的中蒙两国关系有着深刻的文化和历史渊源。
二、东亚秩序与古代“丝绸之路”和蒙古部落发展的关联
东亚秩序是以中国为中心同东亚周边地区及邦国共同构建的东亚发展繁荣的行为准则,而“丝绸之路”恰恰成为了东亚地区及其周边邦国对外交流发展的重要途径,它覆盖地域广阔,推动周边经济、文化发展广远。据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撰写的《草原帝国》一书中所描述的,亚洲高原的天山和阿尔泰山的海西褶皱与喜马拉雅山把突厥斯坦和蒙古利亚包围起来,其中间呈现一片大平原,这就是一片具有典型大陆性气候的亚洲大陆。在这片大平原北部纵向被一片草原带覆盖着,从中国东北部一直连接到克里米亚和外蒙古的库伦(今蒙古国的乌兰巴托)。这片大草原在灌溉地区仍是肥沃的。沿着南蒙古沙漠边上的草原之路,这一路一带改变了草原上的游牧生活方式,使这条路上的绿洲具有一些都市的商业特征。这条绿洲之路,也就是历史所称的“丝绸之路”。其地理走向,在中国境内可分为三段,从长安到甘肃凉州武威为东段,武威以西进入河西走廊为中段,新疆境内为第三段。东段和中段历代变化不大,第三段尤其是葱岭以西的“丝绸之路”,历代的走向都有所变动。据《隋书·裴矩传》记载,天山山脉以北又增辟了一道,称北道。帕米尔高原以西则比两汉时期伸延得更为遥远,西到波斯湾,南至印度洋。在中国北道则从伊吾(今哈密),经蒲类海(今巴里坤湖)、铁勒部(指今萨斯克湖、阿拉湖至乌鲁木齐一带)、突厥可汗庭(今新源西),渡北流河水(今楚河、锡尔河),至拂菻国(即大秦)达于西海(今地中海)。这时期,高昌(今吐鲁番东南)兴起,成了中道的要冲。“丝绸之路”的繁荣也逐渐随着高昌经济文化的发展由南路转到中路,促使丝绸贸易不断繁荣发展。到了唐代(618—907),我国封建经济空前发展,“丝绸之路”也随之有了更大的繁荣。由内地运往西方各国的丝织物品空前增加,动以百匹计,被称誉为“沙漠之舟”的骆驼成了“丝绸之路”的主要交通工具。唐朝为了适应“丝绸之路”发展的需要,除两汉以后的南、中、北三道外,又开辟了两条新的支路,称为碎叶道和热海道。碎叶道在天山山脉以北,是从庭州(今吉木萨尔北)经青海军(今沙弯东)、黑水守捉(今乌苏)、弓月城(今霍城),到碎叶(今托克马克附近)、怛罗斯(今江布尔)的路线。热海道在天山山脉以南,是从龟兹经姑墨、温肃(今乌升)、勃达岭(今别迭里山口)、热海(今伊塞克湖)南岸,到碎叶、怛罗斯的路线。两条路线从怛罗斯西行,可抵西海;南行经石国(今前苏联塔什干)、康国,可达波斯和大食等国。我国某些著名的佛教旅行家,就是取热海道去印度的。而那时,居于天山北麓的交通枢纽是庭州,东联伊州(治今哈密),南抵西州(在今吐鲁番东南),西通碎叶。长安二年(702年),唐朝在此设置北庭大都护府,成为北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龟兹则是天山南麓的重要交通路线,显庆三年(658年),安西大都护府移至这里后,逐渐成为南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两地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两汉到隋唐的千余年间,是“丝绸之路”发展和繁荣的时期。唐代以后,我国政治中心的南移,以及造船和航海事业的发展,促使我国又发展了海上“丝绸之路”,使“丝绸之路”海陆并举,通联周边万邦。周围各邦国和地方政权都借“丝绸之路”之便,发展货物贸易,扩大人员往来、文化交流,促进了周边邦国和地方政权的繁荣发展。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蒙古民族就出现在中国北部,分布在东至黑水靺鞨,西邻突厥,南抵契丹,北达于海,今黑龙江上游两岸及额尔古纳河一带。在隋朝初期,蒙古部落虽依附于突厥,但也直接向隋朝遣使纳贡,有一定的独立性,与高句丽、契丹等邻近诸多民族多有交往,在得益于“丝绸之路”的契丹、高句丽、突厥等部落的发展中,蒙古族各部落均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丝绸之路”所带来的利益。到了宋、辽、金、西夏时期,将蒙古族前身室韦族在北魏以后的不同译名,即唐代的“蒙兀”、“蒙瓦”及宋辽金时期的“萌古”、“漠葛失”、“毛褐”、“盲骨子”、“朦骨”、“毛割石”、“毛褐室”、“蒙国”等统称为蒙古。“蒙古”不只是某一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称谓,而是指整个民族的共同体,特别是成吉思汗最初统辖下的大漠南北,概称为蒙古地区,统称为蒙古人。他们共享着“丝绸之路”所开拓的黄金通道,使大漠南北从贫穷走向繁荣。这促使大漠地区实力不断增强,也给成吉思汗增强了对外扩张统一中原的底气。
历史发展到元朝大一统时期,“丝绸之路”也敞开了西方旅游家来中国进行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大门。其中较有影响的旅游家有马可·波罗、鄂多立克、伊本·拔图塔和尼哥罗·康梯,他们畅通无阻地经由陆上、水上、海上的“丝绸之路”与中国进行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
在元朝时期,因为中国的地理版图特别大,国土面积达3300万平方公里,几乎占全球的一半。因此,在元朝,“丝绸之路”几乎全在中国的境内。陆上的“丝绸之路”是在岭北行省、中书省、甘肃行省、辽阳行省以及察合台汗国辖区。水上、海上“丝绸之路”在中书省、河南江北行省、江浙行省、江西行省、湖广行省辖区。①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第5-6页。“丝绸之路”在成吉思汗对外扩张的征战时作为兵马未到粮草先行的后备补给线,由原本的“丝绸之路”变为战时运送军用粮草之路,战后又变为中央与地方上令下传、下情上报的通信驿站,它与丝绸等贸易货物运送并举。在元朝,“丝绸之路”扩展众多、四通八达。据史书记载,交通驿站有1400多个,而且道路规整,松柏、杨柳夹道,纵横交错,是元朝政治统治的神经脉络、经济动脉,促使元朝经济发展,欣欣向荣。
当时,世界旅游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记载了有关中国大市场的齐备与繁荣。他在游记中写道:中国每天都有上千辆装满蚕丝的马车涌进北方的丝绸中心北京,在北京加工成金丝布又销往各地,特别是四川成都加工的薄绢和蜀锦远销中亚。杭州的商业贸易更加兴隆,商店出售的商品琳琅满目,体现中国特色的生丝、织锦、缎锦遍布商铺,很多阿拉伯人从海上“丝绸之路”乘船到中国杭州,他们带来印度和东印度的香料换取中国丝织品带回南亚和中亚。马可·波罗将杭州这个最繁华的贸易中心称为“东方威尼斯”。①[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193页。在中国福建的两个大港口城市福州和刺桐(泉州),是生姜、良姜、砂糖、胡椒和珠宝最兴隆的交易大市场。当时中国最大的货栈是刺桐,从印度来的大部分商船都到此港,南方少数民族的所有商人都云集于此,可以说是整个元朝时期最大的进口中心。打一个比方说,当时世界各港口出运的商船,如有一艘驶进亚历山大港,那么就有一百艘驶向刺桐,可见其商船往来盛况空前。
中国元朝时期的商货市场与东南亚及南亚市场有着密切联系。此外,元朝大汗的幼支旭烈兀家族在波斯建立的蒙古汗国,又使两国有了密切的交往。为管理好从世界云集于中国的交易大市场,元朝在中部港口和广州形成了商会,此商会超过了佛兰德尔的行会和佛罗伦萨的技术协会。云集在这里的大商大贾,各个腰缠万贯,经营着大宗买卖,财源滚滚,集财如山。中国元朝沿着古老“丝绸之路”与欧洲联系得极为紧密。为确保与欧洲的持久贸易,元朝与沿着“丝绸之路”通往欧洲的相关国家缔结了贸易协定,将大量的生丝、精美的丝织品、绸缎、薄绢和金丝锦缎定期通过商船队运往卡亚尔、加韦里伯德讷姆、锡兰和奎隆等港口停泊卸货;然后又装载着欧洲的豆蔻、肉桂、胡椒、生姜、棉布、平纹细布,以及德干高原的钻石和印度洋的珍珠返回中国。元朝利用古老的“丝绸之路”,促使经贸物流业蓬勃发展。
在历史上,中国人很早就懂得一条道理:要想富,多开路。在13世纪,远东与欧洲相贯通的陆路通道有两条。第一条起于欧洲的热那亚和威尼斯,从钦察汗国到敦煌。这条路的主要驿站有钦察汗国首都萨莱、锡尔河中游的讹答刺和伊塞克湖西的怛罗斯和八位沙衮。伊塞克湖有两条小道可到达中国:一条从伊塞克湖过蒙古的叶密立河、也儿的石河、乌伦古河、哈拉和林,然后到达北京;一条从伊塞克湖西出发,途经阿力麻里、别失八里、哈密,通过甘肃进入中国。第二条是从特拉布松城穿过波斯汗国,经过亚美尼亚最繁忙的港口刺牙思,从塞尔柱土耳苏丹国东境抵达桃里寺,中途的驿站主要有可疾云、刺夷、马里、撒马尔罕、塔什干、吐鲁番、甘肃、哈密、库车、喀什。通过这些“丝绸之路”的不同分支商路,把中国的商品直接运往了欧洲。由于商贸流通发展空前,对商路的需求产生了“马太效应”,元朝在原有的古“丝绸之路”之外,又开辟了一条新的水路,即香料之路。特别是在伊朗关闭欧洲之路的情况下,当时蒙古的波斯汗们则为要经海路去中国的商人和传教士开放了他们的领土。此路一开通,这些商人和传教士可以从桃里寺到霍尔木兹,然后乘船通过塔纳、奎隆进入中国。而中国的丝绸和东南亚的香料则在霍尔木兹卸下,通过波斯蒙古汗国,到达桃里寺大市场,然后运往欧洲的特拉布松和刺牙思港。
元朝继承和开拓了中国汉代以来的古老“丝绸之路”,国运升腾,也滋生了蒙古贵族奢侈腐败之风,特别是宫廷生活骄奢淫逸,文化生活附庸风雅,于铁穆耳皇帝之后已呈现了衰败迹象,最后被驱逐到漠北,成为漠北的一个地方的霸主。尽管蒙古贵族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虽有“土木之变”,但也无力东山再起,明朝实行“景泰议和”,使漠北蒙古地方政权再次与明朝通贡互市。在几百年的互市中,仍然沿着“丝绸之路”通商贸易,不断推动蒙古民族的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
历史发展到清代,游牧于漠南、漠北、漠西的蒙古数百万人被先后统一于清政府。清政府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对蒙古人实行封授爵职、联姻婚娶等羁縻政策。特别是在朝贡互市方面,增进了满、蒙、汉之间的关系,清政府制定了贡市、互市的政策,使蒙古各部王公按期沿“丝绸之路”遣使进京朝贡,既可领取清帝赠赐的丰厚物品,又可在京市出售马驼。在“丝绸之路”沿途蒙古境内各部皆有互市地点。正常的互市让蒙古人的马匹、皮张换回盐、茶、丝绸布匹,既解决了蒙古族所需的生活用品,又方便了满汉人民所需。长期的经济交流和贸易,不但密切了满、蒙、汉之间的友好关系,而且还提高了蒙古地区的生活水平。特别是“丝绸之路”给商品交换提供了方便,汉族人从北京和山西结成商帮,沿“丝绸之路”进入蒙古区域,带去茶、丝绸布匹和日用品,换回畜产品。随着商品的发展,“蒙古地区逐渐有城市的兴起”,使汉民族的农耕文明以强大的正能量改变着游牧民族大草原的面貌。
三、东亚秩序与中蒙合作的价值取向
东亚秩序在与时俱进中,应成为中蒙合作的价值取向。东亚秩序与中国历代的“丝绸之路”是密切相关的。“丝绸之路”,既是周边万邦朝贡之路,又是与各邦国之间的和亲之路;既是丝绸、香料、珠宝等商品往来贸易之路,又是西方传教士向中国传播宗教和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之路。特别是“丝绸之路”对外传播中华文化,学者唐任伍所著的《中华文化中的世界精神》记述了中华文化对朝鲜半岛、越南、日本、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美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广泛传播,使中华文化的政治哲学、经济思想、军事思想、科学技术、语言艺术等直接影响和作用着世界。尤其是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和谐了东西方,和睦了周边万邦,史称“万邦来朝”。可见“丝绸之路”的效应是诸多方面的。可以说,“丝绸之路”是面向世界的政治之路、经济之路、文化之路,是东亚秩序的应有内涵,是东亚秩序的具体表现。
历史上,在中国汉朝的“文景之治”时期,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开创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为后来历代立下了不朽功勋,可以说“丝绸之路”走出了“大唐盛世”,元朝的繁荣,明朝的强盛(尤其杨良瑶下西洋与郑和七下西洋都是可圈可点的),以及清朝的“康乾盛世”。这一切虽说不能完全归功于“丝绸之路”,但在国际社会上“丝绸之路”体现着商品交易,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大发展。从历史的角度这不仅证明了邓小平所讲的,资本主义有市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道理,同时也更深层地揭示了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同样有市场,民族间各部落也同样有市场,华夏农耕文明、女真人的森林文明、蒙古民族的草原文明都有市场的道理,市场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丝绸之路”还告诉我们一条道理:“各国要富,相互要通路”。“路”可以上升为方法论去认识,“方法”这个词在西方则起源于希腊,指沿着道路走的意思,可以理解为遵循正确道路行动。方法的本质是工具、手段,是主体与客体的中介,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说:“手段是一个比外在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犁比犁所造成的、作为目的的、直接的享受更尊贵些。工具保存下来,而直接的享受则会消逝并忘却”。①陈维新:《文章写作方法论》,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页。所以说“丝绸之路”一直从遥远的历史延续下来,应是“更尊贵”。它与东亚秩序一脉相承。
然而,中国元朝时期的“丝绸之路”是以屠杀开路的问题应要反思。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所著的《草原帝国》,在谈到元朝的“丝绸之路”时,强调指出:“这些道路的顺畅,是以大屠杀为代价,是蒙古征服欧亚大陆的客观后果”。②[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195页。元朝以屠杀、战争为手段实现了“丝绸之路”的畅通,而今天恰恰相反,是继承汉、唐、明、清“丝绸之路”的化干戈为玉帛的传统,是以“丝绸之路”为途径,政治上坚持和睦、团结、友好,坚持“亲、诚、惠、容”理念;经济上,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搞合作、共生、共赢、共荣;在安全领域,坚持共同的、综合的、合作的、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以发展为“总钥匙”去维持亚洲的全面安全。为顺应经济、文化全球化,走全球和平发展的繁荣之路,特别要维护中国周边的战略安全,密切我国同周边国家的政治友好关系,加固周边的经济纽带,深化周边安全,密切周边的人文联系,让我国与自己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意识落地生根,让我国周边国家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牢固的地缘战略依托。①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国周边战略新构建》,《求是》2015年第3期,第56页。
中国秉持睦邻、富邻、安邻的理念,建立中蒙好邻居、好朋友的战略伙伴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4年8月21日—22日走访蒙古国,这应是两国人民的大喜事。作为东北亚儒学文化圈的中蒙两国,作为民族间通过和亲具有血缘关系的中蒙两国,作为毗邻经济发展互利互惠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中蒙两国,作为对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都有共同历史记忆的中蒙两国,作为历史上共同享受“丝绸之路”带来福祉的中蒙两国,作为在东亚秩序下共同走过两千多年历史的中蒙两国,彼此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去“守望相助,共创中蒙关系发展新时代”,没有半点犹豫的理由。当然作为邻国,之间磕磕碰碰也在所难免,都是前进发展中的问题,是主流中溅出的点滴水珠而已。特别令人欣慰的是,2014年8月21日—22日,习近平访问蒙古国,发表了自己的署名文章《策马奔向中蒙关系更好的明天》与《守望相助,共创中蒙关系发展新时代》的演讲,还有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提出愿从5个方面提升蒙中关系,即进一步增加互信,扩大两国安全合作,在过境运输和基础设施合作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进一步丰富多边合作的形式和内容,把两国经贸投资合作提升到新台阶。②冯坚、谢开华、王宁:《蒙古国总统:愿从5个方面提升蒙中关系》,《新华每日电讯》2014年8月20日,第8版。同时,中蒙两国还发表了联合宣言,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关于建立和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以及中蒙签署的26项合作文件。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关于建立和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人民日报》2014年8月22日,第2版。双方表示:在政治领域,经贸领域,教育、卫生、文化、人文领域,国际、地区合作以及其他方面,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中蒙的友谊、合作、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积极倡议愿同蒙方加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并对蒙方提出的“草原之路”倡议持积极和开放态度。蒙方也愿意加入“丝绸之路”的合作发展之中。正像习近平主席所讲的,不管蒙方是搭中国的快车或便车都欢迎,“独行快,众行远”。④习近平:《守望相助,共创中蒙关系发展新时代》,《光明日报》2014年8月23日,第2版。蒙古国也是发展中国家。如何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别,也是中蒙两国人民共同奋斗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国际社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产生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为了首先解决周边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国设计的“一带一路”加“两个走廊”、实现“三位一体”联通的周边战略新架构逐步形成与实施,那么,中蒙合作发展将获得更多资源、更强动力、更大空间,将带动东北亚地区的发展有个新的跃升,⑤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国周边战略新构建》,《求是》2015年第3期,第57-58页。最终实现两国平衡发展,共同富裕。
国家间合作要讲互利、互惠、共赢,就要有一个正确的利义观。东亚秩序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价值取向的,坚持利义并举,在利与义产生矛盾时,坚持以义为主。在中华文化的“大同世界”理念下,与蒙古国合作,是“不搞我赢你输、我多你少,在一些具体项目上将照顾对方利益”。⑥习近平:《守望相助,共创中蒙关系发展新时代》,《光明日报》2014年8月23日,第2版。在此借用中华文化智慧化身的诸葛亮南阳武侯祠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辩襄阳南阳”⑦王存信、王仁清:《中国名胜古迹对联选注》,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3页。的内容,用以表达中蒙两国关系,可改为“心在大同,原无论中国蒙古;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中蒙两国携手合作,共同走向世界,在同一蓝天下发挥龙马精神,共同奋斗,共圆中蒙两国之梦。
中国一直秉持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富邻、安邻的理念,决不搞以邻为壑,远交近攻,“己所不欲,强施于人”的那一套把戏。正像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讲的:中华民族是酷爱和平的民族,5000年的文明发展,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观念和传统,因为这是东亚秩序的核心思想在中国历代的不断传承。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对外交往通商,而从未有过对外侵略扩张;执着于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而没有一丝一毫的开疆拓土的殖民主义。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如此,那么还能怀疑未来吗?中国与蒙古国是近邻,蒙古国搭中国发展的列车,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只需政治互信,不必靠域外大国来作保险。
美国把蒙古国当作“第三邻国”,这也是美国搞“亚太再平衡”所走的一步棋,蒙古国也就成为了“地缘政治的活化石”。①王建国:《蒙古与美国关系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第47页。“远亲不如近邻”,近邻近在“近水楼台先得月”,发展是硬道理。中蒙两国只要有坚如磐石的互信、诚信,那么,中蒙两国和谐、合作、发展的航船就会乘风破浪,奋勇前行,一定会迎来中蒙两国最美好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