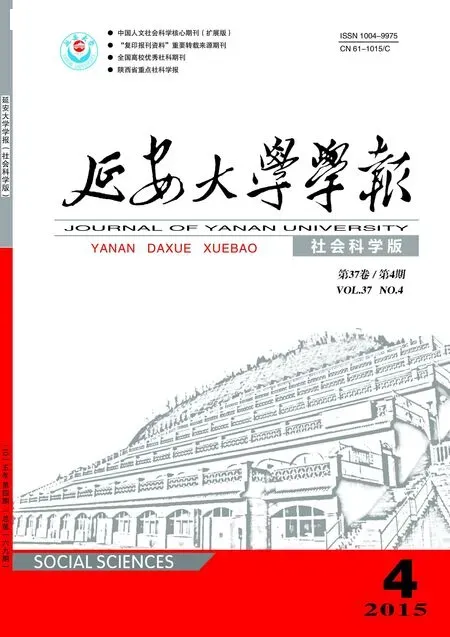论《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的圣经文化成分
郭先进
(凯里学院外语学院,贵州凯里556011)
■外国文学研究
论《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的圣经文化成分
郭先进
(凯里学院外语学院,贵州凯里556011)
奈保尔小说《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有着清晰的圣经文化的印记。小说大量地征引了《圣经》的原型场景、原型人物、U型叙事结构和苦难及虚无主题,将深沉的历史感与强烈艺术感统一起来,更好地展示了20世纪30年代特立尼达社会底层“边缘人”的生存境遇和社会现状。
《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原型场景;原型形象;U型结构;苦难与虚无主题
瑞典文学院在2001年年度诺贝尔奖授奖辞中指出奈保尔小说中“边缘人的形象占据了伟大的文学一角”[1]。的确,奈保尔创作了许多“边缘人”的形象。尤其是,奈保尔在《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中融入《圣经》的原型场景、原型人物、U型叙事结构和苦难与虚无主题等元素,凸显“边缘人”的形象、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特立尼达社会状况,取得了不同寻常的艺术效果。
一﹑原型场景
小说中场景的设置和描写是小说家渲染气氛、表达情感和呈现作品主题的常用手段。在《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中有着最为典型的《圣经》原型场景——失乐园。《圣经》中《创世纪》详细记录了人类先祖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过程:亚当和夏娃无忧无虑地生活在青草葱葱、绿树茵茵的伊甸园,后来,亚当和夏娃因受化身成蛇的撒旦的诱惑偷食上帝所禁的智慧果而被诅咒,从此失去了乐园,劳苦度日。奈保尔在小说的第一章对失乐园原型场景有直接呈现。毕司沃斯先生诞生之日,梵学家预言其将给他的父母带来灾难,尤其是会给父亲带来厄运。果不其言,父亲因潜入水塘寻找毕司沃斯先生和丢失的小牛而不幸身亡。当他的父亲去世后,他们的邻居达哈里强行进入庭院挖掘传闻中毕司沃斯先生的父亲拉格胡埋在花园中的财宝。当达哈里在花园里挖掘寻宝时,毕司沃斯先生的哥哥普拉塔普把他比作一条蛇。最后,母亲不得已卖掉这座院子。“结果毕司沃斯先生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他惟一有些权力的房子,在以后的35年里,他只得成为一个漂泊者,辗转在没有一处他可以称为是自己的地方”。[2]36不难看出,这个场景与《圣经》中失乐园场景极其相似。评论家蒂姆对小说中原型场景的描写发表了独到的见解,“小说开篇题为‘田园诗’,随着‘蛇’入侵花园这件事情的发生,意味着毕司沃斯先生童年伊甸园般生活的终结。虽然其出生的西印度社会一开始就显示出衰减的状态。但对毕司沃斯先生来说,它仍旧不失为一个乐园,因为它至少是一个给毕司沃斯先生带来归属感的地方”[3]74。像亚当和夏娃一样,毕司沃斯先生被迫离开家园之后,遭受了各种磨难。在某种意义上讲,小说这部分用《圣经》中失乐园的场景来比照像毕司沃斯先生一样众多的特立尼达印度移民后裔的生存境况,意在表明,这些特立尼达的社会的“边缘人”命中注定只能是无根的漂泊者。
另外,在小说第二部分第三章“矮山的冒险”中,奈保尔再次呈现了一幅失乐园原型场景。在矮山,毕司沃斯先生第二次设法筹资建造了他的房子。毕司沃斯先生一家搬了进去,他甚至把母亲贝布蒂也接了过来。一个下午,当毕司沃斯先生推着自行车回家时,“在落日的余晖中,在这伤感的薄暮中”,他看见母亲在花园里锄地,感觉到“那个花园仿佛是他许久以前熟识的,时空消失了”[2]425。这个场景唤起了他对过往花园的记忆。虽然房子不是十分令人满意、环绕房子的灌木丛弥漫着蛇的气味,但至少是一个临时安身之处。毕司沃斯似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园,找到了身份和归属。然而,好景不长,房子不幸被烧毁,离厨房二十码之处发现了一条蛇。显然,此处的场景与失乐园原型场景有着紧密的联系。有论者认为,从奈保尔此处对失乐园原型场景的借用,不难看出作家悲观地使用神话原型场景来比照20世纪30年代特立尼达的社会情形,力图暗示在特立尼达重新找回乐园是不可能的。[3]78
可见,奈保尔在小说中精心借用《圣经》的原型场景艺术地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特立尼达社会现实,还原了特立尼达社会底层“边缘人”的生存处境。
二﹑原型形象
《圣经》中原型形象——撒旦,在《创世纪》中化身成蛇引诱了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在《新约·启示录》中化身成龙与天使争战。可见,撒旦与蛇为一体。西方传统观念将蛇视为撒旦的化身。后世文学作品中的撒旦形象一般可归为两类:一是十足的魔鬼形象,二是具有叛逆精神的反抗者形象。撒旦作为反抗者的形象在英国第一个基督教诗人凯蒙德﹑17世纪英国诗人弥尔顿和浪漫派诗人拜伦的诗作中得到生动展现。显然,奈保尔延续了这个传统,借用撒旦原型形象,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反抗者”——毕司沃斯先生。
在毕司沃斯先生入赘图尔斯家族、入住哈奴曼大宅之前,哈奴曼大宅呈现出安宁的氛围。哈奴曼大宅是由图尔斯太太和妹夫赛斯建立起来的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女主人公图尔斯夫人被称为“老女王,是世界的中心,她执行惩罚和赏赐。两位“神”——图尔斯夫人的两个儿子,享有特权和奢华,生活非常舒适。女儿们和孩子们负责家庭清洁,在商店工作,丈夫们,在赛斯的监督下,在图尔斯的土地上劳作。“作为工作的汇报,他们有食物吃和有地方住,也有一点酬劳;他们的孩子也还有人看管;……他们的名字已经被遗忘了;他们成为图尔斯家族的一部分。”[2]93毕司沃斯先生入赘图尔斯家族、被限制于哈奴曼大宅,对这种不平等关系进行抵制和反抗。毕司沃斯先生反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宣传平等的价值观,如男女平等和自由选择;二是拒绝赛斯安排的工作。当赛斯意识到这些观念的力量和行为对图尔斯家族的潜在威胁,因而惊恐地向图尔斯太太说道:“这个房子已经是个共和国了。……黑暗的时代终于来了。姐姐,我们接受了一条毒蛇。”[4]的确,毕司沃斯先生已构成图尔斯太太专制统治的直接威胁。[5]但是,毕司沃斯先生没有任何经济独立的能力。他对图尔斯家族的反抗注定要失败。
对于图尔斯家族中这种统治方式和毕司沃斯先生的反抗斗争,西印度群岛大学教授戈登·罗莱见解可谓一语中的。他指出,毕司沃斯先生的反抗与他在哈奴曼大宅的处境和哈奴曼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有着紧密联系。在哈奴曼大宅,图尔斯夫人和赛斯进行专制统治,作为家族成员的女婿和女儿没有自由支配自己的权力。“奈保尔的毕司沃斯先生反抗的原因在于他置身的社会否认他的个性,并强迫他接受自己卑微地位及其存在的微不足道。”[6]无独有偶,也有评论者认为,毕司沃斯先生所反抗的是任何否认自由和尊严的价值体系。[7]从小说中对哈奴曼大宅等级社会的描述和赛斯的话语“黑暗的时代终于来了。姐姐,我们接受了一条毒蛇”可以看出,作家奈保尔把毕司沃斯先生类比成《圣经》中的撒旦。但是,在塑造毕司沃斯先生这人物时,奈保尔并不是对《圣经》原型形象生硬地嫁接或笨拙的模仿,而是被注入了现时的气息,并赋予人物多重性格,最终化为原型的某种变体。
小说以撒旦形象为原型,将其反抗精神作为主人公最优秀品质加以呈现,展现其生命的坚韧;小说以艺术的方式对身处底层“边缘人”斗争经历再现,展现作家深切的人文关怀。
三、U型叙事结构
在小说中,奈保尔不仅借用《圣经》中的原型场景、人物,还直接借用《圣经》中U型叙事结构。原型批评理论家弗莱发现,整部《圣经》,“它被包含在在这样的U型故事结构之中:在《创世纪》之初,人类失去了生命和生命之水;到《启示录》结尾处重新获得了它们”[8]220。
小说的叙事结构“主人公出生给家人带来灾难、被迫离家——入赘图尔斯家族、四次迁徙和两次建造房子失败——住进自己房子”正好与《圣经》中U型曲线契合。毕司沃斯先生在父亲去世、离开部分属于自己的房子、经历求学和短暂学徒生涯之后,入赘到图尔斯家族。他一生历经磨难,历经四次迁徙和两次营建自己房子的失败。第一次建造房子是在捕猎村经营商店失败后被谴往绿谷作为一名监工的任期内。因为绿谷的营房破败不堪,臭气熏天,并且和种甘蔗的劳工住在一起,所以,毕司沃斯先生感到居住不便利,也没有安全感。他决定存钱准备建造一个所属于自己的房子。最后他花了一百多美元,建成的却是一座无法居住的房子。在一个暴风雨之夜,房子被毁、毕司沃斯先生身患重病被抬到哈奴曼大宅。至此,其人生跌入最低谷,小说的叙事进程也达到U型的最低点。遭遇此经历之后,毕司沃斯先生前往西班牙港妹夫家串亲戚,因机缘凑巧和写标牌的特长“让他在《特立尼达守卫者报》报社找了一份工”[2]324。因图尔斯家族要搬到郊区乡村矮山,并把西班牙港的房子和商店分别卖掉或出租,毕司沃斯先生掏出自己一些积蓄在矮山建了一所与原先模式相仿的木房子,但不幸被孩子们烧荒的野火毁于一旦。回到西班牙港之后毕司沃斯先生一家重新住进图尔斯家族的房子。没过多久,毕司沃斯先生和儿子阿南德冲撞了刚从国外回来的图尔斯太太的儿子奥华德。最后,他只好离开,在仓促中花光了一生积蓄买了一所有许多缺点的房子。但无论如何,毕司沃斯先生最后还是拥有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房子。另外,小说结尾处交代毕司沃斯先生的儿子阿南德和女儿赛薇都在国外即将学业有成,预示着家庭将得以拯救以及未来美好生活的召唤。到此,小说叙事进程又回到新高。不难看出,小说叙事结构是比较典型的U型叙事模式。
《圣经》这个大的U型结构又包含许多小的U型结构。例如,《士师记》的U型模式:以色列人不听从上帝指示陷入磨难境地,然后受到启发,进行悔过,最后受到上帝的恩惠得以解救。同样,《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各个部分故事的叙事结构也基本上属于U型模式。例如,小说第一部分第二章“在去图尔斯家之前”。毕司沃斯先生和母亲在父亲去世后投奔姨母塔拉。在塔拉的帮助下,跟一个叫杰拉姆的梵学家做学徒。虽然学习的内容枯燥无味,有时受到一些训斥,但至少生活有着落。有一次,他经不住诱惑偷吃一个别人送给梵学家的尚未完全成熟香蕉,被发现后被罚连续吃完了剩下的香蕉。结果到了晚上,因为拉肚子、害怕一个人去上厕所,毕司沃斯先生就把排泄物包在手帕后扔向窗外,结果弄脏了一棵圣树,被杰拉姆辞退。在绝望之际,再次被姨妈塔拉收留作为一名店员学徒。毕司沃斯先生在与命运的抗争屡屡遭受磨难之际,总有一些机缘凑巧和幸运使他度过难关。这种U型模式成功地将其波折起伏的人生经历联结在一起,并在结尾处达到高潮。
不难看出,源自《圣经》的U形叙事结构在小说中得到明显而巧妙的运用。U形叙事结构够不仅展示了“边缘人”毕司沃斯先生曲折起伏的人生经历,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彰显了善恶冲突观和信念价值。
四、苦难和虚无主题
奈保尔在小说中借鉴和化用了圣经的思想传统手法,《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透露出与圣经母题相关的主题,如苦难、虚无和堕落等。“圣经中描绘了无数苦难的例子,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它们来自战争的破坏、疾病的创伤、巨大的肉体痛苦、被拒绝陷入孤寂的心态、精神上遭遇的种种折磨,乃至民族信仰体系的毁灭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9]136其实,“圣经就是一部纪录犹太民族苦难历史的典籍。”[9]137在小说中,作家不遗余力地对主人公毕司沃斯先生的苦难经历进行书写。例如,小说开篇可见一斑。作家描绘毕司沃斯先生的出生情形似乎表明其诞生只是为了感受活着的痛苦。他的身体常常没有清洗,变得“沾满污垢”,营养不良使他感染“湿疹和脓疮”,在他身上留下火山一样的伤疤,营养不良还阻碍了他的发育,使得他“鸡胸和瘦骨伶仃的四肢,”和“一个隆起的腹部”。[2]17
除了以细节描写刻画毕司沃斯先生苦难的经历之外,小说还多处用隐喻的手法来呈现其生存艰难的处境。例如,在小说第一部分的第五章,在描述毕司沃斯先生和儿子阿南德被困在风雨飘摇的﹑刚刚建成的木房子时窘况时,作家采用了隐喻的手法。在暴风雨袭击木房子之际,阿南德看见“有一个东西落在他的附近。那是一只长着翅膀的蚂蚁,它的翅膀已经折断,它蠕动着,仿佛不胜翅膀的重负。这些蚂蚁只有在暴风降临的时候才出来,而且很难在暴风雨中存活下来。当它们落下来以后就再也不能飞起来了”。[2]287此处,蚂蚁无疑是一个绝佳的隐喻:因为暴风雨中与风雨搏击的蚂蚁形象与毕司沃斯先生并无二致,两者都不甘向命运屈服,用自己脆弱“翅膀”向强势反抗,至死都怀揣着“飞起来”的梦想。显然,蚂蚁悲惨的命运就是毕司沃斯先生历经磨难、悲苦人生的比照:为了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毕司沃斯先生从精神到肉体都被无情地蹂躏。小说通过叙述毕司沃斯先生这样一个小人物的人生起伏,向读者展示了20世纪30年代特立尼达普通民众或移民的苦难和对安定生活的追求。同时,主人公的苦难经历也是整个特立尼达印度移民的缩影。
《圣经》中包含着空虚﹑虚无的思想,以《传道书》最为典型。《传道书》一开篇就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10]它透露出悲观的情绪。其实,小说中多处出现虚无的字眼,弥漫着空虚、虚无情调;生活的虚无感笼罩着毕司沃斯先生,如影随行,使他常常感到透不过气来。在小说第一部分第三章“图尔斯家族”,奈保尔对毕司沃斯先生入赘图尔斯家族之后,因人际关系紧张、丧失个人独立性而产生的不安和空虚感进行多次描述:“他害怕的未来降临在他身上。他陷入了空虚。[2]224即使每次逃离图尔斯家族、在外遭遇厄运又不得不回来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在自我矛盾、个人与他人矛盾的夹击下,自欺欺人,人格产生内在分裂。虚无感也不期而至。在殖民地特立尼达看不到希望,毕司沃斯先生经常萌发逃离的念头。他想逃离图尔斯家族,逃离开特立尼达。他始终未写完的小说《逃离》潜在地暗示他出逃心迹。“主人公上当受骗结了婚,为家庭所累,他的青春耗尽了,他遇到一个年轻的姑娘。她身材苗条……身穿白衣。她新鲜、温柔、没有被亲吻过;而且她无法生育。见面之后,故事就没有了下文。”[2]346毕司沃斯先生总是徒劳地打出一页相似的开头和差不多的情节之后,便不了了之。这是其逃离无情空虚的方式。尤其是小说第二部分的第五章标题是“虚空”,重点描述了毕司沃斯先生在工作上和与图尔斯家人交往中经历挫折所带来的痛苦和无休止的折磨,使他经常处于一种虚空状态。
毕司沃斯先生作为身处社会底层的印度移民后裔、一个“边缘人“,对于他来说,是无路可逃,无处可去。因为,“这是一个处在权力和繁荣边缘的社会。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就像奈保尔经常感觉到的那样,认为生活是不真实的、徒劳的”。[11]不难看出,作家通过对“苦难”和“虚无”主题的阐释,向读者展示了作为“边缘人”个体生命的生存的痛苦和精神危机。
五、结语
评论家布鲁斯·金曾言,“奈保尔将欧美文学模式以及来自《圣经》、詹姆斯·乔伊斯和马塞尔·普鲁斯特作品中的典故与特立尼达的社会历史融合在一起,创造一种与欧洲风格不一样的小说”[12]。换言之,奈保尔在《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中对《圣经》的借用主要表现在将《圣经》原型场景、原型形象、U型叙事结构等元素都化成复杂的隐喻和象征,将深沉的历史感与强烈艺术感统一起来,更好展示了20世纪30年代特立尼达社会底层“边缘人”生存境遇和社会现状。圣经文化在小说中的积淀极大地加深了该作品的表现力和文化意蕴,增进了小说的叙事效果。
[1]瑞典文学院200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J].阮学勤,译.世界文学,2002(1):134.
[2]V.S.奈保尔.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M].余珺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3]Thieme,John.The Web of Tradition:Uses of Allusion in V.S.Naipaul's Fiction [M].London: Dangaroo Press,1987.
[4]Naipaul,V.S.A House for Mr.Biswas [M].London: Deutsch,1961;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1969:123-124.
[5]Cudjoe,Selwyn.V.S.Naipaul:A Materialist Reading [M].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8:55.
[6]Gordon Rohlehr.The Ironic Approach: The novel of V.S.Naipaul,in Robert D.Hamner,ed.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V.S.Naipaul [M].Washington,D.C.,Three Continents Press,1977:187.
[7]Ganjewar,D.N.Philosophic Vision in the Novels of V.S.Naipaul [M].New Delhi: Adhyayan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2008:93.
[8]诺思洛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
[9]邱业祥.圣经关键词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
[10]The Holy Bible:King James Version [Z].New York: The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1991:608.
[11]Timothy,Weiss.On the Margins: The Art of Exile in V.S.Naipaul [M].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2:60.
[12]King,Bruce.V.S.Naipaul [M].Houndmills,Basingstoke (UK): The Macmillan Press Ltd.,2003:45.
[责任编辑 王俊虎]
I054
A
1004-9975(2015)04-0082-04
2015-05-09
2011年贵州省教育厅规划课题“反讽·语用·圣经文化——小说《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文本多重解读”(11ZC060)
郭先进(1973—),男,湖南汉寿人,凯里学院外语学院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