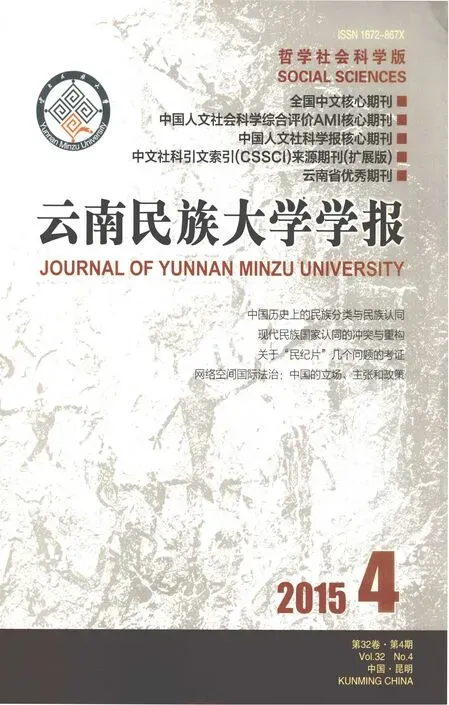网络空间国际法治:中国的立场、主张和对策
黄志雄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湖北武汉,)
当前,国际法在网络空间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网络空间国际法治的观念已经得到广泛接受。不过,由于各国对于网络空间的认识和相关实践还较为有限,也由于意识形态、价值观以及现实国家利益等方面的差异乃至对立,网络空间国际法治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国家正在围绕网络空间国际法规则的制定和适用开展激烈的博弈。在此背景下,梳理、总结中国在网络空间国际法治中的立场和主张,提出我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对话和立法进程的相关对策,对于提升我国在网络空间国际秩序构建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网络空间国际法治的发展与现状
“网络空间”(cyberspace),是指包括互联网、电信网络、计算机系统和嵌入式处理器、控制器组成的相互依赖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通常,这一术语还包括真实的信息环境和人们的相互交往。①The White House,Cyberspace Policy Review:Assuring A Trusted and Resilien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http://www.whitehouse.gov/assets/documents/Cyberspace_Policy_Review_final.pdf,last visited on 12 December 2014.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下形成的网络空间,已成为人类生活的一个新空间,即陆地、海洋、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之外的所谓“第五空间”。
尽管网络空间已经对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国际法在网络空间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和“网络空间国际法治”的提出,是比较晚近的事情。迄今为止,关于网络空间秩序与规则的讨论,大体经过了从“自我规制”到“国内法治”、再到“国际法治”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演变。
从互联网的发明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网络空间通过各种技术标准及行业准则进行“自我规制”和自发、自治发展的阶段。互联网所体现出来的开放、扁平、无中央权威的网络体系结构,因其异常良好的可扩张性和对于各种创新行为的包容性而焕发出巨大的活力。②申琰:《互联网与国际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页。因此,在互联网产生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居于主导地位的观念是将网络空间视为一个自由放任的“自主体系”、反对将现实世界的各种政府管制延伸到网络空间,美国网络活动家约翰·巴洛发表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就是这一观念的突出表现。③John Barlow,A Cyberspace Independence Declaration,8 February 1996,http://w2.eff.org/Censorship/Internet_censorship_bills/barlow_0296.declaration,last visited on 5 October 2014.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00年是各国纷纷制定相关国内立法和政策、网络空间走向“国内法治”的阶段。随着网络用户群的急剧扩大和用户成分的日益复杂,网络侵权、网络病毒和黑客攻击等各种不法行为以及安全威胁不断涌现,网络空间“自我规制”下的自由放任状态已经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网络空间所谓“国家回归”的态势日益明显,国家越来越多地通过制定各种国内立法和政策参与网络空间治理。例如,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和互联网技术最为发达的国家,它一方面长期倡导“互联网自由”,另一方面也是网络安全立法方面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特别是“9·11事件”以来,美国先后通过了《爱国者法》、《国土安全法》、《保护美国法》等法案,对互联网加以更为严密的监控。①尹建国:《美国网络信息安全治理机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法商研究》2013年第2期。
21世纪10年代以来,网络空间开始进入一个相关国际立法逐渐强化、“国际法治”蔚然兴起的新阶段。主权国家进入网络空间并成为网络活动的重要主体,使现实世界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开始向网络空间延伸,这必然要求国际法在网络空间的秩序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代信息传播与交流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国家对网络信息传播的监控和管理,必然会带来网络言论自由和隐私权保护的国际法问题;由于网络空间跨越国界、全球联通的特点,即便一国对其国民利用其领土范围内的网络基础设施从事的网络行为加以监控和管理,往往也会产生超出该国领土之外的效果和影响,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国家主权及相应的管辖权应当如何适用于网络空间?这些问题涉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国家的权利义务,不可能由各国通过其国内法单独加以解决,而必须依照各国共同制定和遵循的国际法规则来解决。
网络空间国际法治的兴起,与当代国际关系法治化的发展趋势相吻合。美国著名国际法学者路易斯·亨金曾经指出:“在各国的关系中,文明的进展可以被认为是从武力到外交、从外交到法律的运动。”②Louis Henkin,How Nations Behave:Law and Foreign Policy(2nd editi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p.1.正如国家的活动范围进入空气空间、外层空间等领域后,催生了空气空间法、外层空间法等国际法新分支一样,国家在网络空间的存在,也需要有相应的国际法规范来调整各国在网络空间的活动。同时,这一发展也反映出现代国际法与科学技术紧密结合的重要特征,即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进展,人类的生存空间和活动天地随之扩大,国际法的调整范围和领域也随之扩大。③贺其治、黄惠康主编:《外层空间法》,青岛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于网络空间的国际法问题关注和研究较早,并率先就国际法在网络空间的适用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主张。在2011年出台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中,奥巴马政府第一次提出了“网络空间法治”概念,并强调:“长期存在的在和平时期和冲突中指引国家行为的国际规范也适用于网络空间。”④The White House,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Cyberspace:Prosperity,Security,and Openness in a Networked World,May 2011,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international_strategy_for_cyberspace.pdf,p.9,last visited on 21 December 2014.尽管美国的上述立场是从维护其本国利益的角度出发,其有关国际法如何适用于网络空间的主张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总体而言,主张国际法适用于网络空间反映了网络空间国际秩序构建的客观需要,也符合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
正因为如此,进入2013年以来,国际社会已经就这一问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这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6月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达成的一份共识性文件。该文件指出:面对恶意使用信息和通讯技术造成的威胁,必须在国际层面采取合作行动,包括就如何适用相关国际法及由此衍生的国家负责任行为的规范、规则或原则达成共同理解;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宪章》的适用,对国际维持和平与稳定及促进创造开放、安全、和平和无障碍的信息和通讯技术环境至关重要。⑤Se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Report of the Group of Governmental Experts on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24 June 2013),Sixty-eighth session,A/68/98,para.11,paras.19-20.之后,2013年“伦敦进程”首尔会议通过的《首尔框架和承诺》也以基本相同的措辞,重申了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上述文件中有关国际法适用于网络空间的共识。⑥Seoul Framework for and Commitment to Open and Secure Cyberspace,http://www.mofat.go.kr/english/visa/images/res/SeoulFramework.pdf,last visited on 7 December 2014.由此,网络空间的秩序构建离不开国际法的适用,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观念。
二、中国在网络空间国际法治中的处境与地位
应当看到,与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大多数领域相比,网络空间国际法治仍处于起步阶段。简言之,由于各国对于网络空间的认识和相关实践还较为有限,更由于意识形态、价值观以及现实国家利益等方面的差异乃至对立,国际社会对于网络空间国际法治的具体主张 (包括哪些国际法规则应当适用于网络空间、这些规则如何适用于网络空间等等)仍存在很大分歧。
美国等西方国家较早地认识到:全球联通的网络空间可以成为传统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重要渠道。因此,它们通过倡导“互联网自由”和“网络空间法治”积极开展“网络外交”,对坚持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进行价值观和规则打压。互联网发展迅猛而又奉行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中国,首当其冲地成为西方国家施压和发难的对象。反过来说,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法治,首先是出于“被动应对”西方国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施压和发难的现实需要。
2010年“谷歌退出中国事件”,堪称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法治的一次“前哨战”。①黄志雄、万燕霞:《论互联网管理措施在WTO法上的合法性——以“谷歌事件”为视角》,载孙琬钟主编:《WTO法与中国论丛 (2011年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277-294页。2010年初,互联网巨头谷歌公司借口受到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和中国政府限制互联网言论自由,试图通过威胁退出中国市场迫使中国政府改变现有互联网管理政策。在该事件中,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国际法 (特别是国际人权法上有关表达自由的规定和WTO法上有关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规定)为依据,对我国互联网监管措施加以批评。中国政府也多次针锋相对地发表声明,强调中国依法管理互联网,有关管理措施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并“坚决反对将商业问题政治化”。②《国新办网络局负责人就谷歌退出中国内地发表谈话》,http://news.china.com.cn/txt/2010-03/23/content_19661008.htm.在2010年6月8日发表的《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中,中国政府进一步提出:“互联网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互联网属于中国主权管辖范围,中国的互联网主权应受到尊重和维护”;“中国恪守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应履行的普遍性义务和具体承诺义务,依法保护外资企业在华合法权益,并积极为在华外资企业依法开展与互联网相关的经营业务提供良好的服务”;“依法保障公民在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③参见《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 (2010年6月8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6/08/c_12195221.htm。这些政策宣示,初步展现出中国对于网络空间国际法治的基本主张。
围绕网络空间国际秩序构建和规则博弈的分歧,也与各国现实国家利益的争夺密切相关。这是因为,随着互联网发展为各国以信息化方式运作的金融、商贸、交通、通信、军事、思想文化等系统的神经中枢,信息网络正在成为与土地及其他有形资本一样重要的权力资源,对国家实力、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④申琰:《互联网与国际关系》,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前言第1-3页。而在网络空间确立和适用何种国际法规则,直接关涉各国对信息网络资源的控制和支配,关涉各国在网络空间国际秩序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并反过来对现实世界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产生影响。
中国与西方国家围绕网络黑客问题的纷争,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点。中国是网络黑客攻击的主要受害国之一。但是,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和媒体出于树立“假想敌”的需要,持续炒作所谓的“中国网络威胁论”,大肆渲染来自中国的网络黑客攻击,甚至指责中国政府和军队从事通过互联网窃取外国公司商业机密的行为,并主张受害国可以援引《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的自卫权,通过单边军事行动来应对特定的网络攻击。对此,中国政府在《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中明确提出“反对任何形式的网络黑客攻击行为”,并在其他场合一再对西方国家无中生有地的指责加以否认和驳斥。中国还作为共同提案国之一,在2011年9月向第66届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一份《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呼吁制定相关国际规则来规范信息和网络空间行为;提出“不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包括网络实施敌对行动、侵略行径和制造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主张“在涉及上述准则的活动时产生的任何争端,都以和平方式解决,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①中国外交部:《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tytj_611312/zcwj_611316/t858317.shtml.
2013年的“棱镜门”事件,更是对各国围绕信息安全问题的博弈产生了深远影响。根据2013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局承包商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叛逃引发的“棱镜门”事件,美国依仗其互联网技术优势和对网络资源的垄断,长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进行持续和大规模的监听、窃密行为。对此,中国政府重申中方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网络安全问题,反对任何形式的黑客和网络攻击行为。②中国外交部:《2013年6月13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http://www.fmprc.gov.cn/mfa_chn/fyrbt_602243/t1049998.shtml.同时,对于美国极力对其网络情报活动和所谓网络经济间谍加以区分、认为前者符合国际法而后者违反国际法的主张,中国政府强调反对一切形式的网络攻击,反对一些国家在网络安全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并再次倡议各国通过制定网络空间的国际规范和行为准则,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③中国外交部:《2013年6月25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http://www.fmprc.gov.cn/mfa_chn/fyrbt_602243/jzhsl_602247/t1053144.shtml.
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网络空间的核心利益攸关方之一。中国在1994年获准加入互联网,并在同年4月完成全部中国联网。在此后的二十年中,互联网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目前,中国互联网是全球第一大网,网民人数最多,联网区域最广。网络空间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的走向,与我国未来的发展空间休戚相关。换言之,我国在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博弈中所处的地位,关涉我国在未来网络空间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和权利,因而也将直接关系到我国在网络空间这一人类社会“第五空间”中获得的资源和权益。
围绕着网络空间的国际秩序构建和规则博弈,形成了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为一方和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国家为另一方的两大阵营。由于上述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现实国家利益等方面的分歧,各方往往本着“各取所需”的态度,利用国际法来为其不同的立场提供依据。④See David Fidler,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Future of Cyberspace: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Cyberspace,in ASIL Insights,vol.15,issue 15(June 8,2011),http://www.asil.org/insights/volume/15/issue/15/international-law-and-future-cyberspace-obama-administration%E2%80%99s.美国等西方国家作为现有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力图通过国际法来确立对其有利的网络空间国际秩序;这些国家有关网络空间国际法治的主张,很大程度上正是服务于其外交政策的上述需要。而中国作为西方国家在网络领域的主要“假想敌”之一,面对西方国家在互联网监管政策、网络黑客等问题上的种种施压和指责,也日益呈现出“主动出击”、在网络空间国际法治领域提出各种重要主张的态势。
三、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法治的基本主张和贡献
除了对2010年“谷歌退出中国事件”等具体问题的表态外,近年来,中国政府还在各种多边和双边场合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网络空间国际法治的主张。
第一,旗帜鲜明地支持网络空间的国际法治,主张法治应当成为网络治理的基本方式。在2012年网络空间布达佩斯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条法司黄惠康司长提出: “‘无规矩不成方圆’。当今世界是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网络空间虽是虚拟空间,同样必须遵循公平、合理的规则。”⑤《黄惠康司长在网络问题布达佩斯国际会议上的发言》,载《中国国际法年刊 (2012)》,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718页。在2013年中美互联网论坛上,中国代表进一步提出: “我们需要一个国际法治的网络空间……互联网发展到今天,我们需要法律规则的引领。法治应当成为网络治理的基本方式。”⑥《中国代表在中美互联网论坛上的发言》,载《中国国际法年刊 (2013)》,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666页。
在网络空间践行法治、摒弃强权,是国际关系的大势所趋,也完全符合中国作为网络空间核心利益攸关方之一的利益。中国政府的上述主张,既是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所提出的“网络空间法治”的呼应,从而顺应了网络空间治理的客观需要,推动了国际社会关于网络空间国际法治的共识;又着眼于遵循公平、合理的规则,丰富和发展了网络空间国际法治的内涵。
第二,强调联合国应成为讨论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的主渠道,同时重视利用各种区域和双边场所作为有益补充。在上述2012年网络空间布达佩斯会议和2013年中美互联网论坛上,中国代表指出: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是网络国际治理和网络国际规则制定的最佳场所;中国支持进一步发挥联合国的主渠道作用,乐见在联合国框架下各国正在进行的关于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打击网络犯罪、国际电联有关网络管理授权等问题的探讨取得积极成果。①参见《黄惠康司长在网络问题布达佩斯国际会议上的发言》,载《中国国际法年刊 (2012)》,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718页;《中国代表在中美互联网论坛上的发言》,载《中国国际法年刊 (2013)》,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668页。与此同时,中国也积极参加了由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发起的网络空间“伦敦进程”②2011年发起的“伦敦进程”,迄今已分别在伦敦 (2011年)、布达佩斯 (2012年)、首尔 (2013年)举行了三次网络空间国际会议,并将于2015年4月在海牙举行第四次会议。以及东盟地区论坛、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等区域性组织有关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讨论,并重视通过中美互联网论坛、中欧网络工作小组等多种双边机制来推动相关磋商和对话。
当前,国际社会涉及网络空间治理的全球性、区域性和双边磋商、对话机制为数众多, “碎片化”状态较为明显。强调发挥联合国在国际事务(包括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中的主渠道作用,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贯立场。而从务实的角度看,兼顾各国利益和关切的其他国际网络机制可以为联合国机制提供有益补充。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2011年网络空间伦敦会议后所指出的: “中方希望,伦敦会议及相关论坛的讨论能够对于国际社会在联合国框架下讨论制订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进程形成有益补充。”③中国外交部:《2011年11月2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举行例行记者会》,http://www.fmprc.gov.cn/mfa_chn/fyrbt_602243/jzhsl_602247/t873171.shtml.中国政府上述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的主张,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也有利于推动网络空间国际法治的健康发展。
第三,倡导以《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国家主权原则等国际法基本原则作为网络空间国际法治的基石。中国政府强调国家主权原则在网络空间的适用,认为网络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自然延伸,应受到尊重和维护;各国有权根据本国的网络发展水平、历史传统、文化语言和风俗习惯等,在充分考虑本国广大民众意愿和适当借鉴国际通行做法的基础上,制定本国的网络公共政策和法律,并依法管理互联网。中国政府还提出:互联网的发展并未改变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网络国际治理应遵循一般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国家主权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原则等,这是确保网络空间国际秩序公正合理的基石。④参见《中国代表在中美互联网论坛上的发言》,载《中国国际法年刊 (2013)》,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666页。
国家主权原则等国际法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已经在国际关系的长期实践中得到验证。然而,西方国家在探讨网络空间国际法治时,却往往出于一己之私,有意无意地对这些基本原则加以回避,而使自卫权等例外“喧宾夺主”。正如黄惠康司长在网络空间首尔会议上所指出的:“不使用武力原则是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核心,自卫权只是其例外。然而近年来,大谈网络战、网络自卫权等‘例外’的论调不绝于耳,不使用武力原则却受到冷落,网络空间面临滑向军事化的危险,必须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⑤《中国代表在网络空间首尔会议上的发言》,载《中国国际法年刊 (2013)》,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681页。中国的上述主张,正是对西方国家有关论调的重要制衡和纠偏,有助于避免网络空间国际法治的方向性迷失。
第四,主张网络空间国际法治不仅需要注重现有国际法的适用,也应当重视对新规则的探讨。中国认为,需要对现有的一般国际法和新的网络特别法各自的作用加以适当平衡。事实上,在网络空间治理的很多重要问题上,现有国际法要么大量存在模糊和有待澄清之处,要么没有相关的规定。正因为如此,中国代表在2013年中美互联网论坛上指出:“还应看到,互联网的发展也引发许多新的、复杂的问题,现有国际法和国际机制已难以满足网络空间发展的现实需要。”①
在西方国家有关网络空间国际法治的主张中,主要是强调现有国际法在网络空间的适用,而基于各种理由反对制定新的国际法规则。②在网络空间秩序构建的初期阶段,现有国际法的适用无疑有利于填补相关国际规则的空白状况。但是,随着网络空间逐步走向法治化,网络空间相关国际法规则的制定和完善仍然势在必行。中国主张在充分酝酿和合作的基础上适时制定新的国际法规则,同样反映了网络空间构建国际秩序的客观需要。
第五,强调对个人以及国家在网络空间的权利义务都需要加以平衡。中国政府认为,网络空间涉及不同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不仅要保护言论自由,也要保护个人隐私权和名誉权;不仅要保护网络交易畅通便利,也要保护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不受侵犯;不仅要保护网络自由,也要维护社会秩序、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件的规定,言论自由 (包括网络自由)并非是绝对的。网络空间不是一个不受监管的真空地带。各国在不违反公认国际法的前提下,有权根据自身的国情依法管理网络空间。③
在网络空间国际法治问题上,西方国家的主张有着很大的虚伪性。例如,它们往往热衷于利用国际人权法的有关规定来鼓吹“互联网自由”,但这主要是着眼于限制其他国家 (包括中国)根据本国法对相关网络活动进行管理,对其自身而言,则是在维护网络安全名义下,最大限度地确保在大规模网络监控和窃密甚至采取单边军事行动方面的行动自由。④中国则认为:在网络空间,个人的权利义务和国家的权利义务都需要加以平衡;也只有这样,才能在网络自由和网络安全、网络主权和网络人权之间达成合理的平衡。这一主张无疑是符合国际社会的长远利益的。
第六,为网络空间国际法治提供“和谐”、“共进”等重要理念和目标。在2013年网络空间首尔会议上,中国代表指出:我们主张建立一个以“和谐”为本质,以“共进”为目的,以“携手共建”为成就之路的国际网络空间秩序,致力于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使各国人民在网络空间和谐共处,并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使各国在网络空间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实现共同繁荣。他还指出:实现网络空间的法治化和民主化正是和谐共进的国际网络空间秩序的内在要求。⑤
上述“和谐”、“共进”等理念和目标,站在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高度,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对当前的网络空间秩序构建和网络空间国际法治尤其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之,中国政府关于网络空间国际法治的各项主张,不仅是对西方国家有关主张的重要补充、牵制和抗衡,也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对网络空间国际法治作出的重要贡献。作为一个缩影,这些主张体现了中国政府日益重视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依法处理涉外经济、社会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⑥
四、问题与前瞻
随着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向网络空间的延伸,网络空间的国际法治成为人类的共同目标。如何更好地发挥国际法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作用,直接关涉国际社会能够在网络空间建立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如何共同分享网络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繁荣和福祉,对未来影响深远。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推动网络空间国际法治既是当前国际法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新课题和新挑战,也是网络空间国际秩序构建中
① 《中国代表在中美互联网论坛上的发言》,载《中国国际法年刊 (2013)》,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666-667页。
②See e.g.The White House,VP's Remarks to London Cyberspace Conference,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11/01/vps-remarks-london-cyberspace-conference,last visited on 3 July 2014.
③ 《中国代表在中美互联网论坛上的发言》,载《中国国际法年刊 (2013)》,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667页。
④See Harold Koh,“International Law in Cyberspace:Remarks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by Harold Hongju Koh to the USCYBERCOM Inter-Agency Legal Conference Ft.Meade,MD,Sept.18,2012,”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Online,vol.54(December 2012),pp.1-12.
⑤ 《中国代表在网络空间首尔会议上的发言》,载《中国国际法年刊 (2013)》,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681-682页。
⑥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第1版。的一个重大问题。
网络空间相关国际法规则和制度尚未成型,这为我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法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但另一方面,在网络空间这样的新领域,由于国际法是否适用、如何适用等诸多问题还存在不确定性,这对我国运用和塑造国际法的能力提出了更大的挑战。近年来,我国对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制定和适用日益重视,提出了以“网络主权”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主张。当然,与西方主要大国相比,我国在网络空间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都处于较为明显的弱势地位。究其根源,我国在研究和运用国际法并据此提出符合本国利益的主张这一“软实力”上还有着较大的欠缺。①何志鹏:《走向国际法的强国》,《当代法学》2015年第1期。例如,我国政府提出的“网络主权”原则已经在国际上引发较大关注,国家主权适用于网络空间的理论依据是什么?“网络主权”包含哪些具体内涵?其确立和适用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有待于通过深入研究加以回答,以加强其说服力和影响力,从而为我国的网络外交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另外,我国国际法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在国际主流媒体和学术期刊上能够发出的声音也较为有限,这同样不利于我国有关网络空间国际法治的主张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同。
当务之急,我国政府应在战略层面对网络空间国际法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有着充分的认识,并通过认真研究这一问题的发展态势和最新动向,更加深入地参与到网络空间国际对话和立法进程中,积极影响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和适用,充分反映自身的利益和主张。本文作者的主要建议包括:
1.积极开展“网络外交”,全面提升包括网络空间法治在内的网络问题在我国外交工作中的地位。当前,网络空间的秩序构建已成为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斗争与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而网络空间国际法治正是网络空间秩序构建中的焦点问题之一。如前所述,网络空间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的走向,与我国未来的发展空间休戚相关。我国政府应高度重视包括网络空间法治在内的网络问题在我国外交工作中的地位,以中美、中欧、中英网络对话和新兴国家互联网圆桌会议等既有机制为基础,开展全方位的“网络外交”,在开放博弈中与其他国家求同存异,使我国有关网络空间国际法治的主张得到最大限度的宣扬和接受。
2.加强对网络空间法治领域主要争议问题的研究,为我国的相关网络外交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我国在参与网络空间国际对话和立法进程时,既应当对其他国家特别是主要西方国家的政策主张加以跟踪研究,又应当对我国的相关政策加以系统研究,特别是通过有效地加强实务部门和学术界的联系与互动,推进在以下重点领域的研究:(1)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适用及其边界;(2)国际人权法在网络空间的适用限度;(3)对网络攻击行使自卫权等诉诸武力权问题以及战时法规 (国际人道法)对网络攻击的适用问题;(4)在现有国际法之外为网络空间专门制定新规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5)网络空间治理机制和规则“碎片化”状态的应对路径;等等。这些研究,将有助于从制度和能力建设层面帮助我国积极、深度参与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制定,切实提升我国在网络空间国际秩序构建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3.适时发布《中国网络空间战略》,向其他国家明确宣示我国有关网络空间 (包括网络空间国际法治)的政策主张、理论依据和行动方案。近几年来,很多国家纷纷发布本国的网络空间或网络安全国家战略,反过来说,这些国家往往对中国的互联网政策和网络安全战略存在各种各样的偏见、误解和责难。笔者认为,中国也很有必要适时发布一份《中国网络空间战略》白皮书,系统提出我国对网络空间的政策主张、理论依据和行动方案。这不仅有利于在国内层面推动我国网络空间政策的统一性或一致性,更好地指导我国不同政府部门、不同地方的工作和实践,更重要的是,它将在国际层面有力地进行我国的政策宣示,回击一些国家的无端指责,为我国在网络空间国际法治的话语权争夺中赢得先机。事实上,我国政府在2010年“谷歌事件”后发布了一份《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如今,专门以白皮书形式提出我国网络空间战略的时机已趋于成熟。
4.高度重视非国家行为体和“软法”在网络空间国际法治中的作用,并采取必要措施加以应对。在当前的网络空间国际合作中,各种非国家行为体 (包括行业性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智库等)的影响力不可忽视,这类行为体在2011年以来“伦敦进程”历次网络空间国际会议中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同时,由于各国在网络空间的诸多领域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制定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短期内尚不具备可行性,在此情况下,西方国家力图通过行业规范、企业标准等形成“软法”,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反映其利益和主张的国际习惯趋于确定。我国应对这一态势有着清楚的认识并加以有效应对。这就要求:第一,我国应当大力支持本国的行业组织、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法治领域的对话与交流,在民间层面开展网络外交;①在“伦敦进程”历次会议前后,我国政府特别是外交部已经推动了这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良好效果;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机构也在大力推进相关工作。第二,我国的网络外交对象不仅包括其他国家的政府,还包括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第三,我国还应重视研究“软法”的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力争主导网络空间国际软法的内容和走向。
5.在国内大力奉行“依法治网”,推动我国互联网管理体制不断走向完善。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国际法治和国内法治之间相互贯通、相互影响,二者之间存在着持续的动态互动。②赵骏:《全球治理视野下的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从国内层面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我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这里,依法治国必然包括“依法治 (互联)网”。我国现行的互联网管理体制,从我国国情出发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也越来越暴露出不少弊端 (如对网络信息的审查和过滤缺乏清晰的标准和透明的程序),并因此而受到各种非难和指责。我国政府应当在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本国核心利益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借鉴其他国家互联网管理的成熟经验,大力完善我国的相关国内立法和措施,使我国的互联网监管政策在法治理念的指引下,向更为透明、更为合理的方向迈进。加快改革和完善互联网管理体制,有助于我国在国际法治博弈中占据道义制高点,从而增强我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五、结语
国际法所确立的国家和其他国际行为体的行为准则,是维系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网络空间国际法治”这一共同理念和话语的确定,为网络空间治理和秩序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网络空间国际法治的实现还面临着种种障碍,但出于对网络空间的共同依赖和对网络空间国际秩序的共同需要,各国有理由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通过国际合作谋求共同利益,共同致力于构建和平、和谐的网络空间国际秩序。
作为网络空间的核心利益攸关方之一,中国理应成为网络空间国际法治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建设者。这是因为,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网络强国,必然需要同时成为一个网络空间国际法的强国,掌握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和适用的主导权。事实上,中国在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法治、运用国际法维护我国利益方面,正日益展现出开放自信的心态和积极有为的态度。展望未来,我国应在战略层面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有着充分的认识,并大力加强相应的制度和能力建设,更加广泛、深入地参与到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中去,为网络空间国际法治这一目标的实现发挥建设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