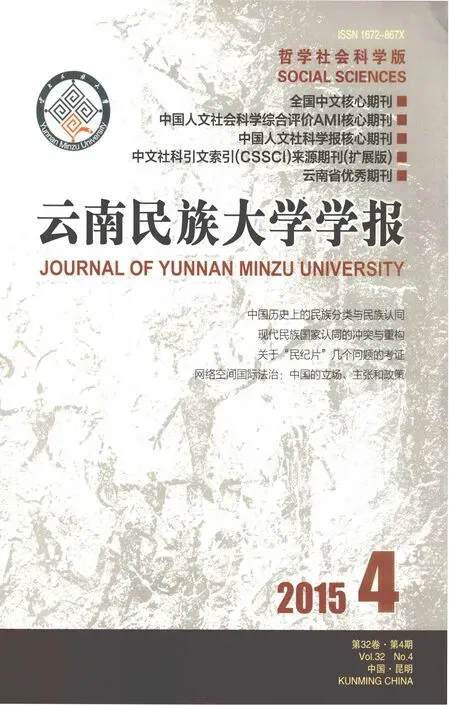拓跋魏宫廷文化述论
刘 军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吉林长春130012)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曾有论断,中古文化重心由官方学府向私人家族转移,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家学渊源是推进文化发展的动力。此论堪称经典,早已获得学界共识。不过,对于少数民族拓跋鲜卑统治时期的中国北方,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划一,在这里家学与官学融会贯通、交相辉映,共同谱写多元文化荟萃的绚烂篇章。其中,兼具家学与官学特质的皇家宫廷文化尤其令人瞩目,它对北方文教事业的复兴和胡人勋贵的汉化起到示范、导向和促进作用。本文所说的宫廷文化,专指在禁中范围内充分利用皇家文化资源,搭建高端对话平台,以国宗为参与主体的文化类型之总和,它是中古北方学术的制高点和主阵地,也是民族融合、社会进步的风向标。鉴于此,笔者在前人成果基础上,试论述北魏宫廷文化的大致梗概,挂一漏万之处,还望方家不吝赐教。
一、北魏宫廷文化氛围的营造
创建北魏政权的拓跋鲜卑与华夏文明接触较晚,属于相对滞后的草原“生番”。当他们势如破竹地挺近中原时,发觉自身在意识形态等软实力方面有严重缺陷,而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改弦更张、变夷从夏。只有掌握先进的汉文化,才能在这片陌生地域站稳脚跟。于是,历代拓跋君主无不注重汉文化的吸收,他们礼贤下士、招揽人才,把酋豪议事的毡帐变成学习的课堂,由此奠定了日后宫廷文化氛围的根基。实际上,早在代北酋邦时期,尊重士人、崇尚知识便已蔚然成风。《魏书》卷24载,汉人燕凤“好学,博综经史,明习阴阳谶纬。昭成素闻其名,使人以礼迎致之。……后拜代王左长史,参决国事,又以经授献明帝”;许谦“少有文才,善天文图谶之学。建国时,将家归附,昭成嘉之,擢为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记,与燕凤俱授献明帝经”。西晋永嘉之乱以后,中原士人大多流徙避难,然仍不乏滞留乡梓、聚众自保者,拓跋积极联络争取,使之兼具幕僚和教师的双重身份,在出谋划策之余传授文化知识,此乃拓跋族精神世界启蒙之始。
北魏立国后,继续保持重用汉族士人的传统,孜孜不倦地汲取汉文化的营养,为巩固统治做充分准备。道武帝曾引北方顶级冠族清河崔宏 (字玄伯)随侍左右、顾问应对。 《魏书》卷24《崔玄伯传》:“太祖常引问古今旧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则。玄伯陈古人制作之体,及明君贤臣,往代废兴之由,甚合上意。……太祖曾引玄伯讲《汉书》,至娄敬说汉祖欲以鲁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叹者良久。是以诸公主皆厘降于宾附之国,朝臣子弟,虽名族美彦,不得尚焉。”崔宏累世儒学修身,精通古代典籍和朝仪故事,他通过系统讲授,帮助道武帝出台了北魏初期的体制框架和皇室的婚姻政策,提升了统治者的应对能力和施政水平。获得道武帝青睐的汉族士人还有辽东公孙表和赵郡李先,《魏书》卷33载,公孙表献计献策,“初,太祖以慕容垂诸子分据势要,权柄推移,遂至亡灭;且国俗敦朴,嗜欲寡少,不可启其机心,而导其巧利,深非之。表承指上《韩非书》二十卷,太祖称善。”李先声名远扬,早为道武帝熟知,他“迁博士、定州大中正。太祖问先曰: ‘天下何书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对曰:‘唯有经书。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从道武帝与上述3人的交往记录来看,他对中原事物懵懂无知,甚至有可能不说华语、不识汉字,决非某些学者所说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据此推断他在代国灭亡之际被苻坚掳至长安并强迫接受汉化教育的结论实难成立①孙险峰:《北魏道武帝早年经历论考补释》,收入《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页。。道武帝还特别重视皇子的培养,延聘礼经博士新兴人梁越, “太祖以其谨厚,举动可则,拜上大夫,命授诸皇子经书。”②《魏书》卷84《儒林·梁越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43页。汉族士人进入北魏宫廷,带来新鲜的文化气息,坚定了道武帝走汉化路线的决心,宫廷文化的风格基调也就此形成。
后续的北魏诸帝也都恪守祖制,与中原知识精英群体保持密切往来,矢志不渝地夯实宫廷学术的基础,累世积淀浓郁的文化氛围。如明元帝师从赵郡李先,学习《韩子连珠》二十二篇、 《太公兵法》十一事,诏有司曰: “先所知者,皆军国大事,自今常宿于内。”③《魏书》卷33《李先传》,第790页。崔宏之子崔浩博学多识,也曾入宫教授,“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常授太宗经书。……太宗好阴阳术数,闻浩说《易》及《洪范》五行,善之,因命浩筮吉凶,参观天文,考定疑惑。”④《魏书》卷35《崔浩传》,第807页。明元帝还委派儒生训导太子,昌黎徒河卢丑应选,“世祖之为监国,丑以笃学博闻入授世祖经。”⑤《魏书》卷84《儒林·卢丑传》,第1843页。太武帝时,随着民族矛盾的缓和,入宫讲学的汉族士人逐渐增多,如昌黎谷洪“少受学中书,世祖以洪机敏有祖风,令入授高宗经”⑥《魏书》卷33《谷浑传附谷洪传》,第781页。。再如赵郡李灵“以学优温谨,选授高宗经”⑦《魏书》卷49《李灵传》,第1097页。。这些随机举行的教学活动不断累积,最终成型了固定的皇家侍从讲读制度,它使北魏宫廷网罗了一批优秀学者,也为知识精英提供了施展才华和抱负的舞台⑧高慧斌:《南北朝侍从讲读制度的发展与变迁》,《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7期。。《魏书》卷32《高湖传附高谧传》载,勃海高谧文武全才, “显祖之御宁光宫也,谧恒侍讲读。”同书卷55《刘芳传》载,大儒彭城刘芳“从驾洛阳,自在路及旋京师,恒侍坐讲读”。又卷90《逸士·冯亮传》载,南阳冯亮“博览诸书,又笃好佛理。……世宗尝召以为羽林监,领中书舍人,将令侍讲《十地》诸经”。内廷于是常设侍讲、侍读、侍书、侍学诸席位,由学识出众、才干突出的朝臣兼领,北魏宫廷学术迈上了制度化的轨道。
北魏大力倡导宫廷文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形势的客观需要与统治阶级主观意愿交互作用的结果。诚如恩格斯《反杜林论》所言:“由比较野蛮的民族进行的每一次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由于征服而面临的比较高的‘经济状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⑨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3页。拓跋鲜卑跨越阴山,面对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北部中国,遭逢同样的历史命题。在与汉民族的深入交往中,他们不知不觉地由武力的“征服者”变成了经济和文化的“被征服者”。作为内徙胡人精神领域最高殿堂的宫廷学术于是应运而生,加速了其个性修养与气质面貌的质变。《魏书》卷84《儒林列传序》对此有精辟的阐述:“太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岂不以天下可马上取之,不可以马上治之,为国之道,文武兼用,毓才成务,意在兹乎?”孝文帝亦语重心长地告诫臣下:“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书,朕闻此,深用怃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朕自行礼九年,置官三载,正欲开导兆人,致之礼教。朕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孙,博见多知。若永居恒北,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孙,不免面墙也。”①《魏书》卷21《献文六王上·广陵王羽传》,第550页。北魏皇帝对汉文化持开明、谦逊的态度,以皈依汉学、文治天下为北魏建政立国的基准。在此背景下,宫廷除政治用途外,不可避免地还要发挥文化功效。
北魏皇帝的文化价值取向对宫廷学术的发展也起到决定作用,试想没有至尊的支持,宫闱必将是文化的禁区和荒漠。所幸,《魏书》帝纪部分保存了相对完整的记录,可供后人参考。不难发现,北魏皇帝普遍尊崇华夏,对传统文化的痴迷程度决不啻于汉族统治者。如明元帝“礼爱儒生,好览史传,以刘向所撰《新序》、《说苑》于经典正义多有所阙,乃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兼资文武焉”②《魏书》卷3《明元帝纪》,第64页。。景穆帝“明慧强识,闻则不忘。及长,好读经史,皆通大义,世祖甚奇之”③《魏书》卷4《太武帝纪下附景穆帝纪》,第107页。。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④《魏书》卷7《孝文帝纪下》,第187页。。宣武帝“雅爱经史,尤长释氏之义,每至讲论,连夜忘疲”⑤《魏书》卷8《宣武帝纪》,第215页。。正是历代君主的由衷挚爱,并不遗余力地扶植,才使宫廷文化繁花似锦,结出累累硕果。
此外,北魏宫廷学术植根中原文化固有的肥沃土壤,不断汲取丰富的养料充实肌体。北方政治祥和、社会安康和民族融合也为其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人所共知,文化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建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与物质基础之上。拓跋虽是异族,但治下的北方朝气蓬勃、生机盎然,政治、经济、社会、法律诸方面基本回归汉晋正统,民族融合更是处于史无前例的高潮状态。特别是汉族士人对北魏政权的认同感逐渐加强,双方由最初的仇视敌对步入友好合作的新阶段。孝庄帝永安二年 (529年),弘农大族杨元慎对梁将陈庆之说: “我魏膺箓受图,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常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岂卿鱼鳖之徒,慕义来朝,饮我池水,啄我稻粱;何为不逊,以至于此?”⑥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2《城东·景宁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18页。其向背立场足以代表广大汉人士族,他们主动摒弃夷夏大防之偏见,倾心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北魏皇室共同努力浇灌文化新花,推动了宫廷学术的进步成长。
二、北魏宫廷文化活动的类型
先进的华夏文明对拓跋鲜卑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北魏统治者虚心接受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坦诚地结交汉族知识精英,把权力中心宫廷竭力打造成文化圣殿。北魏宫廷经常举办内涵深刻、形式多样、轻松活泼的文化活动,极大促进了宫廷学术的繁荣。细加归类,其具体类型如下:
第一,讲学研讨,切磋琢磨。北魏帝后热衷学术,常于禁中以贵族沙龙的方式交流学问。献文帝开风气之先,《魏书》卷114《释老志》:“显祖即位,敦信尤深,览诸经论,好老庄。每引诸沙门及能谈玄之士,与论理要。”凉州学者程骏是他的知音, “显祖屡引骏与论易老之义,顾谓群臣曰:‘朕与此人言,意甚开畅。’”⑦《魏书》卷60《程骏传》,第1345页。宣武帝则将研讨之风推向极致,早在即位以前,便与聪颖的清河王元怿“特加友异,每与王谈玄剖义,日晏忘疲”⑧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页。。日后兴致更浓, 《魏书》卷84《儒林·孙惠蔚传》:“正始中,(武邑孙惠蔚)侍讲禁内,夜论佛经,有惬帝旨,诏使加‘惠’,号惠蔚法师焉。”降至北魏末叶,学术研讨已为宫廷常态。《魏书》卷53《李孝伯传附李郁传》载,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年)春,“于显阳殿讲《礼》,诏 (赵郡李)郁执经,解说不穷,群难锋起,无废谈笑。出帝及诸王公凡预听者,莫不嗟善。”皇帝甚至亲登讲坛,答疑解惑。《魏书》卷15《昭成子孙·毗陵王顺传》: “太祖好黄老,数召诸王及朝臣亲为说之。”孝文帝才学出众,常登台宣讲。《魏书》卷21《献文六王下·彭城王勰传》:“高祖亲讲丧服于清徽堂,从容谓群臣曰:‘彦和、季豫等年在蒙稚,早登缨绂,失过庭之训,并未习礼,每欲令我一解丧服。自审义解浮疏,抑而不许。顷因酒醉坐,脱尔言从,故屈朝彦,遂亲传说。将临讲坐,惭战交情。’”同书卷72《阳尼传》:“高祖尝亲在苑堂讲诸经典,诏 (北平阳)尼侍听,赐帛百匹。”宣武帝则更胜一筹, 《魏书》卷8《宣武帝纪》载,正始三年 (506年)十一月甲子,“帝为京兆王愉、清河王怿、广平王怀、汝南王悦讲《孝经》于式乾殿”;永平二年 (509年)十一月己丑, “帝于式乾殿为诸僧、朝臣讲《维摩诘经》”。同书卷114《释老志》亦载:“世宗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值得注意的是,嫔妃所居永巷也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胡太后姑母在洛阳主持胡统寺,“其寺诸尼,帝城名德,善于开导,工谈义理,常入宫与太后说法。”①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1《城内·胡统寺》,第59页。听众广及宗女。史载,兰陵长公主与驸马刘辉不睦,“公主姊因入听讲,言其故于灵太后。”②《魏书》卷59《刘昶传附刘辉传》,第1312页。出身书香门第的嫔妃则主动承担传播知识的重任,如御史中尉李彪之女“幼而聪令,彪每奇之,教之书学,读诵经传。……彪亡后,世宗闻其名,召为婕妤,以礼迎引。婕妤在宫,常教帝妹书,诵授经史”③《魏书》卷62《李彪传附李志传》,第1399页。。可见,北魏宫廷俨然自由活跃的学术园地。
第二,创办学校,培养皇族子弟。与六朝其他政权官学衰败、私学兴盛的境况不同,北魏格外重视学校教育,在中央创办4所高等学府,即皇宗学、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小学。设于禁中的皇宗学级别最高,专门招收国宗贵胄,因而成为宫廷学术之重镇。其办学宗旨见《魏书》卷21《献文六王上·咸阳王禧传》所载太和九年 (485年)文明冯太后令,曰: “自非生知,皆由学诲,皇子皇孙,训教不立,温故求新,盖有阙矣。可于闲静之所,别置学馆,选忠信博闻之士为之师傅,以匠成之。”皇宗学运作选择高端路线,精选教师教案,主要教官皇宗博士位居正五品下阶,高于从五品上阶的国子博士和正六品中阶的太学博士,更非流内边缘的四门小学博士能比。④《魏书》卷113《官氏志》,第2984~2987页。应选者皆知名学人,如鸿儒武邑孙惠蔚“年十三,粗通《诗》、 《书》及《孝经》、 《论语》;十八,师董道季讲《易》;十九,师程玄读《礼经》及《春秋》三传。周流儒肆,有名于冀方。太和初,郡举孝廉,对策于中书省。时中书监高闾宿闻惠蔚,称其英辩,因相谈,荐为中书博士,转皇宗博士”⑤《魏书》卷84《儒林·孙惠蔚传》,第1852页。。皇帝对皇宗学关心备至,孝文帝于太和十六年 (492年)四月甲寅,“幸皇宗学,亲问博士经义。”⑥《魏书》卷7《孝文帝纪下》,第169页。又任城王元澄追忆孝文帝道:“昔在恒代,亲习皇宗,熟秘序庭无阙日。臣每于侍坐,先帝未常不以书典在怀,礼经为事,周旋之则,不辍于时。”⑦《魏书》卷19中《景穆十二王中·任城王云传附澄传》,第471页。迁洛后,皇宗学虽一度萧条,但在元澄诸人的奔走呼吁下,得到及时恢复,宣武帝亲诏: “胄子崇业,自古盛典,国均之训,无应久废,尚书更可量宜修立。”⑧《魏书》卷19中《景穆十二王中·任城王云传附澄传》,第471页。皇宗学既立,入学宗室络绎不绝。《元孟辉墓志》:“永平之季,解巾给事中,时始八岁矣,有诏入学,听不朝直。”《元灵曜墓志》:“爰甫就学,师逸功倍。” 《元信墓志》: “幼入书堂,无竹马之欢。”《元维墓志》:“受教二庠,声高两观。”《元賥墓志》:“裁离襁褓,便游庠塾,月习礼仪之事,体安仁义之风。”⑨分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116、137、230、256、368页。皇宗学师资雄厚,教学严格规范,对于提高宗室的知识素养,繁荣宫廷学术大有裨益。
第三,皇家藏书、校书活动方兴未艾。书籍作为知识信息的载体,是无比宝贵的学术资源,藏书、校书活动是文化品味的体现。北魏皇家热衷图书的搜集、整理工作,成绩斐然。早在道武帝开国伊始,便咨询赵郡李先: “天下书籍,凡有几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备?”李先建议:“陛下诚欲集之,严制天下诸州郡县搜索备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难。”①《魏书》卷33《李先传》,第789页。皇家藏书自此发端,其数量和质量颇为可观。孝文帝时又责成臣僚查访珍籍善本, 《魏书》卷44《薛野猪传附薛昙宝传》:“高祖诏昙宝采遗书于天下。”在皇帝的鼓励下,民众踊跃献书,代表人物是河西学者江强,“献经史诸子千余卷,由是擢拜中书博士。”②《魏书》卷91《术艺·江式传》,第1960页。北魏又组织优秀学者校勘修订皇家图书。文成帝时,勃海高谧“以坟典残缺,奏请广访群书,大加缮写,由是代京图籍,莫不审正”③《魏书》卷32《高湖传附高谧传》,第752页。。孝文帝则征调与中山张吾贵齐名的北方儒宗博陵刘献之“典内校书”④《魏书》卷84《儒林·刘献之传》,第1850页。,即出任皇家图书馆的馆长。另外,清河崔光韶奉敕“兼秘书郎,掌校华林御书”⑤《魏书》卷66《崔亮传附崔光韶传》,第1482页。。宣武帝对皇室藏书进行了最大规模的系统整理。《魏书》卷84《儒林·孙惠蔚传》载,孙惠蔚见东观图籍杂乱,上疏曰:“观阁旧典,先无定目,新故杂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数十,无者旷年不写。或篇第褫落,始末沦残;或文坏字误,谬烂相属。篇目虽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丞臣卢昶所撰《甲乙新录》,欲裨残补阙,损并有无,校练句读,以为定本,次第均写,永为常式。其省先无本者,广加推寻,搜求令足。然经记浩博,诸子纷纶,部帙既多,章篇纰缪,当非一二校书,岁月可了。今求令四门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书省专精校考,参定字义。如蒙听许,则典文允正,群书大集。”此议经皇帝诏准后实施。史载,广平宋道璵“世宗初,以才学被召,与秘书丞孙惠蔚典校群书,考正同异”⑥《魏书》卷77《宋翻传附宋道璵传》,第1690页。。足见此次校书受到高度重视。北魏皇室借助行政手段,集中力量抢救典籍,既有益于宫廷文化,又使华夏文明得以延续,功莫大焉。
第四,宫廷宴饮,诗赋并兴。中古文士群体交际流行宴饮,其旨趣决非解口腹之快,而是专为诗为礼举行的象征仪式。⑦黄亚卓:《汉魏六朝公宴诗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北魏宫廷追随魏晋时尚新风,使皇家赐宴成为交流文化、展示风采的平台。
宫廷宴饮时称“公宴”,通常由帝后召集群臣举行,席间觥筹交错、赏景吟诗,把酒临风、直抒胸臆,俨然一场气氛轻松的文化盛会。《魏书》对宫廷宴饮着力渲染,彰显王朝的文治气象。卷19《景穆十二王中·任城王云传附澄传》载,孝文帝大宴臣工于洛阳清徽堂,依次游览流化渠、洗烦池、观德殿和凝闲堂,畅谈名物典故,“即命黄门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峦、崔休等赋诗言志。烛至,公卿辞退。李冲再拜上千万岁寿。高祖曰:‘卿向以烛至致辞,复献千万之寿,朕报卿以《南山》之诗。’高祖曰:‘烛至辞退,庶姓之礼;在夜载考,宗族之义。卿等且还,朕与诸王宗室,欲成此夜饮。’”同书卷21《献文六王下·彭城王勰传》:“宴侍臣于清徽堂。日晏,移于流化池芳林之下。高祖曰: ‘向宴之始,君臣肃然,及将末也,觞情始畅,而流景将颓,竟不尽适,恋恋余光,故重引卿等。’因仰观桐叶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实离离,恺悌君子,莫不令仪,今林下诸贤,足敷歌咏。’遂令黄门侍郎崔光读暮春群臣应诏诗。至 (元)勰诗,高祖仍为之改一字,曰:‘昔祁奚举子,天下谓之至公,今见勰诗,始知中令之举非私也。’勰对曰:‘臣露此拙,方见圣朝之私,赖蒙神笔赐刊,得有令誉。’高祖曰:‘虽琢一字,犹是玉之本体。’勰曰: ‘臣闻诗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赐刊一字,足以价等连城。’”值此良辰美景,君臣酒酣,切磋诗文,咏物言志,颇具魏晋名士风范。
皇族内部还时常举行“宗宴”,文化要素仍不可或缺。史载: “申宗宴于皇信堂,不以爵秩为列,悉序昭穆为次,用家人之礼。高祖曰:‘行礼已毕,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赋诗。’特令(元)澄为七言连韵,与高祖往复赌赛,遂至极欢,际夜乃罢。”⑧《魏书》卷19《景穆十二王中·任城王云传附澄传》,第464页。为王公重臣送行的“饯宴”亦有赋诗的环节,皇弟咸阳王元禧赴任冀州,“高祖亲饯之,赋诗叙意。”①《魏书》卷21《献文六王上·咸阳王禧传》,第534页。足见,规范典雅的宴饮仪式承袭魏晋风度,是北魏宫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北魏宫廷文化的特点及意义
北魏宫廷文化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沐浴华夏文明的阳光雨露而充分绽放的一朵奇葩,以其独有的风格韵味闪耀古代思想文化领域。在中古文化绚丽景致的映衬下,它显现出异常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是把握北方学术演变轨迹和整体趋势的关键。
首先,北魏宫廷学者以北方士人为主体,因而打上河北学风的深刻烙印。以本文列举典型人物为例,其郡望俱在华北,如早期的燕凤、许谦世居代地,建国后的崔宏、崔浩、崔光韶、崔光、崔休出自相州清河郡,李先、李灵、李郁出自定州赵郡,宋道璵出自相州广平郡,邢峦出自瀛洲河间郡,高谧出自冀州勃海郡,阳尼出自幽州北平郡,刘芳出自徐州彭城郡,公孙表出自营州辽东郡,郭祚出自并州太原郡,梁越出自肆州新兴郡,孙惠蔚出自冀州武邑郡,刘献之出自定州博陵郡,卢丑、谷浑出自平州昌黎郡,李冲出自秦州陇西郡,江强、程骏祖居凉州。再谈史籍有载的皇家侍从讲读官员,侍讲崔宏、崔浩、高允、司马金龙、高谧、李式、刘芳、释道登、孙惠蔚、崔光、裴粲、贾思伯皆北方学士,②刘军:《北朝侍讲制度考述》,《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侍读孙惠蔚、冯元兴、温子升、邢昕、李业兴亦北学嫡传。③刘军:《北朝侍读考述》,《北方论丛》2010年第3期。北方士人主宰宫廷学术,其所秉承的河北学风自然大行其道。所谓河北学风,源于汉末以来流行河北地域的学术流派,与江左新风尖锐对立。二者的差别在于,前者是汉代经学的孑遗,注重名物训诂考据,崇尚渊综广博、艰深刻板、保守务实;后者是魏晋洛阳新风的延续,偏好义理的诠释阐发,标榜清新洒脱、自然自我、任诞虚玄。④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从北魏宫廷学术的具体内容来看,研读经史、探讨礼义、咨询政务、寻本溯源所占的比重远超其他,凸显出经世致用的原则,完全契合河北学术的信条。特别是,北魏在儒学式微的大背景下仍奉其为圭臬,使之成为宫廷学术的灵魂和骨干。《魏书》卷38《王慧龙传附王遵业传》:“(太原王)遵业,风仪清秀,涉历经史。……与崔光、安丰王延明等参定服章。及 (崔)光为肃宗讲《孝经》,遵业预讲,延业录义,并应诏作《释奠侍宴诗》。”河北学者太原王遵业、延业兄弟与清河崔光为皇帝讲解儒家经典,仪式盛况空前,宫廷学术的价值取向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北魏宫廷文化体系并非僵化闭塞,而是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适应能力,随着社会交往的频繁,多元化特征愈益显著。前文已述,河北士人推崇的儒学是宫廷学术的根底,暗合拓跋鲜卑励精图治、开拓进取的入世精神。但其他文化因素也不受排斥,以玄学、文学为代表的江左学术和以佛学为核心的南亚文明并行不悖。如道武帝倡导儒学,通晓黄老,还效仿魏晋名士服用寒食散,同时与僧侣关系莫逆,沙门法果“每与帝言,多所惬允,供施甚厚”;明元帝礼爱儒生,“亦好黄老,又崇佛法”;太武帝则摇摆于佛道之间;景穆帝擅长经史, “素敬佛道”;献文帝涉猎经学、玄学和佛学。⑤《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30~3037页。孝文帝汉化改革,汇聚南北、融合东西,缔造更高层次的文化类型,他文史并重、礼玄双修、兼通佛学,是罕见的全才。宣武帝的学术视野亦极开阔,囊括儒释玄。孝明帝虽专攻经学,但临朝称制的胡太后却崇信佛法,后宫俨然禅林讲堂。可见,北魏帝后的知识架构是层累叠加的复合体,这势必会对宫廷学术产生导向性影响,使其趋于多元化。该特征亦可从宗室墓志得到间接反映,《元扬墓志》: “若夫优游典谟之中,纵容史籍之表。……高枕华轩之下,安情琴书之室,命贤友,赋篇章,饮渌酒,奏清弦,追嵇阮以为俦,望异代而同侣。”《元举墓志》:“坟经于是乎宝轴,百家由此兮金箱。洞兼释氏,备练五明,六书八体,画妙超群,章勾小术,研精出俗,山水其性,左右琴诗。”《元袭墓志》:“错综古今,贯穿百氏,究群言之秘要,洞六艺之精微。……又工名理,善占谢,机转若流,酬应如响,虽郭象之辨类悬河,彦国之言如璧玉,在君见之。”⑥分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75、215、295页。显然,他们都是在经学的基础上搭配江左新风和异域宗教元素,并接受时尚的生活方式。宗室平素出入宫闱,其品性修养定是宫廷文化真实客观的翻版,这说明北魏统治者对待文化一视同仁,奉行兼收并蓄的开放方针。
再次,随着综合素质的提高,胡人贵族对宫廷文化的参与精神和主体意识渐趋增强。文化的传播有主体和客体之别,角色的嬗变标识着能力水平的高低。拓跋鲜卑蒙昧落后,宫廷文化起初是汉族士人的独角戏,胡人完全是被动的客体。经过长期的学习成长,宗室等胡人崭露头角,实现与汉族文士的对等交往。①刘军:《论北魏宗室阶层的文化参与及角色嬗变》,《东北师大学报》2012年第6期。不仅皇帝能登坛讲学,宗室还独立执掌教授职责。《元延明墓志》:“翻为国师,郁成朝栋。既业冠一时,道高百辟,授经侍讲,琢磨圣躬。”《元顼墓志》: “明帝春秋方富,敦悦坟典,命为侍学。王执经禁内,起予金华。” 《元彝墓志》:“孝明皇帝春秋富冲,敦上庠之学,广延宗英,搜扬俊乂。王以文宣世子,幼缉美誉,参兹妙简,入为侍书。”②分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289、290、226页。又负责校勘皇室藏书,《元延明墓志》:“监校御书。……固仇校之所归,杀青自理。”《元璨墓志》:“特被优诏,擢秘书佐郎。时寻有敕,专综东观,坟经大序,部帙载章,所进遗漏,缉增史续。”《元邵墓志》:“以本职监内典书,折简无遗,绝编咸举。”③分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288、152、221页。在宫廷宴会上,宗室亦高光亮相、独领风骚,其诗作足以流传后世。如彭城王元勰诗: “问松林,松林经几冬?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④《魏书》卷21《献文六王下·彭城王勰传》,第572页。可谓浑厚质朴、苍劲有力、境界高远、气度非凡,不可与南朝萎靡之作同日而语。胡人文化主体地位的获得,实乃中古文化格局之巨变,是拓跋鲜卑自身进化和民族融合的结果,宫廷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
总而言之,文化底蕴深厚的北魏宫廷是铸炼学术的熔炉,它与官办学府和门阀士族的家学共同作用,保护并推进了华夏文明。优秀的胡汉学者云集这里,各种思想激荡碰撞,产生创新的火花,为隋唐盛世局面做了必要铺垫。北魏宫廷学术在古代文化发展史上写就了辉煌的一页,其重要意义还在于对内徙胡人的蜕变起到关键的指引、示范和带动作用,以拓跋宗室为例,汉化、文士化及贵族化进程高歌猛进,⑤孙同勋:《拓拔氏的汉化及其他——北魏史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一时间人才济济、著述锋出,这些都应拜它所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