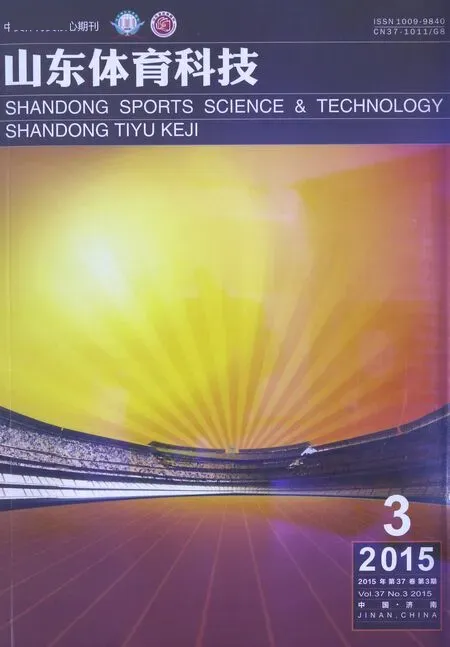武术表演:中国武术文化的再生产
刘红军,陈发祥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学工部,安徽宣城 242000)
武术表演:中国武术文化的再生产
刘红军,陈发祥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学工部,安徽宣城 242000)
现代化是一个重新解释传统的过程,武术表演作为武术现代化的产物,是对中国武术文化再生产的过程。运用文献资料、对比分析等方法,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大背景下,从武术运动员与武术演员的身份比较,武术“打”与“演”的艺术纠结以及武术表演与大众体验的真假之辨三方面的解读。研究得出武术表演中表演者对于中国武术文化的身份再生产、武术表演舞台对于中国武术文化空间再生产以及武术表演中观众对于生活武术的再生产。
武术表演;文化再生产;身份;空间生产
今日的中国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是一个文化与社会的变迁过程,社会充满了差距与矛盾,“文化脱序”[1]现象比比皆是,武术在此过程中也呈现出种种异化现象[2],并引起人们对于“武术现代化的困惑与反思”[3]。这实质是武术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文化认同危机”[4],在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就存在“真我”的迷失与“认同”的危机。如中国学界存在的“反传统”的呼声,就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体用之辩,但“反传统”反的是“文化传统”,而不是“传统文化”[5]。“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等人的反传统其实不是反中国的元传统终极信念,而是对传统文化的再解读,其反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僵化传统解释[6]。对于这种“文化传统”下的中国,汤因比称其为“僵化的文明”[7],因此金耀基提出新传统化的观点,对传统进行“重估”[8],也就是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9]。武术研究者对于武术现代化的再生产认识经历了从“武术观念现代化”[10]到武术现代化“出场”[11]的过程,即对于“武术现代化的转型”[12]的关注,武术表演就是武术现代化转型的结果。在武术发展的过程中,就其“生活化与艺术化”[13]而言,武术表演在重新解读武术文化的同时,通过“视觉队伍”[14]的生产来达到“自我认同”的目的。但现代化的武术表演在赋予赛场选手与舞台演员身份转变的意义重组之时,在“打”与“演”的文化模式重构之时,在观众“新体验”出生活武术之时,如何在不知不觉中进行文化再生产?本研究将试着从转变的身份、重构文化模式以及生活武术再生产等方面进行解读。
1 身份的转变:赛场选手与舞台演员
身份根植于现代化的内在矛盾,其最根本在于对“我是谁”的追问,以致达到一种身份的认同。武术表演在同化武术运动员身份的过程中经历了从传统固定身份认同向现代多元身份呈现的转变过程,以达到对于武术演员身份的认同。简而言之,规训化的武术身体从赛场以“打”为主的运动员身份向艺术化的武术身体在舞台上以“演”为主的武术演员身份转变,在武术表演中,武术演员实则是一种传统(运动员)身份与现代(武术演员)身份的重叠。
1.1 规训化的角色
武术运动员是通过长久的武术训练而获得的一种身份“称号”,现代化社会中的武术运动员较古代武者有所不同,已不再是暴力的所指,亦不是侠高义重的尊称,而是一种围绕“奖牌”而吃苦耐劳的群体。比如2007年春晚武术节目《行云流水》则主要由世界武术冠军周斌以及全国武术冠军马建超等领演。由于武术技能对人体极限的要求,武术运动员多通过艰苦的训练而具有一定的武术技能水平,这一过程是刻骨铭心的。正如米歇尔·福柯的身体规训认为的那样,规训权利不放过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从而使身体变为一个机器,一个工具,“这是一种操练的肉体,而不是理论物理学的肉体,是一种被权威操纵的肉体,而不洋溢着动物精神的肉体,是一种受到有益训练的肉体,而不是理性机器的肉体”[15]。规训化的武术身体,已经是具有武术自觉的身体,正如“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的气质,其言行举止已经嵌入武术运动员所特有的标签。
经过这种脱胎换骨似的训练之后,人体从自然人转变为具有特殊武技的“超人”,从一般的社会人身份转变为“武术运动员”身份。这种转变往往伴随着痛苦延长的过程,从其被赋予“武术运动员”身份之时开始,一直延续到“武术运动员”身份的“退役”,甚至在其生命即将终结之时,这种职业的痛苦可能依旧牢牢的被规训到其灵魂深处。值得庆幸的是武术运动员的职业痛苦也有其摘金夺银的辉煌,当历史回过头来审视武术的成功历程时,也许喝彩与感动能够抚平一切。1.2 传统与现代的身份重叠
如果说以赛事夺取奖牌的武术运动员是其传统身份,那么在舞台上进行武术表演的武术运动员则具有了一个现代化的身份——演员。基于此,在武术表演中的武术演员则具有了传统与现代的两种身份,武术演员实则是一种以现代方式演绎传统的“混合人”。这个“混合人”既要与传统的规范化武术运动员对话,又要与艺术化的演员交流;既不能丢失传统武术的“高、难、美、新”,又要紧紧依附在唯“美”马首是瞻的观众需求;既要具有赛场的淋漓尽致,意气风发,又要有舞台上真切的感觉和艺术的想象,比如李连杰、吴京等早期武术运动员,今日众所周知是其武术演员的身份。
武术表演的传统与现代身份,其实也可以认为是武术的媒体形象和武术的自我形象。媒体形象就是人们在大众传媒中所接触到的武术规范动作,这些动作规范极严,极具典型。而武术的自我形象则是将武术的想象力(攻防技击)完美地传达到观众中间,具有一定的自由把握,这时候的观演关系就是打与想的关系。武术的技击性不是演练的套路,亦不是简单拳腿组合的散打。观众要具有武术的想象力,理解武术规范动作与规范基础上自由打的动作之间的含义;这也对观众的武术基本常识提出了挑战,武术演员的水平与观众的水平落差要足够小,这样才能促使打与被打之间的衔接与观众武术想象力相吻合。
1.3 呈现艺术的身体
武术演员出现在舞台上时,就不再是武术运动员以“战胜对手,夺取高分”的身份宣扬了,而是一种满足人人皆可体验真切性的观众心理需求。武术演员的身体是一种运动规训后的身体,具有自我规训的意识,其满载着中国武术——身体文化的全部要义[16]。武术演员的身体已经不是呈现武术的身体,而是一种“艺术品”,正如福柯所倡导的那样,“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创造成艺术品”,才能把每个人的生活都“变成一件艺术品”[17]。
武术表演不同于武术比赛,武术比赛是按照评判标准而推进的,武术表演则是按照观众审美而演绎的。这就要求武术演员缩短自我与角色之间的距离,缩短角色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规训化的身体如何与复杂多变的观众心理产生共鸣呢?武术演员如何在规范与自由之间定夺呢?在这里我们引用人类表演学中的一个术语——规范的自由动作,[18]以做解答。规范就是整个武术表演要经过编导的精心构思,角色与武术风格的匹配,武术风格与故事情节的切合等等。在规范与自由两端之间有着各具特色的类别,对于某些武术动作规范极严,一点都不能走样;有些则要求大量的即兴表演,有很大的自由度。在规范与自由之间探寻武术表演的平衡点,以期满足观众对于现代身体通过光怪陆离的舞台演绎古老的武术传说。
2 模式的重构:“打”与“演”的纠结
武术表演将武术引入到另一种艺术文化模式之中——表演艺术。武术表演不同于武术比赛,在赛场与舞台之间,武术由“打”的场域再造出“演”的空间,通过对武术文化场域空间的再造,形成一种以“演”为主的文化场域。这种新的武术文化场域不再纠结于“打”与“演”的关系,而是根据新场域的游戏规则进行武术文化再生产。
2.1 场域的再造
场域是指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是一个构型[19]。武术表演将武术文化纳入到一个新的场域之中——表演艺术,这种新的关系网络是对武术文化场域的再造,亦是武术文化空间生产的结果。新的场域的产生就意味着一种新的武术文化模式(网络)的构筑。特别是近年国家武术表演艺术团体的成立,高校武术表演专业的设立等,为武术表演在表演艺术中的确立,开辟了新天地。伴随着场域再造的是资本的争夺,“作为包含各种隐而未发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空间,场域同时又是一个争夺的空间”[20]。将武术纳入表演艺术行列,表面上是对社会大众资源的占领,实则是武术的话语权控制范围的延伸。
相较于传统的武术的拳场、赛场、擂台以及仪式等文化场域,再造的武术文化场域是武术现代化的标准,其具有接近生活、易被大众认同、具有明显的现代科技痕迹等特点。武术表演为武术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也为武术文化的生产提供一种模式。
2.2 武术空间的转移
武术表演将武术意义空间从“打”的赛场扩大到“演”的舞台之中,这种场域的转移(扩大)可以说是武术文化在赛场与舞台两种不同的场域中,进行自我场域意义的再生产。赛场具有激烈残酷的竞争性,其表面上是与对手的较量,实则是对自我极限的挑战。赛场上的武术之“打”更多的是遵循武术运动规律,以及严格的武术规则进行的[21],这种“打”的对象可能仅仅局限于裁判。
从强调“打”的空间向“演”的空间扩大,则武术这一文本就从运动的规律性,规则的严格性向观众的妥协性发生转变。按照观众的审美需求,武术表演仅有“高、难、美、新”是很难生存,其“演”要在“打”的基础上进行重新构造。首先要融于舞台的艺术化要求,与灯光、音乐、角度等等紧密结合;其次要具有故事性,如少林舞台剧的取材大多呈现的是一种故事化的少林寺僧徒;最后在迎合观众审美口味的同时,也要敢于挑战观众的审美习惯,给其一种超乎想象的惊叹美。武术表演只有牢牢的把握观众的审美空间,不断的调试不同文化之间的表现形式[22],才可以牵引观众。
2.3 “打”与“演”的艺术化
武术表演不是“打”与“演”媾和妥协的结果,而是一种内在化的艺术行为,是以观众欣赏,艺术需求进行的艺术行为。关于“打”与“演”辩论,自民国以来便一直喋喋不休,蔡龙云大师曾有过关于“击”与“舞”的精彩论说,戴国斌教授利用霍尔的解码理论学说对“打”与“演”进行了重新解释,并认为“打”与“演”实则是两种不同的编码和解码系统,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来解读身体语言和动作信息,有不同的消费方式和不同的解读方式[23]。舞台艺术针对不同的编码系统,进行艺术化的意义解读,不管是武术的“打”,还是武术的“演”,最后都转变为观众的“看”,这样的武术表演才具有表演的意义性。
武术界存在“打”与“演”的争论焦点都是围绕武术“技击”的特性。武术发展至今,对于“技击”二字,很多人仍是“宁死不放”的态度,随着人们对于武术研究领域的开拓,对于武术意义的重组,作为文化现象的武术已经远远超越身体技术这一范畴。就武术表演的话语而言,其强调的首先是对于艺术的追求(大众的审美),其次才是武术的技击性,但是这并不说明“技击性”不再受到重视,只是强调的表现面不同,武术表演更加强调艺术化的武术。
3 生活新体验:舞台与社会
武术表演以迎合大众审美进行武术文化意义的重组,在这个再造的场域中,主导武术命运的不再是评判运动员的裁判,而是舞台下一排排的观众。武术表演对观众审美的迎合与观众对武术艺术集体体验是同时的,这种体验关系直接取决武术表演与观众的共鸣。舞台上的武术表演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描绘,即武术生活的再生产,形成迎合——体验——归真的武术生活化再生产。
3.1 对大众的迎合
在武术表演中,观众作为一个接受者的群体,在心理活动上具有公共性和预设性,这是武术表演最大的透明障碍,也是武术表演意义之所在。正如法国18世纪著名戏剧家席勒所言,一切艺术的基本形式,皆由接受者的需要决定。这就要求武术表演的主题必须涉及人类的天性,且富有感染力;武术表演的角色塑造要迎合观众的口味。
武术演员要以承载着武术特色的身体艺术满足观众的期待视域,但是这种期待视域的满足并非易事,由于武术在大众思想中的神秘性,以及大众在此之前的审美经验和生活经验的积累,很容易造成武术表演与观众期待视域之间的落差。这种落差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观众审美心理定势造成的,这也是观众在观看演出时接受、排斥、错位或者误读演出的基点。比如2010年春晚节目《对弈》,实则是一种“武”与“舞”的对弈,而并非人们所期待的对打。表面上看观众的心理定势仿佛是武术表演的天然障碍,实则不然,按照余秋雨先生的观点:心理定势使观众的心理活动出现了稳定性、有序性和可辨析性,为探寻观众心理规律带来极大便利[24]。不难看出武术表演可以利用观众的审美心理定势发展,以迎合观众的审美口味。但是“口味”迎合也未必是长久之计,按照接受美学学派——康士坦茨学派的观点“任何一种接受,都是一种落差的改造”[25],武术表演被观众接受或者记忆都是对这种落差改造的过程或结果。但是“迎合”则明显的指出武术表演对于观众的屈服,改造落差的过程中,武术表演始终是主动的。
3.2 从个体体验到集体体验
武术表演是预先设计的艺术行为,这种设计的节奏是环环相扣的,只有导演和演员心知肚明整个故事的过程,观众总是依据一种已经确定或已经被设计好的主体位置来回答武术剧本的召唤。武术表演的过程性,存在于舞台与观众之间的不断连接中,即舞台表演者的呼唤与台下观众的回应。这种不断的连接,形成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心理交融,其结果是台上、台下共同进入一种集体体验。演员与观众联成一体,共同感受,共同领悟演出的内容。武术表演就是为这种集体体验提供一种机缘。
西方戏剧家认为观众是“只有一颗心的多头巨人”,这意味着观众之间更容易取得一致性,这对于武术表演的评价在观众之间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如邻座主观臆断的评论,可能就会造成正常审美程序的顿挫,甚至断裂。由于观众身份各异,武术表演就要以整体性情境来消解某些观众的尖锐,武术表演主要以肢体语言为主,这种无声的语言更多传达的是一种力量感。如2013春晚武术节目《少年中国》中武术演员着中山装的正派凌然,打通背拳的潇洒矫健以及壮丽山河的背景等等都是一种对观众热血沸腾气氛的营造,从而促使节目要传达的精气神在观众那里得到回音。但只有无声语言是很容易造成部分脾气急躁观众的失落,武术表演就要满足观众的眼睛,又要满足观众的耳朵。武术表演的服装、器械以及布景等等皆可设计成“似曾相识”的生活。在整个武术表演过程中使观众产生一种“恍若前世见过”的感觉,这大多出于今世已有的审美经验的延伸和衍发。
3.3 武术表演在生活中的真假矛盾
武术表演小则是在模仿具有攻防技击意识或行为的人,大则是在模仿人的社会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生活是原点,是客观存在的,然后戏剧才去模仿它。武术表演要源于生活,这样才能拉近与观众的距离。武术本是用于攻防打斗的技能,现在又结合舞台而演示出来,那么武术表演就必然要融入舞台。
融入舞台的武术表演在紧贴生活的过程中要积极营造一种“貌似极真实”的错觉,当然舞台上的真实与生活中的真实不同,“舞台上的真实是演员真正相信的真实”[26],这种“真实”是存在于武术演员自身、武术演员之间以及武术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在武术表演的过程中,演员手中挥舞着刀剑等器械进行貌似真实的打斗,事实上,他们不能真的刺中对方。但是古罗马的角斗士表演却是真的杀人与被杀,虽然他们的表演和今日武术表演一样是为了取悦观众,但这种“真杀”难道就不会出现在武术表演中吗?武术表演如何避免“真杀”的出现呢?首先是武术表演者的自我失误的规避,其次是武术表演者之间对于误伤的规避,最后是武术表演者与观众之间防止“器械意外”。我们更要防止的是生活中人们对于武术表演“杀人”的模仿,以及戏里戏外,以假当真的错觉。但矛盾的是武术在台上炫耀自己的技击性,却又要在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与仿真生活的武术表演之间构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
4 结语
武术表演是一种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艺术行为,不管是武术表演本身还是武术表演场域中的所存在的意义,都是对于中国武术文化再生产过程。以“打”为主的武术运动员从对于赛场上分数的追求,向以“演”为主的武术演员对舞台上的艺术追求的身份转变,实则是一种对武术文化空间与身份的再生产。不管是扩大化的场域还是转变的角色,其终究没有偏离“打”与“演”的命题,不同的是前者重在以“打”取悦赛场上的裁判,后者通过“演”来改造身体的艺术化,达到对舞台之下观众的审美迎合,这个过程中也是武术生活化生产的过程。
[1]Dodd,Elizabeth.Disorder[J].Georgia Review,2008,62(1): 81-94.
[2]戴国斌.武术现代化的异化研究[J].体育与科学,2004,25 (1):8-10.
[3]刘鹏,等.武术现代化发展的困惑与反思[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8,32(3):70-74.
[4]E.H.Erikson.The Childhood&Society[M].W.W.Norton&Co.,1950.
[5]庞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J].科学中国人,2003(4):9-11.
[6]张光芒,王明科.中国文化的当下语境:在传统、现代化与现代性之间[J].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5(1):26-39.
[7](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8]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15.
[9]Pierre Bourdieu,Jean-Claude Passeron.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Society and Culture[M].London:Tavistock,1971:98-110.
[10]郭志禹.论观念转变与信息化促进武术现代化[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28(10):1301-1302.
[11]李龙.论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现代化出场[J].中国体育科技,2010,46(2):140-144.
[12]杨旭峰.武术现代化转型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1 (6):113-116.
[13]陈春娣,乔凤杰.作为艺术的武术[J].体育科学,2007,27 (6):77-81.
[14]戴国斌.武术的文化生产[R].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2008:111-113.
[15](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元婴,译.规训与惩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75.
[16]戴国斌,著.武术:身体的文化[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11:3-4.
[17](英)路易斯·麦克尼,著,贾湜,译.福柯[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164-165.
[18]孙惠柱,著.社会表演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94.
[19](法)布迪厄,华康德,著.李猛,等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4.
[20](法)布迪厄,华康德,著.李猛,等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9.
[21]蔡龙云.如何欣赏武术表演[A].蔡龙云,著.琴剑楼文集[C].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7:75-76.
[22]Cheng zhou.World drama and intercultural performance: Western plays o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tage[J].Neohelicon,2011,38(2):397-409.
[23]戴国斌.武术:身体的文化[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11:202-203.
[24]余秋雨.观众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35.
[25]姚斯.文学史作为对文学理论的挑战[A].朱刚 编著.二十世纪西方文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42-245.
[26]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吴霜,译.我的艺术生活[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369.
Wushu performance:the reproduction of Chinese Wushu culture
LIU Hong-jun
(Dept.of Student Working,Hefei Polytechnic University,Xuancheng 242000,Anhui,China)
Modernization is a process of re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Wushu performance,as a product of Wushu modernization,is also a process of reproduction of Chinese Wushu Culture.This paper,based on the overall background of modernization and by apply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has clarified the three aspects of Wushu culture,including:the identity comparison between Wushu actor and Wushu player,the art entanglement of"fight"and"performance"and the relationship of people's life and Wushu performance.In addition,this paper has sorted out the reproduction of Wushu identity by Wushu actor in Wushu performance,the reproduction of Wushu culture space in the performance stage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Wushu culture in people's lives by the audience in the Wushu performance.
Wushu performance;reproduction of culture;identity;space reproduction
G80-054
A
1009-9840(2015)03-0017-04
2014-09-05
上海体育学院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编号:xsxr2013039)。
刘红军(1987- ),男,安徽涡阳人,硕士,研究方向武术教学与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