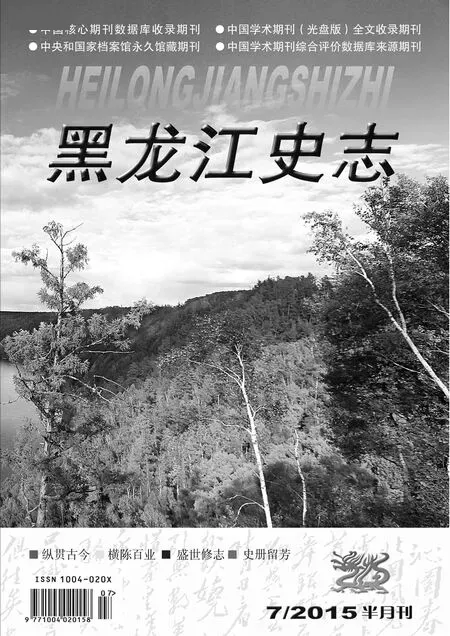符命神话与中国古代王朝的天命建构
——基于政治传播视角的考察
王慧珍
(许昌技术经济学校 河南 长葛 461500)
符命神话与中国古代王朝的天命建构
——基于政治传播视角的考察
王慧珍
(许昌技术经济学校 河南 长葛 461500)
作为思想文化的基本形态处于相对混沌与蒙昧的封建时代,为了实现控制人心,加强政权统治建设,满足小农思想统治下的民众对传奇帝王的图腾心理需求,符命神话在封建王朝的人治体制中往往成为一种无声的政治话术,并对人心起到了不可遏止的垄断作用。与欧洲的很多封建国家相比,中国的封建王朝体制建设更加健全系统,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命脉更加根深蒂固,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符命神话文化体制在古代王朝中的天命建构远超过同时代的西方国家,在政治文化的中国成为不可忽略的粉饰帝王雄主的重要手段。
符命神话;天命建构;古代王朝;政治传播
前言
尽管中国历来奉行政教分离的统治原则,宗教因素并不占据国家政治生活的首要地位,并要接受世俗政权的支配与控制。但是封建主义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搭建起的统治平台,除非像美国这样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的国家,大多民族在封建王朝的发展历程中,尤以符命神话的帝王色彩手段为甚,广泛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封建王朝统治时期。作为一个以天命为抽象信仰单元的民族,帝王如欲促成有效的长期统治,往往需要在民间广泛播撒有关自身符命神话的渲染色彩,将世俗的权力与作为披上神秘的外衣,以强化统治。
一、符命神话的理论支持
(一)君权神授
符命神话在中国古代君权专制年代中的理论形成,始于西汉武帝时代。哲学家董仲舒鼓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方略,将孔孟时代的绿色儒学注入了宗教教化的色彩,完成了儒家学说的官方化任务,为封建统治的思想驾驭填充了丰厚的精神内涵。“天人感应”与“君权神授”成为了封建统治者驾驭民众的有力武器,并获取了秦朝的酷刑没有收获的统治成果[1]。因此符命神话在封建政体内的完全确立,首先属于一种统治成本的降低与其效果利润的最大化所致,易中天先生在《帝国的终结》一书中将这种转变性的成就评定为“权力阶层取代了暴力机构”,自此开创了权力治国的天下。中国古代王朝的天命架构,就在这种君权神授的指引下,逐渐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驭人之术。
(二)民间方术与经典论著
符命神话在民间的文化视野中能够得以广泛的传播,并能够形成稳定的信仰群众,除了官方御用者们的渲染之外,浓郁的乡野文化与民间方术在民众观念中的根深蒂固也是重要的理论基础。论及民间方术,便是盛行于民间的巫术操作技术,后来与《周易》相结合而形成了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文化[2]。民间方术在符命神话的影响之下,仍然能够起到垄断精神意识的作用,如陈胜起义的前夕,暗中令军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又如宋神宗时期,广西地区所谓的麒麟降生等无稽之谈的出现,均体现出民间传说对传统政治的垄断与渗透。至于经典论著,主要的代表作便是《周易》,以及根据《周易》的推演而形成的《推背图》、《烧饼歌》等对国运及统治者个人的推理和演算,也往往被历届统治者奉为圭臬,并依据其中的说词而针对个人的仕途而大做文章。
(三)奇闻意趣
除了官方的宗教伦理与民间方术的巫蛊技术外,奇闻意趣的流传也是构成符命神话的主要元素。汉高祖能够开创大汉王朝四百年的基业,与当初的斩白蛇起义的传闻便存在着浓烈的渲染联系;三国时期的曹操谯水击蛟、刘皇叔跃马过檀溪等传奇故事的流传,也无非是为曹操、刘备等枭雄的天命所归而制造舆论声望。但是这种奇闻意趣的故事体制仍旧与官方所渲染的天命意识息息相关,并受到其支配与约束。总体看来,帝王或成功起义领袖的符命神话正是官方理念、民间传闻以及个人经历等方面的综合体[3]。如著名的笔记体小说《世说新语》中曾经记载着这样一篇微故事,晋武帝司马炎率领文武百官抽签以定夺帝王谱系的传承代数,当抽到很尴尬的“一”的时候,群臣皆变色。唯有大臣裴凯从容应答:“天得到了一便清净纯朗,陛下抽得一,江山必可高枕无忧。”这一句机智的应对中,实则蕴含了中国古人对天的崇敬,并且在民间迷信的官方化进程中也体现出了浓烈的趋向。
(四)生理异化
除了奇闻意趣之外,帝王的一些奇异的相貌也是能够促进符命神话体制丰富的主要来源。所谓的帝王之相,往往在传统的传说意识中占据重要地位[4]。如刘邦的“美须髯,左股生七十二黑子”,晋文公的肋骨相连以及舜、项羽以及南唐后主李煜等帝王的“一目重瞳子”等异化的形象写照,都是符命神话追加在封建帝王身上的有力武器,并为在实现自家统治的软环境建设过程中,达到了震慑性的信服力与知名度。除了相貌方面的一些记载之外,一些英雄壮举也成了堪称有口皆碑的重要素材。中国历史上有南宋高宗的“泥马渡康王”、皇太极因荣获传国玉玺而被认定为称帝上的众望所归等,均可视为对形象异端上的变相补偿。此外在西方国家的封建历史上,类似于英国金雀花王朝的狮心王理查德、德国神圣罗马帝国的红胡子腓特烈等同样是不胜枚举。
二、符命神话的表现特征
(一)主要围绕时任统治者
符命神话的主要修饰和渲染的对象,在于时任统治者。符命神话的浓墨重彩本身的目的在于增强在世帝王的威信和魄力。因此在帝王在世之时,越是繁多的神话特征的凸显,便越是能够引发对当朝帝王的图腾意识,如汉武帝、宋太宗的几次进行的封禅典礼便是重要的写照[5]。除了针对一些当朝的帝王而言外,在动乱年代也着重体现在权臣篡位的神话天命上来。如著名的《太平御览》中曾经做出如此的断言:“代汉者,当涂高也。”围绕着这一毫无依据的论断,便展开了各种粉饰自己的解释。如袁术字公路,其中的“路”与“涂(涂)”相对应,袁术便认定当涂高隐喻的是自己。而对于当涂高官拜丞相的传说,曹操又在许昌朝廷内恢复了东汉时期荒废二百年的丞相三公制,并在最终成为了实质意义上的胜利者。而曹操百年之后,司马昭再度谋权篡取魏国江山,其心腹贾充硬是在民间收集到一张多匹骏马组成的“大讨曹”字样的全图,进一步暴露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本质与野心。凡此种种,均可称得上是不胜枚举。
(二)紧密联系天文学理论
由于中国人对天存在着一种莫名的崇敬心理,因此在古代符命神话的编制过程中,往往少不了借助天文形象来预测国运的途径。中国古代星象天文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到唐代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质变:星象天文学在此之前,一直是单纯的占星术,而在唐代则与算命术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星象学:星命术,即用星象与生辰八字及干支神煞等因素相结合,来分析判断一个人的人生命运[6]。占星术是用来预测国家社会或自然界的灾异变化的学说和技术,它不针对某一个人,而星命术则与之完全不同,它不关心国家、社会、自然等非个人的事务,而只求认识一个具体人物的未来的命运。两者不仅在对象上完全不同,而且在预测时间上也有较大差异。作为文化的现象之一,星命术能在近千年的历史过程中生存于世俗社会,并起到一种宗教替代物的作用,而且是以一种自然的和风俗的方式存在着,这表明它是适应了一般民众的心理需要和知识水平的文化,故不须外力灌输而自有其感染力和生命力[7]。
(三)浓烈的思祖意识
除了针对封建帝王个人的渲染与粉饰之外,由于中国的封建王朝崇尚着的是“家天下”的本质和意识,因此对于个人代表着的家族背景与荣耀,也往往致力于带有符命化的夸饰与渲染。如唐高祖李渊追奉老子为其先祖,并在有唐一朝将道教的统治地位凌驾于儒、佛之上,这便增强了祖先的优越感,为封建统治的维系奠定舆论根基。三国时期的刘备假借皇叔的名义在各路军阀之间东征西讨,无非也是以述祖的手段扩大自己的政治品牌影响力。祖先崇拜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体系中根深蒂固,因此在具体的史书编纂或口述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有关祖先而实现神话描写的篇章。如伏羲与女娲的兄妹交尾而繁衍华夏先民、商王朝的简狄吞食鸟卵而生契、满足官方史料中记载着的仙女佛库伦吞咽鲜果而生育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等各种描写,都凸显出了祖先崇拜的浓烈的生命意识与情怀。
(四)鲜明的动物图腾
除了在帝王及其祖先的渲染之外,动物图腾也是符命神话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其国号的谋取便是借助了夏季昆虫活动频繁的层面与特征,而夏朝的开山鼻祖禹的原型正是一条虫子。及至秦始皇以后的封建大一统时代,动物图腾文化中最为鲜明的当要数龙。早在夏朝时期就存在着国王孔甲养龙的传说,及至汉武帝时代,民间针对龙的传说便纷至沓来,从“九似之说”一直到近代的各种考究,方才得以盖棺定论。闻一多先生认为,龙的主体是蛇,再加上马头、鹿角、鱼鳞等其他部件器官,便形成了龙。而汉族人在华夏时代以蛇为图腾,所记载的传说人物如伏羲、女娲、共工、祝融等均是人首蛇身的形态。而巴蜀的古鱼国以鱼类为图腾、西北的羌族人以白马为图腾,以及北方的匈奴族以鹰鹫为图腾,各种民族崇仰的动物各取其一,便构成了以蛇为主的各种神圣动物的综合体。龙作为帝王的代称,在君权文化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分量,因此动物图腾也是符命神话体系中的重要一环[8]。
三、符命神话的横向比较
符命神话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性质与地位,在传统政治传播的途径中显示出与西方封建社会截然不同的特征。首先在于经济基础的不同,中国封建社会与西方国家的封建社会虽然均以“封土建国”为主要政权组织形式,但是其经济基础却存在着截然的不同。中国的封建经济基础以小农经济为支柱,工商业处于从属位置;而欧洲和日本的封建社会恰恰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庄园经济,工农商各种产业的相对分离,使得封建王权的控制力度远不及中国的皇权。溯及到帝王的符命神话中,欧洲帝王除了理查德、路易十四等寥寥可数的帝王之外,少有对帝王进行符命的渲染与描摹;其次在于王权的地位不同,中国的皇权凌驾于一切权力,至高无上,而欧洲的国王享有的世俗权力则要让位于天主教皇们的教会权力,在亨利八世以前的时代,国王对国家起到的作用相对有限。而这也造成了皇权图腾的程度在欧洲远远逊色于中国的汉唐王朝。最后在神话与宗教的结合程度上,欧洲的教皇主要借助巫术技术实现对国家秩序的操控,形式单一而死板,导致中世纪欧洲的上层活动较为贫乏。而中国封建社会由于地地道道的人治色彩,在帝王活动中,越是雄才大略往往越容易对固有体制产生冲击,这便在客观上滋生了对圣君的崇拜意识,而各种符命神话的渲染描摹也就不请自来。
结论
制造与传播符命神话是古代中国开国帝王建构王朝天命最常用的政治传播手段。这些符命神话或者表现为以帝王身体为载体的感生、相貌异象、异事等帝王神话,或者表现为以自然异象或谶言为载体的一般符命神话。在符命神话的传播中,历代王朝既运用以官方信息传递系统为载体的官方传播模式,也依靠以谣言为载体的非官方传播模式。符命神话在王朝天命的建构中是有效的,不仅是因为其传播的速度与范围非常可观,更是因为这些符命神话的制作是基于当时民众普遍的信仰与历史记忆体系。
[1]白文刚.符命神话与中国古代王朝的天命建构——基于政治传播视角的考察[J].青海社会科学,2014,1(1):12-15.
[2]张华.汉代文学中的神话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3.
[3]李莉.神话谱系演化与古代社会变迁[D].长春:吉林大学,2014.
[4]白文刚.政治传播在中国古代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2):28-32.
[5]赵沛霖.中国神话的分类与『山海经』的文献价值[J].文艺研究,2013,1(1):95-104.
[6]胡晓明.图腾、图腾神话与古代符瑞——中国古代图腾文化新说[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85-90.
[7]叶舒宪.中国神话学百年回眸[J].学术交流,2010,1(1):154-164.
[8]李丽丹.中国神话研究现状:进程中的反思——以2004年神话研究为中心的分析[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1,1(1):1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