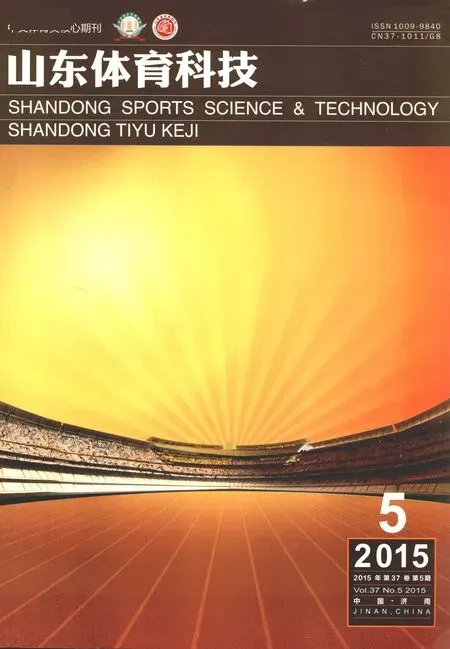我国体育法学理论类型研究
孙国友,李 江
(南京体育学院,江苏南京 210014)
我国体育法学理论类型研究
孙国友,李 江
(南京体育学院,江苏南京 210014)
基于不同的理论生成方式可以形成不同的理论类型。梳理我国近30年的体育法学研究成果,探讨基于“外生型”和“内生型”、“实践型”和“理论型”、“前瞻型”和“回溯型”等不同理论生成方式所形成的“理论的体育法学”与“实践的体育法学”、“法学的体育法学”与“体育学的体育法学”、“西化的体育法学”与“本土的体育法学”、“回溯性的体育法学”与“展望性的体育法学”等理论类型,希望以此为我国体育法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理论品质的提升提供借鉴。
体育法学;理论类型;生成方式;体育法学研究
我国体育法学主要有“外生型”和“内生型”、“实践型”和“理论型”、“前瞻型”和“回溯型”等不同理论生成方式[1]。“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以不同视角察看问题,对问题认识的广度、深度也会不同,甚至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同样,不同的理论生成方式,基于其不同逻辑思路和分析视角,也会形成不同类型的体育法学理论。在梳理我国近30年的体育法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释基于不同理论生成方式,希望以此为我国体育法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理论品质的提升提供些许借鉴。
1 “理论的体育法学”与“实践的体育法学”
从“理论-实践”的维度看,我国体育法学研究采用“实践型”和“理论型”生成方式,主要形成“理论的体育法学”与“实践的体育法学”。所谓“理论的体育法学”是指以“发现”和“解释”为主要任务与重要特征,以构建、运用和反思体育法学学科系统理论为直接目的体育法学。“‘发现’的主要功用是陈述和测定社会事物之间的普遍关系”[2]。“解释”的功用是对在某种情况之下会出现什么现象做出叙述,但却不是那种一般性的或笼统的叙述[3]。“有了‘发现’才算科学,有了‘解释’人们才能判断这门科学成就的大小”[4]。“理论的体育法学”主要涵盖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以体育法学哲学研究为代表,这类研究更关注体育法学的应然状态,而不是对体育法学发展现实和体育法律实践的审视,更不是思考体育法学实践价值。如有学者从法哲学各种流派的诸多视角对法与法律、法律与国家、国家法与“活法”以及法律的本质属性等法学的基本问题进行解析,并据此对体育法概念的内涵、外延及体育法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等进行深入研究[5]。二是以体育法学元研究为代表,此类研究关注的焦点是实践问题的哲学化、理论性思考,以及“体育法学是什么”、“如何进行体育法学研究”等元问题,对理论研究进行反思和瞻望。如,逻辑起点是理论体系赖以建立的最基本的、可以统帅和建构理论体系的范畴或概念,有学者基于体育法学学科的内在属性,对研究起点与逻辑起点的关系进行甄别,认为体育行为是体育法学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6]。
“理论的体育法学”常常因为不能直接解决实践问题,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之间常常产生冲突,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鸿沟,而饱受质疑。有学者认为“理论的体育法学”有“以逻辑的实践代替实践的逻辑”的倾向,甚至可能陷入“为理论而理论”的窠臼。其实,这种担心有点“杞人忧天”,有窄化“理论的体育法学”内涵的嫌疑。“理论的体育法学”并不排斥“实践研究”,只不过其最终目的在于“发现”和“解释”,而不在于实践问题的解决。
无论是我国体育法学的研究现状,还是未来,对于“理论的体育法学”我们需要加强,而不是弱化,更不应是排斥。“理论不应该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解释,而是某种专业知识,是对常识的解构”[7]。在体育法学哲学研究方面,尽管法哲学对体育法学研究的指导价值已经得到广大学者们的认同,但系统深入的哲学研究却不多,这可能与体育法学研究人员知识背景有关。在体育法学元研究方面,有关体育法学研究的本质、目的等问题,鲜有系统涉及。“理论的体育法学”遵循理论—理论、理论—实践、抽象—具体、一般—个别的逻辑思路构建理论[8]。我们在呼吁关注实证研究和实地研究[9]的同时,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排斥思辨研究,盲目地否定和拒斥“理论的体育法学”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体育法学研究是一门应用性学科,但并不意味着不需要纯理论研究,完善的理论体系是学科重要标志之一。尽管思辨研究常导致“研究者很容易陷入自我思辨和‘独自’的泥潭,局限于自身经验而成为‘井底之蛙’”,看不到‘天外天’”[10],但问题绝不在于思辨本身,而在于我们研究者对思辨的掌控能力。
当然,就谋求体育法学改进之道的学科使命而言,“实践的体育法学”因“体育实践的需求而产生,重点关注社会实践,关注社会大众的现实需要求”[11]。正如“理论的体育法学”也以特定的方式讨论实践问题一样,我们不能因为“实践”二字,而误以为“实践的体育法学”和理论无关。事实上,“实践的体育法学”本身即是一种理论,它和“理论的体育法学”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上。在研究内容上,“实践的体育法学”“更多地关注法学理论在体育实践中具体应用和创造性地应用,以解决体育领域的法律问题”[12]。在研究方式上,“实践的体育法学”遵循着遵循经验—理论、具体—抽象、现象—本质、个性—共性的认识发展过程。在研究目的上,“实践的体育法学”主要为了促进体育法律实践中问题的公平、公正的解决,以促进体育和谐发展。“实践的体育法学”就是对体育法学相关人员,包括法律实务工作者和科研院所、高校的专家学者,针对体育法律实践日常所做与能做之事的概括,针对体育实践中产生的体育法律现象和问题进行阐释和解决为直接目的,它试图诠释体育法学的行动知识,并使之日臻完善。如,有学者通过对真实、典型体育法学案例进行法理上的分析,为体育争议处理机构解决纠纷提供法律上的指导。研究既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也分析体育法的具体运用中应当注意的问题[13]。
和不断变化着的、纷杂繁芜的体育法律实践相比,“实践的体育法学”尚不能完全担当起应有的责任。真正意义上的“实践的体育法学”尚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对于“实践的体育法学”如果理解偏差、运用不当,也会产生某些瑕疵,甚至可能无法达到服务实践的目的。研究者往往将研究的旨趣聚焦于自己熟悉或较易获得的主观经验上,这往往会给问题认识不全面埋下隐患,从而影响研究的“广度”。如在我国体育法学研究中微观层面的体育法律问题明显多于宏观层面的体育法律问题,主要是因为研究者更方便获得微观层面的经验,而宏观层面的经验较难获取。研究还停留在经验层面,尚未完成从经验上升到系统的理论层面,有些研究只是一些常识的改头换面。而“任何真正的理论,都以概念的逻辑体系的形式为人们提供历史地发展着的世界图景,从而规范人们对世界的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以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规律性和理想性为人们提供历史地发展着的价值观念,从而规范人们的思想与行为”[14]。否则,难以在更高的层次上对实践予以阐释,以指导实践者正确地、深刻地认识问题。秉承实践取向的研究者,通常还坚信并推崇“经验即真”的信条。经验是实践的结论,前提条件是很难被复制的,因此经验并不总是可靠的。如果对实践经验缺乏必要的识别与辨析,就可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信度”问题也随之而来。我们不应刻意回避归纳、演绎和推理,因为“实践的体育法学”存在着实践的代表性与理论提升局限性等隐患。
2 “法学的体育法学”与“体育学的体育法学”
从理论的学科来源来看,在体育法学研究中,“外生型”和“内生型”理论生成方式,可以形成“法学的体育法学”与“体育学的体育法学”两种理论类型。所谓“法学的体育法学”是指,以法学的知识与理论为基础和依据建构而成的体育法学理论体系。此类体育法学理论在体育法本质的认定上,偏向“法学”而不是“体育”。首先,具体表现在诸多体育法学论著与教材中,大量借用法学的概念体系和逻辑框架来构建体育法学理论体系。还有意无意地接受了一般法学的学术旨趣、价值取向、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具体研究内容上,大量存在着法学理论流派、法的原则、法的渊源、法的功能、法的价值等具有法学典型特征的内容。其次,表现为运用法学基础理论分析和解决体育法学问题;三是沿袭法学研究范式。我国体育法学研究存在政治法学、立法法学、解释法学和社科法学等四种研究范式[15],这四种研究范式和法学研究范式基本一致。由此看来,“法学的体育法学”借鉴或移植法学的痕迹显而易见。
尽管研究者也对我国体育法学中“借鉴多,原创少”、“移植多,消化少”等问题早有清醒认识,但就理解与建设“法学的体育法学”而言,借鉴和学习法学理论体系,是体育法学发展和完善的必由之路,尤其是在体育法学学科尚未成熟之时,没有比较成熟的话语体系,无法诠释相关理论,更需要借鉴法学的相关理论来作为学科理论构建的框架基础。学与不学,学多与学少,无需讨论,需要讨论的是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学习和如何学。我们对学习法学既不能以抗拒的态度全盘否定,也不能顺从的态度全盘吸收。我们要建设的毕竟是“体育”的法学,因此,我们既要深入探析法学经典知识,也要及时而适恰的引鉴法学当代理论;既要关切法学的学术旨趣,也要适当借鉴法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
在建设“法学的体育法学”的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体育法学的“体育”底色。体育法学的研究对象是体育法律问题和法律现象,其研究目的是为了体育的健康发展体育法学的根本出发点是体育发展效益,包括政治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学习借鉴法学理论体系和逻辑框架,主要是为了提升体育法学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而能否达到此目的,关键在于能否把握住“体育”二字的内涵和本质。因此,那种经由“内生型”的方式生成的“体育的体育法学”,才是支撑并引导体育法学理论与实践的“体”。
与“法学的体育法学”不同,“体育的体育法学”关注焦点集中在“体育法”与“体育”二者之间的关系上,即如何基于“体育”来思考和研究“体育法”。离开“体育”去研究“体育法”,无异于缘木求鱼。如,体育纠纷中有相当数量的关涉体育专业技术性质的纠纷,尤其是那些竞争型体育纠纷、管理型体育纠纷和保障型体育纠纷。对于这些体育纠纷,一般商事仲裁机构难以胜任。对此进行相关研究,如果无视其中的“体育”特殊性,其研究成果肯定无益于“体育”,,甚至可能造成体育纠纷无法解决。
尽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法学专家学者和法律实务工作者加盟体育法学研究,但由于绝大多数体育法学研究者是体育专业知识背景,因此,我国的体育法学有着较为浓厚的“体育学”味道。这既是我们建构“体育学的体育法学”的优势,也是我们的劣势。大多数体育法学研究者,能基于“体育”的特殊性分析,去解决体育法律问题。但常囿于“体育”的视角,局限于“体育”,而且对这种研究范式、方法论的理论自我意识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理论品位的上升空间较大。弄清“何谓体育学的体育法学”、“如何构建体育学的体育法学”等基本问题,并据此重新审视既有的体育法学研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3 “西化的体育法学”与“本土的体育法学”
就空间的角度而言,采用“外生型”或“内生型”的理论生成方式,又会相应地形成“西化的体育法学”与“本土的体育法学”。所谓“西化的体育法学”是指,我国研究者参考、借鉴或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体育法学理论,学习体育法律实践构建而成的体育法学。此类体育法学理论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直接介绍西方体育法学理论或实践,或翻译体育法学专著等为主要任务的相关研究。如,有学者以欧洲体育法规和政策为研究对象,分别从欧盟法层面和欧盟成员国国内层面揭示其独特和具体的体育法制度和规则,还介绍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等8个国家的体育法现状和经验[16]。这些译著或引进理论,为我国体育法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二是表现为,在消化、借鉴西方体育法学理论,或参照、探究西方体育法律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体育法学理论。这些理论倾向于用西方的理论主张改造我国体育法学理论或借鉴实践措施解决我国体育法律问题。如,有学者通过大量西方体育法律案例的剖析,阐释“用尽体育自治规则救济”“技术问题不审查”等西方国家争端解决原则适用特点,分析国际上体育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律和发展趋势,希望我国在体育争端解决机制的探索、发展和完善过程中能够予以吸收和借鉴[17]。
我国体育法学的发轫与发展,始终伴随着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体育法学理论和实践,尤其是在我国体育法学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更是如此。这种学习与借鉴不仅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亦具有现实的必要性,“拿来主义”有时候还是必要的。就历史必然性而言,一方面,西方不仅在现代体育法律实践的探索上先于我国,而且在理论构建上也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如,美国早在1950年就相继颁布了《奥林匹克协会组织法》等一系列包括体育内容的公共立法和专门的体育立法,并相应出现了系统化的体育法研究[18]。另一方面,尽管中外体育法律实践与理论建设过程中存在着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异,但共通之处也比比皆是。因此,我们在思考体育法学理论与实践问题时,必然会将目光转向国外,借鉴他山之石。
回顾我国“西化的体育法学”理论发展之路不难发现,在理论方面,我们当前对于西方体育法学理论的学习既存在对西方体育法学理论介绍偏多,研究较少,尤其是系统研究更是廖若晨星。对理论的吸收消化也存在囫囵吞枣,常抽空理论的深刻政治社会背景,就理论而理论,这很可能出现片面、粗浅甚至错误的理解和运用。“西化的体育法学”还存在着学习仅仅局限于学习和研究上,而落实在实践和探索体育法善治之道的不多,属于典型的“敏于知,讷于行”。如,关于体育法学研究方法方面,西方研究者比较注重实证和实地研究,并深刻认识到思辨研究的局限性。对于这一点,我国学者也早有深刻认识,但是能将此认识转化为行动的却鲜有出现。“西化的体育法学”在介绍或引鉴西方体育法律实践时,大多满足于案例和素材的简单呈现,而至于其实践背后的政治、文化和社会逻辑的分析鲜有涉猎。而这恰恰是我们借鉴和学习西方体育法学理论是最不可缺少的内容。
纯粹地做“东洋拉车夫”,将西方的体育法学理论和实践“搬运”到中国,这可能产生“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问题,会生产一些可增闻广见却无甚实用价值的知识。甚至可能会产生理论和实践无法耦合,将问题认识引入歧途等弊端。任何一种体育法学在最终意义上都应成为本土的体育法学,这是体育法学所担负的学科使命使然。
所谓“本土的体育法学”是相对于“西化的体育法学”而言的。借鉴学者对于“本土化”的观点[19],我们可以将“本土的体育法学”具体化为这样两类理论:一是指从本国国情出发,吸收、改造、借鉴西方体育法学理论与实践而成的体育法学;二是指基于本国的体育法学理论积淀和体育发展现状,自主创新而形成的体育法学。前者是次生性的本土体育法学,它主要起“洋为中用”的作用;后者则为原创性的本土体育法学,其不仅在应用上直接指向我国体育法律实践,也能够进一步丰富我国体育法学理论体系,提升其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
无论从提高与世界体育法学的沟通对话能力,还是从回应本土体育法律实践问题的能力来看,当前我国体育法学的本土化水平都亟待提升。首先,在学习西方体育法学理论与体育法律实践时,不能脱离西方和我国体育法律实践,更不能无视其主要是解决本土体育法律问题。其次,不能忽视我国体育法学发展历史、体育法律制度及其演进逻辑、以及研究体育治理的历史背景等,着力提炼出属于本土化的体育法学概念体系和理论架构。
4 “回溯性的体育法学”与“展望性的体育法学”
从“时间”维度来看,采用“前瞻型”和“回溯型”生成方式,主要形成“回溯性的体育法学”与“展望性的体育法学”两种理论类型。“回溯性的体育法学”是指以“过去之体育法律实践与理论”或“体育法律实践与理论之过去”为研究重点的体育法学理论。它一方面表现为总结过去研究成果和研究进展。如有学者回顾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进程,将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的发展进程分为:改革开放初期的逐渐起步、《体育法》促进下的广泛开展和研究组织推动下的日渐繁荣三个阶段;当前我国体育法学研究呈现出研究力量逐步加强,研讨活动持续开展,研究成果不断增多,研究内容日益扩展等态势[20]。另一方面表现为基于“理论的过去”或“过去的理论”,考察体育法律实践与理论之缘由。总结分析解决问题的方式、特点和规律等。如,体育法基本原则在学界尚未取得共识,有“九原则说”、“七原则说”、“五原则说”、“四原则说”和“三原则说”。之所以存在这些差异,有学者总结其根本原因在于体育法学方法论的薄弱,以及体育法学与法律哲学对话的不足[21]。“展望性的体育法学”则是指将研究重点聚焦于“未来之体育法律实践与理论”或“体育法律实践与理论之未来”的体育法学理论。在《体育法》颁布前,有学者就体育立法的指导思想提出建议,对体育法的基本结构和内容、体育法律体系等进行研究[22]。《体育法》颁行后,有学者对我国配套体育立法的内涵、设定目标的依据、原则和目标的主要内容、当前配套体育立法的主要任务及其实现条件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研究[23]。而无论是强调“过去”的“回溯性体育法学”,还是关注“未来”的“展望性体育法学”,它们又都以“现在”为立足点。只不过前者视“现在”为“作为过去的现在”,后者视“现在”为“作为未来的现在”。
缘于体育法学学科性质被认定为一门应用性学科,使得我们的体育法学研究习惯用横断的视角分析当下的问题,而缺乏纵向思考与历史意识。这首先反映为我国体育法制史研究比较欠缺。尽管近代体育立法最早可以追溯至18世纪初,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立法进入迅速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体育立法也逐步出现。但这演进路径是什么,变化背后的逻辑思路又是什么,我国学者鲜有涉猎。其次,我国体育法学历史意识的淡薄,还进一步体现为我们对于现实问题的探讨,往往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多作横向的考察,少有纵向的审视,习惯于快餐式研究,而缺乏对动态化发展过程的审视,只关注问题表象,不擅关注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隐藏于问题背后的东西。
就发展“回溯性的体育法学”而言,作为基础性的任务,我们除了要做好有关研究成果的梳理、总结,还要做好相关历史的“拾遗补缺”工作。首先,要对我国体育法律实践经验和重要体育法学思想进行系统梳理,逐步深化体育立法史、体育法学思想史等的研究,增加我国体育法学历史“厚度”。其次,要对我国体育法学科史进行研究,藉此厘清学科发展的渊源或核心问题,增进我们对体育法学学科发展历程的理解。第三,要对体育法学史研究的历史进行研究,以此提高我们理解体育法学研究史和思想史的深度、广度和信度。发展“回溯性的体育法学”还要求我们在理论建构过程中,对任何现象和理论,都要去伪存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养成证伪和证实的思维习惯,不盲从,不盲信。既要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又要审时度势,结合具体历史背景,认识理论的科学性和证明力。要科学的、发展的和联系的观点认识和理解各种理论和现象。卡尔·维克(Karl E.Weick)说过:“让一个人说自己吃了什么相对容易,而决定要点些什么则会更困难一些,……在科学研究中,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无法预知我们将会发现些什么,也无法预料在眼界更为开阔的明天,人们会对什么感兴趣”[24]。较之“回溯性的体育法学”,“展望性的体育法学”建构难度要更大。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不乏《体育法》立法、修改以及配套立法规划、体育仲裁立法等方面的探讨,但这些讨论往往止步于形式化的呼吁和倡议,局限于知识层面的分析和阐释,徘徊在研究行动边缘。大多时候,我们的研究或停留在“新坛装老酒”、重复陈旧论题的层面,或故作高深、其实讨论的是常识问题,或追求时髦、热衷于跟踪理论新潮,或坐井观天、局限在“以体育看体育”的狭隘视域中,缺乏用一种宽广的、面向未来的视野,从我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体育现实需求的角度讨论体育法律问题。真正以一种展望性的视角来确立研究范式、设计研究思路、选择研究方法和确定研究内容,是“展望性的体育法学”努力的方向标。
我国“展望性体育法学”存在的局限性,既与我们传统的思维惯性和研究价值取向有关,也与我们研究者认识能力和研究水平有关。在研究的思维惯性上,我们体育法学研究者对外来理论普遍采用的认可或接受的态度,缺乏必要的反思和创新,从而使得我们现有的研究重解释、轻预测,重论证、轻展望。在研究价值取向上,急功近利,心态浮躁,参杂着诸多工具主义价值取向,从而造成诸多研究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盲目短视的研究行为,对于“展望性体育法学”无异于自我毁灭。在认识能力和研究水平上,方法论和研究方法方面缺乏系统、严谨的训练,使得研究者对于未来的敏锐感知和准确把握缺乏研究工具。我国体育法学学科发展起步较晚,基础薄弱,研究者的水平参差不齐,对我国体育法律实践的认识和社会发展趋势的把控方面缺乏必要的体育法学知识基础。
5 结语
与体育法学理论生成方式一样,这里的理论类型的划分,并不是基于非常精准的、可量化的判断标准。在分类上,难免有相互重叠交叉的可能。有的研究可能同时属于几种理论类型,有的分类可能并没有穷尽选项,不能涵盖所有理论。作这样的分类研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呼吁更多学者培养自觉的理论意识,逐步提升我国体育法学的理论品位,促进体育法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成熟。
[1][8][11][12][21]陈荣梅,孙国友.我国体育法学理论生成方式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4,(29)3:203-208.
[2][3]乔治·荷曼斯.社会科学的本质[M].杨念祖,译,台湾:桂冠出版社,1987:6,18.
[4]邓正来.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88.
[5]周爱光.法哲学视野中的体育法概念[J].体育科学,2010(30)6:3-12.
[6]贾文彤,郝军龙,王晓强.体育行为:体育法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7(27)6:19-21.
[7]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16.
[9][10]孙国友.体育法学研究方法之研究[J],四川体育科学,2012,(3):4-7.
[13]苏号朋,赵双艳.体育法案例评析[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
[14]孙正聿.理论及其与实践的辩证关系[N].光明日报,2009-11-24:11.
[15]孙国友.回顾与瞻望:我国体育法学研究范式之研究[J],浙江体育科学,2013,(35)1:10-18.
[16]黄世席.欧洲体育法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17]李智.体育争端解决法律与仲裁实务[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2.
[18]钟薇.体育法热点问题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2.
[19]邬志辉.新世纪中国教育管理面临的挑战与教育管理学的使命[J].中小学管理,2005,(2):15-18.
[20]于善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的进程与评价[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5)6:29-39.
[22]刘晖,吴礼文,石刚,等.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若干问题的探讨[J].体育科学,1988(3):72-77.
[23]阎旭峰,于善旭,胡雪峰.论我国配套体育立法的目标与任务[J].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1998(4):7-13.
[24]卡尔·维克.组织社会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2.
Theoretical type of sports law in China
SUN guo-you,LIJiang
(Nanjing Sports Institute,Nanjing 210014,Jiangsu,China)
Different theory generation ways can form different types of theory.This paper has summed up the sports law research for nearly 30 years and analyzed different theoretical type of sports,including"theoretical sports law"and"practical sports law","sports law in law"and"sports law in physical education","westernized sports law"and"local sports law","retrospective sports law"and"prospective sports law"based on different theory generation ways such as"exogenous"and"endogenous","practical"and"theoretical","forward"and"back-type",hoping that it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sports law theory system.
sports law;theory type;generatingmode;sports law research
G80-05
A
1009-9840(2015)05-0024-05
2015-06-29
江苏省优势学科建设基金资助项目(苏政办发〔2011〕6号)。
孙国友(1973- ),男,江苏盐城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体育发展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