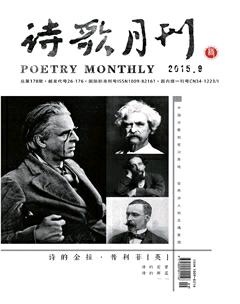道辉近作

道辉,1992年初创立“新死亡诗派”。200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版专集《大呢喃颂》(长诗)、《无简历篇》《语词性质论》《论人性文化·创造了不可能性》等多部。获第二届北京《十月》文学新锐人物奖。获2010年《诗选刊》第三届“中国最佳诗歌编辑奖”。获2012年《诗歌月刊》“年度诗人奖”。策划、主持“南方诗会”、“首届八闽民间诗会”、“新死亡诗派20年暨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研讨会”等诗歌会议多次。主编大型诗丛《诗》1-21卷。主编《新死亡诗派丛书》共40部。主编《诗书画》季刊。2010年创办天读民居书院。2013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和北师大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联合在北京召开道辉诗集《无简历篇》学术研讨会。
主持人语:
诗人道辉偏隅海边一角,近20多年来以他的写作毅力和创造力成就了一个奇迹一一他创建的“新死亡诗派”经历风雨,至今屹立不倒。可以说,道辉与“新死亡派诗歌”已经成为一个同义词。他的诗,充满了对语言的狂欢,或者说,语言是诗人的见证。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理解道辉,就是理解了修辞学上的阻截死亡。
一一兰坡
道辉的诗
道辉
房石
这些盲目之石
你确实辨认过它:怎么摸索到墙上
怎么混进了房间,变作一束飞蛾之光
你以养尊处优供它喝
这坚硬
你的手中用尽与黑暗通途衔接的晨野赞歌
那报丧草和从教堂移植过来的菠萝树
生长得多么快活
这时日,垒高的重量,飘吧
你仰视它像一幅赤裸的油画向太阳飘去
你的心胸
涌起新开凿人,踢踏起太阳石裙舞
把你践踏成路上的垫基石吧
那带着盼望、乡愁、幻影的防护堤石,来筑你之心
你破碎的心,长出疼痛之石
这世界的矗然起立
你心之石:大海的波涛天空的云朵
还有那凿刀不敢触碰的花朵,用尽沉默的喊叫
你在,世界就在
这边没有所有的人来为你筹措
只惟有一人用泛红的脸颊来与光亮磨蹭
直到你捧出明镜似的心看
所以,生活着就别发愁
银鱼像抖擞的诗句在屋檐下游
这幻景,比透明的狐狸出没还使你遗忘
你踩过长街的木屐,你挂上山崖的油灯,双行来采韵
所以,生活着就在希冀
那些爱上浮萍的人干起打捞流亡的活
他们的手腕不戴玉镯却戴废弃的铁丝网
他们刚走出一个贫民窟又在你面前划出二条生死线:
所以,你在,世界就在
噢品尝一股激流
你课桌上的水,可比海洋多,你可不敢说,日光四处有
掩饰了薄弱
你即可伸手凭空采来向阳花,白花瓣,做成旋转的塔
鸥鸟在啄身上的虫,给自己疗病
阴暗给未长大的孩儿教会土著话
那遥远的遗失的敲梆声重来围攻诗意的不安
一句句静静摇成“睡房内的摇篮”
歌声贩换“测试的钟表”
一个三国关联的村庄挂三只大咖啡杯当旗帜
家园:已从坦克履带上盛长出一棵棵棕榈树上黑熊的爪子,来照亮你头颅
你目光需要的是蓝宝石群宽恕的闪光,瞬间前
点水的蜻蜒就从闪光内飞掠出
放下屠刀的屠夫,重提锄刀的革命段子,伴着品尝这非凡激流
海洋仍把你的诗句变作窄巷
你手中的酒杯倒立,那已丧失教会你摸索灵魂能力的诸神的圣杯
却倒在稻草杆的摇曳中,大洋彼岸,仍在舰艇和面包的包绕中
今天,你仍食不果腹,但照常活着
你的嘴,仍被亲人们一次次翻新的谈情说爱占据
犹似疯子推着满卡车的榴莲果,来换一颗颗忧伤之心
那把阴暗当帐篷的人一个个走进去,那把
阳光当原野的人一个个走出来,犹似幻想,就在脚趾上
犹似天堂,就在你一个人的眼前,一个人,多么大的财富
你,即可伸手抓来鸡冠花,即可,抓来比天大的王冠光
即可在暴风雨降临前,把那一幅日出画
画得比油轮大,挂在自己的家门上
这实质是死亡之物的作品,也在眩惑闪光
你也即可
把那位为平分三寸地基石霸道的邻居
诅咒成不寒而栗的半只乌鸦
爱的字典
“隐秘”不是你能说,就能说出,现身面前
升日,蝎子一样爬上嘴唇
再爬高上去,即是冒烟的鼻管,呼吸喧嚣的世界
两个人的世界,牵扯一个气球
挂在教堂的尖顶上,教堂在暗光中坍陷
黑色的烛光拉扯大孩子,长大成梦想中的泪人
浆糊是来糊战乱的史书页,而不是日子之墙
沉默,谣言,墙上的杏树很快流产
草堂被残疾鸟投落的果子种击倒
轰跑出持刀偷情的情人,一周后,他们又摸黑拾回遗落的镜子和梳子
七年后,挂银镯子的儿子,来辨认真假父亲
假父亲品尝真父亲的勇气
真父亲教会假父亲用甜言蜜语吸引了异性;像巫婆嘴
把偷食的大公蜂吸收在灵魂乳房歌唱的陶罐里
直至我们的家,再也装不入呼唤的诗句
大海,在早晨的万光中爆破,波涛在偏向西方的光芒中耸立
那歌喉沙哑的精灵,重演着一幕幕死亡的戏剧
那不屈服死亡之人
穿着加冕的长袍
一伸手,就相安无事,广大无边,而不是说:隐秘,现身吧
隐秘一如黑洞,革命挨饿的黑洞
爬出一只只背着肉砧的铁蟹,沿途吞食萍草铺就的道路
鸥鸟冲掠如刀刃,把心灵劈作柴禾,伴同着煅烧世界
这爱情的字典内曾未出现过的象征词。
你的爱情
至今把我推到亲如绞杀的前线
不是让我呼吸花朵和鲜奶,而是死亡的气息
难道我们能把死亡
捧着比世界还硕大的
敞向而轰鸣的双乳房……
黑舵
荒原的空气
黑的舵
什么都会是可能,遗迹随时来砸你
你的心,衔接上草的头颅,未变灰前
草的头颅从地下冒出
思想时,挤出自己的苦汁
被读时,又回到轰隆隆的石垄处
那上边站着孤渴人,未变作良禽
先展开翅,翅上挂着轮子
手臂上托着家,家,第三只眼,骨碌碌
探照着白栅栏,挂满标语横幅的街区
生命、肉、花菜市场
孤渴人放弃油画来订制马铁蹄,穿越远方而去
最早揭锅的流星之光,也攀附不上你
云的衣裳淌下的血
野玫瑰,来虐待
你心灵,采摘人未来打理
那上边,没有头头,只有下属
累了在一枝叶树上挂布床,睡了还在仰望
他们为泉眼钻探,为山峦去污,干活,累了
什么都想放弃。所有的,一切
都等候死亡重来命名
说过的一一一句话,永不糜烂
看见的一一灿烂
都属于天上的,天不属于任何一人
天空,也睡觉
窥视着
长着双身榴莲果肉瓣的凡人之身。
闻着、闻着、向上旋转的
巨硕花般的,魂不附体的肉瓣
你就来蛊动我呀一一
你就是我能听得见的鼓,在空荡中发声
我转瞬
欲从你的胸怀走出,广大无边的胸怀,我走出
同你交了运,这是命呀
不是草,也不是暗中发光的草
在你闻见转声,天空就亮了
在你只身走出石屋外时,就见到
那举着锤子,站立着睡觉的草
那个鼻孔穿着草尖呼吸的我
远处,近处
荒原,是有年岁的
爆破,爆破,爆破,一个人,小荒原
你试着用手指尖转动的绸缎纽扣
来映照
腐烂处,更明亮,你拉开心的口子打理
心,幸福的家,也长在口子上
忧伤也长出来,伴着你扯住旗布的手
一同把天地覆盖住
我们,和我们朗读死亡的诗篇
就都住在这个覆盖内
想象,无意义
那样地迎接叛逆者,向暴风雨
致洗脑髓词
像雷达站,为海面的鼠患扫描
叛逆者
取下头颅的钢盔,放回
养金鱼的,一个人的家中
钢盔当
金鱼的家,夜光内,曾是子弹
把金鱼弹射出去一一如此幻象的
金灿灿的,思想刽子手
思想,上升
天空长成大草包
向人们倒下驱散乌鸦的稻草人
蜻蜓
电视架,避雷针
行了,危害皆无,它们,白忙,白搭
只是一些尘粒
投照着一群盲按摩师脚趾龟裂的反光
你知道,生存逆道而行
再厚的经书里读不到它
如此
舒坦人法则
如此,心机
交换法一一要么
面对着刷漆墙,打鞭子
你握鞭子的手,除了抓新疆的葡萄蹄子
其它的
抓住的,都美如画
天堂
印记
别学着坏人学习它了:骑在下属头上
当座椅,沉默
往往是一件短暂的外衣
旅途到相辅相成为止
旅途一一从你第一声呼喊
到海峡那边,一个人,听到为止
迷茫
变作毒汁为止,永是,招魂人
揭下面具遮住的伤疤
犹似在一片盐卤水击拍的晨光之岸
把番薯招揽为船坞
如此,沉默的
旅途,在座椅上
好给那些恶搞民意选神之人
够喝空荡一壶
可不是,鲸鱼,喷水柱的
一壶
这烫人的壶,神培植的番薯标本
你也别轻信
那双手捆稻草链的老妪
已在用符咒
念人
在广大无边泅渡
她,还用硬石敲纸扎的墙试一试
纸墙内
纸做的人,恍若
隐有所指,一个个叛逆者,一个个
对立的国家
敌人,罪恶的敌人,都死去吧
都化成灰吧
千万别轻信
念咒声,会成效,会成为
嘴唇翕动的
绿色广场,那赶着篷车的国王,会沿途
抛洒橄榄枝水和葡萄酒
来祭奠赠送一一真的,好东西
会让死亡,骑着他的手势
返回民间
返回,少男少女的腰鼓上
咚咚咚地响,大街小巷,响彻云霄地响
死亡,死亡
别在腰鼓上的魂,轻轻地响,愈响愈远
这,方才是
我们要听见的草的呼声,正午之雨
润万物之声,万家人
破门窗之声,声内,开始进出
拥抚幽禁睡去的自由人,繁殖的
敢向天空
抛掷重锤人,来了
你举手帮我在眼瞳内,夹出虫子
歌之技艺,修补了身
美好的,幻想中物
划出一道道淌着甜之血的闪电,修补了
你我合二为一的处子身
一个新世界的处子身
合着牛奶和钟声
能
把原子气筒,重塑为马蜂蜜罐
歌之虫,化世界为茧
你加入到抛掷重锤的队伍里
拿太阳,来融化白糖
圆的法则,由上至下
方方块块,再到黑暗的地下
地下人,世界正把他们当做亲切可敬的主人
地下的太阳,大理石诗章
开垦以至,不谦让时光,划分黑暗
地下,一个国连接上一个国
边界,撒旦,生死之界
互不侵略
互不论输赢,仅有,和睦的天平
让
彼此飞翔的翅膀,放在上面
扁的,歪斜的
粗糙的,尖利的
都变作圆的,来平分
太阳,不做侵略
高悬之镜,诺亚方舟
屠夫,锄草场
向星空撤除草剂
若
星都没了,你我的枕畔,哪还有安宁的夜晚
夜晚,你我身边扭曲的屠夫
专盯住
爱情遗落的一渍一迹,当做
疯狂的泄愤
疯狂一一创作,历来
即是,屠夫的品牌
垄断了,快乐城邦
诗篇中飞着的城邦,当,蜻蜒
变作云鹰时
这,上帝咆哮的粪便
常是,给你
煽动一根根个人小宇宙的白骨,当,你
专盯住光芒时
刹那遇见了鹰的白骨
眼睛便瞎掉
便陷入了世界新的黑暗中
诗篇
黑撒旦
用白骨飞着,用草灰
说还能用耳朵听的话
而不是爱情的腰鼓发出的声
远远望去
草叶上的晶露
如你转动欲的头颅
荒原已鸟散
黑的舵
插着桥墩像亿万个蒲公英
来带走你
所有的,一切
遗渍
闪闪
发光
有如你期待的幻想从天空向你抛掷幸福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