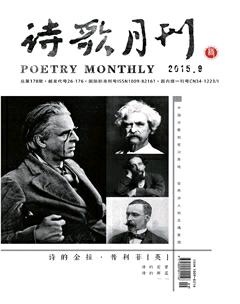爱是我创作的基础和出发点
黄沙子 曾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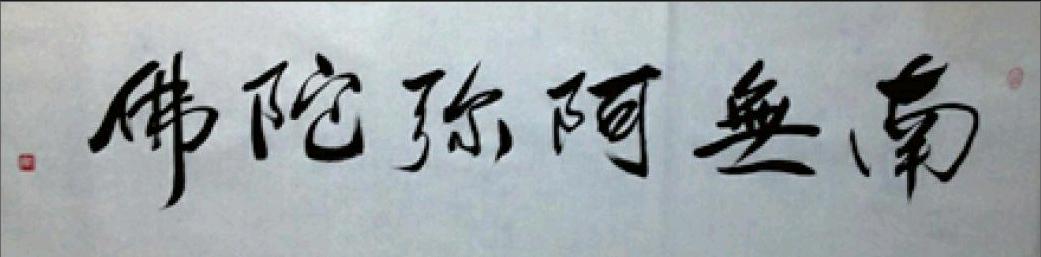
黄沙子:就我所知,你从事过的职业非常多。一多半时间,我觉得你是生活很优裕的人,虽然其中也曾看到你有一段时间非常窘迫,但总体来说,你是一个很善于享受生活的人。这些经历,对你的创作,包括诗歌、雕刻、书画的创作,带来多大影响?
曾宏:我的经历是比较复杂,也是迫不得已的事,一切为了个人生存及家庭的责任和义务。16岁初二毕业就去工厂当机修工,到30岁有孩子后才想到必须挣钱养家糊口。所以选择放弃铁饭碗。下海后大体是三个身份:营销员、地产从业者、职业经理人。干过的行当不下十个。你说的操盘手,那是个人投资,在股票上赚得很多,在期货上输得很惨,所以为了重新站起来,最多时每天三份工,比如早上到地产安排各项工作后,下午去私企当管理,晚上再去娱乐城当管理。也教过书,开过电脑培训连锁,还给专栏撰稿,并接手各类遭遇瓶颈的小企业的短期治理。的确有过帐面富翁的快感,也遇到一贫如洗的烦忧。总体上说,这些经历丰富了人生经验,拓展了写作与艺术的感受力。人生丰厚与否,视野和胸襟开阔与否,都关涉到创作的思维和表现方式,对人的认知和悟性都起着重要作用。
黄沙子:我最早得知你的名字,是在八十年代的诗群大展的“星期五诗社”。后来我自己也成为“或者诗群”的一员。对于这种相对松散的组织一一并非那种聚集在某种主义下的群体,我更多趋向于认为是一种兴趣或者说趣味相投的人走在一起,但诗歌写作又是极其个人化的,你觉得这是否矛盾?你的写作是否受到星期五诗社其他成员的影响?
曾宏:好像早年我也跟你说过,要跟优秀的有头脑的人在一起,所谓近朱者赤。“星期五诗社”没有任何“主义”,却不缺乏因长期交流所自然而然产生的阅读认同与写作上相应的倾向和偏好,比如都比较喜欢朴素自然、充满形象的生活化语言和表达方式。吕德安写我的文章中提到“特立独行”这个词,我觉得很享受。但是,老朋友们的“只言片语”都可能是写作的养料,精神的灯火,它渗透到个人心灵和自觉创作中去。所以,参加一个趣味相投又保持相对独立的群体,确实是件好事。
黄沙子:我在福州待了四年,到目前为止我最好的兄弟仍然是在福州大学结识的同学,我也接触过不少福建诗人,觉得他们充满了温润的气质,那是一种自满自足、天生窥见真理的性格。你认为是这样吗?
曾宏:所谓南方特质吧,相对的温和、安静、自足。我想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还是蛮重要的,比如我家门前的闽江,它注定了我外表粗糙,内心柔软。“温润”这个词用得很适当。福建还是有好诗人的。
黄沙子:是怎么想到雕刻的,而且以鱼为主题7
曾宏:在随笔集《挣扎与美》中有一篇《我学石雕》,比较详尽地介绍这个。寿山石资源殆尽,有段时间我和老友大荒、德安三人每周都到山上捡拾。大荒刻的是《山海经》系列,我受他启发和影响找到了鱼系列,因为“鱼”的造型以及所承载的意义都极具空间感和想象力,是寓丰富于简单、于简单中见丰富的很好题材。此前还有两个系列,即脸谱和身体,以及零星的花卉动物及创意题材。这些以后还要继续。创作系列作品,是籍此希望在一个对象上穷尽各种形态与形式,只有这样才可能深入挖掘和表现,才可能发现造型艺术层出不穷的美。
黄沙子:我不知道雕刻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但我知道起码要经过制坯、打磨、上油,反正是很细致的活。你觉得诗歌也要这么精雕细琢吗?还是像有的人说,诗歌是一瞬间的事,感觉突然就来了,写下就再也不修改?
曾宏:雕石大体上是选择材料、构思设计、打坯、细节处理和修光、打磨包括多次修整,然后是上油、抛光等。作品经处理形成包浆后就不用再抹油。雕刻是对材料不断剔除的过程,而诗歌像泥塑,运用语言材料不断添加和垒积,也是个制作过程。精雕细琢和瞬间完成这两种情况都存在。在我理解,前者是个常态,在绝大多数的诗作推进与形成过程中,其表现为一种技术和语言的控制,它还包括后期若干次的修改、订正。而后者几乎是天赐的,一念成诗;或许因了潜意识和内心意念的长期累积,一旦找到形式感(或者说灵感),一倾而尽,没有多余。
黄沙子:你的诗歌多处写到“爱”,而且不是那种狭义的情爱,我在集中阅读后,想到一个词“慈悲”,我认为慈悲是大于欢愉的,这是天性使然吗?武汉诗人张执浩说,诗歌最终要传递出“善”,你认为这是相通的吗?
曾宏:真被你看到了!谢谢!“爱”是我生活、写作、艺术创作的基础和出发点,“美”和“真”是目标,“抗争”是过程。前些年的某 天吕德安对我说:你的诗里暗含着抗争的基调,这很好。现在你把我诗中的爱的基调也发掘了出来,而且正如你所说,它是一种“慈悲”。慈悲即善,爱即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所以我认同张执浩的说法,“善”可以改善人性,使世界有光,而诗歌即是有效的工具之一。
黄沙子:我知道你最推崇的两位外国诗人是索德伯格和狄金森,他们的什么东西吸引了你?说实话,我也看过很多外国诗,但是 多半是记不住作者的,只有这两位因为很早听你提起过,我记的很牢。
曾宏:这两位都是开创性的诗人,极具性格、想象和感性上的魅力,且在我恰当的时期所读,并各取其名一字作为我女儿的名字,因而我会更多地提到。在我的阅读中没有“最推崇”,不同的大师提供了不一样的养分。我们都从阅读与写作训练的自觉和不自觉中走过来,身上带着大师们斑驳的投影,但归根结底,我们应该也必须是活生生的个人,一个面貌清晰、有点脾气、大气磊落、随心所欲的写作者。
黄沙子:我还保留着大学毕业时你送给我的《狄金森诗选》,你还记不记得当时你给我的留言?“一个大师给你一片羽毛,另一个大师再给你一片羽毛……你会拥有一双翅膀”。写作肯定是从模仿开始,首先是跟随,然后才是独立,直到面目清晰、随心所欲。你觉得你现在已经到了随心所欲的阶段吗?我说的不仅仅是写作,而是整个生活。
曾宏:我记得的。你说的这些应该是写作者必然的经历和体验。前些年,寿山石界顶级艺术家刘北山先生对我说 我现在没什么想干干不成的了。当时还猜疑,现在我能理解了。主要是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局限和潜能以及未来的若干可能性:已没有写作障碍和名利焦虑,生活也没压力,精力与体力都好,整个很放松的状态。外界已很少能够影响和把控我,我只需要不停地干活、创作,好像没有什么干不成、学不了。看得很清楚,想得很开,怎么做就怎么好,写诗如此,生活如此,这是我人生最好的时期,应该可以叫随心所欲。
黄沙子:谈谈你生命中的四个女人吧,祖母,母亲,夫人,女儿。你的诗歌中,父亲出现得较少。
曾宏:女性在我生命和写作中都很重要。祖母是我的养育者和人生导师,教育我正派做人,做心胸广大的男人。她对我的影响是根本的。我跟早逝的母亲在一起的时间非常少,可以说是熟悉的陌生人,却也是我唯一的、血缘的、气质的偶像,甚至不必深究其中的意义。我太太是个贤妻良母,一个好搭档;已长大成人的女儿所显示出来的优秀品质则令我骄傲和满足。此外我还有一个好岳母。她们都爱我,宽容一个无所事事写诗玩艺术的人,这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事实上,我写过几首以父亲为题的诗,但我从小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一直把拉扯我长大的木匠祖父作为精神上的父亲,他教我爱和宽容,他是我一生的挚爱!
黄沙子:说到木匠,我看到很多人戏称你为曾木匠,你也乐于接受。很显然,一个手艺人是令人尊敬和受人喜爱的,不管是写诗的手艺还是做工的手艺。
曾宏:手艺在过去是挣口饭吃的行当,手艺人有些优秀的品质一一朴实、认真、专注、精益求精等等,在当今社会是很欠缺的。我12岁左右就跟祖父学木匠活,他的技术是一流的,为人忠厚,老福州领事馆区的外国人都只找他定制各类家具。勤勉耐劳,精工细作,一丝不苟、负责任的态度,这些品格用到哪儿都是好东西。写作也一样。
黄沙子:我也看到你确实做了很多木匠活,你不知道,我夫人也很羡慕和佩服你能找到那么多旧家具,还能改造得焕然一新,以至于现在我们碰到垃圾堆或者拆迁地,都要刻意去巡视一番,可除了捡到一些被丢弃的植物外,一件有改造价值的东西都没有发现。是不是福州的古董更多一些啊?
曾宏:哈哈!很多的羡慕嫉妒恨。并不是福州古董特别多,而是捡破烂你得有时间、有经验、有眼光、能搬运、会修理,还不怕丢人现眼,敢闯拆迁的民宅。往往是别人都看不上的,我搬回家它就能派上用途。其实这也是技术活,一般人干不了。我捡的东西翻修后就自己用,淡淡的怀旧气息,大家都喜欢。
黄沙子:现在的阅读量大不大?除了文艺类的书籍以外,还看些什么书?我知道很多初学写诗的人,大量词读的就是诗歌,但仅仅阅读诗歌肯定是不够的,对此你有些什么建议吗?
曾宏:我的阅读量主要在年轻时。你想我只初二毕业,早年又没书读,靠的就是后期的大量阅读来弥补先天不足。学文学以后,阅读胃口比较大,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各类艺术书籍都读的。早年很多书读得一知半解、糊里糊涂,也就这么读过来。慢慢地掌握了一些读书方法,“书越读越薄”了,读得更有效了些。对于初学写诗的人来说,也应该读读各学科门类的概论和个别重要作品,了解个大体,这对丰厚自己的写作是很有好处的。另外,不仅要读当代诗,也要读古代诗,无论中外,你对横的和纵的诗歌变化、发展都得有一定认识。我是做过系统阅读的,所以我对别人的作品有自己的判断力。
黄沙子:吕德安应该是你最好的朋友之一,如果可以互换,你愿意过他那种近似隐居的生活吗?佛经里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怎么理解这种说法?
曾宏:我觉得人们对他的“隐居”生活有误解,他从来都在忙于个人生存和家庭生活。在美国、北京与福州之间,满脑子都想着如何让自己和家人过得更好一点。他的山间居所几乎是用来劳动的,不断地建造、整修、除草、修剪等等,花费相当多的精力,居住和利用的时间却很少。不过现在倒成了一份财富和诗人身份的象征。我们都是安静的人,哪一天条件具备了,真的可以归隐山林,只做自己愿意做的事,而不问世事。
你提到的“无我相”等是《金刚经》精髓,我没研究过,没有发言权。我也抄心经和金刚经,却一知半解。我没有宗教信仰。宗教主要还是用来指导现世生活的,并给心灵以一个抚慰的空间。人的内心越清明,就越能删繁就简,自然地接近觉悟。做好一个人,是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到达的。
黄沙子:是怎么想到写诗的?人生中写下的第首诗现在还记得吗?
曾宏:我写过一篇《为何写诗》,它回答了这个问题,收在我的随笔集里。总之是个偶然,后来才慢慢感到,偶然又是个必然。
黄沙子:你和你夫人认识,是因为诗歌吗?
曾宏:不因为诗歌,虽然那时她也读我的诗。那时我是工人老大哥,她是中文系大二学生,可能被我工人阶级的外表和气概给震住了。还有我故意讲笑话逗她笑得肚子疼,这个办法很管用,年轻人要学。再就是,估计她想把我拯救出黑暗,她果然做到了。
黄沙子:你创办过诗旅程论坛和博客群,九十年代前后对福州的大学生诗歌也多有提携,这些都是我知道和经历过的,这算是对诗歌事业的贡献?
曾宏:我是个好玩、爱玩、精力过剩的人;没事瞎折腾当休闲,就像现在玩微博,一回事。在论坛、旅程网、博客群打理期间,认识了很多至今虽少联系却铭记在心的朋友。这也是财富。支持比我年轻的朋友写作,我觉得谁都应该那样,谈不上贡献。只是早年我比较呆板,就诗论诗,容易直话伤人,但真心是希望别人的好。
黄沙子:社区、论坛、QQ群、博客、微博、微信,这些交流工具你肯定都玩过,最喜欢的是那种形式?还有,写作这么多年,你觉得有必要总结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吗?有没有这个打算?我知道有很多伟大的写作者并没有理论支持。但这至少有助于整理自己的方向,同时也可以让自己的面貌更加清晰。
曾宏:早期的乐趣园论坛和现在玩的微博比较喜欢,接下来可能又没得玩了,但也无所谓。
至于你说的总结一套理论,可以使自己的面貌更清晰,是有一定道理的,即便我们并不依照理论来写作。我更愿意以“经验”来替代并融入“思考”的那类随意自然的文字存在。以前文章中提到过《美国诗人谈诗》中的部分文章,就是对写作的经验记录和总结及必要的整理与展望。不必非写成书卷式、学院气十足的著作。我在写作的不同阶段都写过零散的诗观,它对个人具有理论指导和方向意味,以后可以整理出来。诗歌没有所谓正确的理论和法则,我们一生都在修正自己。
我倒是希望写一部有关艺术审美的理论著述。通过自己熟悉的写作、绘画、雕塑、书法、摄影等门类的共性及区别,来论述自己心中的审美倾向与理想。这部书要写很多年,我现在应该开始着手准备了。
黄沙子:福州方言和普通话,应该是不同的语系,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方言,写作中使用普通话,不同的语言习惯对于诗歌写作会产生影响吗?
曾宏:我曾经为此苦恼过,特别是刚开始时的小说写作训练,这两者的差异使得自己丧失信心。后来写诗,才逐渐缩小这两种语言的距离,或者说一种语言归顺了另一种语言吧。到现在,我早已没有这个障碍,因为运用无论汉语写作、外文写作、闽越方言写作都只关系到语言材料的不同,与诗歌的洞察力、想象力无关,与诗的意趣、内涵无关,甚至跟表现力无关。只是哪一个用得更得心应手而已。当然最终受众是不同的。诗的秘密不因为不同语言习惯而改变和消失。
黄沙子:如果让你十年不接触到外界任何一个诗人,你还会继续写下去吗?
曾宏:这个没问题。本来就不是一个依赖别人掌声和关注写作的人。所以几十年来,少而又少主动投稿,我不觉得这对我个人和写作有什么不好。把发自内心、不得不说的那些话写出来,就解决了我自己的内部问题。写作对我,就是不得不做的事情之一。
黄沙子:你的一本诗集是以1992年的诗作《请给我》作为诗集名,2013年又写了一首《还给你》,这两首诗相隔11年,我觉得是可以对照阅读的,是期望,一是绝望,可以这样理解吗?如果是,为什么?
曾宏:这两首诗的意义与指向可能与你的阅读理解正相反,倒过来说就对了。《请给我》是向天地万物的祈求与索取,《还给你》则是对现世的舍弃与给予,这跟标题的指向一样确切。一路走来,早年是不断地从外部向内求取,到现在可以从内部向外回馈了。
黄沙子:你这样说,我觉得也有道理,期望和绝望本就是互生,人生一辈子就在不停地打通这两者的关节。引申出两个问题:一、有人说诗歌是通向另外一个世界的道路,但永不可及,又有人说诗歌是写作者代替神在启示世人,你是怎么看的?会不会觉得这两种说法都有些高蹈?二、你怎么看待诗歌和哲学的关系?呵呵,这两个问题本身就有些装神弄鬼。
曾宏:期望和绝望互生,对的!一些人常喜欢提出干奇百怪的“说法”,貌似“发明”吧,可以引以自慰,也可以吓唬人,我觉得能够自圆其说也挺好;把不存在的东西说得活灵活现还真是一种本领,而我们不必对此太较真。至于诗歌与哲学的关系,我真不知道。我们有必要将哲学写进诗歌吗?对的,诗歌有人生观和世界观存在其间,对人世和自我的意识存在其中,它们跟纯粹的哲学没有关系。不少人强调诗歌的所谓深度,对我个人来说它是生命、生存的厚度,一个人有多厚重、多开阔、多高远,他写得的东西在最好状态下是相等或接近的。刻意“深刻”的诗,那是装神弄鬼弄出来的。
黄沙子:07年写的那一组《妻子》看得我几欲泫然泪滴,是你夫人患病的时候吧,现在她身体怎样?她看过这组诗吗,我想她一定也流泪了。
曾宏:这组诗前三首写得较早,后来遇到她生病,一时又写了许多首。我想她是看过的,有没有流泪我不清楚。她不是诗歌爱好者,我的诗早年她还看,后来就基本不看了,这样也就不会把我诗中的抒情拿来乱联想,我觉得很好。她从事自己的职业,管理好家庭,已经很称职。夫妻没必要兴趣同一。她恢复得很好,发病治疗到现在快八年了。希望她每一天都开心,这是我最想给她的。
黄沙子:说实话,我很少看到你的诗歌中有纯粹的欢乐,除了有关你女儿的诗歌。是这样吗?
曾宏:是呀,很快乐了还需要写诗吗?写诗是疗伤,是发泄所见所触而淤积内部的黑暗,或者某种情绪与愿望。早年主要表现对人世的挣扎与反抗,近年则是平和生活的反映以及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首先是为自己写诗,然后才关涉到读者,在得到共通共鸣的时候,我就会感到很快乐。
黄沙子:我不记得是谁说过,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潜在的故乡,写作的过程就是不断向故乡靠近。你虽然生活在福州,但我觉得你还是很怀念出生地济南,你在济南呆的时间应该并不长,为什么会这样?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更愿意在哪里度过一生?
曾宏:故乡这个概念对我倒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居住习惯。所谓潜在的故乡,在我看来就是你在哪里能活得更接近理想。济南是我的出生地,四岁时回去次,前两年参加青岛画展时又去过一回。我为它写过文字,但我的故乡肯定在福州,我熟悉这里的山水草木,还有天天游泳的家门前的闽江,后半生不会有别的选择。对了,我女儿定居上海,我觉得自己留在福州最适合。
黄沙子:我记得你好像也曾经北漂过一段时间吧,是做什么去了,怎么又放弃了呢?
曾宏:去了七个月。接手管理一家大型网站。去时就商定好只干半年。我对接手的公司一般就这时间,能整就整过来,整不了原因就很复杂了。我有一套自己的管理系统和理念,但投资人的放权配合很重要。这很难。
黄沙子:喜欢旅游吗?很多人认为陌生的环境可以触发写作的灵感,就像丰富的阅历更有利于反省自己一样,你也是这样理解的吗?
曾宏:骨子里应该是很喜欢旅游的,我走过不少地方,却很少真正享受到旅游的乐趣。我比较喜欢旅行中有充分的时间发呆和一定时间的懒散,不爱疲劳游;矛盾的是,也一直希望某一天开始做背包侠,走遍天下,过苦行僧的日子,但貌似时机还没到来。陌生环境触发灵感,旅行有助于开阔视野、更新思维,这肯定是好的、对的。也有一类人,坐在家里,天上地下内心神游,一样可写出好作品,比如狄金森。
黄沙子:再说说陌生这个词。有些人因为身处与众不同的地理位置,诗歌中描述的事物和意象相对奇特,会带给阅读者新鲜的感受,我认为这其中就有陌生带来的效果。相比之下,那些生活在我们熟知的地区的诗人,就不能获得这种“便利”,他们的写作是不是会艰难一些?
曾宏:缺少对事物的体验是个遗憾,但又往往刻意不得。御用文人不也常常被组织下乡“体验生活”吗?又写出多少粉饰太平之外的奇特事物与意象?生活在西藏、新疆、青海等地的诗人,所描述的事物和意象,也常让我们感到好奇,但仅此而已。诗写得好不好,终究不取决于他所描述的那类东西对你来说是不是陌生和奇特,归根结底是诗内部所提供的、与读者思想情感相沟通的、具有智慧、力量和爱的那部分品质。写不了宏观就写微观,写不到奇特事物就写平凡熟悉的生活。只有自我的写作状态与感受是奇特新异的,写出来的东西才可能惊人,而这种感受力需要培养。事物对象的陌生化效果都会淡化掉,最终露出来的仍然是心灵这种东西。
黄沙子:最后一个问题,是请你帮我解惑。有很多诗人,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突然终止了写作,然后时隔多年,又重新开始。我就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自己一直没有弄明白这中间到底是什么缘由,或者说没办法把这其中的思路理清楚,你作为我亦师亦友、也是前辈的写作者,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你有没有同样的经历?
曾宏: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也停写过三年。1997年时吕德安逼我重新恢复,说他已经提名我“刘丽安诗歌奖”,必须整些新作品出来。后来就又开始写了。人生旅程多变化,也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人偏离原来设想的轨道和习惯的生活。放弃写作未必都是刻意的,当然也有刻意回避的,如果有更适合的方式来安慰和充实某段人生历程,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但写诗的人会有种情结始终深藏内心,你未必看得见,日常也未必想到,它却在随时走回来的路上。我的确没办法帮你理清楚这缘由,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有时厌倦是其主要原因。
最后我要说,认识优秀的你是我人生的荣幸,我们是朋友,是好兄弟!谢谢!
2015年7月7日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