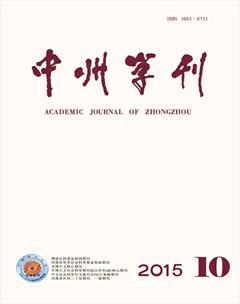项羽入关后“弱刘”战略疑点考证
郭霞
摘要:项羽入关后施行削弱刘邦的战略,通过迫其称臣、迁其汉中、削其军队等一系列举措,极力压缩刘邦战略发展空间,楚汉双方因此得以维持一年多的相对和平。而随着项羽东归,失去武力护佑的“弱刘”战略,最终因民心向背而为刘邦破解。考证项羽集团所推行的“弱刘”战略,还有助于厘清相对模糊的历史细节,比如鸿门宴事件中,项伯应是衔命谈判的使者而非告密者,刘邦受封后即赴南郑就国,并非于四月和诸侯一起罢兵戏下。
关键词:〗项羽;刘邦;鸿门宴
中图分类号::K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0-0107-04
根据《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记载,从鸿门宴项刘会到刘邦袭取彭城挑起楚汉战争,双方维持了约一年零四个月的和平局面。这固然与刘邦积聚力量及时局演化有关,但也从侧面证明,项羽入关后对刘邦采取的一系列战略性削弱措施是有一定成效的。这些措施在前人已有涉及①,当代的一些学者也从个别方面进行过论述②,但较少有人进行系统性关注。研究项羽对刘邦的战略削弱措施,有助于厘清以下几个问题:鸿门宴事件中,项伯是告密者还是衔命谈判的使者;刘邦受封之后,是四月与各诸侯同时就国还是早已单独提前就国;刘邦受封前拥兵十万,受封后军队削减至三万人,削减的军队去向何处;主张“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③的项羽集团,为何分封毫无军功的韩公子成为韩王。笔者不揣浅陋,依据史料对这些问题略作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鸿门宴中的项伯角色
项羽入关前与刘邦在函谷关已经发生过一次冲突。《史记·项羽本纪》:“函谷关有兵守关,不得入。又闻沛公已破咸阳,项羽大怒,使当阳君等击关。项羽遂入,至于戏西。”④随着项羽率诸侯军破关进驻于戏,围绕关中地区的主导权之争刚启幕就已无悬念。项羽破关而入击跨了刘邦占居关中以拒诸侯的信心,让其认清了双方的实力对比“固不如也”⑤。项羽集团的“弱刘”战略在此背景下启动。入函谷关前,项羽集团对关中地区已有分配方案,并且这一方案基本无视“先入定关中者王之”⑥的约定,在逼降章邯的过程中,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置楚军中”⑦。立章邯为王既是项羽亡秦战略的一部分,又反映出项羽集团分割天下的规划,但这一安置显然与刘邦占居关中是有冲突的。
在如何处置刘邦的问题上,项羽集团内部拥有较大影响力的两人分歧明显,一位是被项羽尊为亚父的范增,一位是项羽的本家长辈项伯。根据班固和司马光记述,项羽随项梁起兵时很年轻,“初起,年二十四”⑧,“籍是时年二十四”⑨;刘邦还军霸上时“岁在乙未”⑩即公元前206年,依此推算,鸿门宴前后项羽年仅27岁。对这位年轻的统帅,范增与项伯均试图展现自己的影响力。范增主张对刘邦“急击勿失”,将其排除在“计功割地”名单之外;项伯主张“不如因善遇之”,实质是逼刘邦称臣。
至于项伯的角色,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被司马迁刻画成和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一样的告密者形象,对此早有学者提出质疑。梁玉绳就称:“项伯之招子房,非奉羽之命也,何以言报?且私良会沛,伯负漏师之重罪,尚敢告羽乎?使羽诘曰‘公安与沛公语,则伯将奚对。”现代学者韩兆琦也认为,鸿门宴“汇合了许多人艺术加工的民间故事”。两位学者的观点不无道理。结合《黥布列传》中的记载,黥布降汉后,“(布)于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项伯收九江兵,尽杀布妻子”,楚汉战争时,项伯仍备受项羽信任。倘若项伯在鸿门宴前未经项羽许可而私会张良及刘邦,是泄露军情之重罪,不可能再受信任。然而鸿门宴后项伯在楚军中仍受重用,照此分析,其与张良乃至刘邦会面,逻辑上应是衔项羽之命劝其臣服,绝非私会。
由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测,鸿门宴前项伯奉项羽之命前往刘邦营中,劝说刘邦交出关中地区的控制权。而刘邦此时的军事力量不足以与项羽对抗,又无稳固后方可退,因此急于加入项羽阵营,一则免受攻击,二则可参与分割天下。刘邦的理性选择保证了项伯使命的圆满完成,关中地区的主导权得以和平移交,随后项羽设宴鸿门,刘邦正式称臣于项。项羽集团此种手法和之前逼降章邯如出一辙,都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威慑对方,进而达到目的。
至于刘邦在鸿门宴所言“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不过是臣服之词。项羽之所以任由刘邦解释,根本原因在于其战略目的已达到,“项羽亦因遂已,无诛沛公之心矣”。项羽和范增虽然“疑沛公之有天下”,依当时情势,“逐秦守宰而自王故地”者比比皆是,在刘邦已然臣服的情况下,项羽自不必与之再有口舌之辩。
鸿门宴座次安排是考察双方关系的一个指标。项羽与项伯“东向坐”,范增“南向坐”,刘邦“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对此,学者杨树达认为,“秦汉座次,自天子南面不计外,东乡最尊,南面次之,西面又次之,北面最卑,其俗盖承自战国”。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中,引中井积德的观点“堂上之位对堂下者,南向为尊;不对堂下者,唯东南为尊,不复以南面为尊”。项羽与项伯、范增等自居尊座,置刘邦于北向卑座,清楚地表明项羽已然把刘邦当作属下而非对手。笔者认为,这些关于座次的安排,应当在项伯衔命会刘之行中已有所约定,项羽已事先得知刘邦前来臣服,故以卑座安置。
二、诸侯罢兵戏下与刘邦就国的时间差
项羽迫使刘邦臣服并取得关中地区控制权是其“弱刘”战略的第一步。在随之进行的“分土而王之”过程中,项羽与范增借机迁刘邦于巴蜀,极力压缩刘邦集团的发展空间。
当时的关中地区,“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进一步将天下财富集中于此。
从战略地位分析,刘邦谋臣张良称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项羽驻兵于戏后,也有谋士进言“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如此重要的地方,“疑沛公之有天下”的项羽显然不可能将之封于刘邦。而项羽自身,又因坑降卒、屠咸阳、杀子婴、烧秦宫室等一系列事件而无法立足于此,于是项羽采取三分关中的策略,试图以此弱化关中诸侯的实力,并在分封诸侯时作了策应安排。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述恽敬观点,认为“项王之所忌,唯汉王也,是故未为取秦之谋,先为救秦之策。三川者,救秦之要道也,以瑕丘申阳据三川,而北函谷、南武关,挈其要领矣,以司马卬辅三川之北,而函谷之军无阻矣,以韩成夹三川之南,而武关之军无留矣,二王皆赵臣,赵睦于楚,故道通。韩成不睦于楚,不使之国,而楚制之,故道亦通”。近代的夏曾佑也认为:“项王之弃关中而归也,非真欲归故乡也,许以己新残破关中,留都之,民必不安,乃以三降将居之,而自居彭城,以遥制三秦,为待时而动之计,其所以策汉王者周矣。”
利用分封压缩刘邦的战略空间,透露出项羽和范增的真实意图,一方面“如约”封刘邦为汉王,另一方面将其赶到巴蜀等相对偏远之地。“巴、蜀亦关中地也”的解释,很容易让人想起刘邦的“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之说,都不过是应景之言。实际上,“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才是封刘邦于此的最重要因素,接着项羽“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打压刘邦的战略意图暴露无遗。项羽此举,就连刘邦的部属都认识到“独居南郑,是迁也”,进而导致追随刘邦的一些将领(包括韩信在内)因看不到前景而逃跑。刘邦个人在初闻所封之地时也曾有愤怒,“欲攻项羽”,所幸萧何、周勃、灌婴、樊哙相劝而未实施。
迁封巴蜀是项羽削弱刘邦的重要一步,此举证明了范增的远见和谋略。偏远的巴蜀之地不足以供养大量兵员,刘邦若安于现状,势力必然逐渐衰减。一旦刘邦出现异动,需要冲破三秦之地才能出关,项羽可有充足时间予以应对(可惜项羽后来北攻齐地,给刘邦以战略机遇)。刘邦受封汉王后,实则已困于巴蜀,战略空间极为狭小。幸运的是,项伯作为项羽集团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由于收受张良之礼,“汉王赐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结果刘邦如愿得到了汉中之地,汉中后来成为刘邦进入三秦的重要跳板。
关于刘邦受封和就国的时间,也是项羽对其战略削弱的一个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考证。《史记集解》徐广认为刘邦受封“以正月立”。《秦楚之际月表》载,正月分关中为汉,《史记索隐》称之为高祖及诸侯受封之月。《资治通鉴》中,司马光记载为“二月,羽分下王诸将”。但对于刘邦何时赴南郑就国,《史记》中未明确记载,仅称“四月,兵罢戏下,诸侯各就国”。
从项羽分封诸侯到诸侯就国,时间长达数月,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现象,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知道的是,当时的天下形势仍相当混乱,旧的中央政权不复存在,新的中央政权与各地的联系并不紧密,仅就楚地来说,陈胜吴广起兵后,“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虽说大部分渐渐汇聚到项梁、项羽旗下,但仍有相当数量的武装力量在各地普遍存在着,项羽分封后,各诸侯理应急赴各地重建统治秩序,而非留在残破的关中无所事事。对于项羽和诸侯分封后长期滞留关中,合理的解释是,各诸侯就国之前的这段时间,项羽及诸侯驻兵关中应是监视刘邦就国,观察刘邦及各地不顺从者对于分封的态度,以随时应变。
这从刘邦就国的举动中也可窥其一二。“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倘若是诸侯同时就国,刘邦根本无须防备诸侯攻击,因为项羽和诸侯是率兵而东,单单三秦之章邯等,不至于迫使刘邦做出烧绝栈道之举,《高祖本纪》里也未明确记述刘邦是在四月和诸侯一起“各就国”。笔者认为,刘邦就国时,诸侯兵仍在戏下。也就是说,刘邦是在四月之前赴南郑就国,与项羽及其他诸侯就国的时间并不一致。刘邦就国时,项羽和其他诸侯仍拥兵在关中,直至刘邦行至南郑后,诸侯才“罢兵戏下”。这也能合理解释为何一月分封,直至四月诸侯才“各就国”。而刘邦在就国过程中,为防备项羽和诸侯袭击,无奈之下才边行军边烧绝栈道。
三、刘邦所获关中兵的再分配
与夺地、迁封等系列措施相伴随的,还有对刘邦军事力量的削弱以及对刘邦重要谋臣的拔除。
鸿门宴之前,项刘双方相持时,“沛公兵十万,号二十万”。到了刘邦受封赴南郑时,“项王使卒三万人从”,刘邦所属兵力骤然减少七万人。那么,刘邦被削减掉的军队流向何方呢?史书未提,已无确证。我们不妨先分析一下刘邦军队的来源。刘邦起兵时“收沛子弟二三千人”。刘邦自武关进入关中时,仍不过区区两万兵力,“沛公欲以兵二万人击秦峣下军”。之后在秦地收降纳叛,还征兵以自益,迅速扩军至十万人。
刘邦到南郑就国后的部属籍贯,史料记载称“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跂而望归”。这说明刘邦入关中后所得八万秦地兵多数并未前往南郑。再看项羽所封秦地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三人所率20余万军队已于新安城南被项羽军坑杀,关中三王属下已无兵力。刘邦在关中所得兵员,较为合理的去向是被项羽借助分封之机,为平衡各方实力而划归关中三王以及其他诸侯。
项羽集团对刘邦人才的拔除,突出表现在对张良动向的安排上,此一策略在分封诸侯时以较为隐蔽的形式实施。项羽分封诸侯所提的口号是“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十八王中,刘邦等十三人被为有功者而封王,徙封者有魏王豹等四人,既无军功而又未徙封的是韩王成,韩王最早是项梁受张良所请而立为韩王。事实上,项羽封韩王成不过是权宜之计,处心积虑削弱刘邦势力的项羽和范增,不可能容忍一个与刘邦交好的韩王存在,“韩王成无军功,项王不使之国,与俱至彭城”。至此,项羽封韩王成的真正目的显露,一方面项羽谋求自己控制韩地以监视刘邦动向,另一方面迫使张良离开刘邦,因为当初是张良请立韩成为王,在项羽承认并继续封韩成为王的情况下,张良不可能弃之不顾。从结果上看,项羽分封韩成确实达到了目的,“汉王之国,良送至襃中,遣良归韩”。项羽暂时拔除了刘邦部属中最有谋略的人才。
四、“弱刘”战略早期成效及其消解原因
若仅仅以早期效果观察,项羽集团的“弱刘”战略可以说基本达到了目的。刘邦集团对于所有加诸自身的束缚均予以接受,离开拥有战争潜力的关中而局促于偏远的巴蜀,实力弱小到一度只能靠“烧绝栈道”来防备诸侯袭击的程度,部属也大量逃离。至少从表面上看,项羽与诸侯“罢兵戏下”时,刘邦已经不具备与之争夺天下的能力。
然而,随着时局的演化,“弱刘”战略的缺陷逐渐显现。项羽集团此一战略有赖于两个主要支撑点:其一,项羽拥有对刘邦强大的威慑力并随时可以使用;其二,关中三王自身具备短期对抗刘邦的能力。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上述两个支撑点都经不起检验。就第一个支撑点而言,项羽率军东归后,其对刘邦的威慑力大为削弱,齐梁等地举兵反楚造成项羽多线作战,而项羽并不具备同时战胜田荣和刘邦的能力,所以对刘邦采取守势以便专心攻齐,由此给刘邦带来难得的崛起机遇。第二个支撑点则是严重先天性不足,秦地自商鞅变法后民俗以军功为重,章邯等“欺其众降诸侯”不仅为秦人所轻,还使得20万秦军被坑杀,虽然被项羽分封为王,但“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其抗拒刘邦的能力因而大为折损。失去支撑点的“弱刘”战略,因主导者远在彭城而无法遥制,最终被刘邦逐一突破。
战略空间的拓展方面,刘邦乘齐地田荣、梁地彭越等反楚之机而占居关中。为减少来自项羽方面的干预,刘邦在平定三秦时让张良捎信给项羽:“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并警示项羽“齐欲与赵并灭楚”。从而争取到宝贵的平定关中的时间,关中丰厚的战争资源再次为刘邦所掌握。
兵源扩充方面,刘邦首次入关占居咸阳时,萧何就“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所以对于“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均有所掌握,加上此前在秦地的征兵经验,刘邦集团在兵源补充方面相对得心应手。即便在此后楚汉争战期间,关中地区也为刘邦提供了充足的兵源保证,“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
综合来看,项羽集团的“弱刘”战略之所以随着时局演化而消解,根本因素在于双方对于民心的争取方面。刘邦在秦地经营的时间虽短,却通过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而赢得秦地民心。并且早在项羽入关前,刘邦已派人与秦地官吏到关中各县乡宣告“吾(指刘邦)当王关中”,还发布多种措施与秦人交好,“诸吏人皆案堵如故”,着手构建统治体系和舆论导向,从而在秦地累积了较高的声望。反观项羽集团,坑秦降卒、杀秦王子婴、烧咸阳王宫、封降将为王,事事给予秦人以羞辱,这种由羞辱所激发的民心疏离,随着项羽武装力量的撤出,而投射到其所封关中三王身上。民心的向背使得“弱刘”战略终究无法长期维持,东归后的项羽,再也没有能力二度跨进函谷关。
注释
①如裴骃《史记集解》、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梁玉绳《史记志疑》、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等。②如杨东晨:《张良在反秦助刘邦封汉王中的贡献》,《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李振宏:《项羽“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献疑》,《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③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622、2612页。④⑤⑦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310—311、311、310、311、312、312、316、315、316、316、317、320、321页。⑥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356、367、367、367、364、367、350、367、362、362页。⑧班固:《汉书》卷三十一《陈胜项籍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1795、1789页。⑨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秦记二》,中华书局,2009年,第87、103、103页。⑩司马迁:《史记》卷十六《秦楚之际月表》,中华书局,1982年,第773、775页。梁玉绳:《史记志疑》,中华书局,1981年,第202页。韩兆琦:《韩兆琦〈史记〉新读》,北京燕山出版社,1959年,第47页。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一《黥布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602页。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五《樊郦滕灌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654页。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六十八《封建考九》,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131页。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科学出版社,1954年,第247—249页。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第556、570页。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3261—3262页。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239页。司马迁:《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第2044、2038、2037、2038—2039页。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6页。司马迁:《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第2014页。
责任编辑:王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