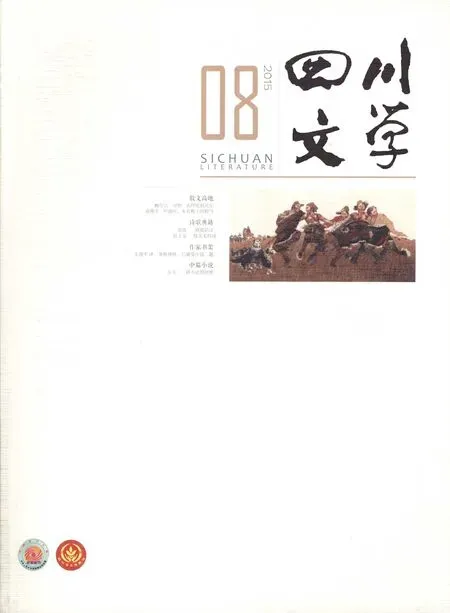安吉梅朵
○ 伊熙堪卓
起初,大家都没在意女人的出现。
一个穿着整洁的汉人女乞丐在高原小城不会引起人们更多关注。
好心的主妇们见家门外立着抱着襁褓的女人,怜悯地拿出家里不多的吃食:一块冷馒头、半拉锅盔(四川方言面饼)、一坨糌粑团,母亲给她倒碗滚热的酥油茶,她不做声咕咚咕咚大口吞下,母亲怕她烫坏喉管,说茶还多只管慢慢喝,她却不领情扔下空碗漠然转身离开。
不多时,女人怀里除了襁褓,便堆满了食物,那是小城里众多主妇们的同情心。
她不道谢也不吃,抱着襁褓跟一堆食物呆呆在高原深秋的冷风中踲行。
时是八零年代,我尚在城区小学念书,高原小城物质极不丰裕,即便父亲在林业局做局长我依然觉得女人怀里抱着的那堆食物是可口的。
忽忽的,她的疯态渐显。
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放声大哭,将怀里的食物满地乱扔,暴跳着用力踩踏。
那年代,荒芜平淡的高原小城忽然来了疯女人,如同安静的死水潭里扔下了大板砖,顿时沸腾。
女人疯到哪大家跟到哪。
最初人们只是围观,相互询问是哪家的女人,看她傻笑叫骂看她呼号魔怔,人群相互问了个遍也没人知道她何时来?从哪里来?如何来的?又将如何?
我们一堆孩子,好奇地围着她,见她白皙的皮肤和美丽无神的大眼,甚是稀奇。
只是她襁褓里的孩子始终没有任何动静,任凭女人怎么哭闹,怎么疯癫。
我曾见过另一疯女人。
这之前,父亲在区委做书记,区卫生院设在一幢陈旧的土司官寨,大门口常年坐着一个极清秀当地打扮的藏族女子,支着织锦腰带的木制工具席地而坐。
那是种需要在四角钉桩,全然手工纺织的活儿。
她从不与人交谈,只日日坐在铺着几张硬纸壳的地上不停织着棉线、锦线或羊毛线。
她织的腰带很得附近人们喜爱。母亲是和善的人,时时拿家里的食物水果送予她吃。我虽几岁却也记得,她接过食物放在身边也不说话,只是红脸笑笑又低头纺织,大人们说她尚有年幼的女儿在家中等候。
我看着她纺织很是稀奇,偷偷把母亲的毛线团拿出,捡来几根木条绑在腰间学着她的样子织,织来织去也只得一团乱麻,还被母亲狠狠一顿教训。
母亲的樟木大箱里,至今保存着一条织工精细的黑白小方块长腰带,那便是她织来送给母亲做纪念的。母亲不大穿藏袍,说是不便做家务,且那是穿豪华大藏袍时系的,故而一直那么簇新地躺在木箱里。
彼时我太小,不知大人口中疯了的人是何概念,也不知她因何而疯癫,只觉得灰暗的区卫生院,那栋老旧的土司官寨大门前,女人低头织锦的模样像一幅画静静挂在我记忆中,从未褪却。
小城人追着汉地来的疯女人跑,大人、小孩、男人、女人,她的疯癫引来阵阵惊呼、哄笑或几句怜悯的议论。
顽皮小男孩在几个楞青头唆使下,一把将女人怀中的襁褓扯在地上。
事情太过久远,我已不记得是谁扯开了襁褓的棉带,只记得那包袱被人东拉西扯冒失散开来,由里内小童毯骨碌碌滚出一个小小的,貌似婴儿的头颅的骨头,还有一些白色呈面糊状散发恶臭的东西。
人群惊呼,四散逃逸。
她却也不疯了,低头看着散落在地上的襁褓,呆呆不出声继而嚎叫着跑远。
只剩散落在地上小小的一堆包袱,失神地躺着。
不几日,牧羊人在河岸下游草滩上发现了她的尸首。
那条绕城河我最是清楚,因为常和姐姐偷偷去涉水捉鱼,被父亲不知教训过多少次。河流绕过草原缓缓而去,水面宽阔平坦,最深也只到六七岁孩子胸口,决计淹不死成年人,她却不知如何会殒命。
因为来路不明找不着亲属,那尸首最终被附近的寺庙领去超度火化了。
那时,我从未认为小城对于谁是不厚道的,对她却例外。
小城很小,人们相互亲厚,孩子们在众多相互情谊深厚的长辈组成的家庭间放养。
记得班主任的丈夫是父亲的朋友,两家时常聚会,聚餐前叔叔会带我和他儿子去小河边洗菜,在波光潋滟的流水旁,带着厚厚镜片的眼镜叔叔用俄语给我们念诗,我不喜欢发音古怪的俄语,但我是喜欢叔叔也喜欢他两个儿子的。
这是小城在我心中的模样,我始终认为即便气候苦寒,我却在朴实深厚的温暖中生长着,从未吃苦,若非想起那个抱着襁褓的汉地女子……
举家回到父母故乡,刚开始尚未分配房屋,我们全家挤身舅舅家六七十平的三居室小屋里,舅妈是县医院护士长,医院隔壁是当时红火异常的云母矿矿部。医院门口栽着一溜高高的夹竹桃,我们不顾大人警告有毒,常在附近穿梭疯玩。
云母矿是个奇怪的单位,当年它在故乡雄霸一方,矿工虽在距离县城十分遥远的矿山工作,但总部却设在县城,他们的收入远远超出公务员们,当时矿部甚至有着属于矿工自己的电影院、歌舞厅、医院、子弟校……,这些设施是县上的人们无法享受得到的。
小城里,每每听见讲着普通话或外省话的,一定是矿里工作的人们,偶然在街头遇见走路昂首阔步举止优雅的人们,那必是云母矿的人。
钱币是奇怪的东西,它附着在人身上时,是可以改变一个人外在的所有器形的,机关公务员们上街只会畏畏缩缩,锱铢必较地与小贩讨价还价,而出手阔绰的往往是旷工的家属们。
于是在小城里,男人们渴望在矿上工作,女人们梦想嫁给矿里工作的男人。
效益爆棚后云母矿从州属企业变为省属企业,最后一跃为中央直属企业。
然而,云母矿最出名的不是光亮闪闪的云母,却是疯女人岳美丽。
没有人知道她的大名,只是路人某偶遇一时兴起对着她大喊:
“岳美丽!跳个舞!”
她会不假思索放下任何手中的东西边唱边跳,她的歌词含混恶俗,最后一句结束语总是:“我在河边洗勾子(屁股),老鸦啄我的肥勾子。”
路人哄笑,她跳完又急匆匆拿着自己的物什窜入人海。
岳美丽看着不似疯人,干枯发黄的卷卷头发整齐地梳着独辫盘在脑后,穿着洁净的碎花衬衫,只是脸上抹着厚厚一层白粉和艳丽的胭脂,嘴唇上乱七八糟涂着血红的唇膏,仿似画坏了的京剧脸谱。
我喜欢她,因为我从没自信可以在人群围观的地方唱歌跳舞。
三年级,班里音乐考试,要求每人站起来给大家唱首歌便算合格。轮到我,考试再也进行不下去,我站在座位上低着头不知怎样才能让美妙的音符从自己嘴里飞出来,因为害羞我只能低着头,倔强地站在自己座位上一声不吭。
按时下流行的话来讲,音乐老师是母亲的闺蜜,她美丽丰满,但绝对的脾气暴躁。各种威逼利诱无效,她只得让我站在座位上听全班同学一一唱歌,中午同学都放学回家,她将我单独留在教室,非要唱完才肯放人。
让她气急败坏的是她小觑了我的腼腆,直至她饿得七荤八素,苦口婆心白沫四溅,我的喉咙里依然没有飞出一个字,那场音乐考试最终以母亲亲自来接驾告终,由头到尾老师没有听见我哼一声,甚至连认错都没有。
所以那时我是佩服岳美丽的。
一个女人,打扮怪异,却自信满满在众人注视下载歌载舞,她得有多么大的能耐才能如此。
高中时,表哥的班里从内地转来一个皮肤雪白,头发焦黄的时髦女生。
她脸小小的很瘦中等个头,齐耳短发头发极潮流的烫着爆炸式,她爱穿黑白条纹的窄腿裤,眼睛不大眼皮上总抹着蓝色的眼影,涂着粉色唇膏。
匪夷所思的是,同学告诉我那是岳美丽的女儿。
我无法把这个个性十足又十分洋气的女生跟岳美丽联系在一起,那时候随着云母被采空,云母矿已经十分萧条破败不堪。
由中央直属企业直接被扔烂尾楼般扔给了县上,县里对此头疼不已。
那间漂亮的电影院像恐怖片里的鬼屋再也没有开放过,曾经人潮攒动彩灯闪烁彩纸飘飘的歌舞厅,窗玻璃早被孩子们砸得稀烂,厚厚的灰尘上印满孩子的脚印,矿部医院对外开放后就诊的只有来自农村经济拮据的人们,相对县医院那里费用还算便宜。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岳美丽的消息,只听闻她随转产的人们一起到了广元或是威远。
这两个地名都是第一次听说,矿里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失去了工作,即便留下的也只依靠着微薄的薪水煎熬着度日。
那女生念了不多久,也再没瞧见她在学校出现,说是不爱念书混社会去了。
偶尔想起岳美丽,内心有隐隐的痛。
生完孩子后记性愈发糟糕,奇怪的是她的长相我从不曾忘记:胖乎乎的大圆脸,下垂的眼角和嘴角泛浮层层皱纹,浓密粗大的汗毛沾染着白粉自由自在在嘴皮上生长,短小的卷卷发茬在小城干燥的风中微微荡漾。
高原上有种有着奇怪传说的花儿安吉梅朵。
隆冬时节它从地底探出头来急急开花,眼见万物萧瑟别的花朵都在沉睡,便惶惶说:“我开早了!我开早了!”于是匆匆将身体缩回泥土酣酣大睡,不想一觉醒来已是深秋时节,她再次从泥土中生长开花,此时又是百花凋零万木疏落时节,它只得继续惶惶:“我开迟了!我开迟了!”
我常思索,那些曾途经我人生的疯癫女人们似极了呆头呆脑的安吉梅朵,鹅黄的花朵瑟瑟在寒风中惶惶不安地盛开着。
2007年,与朋友开车沿着川藏线去拉萨,偶然翻越不知名的大山,海拔四千米的高山上安吉梅朵正好盛开。
寒风凌冽,它惊慌失措又无所依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