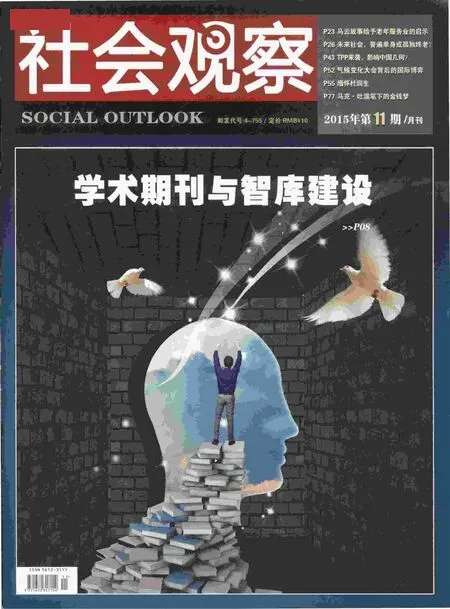喜剧电影的囧途:生于通俗死于低俗
文/刘宇清 张瑶
(刘宇清系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张瑶系西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目前,喜剧电影对性期待的展示,对性别奇观的畸形倒错,对精英文化的拆解,使大众审美扭曲化、符号化、低俗化。原本喜剧片中由讽刺带来的社会批评,或者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和关怀被销蚀成一盘散沙式的色情段子合集。
近年来,国产喜剧电影既开拓了类型,又培养了观众,对中国电影市场和事业的繁荣功不可没。在这个过程中,由《甲方乙方》开创的“贺岁”系列以及由《人在囧途》演绎的“囧途”系列,绝对堪称“首功之臣”或者“典型代表”。但是,从《甲方乙方》到《不见不散》《没完没了》《非诚勿扰》,从《人在囧途》到《泰囧》《港囧》,几乎每一部电影都经历过“鲜花与板砖齐飞,口碑与口水对决”的遭遇。奇耶?怪耶?在众声喧哗的嘉年华时代,人们忘情地迈步在人生自我的“囧途”上,谁愿意辩证评价分歧的缘由?谁在意喜剧电影“生于通俗死于低俗”的隐忧?
人在囧途,路在何方?
2010年,《人在囧途》以800万元投资获得4650万元票房,创下中小投资电影的一个奇迹;2012年底,《人再囧途之泰囧》斩获12亿超高票房;截至2015年10月20日,《港囧》再攀票房高峰,收入超过16亿。参照当前中国电影市场的趋势,徐峥团队的下一部作品无论是《荷囧》还是《非常囧》,票房价值依然可期。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囧”字电影无疑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但若换成文化艺术的视角,可能很多人都有点担心“囧途”系列电影的社会内涵和批判力度会“再而衰、三而竭”。

从一定程度上讲,《人在囧途》的故事是从社会生活中“拣”的,《港囧》的故事是根据个人情感“攒”的;《人在囧途》的情境是典型的,情节是生长的,表演是生活的,《港囧》的情境是规定的、情节是编制的,表演是夸张的;《人在囧途》表现“打工仔”在“春运”期间回家过年的“霉运”,引发了“群众”的普遍共鸣,《港囧》表现“成功人士”“始终无法接成的吻”,本身可能只是“小资”的矫情;《人在囧途》采用《人在旅途》的旋律——从来不怨命运之错,不怕旅途多坎坷——教人“平平淡淡最是真”,《港囧》的旋律则有点像铜板的碰撞和观众的笑声在交响,教人白日梦想或者选择性健忘。从《人在囧途》到《港囧》一路走来,各种“窘境”越来越离奇、怪诞、脱离地面。眼看着“囧途”就要变成“穷途”,会不会有一个“柳暗花明”的转变?10月25日,徐峥在“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上表示,不管接下来的作品是《荷囧》还是《非常囧》,他都会带着自身对生活的感悟与观众一起上路,与观众一同在“囧途”中品味人生。结果如何?不妨拭目以待,并致美好的祝愿。
眼馋《人在囧途》《泰囧》《港囧》赚得盆满钵满,大量山寨版“囧片”闻风而至。据《法制日报》统计,2013年上半年立项的电影剧本中,片名里带“囧”字的多达24部;从今年8月到10月,就有《沪囧》《韩囧》《囧途陌路》《飞在囧途》《囧神恋爱》《疯狂囧途》等6部“囧”片立项,剧情都是在“囧途”上追逐、冒险、阴差阳错的爆笑故事。齐白石有句名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爱默生说,“羡慕就是无知,模仿就是自杀”。前几年的《猪猪侠之囧囧危机》、《囧探佳人》和《临终囧事》,无一例外地身陷“囧境”、亏本失利。事实证明,一味地跟风摹仿,粗制滥造,注定是穷途末路。“囧”字电影,可能是金字招牌,也可能是致命符咒。国产喜剧电影如果都像鸵鸟那样一头扎进“囧途”,无疑会成为一道刺目的“煞风景”。
笑人笑己?摹仿何人?
亚里士多德说,“喜剧摹仿低劣的人”。换句话说,“喜剧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差的人”。亚里士多德还说,“喜剧的目的在于通过滑稽的表演和情境逗人发笑”。人们在为喜剧电影撑腰的时候,或者在为“娱乐至死”辩护的时候,大抵都会变相地援引这两句“金科玉律”。比如:理性者说“现场观众的笑声就是对喜剧的最高奖赏,也就是最终评判标准,不必对其思想性、艺术性做更多的苛求”;率性者说“娱乐有理,恶搞无罪”。那么问题来了,当前的喜剧电影到底摹仿了什么人?观众发笑时,是在笑别人,还是笑自己?
喜剧电影摹仿的对象,要么比我们好,要么比我们差,要么与我们一样,这是与电影观众相对而言的判断。但是不管怎样,真正通俗的(popular,受欢迎的)喜剧总是“摹仿我们”,最有意味的喜剧总是“调侃自己”,缺乏善意的喜剧才“嘲笑别人”。换句话说,“我们”所包含的范围越广泛,喜剧电影就越通俗,越受欢迎;调侃自己越彻底,评判别人越宽容,喜剧电影就越有意味。《甲方乙方》和《人在囧途》刚放映的时候,都曾遭遇有人撒花有人拍砖、有人取经有人吐槽的“囧境”,但现在却被普遍地承认是“有意味的形式”,被赋予开创性的经典地位。个中缘由,耐人寻味。
《甲方乙方》里“好梦一日游”牵扯出了整个社会的众生相,很多人都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影片针砭吃喝风、食文化、追星族、伪道德,让观众在笑声中与过去告别,好评如潮。《私人订制》的故事架构和艺术趣味与《甲方乙方》并无本质差异,但恶评漫天,原因何在?一方面,观众对“小品加段子”式的电影产生了审美疲劳;另一方面,影片“挖苦”了现实社会中真正的弱者,而对真正可笑的现象却“嘲笑”不力,甚至造成价值观的混乱。比如:官员腐败是群众导致的,不是他自己的原因?不喜欢俗的人都是神经病,此生只配弹棉花?有钱人过得真惨,穷人的日子好多了?环境遭到污染,需要道歉的是群众?在一定程度上,《甲方乙方》“不太真实又煞有介事”,如梦似幻又实有所指,令人开怀又发人深思,笑人笑己又辩证平衡。《私人订制》靠“编段子”和“说狠话”来取悦观众,实质上既不尊重电影,也不尊重观众。
《人在囧途》中的挤奶工牛耿非常“可笑”:长相矬,嗓音怪,衣衫不整,动作滑稽,又土又穷,但他生性戆直,是非清楚,爱憎分明,也非常“可爱”。换句话说,就“条件”而言,牛耿比“我们”很多人都差;但从“精神”来看,牛耿比很多人都好。玩具店老板李成功更体面、更有钱、更聪明,令人“羡慕不已”;他的情感生活开小差,价值判断有杂念,令人心照不宣。牛耿“丑陋的外貌”和“愚笨的心智”令人发笑,但他堂·吉诃德式的精神令人敬仰。李成功外强中干的行为非常滑稽,但他心存善念知错能改的本质令人同情。他们都是形形色色“民工”中的一员,历尽艰辛渴望在春节回家。他们阴差阳错的遭遇,何尝不是“我们”大家的笑话。
“喜剧的目的在于通过滑稽的表演和情境逗人发笑”,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滑稽的动作令人发笑,近似一种生理反应,引起低层次的快乐。幽默的语言令人发笑,必须经过心灵的反应,接近理性的快乐。滑稽之人做可爱的事,可爱之人做滑稽的事,“我们”若能感同身受,就会开心地笑,会心地笑。
通俗低俗,一念之间!
客观地讲,《甲方乙方》和《人在囧途》都是具有开创性的成功之作。以此为原典的系列电影,可能走出三条轨迹:其一,为了提升“艺术品味”而向上行,日趋高雅,变成正剧;其二,为了满足“娱乐趣味”而向下行,日趋低俗,沦为闹剧;其三,围绕“通俗”的价值基准,若即若离,雅俗共赏。以《甲方乙方》为开端的贺岁喜剧,在中国影坛风靡十余载后,原本计划通过《非诚勿扰》过渡到第二个系列,但《私人订制》却沦为“小品电影”或者“段子电影”,其下行的轨迹清晰可辨。对比《人在囧途》和《泰囧》《港囧》,下行的趋势已露端倪。影片当然应该“接地气”,但最好贴着地面走,不要往底下钻。从通俗到低俗,距离只有一板之隔,选择只在一念之间。

《港囧》表现“成功人士”“始终无法接成的吻”,本身可能只是“小资”的矫情。
通俗与低俗要合度。“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近年来颇受瞩目的喜剧电影,对通俗与低俗的关系,似乎都有点拿捏不当,进退失“度”。车震、床戏、异装、性别倒错,男人怀胎……尽皆过火,尽皆恶俗。比如:《港囧》里的丈夫徐来无心无力,妻子蔡波趁其熟睡,虎胆雄威地完成生子计划,“药不能停”成为口头禅,丈母娘家人都是势利眼;《捉妖记》中,宋天荫被迫误食妖蛋,在仓皇逃亡的过程中,宋天荫也像普通孕妇一样出现了妊娠反应,例如特别喜欢吃酸的东西,随着怀孕时间的增加,腹部逐渐隆起,并且出现分娩的迹象。迎接新妖王胡巴出生的段落令人匪夷所思。霍小兰教宋天荫如何调理气息,而她更是扒开宋天荫的裤子,拿着大剪子,为他待产,而这时,最吸引观众眼球的地方在于不具备女性生殖系统的宋天荫如何生产一名婴孩。至此,宋天荫的男性气质在本片中几乎泯灭殆尽。娱乐至上的社会导向善于营造一种视觉奇观,同时,观众的无理需求把这种期待推上高峰。
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分野后,文化的高低排序次序俨然已变为高雅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群氓文化。高雅文化长久以来一直以高屋建瓴的姿态俯视大众文化,以呈现出一种排他性。而当下,高雅文化的排他性却受到大众消费文化的干扰。观众对精英观点以及传统文化的消遣成为当下喜剧电影低俗化的又一特点。在《港囧》中,徐来的小舅子蔡拉拉梦想自己能成为纪录片大师。在香港的旅行中,他片刻不离摄像机,妄想自己是“电影眼睛”的理论践行者。在和徐来的对话中,蔡拉拉说他的父亲是弗拉哈迪,徐来转问蔡拉拉,那谁是你的母亲呢?在这次对话中,提到了纪录片之父罗伯特·弗拉哈迪,同时也提到了电影眼睛派的创始人吉加·维尔托夫。显然,大多数观众并不了解弗拉哈迪或维尔托夫,而影片中蔡拉拉成为大众的一个缩影,对精英观点的消费,成为一种符号性的消费。也就是说,像蔡拉拉一样的普通大众在面对精英观点时,实际上是手足无措的,这种手足无措在于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断裂。弗拉哈迪与维尔托夫虽在大众头脑中留下短暂的印象,但大众并不是接纳其经典的观点,而只是浅显地消费这艺术这一符号,而就在这种转呈关系中,艺术大众化、庸俗化。
目前,喜剧电影对性期待的展示与凝视,对性别奇观的畸形倒错,对精英文化的拆解,使大众审美扭曲化、符号化、低俗化。原本喜剧片中由讽刺带来的社会批评,或者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和关怀被销蚀成一盘散沙式的色情段子合集。观众的捧腹大笑已然不能成为当前喜剧电影低俗化的避风港。喜剧片作为当下观众最易于选择观看的类型片,特别是在以家庭为观影团体的观众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如何清理喜剧片中的“垃圾”,遏制其低俗化倾向,成为喜剧片制作者不得不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