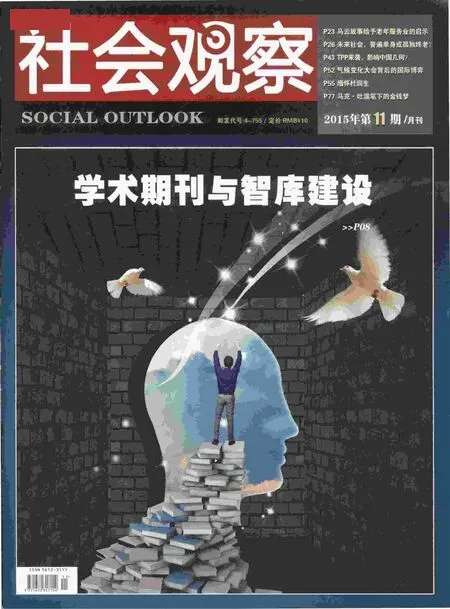气候变化大会背后的国际博弈
文/汤伟

气候变化无疑是当前最为重要的全球性问题之一,其内嵌的发展空间、能源安全、资金技术等议题迅速蔓延渗透到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领域,成为各国发展的核心变量之一。然而国际制度的构建并非一帆风顺,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碳排放总量以及生态脆弱性决定了不同的利益归属,并且随着碳排格局的变化,这种利益归属还将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有鉴于此,一些学者认为,气候谈判阵营正在走向“碎片化”,“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尽管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理解不同政治阵营的基本向度,但是也正在趋于弱化。
2015年12月,即将召开的巴黎气候峰会将产生一份对2020年减排格局、资金技术分配作出全面安排的巴黎协议,这份协议无疑将产生里程碑式的影响。然而,在长达20多年的谈判进程中,阻碍广泛协议达成的因素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由此巴黎协议仍很可能是一份各方有限接受但难以满意的文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达成巴黎协议的征程中进行过怎样的交锋博弈,值得我们梳理和反思。
围绕气候问题的国际博弈一直十分激烈,甚至可用“生死相搏”来形容,其原因就在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小岛联盟的确面临生死存亡或者严重灾难,由此气候博弈就不能不在“气候变化是安全议题”的氛围内进行。这种“生死相搏”的紧张气氛具体体现在关于气候谈判的规范、内容、架构、主体等四方面。
围绕气候问题的国际博弈一直十分激烈,甚至可用“生死相搏”来形容,其原因就在于很多发展中国尤其小岛联盟的确面临生死存亡或者严重灾难,由此气候博弈就不能不在“气候变化是安全议题”的氛围内进行。这种“生死相搏”的紧张气氛具体体现在关于气候谈判的规范、内容、架构、主体等四方面。
是否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
始终贯穿气候谈判全过程的核心规范是,是否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共同”是指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责任,每个国家甚至每个个体都要采取相应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践行低碳责任,而“区别”意味着发达国家要承担绝大多数的减排责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来减缓、适应气候变化。显然,“区别”是要求“强者”比“弱者”承担更多的道德责任和历史责任,因为无论按照历史累积或者人均排放,发达国家都必须承认自身工业化对当前的气候变化担负主要责任。然而,由美国领导的伞形集团却坚持认为,如果只是发达国家减排而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大国不减排,那么任何减排努力都会失效,由此,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也必须实行绝对量的减排。实际上,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和第二经济大国,也由于小岛联盟和欧盟等立场的接近,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基础四国”承担更多责任的呼声迅速上升。对中国等发展中大国来说,这不仅仅意味着更高的减排目标,也面临资金技术对外援助的压力,由此“区别”的责任越来越向“共同”的责任转变。
气候谈判内容聚焦于资金技术
《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和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有效地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甚至设计出了清洁发展机制以激励双方的合作。然而这一双赢理想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发展中国家获取了部分资金,却与发达国家千亿美元的承诺相去甚远,而技术的获得更是极其有限。应发展中国家的强烈要求,《坎昆协定》终于达成妥协,发达国家在2012年前提供总计3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并预期在2020年前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长期资金。然而,即便是这笔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发达国家也迟迟不能兑现。到2014年这一目标缩水至100亿美元,而在德国柏林会议上30国才筹集93亿,更遑论发展中国家此前一再提出的生态损害补偿费。这说明一旦涉及到实质性的以资金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时,发达国家仍不愿意快速有效地付诸实施。在发达国家迟迟没有兑现承诺的关键时刻,中国不断自我加压,在与美国达成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决定向绿色气候基金捐资30亿美元;拿出200亿元人民币(约31亿美元)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包括增强其使用绿色气候基金的能力等。
以何种方式推进国际气候谈判进程?
在气候谈判架构方面的博弈,主要围绕几大谈判集团以何种方式推进国际气候谈判进程而展开。长期以来,由于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导致《框架公约》全面履约协议难以开展,为将所有国家整合进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气候谈判各方设立了《公约》和《议定书》双轨谈判进程。2007年气候大会通过《巴厘路线图》,明确坚持双轨制谈判,所有发达国家都要履行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减排责任,美国也不例外,其设立的特别工作组在2009年向《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递交工作报告,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谈判完成时间一致。遗憾的是,2009年哥本哈根谈判大会没有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但决定延长巴厘路线图的法律效力。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又决议再延长5年《京都议定书》的法律效力,设立德班增强行动平台,负责2020年后减排温室气体的具体安排。这种架构充分保证发展中国家不能和发达国家一样承担绝对减排义务的核心关切,也保证所有国家有着充分机会和可能性参与到谈判进程中来。然而,美国在长期谈判进程中要求双轨合一,既讨论发达国家的减排责任,也要讨论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义务,实际上是要模糊两大阵营的核心区别,要求发展中国家无差别地共同承担责任。2009年哥本哈根谈判大会失败之后,欧盟作为气候谈判的火车头遭受重创,谈判的核心引擎出现缺失,谈判意愿和动力明显不足。直至去年以来美国气候外交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中美接连达成两项《联合声明》。这说明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代表,中美开始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出发推进全球气候谈判,并且分别作出了符合对方期望的若干承诺。这意味着有关气候谈判架构的博弈出现缓和迹象。

气候谈判的博弈主体出现分化组合
本来气候谈判的主体主要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欧盟、美国领导的伞形集团和“77国+中国”三大集团,然而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和碳排放的持续增长,“77国+中国”也分裂出了各种小的谈判群体,譬如小岛联盟和最大不发达国家、“基础四国”,还有各种区域性谈判群体等,由此博弈主体逐渐从“南北格局”向“排放大国-排放小国格局”转换。需注意的是,这一转换并不是孤立的单一过程,而是伴随其他行为主体对气候谈判的不断介入,譬如各类绿色环保组织、联合国的其他机构、各类智库和其他国际组织。这些新型行为主体以及联合小岛联盟,或者代表发达国家,或者通过自身的研究影响世界舆论,对气候谈判进程施加了极大的影响。总体上看,这些非政府行为主体和国际组织多数来自发达国家,拥有丰富的知识和参与经验,也有着自身独特的价值取向,对碳排放日益增多的发展中大国产生了显著压力。
总体朝不利于发展中大国方向发展
综合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交锋博弈整体朝着不利于发展中大国的方向发展,如何维护自身的利益,并与全世界一道实质性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大国需要拿出一整套的解决方案,而这套解决方案需要在上述四方面作出适宜的安排。在巴黎气候大会前夕,中国通过与美国的双边联合声明,无论在国家自主贡献还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方面都作出了史无前例的承诺。不过,这些承诺能否转化为谈判要件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得来自发达国家更多的资金技术,还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