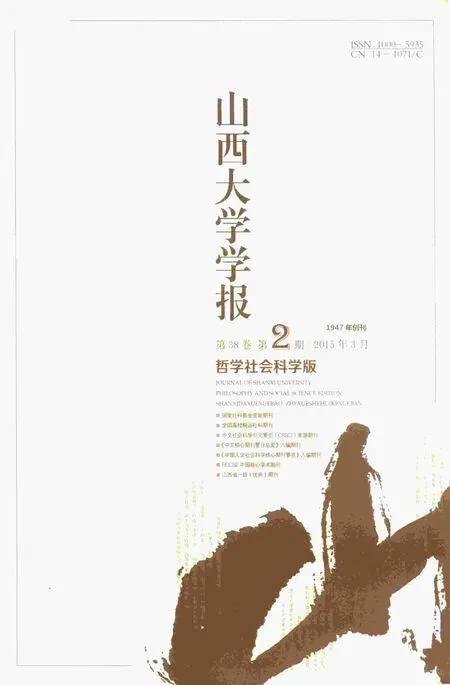晚清山西厘金起源及发展探析
颜冬梅,雷承锋
(山西大学 晋商学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06)
作为支撑晚清财政的重要税种之一,厘金的产生、演变与晚清财政史、政治史、军事史皆有着密切的联系,长期为学界所瞩目,王振先、罗玉东、何烈、彭泽益、周育民等学者已先后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探,但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全国性经济史研究的层面上。近年来,关于区域厘金史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可惜的是,晚清山西厘金的起源与扩张的问题仍是清季厘金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笔者不揣浅陋,拟从区域社会史发展的角度出发,选取山西厘金作为考察对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史料分析法和考证法,对晚清山西厘金的起源、推广等内容进行探佚和梳理,揭示其在特定地域环境下所具有的特性。
一 厘金是晚清财政的重要补充
厘金是在清廷镇压太平天国时期为接济饷需偶然间创制的一种临时筹款方法,其产生兼具历史性与偶然性。清朝财政的主要税收,在咸丰以前,主要由地丁、关税、盐课、杂赋四项构成。四项税收中以地丁收入最多,但是作为清廷税源支柱的地丁却受到“康熙五十年以后续生人丁,永不加赋”[1]的法律的限制,其结果是使大部分税收失去了扩张性,而其他三项税收或与地丁性质相似或受定额限制,亦不能随意加征[2]。由此可见,清朝财政的最大缺陷在于缺乏弹性,一旦财政吃紧,很难在短期内得到快速弥补。
以鸦片战争为界标的清代后期的财政收入政策与财政收入结构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对这种变化带来的结果予以揭示:“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3]赔款的催偿进一步加深了封建剥削关系,“以致富者益富,贫者益贫”[4],“流亡之众,通欠之多”[5]的社会现象日趋普遍,及至太平军起义前夕,清朝政府财政窘迫的情势,即已日甚一日。这表现在“入款有减无增,出款有增无减”[6]。1850年至1851年间,太平军起事之初,清廷即从各省调兵防堵“围剿”,先后共计用银1 800 多万两[7]。军兴三年以后,据统计,由户部国库拨给和各省截留筹解的军饷,即已耗银2 963 万两[8]。所以,从1853年起,清朝政府便因军费激增而又“罗掘俱穷”,开始面临着空前的财政危机。
国库财政稳定与否,它取决于实收银两的多少。由上表得知:1853年“实银”收入仅有48 万两,以后不断减少,每年只十几万两。十二年间总计不过232 万余两,平均每年不过19 万两而已。支出方面也相应受到限制,总计229 万余两,平均每年也只有19 万余两。就其“实银”进出总数的规模而言,可以说,大约只抵得上两个中等县份的田赋收入,这简直微小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了。

表1 1853 -1864年户部银库出入实银总数
户部银库岁计,向来常有盈余。十八世纪后期,库存银数经常在7 000 万两,其后库贮大为降低,1821年至1834年平均只有27 162 949 两,1850年只剩800 万两[9]。到太平军起义后,银库入不敷出的现象愈加突出。1852年亏银190 多万两,1853年亏银400 多万两[10]。

表2 1853 -1861年户部银库年终结存银数
以上数据表明,1853年至1861年平均仅存银180 余万两,约当1821年至1834年间的1/15,约当1777年的1/45。据1865年户部报告,战时银库每年结存的“实银”,1853年至1857年间平均约11 万多两,1858年至1864年平均只6 万多两[11]。此时的大清库储已经是岌岌可危矣。
这里还要指明的是,战时国库收入总额能够维持在平均每年957 万两左右,一则是自1853年起,靠发行银票、钱票、铸造大钱、铁钱;再有就是从1856年起,把京饷原由各省预拨改为临时定额摊派解款的结果[12]。实际上,这都只能做到勉强维持封建朝廷的苟延残喘而已。战时清朝中央国库支细情况如此,各省地方财政“更属竭撅不遑”[13]。早在1853年间,各省库款即因屡次筹拨军饷,据说,由于“移缓救急,悉索无遗,封储之款一空,征解之难数倍”,结果“不特部库时时支绌,而且外库处处拮据”[14]。可谓“百计罗掘,十不一应。”
其时刑部侍郎雷以讠咸奉旨在扬州帮办军务,为筹措军饷,遂奏请于里下河设局劝捐练勇,以保东路。考虑到劝捐并非长久之计,他听从幕僚钱江的提议,仿效林则徐的一文愿之法,实行所谓“抽厘之法”[15]。最初抽厘不曰抽或征,而叫捐;雷氏既得此法,遂于咸丰三年(1853)九月派人到扬州城附近之仙女庙、劭伯、宜陵等镇,劝谕米行,捐厘助饷,并于咸丰四年(1854)三月奏请苏省各府州县也仿行劝办抽厘。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厘金是清朝政府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曾一度是清政府财政的重要补充。
二 山西厘金创办的背景及特点
近代以来,由于山西地处内陆,受战争影响较小,社会经济状况基本稳定,进而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清朝政府疯狂搜刮钱财的主要区域之一,甚至连地方各省此时都将山西作为财源之蔽,一遇不测便想到让山西出资化解。咸丰、同治年间的几次战争中,山西商民捐输最多。从咸丰元年(1851)十一月间开始,清政府几次命令山西巡抚哈芬、布政使郭梦龄和在籍官员徐继畬等,实力劝说并强迫商民捐款。据统计,咸丰二年(1852)至咸丰三年(1853),山西票号商人捐款达到267 万两之巨,山西盐商捐银总额也超过了300 万两,光是咸丰三年(1853),山西为筹解军饷捐银已达40 余万两。[16]据清末山西籍开明士绅徐继畬统计,“晋省前后捐输已至五六次,数逾千万”[17]。
捐输之外,清政府也不断加强对山西的摊派。山西境内虽然大部分时间没有战争,却也疲于应付繁重的战争后勤供应,不时向战场上提供诸如火箭、炸炮一类的武器,这与山西富商云集且为制造兵器大省有关。比如在太平天国战争爆发以后,山西每年仅办理征解高平生铁一项就达100 万斤,一直到咸丰九年(1859)才告停止[18]。当时山西额解之物有五大宗,即铁、绸、绢、纸、磺。每年例解平铁1 批,80 498 斤;好铁4 批,20 万斤;大潞绸1 批,30 匹;小潞绸1 批,50 匹;农桑绢1 批,300 匹;生素绢4 批,1 200匹,遇闰加40 匹;呈文纸1 批,4 万张;毛头纸1 批,100 万张;硫黄1 批,10 万斤[19]。通年需银十一二万两。与此同时,晋省每年承担汇拨京、协饷重任,为数甚巨,山西每年奉拨京饷附划拨绥远旗兵要需银50 万两,每年解协饷87 万余两(甘肃新饷78万两,乌科二城经费银95 666 两,直督养廉银3 000两),其中,河东每年应解京部十六款共银175 549两有奇,奉拨外省协款每年52 万两[20]。曾国荃曾叹曰:“思军兴以来至光绪三年,晋省奉拨协济各路及各省饷项,无不竭力筹解,先后核计不下二千万两。”[21]
纵观晋省之财力,一向地瘠民贫,虽接近京畿,地文稍占优胜,但藏富于地,仍无补益;若交通机关则山深水浅,不逮沿江沿海各省远甚,然以西陲壤僻之乡,其田赋之负担竟抗衡于川、鲁、汴诸省,额征将近三百万,彼观此赋亦不为轻[22]。今查山西财赋以地丁为大宗,杂款、盐税次之,而他项稍辅之。清代山西丁银税基数无闰之年额征银约2 936 754 两,遇闰加征银2 920 余两,唯因灾蠲缓及民欠未完岁所不免,而报垦升科其增加有限,故征收讫难如额[23]。且查咸丰元年至咸丰九年,山西丁口虽逐年上升,由1 589 万增加到1 612 万,[24]每年增加额在2.4 -4万之间,增长率不超过0.3%,土地有定数,人丁也就那么多,所以通常情况下地丁银的征收比较稳定。河东盐课是山西又一大财源。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时,河东正杂课银为66.5 万两,咸丰三年(1853年)河东因盐商捐输军饷过巨而进行盐制改革,由先课后盐制改为就场征课,剔除各项规例摊派之后,咸丰四年免商之始照商运旧制每纲征正杂课额524 800 余两[25],这是近代河东盐课的收取基数。用光绪六年(1880)间署理山西巡抚葆亨的话说,“晋省地处山瞰,既无关税之盈余,亦无槽折之余羡”,所以山西在近代时期财力十分有限,地丁银难以挤占,就要从别的方面想办法扩展财源。
据光绪版《晋政辑要》记载,咸丰九年(1859)正月,巡抚英桂奏准,据藩司常绩、臬司沈兆云、冀宁道瑞昌等称:“晋省每岁正供,除本省俸工役食杂支等款外,库储二百六十余万两,岁运京饷、生铁、工程等项,已在二百二十余万两;此外本省兵饷及各路协饷、例饷经费等项为数甚巨,连年幸赖士民捐输得以斟酌缓急分途解运。唯自咸丰二、四、五、六、七等年历次动捐后,商民多称资本折亏,家业消落,骤难强其再捐外,实无长策。查近年各省抽收厘税,尚可酌盈剂虚,办理得宜或可有清第。晋疆僻处一隅,非若他省之水路衝衢商贾辐辏,且山城贩运脚费较多,故货价倍昂于他省,民情重利,创始颇难。且查咸丰七年,部咨义覆胜保奏请普抽厘税一折,凡无军务省份未经抽收者,断不可纷更朘削,致失人心等语藉思。国家经费有常,当承平无事之时原可量入为出,若值军务浩繁,转输无述,亦不得不略为变通,权济一时之急。兹除有关民食及一切零星贩卖有碍于生计毋庸抽收,以示体恤,仅择数大宗酌议简明章程,分别省内省外,设立总局分局,或慎选委员,或责成地方官妥善经理。”[26]
咸丰九年(1859)二月初二上谕:“英桂奏筹拨饷项不敷拟试抽厘税一折据称,山西省连年抽收京协饷项及部拨各款为数甚巨,多借助于捐输。现在俯察舆情,自叠次捐输之后,未能踊跃,唯有仿照各省抽收厘税尚可酌盈剂虚。自系一时权宜之计,著照所请,除有关民食及零星贩卖者,均毋庸抽收以示体恤。其余当酌议简明章程,分别省内省外设立总局分局,慎选委员,责成地方官妥为经理,勿许抑勒滋扰,并密查影射侵渔之弊,庶不致有名无实,如试行有效再行定议,具奏倘有窒凝,即行停止,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27]
总结以上资料,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从晋省创办厘金的时间和背景上看,相对较迟,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首先,太平军起义初期,山西离战区较远,受战争影响较小,社会经济环境相对稳定,财政运行相对平稳,并未出现紧缺;其次,清廷内部已有既定行政方针,为保皇祚,断不轻言厘税,渔利百姓。卷查咸丰七年(1857),遵议胜保奏请《各省普抽厘税一折》内载,“凡无军务省份,未经抽收者,断不可纷更朘削,致失人心等语藉思。”[28]此番开征,实属权宜之计;再者,晋省每岁正供京饷、例饷等经费为数甚巨,连年劝捐致使商民资本折亏,家业消落,况且晋疆僻处一隅,非若他省之水路街衢商贾辐辏,且山城贩运脚费较多,故货价倍昂于他省,民情重利,创始颇难。
其二,从山西厘金创始和确立的过程来看,山西厘金在其空间分布与类型上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山西厘金的空间分布在推广上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其推广趋势上看是先总后分,先府后县;二是从厘金局卡的设置来看,总分结合,守其扼要,兼顾其他,而且这两个特点始终交错在一起。此外,苏省厘金在创办之始,其类型是以“认捐”的形式出现的坐厘,然后才逐渐出现卡厘形式的行厘[29]。而山西厘金在其创办之初即设坐厘和行厘。并且,山西厘金在一开始就是以“筹饷”的名义创办的,而非江苏或其他省份的“认捐”。
其三,从山西厘金征收范围来看,主要以大宗货物为主,米面杂粮不算在内,其中药料由于获利颇丰,按产地不同,税负各异,均较其他货物税负繁重。从征税对象来看,主要是针对行商与坐贾,小商贩则不算在内,以示体恤。从征抽税率来看,则较之江苏、湖北等地略微轻减。从组织机构与人员设置上看,创办伊始,山西厘金采用总分式结构,监管人员是政府指派,而非苏省的“官为督办,绅为经理,官绅结合”[30]的模式。实际上,自光绪二十八年正月起,为变通厘务用人以祛积弊,山西地方政府开始参照湘鄂奉吉办法,酌选派外省候补候选人员会同稽征或拣本省绅衿允当司事,以杜厘务弊端。
三 山西厘金的推广及沿革
咸丰九年(1859),巡抚英桂批准筹饷局详如:“各该商贩有图省厘金绕越偷漏者,将货物全数追缴,货价一半充饷一半给赏。”[31]咸丰十年(1860)三月户部议准嗣后“碛口、风陵渡两卡改厘为税,自本年(咸丰十年)三月初一日起,改行商药料厘为税。二卡洋药税则仿照崇文门湖北省章程发给税票,每药百斤抽税银二十两外加收银二两以为公费,其余槐树铺等五卡均需验有碛口等处税票始准放行。”[32]咸丰十年(1860)巡抚英桂批准“各州县坐贾药料均应入行销售,准行头于坐贾药料每百两除厘银外另收行用银一钱六分。”[33]
同治元年(1862)四月,英桂批准筹饷局,“嗣后各卡各属查获行商坐贾绕漏厘税之案,查照匿税定律将药料货物追罚一半入官,一半给还本人,仍于一半入官物内以十分为率七分充公三分充赏。”[34]“坐贾仍完厘金,另有售卖药膏各户,曾经令各县按户抽厘。后以体恤小贩为由,停止征收。”[35]
光绪三年(1877),山西大祲,正项既减,公费愈绌,行商裹足,坐贾滞销,所有各路添设分卡,均奏准裁并,以节浮糜。嗣后山西节年厘金收数仅六七万两,连年收数不旺,遂于光绪七年奏准又将各卡一律分设。实缘山径丛杂,偷漏太多[36]。光绪八年(1882)十月巡抚张之洞批示永和县禀查湖北厘章罚款半归公半充赏,可为成式,此后应一律改于罚半充公之中以一半解局一半充赏,仰筹饷局通饬该县并各州县关卡遵照[37]。同时又以各州县经收坐贾厘金,每易滋生流弊,因将商务较繁之处,一律改添委员会同稽征[38]。光绪九年份厘税两宗共收银十八万两,十年份共收银二十一万两有奇,收数畅旺。但因改派委员应需经费为数较多且京官津贴亦议于厘金公费项下动支厘捐公费一成断然不敷,遂奏准自光绪九年(1883)以后,无论收数比从前如何畅旺,除照从前极旺年份收数十七万两仍按旧章提出一成之外,其十七万两以上多征之项准予旧章一成之外按多收之数再提一成作为外销公费。至谓药税加收公费一律收归正项照厘捐例统于通年收款内按实开支[39]。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又奏准山西省咨送光绪三年至八年厘金销册,列有未完款项恐有挪用情弊,应令该抚不时访察经收人员,如系欠解,即行撤委勒追,逾限不完,从严参办,不准再列委员欠款,以杜侵挪[40]。又奏准嗣后山西省厘税两宗,如收数在十八万两至二十一万两以上者,准予旧章一成外,由正款提出银一万两弥补一成公费不敷支用;如收数在十七万两左右,仍照旧章提用一成,不准多支以示限制[41]。光绪十二年(1886)九月又奏准令将土药厘金或与行销处所从重加征或仿照甘省章程药厘之外加抽膏厘,此后无论洋药土药入口时每百斤抽银三十两再于落地时每百两抽银九钱三分八厘,如系本地所产贩运本省售卖者,于起载处所每百斤抽银三十两再于落地行销处所抽银九钱三分八厘,合并计之每药料百斤共抽银四十五两;如有本地贩运出省比照外省入口章程于出口厘卡每百斤抽银三十两以昭平允,拟请不论广膏土膏饭外省入口本省起载时均按一百两抽银三两七钱五分落地行销处所每百两抽银二两二钱,出口膏厘亦照入口抽收如此办理[42]。光绪十二年(1886)十一月奏准山西将征收药膏两项厘金奏咨立案,各属征收药膏两项厘金仿照夔关按四季造册报部听候拨用,不准擅行动支以符奏章[43]。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谕旨准郑思贺所奏,依议饬各省裁并厘局[44]。山西覆奏称通省局卡迭经淘汰,实存总卡七处,分卡十八处,兼处要隘,无可再裁,后奉诏将原设苇泽关分卡归并槐树铺总卡兼办,关头村分卡暂撤,归地方官稽查,若无碍抽收,再行永远裁汰[45]。光绪二十二年(1896)遵户部奏咨筹款案,开办烟酒税,由筹饷局办理,议定烧酒一斤抽税钱三文,旱烟一斤抽税钱五文,棉烟一斤抽税钱十文;光绪二十六年(1900)奏明烧酒每斤于原抽三文外,加抽二文,共计五文,旱烟每斤加抽二文,合前共计八文[46],光绪二十七年(1901)山西因每年派担赔款数十万两,为筹款计,设局抽收煤厘,土盐税,并增定厘则,添抽货物。翌年复加抽烟酒税,计每酒一斤加抽十一文,合前共计十六文,旱烟每斤加抽四文,合前共计十二文,棉烟每斤加抽八文,合前共计二十四文[47]。光绪二十九年(1903),将收数无多之煤税局及土盐税局改由地方官兼办,以节经费[48]。因江西改办统捐颇见成效,光绪三十年(1904)十二月二十七日,户部奏请各省筹办百货统捐,山西依奏试办统捐,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成立统税局,重订厘则,整顿局卡,将售日应抽加抽之数统作原抽,再按价酌加,计为加抽,并添抽各货,后因商民对此新税啧有烦言,于宣统元年(1909)调取光绪三十四年之崇文门税则为参考,将原定新章税率视崇文门减半[49]。
综上所述,山西厘金虽由外省植入,但并非简单复制,而是因地制宜。从外省移植到本土推广,厘金逐步由“筹计应需”的临时筹款方式转变为“妥办善后”的经常税,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山西厘金基本延续着自身发展与区域本身特征相结合的思路。随着厘金制度的发展,厘金之弊愈发明显,整顿厘金势在必行,山西响应朝廷号召,积极试办统税,一方面适应了晚清财政体制改革的需求,另一方面却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严重阻碍了本省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 结论
厘金肇始于咸丰三年(1853)的江苏,原本是清廷为镇压太平天国、筹措军费而加征的一项临时性税收,因颇具成效,各省渐行效仿,随后逐渐演变成全国性的具有商税性质的一种征税制度。山西厘金创办于咸丰九年(1859),虽由苏省植入,但并非简单复制,晋省举办厘金有其特殊的背景。咸丰以来,山西地近京畿,深处内陆,故而受战争影响较小,社会状况较为稳定,山西不可避免地成为清廷化解财政危机、疯狂收刮税负的首选之区,连年的捐输、摊派架空了山西财政,而山西疆僻一隅,本就地瘠民贫,山径丛杂,商业发展较沿海地区相对滞后,长此以往,财源短缺也就不足为奇了,山西厘金的开办实属一时权宜之计。从外省移植到本土推广,山西厘金基本延续着自身发展与区域特征、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结合的思路,逐步发展、完善、形成了一整套以省情为基、分层管理、职权明确的厘税征稽制度。随着厘金制度的发展,厘金之弊愈发明显,整顿厘金势在必行,山西响应朝廷号召,积极试办统捐,一方面适应了晚清财政体制改革的需求,另一方面却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严重阻碍了本省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1](清)昆 冈,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五十七[M].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石印本.
[2]罗玉东.中国厘金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10:4.
[3]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恩格斯·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
[4]贺长龄.耐庵公赎存稿:卷四[M].中国台湾:文海出版社,1882:6.
[5]吴嘉宾.求自得之室文钞:卷四[M].富文斋,1866:11.
[6]《道光三十年四月十一日卓秉恬折》转自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38.
[7]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十七[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8232.
[8](清)官 修.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32 -33.
[9]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84.
[10]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84.
[11]《同治四年三月十三日户部左侍郎皂保折》转自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43.
[12]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43.
[13]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十九[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8260.
[14]《咸丰三年七月初三日户部折》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44.
[15]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四十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12:8037.
[16]山西省志研究院.山西通史:第六卷[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38 -39.
[17]徐继畬.松龛全集·文集:卷三[M].刊印本.1915:14.
[18]山西省志研究院.山西通史:第六卷[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38.
[19]苑书义,等.张之洞全集:第一册[M].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117.
[20]经济学会.山西省财政说明书·沿革利弊·各论[M].北京:经济学会,1915:110.
[21]梁小进.曾国荃全集[M].湖南:岳麓书社,2006:275.
[22]经济学会.山西省财政说明书·沿革利弊·各论[M].北京:经济学会,1915:52.
[23]经济学会.山西省财政说明书·藩库内外销收款[M].北京:经济学会,1915:1.
[24]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1955:367 -368.
[25]经济学会.山西省财政说明书·沿革利弊·各论[M].北京:经济学会,1915:101.
[26](清)刚 毅,等.晋政辑要:卷十二[M].刊印本.1888:21 -22.
[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九册[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51.
[28](清)王延熙,等.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三十七[M].上海:上海久敬斋,1902:2.
[29]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66 -167.
[30](清)王延熙,等.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三十七[M].上海:上海久敬斋,1902:1.
[31](清)刚 毅.晋政辑要:卷十二[M].刊印本.1888:22.
[32]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三辑[M].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73:486.
[33]刚 毅.晋政辑要:卷十二[M].刊印本.1888:27.
[34]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883 史部·政书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535.
[35]《同治元年八月二十六日御批山西巡抚英桂折》转自罗玉东.中国厘金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9 -20.
[36](清)昆 冈,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重修本):卷二百四十一[M].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石印本.
[37]刚 毅.晋政辑要:卷十二[M].光绪十四年(1888)刊印本,第27 页.
[38]《光绪十一年六月初四日御批暂署山西巡抚英桂折》转自罗玉东.中国厘金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90.
[39]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883 史部·政书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535.
[40](清)昆冈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重修本):卷二百四十一[M].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石印本.
[41]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五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12:8048.
[42]刚 毅.晋政辑要:卷十二[M].光绪十四年(1888)刊印本,30 -31.
[43]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883 史部·政书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537.
[44]罗玉东.中国厘金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90.
[45]《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四日御批山西巡抚张煦折》转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七十七辑[M].北京:中华书局,1995:706 -707.
[46]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二十三辑[M].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73:486.
[47]《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朱批护理山西巡抚赵尔巽折》转自罗玉东.中国厘金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90.
[48]经济学会.山西省财政说明书·沿革利弊·各论[M].北京:经济学会,1915:28.
[49]桑 兵,等.续编清代稿抄本:第九十七册[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424 -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