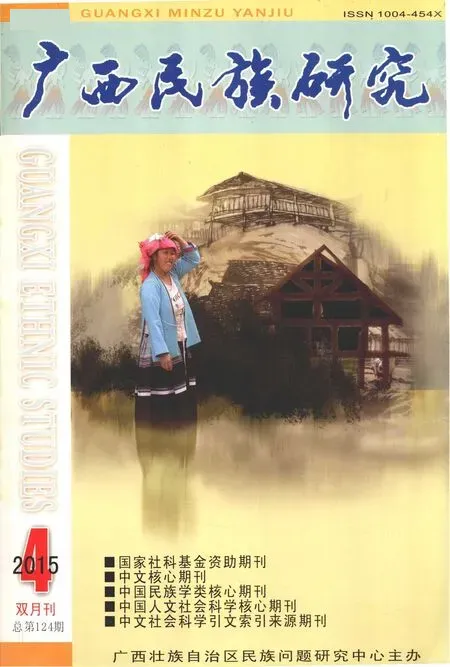骆越文化研究一世纪(上)*
覃彩銮 付广华 覃丽丹
骆越是商周至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南方百越民族中居住在岭南西部的重要一支。其分布东至今广西中部的柳江和红水河流域,西至滇桂交界地,北及贵州南部,西南至越南北部,南至广西南部,东南至广东雷州半岛及海南岛,地理上相连成片。骆越创造的丰富、灿烂和特色鲜明的文化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中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又因骆越分布区地跨今中国和越南两个国家,与中国壮侗语诸民族及东南亚侗台语诸民族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因而骆越历史文化很早就引起中外学者、特别是中国和越南学界的关注。自20 世纪2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便开始对骆越历史文化进行研究,至今已近百年,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大量专著,发表了近千篇论文,内容涉及骆越的来源、分布、名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及民族关系等方面。现将近百年来关于骆越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作一简要的梳理与评述。
一、中国学者的骆越文化研究
据史书记载,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岭南西部地区的骆越人就与商周王朝有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中原地区的精美青铜礼器及青铜铸造技术已传入骆越地区。而骆越分布区地跨今中国、越南两国。因而,骆越历史文化不仅是中国古代史、民族史研究的重要对象,而且也是中外史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中国学者一直是骆越问题研究的主体之一,无论是研究持续的时间,研究学者人数,还是研究的广度、深度及其成果,都是最多的。由于史书对骆越的记载既少且简略,学者们对相关史料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或诠释,故而其观点也不尽相同。
(一)骆越起源与分布
骆越起源与分布问题,是骆越历史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凡研究骆越者,几乎都会涉及骆越的起源与分布问题。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时间较早,研究的学者和取得的成果都比较多。1920年,童振藻在《岭南学报》发表《牂牁江考》一文,作者在考证牂牁江的名称、源流等问题时,述及当地的骆越人,这是最早涉及骆越的一篇文章。1923年,梁启超发表《中华民族之成分》一文,述及古代南方百越支系时,介绍了分布在岭南地区的骆越族。1928年龙潇《中国与安南》、1933年郎攀甘《中国南方民族源流考》、罗香林《古代越族考》 (上、下篇)、王辑生《越南史述略》、1935年潘莳《汉初诸国越族考》、1936年岑仲勉《秦代初平南越考》、1937年罗香林《古代越族之文化》、《越族源出于夏民族考》(1940)、《古代百越分布考》等文,对骆越来源、分布及其文化作了记述,认为骆越是中国南方百越族群居住在岭南西部地区及越南北部的重要一支,与百越民族及其文化关系密切,属于同一族群和同一文化类型。1936年,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一书中有“百越系”一章,其中对骆越的分布及来源作了记述。1943年,罗香林出版《中夏系统中之百越》一书,对百越各支系的来源、分布和社会发展等问题作了论述,这是第一部较为系统研究包括骆越在内的百越历史的专著,其中简述了百越共同文化特征,如流行文身、使用铜鉞、铜剑、铜鼓、善使舟楫等。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1939)、《泰族僮族粤族考》(1947)、蒙文通《越史丛考》(1983)中,都有专门章节,从不同角度对骆越起源、分布及发展、演变等进行论述;特别是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利用地名、语言考证法,论证岭南地区的壮族为旧越人。据不完全统计,从1920年至1949年,有关越族研究的论文148 篇,专著10 多部。[1]这一时期包括骆越在内的百越研究,主要是对百越各支系的来源、分布、文化及其与中原民族的关系方面的研究,而且主要是依据相关的文献记载进行梳理、诠释和分析,因相关史书记载简略,且缺乏相关的考古资料,所以其研究和论述多属宏观性和平面性的,尚缺乏应有的广度和深度。然其重要意义则在于开启了我国南方百越族群或骆越研究之先,为后来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方法。
20 世纪50 至70年代,我国老一辈学者继续对包括骆越在内的百越族群诸支系的历史、源流、经济、文化及与中原民族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如著名学者罗香林相继发表了《古代百越文化考》(1954)、《古代越族方言考》(1955),在台湾出版了集越族研究成果于一体的《百越源流与文化》(1955)一书,对包括骆越在内的百越诸支系的源流、名称、分布、文化及语言等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包括民族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得到较大发展,骆越历史文化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其特点是研究队伍扩大,研究学者增多,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研究问题也进一步深化,而多学科及其方法的应用,使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特别是大量的考古发现和丰富的出土遗物,为包括骆越在内的百越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其中的重要标志是1980年6月在厦门大学成立的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会员遍及全国各省、自治区及港澳台,其中以中南、华南、东南、西南地区和北京的学者居多。学会的成立,使全国从事百越民族研究者得以汇集,学术研讨与交流日趋活跃,使从事百越民族的研究力量得到整合,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不断增多,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问题不断深化,学术水平不断提升。学会每2年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每次研讨会都设定不同的研讨主题,至今已经召开了16 届。每次研讨会之后,都把学者提交的论文汇编成集出版。自20 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骆越在内的百越历史文化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都集中汇集在论文集里,如《百越民族史论集》(1982)、《百越民族史论丛》(1985)、《百越源流研究》(1986)、《百越史研究》(1987)、《百越史论集》 (1989)、《百越民族研究》 (1990)、《国际百越文化研究》(1994)、《百越民族史研讨会论文》(1996)、《百越民族史研究文集》(1998)、《龙虎山崖墓与百越文化》(2001)、《百越民族史》 (2004)、《百越文化研究》 (2005)、《百越研究(第一辑)》(2007)、《百越研究(第二辑)》(2011)、《百越研究(第三辑)》(2012)等等。在每一次研讨会和论文集中,都有一系列关于骆越历史文化的研究。此外,何光岳《百越源流史》,郭振铎、张笑梅主编《越南通史》,林蔚文《中国百越民族经济史》等著作,对骆越的历史、经济、文化作了多视角、多维度的系统研究。王文光《百越民族发展演变史》(2007)一书,从宏观或整体上对中国南方及中南半岛百越发展、分化、融合、演变等进行考察。彭适凡《中国南方考古与百越民族研究》(2009)则利用南方百越地区考古发现的资料,对百越历史、经济、文化发展面貌进行了揭示。这一时期的骆越历史和文化研究,揭示了骆越名称的由来、内涵及骆越源流、分布、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及骆越与其他越族的关系等。
在此期间,广西学者是骆越历史文化研究的主要力量,研究对象更加明确、具体和深化,既有综合性研究,也有专题性研究,对骆越的起源、发展与演变,骆越名称的缘起、骆越与西瓯的关系、骆越与中南半岛民族的关系、骆越分布、文化特征、经济、语言、社会发展及其性质、骆越青铜文化、骆越历史文化遗存等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与探讨,涉及骆越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及生产方式等各个方面。
关于骆越起源、分布及其与西瓯以至中原秦汉王朝关系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广西历史、考古和民族学者研究的重要问题。发表的论文主要有:黄国安《骆越与广西壮族及越南民族的历史渊源关系》(1980),张一民《西瓯骆越考》(1981),陆明天《秦汉前后岭南百越主要支系的分布及其族称》(1985),范勇《骆越族源试探》 (1985),张一民、何英德《从出土文物探骆越源流及其分布》(1986),蒋炳钊《关于“西瓯”、“骆越”若干历史问题的探讨》 (1987),黎之江、吴作韬《珠江流域的民族源流初探》(1987),马头发掘组《武鸣马头墓葬与古代骆越》(1988),覃圣敏《关于马援得骆越铜鼓地点的商榷》 (1988),叶浓新《武鸣马头古骆越墓地的发现与窥实》(1989),梁庭望《西瓯骆越关系考略》(1989),王明亮《西瓯骆越三题》(1993),白耀天《骆越考》(1995),邱明《西瓯骆越族称辨析》(1995),梁敏《论西瓯骆越的地理位置及壮族的形成》(1996),吴小玲《北部湾地区的古代居民探源:骆越》(2001),覃圣敏《中国和印支半岛的瓯骆越人及其后裔》(2005)、《中国南部和中南半岛的瓯骆越人及其后裔》(2006)、《有关西瓯骆越的文献记载及考证》(2006)、《西瓯骆越新考》(2007),于向东、刘俊涛《“雄王”、“雒王”称谓之辩管见》(2009),谢崇安《关于骆越族的考辨》(2011),张应斌《博罗与骆越的起源》(2013)等。在黄现璠等《壮族通史》(1988)、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1997)、郑超雄《壮族文明起源研究》(2005)、罗世敏主编《大明山的记忆:骆越古国历史文化研究》 (2006)中,都有专门章节较为全面、深入地论述了西瓯与骆越的关系及骆越的分布问题。上述研究成果,基本弄清了西瓯、骆越的关系及其分布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西瓯与骆越究竟是岭南越族的两个分支,还是越族的同一支在不同时期的称谓,学者们存在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西瓯、骆越是百越族群居住在岭南地区的两个不同分支;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同一支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称谓。二者所引用的史料相同,只是理解或诠释不同而已。主要原因是史书记载既简略,而且语焉不详,甚至有时还互相矛盾。但多数学者的著作包括黄现璠等《壮族通史》 (1988年)、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 (1997年)、罗世敏主编《大明山的记忆:骆越古国历史文化研究》(2006年)等著作中,通过相关史料记载的分析,认为西瓯、骆越是百越族群居住在岭南地区的两个不同分支,西瓯主要分布在今广西中部柳江及下游浔江以北至桂江流域,即今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骆越主要分布在今广西中部柳江及下游浔江或红水河流域以西、左江、右江及上游驮娘江,西江下游的雷州半岛、海南岛以及越南北部的戏河流域,即今广西西部、西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及越南北部地区;今广西南部是西瓯与骆越交错分布之地。目前这一观点已为多数学者所认同。
(二)骆越文化研究
骆越文化是骆越区别于百越其他分支族群的重要标志,也是骆越族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学资料看,骆越既有与百越共有的文化特征,也有自己的地方或民族文化特色。关于骆越与百越共有的文化特征,无论是老一辈的学者还是后来的中青年学者,有专门的著作或文章论述。如罗香林《百越源流与文化》(1955)、陈国强《论百越民族文化特征》《1999》、蒋炳钊《百越文化研究》(2005)等。一般认为,百越共同的文化特征为:流行凿齿,种植水稻、断发纹身,契臂为盟,喜食海产,习嚼槟榔,居住干栏,行岩洞葬,善使舟楫,擅长铸造青铜器,崇拜蛇、鸟、雷神,行鸡卜等。
广西是骆越主要分布地区,因而,广西学者一直是骆越文化研究的主要力量,成果也比较多;也有区外的学者论及骆越文化。发表的论文主要有:覃彩銮《骆越青铜文化初探》(1986)、《骆越青铜铸造工艺及其装饰艺术初探》(1987年),认为骆越青铜文化是在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因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同,骆越青铜文化具有自己的特点,如崇尚铜鼓,流行铸造和使用扁茎短剑、环首刀、羊角钮钟、靴形钺等;覃圣敏等《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1987)、玉时阶《从花山崖壁画探讨骆越的文化特点》(1987)、梁庭望《花山崖壁画古骆越文明的画卷》(2008)等论著,对骆越人绘制规模宏大、风格独特、内涵丰富的左江流域崖壁画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认为左江流域崖壁画是骆越文化的集中展示,是骆越创造的艺术杰作;罗长山《骆越人创造过自己的文字》 (1992),廖国一《论西瓯、骆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1996),刘美崧《雒越铜鼓与东山文化——驳“越南北部是铜鼓的故乡”说》 (1996),农学冠《论骆越文化孕育的“灰姑娘”故事》(1998),尤建设、周伟《试论秦汉时期儒学在交趾的传播》(2002),袁运福、尤健《论秦汉时期汉文化对交趾的影响》(2003),蓝日眷等《浅谈骆越文化与壮医药文化的关系》(2008),曲用心《论岭南地区先秦铜器的考古发现、分布及其社会影响》 (2009),李斯颖《骆越文化的精粹:试析布洛陀神话叙事的起源》(2011),覃圣敏《特掘、广西商周文化和“骆越古都”》(2006),赵明龙《骆越文化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2011),王昭《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文化原型骆越文化的内涵及现代转型》(2013),覃乃军《试论广西骆越古乐文化的形成与精粹》(2014)等,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或不同学科,对骆越文化进行了多维研究和揭示。
对于骆越文化的深入研究与全面揭示,集中于覃圣敏等《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1987),黄现璠等《壮族通史》(1988),余天炽等《古南越国史》(1988)》,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1997),郭振铎、张笑梅《越南通史》(2002),郑超雄《壮族文明起源研究》(2005),罗世敏主编《大明山的记忆:骆越古国历史文化研究》(2006)等著作中。在这些著作中,对骆越的起源、分布、社会、文化、艺术乃至宗教信仰等,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与揭示,认为骆越文化内涵丰富,既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又吸收了中原文化元素,特别是青铜文化是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1997)、覃彩銮《壮族史》 (2002)中,对骆越文化及其特征作了全面归纳与揭示,即骆越文化是以稻作文化为核心,以左江花山岩画和铜鼓文化为标志,突出地表现在青铜文化,歌谣文化,以拟蛙舞、翔鹭舞以及铜鼓、羊角钮钟、竹笛等乐器为代表的音乐舞蹈文化,织锦文化,干栏文化,语言文化,以那、板、陇等地名为中心的地名文化,以巫麽、鸡卜、雷神、蛙神、水神、蛟龙(图额)、鹭鸟、牛、犬、花神、竹神、生殖崇拜、图腾崇拜以及祖先崇拜为代表的宗教文化,以骆侯、骆将、骆民为标志的制度文化以及生活习俗上流行纹身、岩洞葬和善使舟楫、火耕水耨、饭稻羹鱼等方面。通过学者多年的研究与探索,分布于岭南西部地区的骆越文化得到了较为全面、系统、深入的揭示。
(三)“骆越”族名的含意
关于骆越名称的由来和“骆”的含意问题,学者从语言学(古壮语)、宗教学、民俗学及地理学的视角进行了探讨。如李延凌《“瓯雒国”辨》(1983),秦钦峙《“雒田”、“雒民”、“雒王”析》(1984)、《“雄王”、“雒王”称谓之辩管见》(2009),杨凌《“骆越”释名新议》(1989),谷因《骆越之“骆”义何在》 (1993)、《骆是夏越民族最早的名称》 (1994),覃晓航《“骆越”、“西瓯”语源考》(1994),白耀天《骆越考》(1995),武忠定《“雒越”之“雒”义新考》(2012),王柏中《“雒田”问题研究考索》(2012)等论文;在黄现璠等《壮族通史》(1988)、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1997)、郑超雄《壮族文明起源研究》(2005)、罗世敏主编《大明山的记忆:骆越古国历史文化研究》(2006)等著作中,也都有关于“骆越”名称由来和含意的诠释。学者们根据其语音和骆越居住生活的自然环境,结合文献记载,用壮语进行诠释。目前主要有三种解释:一是认为“骆”音“Lue”,与壮语“鸟”的读音相近,史书中有骆越地区有“鸟田”的记载,而骆越人流行崇拜鸟之俗,在出土的铜鼓上,铸有许多翔鹭、翔鹭衔鱼等图像,应是骆越人鸟崇拜的形象反映,很可能与骆越奉鹭鸟为图腾有关,并且以其崇拜的鸟图腾作为族名。二是认为骆越名称与其居住生活的地理环境有关。因“骆”音与“麓”或“陇”音近,壮语称山麓或山谷为“骆”应是“居住在山麓或者山谷里的人”之意。三是认为壮语称铜鼓为la2,与“骆”字的古代读音很相近,意为“拥有铜鼓的越人”。目前,多数学者赞同前两种说法,后一种说法只是个别学者意见。[2]
(四)骆越社会经济研究
骆越社会经济的发展,是骆越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因此,骆越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是骆越研究者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余天炽等《古南越国史》(1988),黄现璠等《壮族通史》(1988),张声震《壮族通史》(1997),覃彩銮《壮族史》(2002),郭振铎、张笑梅《越南通史》(2002),郑超雄《壮族文明起源研究》 (2005),罗世敏主编《大明山的记忆:骆越古国历史文化研究》(2006),林蔚文《中国百越民族经济史》(2007),陈国保《两汉交趾部研究:以交趾三郡为中心》 (2012)等著作中,对骆越族的经济生活方式、稻作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及其原因等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与揭示。学者们还从不同维度,对骆越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特点进行研究与探讨,如玉时阶、徐继连《秦汉时期的骆越经济》(1990),黄汝训《秦汉时期骆越社会经济概况试述》(1990),吕名中《秦汉时期的岭南经济》(1990),杨盛让《秦汉时期岭南社会经济发展述略》 (1998),陈国保《汉代交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之探析》 (2005)、《周秦时期交趾与蜀、滇区域间的密切交往及其与中原联系的发展》(2006),程有为《先秦至秦汉时期中原与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2010),李新平《马援平定交趾及对交趾的贡献》(2010)等,通过相关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对商周到秦汉时期骆越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了分析研究,认为秦始皇统一岭南、特别是汉武帝对岭南骆越地的统治与开发,包括中原移民的南迁、汉王朝派驻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郡官吏重视发展农业、手工业,推广包括牛耕、犁耕等先进的生产技术,输入先进的铁制生产工具、培育优良稻谷品种、人工施肥、修渠引水灌溉等生产技术,促进了骆越地区经济的发展。
(五)骆越宗教信仰研究
骆越宗教信仰,是骆越宗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内核,也是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自20 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不断有学者进行研究,其成果集中体现在覃圣敏等《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 (1987),黄现璠等《壮族通史》 (1988),廖明君《壮族生殖崇拜文化》(1994)、《壮族自然崇拜文化》(2002),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1997),郑超雄《壮族文明起源研究》(2005),罗世敏《大明山的记忆:骆越古国历史文化研究》 (2006)等著作中。这些著作都设有专门章节,较为详细地论述了骆越源远流长的宗教信仰形式、内涵、特征等,认为骆越的宗教信仰是由前期原始先民的原始宗教发展而来,流行巫教和鸡骨卜,流行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始祖崇拜等,其中的雷神、水神、花神、太阳神、竹、蛙、牛、犬、鹭鸟、鳄、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和铜鼓崇拜,是骆越宗教信仰的重要内涵和鲜明特征,而雷神、水神、蛙神和铜鼓崇拜,又与骆越族的稻作生产对雨水的依赖或需求有着密切关系。学者们还从不同视角,对骆越宗教信仰进行研究探讨,如谈琪《骆越人原始宗教祭祀的历史画卷:论广西左江崖壁画的族属、年代和内容》(1988)、于欣《骆越巫风的遗韵——试析女巫舞》(1988)、郑超雄《武鸣先秦墓葬反映的骆越宗教意识》(1994)、海力波《左江崖壁画与骆越人之生殖崇拜》(1995)、覃义生《战国秦汉时期骆越宗教性青铜器探索微》(1999)、黄世杰《大明山下元龙坡的铜卣是西瓯骆越瘗埋——礼拜山岳留下的东西》(2008)等。
(六)骆越与周边及现代诸民族的关系
随着骆越历史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领域逐步拓展到骆越与周边乃至后来诸民族关系的研究,包括骆越与中原华夏民族的关系,骆越与西瓯的关系、骆越与印支半岛及其后裔(壮、侗、临高、京及东南亚侗台语民族)关系的研究。有学者认为,越族源于华夏民族,是华夏民族与越族融合的结果,属华夏系统,如罗香林《越族源出于夏民族考》(1943)、周宗贤《越族与华夏族及其他民族的关系》(1986)等便持此观点。还有学者认为,骆越是华越民族的最早名称,如谷因认为:“夏越同源,即都源于更早的路人;而越族则是南下的夏人与其同族系的路人融合的族群。骆是越族的别称和最早名称,也是夏族的最早名称。”[3]但更多的学者则认为,骆越是壮侗语诸民族(包括东南亚地区的越南岱、傣、侬,老挝老龙族、缅甸掸族、泰国泰族等侗台语族)的祖先,这些民族是由骆越发展演变形成的。如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1939)中说:“至迟在周朝初年,僮人已布满两粤流域。所谓百越,所谓骆越,所谓路人(其实路人、骆人就是獠人的同音异写),所谓俚僚,所谓乌浒,所谓土人,皆僮类。”[4]80罗香林《海南黎族源出越族考》 (1939)及詹慈《试论海南岛临高人与骆越的关系》(1982)认为,海南黎族由古代骆越发展演变形成,汉武帝平定南越国以后,部分骆越人越过琼州海峡,来到海南岛,经过不断繁衍发展,演变成黎族。海南临高人与壮族同源,也是由古代骆越发展演变形成的。张一民、何英德《西瓯骆越与壮族的关系》(1987),徐杰舜《从骆到壮——壮族起源和形成试探》(1990),王文光《越南岱依、侬族源流考》(1992),张民《试议侗族为土著骆越说》(1993),田晓雯《交趾探源》(1994),梁敏《论西瓯骆越的地理位置及壮族的形成》 (1996),徐杰舜、韦小鹏《岭南民族源流研究述评》(2008),徐芳亚《秦汉时期中原人士移居越南析论》(2010),覃圣敏《中国和印支半岛的瓯骆越人及其后裔》(2005)、《中国南部和中南半岛的瓯骆越人及其后裔》(2006),王文光 李晓斌《百越民族发展演变史——从越、僚到壮侗语族各民族》(2007),王文光、姜丹《从同源走向异流的越南百越系民族》 (2008)等,以及黄现璠等《壮族通史》 (1988),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1997),郭振铎、张笑梅《越南通史》(2002)等专著中,对骆越的发展、演变及其与中国壮侗语诸民族以及东南亚侗台语民族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研究与阐述。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和东南亚壮侗语诸民族起源于骆越族。东汉后期至南朝时期,骆越族称演变为乌浒、俚、僚人;秦汉至南朝时期,骆越及其后裔部分乌浒或俚人逐步向西迁移,经过滇西进入今老挝、缅甸、泰国北部地区;南朝至唐代时期,黎、傣、侗等先民逐渐从俚僚族分化出来,分别进入今海南岛、滇西西双版纳和广西北部地区,形成单一民族共同体;宋代至元明时期,形成僮、布依、水、仫佬、毛南等民族。骆越及乌浒、俚、僚在发展、演变和重组成壮族的过程中,吸收和融合了从中原迁居广西的一些汉族。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骆越是今越南京族的祖先,如秦钦峙在《中南半岛民族》(1990》一书中认为:“古代百越民族中的瓯越、骆越是今天京族的祖先。”[5]242其他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吴凤斌《百越族与京族的关系——京族族源初探》 (1982)、潘雄《骆越非我国南方诸族先民考》 (1984)、王文光《越南京族、芒族的由来与发展之我见》(1994)等论著。覃圣敏主编《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2005),是中泰学者历时12年,汇集了中国和泰国数十位专家学者,对骆越后裔——壮泰民族关系研究的重要研究成果。中泰学者认为,壮泰民族共同起源于古代骆越。后来,有一支骆越人向西迁移,经过云南西双版纳,进入老挝、缅甸,最后进入泰国北部,逐步发展成现代的泰族。
(七)骆越社会及其性质问题
骆越社会发展及其性质的研究,是近年来骆越问题研究的拓展、深化,并取得了重要新成果。如郑超雄《壮族文明起源研究》 (2005),通过对史料记载的梳理与考证,结合考古发现的资料,对骆越社会的发展及其性质进行研究,认为商周时期,骆越地区形成了诸多部落或部落联盟,进入了古国社会发展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发展进入方国时期,骆越各地形成诸多方国,出现骆王、骆侯、骆将、骆民等阶层。今大明山西麓下的武鸣县马头乡元龙坡、安等秧发现有数量众多的周至战国时期的墓地,出土有许多青铜器及铸造青铜器的石范。在左江及其支流明江两岸发现有82 处战国至东汉时期的岩画,从上游的龙州、江州、宁明、大新至下游的扶绥县,绵延了200 多公里。因而,今武鸣县马头及左江一带应是骆越方国的中心。罗世敏主编《大明山的记忆:骆越古国历史文化研究》(2006)、梁庭望《古骆越方国考证》 (2014),对骆越古国的相关问题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认为今大明山西麓下的武鸣县马头一带应是骆越国的中心。2013年,中央民族大学梁庭望教授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古骆越方国考”,对骆越源流史、古国范围、社会面貌、经济发展、文化成就等作了全面、深入研究与揭示,认为骆越国的范围东至今广西中部的红水河流域,南至今广东雷州半岛以至海南岛,西至云南东南部的广南、富宁一带,西南至越南北部以至南海诸岛。
(八)中国学者对越南境内骆越文化的研究
关于中国学者对今越南交趾及骆越文化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及其成果。今越南北部是古代骆越分布地,秦始皇统一岭南后,设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郡下设县,委派官吏,实行封建统治,包括骆越分布地在内的岭南地区纳入秦王朝统一版图。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割据政权后,重新统一岭南,将秦朝设置的三郡析为九郡,包括骆越分布地在内的岭南地区划入汉王朝统一版图。在秦汉王朝的统一开发和中原文化的影响下,骆越社会经济文化、特别是青铜文化有了长足发展,其中以东山文化和铜鼓文化最具代表性,因而许多中国学者对之进行了研究与揭示。1943年,陈修和《越南古史及其民族文化之研究》,对越南骆越时期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了研究与论述。尤建设、周伟《试论秦汉时期儒学在交趾的传播》 (2002),袁运福、尤健《论秦汉时期汉文化对交趾的影响》(2003),陈国保相继发表或出版《周秦时期交趾与蜀、滇区域间的密切交往及其与中原联系的发展》(2006)、《恩抚与制约:汉初的南部边疆政策》 (2007)、《汉代交趾地区的内地移民考》(2007)、《两汉交州刺史部研究——以交趾三郡为中心》(2010)等论著,对骆越居住的交趾地区与中原、蜀、滇地区的关系,汉王朝的统治政策,开发措施及交趾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吴春明《红河下游史前史与骆越文化的发展》(2008)一文,通过考古学资料,对红河下游地区史前社会发展历史和骆越文化的发展及其特点作了简要论述。谢崇安《滇桂地区与越南北部上古青铜文化及其族群研究》 (2010),李昆声、陈果《中国云南与越南的青铜文明》(2012)两部专著,通过桂、滇、越三地出土青铜器的种类、器型和纹饰特征作了全面梳理和比较研究,揭示了三地青铜文化的发展及密切关系,认为三地青铜文化属于同一文化类型,其产生与发展,受到中原青铜文化的深刻影响。王超超《越南东山文化及其起源的有关问题概述》(1992)一文,对越南东山遗址的发现、分布、发掘和出土青铜器作了简要介绍,即广义的东山文化分布在越南义静省以北至中越边境这一广大的地域内,而典型的东山遗址位于清化省的马江畔。从1924年到1979年,在朱江、马江和兰江的三角洲地区共发现90 处东山遗址,先后出土遗物2800 余件,其中的青铜器有1500 余件(河内东英县古螺城发现的10000 多件铜镞未计入)。一般认为,东山文化的年代约从公元前5 世纪到公元前1 世纪。就越南来说,东山文化代表了广布于越南北方青铜文化和早期铁器文化的中心,并且成为青铜文化发展的顶点。同时归纳了学术界对越南东山文化起源问题看法:(1)东山文化源于中国或深受中国影响说;(2)东山文化源于西方说;(3)东山文化土著说;(4)东山文化源于本地但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说。[6]陈果、胡习珍《简论越南的东山文化》(2012)一文,对越南东山遗址的发现、分布和东山文化类型诸遗址的发掘、出土遗物、文化内涵、特征、年代乃至研究状况等作了全面介绍与论述。黄丽英《越南青铜文化研究初探》(2013)一文,通过对越南发现青铜器资料的收集,分别对越南青铜文化艺术的起源、青铜器的类别、铸造技术、文化艺术之内容、纹饰纹样艺术特征、中越民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青铜器纹饰中蕴藏的社会生活和民俗意象等进行研究与论述,认为越南铜器既有鲜明的特色,也表现出与其他外来文化之间的渗透与交融。
(九)中国学者对越南学界关于骆越历史研究的不实之论的批驳与辨正
自20 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针对越南学者在骆越历史文化研究中,将神话传说当作信史,对中国古籍记载采取断章取义、歪曲编造、以今论古的手法,把五千年前还处在原始部落时代的骆越就建立了所谓“文郎国”和“雄王”。事实上,20 世纪70年代以前,越南国内以及中国、法国、日本的学者对于所谓的“文郎国-雄王”问题,一直存在不同看法。但从70年代以后,越南当局为了适应其反华政策与地区霸权主义政策的需要,组织一批学者重新编纂《越南历史》(第一集)、《雄王时代》等书,极力宣扬公元前3 世纪后半叶至公元前2 世纪初,存在过一个强大的“瓯雒国”,其疆域北起中国广西的左江南岸,南至今越南中部,地域相当辽阔,经济、文化亦相当发达,是一完整独立的国家实体[7];同时还不遗余力地宣扬秦始皇统一岭南,建立桂林、南海、象郡(一部分在今越南北部),就是秦朝对“瓯雒国”的“侵略”,这也是北方在历史上对越南的“第一次大规模”“有系统”的入侵[7]49;声称“雄王时期,我国开始建国,从那个时候起,就要抵御外族封建国家或强悍部落对我国的侵略和吞并”;并且在教科书中大肆渲染“来自北方(中国)的侵略”等等。中国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基本观点,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对一些越南学者的荒谬之说进行批驳或辨正,如黄铮《论马援征交趾》(1980)、《越南李朝的对外侵略和扩张》(1981),范宏贵《关于越南民族起源问题的论争》(1982),李延凌《“瓯雒国”辨》(1983),陈玉龙《略论中越历史关系的几个问题》(1983),杨立冰《评越南史学界对越南古代史的“研究”》(1983)、《评越南史学界歪曲中越关系史的几个谬论》(1985)、《雒越铜鼓与东山文化——驳“越南北部是铜鼓的故乡”说》(1996)等。而郭振铎、张笑梅《越南通史》(2002),对越南古代历史作了客观的论述,同时对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的《越南历史》(1971)中关于骆越历史及所谓的“文郎国”“瓯雒国”的种种谬误一一作了批驳或辨正。叶少飞、田志勇《越南古史起源略论》(2013),对越南古代骆越历史作了梳理,对越南学者关于越南古代史、特别是骆越的起源、传说中“文郎国-雄王”“瓯雒国-安阳王”以及“骆越是越南民族的直接祖先”等观点进行了批驳或辨正。
总之,多年来,中国学者对骆越相关问题作了多视角、多维度的深入研究与揭示,内容涉及骆越名称、源流、分布、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等方面,在骆越起源、分布、文化及其与壮侗语诸民族的历史渊源关系、与百越各支系以及中原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取得了共识。但也存在诸多不足,留下了许多尚待深入研究的空间。
(待续)
[1]蒋炳钊.百年回眸——20 世纪百越民族史研究概述[C]//百越文化研究——中国百越民族史学会第十二次年会暨百越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2]覃晓航.“骆越”、“西瓯”语源考[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6).
[3]谷因.骆是夏越民族最早的名称[J].贵州民族研究,1994(3).
[4]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M].上海:中华书局,1939.
[5]秦钦峙.中南半岛民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6]王超超.越南东山文化及其起源的有关问题概述[J].东南亚,1992(2).
[7]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越南历史[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