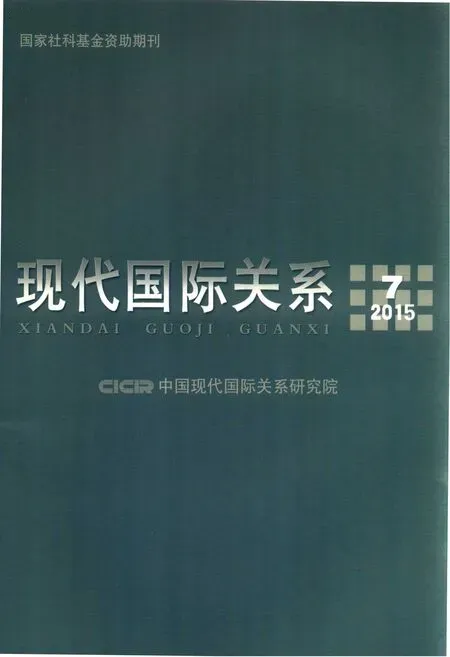“21世纪的美国病”——美国的“现代国家治理难题”初析
王鸿刚
美国到底行不行?这是近年来中国战略界极为关注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中国对国际局势的长远判断以及中国对外战略的整体设计。但由于这一问题牵涉甚广,要得出科学全面的结论并不容易,需要中国研究者集体努力,从不同角度深入探寻。当前,一些研究者从经济、军事、科技、能源等多个领域入手,对美国的实力地位及发展走势做出分析评估。本文作为这种集体努力的一部分,尝试从国家治理方略的发展演变及其合理性这一角度,更加历史、全面和辩证地剖析当前美国内部各类难题的深层原因及相互联系,并对美国的未来前景做出展望。
一
现代国家内部普遍存在着不可进一步化约的三类基本力量:市场、政府和社会。三类力量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构成了现代国家运行的核心机理。现代国家的治理,需维持市场、政府与社会三种基本力量的平衡及三者间的相互依存与制约关系。其中某种力量过强过弱或畸形发展,将导致国家治理体系失衡。如果市场力量过强,将对政府意志形成控制,对社会形成过度剥削,带来社会分化和社会动荡,这反过来会给市场有序运转带来困难。如果社会力量过强,难免对政府要求过高,造成政府表现扭曲,并将压力传导到市场,挤压市场空间。市场长期负担过重会造成其效率下降,政府用以再分配的税收资源反而减少。当然,如果政府管得过多,对市场和社会形成控制,将造成国家整体缺乏活力、政府自身负担过重及合法性不足的情况。上述三种力量失衡的状况,都是不可持续的国家治理模式。总体看,政府虽非全能至善,但市场的盲目性和社会的依赖性更加突出,政府作为三者之中最为理性和能动的力量,承担着调节三者关系模式,使现代国家体系持续运转的任务。政府对三者关系的调控,即构成现代国家的治理方略。
美国作为不断演进的现代国家,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国家治理体系的失衡,美国均通过治理方略的变革予以纠正,但每次纠正都为下次失衡埋下伏笔。美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第一次失衡发生在20世纪初,其原因在于建国后一直奉行的国家治理方略至此已难以适应现实。从独立建国到20世纪初百余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奉行亲市场而轻社会的治理方略,全力为市场扩张和财富积累提供环境和制度支持。一方面,以积极作为的方式,应对南部各州分离倾向,通过购买、兼并、武装夺取等方式开疆拓土,同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吸引外来移民,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更好条件。另一方面,以消极作为方式,约束政府管理权限,维系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为资本积累和工业革命营造有利环境。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指出,联邦政府治理方略的核心,是增加政府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纽带,推动联邦政府与全国有产者形成联盟。①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通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6页。19世纪20年代杰克逊政府时期确立的“分赃制”原则,更便利了日益崛起的资本家对政府资源的控制和利用。与此相比,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和公民权益的保障则处于较低水平,限于生命权、财产权以及行动自由权等;其范围也限于白人男性和有产者,对妇女、儿童、黑人以及印第安人权益缺乏保护,对工人罢工往往予以镇压。
这种治理方略的历史功绩是使美国在19世纪末成为全球头号经济强国,但也造成市场经济高速发展、政府治理裹足不前和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失衡局面。内战结束后,美国资本主义进入飞速发展的“镀金时代”,全国统一市场进一步确立,生产力极大提高,各主要行业相继进入垄断阶段。而美国联邦政府在组织上依然奉行“分赃制”原则,结构上依然维系国会强而总统弱、地方强而联邦弱的格局,两党治理方略均延续亲市场原则,政府治理能力难以与时俱进。这一时期,随着人口在大型城市日益集中和渐趋稳定,生活和教育水平逐步提高,以及报纸快速普及,社会力量的发展具备了一定条件;但由于缺乏政府的体制性支持,其发展进程大大滞后。这种国家治理体系的失衡,带来政府体制性腐败、大范围经济危机和大规模社会动荡的严重后果。这段所谓“镀金时代”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时期。②周琪:“美国的政治腐败与反腐败”,《美国研究》,2004年,第3期,第45~68页。经济上,1893年爆发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继而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社会层面,则出现贫富高度分化、城乡差异突出、劳资矛盾激化、新老移民对立、生产环境恶劣以及生态环境污染等诸多社会问题,大规模抗议和罢工此起彼伏。③马俊:“经济、社会变迁与国家治理转型:美国进步时代改革”,《公共管理研究》(第六卷),2008年2月,第3~43页。
危机成为变化的催化剂,促成美国政府对国家治理方略的第一次变革,主要体现在干预市场、扶持社会和政府自身改革三方面。在干预市场方面,针对钢铁、石油、铁路运输等垄断行业,制定《州际商务法令》(1887年)和《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890年)等反垄断立法,重启和保护市场竞争;制定《联邦储备法》(1913年),设立联邦储备银行体系,扩大联邦政府的货币管理权。在扶持社会方面,制定《最低工资保障法》(1912年),在保护妇女和童工权益、限制最高工时等方面做出规定;转变对劳资纠纷的态度,1913年成立劳工部,对工人权益予以更多保护;推动地方、州、联邦等各层次选举制度改革,消除种族、性别及财产等因素对选举权的限制,确保政府对选民更加负责。在政府自身改革方面,着力推进预算和人事制度改革,通过制定《1913年预算与会计改革法》,约束财政纪律,提升预算效率,增强总统与国会博弈的能力及对行政部门的控制;依据《1883年彭德尔顿文官法》确立现代文官制度,以“功绩制”取代“分赃制”,扩大文官规模,确保文官中立,消除党魁对政府的控制。其后,以应对“大萧条”为契机推出“新政”改革,几年里先后颁布700多道法令,涉及整饬金融、干预工农业生产、实施税收调节、兴办公共工程、强化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并以1935年的《银行法》、《税收法》和《社会保障法》等系列重大立法,将全面干预市场、积极扶持社会的治理方略变革固定下来,进一步加速政府职能扩张和社会力量成长,力争理顺市场、政府与社会三者关系,重建国家治理体系的平衡。
此次治理方略变革使美国成功摆脱“大萧条”,进一步发展成为全球超级大国。但此次变革也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第二次失衡埋下伏笔。此次变革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开始逐步向综合化、混合联合和跨国化方向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市场繁荣越来越依赖政府开支刺激。一旦政府压缩自身需求,就将明显增大衰退风险。①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通史》(第6卷),第134页。与此同时,美国社会也深刻变化。随着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并日益向大城市集中定居,以及广播电视等更先进媒体的普及,美国社会日趋成熟,表达诉求和争取权益的愿望与能力进一步增长,黑人、妇女、少数族裔对政府的要求快速上升。在这种形势下,美国联邦政府不得不将全面干预市场、积极扶持社会的新政治理方略推向深入,以维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此,杜鲁门政府提出“公平施政”口号,推出扩大社会保障、推进民权立法、提高最低工资、建造廉价住房、增加教育援助、保护自然资源、强制健康保险等多方面措施。艾森豪威尔总统推动联邦出资承担特大型工程建设,支持农产品价格计划,授权联邦政府出口多余农产品,向儿童和贫困家庭提供免费食物,扩大失业保险范围,提高最低工资,并在联邦政府内新组建“卫生、教育和福利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进一步深化新政方略:推动国会制定《1964年减税法》,继续扩大赤字财政并使之长期化,同时辅以双重利率的廉价货币政策以及工资与物价管制政策,大大强化市场干预;提出“向贫困宣战”口号和建立“伟大社会”构想,制定《经济机会法案》,扩大和优化福利制度,加大教育和职业培训力度;制定《1964年民权法》,禁止实行种族隔离,保护黑人就业及选举权;推动制定“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禁止性别歧视,确认女性堕胎权。②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通史》(第6卷),第83~84、207、239、337 页。
但是,联邦政府对市场和社会越管越宽,却使形势日益走向反面,造成经济“滞涨”、社会厌倦以及联邦政府能力透支与信誉下降,国家治理体系再度陷入不可持续的失衡状态。经济层面,20世纪60年代后,常规性的赤字财政政策和膨胀性的货币政策带来严重通胀;垄断程度加深、生产成本上升、私人资本投资热情下降等原因造成经济增长放缓,逐步形成长期“滞涨”,经济危机日益频繁。社会层面,福利制度无法本质上改变财富分配关系、改善弱势群体处境,引发下层民众普遍失望;而占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群体则对与福利制度伴生的“高税收”、“高物价”及经济长期不振、生活水平下降越发不满,迁怒于“大政府”和“赤字开支”,甚至否定新政以来的国家治理方略。政府自身运转也出现问题。卡特总统任职时,福利支出已超军费,成为国家财政沉重负担,联邦机构因福利制度的繁复出现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现象。
这种状况推动美国政府对国家治理方略做出第二次变革。此次变革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酝酿,20世纪80年代里根时期全面展开,其基本思路一直延续至21世纪。1969年上任的尼克松政府启动以简政放权为特点的政府改革,提出“修理政府机器”、“还权于州”和“还权于民”,约束联邦权限和规模,试图以此提升政府效率;大力推动福利改革,变“福利”为“工利”,简化福利发放程序,统一各州福利标准。③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通史》(第6卷),第370~371页。尼克松辞职后,福特政府延续这种努力,并尝试削减联邦预算。卡特政府继续推动压缩规模、提升效率、减少管制的政府改革,并尝试压缩福利开支,提高社会保险税率,压低最低工资,限制劳工权益。里根政府上台后,全面改变新政式的国家治理方略,借鉴供应学派和货币学派等保守经济学主张,大刀阔斧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推出减少管制、简化税制、降低税率、平衡开支、严控货币供应等一系列措施,缩减社会福利支出并优化福利制度,全面开启第二次治理方略变革。④陈宝森著:《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47页。老布什政府对里根路线萧规曹随。克林顿政府虽为民主党政府,但仍致力于解放市场活力、改革税收制度、提升政府绩效、改进福利制度,在市场管制特别是金融管制方面遵循自由化路线。小布什政府上任后将美国治理方略重新拉回共和党传统路线,尤其是在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之际仍奉行减税政策。⑤李琮著:《当代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与世界巨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11~119页。
二
就积极效果而言,第二次治理方略变革显著激发了市场活力,使美国摆脱了“滞涨”,极大增强了美国在这一时期的经济竞争力。里根时期美国经济取得连续6年低通胀增长,不仅使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同苏联的战略竞争中更加自信,而且为90年代克林顿政府时期经济的长时段繁荣打下基础,是美国确立全球霸权的重要保证。21世纪初小布什政府有能力同时发动两场战争,也同此前积累的“家底”有关。但是,正如同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治理方略变革为第二次治理体系失衡埋下伏笔一样,此次治理方略变革也带来严重负面效应,造成市场过度金融化、社会严重分化和政府功能失灵,形成当前美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第三次严重失衡。
其一,政府大幅放宽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使金融部门和金融活动极大膨胀,美国经济产生高度金融化甚至过度金融化的新特征,造成美国企业长期竞争力下降和美国经济日趋空心化,为大规模金融危机埋下祸根。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力推金融体制改革,其初衷是释放活力、规范管理,建立既安全又有活力的现代金融体制,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强化美国金融业的全球竞争力。为此,美国颁布1994年《银行跨州经营和设立分支的效率法》、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等一系列法案,废止自20世纪30年代一直实行的旨在严格限制银行经营范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逐步放开对银行活动的地域和行业限制,为跨州经营和混业经营打开绿灯。此举一方面大大加快了金融业内部的兼并集中,使少数垄断性金融公司对金融市场形成有力控制;另一方面也使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快速上升,成为美国经济中的主导性行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产业利润比其他部门平均高30%,吸引大量资本涌入,1995~2005年美国金融资产与GDP之比从303%上升至405%;1929年美国银行信贷本息占 GDP的9%,2008年升至70%。①刘诗白:“论过度金融化与美国的金融危机”,《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4期,第20~27页。在此过程中,国民经济的其他行业对金融活动的依赖也极大加深。美国经济与美国企业(无论金融性还是非金融性)的利润和资本积累,越来越并已主要来自金融渠道而非商品制造和贸易。②Greta R.Krippner,“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Socio-Economic Review,Vol.3,No.2,2005,pp.173-208.特别是非金融企业也出现明显的资本化趋势,其金融资产与非金融资产比例持续上升,从1980年的38.5%迅速升至1990年的57.85%和2000年的98.63%,2009年该比率甚至升至103.84%的历史最高点。③马锦生:“美国资本积累金融化实现机制及发展趋势”,《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年10月,第5卷第4期,第61~84页。一些人认为,这标志着美国经济正进入所谓“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④John B.Foster and Robert W.McChesney,“Monopoly-Finance Capital and the Paradox of Accumulation”,Monthly Review,Vol.61,No.5,Oct.2009,https://monthlyreview.org/2009/10/01/monopoly-finance-capital-and-the-paradox-of-accumulation/.(上网时间:2015年6月27日)高度金融化甚至过度金融化的直接后果,是金融的功能发生异化,金融体系的主要功能不再是为生产性投资融资,而是蜕变为金融机构自身的投机融资。这种新的金融资本脱离了与制造业等实体部门的关系,却与房地产等产业建立起共生关系,形成所谓“金融、保险、房地产部门”(FIRE),呈现出“投机性”和“掠食性”特征。⑤[美]迈克尔·赫德森:“从马克思到高盛:虚拟资本的幻想和产业的金融化(下)”,《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0期,第39~48、90 页;Greta R.Krippner,“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Socio-Economic Review,Vol.3,No.2,2005,pp.173-208.它不仅不能增加工业生产和社会福利,反而加剧了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化,增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最终酿成2008年金融危机。同时,在“金融化”大势下,非金融性企业的运营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与金融企业相比,非金融企业曾经长期奉行的专注于生产研发、设备购置和人员培训的传统盈利模式,投入成本更大、回报周期更长但利润率却相对有限,因而相当一部分美国企业对这一传统盈利模式的热情明显下降,转而更加关注企业在股票市场的短期表现,热衷于以此获得高额短期回报。非金融企业的这种致力于“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短期主义”倾向导致其对实体经济投入不足,对长远发展缺乏关注,不仅削弱了企业的长期竞争力,而且从整体上加剧了美国经济的“空心化”趋势。⑥Lawrence H.Summers and Ed Balls,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Inclusive Prosperity,Jan.2015,pp.35-37,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https://cdn.americanprogress.org/wp-content/uploads/2015/01/IPC-PDF-full.pdf.(上网时间:2015年6月27日)
其二,由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变化及政府政策转变等原因,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日趋严重,中产阶级逐步萎缩,阶层流动明显减慢,已威胁到美国社会的活力和稳定性。经济的“金融化”引发家庭财富结构变化,由于富人更有能力通过投资增加收入,美国各阶层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且,由于资本不必寻求同社会劳动相结合便可实现增值,长期存在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契约关系”遭到腐蚀,经济的表面增长并不能如以往那样带来更多就业岗位。①Greta R.Krippner,“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Socio-Economic Review,Vol.3,No.2,2005,pp.173-208.为追求股市表现而进行的公司频繁重组更加剧了失业压力。②George Friedman,“The Crisis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American Power”,Geopolitical Weekly,December 31,2013,https://www.stratfor.com/weekly/crisis-middle-class-and-american-power.(上网时间:2015年6月27日)受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竞争等因素影响,可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的传统制造业日益萎缩,1977年其所创造的收入占全国工资总额的22%,2010年前后已降至9%。③Samuel Rines,“Why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Is Dying”,Jan.2,2014,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why-the-american-middle-class-dying-9657.(上网时间:2015年6月27日)加之历届政府均奉行旨在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的减税政策以及旨在减轻政府负担的福利改革措施,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一直呈上升态势。美国的基尼系数在1968年达到历史最低的0.348,此后一路攀升,2006年达到0.444。④Edward N.Wolf,f“Rising Profitability and the Middle Class Squeeze”,Science and Society,Vol.74,No.3,July 2010,pp.429-449.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的收入占全国人口总收入的比例,从1978年的9.0%升至2000年的21.5%,2007年更进一步升至23.5%,已接近1928年23.9%的百年历史最高点。⑤The Office of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Annual Report of the White House Task Force on the Middle Class,Feb.2010,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microsites/100226-annual-report-middle-class.pdf.(上网时间:2015年6月27日)相比之下,处于社会下层的50%人口的收入状况持续恶化,2005年该群体收入只占全国人口总收入的13.4%。⑥李琮著:《当代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与世界巨变》,第119页。与此相应的,则是美国中产阶级群体的萎缩和生活质量的下降。1971年,61%的美国成年人生活在中等收入家庭。到2011年,中等收入家庭的比例已降至51%,而较低和较高收入家庭比例明显上升。上等收入家庭在全国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29%升至46%;中等收入家庭在收入中的比例则从62%降至45%。⑦Samuel Rines,“Why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Is Dying”,Jan.2,2014,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why-the-american-middle-class-dying-9657.(上网时间:2015年6月27日)而且,尽管过去30多年里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总收入有所增长(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且主要源于更长工作时间),但与此相比,在其消费结构中占有很大比例的住房、医疗和教育费用的上涨速度更快。这意味着,即便仍留在中产阶级队伍中,要维持既有生活方式的难度也比以往更大。⑧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Administration,Middle Class in America,Jan.2010,http://2010-2014.commerce.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migrated/Middle%20Class%20Report.pdf.(上网时间:2015年6月27日)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级萎缩的重要后果,是出现更加明显的阶层分化甚至阶层固化。1970~2009年间,生活在中等收入小区的家庭比例从65%降至42%,而生活在富人区和穷人区的家庭比例却增加一倍多。“上层阶级日益在经济、文化和地理上与其他同胞分开”,“富裕的美国人开始撤走他们对公共空间和机构的资金支持,而把这些钱专用于改善他们的私人服务”。⑨William A.Galston,“The Eroding American Middle Class”,The Wall Street Journal,Nov.12,2013,http://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3914304579193663817816486.(上网时间:2015年6月27日)美国的社会流动性随之减缓,贫穷的代际遗传已经出现,“在收入分配底层的1/5出生并长大的美国人有42%在成年后仍然原地不动”,美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速度已明显低于其他发达国家。[10]Niall Ferguson,“Niall Ferguson o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Dream”,Newsweek,June 26,2013,http://www.newsweek.com/2013/06/26/niall-ferguson-end-american-dream-237614.html.(上网时间:2015年6月27日)由此带来的,必然是美国社会不满情绪的积累、社会稳定性的下降和长期竞争力的丧失。多年来,美国就一直存在偏高的暴力犯罪率;近年来诸如“占领华尔街”等社会运动更凸显了美国中下层民众的愤怒;特别是当前再度激化的种族矛盾,背后更是与贫富分化有密切关系。
其三,由于政府主动放权,其对市场活动的调控能力以及对社会的支持能力显著蜕化,从而引发政府的监管危机、债务危机和信任危机,继而出现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担忧。
首先看监管危机。监管危机的根子在政府对市场的过度放权和市场力量对政府的深度渗透。以金融业为例,在政府放权政策扶持下,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的专业性、复杂性越来越高,致使包括美联储在内的联邦机构越来越跟不上金融创新的节奏,难以实施有效监管;那些在监管机构内部能看懂金融模型的专业人员,会很快被华尔街以高薪挖走。①卢菁著:《我在美联储监管银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9页、158~159页。不仅如此,一些监管机构甚至还受到被监管者“挟持”。金融、军工、医药等诸多行业不仅对国会实施强大游说活动,使很多议员完全沦为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且这些行业的精英们还通过“旋转门”进入政府,使被监管者和监管者之间界限模糊,产生不健康的裙带关系。②Samuel Brittan,“The Fight against Crony Capitalism”,The Financial Times,July 5,2012,http://www.ft.com/cms/s/0/9514c700-c5db-11e1-a3d5-00144feabdc0.html#axzz3eFwq5due;Jon Huntsman,“True Conservatives Despise Crony Capitalism”,The Financial Times,July 18,2012,http://www.ft.com/intl/cms/s/0/40227540-cf58-11e1-a1d2-00144feabdc0.html#axzz3eFwq5due.(上网时间:2015年6月20日)
再看债务危机。尽管20世纪以来政府负债是经常现象,80年代以前历届政府对收支平衡还是比较在意的,总体上政府债务规模不大。但自里根政府开始,由于旨在刺激投资和消费的长期减税政策、旨在扩大总需求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及一直未能有效加以控制的福利开支等原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持续快速扩大,仅在克林顿政府二任后期实现短暂财政盈余。1980年,美国联邦国债总额约为8500亿美元;2007年该数字达到8.7万亿美元。③“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Debt 1950-2015”,http://www.tradingeconomics.com/united-states/government-debt.(上网时间:2015年6月27日)2012年,美国国债超过15万亿美元,与 GDP之比达100%。④Richard Wolf,“U.S.Debt is Now Equal to Economy”,USA Today,Sep.1,2012,http://usatoday30.usatoday.com/news/washington/story/2012-01-08/debt-equals-economy/52460208/1.(上网时间:2015年6月27日)据美国国会预算局预测,2014~2024年美国联邦国债还将增加8.5万亿美元。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The 2014 Long-Term Budget Outlook,July 15,2014,https://www.cbo.gov/sites/default/files/45471-Long-TermBudgetOutlook_7-29.pdf.(上网时间:2015年6月27日)虽然一定程度和一定时期内的政府债务有助于经济增长,对到底多少债务才算健康也无定论,但长期高企的债务不仅会增加政府借贷成本和还债压力,更会损害政府信誉,最终制约政府决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2011年,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将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并将展望前景定为“负面”,美国政府在当代历史上首次失去3A主权信用评级,带来重大经济波动,便是重要的例证和信号。
接着再看政府的信任危机。其主要表现为美国一般民众乃至政治精英对政府表现的不认可。由于经济发展成果未被多数人共享,美国民众对政府怨气日益加重;两党之间以及府会之间在治国理念上争执不下,政府大政方针频频难产,甚至出现“政府关门”,民众对政府的执政能力越发怀疑。民调显示,自1964年民众对政府信任率达到历史最高的77%后,几十年来美国民众对政府信任持续低迷,除1991和2001年等特殊年份外,一直在30%左右徘徊。⑥Pew Research Center,“Public Trust in Government:1958-2014”,November 13,2014,http://www.people-press.org/2014/11/13/public-trust-in-government/.(上网时间:2015年6月20日)特别是,美国政治精英对政府和政治体制的信心也出现下降,近来多有反思和检讨,其中当属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的反思最引人注目。⑦Francis Fukuyama,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From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New York:Farrar,Straus& Giraux,2014.
三
与前两次失衡相比,当前这次美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失衡有根本不同。第一次失衡的典型特征是市场力量强而政府和社会力量均较弱,这意味着政府和社会都有广阔成长空间,二者的成长其实标志着现代国家的发展与成熟。第二次失衡的典型特征是市民社会已经发展起来、政府管理职能超强造成市场活力不足,因而政府有可能通过简政放权实现自我克制,从而解决当时最为迫切的滞涨问题。可以说,美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前两次失衡都算不上“病”,至少算不上“大病”,而更应该被视为现代国家的成长成熟和自我调适。对这两次失衡予以纠正的治理方略变革,尽管难度不小,但思路是清晰的,共识是广泛的,方法是有效的。
当前美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第三次失衡呈现出新的特征。其一,不是“发展中”问题,而是在建成高度发达的现代国家后出现并长期持续的问题。在当下的美国,构成现代国家基本要素的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都已高度发达,是业已充分发育的市场经济、民主政府和市民社会。市场经济已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为全球经济和金融活动提供包括机制和规则在内的诸多公共产品,不可谓不强。民主政府的各项制度极为繁复,自认为是全球学习的楷模,政府活动覆盖到内政外交、生产生活一切方面,也不可谓不强。市民社会也发展到十分健全的程度,无论是权利保障的水平、自我组织的能力还是参政议程的渠道,都非常先进。如果说以前是因为政府、市场或社会的不健全而导致治理体系失衡,那么在当前政府、市场和社会都高度发达的状况下仍出现治理体系失衡,就显得有些不寻常了。
其二,不是局部性问题,而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同时出了问题。市场经济的活动陷入“金融化”、“空心化”陷阱,华尔街沉浸于金融套利难以自拔,金融活动对实体经济支持减弱,造成美国经济长期竞争力下降。繁荣的股市背后,是难以摆脱的长期停滞阴影。社会的稳定性和活力出现问题,福利保障的沉重负担被转移到未来,贫困的代际遗传造成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表面富足的和谐社会之下酝酿着不安的潜流。种族矛盾、社会仇视、独狼袭击等社会事件,似乎预示着更大规模的愤怒风暴。特别是,美国政府也出了问题。政府决策受到利益集团和短期民意挟持,缺乏顶层设计,债务压力极大压缩了政府的施政空间,乏善可陈的表现又损害了其在民众中的信誉。
其三,不是阶段性问题,而是陷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恶性互动的结构性困境。形象地说,在前两次失衡中,市场和社会是“相互需要”的,只是相互磨合未达最优而已;经过政府治理方略变革,二者关系是可以好起来的。而在这次失衡中,市场与社会出现分离倾向,过度“金融化”的市场活动对大量社会劳动力的依赖明显降低。社会对自身经济状况不满,只能求助政府。但政府自身负担已然很重,特别是市场力量对政府的渗透,使其很难做出有效改变,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各方面需要。市场和社会同时对政府施压,但政府腾挪空间十分狭小,导致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僵在那里。
对现代国家而言,这显然是一种极不正常、极不健康的状态,已经构成了“病”。首先,它是一种“慢性病”。这种病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体现得并不明显,甚至还带来了一时繁荣,只是在21世纪初期逐步暴露。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是这种病的全面爆发。其次,它是一种“综合症”。不仅体现在经济失调,因而就算美国各项经济数据转好,也不意味着病已治愈;也不仅体现在政治失调,完全将其归结为政治体制缺陷或政治人物无能,是有失公允的。而且,它也必将是一种“长期病”。由于疾病的形成是经年累月的,因而治疗过程也不会短。如果说“‘世界工厂’地位的丧失”、“殖民帝国的过度扩张”、“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和“传统精神的枷锁束缚”构成了“20世纪的英国病”,①罗志如、厉以宁:《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页。那么,市场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市民社会的日趋分化以及民主政府的功能失灵,则构成了“21世纪的美国病”。同“英国病”一样,“美国病”的出现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英国病”是最早实现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病,而“美国病”则是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病,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均是发达了之后才得的病。因此,与新兴经济体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这类发展难题不同,“美国病”是一种“富贵病”,是高度发达的现代国家独有的病,是典型的“现代国家治理难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病”是无药可救的绝症,也不能忽视美国作为全球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疾病的耐受力,更不能忽视美国政、商、学界再度谋求国家治理方略变革的主观能动性。实际上,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各界都在积极想办法,力争通过政府治理能力的改进和治理方略的变革,重塑市场、社会和政府三种力量各自的内部结构,重建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再平衡。具体而言有两个层面的改革建议。一方面是政策层面的调整,核心是重建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能力和对社会的扶持能力。具体建议有:加强对金融资本监管,严控金融衍生品交易,引导金融资本流向制造业,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①Editorial,“Reforming the Financial System”,The New York Times,Sept.13,2009,http://www.nytimes.com/2009/09/14/opinion/14mon1.html?pagewanted=all;Paul Volcker,“How to Reform Our Financial System”,The New York Times,Jan.30,2010,http://www.nytimes.com/2010/01/31/opinion/31volcker.html.(上网时间:2015年6月15日);[美]比尔·克林顿著,蒋宗强、程亚克译:《重返工作:为什么强劲的经济增长需要开明的政府》,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137~225页。大力改革税收政策,提升对资本活动课税税率,打击企业逃税行为,增加国家税收,缓解债务压力,重建财政平衡;②Bruce Bartlett,The Benefit and Burden:Tax Reform-Why We Need It and What It Will Take,New York:Simon &Schuster,2012,pp.185-191;Glenn Hubbard and Tim Kane,Balance:The Economics of Great Powers from Ancient Rome to Modern America,New York:Simon&Schuster,2013.加大在医疗、教育、住房、交通等方面投入,有效应对贫困问题,加强对弱势群体帮扶,重建中产阶级主流,提升社会消费能力,等等。③Fareed Zakaria,“Upward Mobility:Obama's Plan to Expand pre-K Education is a Step in a Long Catch-up Game”,Time,Mar.4,2013,http://content.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2136877,00.html.(上网时间:2015年6月10日)另一方面是政府自身改革。基本方向是重建两党共识和府会合作,改进政府运行方式,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建立更加负责、高效和聪明的政府,确保朝野齐心、政令畅通。④Nicolas Bergguruen and Nathan Gardels,Intelligent Govern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A Middle Way between West and East,Cambridge:Polity Press,2013,pp.181-184.具体建议有:调整和简化国会议事规则,杜绝“否决政治”,破解政治僵局;⑤Francis Fukuyama,“Oh for a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and not a Vetocracy”,The Financial Times,November 22,2011,http://www.ft.com/intl/cms/s/0/d82776c6-14fd-11e1-a2a6-00144feabdc0.html#axzz3eFwq5due.(上网时间:2015年6月10日)改革选区划分办法和选举捐款制度,限制极端意识形态组织和各类游说团体对议员的不当影响,引导议员向温和、主流和理性路线靠拢,为重建两党共识、强化两党合作打下基础;⑥Anonymous,“No Way to Run a Country:The Land of the Free is Starting to Look Ungovernable.Enough is Enough”,The Economist,Oct.5,2013,http://www.economist.com/news/leaders/21587211-land-free-starting-look-ungovernable-enough-enough-no-way-runcountry;Julian Zelizer,“Is American Democracy Dead?”the CNN website,April 27,2014,http://edition.cnn.com/2014/04/27/opinion/zelizer-american-democracy-dead/(上网时间:2015年6月15日);[美]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著,何正云译:《经济繁荣的代价》,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299~300页。改革行政运作机制,强化行政部门权限,更多运用信息技术,使行政决策更加科学高效,等等。⑦David Brooks,“Strengthen the Presidency”,The New York Times,Dec.13,2013,http://www.nytimes.com/2013/12/13/opinion/brooks-strengthen-the-presidency.html(上网时间:2015年6月10日);John Micklethwait and Adrian Wooldridge,The Fourth Revolution:the Global Race to Reinvent the State,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14,pp.18-23.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推进的一系列改革,也基本上是沿此思路进行的。旨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以及旨在扩大医保覆盖范围、控制政府福利开支的《平价医疗法案》,均为典型举措。此外,为推行“中产阶级经济学”,奥巴马还在新型能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劳工教育培训、移民政策改革等方面倡导和采取多项措施。但当前看,奥巴马改革效果有限。金融改革上,《多德-弗兰克法案》内容极为复杂,被讥讽为“律师和咨询师充分就业法案”,其漏洞很难被一般人发现,却逃不过华尔街金融公司的眼睛。而且这一法案在制定过程中已受到华尔街人士影响,能否达到预期效果令人生疑。⑧Samuel Brittan,“The Fight against Crony Capitalism”,The Financial Times,July 5,2012,http://www.ft.com/cms/s/0/9514c700-c5db-11e1-a3d5-00144feabdc0.html#axzz3eFwq5due.(上网时间:2015年6月10日)更关键的是,金融业似乎还在自我循环,对实体经济支持有限,创造的仍是“无就业复苏”,多数民众对复苏无感,贫富差距仍在继续拉大。另外,由于奥巴马强推医改,府会矛盾和两党矛盾大大激化;医改法案实施过程中的瑕疵,更给那些认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的人留下口实,政府信誉未有多大改进。
奥巴马政府改革不顺,并非奥巴马总统本人能力有限,而是因为医治当前的“美国病”本身就是极为困难的工作。其难点在于:第一,经济由高到低难。金融资本主义是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一种食利性的经济形态。在各国经济日益开放的背景下,其还有极为可观的盈利空间。相比之下,投资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十分有限,怎能期待华尔街改弦更张?因此,“去杠杆化”的金融体制改革和“再工业化”的经济结构调整,一定是非常困难的。第二,社会由奢入俭难。提前消费、透支未来的生活方式不可持续,唯有摆脱福利依赖,提升自身技能,适应全球竞争的新现实,才能真正摆脱贫困,过上更好的生活。这话说来容易,但对于知识技能、思维方式已经定型的一代人而言,难度可想而知。社会竞争力的重建绝非朝夕之功,需要一代人甚至两三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实现。第三,政策由放到收难。三权分立状况下,政府各部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难度很大。尤其当前美国利益诉求高度分化,利益板块高度固化,政府要改变对市场和社会的管理方式,必然触碰既有利益格局,出现对改革的抵制阻挠是在所难免的。第四,政府自我革命难。在现代国家中,市场有盲目性,社会有依赖性,只有政府是理性能动的行为体,国家治理方略变革和治理体系重建的关键是政府。但政府作为官僚机构,有自身难以克服的保守性特征。这种保守性并非某个人的主观倾向,而是官僚机构为维持机构与规则的连续性而造成的副产品。①Peter H.Schuck,Why Government Fails So Often and How It Can Do Better,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pp.307-326.对美国而言,眼下的政府改革已不仅是放权或收权,而是涉及到更复杂的运作模式改革。要克服短期考虑、部门偏好、思维惯性和思维惰性,建立更加聪明的政府,谈何容易。所以,即便奥巴马改革之路是正确的,也仅仅是个开始。美国治理方略的第三次变革和治理体系的重建,注定是一个极为漫长、痛苦且反复的过程。
结语
剖析“美国病”,对我们研判美国的实力地位和发展走势,观察当前国际形势,以及思考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都有重要意义。
首先,“美国病”势必影响到美国的前途命运。对于各界高度关注的“美国到底行不行”这一问题,“美国病”是重要的观察视角。如果说“20世纪的英国病”最终导致英国衰落,那么“21世纪的美国病”同样对美国构成严峻考验。无论美国实力多强,也经不起长期折腾和系统性、方向性错误。就此而言,2016年大选以及下届总统治国方略的选择,是观察美国未来发展走势的风向标。能否沿着正确思路,进一步深化各项政策调整和体制机制变革,重建国家治理体系的平衡,是美国国运盛衰的决定性因素。
同时需注意的是,一个长期生病的美国还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由于美国经济同世界经济深度关联,美国业已过度“金融化”的经济形态必然造成全球金融体系紊乱,不仅对各国财富形成隐蔽盘剥,长期看还会进一步加剧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停滞和贫富分化,增大全球动荡风险。在美国的民主体制下,国内社会生态的畸形很容易影响到对外领域,如何应对民粹色彩日益强化的美国对外政策,正在成为其他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如果美国治理方略变革推进不顺,也不排除美国政府会采取更加内顾性的、零和性的甚至是转嫁危机的政策,难免对全球稳定及其他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构成威胁。日益敏感的中美关系和日益拓展的中国海外利益,都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此外,其他国家也需提防“现代国家治理难题”。前文已述,“美国病”的本质是高度发达的现代国家面临的治理难题。环顾全球,诸如欧洲、日本等发达的现代国家,均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经济空心化、社会分化和政府失灵的难题。在此意义上,“美国病”并非美国独有的病,而是21世纪所有现代国家都可能面临的重大挑战。现代国家的治理,绝非轻松愉快的事,而是极为艰巨复杂的工作,对精英的政治智慧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特别是,快速奔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中国更需注意避免陷入“现代国家治理难题”。虽然中国与美国在发展阶段、政治制度、现实国情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就建设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充满活力和政府高效运作的现代国家而言,两国的目标是一样的。美国在治理现代国家方面的得失成败,是中国的前车之鉴。经济方面,我们应在金融体制改革及转移富余产能、淘汰落后产能过程中真正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规避“金融化”、“空心化”陷阱;社会方面,应高度重视社会在转型阶段与政府、市场关系的历史性转变,既避免社会诉求过分膨胀,也避免社会分化阻碍社会进步;对政府自身,则应在简政放权和有效治理之间搞好平衡,不断提升政府的执政能力,切实确保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