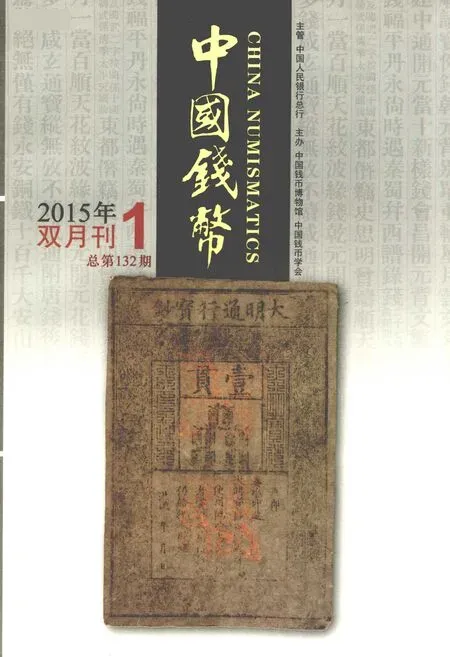试论金代白银的货币化
王 雷 赵少军
白银从商品转化为货币的过程,即白银的货币化,其研究内容意即白银在何时、怎样、为什么成为货币①。目前学术界对白银货币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明代,这与明代最终完成白银的货币化进程有关。而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并非突然出现,而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金代白银的货币化,恰恰是中国白银货币化进程中的重要节点。金代发行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币的形式合法流通的白银货币 “承安宝货”,这在中国隋唐以来的白银货币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与宋代的白银货币化一起,影响了元代以后白银相关的货币政策。尤其是到明代,白银最终彻底完成了货币化进程这个链条上的最后一个环节。正如万明所说,“明代白银的货币化过程,正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趋势发展延续的结果”②。因此,金代白银货币化的探讨,对于究明中国白银货币化进程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试从金代白银的来源、货币化进程及其表现以及意义等方面,结合学界已有的研究,对金代白银的货币化进行进一步探讨。
一 金代白银的来源
在金与两宋并立时期,“铜铁铅锡坑冶者,闽、蜀、湖、广、江、淮、浙路皆有之”③。这些地区都位于南宋境内,而金朝境内相较而言缺乏矿产资源,金朝政府不得不通过多种途径积累白银。一般认为,金代白银的来源主要有四个④:
其一为女真贵族在吞辽、灭宋和废刘豫齐国的过程中,得到大量的白银。
金建立以后,相继在对辽和北宋的战争中获得了大量的金银。在吞辽的战争中,金从辽获得了为数巨大的金银财宝。收国元年六月,金太祖阿骨打占领辽之宁江州时,曾 “括宁江州一路金银帛粟,尽数以往”⑤。金宋联合灭辽后,金军在撤出燕京城之前,“尽括燕山金银钱物,民庶寺院,一扫皆空”⑥。
金朝在攻破北宋都城开封后,清点其库藏 “金三百万锭,银八百万锭”⑦,同时又在民间大肆搜刮百姓,所得无数。据 《南渡录》记载,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一日,“粘罕遣人入城,出榜通衢曰:‘元帅奉北国皇帝圣旨,金者兵马远来,所议事理,业已两国通和,要得金一百二十万两,银一百五十万两’。于是金人执开封府尹何栗,分厢拘括民户金银钗钏环钿等,几悉无遗。如有藏匿不齐出者,动辄杀害”⑧。
另外,在阜昌八年废除伪齐政权时,更是从其国库接收铜钱九千八百七十余万缗、金一百二十万两、银六千万两⑨。
其二为宋向金输出的岁币,成为金朝白银稳定的来源。
金通过与宋订立的合约,获得了以岁币形式支付的稳定货币收益。金宋联合灭辽后,获得了原献于辽的四十万岁币,北宋每年另纳 “燕京代租钱”一百万贯⑩。绍兴八年,金朝与南宋签定 “绍兴和议”,以将陕西、河南地 “赐”给南宋的条件,每年获得 “岁币银帛各二十五万匹两”[11]。隆兴元年,金宋双方签订 “隆兴和议”,约定四事,其中一项为 “岁币银绢之数”[12],“易岁贡为岁币,减十万”[13],每年减少银、绢各五万,计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嘉定元年,金宋双方签订 “嘉定和议”,将岁币增加为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并交纳 “犒军钱”三百万贯文。由于蒙金战争,新的岁币到嘉定四年暂停输纳,当嘉定七年三月金朝使臣到南宋 “来督二年岁币”[14],也被南宋拒绝。从此,由于宋金战争不断,岁币的输纳彻底终止。金接受南宋的岁币银,据统计共计多达1 485万两[15]。
其三为金代的矿业生产,生产了相当数量的白银。
金代白银的矿业生产,主要是增加金境内坑冶的数量和产量。从金代的坑冶来看,实际上是对辽朝采矿业的继承。《辽史》对坑冶有简略记载,“坑冶,则自太祖始并室韦,其地产铜、铁、金、银,其人善作铜、铁器。……太祖征幽、蓟,师还,次山麓,得银、铁矿,命置冶。圣宗太平间,于潢河北阴山及辽河之源,各得金、银矿,兴冶采炼。自此以讫天祚,国家皆赖其利。”[16]金灭辽后,继续扩大坑冶的数量和规模,增加白银的产量。金灭北宋以后,在北宋故地上采矿业的所有权也相应地转为金朝一方,成为金朝坑冶的来源。
正隆二年二月,海陵王就曾 “遣使检视随路金银铜铁冶”[17]。世宗即位以后,在矿产开采问题上,世宗坚持认为,“金银,山泽之利,当以与民”,并遣能吏对坑冶进行经营[18]。世宗先于大定三年 “制金坑银冶许民开采,二十分取一为税”[19],继世宗大定三年放开金坑银冶开采权,仅收取5%的税收之后,大定五年,“听人射买宝山县银冶”。大定十二年冬下诏对百姓开采金银矿予以免税优惠,“诏金、银坑冶听民开采,毋得收税”[20],大定二十年“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21]之后,金银禁榷政策实际上被废止。大定二十七年时还鼓励百姓 “于农隙采银,承纳官课”[22],进一步通过政策刺激白银的生产。
章宗即位后,调整了矿产的开采政策。明昌三年,“以提刑司言,封诸处银冶,禁民采炼”[23]。明昌五年,由于 “聚众私炼”的现象非常严重 “上有禁之之名。而无杜绝之实,故官无利而民多犯法”,故尚书省提出,“如令民射买,则贫民壮者为夫匠,老稚供杂役,各得均齐,而射买之家亦有余利”,“初令民买扑随处金、银、铜冶”[24]。通过买扑[25]的方式,逐步放开各处的金、银、铜矿的开采。这种招募承买的制度,减少了政府的干预,规定 “有冶之地,委谋克县令籍数,召募射买。禁权要、官吏、弓兵、里胥皆不得与。如旧场之例,令州府长官一员提控,提刑司访察而禁治之”,总体而言是比较先进的方式,“比之官役顾工,糜费百端者,有间矣”。由于政府的重视及宽松的政策刺激下,金代的矿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北京、河北、山西境内的银矿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以河北、河东地区势头最为强劲,“坟山、西银山之银窟凡百一十有三”[26]。
其四为宋金之间的贸易,为金代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白银。
金代通过以榷场贸易为主要形式贸易回流钱币,另外还有民间走私贸易活动。金代的榷场是应宋人之请,最先于金熙宗皇统二年五月在金宋交界处设置,先后设置有多处,后置废反复,除泗州等少数榷场始终保持开放外,其他榷场时兴时罢。金代设置金宋榷场对南宋贸易外,还设置有金夏榷场对西夏贸易。金代通过榷场与他国互市,根据金制,“榷货之目有十,曰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27],而实际的贸易中,还包括粮食、丝、绵、绢、药材、羊、马、兵器等。在与南宋的贸易中,金政权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但由于宋金贸易的不平衡,由宋入金的白银要较由金入宋的白银为少,金国在白银方面的处境常居于劣势。为保持白银不外流,同时力争宋银流入,金朝政府采用了减少宋茶及其他商品输入、降低北绢等出口商品价格、严禁榷场互市用银等措施。
南宋商人入榷场进行交易,要以现钱的方式缴纳入榷门票钱、税钱和住宿费用。金代于大定二十年规定了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28],这和宋的商税是一样的[29]。宣宗贞祐三年七月,“议欲听榷场互市用银,而计数税之”,宣宗本人是持否定意见的,他认为,“如此,是公使银入外界也”,平章高琪也持类似看法,认为 “不禁则公私指日罄矣”,而平章尽忠、权参知政事德升则认为,“赏赐之用莫如银绢,而府库不足以给之。互市虽有禁,而私易者自如。若税之,则敛不及民而用可足”[30]。针对截然不同的意见,宣宗提出 “当熟计之”,但从兴定元年集贤谘议官吕鉴提到 “尝监息州榷场,每场获布数千匹,银数百两,兵兴之后皆失之”[31]的记载来看,息州榷场每场获银数百两,可能表明榷场互市用银的政策最终施行,并一度为宣宗朝带来数量不菲的白银。
二 金代白银的货币化进程
早在女真政权建立之前,白银充当价值尺度的职能已被认识。东海女真定宗三年(948)向高丽献马,“王御天德店阅马为三等,评定其价。马一等银柱子一事,锦绢各一匹;二等银钵一事,锦绢各一匹;三等锦绢各一匹”[34]是金建立以前有关白银作为货币的记载。
金代中期以后,白银在经济生活中逐渐成为本位货币,并进入流通领域。承安二年,在交钞阻滞的情况下,金廷将库存的巨额白银投入流通领域,以期能够解决困境,“遂改铸银名 ‘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仍定销铸及接受稽留罪赏格”[35]。学术界普遍认为,作为中国货币史上第一次发行法定流通的银币,是有重要意义的。同时,它也是金代在军费增加、财政困难和交钞阻滞等复杂的情况下由金朝政府出面采取的一种应急措施。张婧认为,“承安宝货”的发行意义不可估计太高[36]。紧随其后私铸 “承安宝货”的盛行,更是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造成 “京师闭肆”的结局,给金代的社会经济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也直接导致了 “承安宝货”在面世短短三年之后即被废止。这是 “劣币驱逐良币”[37]现象在金朝银币流通方面的典型反映。
金代银币进入流通领域时间很短,在金末以前,由于银作为贵金属价值巨大,往往应用于大宗交易,即便在其成为本位货币后,进行在零细交易和支付时,银币也无法取代铜钱的地位,只是在金代末期特定的社会形势下,银的使用成为一种趋势,并承担了货币和计量双重的职能。金朝末年,金朝政府转而以银为基准,过去以铜钱来表示的各类价格,转而用银两来表示[38]。贞祐四年侯挚的上书中提到 “观沧等州斗米银十余两”[39],而三年之前的至宁元年,记述河东、陕西等处大旱时还用 “时斗米有至钱万二千 (文)者”[40]。金代后期,银不但能直接用于交易,还能用于标价。随着战事吃紧,元光二年时,“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41],义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42],银一跃而成为金亡前最重要的货币。天兴二年十月,金在行将灭亡之时,印制 “天兴宝会”,以银为单位,自一钱至四钱四等[43],“同见银流转”,数月后,天兴宝会随金亡而废止[44]。
三 金代白银货币化的表现
金代的白银货币化,是自唐代以来开始,到明代最终完成的白银货币化进程中的一部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白银一直存在于金代民间的交易中,成为衡量价值的尺度。
金建立以前有关白银作为硬通货的记载表明,白银已经以银器的形式在民间行使充当价值尺度的职能。金政权建立以后,金银仍然广泛应用于金代的社会生活中,承担大宗货物的支付货币,这一时期的白银,是以称重的形式来衡量价值的,《金史》载 “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45],在金代的货币体系中,是一种默认的而非官方的货币,在当时铜钱本位的货币体系中充当辅币。期间白银短暂作为法币后 (承安二年至承安五年),白银又回到先前辅币的地位,先后作为铜钱和纸币的辅币,直到金代晚期交钞为本位的货币体系崩溃前后,白银重新以称重的形式活跃在民间的交易中,正大年间,“民间但以银市易”,白银一度成为货币流通市场中唯一被认可的货币。
如我在《物体在水中的沉浮》一课的教学中,物体的沉浮和它们的大小、轻重有关吗?这一问题的提出,我先引用猜一猜的方法,然后让学生在推理的基础上进行实验,最后学生通过亲手实验,将实验的结果与猜测进行比较,激发了学生的学习欲望。
二是金代的白银成为法定意义的货币。
铸行银币,是唐以来白银货币化进程中的一部分。早在唐开元二年 (714),玄宗就提出 “朕欲捐金抵玉,正本澄源。所有服御金银器物,令付有司,令铸为铤,仍别贮掌,以供军国”[46],但唐代的银铤被认为是银料而非货币[47]。宋太宗雍熙四年,曾下诏 “诸州道府军监课利上供银,今后煎作擢角铤送纳,不得更作板石之铤”[48],表明宋初即存在两种银铤的形制。北宋初年开始,白银已经成为市场上广泛流通的商品。王文成认为,至迟北宋真宗朝白银商品化的进程全面完成,初具规模的白银市场正式形成,货币化的物质条件初步具备。宋神宗朝以后,白银与商品的交换,具有了用白银实现商品价格,置换商品价值的意义。宋代的白银,在获得并履行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之际,从商品变成了货币,白银货币化初步实现[49]。
金代铸行银币,正是在受到唐以来白银货币化进程惯性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演变和发展,最终开创性地铸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种白银法币 “承安宝货”。承安二年铸造的 “承安宝货”,虽由银锭转化而来,但是已经不是称重货币,而是规范流通的铸币,并作为大额钱币行用。铸行 “承安宝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币的形式承认白银的合法流通,白银从民间的交易中走上前台,应用的范围也更加地广泛,除了赋税、军费、俸禄之外,还用于商业流通,成为官方正式认可的货币,这一重大意义早已被学术界普遍认可。可以说,以银为本位的货币体系的建立,虽然短暂,却为后世白银的货币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此后,金代再也没有发行银币,即便是在金末交钞为本位的货币体系崩溃前后,民间的交易中也只是将银以称重的方式进行交易,或者由官方发行银的替代纸币。
三是白银为本位的货币体系的建立与白银的纸币化。
这是金代白银货币化继铸行 “承安宝货”之后的又一重要里程碑。金代晚期,实行银钞并行,交钞为本位的货币体系崩溃之后,由于铜钱已经退出流通领域,白银为本位的货币体系的建立成为不二选择。在正大间,白银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主币,“天兴宝会”的印制,更是将白银上升到法定主币的地位。“天兴宝会”是用银的重量作为面值的纸币,与银具有同等的地位,同时也是白银纸币化的标志。金亡前曾经发行了 “天兴宝会”,是第一次以银为单位,以两为面值的纸币,虽然发行短短数月,却对元代中统银货的印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朝政府在印造交钞的同时,“又以文绫织为中统银货。其等有五:曰一两、二两、三两、五两、十两。每一两同白银一两,而银货盖未及行云”[50]。其后又在短时间内发行了流通和银钞,“至大二年,武宗复以物重钞轻,改造至大银钞,自二两至二厘定为一十三等。每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然未及期年,仁宗即位,以倍数太多,轻重失宜,遂有罢银钞之诏”[51],其中的渊源,不言自明。
四是白银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章宗以后白银应用日益广泛,白银被用于支付官兵的赋税、官兵俸禄、军费、官府支出以及与商业贸易和日常生活,与铜钱、交钞并行,成为重要的货币。
在赋役制度层面,除实物和力役外,货币税逐渐加大。金代租税方面的一般规定,即以实物做为主要税收方式。而在其他杂税方面,则见有以货币形式交付的规定。明昌六年二月陕西提刑司曾上言,“本路户民安水磨、油栿,所占步数在私地有税,官田则有租,若更输水利钱银,是重并也,乞除之。”[52]其中即提到水利钱银。在金代以贱金属铜钱为主要货币的形势下,货币支付方式在赋税中所占比例逐渐加大,赋税制度从实物和力役为主逐渐向以货币为主转变,尽管白银尚未完全走上货币流通的前台,但赋税支付方式转变过程中赋税货币化的方向,为白银货币化进程奠定了基础。宣宗贞祐三年时 “议欲听榷场互市用银,而计数税之”以及这一政策的实施进一步表明,在金代榷场税收方面,白银已经作为货币支付手段,并计数上榷场交易税额。
在以白银支付时,不管是官吏俸禄的 “银钞各半”,还是商业贸易中支付一定比例的白银以及支官钱时 “银钞相兼”等等诸多规定,白银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金代实行银钞并行的支付政策,却不拘泥于宋代的钱会中半之制,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在各个时期要求都不尽相同,或四六、或三七、或二八、或三三制,这种支付政策对元及后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元代货币支付中,“元世始终用钞,钱几废矣”[53]。到明朝洪武年间,铸行小钱以后,又实行钱钞并行的支付方式,“复设宝泉局,铸小钱与钞兼行,百文以下止用钱。商税兼收钱钞,钱三钞七”[54],规定的是钱钞三七分的支付方式。可见直到明代,这种银钞并行的支付方式仍然发挥着影响力。
并且,在有金一代,除贞祐年间由于不法商贾在京城买金银获利,导致银价上涨之外,白银保持了基本稳定的价值,得到了金朝百姓的推崇。《大金国志》也记载有宣宗贞祐二年中都被围困时,“京城白金三斤不能易米三升”[55];贞祐四年更是记载了 “观、沧等州斗米银十余两”[56],用白银来表示商品的价格。表明金代后期,银不但能直接用于交易,还能用于标价,之后更是以白银明码标价。如天兴元年 “米一斛,直白金四两”[57]、天兴二年 “时谷价日贵,斗米白金十两”[58]、元光二年 “(茶)袋直银二两”[59]等。相比之下,白银成为金晚期严重通货膨胀阶段最可信赖的表示价格的货币。
此外,在对犯赃罪者量刑时,白银也由于其保值性佳而应用于量刑,犯通宝之赃者以金银价论,使惩罚更加公允。同样,还规定 “赃污故犯者输银”,也是看重其保值性。而通过白银在司法量刑中的应用,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司法的公正。
四 金代白银货币化的意义
金代白银的货币化只是满足金代货币经济需要的选择,更多是作为货币本身行使货币的价值尺度和充当支付手段,还不能像明代白银一样在经济、社会结构乃至于观念上承载深刻的变革。至于金代末年铜钱被强制退出流通领域后,金代白银的货币化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一时期民间对白银货币化进程的倒逼,即民间对交钞的集体抵制和对白银货币的选择使用,逼迫金朝政府默许白银行使货币的职能。在以交钞为本位的货币体系崩溃以后,金朝政府甚至进一步被动地推动白银的货币化进程,发行 “天兴宝会”银钞,尝试建立以银为本位的货币体系。
“自唐代两税法实施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就已出现了经济货币化趋势,但是到宋代王安石变法,征钱仍不免失败,原因主要应归结为社会经济发展条件还不成熟。发展到明代,虽然农业生产力没有发生飞跃,但是,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在铜的资源匮乏、钞币不行、宝钞制度失败的反弹下,白银崛起,白银货币化推动了资本积累、消费和净出口,成为拉动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60]。金代的白银货币化,正是唐代以来中国经济货币化趋势的延续,同时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王文成提出,中国的白银货币化在宋代已经出现,认为 “金朝与南宋一道,共同揭开了中国白银货币史的第一章”[61],审视金代白银货币化的过程,这种提法是很有道理的。
从金代白银的货币化进程来看,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非常勇敢的尝试,对明代白银完成货币化进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同时也表明了金代白银货币化的独特地位。
注释:
① 李埏:《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序》,《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② [60]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16页。
③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铜铁铅锡坑冶》。
④ [36]张婧:《金代交钞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8-20页。
⑤ (金)宇文懋昭撰,李西宁点校:《大金国志》卷1《太祖武元皇帝上》,齐鲁书社,2000年,第3页。
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
⑦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
⑧ (宋)辛弃疾:《南渡录》卷1。
⑨ (金)宇文懋昭撰,李西宁点校:《大金国志》卷31《齐国刘豫录》,齐鲁书社,2000年,第239页。
⑩ (清)吴乘权:《鉴纲易知录》卷76《钦宗皇帝靖康元年》。
[11](金)宇文懋昭撰,李西宁点校:《大金国志》卷11《熙宗孝成皇帝三》,第93-94页。
[12](金)宇文懋昭撰,李西宁点校:《大金国志》卷16《世宗圣明皇帝上》,第125-126页。
[13]《宋史》卷33《孝宗本纪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629页。
[14]《宋史》卷39《宁宗本纪三》,中华书局,1977年,第760页。
[15]朱瑞熙:《宋代的岁币》,《岳飞研究》第三辑,第213-232页。
[16]《辽史》卷60《食货志下》,中华书局,1974年,第930页。
[17]《金史》卷5《海陵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08页。
[18]《金史》卷48《食货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第1070-1071页。
[19][21]《金史》卷49《食货志四》,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1,1110页。
[20]《金史》卷7《世宗本纪中》,中华书局,1975年,第158页;又见卷50《食货志五》,第1116页。
[22][23][26][32]《金史》 卷50 《食货志五》, 中华书局,1975年, 第1116页。
[24]《金史》卷10《章宗本纪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233页。
[25]买扑为宋、金、元时期的一种包税制度。税收由官府核计应征数额,招商承包,由承包商自行申报税额,以出价最高者取得包税权。包商 (即买扑人)缴保证金于官,取得征税之权。
[27]《金史》卷47《食货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1093页。
[28]《金史》卷49《食货志四》,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0页。
[29]据 《宋史》载,“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然无定制,其名物各随地宜而不一焉”。参见 《宋史》卷186《食货志下八》,中华书局,1977年,第4541页。
[30][31]《金史》卷50《食货志五》,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5页。
[33][35][45]《金史》 卷48 《食货志三》, 中华书局,1975年, 第1076页。
[34][朝鲜]郑麟趾撰:《高丽史》卷2《定宗世家》。
[37]“劣币驱逐良币”,又称格雷欣法则,是指当一个国家同时流通两种实际价值不同而法定比价不变的货币时,实际价值高的货币 (良币)必然要被熔化、收藏或输出而退出流通领域,而实际价值低的货币 (劣币)反而充斥市场。
[38](日)高桥弘臣著,仲行编译:《金末货币的混乱》,《中国钱币》1993年第4期,第16页。
[39]《金史》卷108《侯挚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386页。
[40]《金史》卷23《五行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542页。
[41]《金史》卷48《食货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第1089页。
[42][44]《金史》卷48《食货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第1090页。
[43](元)王颚:《汝南遗事》卷3,天兴宝会面值为一钱、二钱、三钱、五钱四等。
[46](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108《焚珠玉锦绣敕》。
[47]唐代慧琳提出,铤,“铜铁之璞,未成器用者也”。参见 (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52《释铤》。
[48](清)徐松: 《宋会要辑稿》, 《食货》64之61。
[49]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50][51]《元史》卷93《食货志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2369,2370页。
[52]《金史》卷47《食货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1050页。
[53]《明史》卷81《食货志五》,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2页。
[54]《明史》卷81《食货志五》,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3页。
[55](金)宇文懋昭撰,李西宁点校:《大金国志》卷24《宣宗皇帝上》,第173页。
[56]《金史》卷108《侯挚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9页。
[57]《金史》卷119《粘葛奴申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2页。
[58](元)王颚: 《汝南遗事》 卷3。
[59]《金史》卷49《食货志四》,中华书局,1975年,第1109页。
[61]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