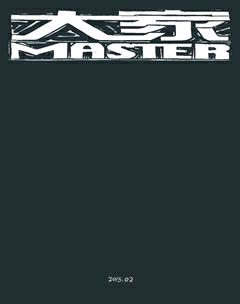民间
李达伟

1
在这个民间,有许多异人异物异事。在这个文本中,我想记录下某些已经消失或可能会消失的民间文化。有些记录的意义在于:可以满足人对过去民间的缅怀和痛感。民间中的一些东西,生命力旺盛且坚韧,不会轻易消失,像那些在大地之上长得繁茂的巴茅草。每次我见到一片长得丰茂的茅草时,都想牵一些牛马来放,让牛马的足踝被青草的摇曳所撩拨。而真实的情形是,我并没有一匹马,也没有一头牛,我只有一具后知后觉的肉身。幸好那些茅草在大地上存活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我的感知能力。但最终,我还是不敢进入任何一片丰茂的茅草地,毕竟那里有着太多美妙的同时,还隐藏了一些让人不安的因子。民间,有着一片茅草地的特质。我所见到的民间,以及我所虚构的民间,里面的茅草地,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葳蕤茂盛,足以吞没一具肉身、许多的小动物和小植物。
某种强烈的乡愁,让我内心极度忧伤。我经常会假设,有那么一群人,像我一样有着无法排遣的乡愁。什么样的乡愁?我们却回答不上来,但我们分明感受到了它的存在:真实的存在,真实的忧郁,真实的中伤。
如果我要虚构一个完整的民间的话,这个民间必须在一个高山峡谷之中。环境的闭塞,能够保持一个民间的完整,不可避免的是落后,但同时也拥有了许多庞杂的内蕴。其实,这样的民间,不需要我的虚构,毕竟我就曾在这样的民间里生活过多年。但这里,我为了避免麻烦,怕给人我是在揭某个传统民间伤疤的错觉,我便选择了虚构。但我的虚构往往脱离不了现实。连绵的山脉,一些切割众多山脉的大河小溪,许多的坡地,许多的土路,许多的尘埃,以及在冬日冻得通红夏日被高原的阳光灼伤的许多脸面。我生活在高原高山峡谷地带,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有时又是一个走入(介入)的人。我的民间,在我用各种眼光和角度观察后,不断丰富起来,变得立体化。解读这样的民间,也就需要多个角度、多种目光。在我口口声声的虚构中,其实我并没有在过多虚构,而是过多拼接。意识到这样的拼接时,我的内心涌起了种种不安,同时也背负了诸多顾虑。用什么样的一个眼光与笔调,来描述一个又一个真实或不真实的民间?这是在很多时候,我所思考的。我绝不能用单纯复制的方式,来复制民间,毕竟民间的有些东西无法复制。
民间是一个异常纷繁复杂的世界,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以简单的线条,就能勾勒出来的角落。我出生于民间,我耳濡目染着人间的一些优良特质。我的身份早就这样被定义了下来。在许多时候,我们都在无意识地定义身份。用语言来界定,我就是一个白族人,而根据白族语言的模糊性与清晰性来讲,或是以白族语言里夹杂的汉语的多寡又可定义生活的地域。各种各样的方言,各种各样的腔调,无意间已经暴露了一些东西。我不需要在别人面前强调自己是一个来自民间的人,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文本中的民间,是一个容器,像语言便是一种容器。
2
小寨。这是地名,或者不是地名。如果真是地名的话,从名字上已经定义了它的狭小。小寨,一个浓缩的民间,这里有着最基本最微小的民间元素:一些古旧的房屋,一些现代的房屋,一些富贵人家,一些穷苦人家,有巫师,有几世同堂共处一室其乐融融,有一些庄稼地,种植着一些经济作物,还有密布的古木(这才是必不可少的)。这些都是任何民间,必不可少的元素,如果里面的一些元素不存在,或者消失的话,会给人怪异的感觉。这个民间,没有给人怪异的感觉,在里面生活的一些人,还因长时间生活其中,而丢了感觉。
有着密林的民间,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就会存在,这便是一片密林所能制造的各种可能性。在一片密林中,一些人秘密地分布着,一些人秘密地成精。一个老妇人早已成精,也许,成精的不只她一个人,还有可能是那些家里的牲畜,以及密林间的许多物,她需要吃肉,人肉最好。老人,身子骨瘦小,脸上的褶皱里夹着许多污垢。水已经无法浸入,那些污垢已经无法得到清洗。她的两个孙子,并不介意那些褶皱以及那些污垢,也不介意她嘴巴里仅剩的几颗牙齿以及嘴巴里暗黑的空洞。她与两个孙子,每天呆在一起,相安无事。某一天,成精后的老人,再也控制不住那几颗豁牙对于肉的饥渴,在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出去干活后,把两个孙子吃掉了。是怎么吃掉的?可能是吞掉的,毕竟她已经不是人了,或者即便是人,她的那些牙齿也已经没有多大力了。到了傍晚,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到处找着两个娃娃,她却异常平静地冒出了一句,“是我把她们吃掉了。”儿子和儿媳在那一刻,面面相觑。但他们并不相信,他们需要一个巫师的判断。巫师掐指一算,她并没有说谎。一家人面临着崩溃。她的儿子,找了个借口,给她买了一头牛,让她到山上暂时放牧,那个季节恰好是草木纷繁的时节。
那是个什么样的日子?我在走访调查中,没有人提及。反正就是在某一天,她和儿子赶着牛往山上走去。她的儿子,泪水涟涟。她,也是泪水涟涟。母子二人,一路无话,似乎都已经心知肚明。她的儿子把她在山上安顿好后,便与母亲告别,一路很沉重,但似乎不得不那样。当她的儿子来到山脚时,听到了山上惨烈的叫声,是牛的叫声,他可以肯定,那头牛也被她吃掉了,吃牛的场景,他想都不敢想,如果一想就会想到自己的两个娃娃被她吃掉的场景。她成了一个熊精,这是后话了。
又是某一天,一些猎人上山打猎,捕获了一只熊,准确些应该是打死了一只熊。那些猎人,在那个村寨里贩卖熊肉。她的儿子,去买熊肉。在买熊肉的过程中,她的儿子突然发现那个熊的手上戴着一个手镯,铜做的,与自己母亲生前手上戴的一模一样。他便买了那只熊的手,回来并没有把它吃掉,而是对着它痛哭,然后把那只手好好地安葬了起来。在这个民间,一切人与物都有可能成精。而这个成精的故事里,她的儿子并没有因自己的母亲曾伤害过自己的娃娃而让仇恨控制自己,他依然是一个孝子。似乎,道德的力量,礼义仁智信,在民间依然能找到。民间,依然神秘,至少在人的思想观念里是这样的神秘,同样有些好的东西依然被传播着。成精的继续成精吧!那些巫师如是说。endprint
3
一些民间,很安静。这主要是许多人的离开,制造了一些空村。所有人,一夜之间,便消失了。传言,那些在夜间依然醒着的鸟群里,一个民间的消失,被传得沸沸扬扬。它们竟也不知道村寨中的人们集体走往何处。那是发生在春天的事。人们竟会突然之间消失不见,那些活人没有遁地的能力,更没有升空的本事,死者的尸体被放入在地之下慢慢腐烂。有那么一段时间,死尸腐烂的气味,随着风到处蔓延飘荡,人们纷纷掩鼻怒目诅咒。那具死尸活着时的得意与失落,早已被那些诅咒的人遗忘,直到死尸不再散发臭味,人们才会安静且冷静地评价一个人,盖棺论定就这样被推迟。有一些鸟类,是喜欢死尸的味道的。而在那个村寨,鸟类没有成神,至少在人们看来是这样。那些失眠的鸟群,却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它们中至少有那么一只是神鸟,就像族群中的头人一样。在族人眼里,头人早已成神,早已成为一种道德的评判标准,头人自己就是一部法典。那些鸟类中的某一只鸟,便是王,便是神,它的鸣叫声忽而悲凉忽而愉悦,它的呼叫似乎是在呼叫着本族的鸟类,它的叫声,还可能是一种征兆。
那个夜晚,没有任何一只会预言的鸟,没有发出代表征兆的叫声,连乌鸦都没有出声。乌鸦,在那个村寨里,往往能预言死亡。由乌鸦的失语推断,那个村寨里那晚上没有人死去,或者是以乌鸦所不认可的死亡方式死亡。村寨,从前年冬天,接连死了一些人之后,便不再死人。那个冬天,死尸腐烂的速度极慢,死尸的臭味,也较之往常淡化了很多。但死尸的气味,在人群中引起了骚动,毕竟有那么多人接连死去,里面还有几个同龄小孩。一种无法医治的疾病,在那个村寨悄悄蔓延了。有许多族人这样猜测。而那些等待着死尸的鸟群,单纯且冰冷,请赐予我们更多的死尸吧!它们那群集的喧闹声中,似乎有着几丝这样的嘈杂。一般而言,许多鸟类的喧闹声,于民间绝对不是噪声,而是一种活着的安静。
村寨中的人们,以悄无声息的方式从民间逃脱。那可以说一次有预谋的逃脱,不然具有着敏锐洞察能力的鸟类,以及同样有着敏锐感知能力的动物,怎么会没有发现。在这里做一些补充:那个村寨旁边有着一大片深不可测的密林,里面聚集着一股深不可测的力,这些力,来自原始丛林的一种原始的力,同样来自众多鸟兽神灵鬼怪聚集的力。我是在某个梦中进入这样一个村寨,以及这样一片密林的。我在那个村寨的庙宇里,看到了一些四不像的神兽,往往是兽头人身,或者是人头兽身,身形或是魁梧,或是瘦弱,手中还执有神杖之类的东西。必不可少的神杖,随处可见的神杖,一挥,兽性消散,民间人鸟兽相互交融,人通鸟语,鸟通人颜,人与兽坐于某个山坡上,晒着高原的阳光,谈着那片深不可测的密林。那时,鸟已经成神鸟,兽已成神兽,人也已经成神。成神就那样简单,把兽欲丢掉,把自己融化在一片密林里。而我不通鸟语,更不通与神兽交流的方式,许多的神兽变成兽,兽欲追赶着我。那个民间里的人们,莫非早已集体成神,并化作一缕青烟,或者化作一抔又一抔的泥土,或者化作一片又一片的树叶(或是绿叶,或是枯叶)。梦并没有给我以启示,梦中只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黑洞,我惧怕那些黑洞,总觉得黑洞是一些无底洞,愈到里面,空气愈加稀薄,也离真正的大地愈远。我的感觉,人的生存,无法脱离真正的大地。
那些人,会不会是进入了某个被现代文明充斥的地界,那里高楼大厦林立,那里灯火通明,所有的鸟类总是醒着,总是精疲力竭?
密林里,有着我嘶哑的吼声,群山无语,只有我的回声,鸟群无声,只有我的回声,鬼神兽无声,只有我的回声。就让这样一个民间悄然消失吧!如果村寨里的人们再不回来,那些土木结构的房子将在虫蛀声中倒塌,接连倒塌,也有可能是齐声倒塌。那些神灵如是说。
4
民间的地点,被隐去,在那么一个地方,有鬼神的存在。讲述者,信誓旦旦地如是说。讲述者说,真实的故事发生在他的家乡,时间是很早以前(一个模糊的时间概念),人们发现了它的荒无人烟,同时也发现了这是一个宽广且能制造富庶的坝子。那个陌生的世界里,适合关于鬼神故事的滋生,这是温床,这里有着原始的粗野与隐秘。一个部队,来到某个山谷中,驻扎下来,并没有长时间驻扎下来,而是在开荒了一段时间之后,集体撤退了。他们的去处,如果去盘根问底的话,一定能够找到,但这已经没有多少意义。这个故事,需要主人公的完全隐去。
讲述者,这样营造气氛:因为接连发生了一些怪事,那些人才最终离开那个地域的,他们的离开是被迫的,是不得不的离开。是在某个白天,其中的一个或者两个兵,在开垦某片土地时,看到了一个或者两个姑娘,曼妙的身姿,妖娆的眼睛,身着少数民族服饰(这里提到了少数民族,下文里可能也会接连提到少数民族,对于这个文本,对于那些鬼神故事,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聚居地是必不可少的),提着水桶,里面的水泼溅着。那条土路上,一条很长的湿痕,拖出来一般,很长时间都没干,而那时毒日高照。他们跟着那些女子,他们猛然间才发现,一个或者是两个女子的脚并没有着地。两个当兵的,并没有昏厥过去,但有一股冷意涌上心头。在来到某一棵大榕树下,女子突然之间消失不见。从那晚开始,奇怪的事情,接连发生。而都是些什么样奇怪的事情?自己想吧!把自己的想象力彻底打开地想吧!讲述者如是说。在某个傍晚,一伙当兵的,来到那棵大榕树前面,拿出枪,枪种类繁多,万箭齐发的味道,枪声惊醒了树上的众生,一群飞鸟扑腾一声飞向夜空,一群蚂蚁从某个枝杈间直接坠落在地。风呼呼地吹着,榕树呼呼地摇着,里面似乎夹杂着几声呜咽。第二天,那个部队便撤出了那个民间。在离开之前,那些当兵的,来到榕树下,看到几滴一夜过后依然鲜红的血。后续无话。
我略微分析一下,在民间,鬼神故事存在的必要性。因为这是一个无法真正看穿的民间。自从那个部队离开后,一棵又一棵茂密的古木依然没有离开,一个又一个被植物世界遮蔽的坟墓不断增加,还有一群又一群巫师,正背身过去,然后拿着一颗鸡蛋往背后一丢,如果鸡蛋不碎,还能倒立,那便是一块风水宝地,在那个角落,就可以新增一座坟墓。这个民间里,有一些能人异士,他们往往是暂时性的医师,但他们治愈病人的方法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群能人异士,在平时你将看不出他们有任何的不同,与那些巫师一样,平时他们便是地地道道的农人,常年打理着五谷六畜。而如有需要,他就会给一些人治病,治病的过程,让人诧异:病人赤裸着背,那个能人异士眼前摆放着一碗清水(高山上流下来,穿过荆棘,滑过岩石,被一些众生舔舐过),他含着自己的拇指,同时用无名指放在病人的背上,然后不断地吮吸,然后朝另外准备着的碗吐出,都是血。一开始吐出来的基本都是接近黑色,然后他又吸一口清水,接着吮吸,这样的行为不断被重复,直到吐出来的血不再是暗色为止。经常会有一些人,突然之间拥有这样的能力。但过一段时间后,这些人又会失去这样医治病人的能力。在这样神秘的民间里,必然要有着一些异人异事的存在。而在一些敞亮的民间里,似乎异人异事便不再存在。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会用吸吮拇指治病的异人。这里,我故意把这个民间的地名隐去,为了避免对号入座,以及抨击我是在胡诌一个民间。我如是说。endprint
5
有一些神灵鬼怪,专门管民间的灵魂。密密麻麻的鬼怪躲在暗处,面貌狰狞,专门跟着人们,管着人们的灵魂。这些鬼怪,有时会跟着那个民间的人们,但鬼影都没有。民间被鬼怪监督,鬼怪每到暮色降临后,便躲在人家的窗棂下偷听人们的讲话。如果人家谈话的内容幽默诙谐的话,那些鬼怪也会跟着笑几声,时而大声,时而小声,但人们可能沉浸在自己制造的谈话中,而忽略了窗外的那些鬼怪,或者是民间根本无法听到鬼怪的声音。
是在某一天,某个巫师,来到村寨,他告诫人们做事不要太过分,毕竟有鬼怪在看着。鬼怪看到了又如何?这是那个民间所坚持的信念,而在那个巫师看来,鬼怪监督有鬼怪的道理,万一某天鬼怪附在某人身上,那人便遭殃了,他(她)的阳寿会折损,有时也会导致这人在平日里打不起精神,似乎魂魄脱离了肉身。巫师和那个民间的一些人,来到了某个庙宇里,在那些香火边沿的角落里找寻着魂魄,那个角落里有许多的蜘蛛网,他们手里拿着一根香,不断地熏着那些角落,巫师口中还念念有词,最终他们找到了魂魄,是一种类似蜘蛛的东西,但比起一般的蜘蛛要小很多。
巫师便是这样告诫着人们,一定要防那些躲在暗处的鬼怪,而最好的防身便是不要做亏心事。那么也应该有着一些神灵的存在吧?人们猜测着,而在他们的信仰里,也确实有着神灵的存在。重点是巫师的存在,给那个民间制造了一个新奇的世界。混沌的世界里,似乎有了清晰的东西:人与鬼神同在。民间的灵魂被控制。民间里便一直充满着善的因子。在那个民间,人们从最初的冷漠里挣脱了出来,人们之间和谐相处,那个民间人们尊老爱幼,在那个民间,属于人类优秀的品质,正慢慢形成,并持续地影响着那个民间的一切人。那个到处行走的巫师,彻底离开那个乡间,人们依然把那个巫师的观念奉为圭臬,并一直传承了下来,直到现在。
现在,那个民间依然专门有着自己的巫师,在每年的那么几个重要的日子里,巫师便会带着全村的老少,在某一棵神树下,或某一个庙宇里,或某个院子里,进行一些祭祀活动。甚至有些祭祀活动,是全村老少都参与的,用某种舞蹈的形式,这样既起到娱人的作用,也起到了娱鬼娱神的作用。那些祭祀活动,不会轻易被简化,它保留了一些最古老的东西。当我来到那个民间,我感到很震惊,人们生活在某个山谷中,周围有着大山的围困,还有江河的阻隔,以及贫瘠的侵袭。但他们并没有怎么抱怨生存的空间,相反很是感激,他们感激因了那么一个民间,他们的灵魂深处便是清澈的,如眼前的大江小河山谷古木杂草一样清澈。山谷里,草木丰美,牛羊肥壮,鲜花绽放。那个民间,庙宇就一个,但对于那个狭小的民间,已经足够。也因了那个庙宇,以及人们的思想坚守,那个民间才变得那般纯净,当然某种程度上也变得落后。那个民间,如果不信命的话,可能落后的情形就会得到一些改变。本来,我想一直在那个民间生活下去,但我还要步入其他的民间,这样我只能忍痛割爱。从那个民间离开后,我总觉得有个躲在暗处的眼睛,不停地监视着我,但我乐于有那样的属于鬼怪的眼睛监视着我,也只有那样的监视,我内心里的恶的因子才不敢随意就泛滥,也才不会轻易就把我吞噬。我的感觉如是说。
6
有一些微民间的存在,这里的“微”是微妙而精致。现在在大理的许多地方,依然有一些甲马的存在。与甲马有关的,是一个微民间。这里只需要如实地复述即可,这里需要如实地复述。甲马,在云南大地,甚至在中原大地,都有它的影子。人们是这样定义“甲马”的:俗于纸上画神佛像,涂以红、黄彩色,而祭赛之,毕即焚化,谓之甲马。以此纸为神佛之所凭依,似乎马也。甲马在民间,是人与神灵、鬼神、自然沟通的载体,是通灵的使者。如果通俗化一点,甲马是一种上面印有图案的纸张。
甲马,早在多年前就充斥于我的出生地。只是那时,我不知道那便是甲马。我以前看到那些纸张时,感觉上更多的是不适应,似乎那些纸张没有任何美感可言。而真正仔细观察那些纸张上的图案,以及与那些图案相互对应的雕版后,我才发现那些雕版是属于民间的最精致的雕刻,那些图案也是属于民间最精妙的画之一。手工的雕刻,有着手工的温度以及质感,精致异常。我在许多个民间,看到了一些老人,在一些大树下,在一些庙宇里,在一些山石下,在一些道路边燃烧着那种纸张。燃烧,代表着烟雾的升腾,代表着一种油墨香的蔓延,也同样代表着一种文化在这个民间的无处不在。那些老人依然在坚持着某种信仰,而这些甲马纸张所对应的信仰是很繁密的。从那些甲马的图案上,就可以发现有着自然的崇拜、祖先的崇拜、本主信仰,以及儒释道信仰。这是用信仰制造的微民间。一种造神与造像的民间。绘画和雕刻艺术,在民间不断精进。民间艺术在那些老人的焚烧中,烟雾缭绕,并日益汇合成一条艺术的河流。而在某些时间里,这条属于民间的艺术河流,曾经出现过断流,但这条河流依然穿过一片又一片的荆棘,并长时间生活在荆棘之中。在“文革”时期,那些甲马画被认为是迷信,甲马纸所对应的雕版,被没收,与之相关的民间艺人,也被时间没收。一些艺人的苦难史,在这里被我弱化了,我深知不能这样弱化。现在,一个微民间正濒临消失。有许多的微民间,需要用微妙的视角深入。而这正是现在我准备做的。我如是说。
7
风景如画的民间,里面夹杂着几丝隐隐的不安,这样的不安是我在入住其中后,逐渐感觉到的。这样的不安,与生存有关。一开始貌似进入了一个妙境之中,但有些只是表象,而表象有时并不真实。风景如画,庄稼作为背景,如果没有那如波浪一样的麦田,一些东西就会感觉不和谐,而不和谐便是不美的。正待收割的小麦,被那些形状不一的土地切割成了形态不一的画面。凡·高的麦田,上面飞过一群乌鸦,飞过一些云雀,麦田里有收割者,麦田上的天空时而烈日骄阳,时而清澈蔚蓝,而更多时候潜藏着不安。不安开始感染着麦田,并被麦田从中心的某个点往外扩散,波及着人。
三个亲兄弟,用“伯仲季”来代指。他们并不是过来收割麦子,他们一个个气势汹汹,怒目圆睁,为了那块地的归属。每个人都肯定地说过,那片地是父亲留给自己的。而父亲是在什么时候说过给他们的?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能够把地点精确到某个点。其中伯如是说:去年你们去打工时,就在这片土地里,跟他说的;然后是仲,精确到了某次父子儿子掏出那物什对着夕阳的坠落撒尿,撒得痛快淋漓之时,那时父亲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仲自己也吸了一口气,那时父亲就指着那片土地说了,那片土地在我离开这民间后归你得了;最后是季,是父亲在他弥留之际对自己说的,你们可否记得在他弥留之际,他曾叫我把耳朵贴到他的嘴巴,那时我闻到了父亲嘴巴里那股浓烈的酸臭味,你们没有真正贴近过他的嘴巴,你们一直都厌恶他行将死去的气味,所以你们根本听不到他说把那块地留给我!没有人放弃那块土地,毕竟上面就是正待收割的麦子,麦穗饱满。与鼓胀饱满的麦子对应的是鼓胀的气,似乎只有通过争斗,只有把三兄弟之间的那份真情扯裂,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赤手空拳,拼劲力量,三兄弟构成了一个隐隐的三角形,没有人真正占到便宜,他们从那个田埂上开始争斗,并慢慢把战场蔓延到了那片麦田里,饱满的麦子被压扁后汁液沾染着他们的衣服、面部、鼻子,甚至是嘴巴,并沿着鼻腔深入腹部,沿着嘴巴深入腹部。没有人来劝。那些在旁边的麦田里,准备收割麦子的人群,拿着镰刀,朝他们兄弟几个望着,望得深有意味。突然之间,其中的某个人突然说了一句。endprint
“可惜了那些麦子!长得多好呀!”
兄弟三个最终精疲力竭,但面部有一些伤痕,被麦芒刺伤,幸好兄弟三人都忘记了从家里拿出镰刀。他们那天,都只是过来看看麦子能不能收了。而那天,离他们的父亲去世才一个多月。他们的争斗,越演越烈。最终一那片麦田,褪去了原来的色泽,在一个大雨瓢泼的日子里,大部分被冲走,有许多倒伏在了地里。其中一次的争斗,三个兄弟都受伤了,仲的眼睛差点瞎掉,镇上派出所的人来调解过几回,但都无效。属于这三个兄弟的民间,精疲力竭。属于那些看热闹的人的民间,同样精疲力竭。民间如是说。
8
矮小的毛驴,在前面走着,驮着一捆柴。柴,湿重。人,也走得湿重。他的名字,在此略去,他的真实与否,在此也不做任何表态。这可以是一个虚构的人。只有那毛驴是无法虚构的。在某天,我见到他的时候,总觉得现在的他,过得很落魄。真实的情形,也确实是这样。不知道,从什么时间开始,那个民间早已抛弃了他。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感受到了来自一个群体的奚落?也许,他早已不再考虑这些东西。生存的艰难,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上的苦闷,在他身上依然很明显。他选择搬离了原来的地方,这样的选择,有点微妙。他搬离了原来村寨,与原来的村寨之间隔着一些松树林,以及随着不同季节变化着和成熟着的庄稼。从他家上去一小段,便是村寨的坟地,几乎所有的坟墓都在那个角落,可以从那些坟墓上知道属于那个村寨的苦难史与幸福史。毛驴与他,并没有起到反衬的作用,而是相互补充,凸显了民间的一些东西。毛驴,看似瘦小,叫声却很大。以前他还住在村寨中的时候,我亲眼目睹过毛驴叫喊的情形,叫声近乎悲壮、悲凉、悲痛。它的存在,是唯一的。在那个村寨里是唯一的。它必然是孤独的。一头性压抑的驴子。情欲,被长时间压抑和克制。而它的主人,似乎并不是这样。至少从以前和他交往的时间里,他对自己过往的讲述中,更多时候,他谈到更多的是女人,似乎他在到处游荡过程中,碰到的基本都是女人,他的民间便是女人的民间。他现在,结婚生子,这让一些还没有结婚生子的人羡慕不已。似乎,有了女人的民间,以及有了女人的家,便是完整的,即便平时的生存被内心扯裂,把内心磨平。
曾经,他简直就是一个怪人,怪异的人。长发,但不常洗,纠结在一块,穿一条喇叭裤,拿着一个录音机,声音开到最大,经常放的是一些民间小调,大部分的内容属于民间,并用那个民间的语言在唱。这样的造型,曾经风靡民间。只是,在那个寨子里,只有他是那样。他可能是赶上了潮流的末梢,或者直接就没有赶着。过时的潮流。但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以那样的造型,在许多个民间(民间本来是一个很宏阔的概念,但在这个文本里,被我不断缩小,它有时是一个村寨,而在更多时候,它甚至就是一个人、一株植物、一颗石头……被缩小化的民间,有时透露了一些被大民间所遮蔽的真实)里到处游荡,他说自己在那些角落游荡时很有面子、很威风,而我总觉得不是那样,我脑海里开始出现了一些假设。很怪异的一个人,甚至有可能是疯子,才会以那样怪异的造型悠闲地穿行于民间。许多人如是说。
9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当这几句话出现时,大部分人想到的是讲故事的叙事方式,但这里不只是故事,民间往往会把时间模糊,“很久”有时未必指的是时间很长,有时候也可以很短),那个民间有一个富矿。当那个富矿被发现后,许多人鱼贯而入,慢慢地变得很拥堵。富矿,深埋在地底下,已经深埋了亿万年。
一些老人,他们似乎时而跟着时间的步子往前,时而是与时间相悖往后退去,时而会把时间定格。其中的李姓老太太就是这样的人。
老人眼睛早已看不清事物,在一种很模糊的状态下,她经常一本正经地跟别人说起,她看到了许多活着的死人,她还看到了无数成神成精成鬼的植物与动物。她甚至在某一天夜间,对着家人说,自己其实是一只成人的动物,别的那些人与物都或是成神或是成精或是成鬼,而她偏偏就成了人。当巫师来到那个院子中的时候,李老太太正模仿着某种动物全身趴在地上,舌头不停地伸出来,舔舐着地上的灰尘,以及地上的污水。巫师,没有任何办法。李老太太的家人,也没有任何办法。神经病,许多人如是说。她的家人,让她搬到了一间屋子里独自住着,她同样是双手双脚着地爬到了那间屋子里,嘴巴还不停地动着,模仿着某种动物的叫声。
某一天,天刚蒙蒙亮,那位老人从沉迷状态中清醒过来,她推开了木门,伸了伸懒腰,脚步变得轻盈,不再是原来老态龙钟的样子,见着人便说出了那个秘密,她见到了在地之下的那个富矿。人们感到很震惊。在地之下,有神灵鬼魂,但不曾听到过有富矿的。人们,半信半疑,但最终还是拿着锄头掘开了老太太所指的地方,掘开了将近一米多,清泉直冒,人们纷纷用双手舀起了那些水,并用舌头舔舐着,甘甜,水原来也是有味道的,也可以是柔软的,而一直以来,那个民间所喝的水,粗糙,淡而无味。人们,继续往下挖掘,挖三米,便见到了那个富矿,那是实实在在的银。人们,开始日夜不停地往下挖,往周围挖,似乎多得用不完的白银,不断被挖出。挖到深处,还挖出一番洞天,人们,终于发现他们挖到了那个清泉的源头,泉水的两边,有着各种古木,那时桃花盛开,那是一个华丽妖娆的世界。那个老人,自从喝了那条清泉的水后,似乎没有什么反应。只有她自己知道,她看到的东西更多了,她看到了那个被人们深挖的洞,就要塌了。但这回,她并没有把这个说明白。她背着个竹篮,挑着水在那个民间里绕着,一些人开始奔走相告,洞里的人们,有些出于好奇,从洞中出来,也有一些人,不想看,毕竟眼前的银的亮度足以把自己的欲望刺穿。当那个老人,以缓慢的脚步走完那个民间,那个洞也随之轰然倒塌。那个老人,背着水,竹篮并不漏水,在人们的啧啧称赞声中,走出了那个民间,没有人追她,只有一群沉浸在某种状态中的人。当我来到那个地方,在与一些人交谈时,一些人觉得,那个老人,很真实,她还有后代呢。也有一些小娃娃,这样认为:一个绝对不真实的人,竹篮怎么能够担水而不漏。那个民间,就这样在真实与不真实交错的状态中,继续向前。那个民间如是说。
10
这个文本是未竟的,因为民间是未竟的。我如实说。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