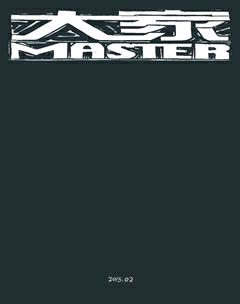静水深流与差异性写作
黄桂元

作家正纷纷被资本收购的时代,“探索”小说的再度倡扬未免不合时宜,却恰恰彰显了一种久已稀缺的艺术坚守品质。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小说实验风潮,曾给一代读者留下金灿灿的记忆,而今时过境迁,恍如隔世,昔日意气风发的“先锋”骄子多成大佬、土豪,锐意不再,品相庸常,仍在消费和享受功成名就带来的红利,不免令人感慨。马尔库塞认为,“艺术家唯一的使命是扩大自己与时代的差异”,而差异性往往也正是艺术家自设的险途。文学探索者的坚忍跋涉注定步履维艰,身影寂寥,位置边缘,却永远值得人们的尊敬,也不可能绝迹。
很久没有读到如此苍凉、深阔、凝重,同时具有某种“形而上”冥想意味和殉道精神的文字了。我说的是张雷的作品。昔日的实验写作多在“怎么写”上殚精竭虑,各施绝技,一度使我心仪。如今我却对那些坚持人文信仰、注重精神内质与心理能量,而不再纠缠于叙述玄机、小说技巧的写作者深怀敬意,也更有感觉。在这一点,我认同卡佛的看法,“小说创作,并不如某些作家所认为的那样,技巧应该优于内容”,我甚至认为,过度纠缠技巧的作家,内在格局不会太大,说到底还是缺乏自信,底蕴不够。
时下的世界,正在本雅明说的“单行道”上高速惯性滑行,经济唯大,市场第一,发展至上,只有速度而没有刹车,人的陷落与异化也在加剧。许多作家随之起舞,笔墨太过喧闹,太过尘相,太过物欲,太多只见肉身不见灵魂、只见欲望不见境界、只见游戏不见追问的文字。仅仅活了47岁的张雷是个异数,他出生于1960年代末,与“70后”作家也仅仅相距两个春秋,写作气象却与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大师灵犀相通,静水深流的叙事仿佛脱胎于遥远时空,已被时尚趣味换了胃口的当下读者会不适应、不耐烦,快餐节奏和网络节奏使他们日益浮躁不堪,心智退化,丧失了思考能力。《瓦尔登湖》的译者徐迟先生曾告诫读者,阅读梭罗,“最好是先把你的心安静下来,然后你再打开这本书,否则你也许读不下去,认为他太浓缩、难读、艰深,甚至会觉得它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张雷也是如此,他写的每个汉字我们都认识,故事也未游离于人间烟火,组合出来的世界,却是艰涩的、诡异的、幽深的,还有几分凌乱、混沌,很难一气呵成地读下来。可以想象,张雷也不奢望自己的作品能获得俗世的大面积共鸣,有道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节选的张雷作品,有“切片”性质,呈现的却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厚重小说文本。他通过虚构的“临河镇”,建立了一个人类如何抗拒生命困境的“隐喻场”。“小镇意象”,连同与之配套的福克纳“邮票理论”,是百年世界文学中的现代小说写作的一大收获,张雷是否受其影响姑且不论,重要的是我们从“临河镇”感受到了一种超越历史语义层面的精神叙事气质。临河镇是一个封闭的边陲小镇,在过往年代近乎于世外桃源,“根据记载,不仅士农工商都有,还民族种类较多。城西小乘佛教的缅寺,城东大乘佛教的临河寺,无数年来和谐相对。各条街巷,不同民族的地理命名杂然互融,奔跑的孩子有着不同的肤色。有临街开铺的手艺人,有驱赶骡马常年在外的马帮人,有保持旧传统的读书人,也有在孔庙里兴办新学的时髦青年。明夷巷有一户姓晋的人家居然还制作小提琴,工艺精良,主要供货给省剧院和文艺团体。每每新琴制成试音时,城里的人都会涌来一听为快”。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同无数小镇命运一样,临河镇被脱缰野马般的现代工业文明大潮冲得面目皆非,以至于后人若想了解当年临河镇,按图索骥都不可能。
“我们彼此都已经没有了故乡,甚至在记忆里也找不到了。小草长在颓败的墙角,摇晃着。雨后它们变得深绿,旺盛得不讲道理。一旦好多天不来雨,又都变得浑身有精无力,灰尘满面……”。临河镇的背景是清晰的,物理时间却有些模糊,这属于现代或是后现代小说惯有的叙事套路。他把失去故乡的现代人比喻为“草木般的人”,他们“不论是抛下故乡投奔远方,就是被故乡抛弃,到四方游荡,都会逐渐枯萎。每个梦都在燃烧,暴风雨过后,烈日下的枯草依旧一触即灭”。全球化时代,人类的精神归属感日益稀薄,致使文学的“永恒主题”被迫扩容,除了公认的“爱”与“死”“战争”,还增添了“自然”“乡愁”“怀旧”系列。“自然”主题是生态灾难中的人类对于返璞归真的呼唤,“乡愁”是空间的置换所带来的人类惆怅,“怀旧”是时间的移动所引发的人类伤感,使得少数作家意外地成了不幸时代的“获益者”。20世纪以来,许多大哲、大师都是现代科技文明的反思者、批判者,张雷不仅步其后尘,更是超越性的精神叙事者。他笔下的小镇,藏匿着许多与历史灾难、人性悲剧有关的谜团,他需要寻访遗址,辨识真相,打捞历史,凭吊岁月。历史之不可知,并非时间的作弄,而常常是人为造成,才会如此千疮百孔,不堪回首。
弗兰克·伦特里契亚认为“全部的社会生活都在其最古怪、最细枝末节的层次上”,临河镇“最古怪”的历史细节,是曾经存活四十余载、消失半个多世纪的南塘诗社,它的旧址是一座早已“灰飞烟灭”的茶楼,“1960年茶馆拆除,建筑起了电影院;到2012年,电影院拆除,建起一个大型超市。楼房拆了又盖,盖了又拆,人来人往,尘埃飞扬又落下,当年的痕迹遗迹荡然无存”,由于当事人或故去,或仍在世却讳莫如深,三缄其口,南塘诗社的往事在坊间扑朔迷离,以讹传讹,寻找的难度甚至不亚于考古挖掘。叙述者关注南塘诗社,最初或许只是出于今不如昔的人文追怀,“痛饮狂歌空度日,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现代人已经没有了那份淋漓的元气,也没有与之相关的一切概念。一切都追逐实用性,讲究功利性的浮躁让愈来愈多的生命体不假思索地跃身投入生活潮流”,同时他的内心挣扎又在加剧,“我不相信进步。回望过去,我又缺乏自信,过去真的就比现在美好么?”随着真相步步逼近,我们明白了,小说所有的交待,都是在为南塘诗社的一位已亡人的命运谜团做铺垫。
已亡人叫叶天青,家谱记载只有十几个字:“生于1936年,失踪于1966年,溺水。”在临河镇人的传说里,这是一个“纨绔子弟”,“百分之百的败家子”,一份家族产业几年间败得一干二净,后来只能干些侍弄花木的活计,穷途末路,自生自灭。当年的占卜先生郭离却看到过叶天青的另一面:目光炯炯,眼眶凹陷,面目苍白而憔悴,由于彻夜在煤油灯下读书常常弄得两个鼻孔都是黑的,郭离叹息“那么单纯的人,就是不见容于社会”。叶天青读书着魔,洞悉人世冷暖,却仍然心存浪漫爱意,不会轻易走向绝路。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面对无常的历史,他是那样的渺小、无助、不堪一击。他因写了一本谁也没见过的书而被批斗,最让他无地自容的是被墨汁涂成大花脸,顶着纸糊的白帽子被群众游街,赖以生存的花卉也全给毁了,尊严丧尽,命运坍塌。他第一次走进河里,那时候的河水还很清澈,他洗去黑糊糊的墨迹,盈盈水面现出一张干干净净的脸,他坐在石头上发一阵呆,转身回到河岸,准备离去,但“眼前的一片空白拦住了他”,花坊狼藉,归路何在?脚下成了虚无的深渊。他再次下河,脱光衣服,赤裸裸向水流深处一步一步走去。生命沉沦于绝境的过程,张雷的叙述竟出奇的平静、出奇的舒缓,像是在讲述一段寓言。岁月的神秘性、偶然性、残酷性、荒诞性汇聚成巨大的解构力,直逼充满悖谬的人类生命伦理,南塘诗社由此获得了象征寓意。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