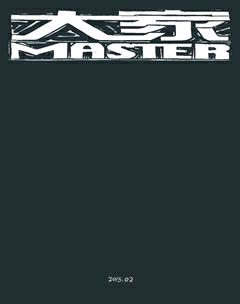诗是世界的隐喻

首次见于坚,是在其诗集《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的封面上,诗人于坚就像个云南土司,傲慢坚硬、目光凛冽,哪里像个诗人?后来与他接触,却发现这位“土司”相当好玩,说话幽默犀利,先天具备出口成章、吸引众生的本事,而且清一色的昆明话,听众经常被逗得哈哈大笑。于坚有些得意:“我这个人是在昆明话里,只懂普通话的永远不会知道我这个人。”
于坚当过十年工人,20岁时开始写诗,后来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进入大学前,他的诗就通过手抄本在大学生里面流传。25岁在公开刊物发表作品,就获得《飞天》大学生诗歌奖。1985年,他与诗人韩东等人创办诗刊《他们》;1986年《诗刊》头条发表他的《尚义街6号》;1994年在《大家》发表的长诗《0档案》被誉为当代汉语诗歌的一座“里程碑”。如今,于坚是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西南联大新诗研究院院长,每学期都要给学生开讲座,叫做“两仪坊”。最近,于坚的第三部法语诗集《被暗示的玫瑰》由尚德兰翻译,在巴黎文字出版社出版。以前卫著称的法国南特子夜诗歌节也邀请于坚访问法国,他先后在巴黎、南特、奥尔良、蒙帕里埃、昂热、雷纳等地举行了8场个人朗诵会,他朗诵了《0档案》《便条集》等首发于《大家》杂志的作品。法国文学界评论,就是在曾经先锋派文学风云激荡的法国,于坚的诗也是独创的,《0档案》会令人想起卡夫卡的《城堡》。
与各路猜测、想象不同,其实“先锋诗人”于坚很喜欢“正常”的生活:每天5点左右起床,早餐后必定像作坊里的工人一样坐下来写作,一写就是一上午;下午,他阅读、写大楷、见朋友、步行;他的房间稍显凌乱,堆满书籍、纸张,墙上挂着颜真卿的拓片和各种各样云南古代匿名工匠们手工塑的泥菩萨、罗汉、陶俑,这是他多年的收藏。“他们都在抢青花,我收的是泥巴,很便宜。”他勤于临摹,如今一手颜体已极具风骨,“我必须保持与汉字的古典关系。手和笔墨纸张的关系,写汉字的人不会写毛笔字还了得!”他骨子里对中国文化仍保持着相当的敬意,与写出《0档案》的那个先锋诗人似乎不太合拍;穿过起居室,后面是一个小庭院,在屋外的林荫下杂草丛生,他经常坐在院中的小亭子里喝茶看书。问他为何不除草养花,他的回答相当精彩:“众生都要栖息嘛,什么草都可以长,哪样花都欢迎来。”
除了写作,于坚还经常行走,拍摄照片和纪录片,对世间万物保持着足够的警惕与悲悯,但他说。“我不从审美的角度看世界,我看到的是一个正常的、普通人看到的世界。我的写作是看见的、不是想当然的。”
于坚和《大家》深具渊源,《0档案》就发表于1994年的《大家》创刊号。于坚也担任过《大家》诗歌组稿人。一晃20年,于坚欣然接受了这次“对话”,我们得以窥见这位诗人现在的所思所想。
《大家》:1985年,你与诗人韩东、丁当等创办《他们》文学杂志,在当时影响很大,也可以说影响深远。你认为现在的中国诗歌和上世纪80年代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
于坚:诗很少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这个时代的主潮是:只要富起来,怎么干都行。我经常在文学家的聚会上听人们谈论自己的“爱车”,诗人冷眼旁观。这些穷人在这个时代真是疯了,还在写诗。因此,诗越来越高级,越来越纯粹,这意味着一种自觉的牺牲,宗教般的使命感。诗已经被时代的庸俗送上了祭坛。如果在80年代,诗还是一种与地方性知识、意识形态语言之间的对抗、解构,那么今日中国当代诗歌是世界性的、普遍的、对汉语本身如何写而不是写什么有实质性的贡献。我可以说,正是诗改变了“文革”以来的汉语面貌,诗令汉语再次成为生活世界的语言。小说以传奇获奖,诗守护着汉语的魅力。
《大家》:你开始写诗是在20岁,那时候你还在工厂当工人,你是怎么写起诗来的?可以谈谈那段经历对你今后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吗?
于坚:1970年,有一天在我父亲流放地、他住的破庙里,发现藏在稻草堆里面的一本内部读物,60年代印给高级干部阅读的古代诗选。谁藏在那里的?这是一件神秘的事,里面有王维、苏东坡、李白、杜甫、范成大等人的诗。我读完像被雷击般震撼,我开始在作业本上疯狂地写诗,想写出他们那样的诗。我记得我在从陆良县回昆明的大卡车的车厢里还在一首一首地构想着。回到昆明,我借到《唐诗三百首》,马上开始背诵,我全部背诵了这本书,之后我背诵平仄,看《诗韵新编》。如果说我为什么会写作,印象深刻的事还要早,我12岁时,“文革”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有一个中午,日头毒辣,大街上浓烟滚滚,红卫兵和群众都在烧纸,我亲眼看着人们将一个图书馆烧掉,图书馆在冒烟!那种触目惊心就像耶稣被绑在十字架的那一日。之后的一天下午,我跟着父亲躲在家里烧书,红卫兵就要来了。我记得我们用一个搪瓷脸盆烧,是别人送我父亲的结婚礼物,里面印着“囍”。满屋飞着黑纸,就像一个仪式。这是我生命里的另一次神秘事件。为什么要把这些美丽的文字烧掉,我记得里面有《新观察》,封面是一张齐白石的白胡子肖像,还有《收获》。这令我困惑而害怕。我决定写作,也许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写作令我恐惧而感到刺激,恐惧是一种动力,今日依然。
《大家》:今天的文学环境,我的感觉是真的和80年代没办法比。现在的孩子谁还写诗、读诗?都捧着手机发微信呢。你怎么看更年轻的一代诗人?80后、90后?他们关注的东西,肯定是不一样了。
于坚:80年代,世界的风吹进来,那时代诗人的知识谱系回归正常。
他们关注的不一样,但是未必全世界都是如此。在法国,地铁上少有人看手机,更没有人拿着手机什么都拍。我与青年诗人聊天,他们的知识谱系非常正常,传统、现代都具备。我们可以聊《诗经》、荷马和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格列柯、莫兰迪、朱耷、罗布·格里耶或者《秃头歌女》。我觉得今天中国的教育相当封闭,与富起来无关的知识无人问津,年轻一代受这种风气影响,阅读、知识的准备急功近利,越来越封闭了。经济走向全世界,但是文化在退回到封闭的地方性知识。我夏天在广州与韩国最有影响力的现代派诗人李晟复聊天,他说《诗经》是最高之诗。我的朋友知道章东磐是研究二次世界大战的专家,他最近告诉我,有人问马歇尔将军,对二次世界大战怎么看,他说,只有但丁可以比喻。我在法国的朗诵,每场都有很多听众,主办者也以为会有很多中国听众,我也很期待有中国听众,我是中国来的嘛,但太少了,太少!有一场来了两个老华侨,是60年前移民的。中国今天对诗的冷落,只与这个国家自己的文化水准有关,不是世界文化的普遍趋势。endprint
《大家》:你年轻的时候曾在云南各地漫游,这期间发生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吗?为什么漫游?
于坚:这是受先辈诗人的影响。李白说,大块假我以文章。在大地上漫游,于天地之间养浩然之气,目击道存,是中国思想的真谛。中国思想是在运动中思的。我在漫游中思。思是一条道路,不是在书斋里苦思冥想。大地保持着天真,这大地总是令我回到文明的开始之处。作者往往会迷失在图书馆的迷宫里,但大地很简单,立刻再次觉悟。有一次我在金沙江的峡谷里行走,大雨之后,另一人从对面走来,我向他问路,聊了两句,停了两三分钟,他继续走,一群巨石从山上滚下,如果他没有停下来,那些巨石就砸在他恰好走到的地点。我现在也在漫游,我去那里都是走的,我讨厌汽车,我最近在法国的卢瓦尔河畔走了一天,城堡、乌鸦和芦苇,原始的河岸,就像回到我少年时代的大地。
《大家》:1983年的时候你写下了《河流》这样的作品,这个阶段的诗歌写作是否就是基于漫游的经历?有人据此称你为“高原诗人”,你认为这个“标签”对你合适吗?
于坚:是的,80年代我写了许多高原之诗。我可以说是高原诗人,我的标签之一。如今人们已经很少这么写了,人们与大地的关系改变了,现代化使大地面目全非,许多高原失踪了、河流死了。人们不再信任大地,地久天长令人怀疑。多么可怕,当我在一个湖边蹲下来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它是否有毒。
《大家》:《尚义街6号》在取材上倾向于世俗化、日常性,描写具体的、琐屑的、平常的生活场景。这样的取材是不是有这样的意思,即这是对重大的、有意义的、整体事件的反抗和反叛?
于坚:尚义街6号是80年代中期云南大学中文系一群诗人作家自发的地下小沙龙。地址确实是昆明尚义街六号。一幢位于昆明老城南部的、1947年建造的法国式的两层临街楼房。这一条街及其周边是旧时代法国侨民和商人集中的地区,到处是梧桐树、百叶窗和褪色的黄色墙壁。在二楼,吴文光独自占了一间七八平米左右的小屋,窗子开朝西面,在那里可以看见梧桐树、落日,云南高原永远蔚蓝的天空以及另一幢法国式建筑的红色屋顶上的鸽子、猫和麻雀。我们之所以在吴文光家聚会,是因为当时这些朋友大都没有单独的房间,只有吴文光有。这里方便秘密地谈话,在那个时代,谈论诸如萨特、柏格森之类的名字都可能有人去告密。而在大学生宿舍里,告密被许多人看成是一种公民责任、进步向上的行为。小屋的光线不好,永远处于阴暗与朦胧之中,看不清事物的细节,只能把握一种整体的氛围,犹如一处教堂中的忏悔室。我记得我们有过无数的谈话,从存在主义到新小说派,从《癌病房》到《聂鲁达诗选》,从帕斯捷尔那克到福克纳,从《人·岁月·生活》到《城堡》《变形记》,从斯大林时代到中东形势,从法国电影到荒诞派戏剧,从肖邦的音乐到黑人的舞蹈……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关于中国政局,关于云南高原某几天的天气,关于女人、性交、生活方式,这个沙龙一周往往要聚会三四次,从黄昏持续到深夜。这个沙龙令我们这一群人在思想和知识上超越了同时代人,尚义街六号的谈话是激动人心的,富于切割性、解构性和滚动性。这些危险的谈话和聚会成了我们的精神寄托,我们的智慧得到交流,在文学观念上处于那时代的前卫。尚义街六号关于当代文学的讨论至少在一九八一年就开始对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泛意识形态、乌托邦神话、鄙视身体、日常生活(生活在别处)的普遍倾向进行了抨击,也具体到对北岛一代诗人的作品价值的怀疑。那是我生命最美丽的年代,在这里,我有一群非常优秀的朋友。我的诗在那时候很难发表,被视为非诗。那时候诗坛流行的是追求想象力的浪漫主义作品,我的诗表现了日常生活,这在中国那时的诗歌中相当罕见。尚义街六号的这些朋友坚定不移地肯定我的作品,给我极大的鼓励。
评论家说这首诗就是写了世俗生活,写了小人物。实际上,《尚义街6号》我受的是杜甫的《饮中八仙歌》的影响。“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实际上八仙都是李白的朋友,是普通人。我写《尚义街6号》,我的那些朋友也是。汉语本身就有神性的力量,把一个活着的人写到诗歌里面去,等于你要把他变成诗教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对这个人的升华。可以说,我就是把他们当成仙人在写。但是仙人不是必然要做仙人的事,仙人做的事是普通人的事。《尚义街6号》是把日常生活神圣化。依靠的是汉语本身的神性。人们以为神圣的东西就是要用所谓神性的语言来写。那是一种观念神性。我的写作不是观念神性。我的升华不是赋予这些人物神性的观念,而是通过对他们的命名,通过汉字本身的力量,让他们具有神性。比如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它只是描述了一个事实,它并没有说神仙在此。但是汪伦因此而不朽。把“汪伦”这两个字写到诗里面,本身就是不得了的事情。它依靠的是语言本身的力量。如果你写的这首诗是将要不朽的,那么这个人也跟着你的诗成为神仙。“子不语怪力乱神”说的是不语虚构的、胡编乱造、想象出来的神,而《论语》本身是具有神力的,来自语词的力量,来自“子曰”这种东西。
这个诗写在1985年,那个时代没有人这么写诗。“文革”的语言暴力使汉语丧失了它的幽默感、生活气息。《尚义街6号》对生活的调侃,自我讽刺、自我反讽、幽默……这种东西在朦胧诗里面是没有的,在朦胧诗以前的当代诗歌也没有。有一年我去天津,南开大学的学生把这个排成了一个诗剧,我很感动。后来我就想:这是为什么?我发现实际上它表达了一种典型的青春经验。可能那个时代过去了,但是这种青春经验是不会结束的。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尚义街6号》,虽然表现的形式不一样,《尚义街6号》有十多种版本,那些版本都是,比如说这一群把这首诗里的人名改成他们身边的朋友的名字,很好玩。诗就是要表达一种普遍经验,虽然它的具体场景是特定的时间中的,但是它传达的应该是一种普遍经验。《尚义街6号》可能正是因为表达了这种普遍经验,才会在发表三十多年后依然被人喜爱。endprint
读这首诗我认为读者是需要智慧的。当年这首诗出来的时候我同时代的诗人是不能理解的,他们认为这首诗没什么意思。比如说其中说到李勃有一本作协会员证,他常常躺在上边,告诉我们应当怎样怎样洗短裤等等,暗含着一种反讽。但是当时我看到评论就认为这种完全没有什么意思,就是一种大白话。那个时代人因为长期的恐惧。已普遍失去幽默感,读不出这首诗的弦外之音。
《大家》:应该说你一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探索者,你认为探索对于一个写作者意味着什么?
于坚:探索,并不是故意标新立异,经验是诗的出发点。探索只在如何说上。在说什么上,我是后退的,就是要回到被“文革”文化否定的中国古代的大道上去。杜甫说的“再使风俗淳”,就是这样。
《大家》:你被誉为“先锋诗人”,如何理解“先锋”一词?或者说,你对先锋精神及其意义是如何定义的?
于坚:先锋总是有针对性的。但是这不只是一个向前再向前的姿势。没有后面何来前面?如果先锋不知道后面为何,这种先锋只是历史虚无主义。知道后面,你才知道你要在什么上先锋。尼采是19世界以来最伟大的先锋派之一,他的“上帝已死”可谓惊世骇俗。但他是基于西方文明的经验,尼采的先锋不是朝向未来的空间扩展,标新立异,而是基于对西方千年历史的反思,他要回到后面,回到希腊,狄俄尼索斯是在后面,不是未来之神。就是弥勒佛这个未来神,他也是在后面就在场的。海德格尔也是如此,先锋只是真理在我们时代的新说法。
先锋,就是一次次重返大道。因为文明的积弊、雅驯、解释总是遮蔽着文明之明、之光,先锋就是要去蔽。使道重新在场。诗经说,“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孔子说,天何言哉!又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每个时代的先锋总是意识到说得太多了,意义纷繁、观念缔结、固执、自我嚣张,道晦暗不明,于是,再次通过写作,“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李白),重新彰显道的“于穆不已”。吾丧我,这是最根本的先锋。匿名于写作,就是写作上的先锋派。我认为。
《大家》: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口语化写作成为你这一时期创作的主要特色,《作品XX号》《事件》等都被认为是与“朦胧诗人”决裂的宣言书。你认同这种观点吗?
于坚:口语的问题,我已经说过很多。我1989年出版的我的第一本诗集《诗六十首》的前言就说,我的诗不是口语,是于坚语。
我读到朦胧诗是1979年。这之前,我已经读过很多书,包括诗经、唐诗,30年代的新诗、波德莱尔、惠特曼、普希金、莱蒙托夫、艾青……对诗我已经有我自己的判断标准。朦胧诗令我震撼的是,我终于在黑暗里遇见了同时代的作者,我不认为就我读过的诗来说,朦胧诗是不成熟的诗。它更像一种地方性知识,是时代而不是诗歌自身的产物。我的作品是与黑暗的对话,是与那些死者、那些不朽的语词之间的对话。我从未想过要与同时代的谁决裂。
《大家》:你曾经说过:“诗歌可以使你摆脱生命的无意义状态,如果你不想庸俗,不想生活在毫无意义的世界里,诗可以帮助你抵达另一个世界,它是与神的对话。”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诗歌的意义,近似宗教的意义?
于坚:我已经多次说过,诗接近于宗教,尤其在中国。文教、诗教就是某种宗教。对汉语这种起源于巫的语言来说,口语是交流工具,文字却是教堂。写作必须诚惶诚恐。海德格尔所谓,语言乃存在之家,用于汉语最恰当。
《大家》:云南老诗人邹昆凌经常说,当下,很多人写诗既缺少对诗歌内省性的充分认识,更多对诗歌所载之物缺乏认识。但这似乎是两个方面,换言之,诗歌或为艺术而艺术,或必须文以载道。中国的诗歌经常在“载道”方面不遗余力,可能却悄然偏离了诗歌的真实内涵……你怎么看这诗歌的两面,是内省的、艺术高于一切,还是必须“载道”?
于坚:必须载道。道在时间中。道在20世纪的解释中,被庸俗地解释为主题、意识形态、意思等等。道是“于穆不已”“天何言哉”。“道可道,非常道”。止于至善。生生之谓易。为艺术而艺术,如果离开对大道的守护,就成为标新立异的空间游戏,不能“生生”,也是死路。后现代艺术一味地玩空间扩展游戏,骨子里与通过技术对物的占有是一致的。今天,技术充斥世界,大地萎缩,道晦暗不显,生生越来越不易了。不善。
《大家》:世界太冰冷,诗人太柔软,你是否经常有绝望之感——诗歌和诗人备受重视甚至能改变时代的时代,真的不复存在了,但诗歌又岂能丢掉它的担当呢?你怎么看诗人、诗歌和一个时代的关系?
于坚:人类正在遭遇根基性的毁灭。我们时代的怀疑主义,是基于对“永恒”的怀疑、对“地久天长”的怀疑。抓住当下,曾经只是诗的细节需要,现在成了根基性的。只有当下,没有永恒,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对于我这种迷信“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的作者来说,绝望是必然的,哪里还有身后事呢,哪里还有读者呢?世界如此疯狂地发展,文明必将终结。年轻人已经读不懂我三十年前的诗了,我歌咏的那个滇池已经不存在了。从前,写《赤壁赋》的苏轼可没有我的这些问题啊,他迷信“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可是现在,他也被迫面临这一局面了。他的诗从大地、文明的证据变成语言中的神话。而宇宙飞船倒成了现实。没有明月飞仙,人类照样发展。死亡在我们时代就是存在,死亡没那么遥远了。苏轼、杜甫都知道他们是不朽的,死亡遥遥无期,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哪里还有风雨、鬼神?这就是文明的悲剧。悲剧就是正剧。我们也许真如福山(《历史的终结》一书的作者)所说的只是最后之人,大地上的最后之人。我与我自己的时代,恐怕也就是我行我素了吧。
《大家》:《纯棉的母亲》抒写的是既柔软又有质感的母爱,这里面有80年代中期把日常生活写进诗的成分,但似乎不再像从前那样冷静。这是不是年纪大了以后对世界的看法有所改变,才有了这样颇为柔软和温暖的诗?
于坚:不知道。我写诗是随物赋形。
《大家》:很多时候,某种温温吞吞的大环境,或者说,在那些被关起来的腐败官员治下的大环境中,我们仿佛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谎言和假象欺骗了……诗人,或者文学艺术家,是否该担负起某种使命,让我们对周围的环境,保持足够的警惕?endprint
于坚:文以载道,生生之谓易。诗是生生的。诗是止于至善的。我们时代充斥着太多的不善,这些不善都已经正常化了。对诗人的敏感性是巨大的考验。诗人就是看得见地狱的人,但丁就是。
《大家》:我们再说一说散文。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始写作散文的?你认为好的散文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于坚:我写散文和写诗同步,只是散文后来才逐步发表。我的写作试图回到古代文人的那种“写一切”,一切都是文。诗、散文、评论什么的,都是文。写作,就是以文明之。
散文,就是散点透视、归于混沌,“篇终接浑茫”。像中国山水画一样,还包括题字、图章。文字的画、文字的诗、思考、叙述、白描都在一篇之中。我现在的散文,还经常插入分行的诗,就像章回小说那样。
《大家》:你说散文因其边界的模糊性,因此保持着文体的试验性。你还说只有散文可以引领思想进入自由写作的王国。你在散文领域也做了很多探索。你认为散文和诗的写作,哪一个能给予你更大的自由?
于坚:自由的方向不一样。散文在空间上更为自由,诗的自由在于与词的时间深度的一次次对话。
《大家》:那么小说呢?你现在也写小说并且出手不凡,让我们写小说的主编陈鹏都击节叫好,艳羡之极,同时也倍感压力——诗人于坚都写小说啦,还让我们怎么活?哈哈。你怎么看待当下的中国小说写作?
于坚:当代中国小说我看得不多,因为不好看。就我看到的而言,好像中国当代小说还是喜欢讲传奇,或者模仿西方罗布·格里耶那些人,而缺乏门罗那样风格老派、自甘平庸、琐碎、喋喋不休着家常世界的作家。我深受托尔斯泰、契诃夫、纳博科夫、普鲁斯特、乔伊斯……这些人的影响,我也非常喜欢卡佛、约翰·契弗或者加拿大的门罗。最近我读了好多门罗的小说。他们的作品影响到我的诗。虽然小说备受时代尊崇,我注意到在主流文化中,诗人几乎已经完全退出。但与寂寞的中国当代诗歌抵达的深度比较,作家们给我的印象,基本上是地方性知识。中国小说理解的先锋性基本上是形式主义的,而在我,这是世界观。
《大家》:《暗盒笔记》中你总是关注那些即将消逝的世界,比如老挝琅勃拉邦古老的生活方式、三峡的老船工、小街边的炒货摊。是不是更古老的生活方式更吸引你?
于坚:我是唱挽歌的诗人。这是命运。
《大家》:你曾经说年轻一代的作者,只在形式上起点高,但在历史感和永恒的价值、上帝方面,要么没有,要么就非常轻。但很多人都说,中国人原本就没有宗教信仰。对这个说法你怎么看?
于坚:西方意义上的宗教是没有。但就宗教所要抵达的某种东西的方式,中国不缺。只是不命名为宗教,也不在教堂里搞而已。宗教说到底,是为世界建立一个世俗的、可以“生生不息”(永恒)的秩序。它的说法是这种秩序天堂已经具备,因此给人宗教是向上的印象。而其实,就是没有宗教,“仁者人也”(孔子),人也通过语言在经验中无所不在地、日日新地辨识着世上的善与恶,神灵与魔鬼。只是宗教更加观念化,将善与恶解释、规定得更加清楚、严密、坚固而已。没有宗教,现世就没有秩序,没有底线,就陷入混乱野蛮。复活总是大地上的事情,此时此地的事情,而不是什么千年禧。中国人的宗教其实就是语言之教。文明,就是以文明之。文明就是要履行宗教的使命,中国直接就是以文明之,文之、文教。文就是底线、秩序。文不是观念的固化,而是意义的随物赋形。所以文要讲中庸,中庸不是量化,而是基于经验的度,止于至善。至善也不是固化的,而要在各时代因地因时制宜。今日中国之世风日下,就是文明被遮蔽的结果。现在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的重要性,乃是基于“文革”的大教训,这个教训是必要的,否则一代代知识分子总是对文明持怀疑态度。文明被摧毁的局面,我们这个时代终于看到了。中国须臾不可抛弃文明。
《大家》:你也抱怨中国的传统思想对年轻一代毫无影响,但这似乎不能忽视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思想对年轻一代没有多少影响是不是也情有可原?
于坚:这是教育的问题。“文革”其实发展了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新文化。历史从我开始,以前只是白纸一张。唯我独尊,这种虚无主义通过教育深刻地影响到青年一代。“文革”新文化的特征,就是观念先行,这导致普遍的名不副实,观念是观念、行动是行动,只说不做。说一套做一套、阳奉阴违盛行。
但是所幸者,汉字没有像五四有些人希望的那样被废除,以拼音文字取代,而汉字就是中国最伟大的传统,根基性的传统。谢天谢地,汉字犹在,我还可以用这种字来写作,汉语似乎已经取代了大地成为我的信任之源。大块假我以文章,所幸者,还有千古文章。
传统文化其实无法不影响青年一代,因为它就是汉语本身。年轻一代还在用甲骨文上的那些汉字写作,复活只是时间问题。我担心的只是他们的现代性是骨子里的还是时髦?我觉得是时髦。
《大家》:这种“没有影响”,会否真的影响到他成为一个优秀的、第一流的诗人或小说家?可鲁迅先生不也一直拿传统开刀的吗?
于坚:是的,绝对影响!写作不是横空出世,写作基于经验。汉字就是历史。每一代的作者要与这个历史对话。读者也是识字的!你的语词如何呈现,读者是知道好歹的。除非你拒绝读者,那么这就是世界观的问题。在古代中国,非历史的写作毫无前途。20世纪非历史的写作成为主流。但是,非历史的写作也无法拒绝读者,人类为什么出现文明,而野兽没有?文是为读者而文,文的冲动就是要创造历史,这个根基无法摧毁,否则,非历史不如就此沉默,无文也就没有什么历史。鲁迅用甲骨文上的那些汉字向传统开刀,而今天在我看来,他正是汉语的伟大传统的继续。
《大家》:不管写诗、写散文还是写小说,你的语言都很朴素但又深具意蕴。为了达到这样的语言高度,你做了哪些方面的语言训练?
于坚:我深受古文的影响。老子说,大巧若拙嘛。司马迁说:不虚美,不隐恶。
我非常喜欢《左传》的语言。endprint
我背诵过字典。我厌恶某些词,自觉地不使用某些词。有些记者采访我,登出来意思是的,但不是我的话,我绝不会那么说。
我记得普鲁斯特的朋友说,普鲁斯特最厌恶的词是“拜拜”。对现在网络流行的某些词我也非凡厌恶,我喜欢创造词,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度,中正朴素。现在创造的新词大多数油滑轻浮。
似乎罗丹这么说过,用旧词就够了。
《大家》:什么语言——无论诗歌,还是小说——是最好的语言?
于坚:朴素。朴素,还是朴素。辞达而已矣。写得不好,因为说得太多,不相信微言大义。自我表白。
《大家》:你认为哪些作家,或者说什么样的作家,可以称得上好作家?你的好作家和好诗人的标准是什么?
于坚:古代的大师都是标准。诺贝尔获奖者倒不一定。作者死掉一百年也许可以说他的好坏。写作是一种语言史。纳博科夫说,是如何说的历史。我同意。
说的都是历史,但陈寅恪说得就比钱穆更庄重。钱钟书才过了五十年,已经有点不知所云了,太聪明。陈寅恪是外枯中膏。外枯中膏是语言的最高境界。
我记得塞林格说,好作品就是那种看了就想打电话给作者的那种。现在许多作品,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发表也可以,获奖也行。这是最糟糕的。平庸就是这种东西。
我怀疑如果一切都以钱为动力,如果已经持续了如此之上的时期,人们是否还知道好歹。
比如现在将鲁迅撤出教材,就可以看出人们已经不知好歹了。也许鲁迅说什么可以再讨论,但是他的如何说绝对是第一流的。他是因为写得好而伟大。
《大家》:有时候你语出惊人,给人留下先锋和前卫的印象,但有时候你又呼唤传统和回归,表现出传统的一面。应该把你归为哪一类,前卫还是传统?
于坚:我没有方向,随物赋形。文人而已,但不是“无足观”,这是我的努力。
《大家》:现在很多著名文人都写字,不约而同啊,说明大家骨子里还是认同书法这种极致的线条艺术,认同这种传统文化的根性之美。说说你练字的缘由吧,想过要卖字、办个展之类的吗?
于坚:我写字,就是保持我和汉字的肉体关系,通过不断地临摹去接近那些古老的呼吸、气韵、节奏,感悟道之运行。颜真卿不仅教我写字,也教我写作、何谓中正。
《大家》:你在国外参加过很多诗歌节和文学活动,国外的诗歌节和中国举办的诗歌节有什么不同?
于坚:国外的诗歌节重点在诗,而不是排场、交际、宣传。我最近在法国的8场个人朗诵,很简单,就是听我的原声念诗、听译文,全场闭着眼睛听,像音乐会一样。然后讨论,我念了许多诗。在中国,诗歌朗诵会,诗是次要的,没有几个人真的要听,大家是来玩。
《大家》:我们再回到诗的写作。你说写诗时很焦虑,那你觉得写诗是痛苦的还是快乐的?是写诗感到焦虑,还是写散文和写小说也同样焦虑?摄影呢,会不会带给你焦虑感?
于坚:焦虑就是复活。当你焦虑时,诗就要来了。
写作是一种劳动,与所有劳动一样,必须聚精会神,此时我是劳动者的快乐。我通常关着窗子写,有时候写到筋疲力尽。痛苦是我永远不知道那些穿越了时间的伟大的死者会怎么看我的写作,而我也无法信任我自己时代的那些溢美之词。在垃圾或者不朽之作间不断地怀疑,不断地写下一章,这令我很痛苦。就像农夫,播种是喜悦的,培土是喜悦的,但没有一个农夫知道秋天,我有时候看见他们在农闲的时候张望田野,那是一种隐秘的痛苦。
《大家》:近年来,先后有几位优秀的诗人以自杀的方式离开了我们,让人莫名悲怆。你怎么看待诗人的自戕?你自己,有过类似的念头吗?
于坚:我前面已经说过,根基性的存在已经动摇,不朽已经动摇。因此,死亡是可以随便接受的。诗人对此更为敏感。这个时代选择死亡很容易,因为无意义已经成为意义本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我的终极意义。吾丧我、齐物,这都是死亡的一个漂亮理由。但是,如果吾是宇宙之吾,我是身体之我的话,那么齐物的悲剧是,无物可齐。滇池那潭脏水你怎么齐?雾霾你怎么齐?无意义已经彻底地无意义。
《大家》:你被业界认为是中国诗人中最具备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实力的代表性人物。你自己怎么看这种说法?
于坚:其实业界也有更多的人说,这个家伙写的都是垃圾,而且自以为是。
我用汉字写作,而那个奖依据的是拼音,仅此一点,这个奖就无法信任。汉字都不在场了,这好比弗罗斯特说的“诗就是翻译中失去的部分”,他指的是拼音文字写的诗。汉语诗损失的不仅仅是诗的空间,损失的更有象形文字。
我不反对翻译这种必须的文化交流,这个世界如此险恶,各民族应当彼此知道彼此的意思。
但是,我不会因为被翻译而获得对我自己写作的自信。
《大家》:这些年,你在云南本土积极参与各种文学活动,对年轻一代也给予了相当支持,你仍然不是一个关在书斋的诗人和作家。怎么看云南的诗歌、新一代的诗人?
于坚:诗人必须互相支持。并不是因为他是年轻人,看见好的诗秘而不宣是道德问题。诗人没有年龄,只有好诗。云南年轻诗人写得好的很多,许多是我的朋友,我愿意尽我所能,让他们的作品抵达读者。
《大家》:说说你的工作习惯吧,每天都写?
于坚:是的。基本上是的。我有太多东西要写。我修改得很厉害,而修改的难度是修改得像是一挥而就。
《大家》:最近在读什么书?给我们推荐一部好书、一部好电影。
于坚:《苏轼全集》、《耳语者》。
我看过大多数费里尼的电影,我非常喜欢他。
《大家》:有什么“宏伟”计划吗?
于坚:没有。写就是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