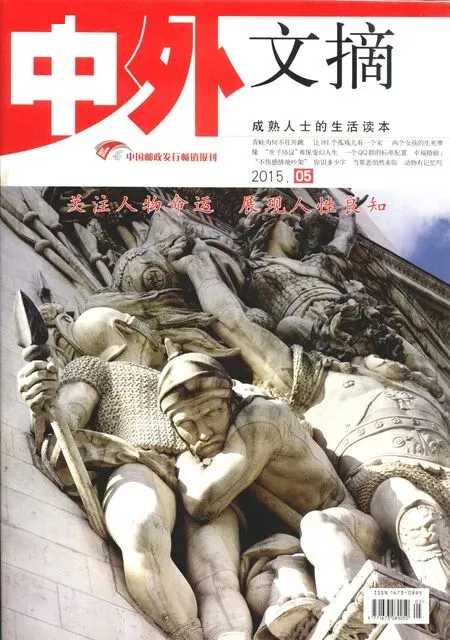东坡词中提到的女子
□ 陈传席
东坡词中提到的女子
□ 梅 茗
这些女子,若非留芳踪于东坡笔下,千载之后,谁人知道她们曾来过人间?如同万千世人,历史云烟中,何曾有过一星半点生命的屐痕。
我读东坡词,能遇到这些生气勃勃的生命,真是阅读中的意外惊喜。在我眼里,她们的芳名已不是书本上冰冷的汉字,而是一个个会歌会笑有悲有欢的美丽女子。能与她们如此结缘,我很珍惜。
忧喜相寻柳氏女
东坡词【满江红】
忧喜相寻,风雨过、一江春绿。巫峡梦、至今空有,乱山屏簇。何似伯鸾携德耀,箪瓢未足清欢足。渐粲然、光彩照阶庭,生兰玉。
幽梦里,传心曲。肠断处,凭他续。文君婿知否,笑君卑辱。君不见周南歌汉广,天教夫子休乔木。便相将、左手抱琴书,云间宿。
附董词:
画艇秋江,摇曳水、波平蘸绿。更隐映、蓼汀芦岸,雾笼烟簇。况有佳人新得意,相看彼此情无足。对酒光、每觑转星眸,勾腮玉。
阳台梦、奏新曲。欢意极,非成续。岂知他身外,是非荣辱。笑指匡庐山渐近,露沾滋润常花木。有鸳鸯、相与瑞云飞,琼林宿。
柳氏是董钺的继室,过门仅三天,夫家就大难临头,董钺被削职为民。正是新婚燕尔之际,转瞬,这甜蜜的新娘已从官太太沦为罪人之妻。天堂到地狱,不该这么近呀。人们常会感叹“人生如戏”,柳氏的遭际却比戏还像戏,只是,她非戏中人。眼下残酷的现实,她无从回避,她必须面对。
董钺久历官场,人到晚岁,早已不戚戚于人生进退,视官场变故为平常事,惟怕年轻的妻子看不开承受不了,不免心中暗暗忧虑。可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自己的担心纯属多余,这小娇妻同忧患如处富贵。董钺老怀,深感欣慰。若非此番剧变,怎知爱妻有这等风骨。正所谓“风雨过,一江春绿”。换个说法,就叫做“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东坡外集》说,董钺“晚娶少妻”,想来她年龄不大。能免除官场俗务,回到乡间,对董来说,虽是生活清苦,但有娇妻忧喜相陪,琴书相娱,二人倒是神仙眷侣了。董钺的日子过得比为官时还要雍容闲雅,看不够的佳人,享不尽的清欢。董钺为妻子填了一曲“满江红”。并教家僮唱会,娱己娱妻,其乐融融。
董钺回鄱阳途中,特意到黄州会一会朋友苏轼。苏轼看老董不仅没有为丢官消得人憔悴,反倒“丰暇自得”,很是好奇。董就让家僮唱了这首词,东坡为之感慨不已。嗟叹之余,意犹未尽,又次董词韵,也填了首“满江红”(忧喜相寻)。
词里盛赞这对和谐琴瑟。巫山神女的梦太邈然,那山崖上不过一堆乱石,所谓“神女生涯原是梦”。怎如人间好眷属夫唱妇随逍遥度日来得实在,如那梁鸿孟光相如文君。其时柳氏夫人已有身孕,故东坡词中有“渐粲然、光彩照阶庭,生兰玉”句。醒里梦里,两人都是心曲相通。以往的断肠事,都可揭过不提。这一切,皆因得此佳妻的缘故。《诗经》里的“周南·汉广”说,“南有乔木,不可休思。”老天垂顾董夫子,偏偏让他休于乔木之阴,让他求得人间好女。白居易“左手携妻子,右手抱琴书,终老于斯”之志,在董柳二人这里,已然实现了。
心安身安点酥娘
东坡词【定风波】
谁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处安处是吾乡。
东坡在《定风波》(谁羡人间琢玉郎)词序中说,“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世住京师。定国南迁归,余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为缀词云。”
王巩王定国因“乌台诗案”株连,被贬南荒五年,身心经历不少磨难,其中包括亡子之痛,他都挺了过来。他自己的修为固是主要原因,另外不可忽略的,则是身边有这个称心可意的美妙女子了。回到京师,朋友惊讶他“瘴烟窟里五年,面如红玉”。东坡词里的“琢玉郎”就是指他。
读词小序,可知这位宇文柔奴姑娘(寓娘也可能是她的名字),不只生得漂亮,还伶牙俐齿,能说会道,解语知心,因此很得主人王定国宠爱。她身处官宦读书人家,随侍于博学多闻的主人身边,耳熏目染,自是不同子庸脂俗粉。否则,她如何能讲出“此心安处便是吾乡”的话来。
要知道,这样的意思是白居易屡次在诗中表达过的。诸如,“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也许是王巩吟诵时,她听得多了,就默默会心了。
一个小小歌儿,竟有这般见识与心胸,难怪东坡要为之赞叹了。
“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这话真是说到东坡心坎上了。人处太平时,有此心不难。人经历过种种困厄后,悟出此心,才尤显珍贵。
王定国不因东坡连累自己而有丝毫怨意,于贬地对自己严格要求,不曾有半点松懈,回京后与东坡的友谊也是有增无减。宇文姑娘随戴罪主人同赴蛮荒之地,艰难困苦中事主人一如往日。
东坡自己屡遭贬谪,都能泰然处之,当真是四海皆可为家,天涯亦可安心了。东坡有诗句为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这首词,不只为好友王定国,为柔奴,亦是为东坡自己而写。
想来,这女子许亦是红拂朝云如是一流人物。
凤凰山下弹筝妇
东坡词【江城子】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蓉,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
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念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粉丝的疯狂,古人毫不逊于今人,有“看杀卫玠”和“掷果潘安”故事为证。苏氏兄弟少年时,文名轰动京城。也许苏轼就是那时的偶像明星吧,他戴的帽子被称为“子瞻帽”,时人竞相效仿,甚至影响到宫中伶人。彼时的苏子瞻三十五六岁,正是帅气与才气交相辉映之时。
这妇人看来是苏子瞻的粉丝。苏轼以诗文享誉天下,她或许不是诗词发烧友,却极可能是知音识律之人。她既然擅长弹筝,自然对那时盛行的“流行音乐”——按乐谱填词非常熟悉。这样,趁机会请苏轼为她写一首好歌,就是情理中事了。
最终她得偿所愿,得到苏轼词作一首。如此奇遇,她大概是追星族中最幸运的人了。
她当时三十余岁,痴迷一个男性诗人,作为一个普通平民的妻子,想来亦算勇气可嘉了。
以前读书印象,总以为宋代理学兴盛,宋人一定拘谨异常,特别在男女大防上,更是小心翼翼。实际上并非那样。二程同时代的很多人,比如苏轼,年龄上比二程小几岁,我感觉他们对二程那套,根本不屑一顾。还有个可能,当时二程学说尚未完全成熟,朝廷还未大力提倡,宣传普及还不广泛。
据宋人《闲评》记载,苏轼与友人游西湖,“至湖心,有小舟翩然至前,一妇人甚佳,见东坡,自叙‘少年景慕高名,以在室均无由得见。今已嫁为民妻,闻公游湖,不避罪而来。善弹筝,愿献一曲,辄求一小词,以为终身之荣,可乎?’东坡不能却,援笔而成,与之。”另一宋人《墨庄漫录》中说她“年且三十余,风韵娴雅,绰有态度。”
苏轼为弹筝妇人填的这首词带有轻谑的意味。“一朵芙蓉,开过尚盈盈。”芙蓉是指弹筝妇人,开过,是指她并不年轻,不是小姑娘了。这首词苏轼戏谑的是谁呢?就是词中的“双白鹭”。当时与东坡一起游湖的人中,有刘姓二兄弟,两人因在服中,身穿白衣,故东坡戏称他们是“双白鹭”。这俩家伙一见舟中美妇,哈喇子长流,及至那女子小舟缓缓远去,“竞目送之”。
曹丕说“高谈娱心,哀筝顺耳。”看来这妇人筝技真是不错,弹得很动人。苍茫暮霭中,她恍若湘水女神,飘然而去。载她的船影已渐渐消融于山影云烟里,铮琮妙曲余音却还缭绕在江面上。
“善戏谑兮,小为虐兮。”苏轼在这首词里,暗地里捣鬼,戏谑刘氏兄弟,明着却在赞美弹筝妇人。偏偏文字及意境又这般轻灵曼妙。这首词的韵非常轻巧,读的次数越多,越有哼唱得出的感觉,心情也随之轻盈欲舞。
逢场作戏杭州妓
东坡词【南歌子】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眨眉。却愁弥勒下生迟。不见老婆三五、少年时。
这女子的心态,我有些琢磨不透,却也因此对她更为好奇。
文豪、高僧、妓女,三者凑到一起,简直是传奇或武侠故事中才会出现的场景。
东坡曾称赞陶渊明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是这样行事痛快毫不做作的人呢。人说“东坡事事爽”,他一生对道教、佛教参悟甚深,但于世俗生活,却并不古怪离群。
记得叶嘉莹先生讲过,东坡是人而仙者,无论环境如何恶劣,他都能很快调整自己的心态并适应。他不仅是自己过得快乐,还能以这种快乐感染身边人。不像李白,是仙而人者,他是谪仙,是天上的神仙被贬谪到凡间,因此,他生活得非常痛苦。
东坡一生好开玩笑,有时还会捉弄人,但他并无恶意。民间有关他的传说很多,有他智赢别人的事,也有别人取笑他的事。也许正因为东坡的个性太丰富,所以才让人觉得他可亲可爱,不似那些表面上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德妄人。
这一次,东坡居然淘气到方外高僧头上去了。这位善本和尚(后被赐号大通禅师)比东坡年长一两岁,此时也并不老,大概五十五岁左右,“操律高洁,人非斋沐,不敢登堂。”
大和尚却没料到,太守东坡会挟带一个妓女登门造访,跟佛家弟子开这么大的玩笑,心中不乐,自然“愠形于色”。估摸那一众小和尚更加狼狈,多半同普救寺中乍见崔莺莺的僧弥差不多。
这女孩子也自教人同情。她当然知道佛门不是她呆的地儿,哪里还敢正视那庄严的禅师,仅偷偷瞄他一瞄。饶她浑身是艺,机变灵巧,在这尊崇的寺院却还放不开身手。
解铃还需系铃人,东坡成竹在胸,当即提笔填词一首,让她演唱。又借来和尚拍板与门槌,交与那女子打击伴奏。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这是佛家名问。东坡以佛家熟语入词,调侃和尚,自是非常贴切。
“逢场作戏”语,亦原出禅宗公案,本无贬义。至于“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眨眉。”就是现场抓拍了,僧妓两人神态活灵活现。你和尚双眉不展,莫不是愁那弥勒下生太迟,无缘看到个貌美如花的女子了。花易谢人易老,来得晚了,她就变为老婆婆了。
更别说色即是空。和尚大师啊,这眼前所见的并非什么小美女,而是一位龙钟老太太年轻时候的梦幻影子啊。
善本和尚不愧为明白人,不禁破颜而笑。
而她,这个并非全无心肝的妓女,估计心中有些郁闷。谁都知道,青春易逝。她捧着的这个青春饭碗,那是只璀璨晶莹,冰做的碗啊。
后人由此敷衍出一段公案,说她叫琴操,并因这首词感悟而出家为尼,惜无详实史料佐证。在我看来,她是不是琴操无所谓。也不见得出家就是圆满归宿,让阿婆前身——这个十五岁的少女出家,了却红尘事,何等残酷?难不成让她后来再演绎一回陈妙常的故事?三五少女也罢,白发阿婆也罢,其实两者都是人生必经之路,又有何惧哉?
(摘自《各界》总第209期)
大商人、大文人、大英雄、大流氓
□ 陈传席
大商人必无商人气,大文人必无文人气。大英雄或有流氓气,大流氓或有豪杰气。
老子云:“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白若辱,大方无隅。”苏轼云:“大勇若怯,大智若愚。”事之极者,必向其反,物之极者,必见其非。人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