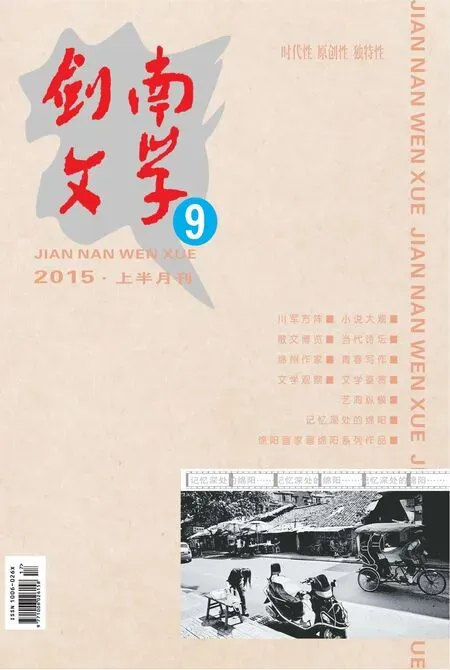瘫痪、救赎、幻灭、重生——《死者》主题解析
■ 王 莹
《死者》是詹姆斯·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的最后一篇,也可以说是整部小说的结尾和压轴之作。它蕴含了乔伊斯对爱尔兰的希望和深刻的情感。小说的主题既涵盖了整部小说集的主题“瘫痪”、“救赎”以及“幻灭”,同时,也包含了另一主题“重生”。死亡是为了重生,尽管爱尔兰社会麻痹、瘫痪、没有生机,但爱尔兰人民的传统美德依然存在,新的时代和新的思想正在爱尔兰年轻人中传播,因此,爱尔兰还有希望,还会重生。
《死者》讲述了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语言教授加布里埃尔携妻子参加自己的两位姑妈和表妹举行的舞会的一系列经历,聚会后他产生的情感冲动,被妻子回忆自己的初恋情人浇灭,从而引发许多的深思与遐想。作为整部小说集的组成部分,《死者》也包含了对爱尔兰社会“瘫痪”以及身处当中的人们想要觉醒,却深感无力,只能寻求“悔罪”,最终“幻灭”的描写,所不同的是,《死者》的结尾也给与了读者希望,同时也是作家本人对爱尔兰社会仍然存在的希望,即爱尔兰社会的重生的精神慰藉。
1、瘫痪与救赎
莫肯家族是一个没落的家族,自从哥哥帕特死了之后,朱莉姨妈和凯特姨妈就带着唯一的侄女玛丽·简搬到了厄舍岛上这幢阴暗凄惨的房子里来住。尽管她们生活简朴,但是他们仍会每年举办舞会,会吃最好的食物,喝最好的茶叶和啤酒。加布里埃尔的母亲是让姨妈们最尊敬的人物,她有着体面的婚姻,两个儿子也都非常优秀,即使已经死去,也受到整个家族的尊敬。她曾经反对过加布里埃尔的婚姻,嫌弃格雷塔的出身与家庭,然而当她长期卧病在床的时候,一直照顾她的却是格雷塔。母亲的冷酷无情,妻子的善良容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是没落的家族、冷漠的家庭,阴暗凄惨的房子以及那存在多年,年年如此的舞会都是爱尔兰社会“瘫痪”的缩影。人们身处其中,却毫无察觉,不想改变。
玛丽·简是加布里埃尔的表妹,她专门教授音乐,并且经常和自己的学生举办音乐会,似乎是一个很有音乐才华的年轻小姐,但在她的身上我们也看不到丝毫生气。她在舞会上演奏乐曲,实际上却没有人在听。她演奏的高难度乐曲,加布里埃尔丝毫听不出有优美的旋律。演奏结束,被报以了热烈的掌声,巴掌拍得最起劲的是曲子一开始就离开,钢琴声停下来才回来的四个年轻人。这似乎有些讽刺,音乐是加布里埃尔喜欢的东西,但表妹演奏的音乐却不能给他任何灵感与美感。而一首简单的爱尔兰民谣却唤起了妻子内心深藏的爱情故事。加布里埃尔似乎感到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麻木的,虚伪的,冷漠的。
加布里埃尔在整个故事中一直在企图“悔罪”与“救赎”。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有很高的文化修养的语言教授,他一直能感受到自己和周围一切的“瘫痪”,且试图冲破它。他给莉莉硬币,希望能给莉莉帮助和温暖。在被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艾弗斯小姐批评,叫他“西部英格兰人”的时候,他并没有激烈的反对。加布里埃尔的妻子格雷塔象征着爱尔兰民族文化,加布里埃尔对她的欣赏也是对爱尔兰民族文化的欣赏。他高傲而高高在上,但同时也有着热情与宽容。因此,他慢慢接受与包容了妻子的爱情与她所象征的最最淳朴的爱尔兰民族文化,看到了自己的缺点与不足。这也是一种“悔罪”与“救赎”。
2、幻灭与重生
《死者》的前半部分并没有对任何死者的描述,所有人沉醉在音乐、美食、美酒所营造的聚会的欢乐氛围当中。当加布里埃尔被这欢乐的气氛所感染,他只想与妻子单独相处。当旅馆的看门人离开房间以后,“他只觉得他们已经逃离了生活和责任,逃离了家庭和朋友,一起怀着奔放而灿烂的心跑开了,开始了新的冒险”。而此时此刻,格雷塔的内心却沉浸在对初恋情人的怀念与悲伤之中。这才引出了小说的第一个死者——米迦勒·富里,进而引出了朱莉姨妈,“不久,她,也将和帕里特·莫肯和他那匹马一样,成为鬼影”;“一个一个地,他们都将变成鬼影”。他的灵魂接近了众多死者栖身的居所。他感受得到他们那飘忽不定忽闪忽现的存在。他自身消融进一个难以捉摸的灰色世界:而这边实实在在的世界正在消解、消失,这些死者曾经一度生长居住在其中。
爱情贯穿小说与全书的内容,因为在这样一个人们思想麻痹,生活一成不变,社会了无生机的“瘫痪”的世界,唯有爱情和音乐还是美好的存在,是唤醒人们内心渴望与追求的源泉。格雷塔对米迦勒·富里的爱情,是由一首爱尔兰民歌引出的,米迦勒·富里为了见到格雷塔,不顾自己病重的身体,冒雨站在树下,浑身发抖,最终离开人世。正是这纯粹的、义无反顾的爱尔兰乡村少年的爱情震撼了加布里埃尔。他认识到了自己的狭隘,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爱情上。他勇敢地承认了自己政治和爱情上的狭隘,似乎在雪中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也得到了重生的机会。
小说最引人入胜的部分就是故事的结尾。窗外下起了大雪,那雪花无声无息的飘落在爱尔兰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优美、祥和。雪花飘落在所有死者和生者的身上,这雪花是生与死的联系,是旧世界与新世界的联系,是生机与希望的象征。整个故事可以说是加布里埃尔认识自我,逐渐与爱尔兰和解,得到重生的过程。
小结
詹姆斯·乔伊斯对爱尔兰的感情是复杂的,他一方面深深的体会到整个爱尔兰社会的麻痹与瘫痪,却无能为力;而另一方面对于爱尔兰人民的热情好客、质朴宽容有着深刻的认同,并在《死者》中借加布里埃尔的嘴表述出来。或许对于故土的这种复杂情感只有作者自己才能深刻体会,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我对都柏林的感情早已是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