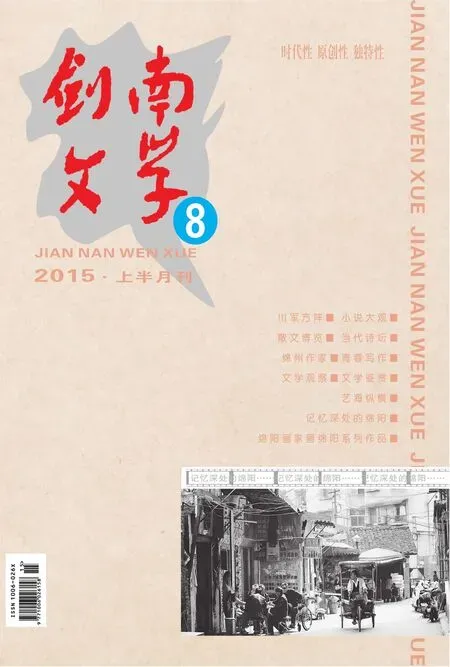立秋前的夏天(外三题)
■谢晓渔
阔别十年之后,暑假回来了。像是一只久困于空气稀薄的狭小空间里的狗,忽然被放置于一片夏花盛开的辽阔原野,惟一的意识就是撒欢儿地跑,极尽所能地呼吸。
然而,意识仿佛是一种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作用的东西,尽管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意识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事物。但诸多的客观事物却一再阻止我的意识。首要的便是这夏天,是“夏满芒夏暑相连”的大暑前后,是立秋前的夏天,是明晃晃的刺目阳光,是从早到晚的热气奔腾,是从晚到早的汗出如浆。
于是,我没日没夜的呆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像是一只久困于空气稀薄的狭小空间里的狗,又被放置于另一个有限的空间。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生长——成为我在这段光阴里的惟一目标。
然而,我能做到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并不能真正做到好好生长。源于自然的规律,因了主观上的愿意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这躯体的重量或许在日复一日的增加中也未可知,但我是不确定的,在这夏天里,不断被蒸发的身体水分,对水果之外其他食物的排斥,更有可能让身躯变得轻盈起来。但若论起细胞的增加,骨质的发育,早已不能称之为生长的阶段。更确切的说,只能是好好维护自己这——尚能抵御酷暑严冬——还寄存着某些意识的躯壳。
如此说来,在这样的阶段,还能好好生长的,便是自己的意识(或者,也叫精神、理想、信念这类高大上的东西?)。但我说过,我并未能真正做到好好生长。在立秋前最酷热的夏天里,我所做一切,均与意识或理想信念无关。傻呼呼的追剧,一部又一部,冷眼看陌生或熟悉的演员们演绎悲欢离合;像一个无可救药的洁癖症患者陷入偏执的状态,每天数次擦拭地板和家具,只为自己所在的空间表面上看起来能一尘不染;在狗狗醒来的时间里,怀着无限的耐心教他做一个会握手,会坐等的绅士……其余的时间,便在浑然的睡梦中。朋友圈晒出的各色美食美景,混合着我在这个夏天的无意识状态,纷乱的干扰着我的梦境。意识的生长和发育,停滞甚至退回到识字之初。
当我发觉自己的生长已经停滞甚至在倒退时,我竟然完全没有惊惶的感觉,我甚至于沉迷其中不能自拔。愈加的远离一切与意识相关的行为——笑或者哭,音乐或阅读,在遥不可及的未知的方向。我仿佛只愿意,这样的日子能天长地久,直到海枯石烂。
然而,我所期望的无意识状态并未能持续到海枯石烂。某个深夜,梦见夏天过去,立秋到来——原本蔚蓝的天空忽然布满诡异的云朵,大地上生长的花草树木,从荣到枯、由盛而衰只是瞬间的过程——竟至突然惊醒。翻开手机,骇然看到日历上,“大暑”之后的第十七天,是“立秋”,是另一个季节的开始。我蓦然惊觉,自己的无意识状态,个体生命的生长停滞,并不能阻止身外事物的发展。
“立秋”前的这个夏天,“立夏”到“大暑”之间,六个节气,像循序的生命,正在消失于看似可以轮回实则无可逆转的季节交替之中。
此刻,距离“立秋”还有十天时间。这意味着,这一年的夏天快要结束了。而我的生长,是要逆时而动,还是顺势而为?或者,就如当下这般,以开天辟地之初般的混沌鸿蒙,走过这个万物生长的立秋前的夏天?
万物生长
用了这标题,并不是觉得同名电影有多么好看,或者有多么难看——我向来不愿意简单的去评价一部电影,就像我从不简单的去评价一个人。我只是觉得,这样好的几个汉字组合在一起,不仅适合一部电影,描述人性、欲念的真实;也适合一首曲子,初春的花开、盛夏的蝉鸣、深秋的流水、寒冬的雪落……但凡大自然的一切美好声音,只要你用心,都可以在这首曲子里听到;更适合引领一篇文字,从中感受阳光的力量,看见生命的努力生长。
我想要的“好好生长”并未能在这个夏天实现。然而,生长这样的事,并非通过文字上的渲染或语言上的表达才能达成。有形的、无形的、热烈的、默然的——生长,如是种种,一刻也不曾停止。
就如同十天前移植的那一小芽水观音,已经生长出第三片小小的叶子。当她以我们通常描绘新芽所喜欢用的那种姿势出现在君子兰花盆中时,她很明确的凸显出一种生长的态势,冷冷的,却是不容忽视的那星绿意,让人徒生自卑和伤感。我恍然记得,七年前,那个花盆里曾经种过一株叶片肥大,主干粗壮的水观音,却因我的不善管理而消殒。之后,我移植了君子兰进去,并年年看着那花开花谢而欣喜,而落寞,却丝毫不曾记得这里曾经有过一株水观音。七年里,那水观音的根系在土里经过了什么样的磨砺和蜕变,最终拱出新绿,重新生长出来,在不思进取的我的观念和意识里,是无法理解和想象的。看到她的那一刻,我只是很强烈的想要给她一个完全的空间,属于她自己的,能尽情生长的更大的空间。为此,我将她移植到另一个空的花盆中,看着她嫩白细弱的根被土壤环抱的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她生长的呻吟,面向阳光,痛苦而欢乐。
是的,痛苦而欢乐,这就是生长的过程。
这个夏天刚刚开始的时候,家里前后阳台上多出了两个鸟巢。那两巢小鸟,从一粒卵,泾渭分明的蛋白与蛋黄,生命从最初的原始形态发展到更高级的状态,经历漫长的窒息和孵化,最终破壳而出的那一瞬间,生长的痛苦和欢乐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然而,这并不是结束。生命刚刚开始,生长也才进入初级阶段,每日对食物的期待,翅翼一天天丰满之后为拥有天空而进行的艰苦训练,张开翅膀向着天空飞去却因力量不足而坠入草丛……我甚至可以想象,于一只鸟而言,天空或者草丛,都隐藏着有形无形的危险,生长的状态,在这些危险的包围之下,随时都有可能终结。然而,鸟的翅翼在天空划过的弧线,翕动的翼尖掠过风的声音,一直都在,并且成为仰望天空的我们的眼里最美的风景。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生长之事,从春天开始,在这个夏天,成为触目可及的盛事——“绿槐高柳咽新蝉,薰风初入弦”、“绿树阴浓夏日长”、“满架蔷薇一院香”。哪怕是那样一株小小的兰,在室内的花架上,也要不依不饶的向着窗外的阳光,努力探出身子。她丝毫不会在意因追逐阳光而生长出的旁逸斜出的枝蔓会影响到她在人的社会里的现实价值。她要的,只是生长,努力生长。
行文至此,我忽然发现自己内心充满焦灼的感觉。在这个七月末的黄昏,我从自己几乎停止生长的身体里望过去,只那么一眼,便看见了那有如烈焰般燃烧却转瞬即逝的锋芒,原来,我的焦灼来自于此——万物生长的欣欣世界里,我一直停留在原地。
躲在这个浑浑噩噩的如炭如火的黄昏里,除了自己伸手捂住那翻来覆去被高温灼伤的疼痛外,我无法做到像一只鸟那般回身梳理被风雨侵蚀的羽翼。我更加难以确定,这样明亮的光里,这样蓬勃的生意里,我所听到的那些遥遥的噪杂而荒芜的声音里,有没有一个有意义的音符,是为着改变我的状态而来?
窗外,是昏黄的天光,晚蝉的鸣叫一如童年所听到那般悠长。而今,除了静静聆听这蝉鸣,除了蝉鸣声里那些残存的记忆片段偶尔光临现下的时光,我有且仅有一只狗。
在它生长的痛苦与欢乐里,我寂然走过。
奶奶的中秋
家族里,无论是物,还是人,最古老的存在,必然是奶奶。出生于民国十六年,经历了八十多年的时光磨砺。在她思维最清晰,脑细胞最发达的那些年月,我曾经跟随着她的记忆一起想象过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日子。在她的描述中,从黑暗到黎明,从贫乏到丰富,从困顿到自由,是一个渐次递增的过程。虽然艰难,却一直在希望中行进。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刚出生,属于蒙昧无知阶段。在后来的某个场合,听闻“几分功劳几分过”的言论后,回家跟奶奶炫耀这个道听途说、不明所以的观点,奶奶的眼神充满了怒气,她严厉的语气我至今难忘:“人,要懂得感恩,要懂得满足,要懂得敬仰……你少给我听信那些胡言乱语。”
在接近九十岁的奶奶心中,有一个景仰的偶像,她将之供奉于心灵的最纯粹处,不容许任何人、任何事去玷污。她那几乎经历一个世纪时光洗礼的眼眸,一直保持着一种坚定、一份平和,在眸子深处,看不到忧伤、看不到欲望。有的只是对于现实生活的热爱,对于未来生活的向往,对于生命延续的强烈渴望。
2014 年中秋,奶奶八十七岁生日。她开枝散叶的儿女、孙子、重孙们,团团的围坐着,相聚的欢乐沁润着时光的某一个片段。奶奶静坐一隅,与这个名叫擂鼓的小镇2008 年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相比,她的脸上,除了多几痕皱纹和几片深褐色的老年斑外,看不出明显的变化。她坐在父亲修建的三层小楼的玻璃房阳台上,看门前宽阔的大马路上车来车往,遥想着那些年月里那些物质匮乏却精神富有的人事,一刻比一刻无限趋近神化……
而她的身外,是恍若隔了几个世纪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变化首先来自于家族格局的改变。由奶奶主宰一个家庭发展的时代不知不觉被父亲取代。父亲忙碌而高大的身影穿梭于人群中的缝隙间,我和奶奶依偎在一起,她拉着我的手,长久的不愿松开,并自顾自的断断续续的说着属于她的辉煌年代。那些年月里,被信仰支撑的奶奶,呈现出迎难而上的激越状态,决绝的送唯一儿子去参军卫国,艰难的扶养六个姑姑成长,充满热情的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无所顾忌地与一切不符合公平正义和道德规范的现象作斗争……只是,当儿女一天天长大,一个个远离,当她的孤独成为一种常态,当时代进入到飞速发展的另一种状态时,她对于社会和家庭生活,甚至对于自我生活的掌控力,完全不知道消失在哪个时间节点。
而外部世界的表象的改变,犹如这个小镇。从儿童,少女,青年,中年……直到2008年,几十年的相濡以沫,奶奶熟悉这片土地犹如熟悉自己的身体发肤。闭着眼睛,便能从小镇的上街走到下街,邮电局的三岔路口,停着谁家的三轮车,走着谁家的小媳妇,她只用思绪便能合个八九不离十。正街上,老王家的油条香味,飘满了整条街。老张家烙的锅圈馍馍,在被炊烟熏染半个世纪的黑砖木楼里,浓浓的散发着新麦的清甜。一扇扇红漆斑驳的木板门取下后,是奶奶熟悉的那些乡亲的脸,一色的红润,洋溢着明亮灿烂的笑容,吐露出珠圆玉润的问候的乡音,仿佛小镇后山的秋天,明朗、清润、丰厚、斑斓……
以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去对比,2008 年那场灾难,对于高龄的奶奶来说,一定是绝望、悲伤与落寞同时来袭的艰难关隘。部分家族成员的离世——奶奶的一个女儿、两个女婿遇难,让她原本清润的双眸一夜之间变得枯涩。大概更让她难以适应的,是继彻底的颠覆后,小镇的彻底改造,视线可及的完全陌生、心理感应上的落寞虚无,来自于整个镇子面貌和格局的变化,来自于那些莫名多出来的街道、巷子,来自于通身气派的一排排小楼房,更来自于楼房之间被阻隔的那份乡里乡情……
但她一直以这样的姿势坐着,在三楼的玻璃房阳台上,恍如一尊雕塑。阳台三面环墙,一面正对着熙熙攘攘的马路。那条路,北边通向地震遗址——北川老县城,南边通往一个日趋繁华的所在——绵阳。她望着那条路,那些车,想象着坐在车中的那些身着华衣的俊男靓女,在废墟中震惊一番、唏嘘一番、感慨一番,然后回到南边的城市,在泛着暗红色光线的灯下,擎一杯微绿的酒,或打量对座那人的表情,猜度他的内心,是波涛汹涌,还是死水微澜?是让利于彼,还是固守防线?或思考着明天的邀约,凑局何为?猜度某人是某人的朋友,还是对头?甚或还有一类人,在刚刚经历那些生死相倚、福祸相携的场景后,转念便为下一次制造“天落馅饼”或接住“天落馅饼”而绞尽脑汁?
以上片段,其实缘于我的想象。当我看见阳台上奶奶如雕塑般的身影时,我视线所见,只是她微闭的双眼隐隐闪现的宁静的光。她的生命,关乎惊蛰谷雨、关乎农事作物、关乎一个叫盖头山的小村庄、关乎信仰、关乎人与人之间简单纯净的交流和沟通,关乎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一种生活到另一种生活的感恩,关乎她对普通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基本满足后的无欲无求。她的思维、她的生活、她的人生经历,使她远离了城市,不仅如此,甚至远离了这个时代,也远离了这个时代那些追逐利益、漠视规律的游戏和规则。
而我,却身在其中。
循着奶奶的视线望过去,看见我们的生活,一切运行都不在既定的轨道上,规则之外,黑暗的现实蓬勃生发……
奶奶回过头,咧开嘴,深刻皱纹的脸上溢满了孩子般纯真的笑容。“给你哥哥说下,下午送我去村上缴纳党费”。是那几十年如一日的执念和坚持,还是她完全游离于现实之外的灵魂和理想,让她满是皱纹的脸上,散发出如此宁静的辉光?
有且仅有一只狗
我转过头去看它的时候,它正闭着眼睛,四肢微蜷,肚皮朝天无所遮拦的睡着,偶尔,发出一两声轻微的梦吠。据说,但凡采取这种睡姿的狗狗,是因为对环境具有相当的安全感,对身边的人具有高度的信任感。想到此,内心竟然涌起一股强烈的自豪感和成就感。终究,在这盛夏逼仄而窒闷的环境中,一只狗是因为我的存在而感到安全。
喜欢狗,应该是很多年积淀的一种情结吧。小时候,家里养过一只狗,我记事起它便存在。脖子上一副锁链,锁链前端一个光滑的铜环,父亲在院里牵根粗铁丝,铜环套在铁丝上,由此限制了狗的活动范围。它凶猛冷峻而温柔热情。每当家庭成员以外的人出现时,呲牙咧嘴,山野的回声里全是它的狂吠。但对于它守护的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哪怕是对于一向不怎么待见狗的女主人,它也愿意在见到她的每一个时刻,像任何一只会讨好人类的狗狗那样,或摇头摆尾,或点头哈腰,或双脚匍匐,或跃起舌吻……它的凶猛冷峻或者温柔热情的因子,流淌在每一个动作和眼神里。只是那时,家里除了狗,还有猫、鸡鸭、牛羊等诸多小动物;除了注意诸多小动物,我还要上学;除了上学,我还要和村庄的男孩女孩们打架……无可避免的,我的注意力被分散。因此,我几乎忽略了它一天天的老去,忽略它渴望被亲近被抚摸的眼神,忽略了它一次次看着我远行时那伤感悠长的呜咽,忽略了我某天清晨醒来看见它停止呼吸时那僵硬的身姿……
之后的很长一段岁月里,在熙熙攘攘的环境中生长。从村庄到城市,从关注小动物到关注陌生或熟悉的人群……那么多的新奇事物,那么广阔的天与地,那么林立的高楼大厦……我很容易便忘记了那样的一只狗。当身边走过形形色色的宠物狗,忍不住去唤两声,或者想弯下腰抚摸时,它们漠然的眼神,头也不回的高冷姿态,会让我想念一只狗,一只视我为唯一依靠、待我温柔而热情的狗。
只是,我一直不确定自己是否准备好了,作为一只狗的唯一依靠,作为它生活的全部而存在。
直到春天的某个午后,在郊外的一条小河边,邂逅了一只狗。它安静的看着我,我蹲下来与它对视,它竟没有丝毫的陌生感,向着我走过里,伸出舌头舔我的手心。我起身沿河边行走,它摇着尾巴,静静地跟着,像养了多年的狗。
我无可避免的陷入了它的安静和温柔里,带着它回到城市的家。到宠物店检查,买沐浴液、牵绳、狗粮,期望自己从此会成为它的全部期待。然而,几天后的一个黄昏,它走丢了。与任何陌生人都可以亲近的本性,不懂得如其他宠物狗那般高傲和冷漠,在这个城市里,注定了它只能是欲望和陷阱的牺牲品。
至此,我开始强烈的想念一只狗,一只眼里只有我、完全属于我的狗。它只需用清澈的眼睛,柔软的爪子,还有无欲无求的忠实,在我喧嚣芜杂的生活中,淡定的消磨我的悲欢离合。
我终于下定决心,养一只狗。或者说,习惯于被身内身外若干因素影响心性的人,终于想要用自己的行为方式去影响一只狗的命运。当我在狗市一眼看到毛茸茸的它带着浅浅的笑意望着我时,毫不犹豫的带它回家。然而,仅有三天的欢乐和欣喜,之后,它开始咳嗽、发烧,去宠物医院检查,竟是最难治的犬瘟。打针,不见好转。输液,日渐萎靡……到后来,竟然不吃不喝。看着它毛色颓败,睡立难安的情状,我的悲伤像决堤的洪水,一次次席卷而来,又一次次被我强压至心底。生病半个月后的一个清晨 (它或许坚持了最后一个晚上)待起床后的我走到它的身边时,挣扎着想要抬起头舔舔我的手,却只能转转眼珠。我扶着它的头,看它安然的阖上了双眼。
时至今日,我仍然会想,我的决定,对于它的影响是如此的恶劣,以至于它失去了性命,终究只能在富乐山的某株柏树下,与它的玩具和用品一起,腐化成泥,能标识它曾经来过这世界的,只是它小小的墓前那两株移植的凌霄花,年复一年的生长。如果,它不曾遇见我,是否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结局?
狗没了。回到家里,再也寻不着一双清澈的眼睛,再也感觉不到自己被完全依赖的存在感。我像被时空遗弃的宇宙尘埃,无所皈依。某天,当我梦呓般的对田田说“我好想念一只狗”时,他淡淡说了句:“我家里正好有出生不久的小狗。”
它来了,到我的生活里。喂食、嬉戏、对视,一天天长大,一天天更深的喜欢我,只要在家,几乎寸步不离。我低头看它的时候,它正四肢伸展的趴在我的腿上,眯着眼睛,嘴巴微咂,咀嚼着生活的味道。
在这逼仄而窒闷的生活中,我有且仅有一只狗。而它,正一天天痛苦而欢乐的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