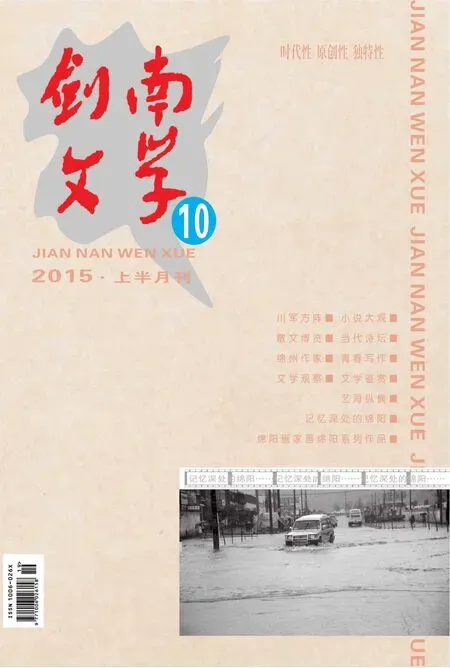古代志怪小说中狐类意象的文化内涵
■杨 婧
在志怪小说题材中,描写妖兽的作品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类。这里的妖兽,是指普通动物因各种原因获得了灵性或者神力,从而转化为妖兽。这类妖兽的原型涉及飞禽走兽无所不有,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集中于狐这种动物身上。志怪小说中以狐类为题材的作品连篇累牍,其内涵随社会意识形态而变化,折射了当时社会的人文背景,也对后世神怪作品具有母题上的借鉴意义。
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是志怪小说创作的高峰时期,经历了由萌芽至发展到纯熟的典型时段。狐类由于其灵异飘忽、鬼魅神秘的特点,以及从古至今加诸于它们身上的文化内涵,成为文人墨士笔下最常光顾的动物形象,作者在创作时会下意识地将其限定在固有的文化含义中,表现其约定俗成的象征意义。民间传说和文字记载为这一时段的志怪小说提供了素材,再通过作品的演绎使狐类意象丰富多彩、细腻生动。如《搜神记》、《戴柞甄异传》、《神仙传》、《拾遗记》、《异苑》、《博物志》、《幽明录》、《纪闻》、《广异记》、《集异记》等,文人们从多角度探析狐类,使其具有了独特的文化魅力。
1、不可抗拒的神性
先秦时期,狐类主要以守护神和祥瑞兽的形象出现,更是主宰国家命运、王朝更替的神兽,此阶段作品中突出表现的是它的 “神性”。当时人们坚信狐是能主宰万物、预测吉凶极具灵性的高贵动物。涂山氏族曾以九尾狐作为图腾,希望部落氏族兴旺,繁衍不息。《宋书》中云:“白狐,王者仁智则至。”①东汉赵晔在《吴越春秋》中云:“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证也。”②郭璞也在《山海经图赞》中说:“青丘奇兽,九尾之狐。有道祥见,出则衔书。作瑞于周,以漂灵符。”九尾白狐是象征着帝王权力和太平盛世的祥瑞之物。在此基础上经过诸子百家文化的浸润及演化,狐最终成为具有美善、仁礼、德行的有德之兽。正如《礼记·檀弓上》所说:“古之人有言日:狐死正丘首,仁也。”
体现在志怪小说作品中,便着重表现了狐高深莫测的神秘力量:它们不仅是人类命运的预言者,掌握人类荣辱兴衰,自身也具有神秘的超自然力量,是凌驾于人类之上并能操纵他们的命运的神祇,这也是此意象的早期源头。
2、复杂矛盾的妖性与兽性
魏晋时期,随着人类对自然界的开拓,狐类的神秘的面纱逐渐被揭开,人们的敬畏之感也随之减弱。同时,外来宗教的传入也推动了民间信仰的多元化发展。志怪小说中,狐类较多表现出了“妖性”和“兽性”。因魏晋时局动荡战乱不休,人民精神紧张脆弱,面对动物时的心理也带上了对抗性与斗争性。人类既未能完全摆脱对狐类的崇拜敬畏的心情,又对它们怀有敌视对立的心态,同时又期望它们具有人伦情感。这种复杂矛盾的感情使得此时期的狐类既保留了它们神秘莫测、凶残诡异的特性,又使它们在部分作品中具有了与人类相似的行为特点。
六朝志怪小说中狐类意象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新的表达方式,较多表现为敌视与对抗的情绪。 《搜神记》、《搜神后记》、《异苑》、《拾遗记》、《洛阳伽蓝记》、《博物志》、《幽明录》、《殷芸小说》等记载了大量的狐类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人类与它们多为敌视对立,狐类被普遍地“妖怪化”。《搜神记》中对于“妖怪”有如下定义:“妖怪者,盖精气之依物者也。气乱于中,物变于外。形神气质,表里之用也。”狐类这种变化多端、灵性长存的“妖性”和“兽性”形成了该意象在这一时期主流的表现方式。
《搜神记·山魅阿紫》中,狐妖“阿紫”化作美貌女子去引诱并加害男子,它幻化、蛊惑凡人,并且凶狠邪恶、伤人害命,为社会生产生活造成巨大威胁。故事中并未提及它自身的心理活动,是纯粹的妖类行为,没有人性特点。而人类如存妖心也可转化为妖,正如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云:“凡人之形,可以随心化。……其人而狐心也,则人可为狐。其狐而人心也,则狐亦可为人。”③茅盾在《中国神话研究初探》中探析原始初民具有的心理特点便是:相信万物有灵,世间万物皆具有七情六欲;且人兽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异苑》、《博物志》、《幽明录》等志怪小说中描写人类与狐类斗争的篇目比比皆是。这段时期的作品中狐妖均狡猾凶残且伤人害命,而人类则以坚定的意志和决心与之对抗斗争。
3、融入现世的人性
唐代作品中,狐类逐渐被赋予了的人类感情,具有了知恩图报、孺慕之情等美好人格。《酉阳杂俎》中狐类就有着多种幻化人形的方法,有了与人类并无二致的外貌与行为,且与人类关系密切。
牛肃所著《纪闻·郑洪之》中狐妖通过预卜吉凶的方法帮助正直的官员;《王贾》中的狐妖则化作王贾逝去多年的阿姨助其管理家务;《沈东美》中的狐妖化为沈东美家早已死亡的奴婢登门拜访;《靳守贞》则讲述了狐妖化为年轻美貌的女子与人类来往密切。这些故事中的狐类都有着十分人性化的一面,既有衣食住行的物质需求,又有喜怒哀乐的精神现象。文人们从多种角度塑造它们的社会性,使得狐类的形象日渐丰满,灵活多变。它们与普通人感情上相通,言行与社会伦理道德相符,与六朝志怪相比减少了妖异神秘性,增加了尘世人情味。它们既有孝悌感恩的人伦之念,又有争夺私人利益的世俗人性。
隋唐时期社会繁荣,佛道盛行,儒家伦理深入人心,封建律法完备。文人们将充沛深沉的情感渗入笔下,让狐类有了浓厚的社会道德伦理色彩,完全符合人们的精神需求。它们与人类产生的深厚感情,既体现了文人对至情至性高贵品质的赞扬和对真挚情感的向往,也表达了人民对孝悌仁义、知恩图报的善念的追求。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中唐戴孚所著的 《广异记》,其中《冯阶》中的狐妖追求与人类的真挚感情,是狐妖至情至性的淋漓体现。而《王黯》、《上官翼》、《王苞》、《刘甲》、《长孙无忌》、《杨伯成》等数十则故事中所记载的狐类形象有的知书达理、有的温柔贤惠、有的聪慧美丽、有的率真可爱……这些形象在展示自身无穷魅力的同时,也使狐类成为了一种社会性的神奇意象和具有独特涵义的文化符号,揉合了人们对世界与自我的认知,被最大程度的人格化。
至此,狐类由最初表现纯粹的宗教信仰转而走向体现儒家的道德伦理。儒家的入世主义使狐类有了多元化的表达方式,志怪小说作者的笔下既赋予了它们才情、美貌、智慧与品性,令它们在人类社会当中一展风采,完成了由“兽性”向“人性”的演变,也使其抽象为一个具有约定性的联想群。此种演化不仅是社会意识形态发展过程的艺术体现,也是后世文学作品中狐类形象塑造的基石。
中国的狐文化源远流长,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都有着丰富的话题。它们经历漫长曲折的演变,具有长久而旺盛的艺术生命力。与外国的“狐假虎威”、“狐狸和葡萄”、“狐狸与乌鸦”等寓言故事中狐类形象流于单一的符号化、概念化相比,志怪小说作品中的狐类形象显得更加丰富多彩、鲜活生动,带给人惊奇、恐惧、怜爱、敬重等多种艺术感受。作为具有深刻社会文化内涵的特殊审美意象,在中国文学史的舞台上散发出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