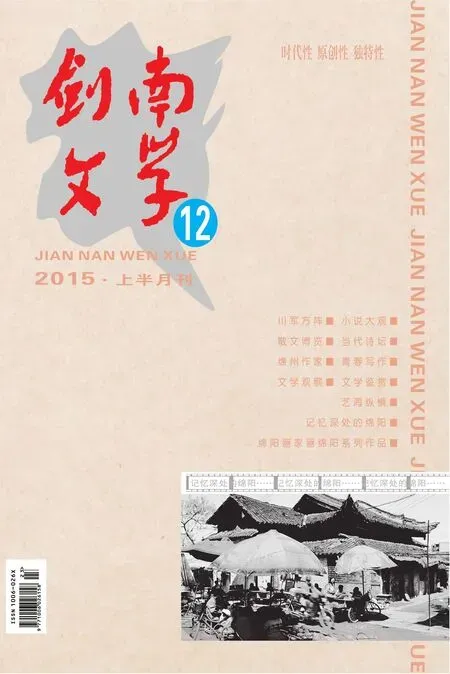俄罗斯人格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叙事
■郑文浩
俄罗斯人格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叙事
■郑文浩
俄罗斯人格的独特性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叙事的一个重要源泉,也是19世纪俄罗斯小说杰作的一个重要基础。人格特征具有环境生成性,俄罗斯的文化历史铸就了其人格类型的宗教本位与理性本位。正是这种本位性人格,构成了陀氏小说的叙事中心。
一、文化与人格
俄罗斯人格在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家们的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成为其叙事力量的一个重要源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典型。俄罗斯文学的特殊气质和历史深度,正是建立在这种特殊的俄罗斯人格的呈现之上。对陀氏小说美学的理解,有赖于我们对这种俄罗斯人格型构历史的深入辨析。
从人格的普泛层面而论,弗洛伊德很早就提出“性本能”对儿童人格发展的影响。后来的文化人类学家则更注重人格的环境生成性。正如专制文化形成了专制文化的人格供养物,如果这种人格环境不再,专制体系也会很快崩溃,但是人性的博弈却使得这种心性论式的变化无法发生,除非马克思所谓的新的生产力为民间社会赋权,从而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权力均势,社会人格就会形成新的人格构成方式,因为博弈的条件改变了。换句话说,人格的环境生成条件,实际上是马克思式的唯物论基础。
文化对人格的影响正是后者之特殊化的一个最大因素,如此而形成在不同文化场域中,男性、女性人格的不同认定。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文化模式》中论述这种区别,两个原始部落的文化与人格具有两种相异的代表性的取向:具有“日神型”文化的祖尼文化和具有“酒神型”文化的夸扣特尔文化。“日神”性文化强调理性的明智和节制,因而始终对激情对人的影响抱有警惕。如此文化结构的影响体现在人格上,就是该部落成员更多具有一种恬静、折衷的文化人格特征。“酒神”文化从人们对饮酒的体验而来,迷醉和狂喜被上升到一种近于本体论的高度,部落成员的人格也表现出这种特点。而且他进一步强调,每一种文化都可以归纳出一种与其文化相应的主导性人格类型。
(一)俄罗斯人格中的宗教本位
别尔嘉耶夫曾说俄罗斯人民的灵魂 “是由东正教教会培育成的,它具有这样纯粹的宗教形式”。俄国诗人丘特切夫也说“用理性无法理解俄罗斯,用公制俄尺无法衡量它:俄罗斯具有独特的气质——对它只能信仰”。要了解这种宗教本位就必须回溯到俄罗斯文化奠基的源头。10世纪末,俄罗斯文化的发源地基辅罗斯,在其与拜占庭的关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罗斯接受基督教(具体为东正教)为国教。它原本信奉的是农耕文化的多神教,此后,罗斯经历了一个数百年的基督教化的过程。而在拜占庭帝国在1453年没落后,原来笼罩于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世界中心的灵光,转移到了莫斯科上空。莫斯科的君主们开始以罗马和拜占庭的继承者自居,称 “现在,莫斯科是真正的基督之都,第三个罗马,也是最后一个罗马”,而莫斯科的君主则是“普天之下所有基督徒的沙皇”。在漫长的历史中,俄罗斯的宗教性渗透到俄罗斯人的心智深处,这并非是说,俄罗斯人严谨于宗教教义和对宗教仪礼的恪守,而是表现在他们整个生活态度中的超越性,超验世界的内心化,面向超然世界来建立人世生存的位置,表现在俄罗斯人普遍的对灵魂、上帝、永恒的生命等宗教及哲学问题所倾注的内心体验。在其《卡拉玛佐夫兄弟》中老卡拉玛佐夫就说过:“整个俄罗斯人的气质在这里显现。”这个气质就是所谓的神圣性的内心体验,因此,可以说“宗教性、东正教及与之相关的对绝对真理的追寻是俄罗斯民族最深层的特点”。
这种宗教性人格也在俄罗斯知识分子身上体现为一种“罪感文化”,他们在面对自己的精神和心灵时往往特别有一种反思的深度和尖锐性,一种历史和现实命运的承担感。而且在那些贵族知识分子当中,也不乏能超脱自身的个人处境,为那些社会最底层的农奴的命运呼喊的人,也能看出这种“罪感文化”的真诚性。
(二)俄罗斯人格中的理性本位
俄罗斯文化中的价值理性的位置也极为突出。这种价值理性有时表现出一种反东正教或限制东正教的面目,但是,宗教性所铸就的某种思维原型已植根于俄罗斯思想中,那就是对超越性价值的关注,在表面上的反对龃龉之下,深层的传承更须重视。
俄罗斯的价值理性的觉醒仍然有赖于西方精神的火炬。17世纪前半期,启蒙主义最初的思想潮流已在英国兴起,到18世纪初,这股潮流已发展为席卷西欧的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们批判宗教的黑暗,宣扬无神论,争取政治自由和公民平等,希望建立以“天赋人权”为基础的“理性王国”,而强调知识的传播,某种程度上以科学取代神学的位置。俄罗斯思想即以此从上帝手中取回的理性自决为前提,发出他们对国家、制度、教育、道德的启蒙呼声,强调社会契约,强调道德、教育对宗教的超脱性。拉吉舍夫(1749-1802)就代表了俄罗斯的这种理性人格耀眼的一面,他超越时代,对专制制度做出了“最违反人类天性的制度”的定义,并且指出,如果君主利用手中的权力反对人民,人民就完全有权把他当做罪犯来审判,因而发出“将沙皇置于死地的暴风雨”的呼声。拉吉舍夫后被叶卡捷琳娜二世流放于西伯利亚,他无疑是俄罗斯人格中以启蒙的价值理性为思想武器的一个醒目代表。
这种价值理性在19世纪初的俄罗斯,体现为当时已遍布欧美的自由主义改革浪潮。自由主义与人权宣言、独立宣言、人权法案等历史文件所宣布的原则联系在一起,划定政府的边界,强调一切价值的终极涵义在于满足人的个性。自由主义可以说是西方文明世俗形式的最高体现。把这种价值理性深深烙印进俄罗斯的民族记忆的,无疑是以贵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十二月党人。十二月党人的的起义确实受限于所谓的 “历史的局限”,社会条件并未做好准备,但他们作为俄国自由主义理性的先驱,以他们那种纯粹的理想主义人格和对历史责任的担负,在俄罗斯的人格谱系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叙事与俄罗斯人格典型
俄罗斯人格的这种宗教本位和理性本位,并不能以启蒙作为分界线。从思维原型来讲,自由主义难道不是一种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新的神学?在他的《白痴》和《罪与罚》中,我们恰好看到两种人格的极端体现。《白痴》中的主人公梅什金作为一个理想形象,本身就是基督精神的再现。梅什金认为上帝和基督都是“俄国”的,只有俄国的思想和俄国的宗教才能拯救世界,“也许唯有俄罗斯思想、俄罗斯的上帝和基督才能使全人类的面目一新,起死回生。”《白痴》作为一个文学作品,无疑以最强烈的方式体现出宗教性人格本位在陀氏小说叙事中的作用和位置。《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科利尼科夫则是不信上帝的,除了在小说最后隐约的暗示,但已经与小说主体无关了。拉斯科利尼科夫提出人类当中少数一类“非凡”的“天才”有破坏和违法的权利,为了实现他们的思想,不惜跨过尸体和流血,而他们通常会被处决或绞死,而这也是公平的。这是一种历史向前运行的法则。《罪与罚》的主人公人格无疑是理性本位的,体现的是一种启蒙后的知识分子人格,对历史的理解已经完全远离基督教的末世论审判,而将意志提升至近乎本体的位置,也就是尼采所谓“权力意志”。而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则是两种人格本位的正面碰撞:“启蒙革命以后,传统的 ‘宗教大法官’何以还有法权审判 ‘罪犯’? ”。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